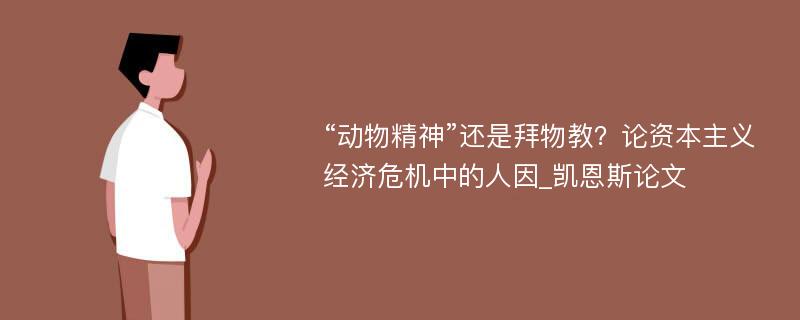
“动物精神”还是拜物教?——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人的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物教论文,经济危机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中人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的这场危机迫使西方国家对时下广受欢迎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进行深入反思,并促使人们将目光重新投向马克思经济学,从而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热潮。① 在人类社会中,“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②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会产生“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③而“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④不仅“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⑤而且“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⑥因为生产资料不仅表现一定的生产关系,而且“只有当它独立化,作为独立的力量来与劳动相对立的时候,才成为资本”。⑦由此可见,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⑧而且还是探究与把握经济学中“人”的因素的必要前提。 然而,在这里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学中的“人”究竟具有怎样的规定性?对此,经济学界并未对之形成一个明确而又为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答案”。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人”本身的复杂性,如人类自身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分工合作等复杂多变的心理模式与相互交织的社会行为使得经济学中的“人”并非可以由“自利”、“理性”等简单的抽象概念就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刻画;另一方面,这与身处不同国度的人们的世界观差异、意识形态差异以及阶级利益差异关系甚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往往对隐藏于资本背后的剥削关系讳莫如深,从而力图以“边际回报”、“一般均衡”、“三位一体公式”等概念及理论来掩盖藏匿于资本背后的生产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辩证的眼光分析问题。总之,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学中的“人”的定义与分析上相去甚远。 同时还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学中的“人”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如何得以体现?具体到解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诱因方面,“动物精神”一说风靡一时,并主张从信心、腐败或者贪婪等方面来解释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然而,由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⑨要分析“人”在经济危机中的根本性影响,就必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分析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人”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否则就无法识别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人格化”的“人”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二、经济学中“人”的不同界定 如何理解“经济人”假设,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区别。⑩ (一)理性的“经济人”还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马克思不仅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而且将其研究中所涉及的“人”定义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12)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认为,“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13)资本家作为资本这一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不仅在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过程中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且“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能受到尊敬与认可,才是统治者。(14)资本主义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身处这一阶段的资本家也必然承载着以追求剩余价值的形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特殊职能。从这一角度来说,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不仅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而且还是“不能让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5)因为“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16) 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不仅包含资本的人格化亦即资本家(如产业资本的人格化即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即为土地所有者),还同时包括雇佣劳动的人格化亦即雇佣工人。“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17)总之,“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18)并且随着“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19) 在西方经济学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斯密对“经济人”的规定之错误不在于他把“经济人”说成是具有利己心的并以此把利己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而在于斯密从人的本性引出“经济人”假设表现了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20)特别地,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是按经济理论行事的趋利避害的理性人,从而功利主义成为了它的分析基础;同时也正是这一功利主义思想才为随后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开启了方便之门,进而使得“经济人”的外延逐渐转向心理规律与行为选择层面。更具代表性地,西尼尔把“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概括为“财富最大化”,亦即“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21) 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假设“经济人”具备“完全理性”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不仅要求人们具有超级计算机般的信息处理能力,而且还意味着经济活动中的个人还能获取完全信息,甚至还可以摆脱不确定性的干扰,进而使得由此建立起来的相关理论均难以准确有效地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在主张用“有限的理性”代替“完全理性”的西蒙看来,“经济学家一般用理性一词表示靠抉择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而不是表示抉择过程的属性”。(22)此外,马歇尔把功利主义所提出的“快乐”和“痛苦”换成“满足”和“牺牲”,认为正是这两者促使人们从事各项经济活动,从而回避了对“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中所涉及的“人”进行具体界定的问题,同时也忽视了由情欲而引发的人的需要或者说“满足”是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变动态势这一事实。(23)可见,西方经济学对“人”的界定不仅离开了规律性的研究而进入了日常经济的运行过程,而且还是在刻意回避阶级关系而又罔顾历史发展过程的肆意修正中延续着的。 事实上,“理性经济人”假设一直以来颇受质疑甚至被尖锐批判。譬如,哈耶克在批评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中的边沁主义者时对他们的经济人动机和理性都做了否定。(24)此外,“理性经济人”还受社会经济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制约,否则只能算是“理性的白痴”。(25)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26)此外,博弈论通过对人们经济行为的模拟实验也表明“理性”并不能完满地解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甚至是一些简单的行为,例如,收益支付差距的扩大往往会促使人们拒绝提议者一个大于零的分配额。(27)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如私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在交换中所面临的“惊险的跳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综上可知,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已从马克思的揭示客观规律性的层面下降到描绘经济运行表面现象的层面。 (二)抽象的人还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的人 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8)所以要对经济学中的“人”进行界定就必然要回归到历史长河中去把握。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9) 马克思并不是如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仅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来论述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还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层面来论证。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对“人”的影响时谈到,大工业“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30)因此,劳动变换是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必然要求每一个个体获得更多的自由与发展。 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脚注(308)中提到一个法国工人的回忆录:“我从没有想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竟能够干各种职业。我原来确信,除了印刷业外,我什么也干不了……可是,一旦处在这个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家世界中,……我也就和别人一样地干了。……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软体动物而更像一个人了。”(31)故而,尽管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被动性——失业的普遍存在迫使劳动者被动地另谋他业,但这还是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当然,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其前提。“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必将促使社会化的人或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届时社会发展的目标则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33) 在西方经济学中,尽管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已经捕获到作为资产阶级的“人”的利己特征,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则早已偏离或者模糊了斯密的最初定义。斯密之后的其他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曲解了斯密的“经济人”只是对资产者这种特殊人性的概括。(34)有的将目光锁定在马克思所说的“实际生产当事人”亦即马歇尔所定义的“实际存在的人”这一狭隘、片面而又静止的视域中,有的则完全偏离了由现实生产关系规定的人而局限于抽象的一般人。总之,西方经济学(尤其源自于庸俗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仅倾向于从抽象层面出发,而且刻意回避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由此使得“经济人”成为一个孤立、同质、静止而又缺乏社会性的抽象物。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马歇尔在阐述“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现实严重偏离这一问题时指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血肉之躯的人”,(35)亦即“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36)更具代表性的当属凯恩斯。凯恩斯在探讨“群众心理”与经济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认为,此时支配市场的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的浪潮“是盲目的,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应该出现的,因为,这时并不存在用理性进行考虑的坚实基础”。(3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从历史发展观的视角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无视生产本身的目的性以及将个人福利同生产这个目的相对立的观点,认为:“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38)可见,西方经济学中所涉及的“经济人”仅仅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完全忽视了他存在的历史条件;(39)而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则强调由现实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规定。 (三)“动物性”的人还是主观能动性的人 人与动物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亦即人是具有思想、精神、意识和意志的动物。然而,人的意识并不单纯是被动地受社会存在影响的,而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经济活动均有着显著反向作用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社会状况以及意识三者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幽灵’、‘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40) 与此相反的是,在西方经济学中,“主观能动性”及其表现的主要方式则被“偏好冲击”、“冒险精神”、投机甚至是“动物精神”等概念取代。比如,刘易斯强调“冒险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增长并不要求人人都冒险,但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是革新者”。(41)当前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往往倾向于在效用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个人偏好(preference)的所谓的“理性”特征或个体的选择(choice)方式进行诸多方面的设定而构造出相应的效用函数,由此进一步推导出需求函数来构筑其经济框架,(42)并且还倾向于研究“偏好冲击(preference shock)”(43)、“偏好冲击与消费”、“偏好冲击与失业”等(44)话题。 自从凯恩斯提出“动物精神”这一概念后,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之展开了研究。在经济模型的拓展和运用方面,库别克和夏普运用代际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强调了动物精神在股票市场均衡中的重要性;(45)此外,彼得和麦克费将动物精神视为外生随机变量加入理性预期模型(rational expectation model)进行分析,(46)也有学者通过引入适应水平理论模型(adaption level-theoretic model)来阐述动物精神,(47)还有学者基于有限预期理论对外汇市场中的动物精神构建相应模型进行分析,(48)更有学者将动物精神加入基于角色的环境模型当中分析相关经济现象与环境政策。(48)在经济周期方面,已有研究一般认为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行为人的“动物精神”密切相关,(50)某些学者还研究了动物精神影响与统治下自由进入与商业周期间的关系。(51)此外,当前研究还讨论了动物精神与投资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52)分析了动物精神与创新的组成部分,(51)探讨了信念对股票价格的影响,(54)同时异质信念泡沫(heterogeneous-belief bubbles)问题也颇受西方经济研究者的青睐。(55)当然,“动物精神”这一概念的再次流行还驱使不少国内学者从这一视角来探讨相关的经济问题。(56) 就过去不久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而言,西方经济理论中所构造出的以“理性人”为基础的经济模型均未预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到来,然而这却丝毫没有冲淡西方学者所表现出来的“事后诸葛亮”的热情。除了从结构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行为金融学视角对股市所呈现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现象进行解释外,(57)希勒与阿克洛夫在其合著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一书中,主张从“动物精神”的视角来解释人们经济行为的突变性。(58) 在《动物精神》一书中,希勒和阿克洛夫分别对信心(confidence)、公平(fairness)、腐败与反社会行为(corrupt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故事(stories)五种动物精神对经济决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主要根源于信用恐慌(credit crunch)、诱惑(temptation)与不满(resentment)的变动以及不断变化的故事(changing stories)等变化的思维模式(changing thought patterns)。 事实上,马克思早已谈到人的思想、精神、意识等主观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具体关系,并由此论述了人类意识的动物性特征(畜群意识)。人类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与物质活动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的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59)“‘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60)但是,人类的意识除了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之外,马克思还看到人们还会“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61)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论及了被当前西方经济学大力宣扬的信用、投机、冒险等行为。譬如马克思在讨论资本过剩时就已指出:“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62)同时,马克思还非常重视信用对资本家经济行为的重要影响,认为“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63) 三、“动物精神”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吗? 以乐观和悲观这两种非理性预期循环交替为基础的商业周期模型在资本主义早期便已有之,希法亭在这方面就有代表性的著述并将非理性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缺陷,(64)随后其思想又先后为马歇尔及凯恩斯承袭。类似地,希勒和阿克洛夫从凯恩斯那里承袭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关于“动物精神”的观点。 (一)凯恩斯的“动物精神”理论及其本质 凯恩斯主张难以捉摸的经济前景使得人类的投资行为只能靠“动物精神”亦即自然本能的驱动来解释,并认为除了投机因素外人类本性的特点也会造成经济的不稳定性。因为“我们积极行动的很大一部分系来源于自发的乐观情绪,而不取决于对前景的数学期望值,……我们的大多数决策很可能起源于动物的本能——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后而得到的加权平均数所导致的后果”。(65)由此出发,凯恩斯断言人类的这种动物本能将影响到经济的兴衰:“如果动物的本能有所减弱而自发的乐观精神又萎靡不振,以至使我们只能以数学期望值作为从事经营的根据时,那末,企业便会萎缩和衰亡”。(66)并且,凯恩斯甚至更为激进地认为“在估计投资前景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决定自发活动的那些主要人物的胆略、兴奋程度甚至消化是否良好和对气候的反应”。(67) 与希勒等人所谓的“动物精神”相比,凯恩斯的这一理论更重视信心与信用等因素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他对经济长期预期状态的论述和解释在本质上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而并非是规律性的认识。凯恩斯认为:“信心和信用状态二者中的任何一个的低靡不振便足以导致股票价格的崩溃,从而给资本边际效率带来灾难性的后果。”(68)由此可知,在凯恩斯的世界里,“动物精神”充其量只能算是“信心状态”、“信用”甚至是“主要人物的胆略、兴奋程度”以及“消化是否良好”等诸多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中的一个而已,而远未上升到希勒和阿克洛夫所宣扬的重要程度。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凯恩斯的“动物精神”理论与马克思从规律性层面去探析各类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形成强烈反差。 (二)“动物精神”理论难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出科学的解释 “动物精神”究竟蕴意何指,这本身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譬如,有人将之视为人的非理性行动,(69)有人将动物精神等同于早期的太阳黑子(sunspots)假说,(70)也有人认为“自我实现预期”与太阳黑子冲击均是动物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71)更有人将“动物精神”视为乐观与悲观的情绪波动变化。(72)由此可见,希勒和阿克洛夫没有充分的证据自信地断言人们是受非理性动物精神(irrational animal spirits)驱使而导致市场波动的。(73)正是出于上述多方面的原因,斯瓦兹指出,希勒和阿克洛夫的这一合著存在一系列的缺陷,这突出表现在未对“动物精神”的组成部分进行解构,并且未能对认知因素(cognitive factors)、情感因素(emotional factors)、文化因素(cultural factors)以及内心因素(visceral factors)等方面进行有效区分上,进而斯瓦兹几乎针对该书的每一章均提出了相关的质疑与批判。(74)此外,希勒和阿克洛夫对“动物精神”所作做的定义亦乏善可陈。譬如,他们并未将贪婪(greed)与恐惧(fear)纳入到动物精神的范畴中进行分析。(75)总之,采用“动物精神”这么一个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均不确定的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无疑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其实,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积累限制的根源,并不在于银行家和商人心情的波动或信用政策的限制,而都在生产领域。(76)特别地,马克思十分重视资本家的贪婪——这充分体现在他们对剩余价值的拼命追逐上,并且他对资本家这种贪婪的分析是建立在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马克思证明了资本主义处在永久性的危机之中: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恰恰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久性矛盾的驱使下,不断努力避开危机的结果。(77)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贪婪正是人的意识上的反映,而资本家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敲骨吸髓的贪婪剥削正是致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重要诱因。由此可见,马克思所强调的,似乎正是西方经济学家所忽视、遗忘甚至是刻意回避的。 四、拜物教与资本家的贪婪本性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代表人物,斯密和李嘉图不仅“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78)而且均将其研究视阈静止地锁定在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79) (一)商品拜物教 要厘清拜物教的发展脉络,就需要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剖析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的“细胞”,因为“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80)而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它“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81) 然而,商品形式及其自身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使得人们自己相互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这一虚幻形式表现出来。此时,“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82) 拜物教的产生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物以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无疑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有现象,而非物本身与生俱来的特征。同时,价值其实也并不单纯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还应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才出现的——因为某些阶段的人类产品并不需要采用价值形式来表现(如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便是如此),而其中的主要条件便是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只有在这两大条件下,不同生产资料所有者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才需要彼此交换(此时的劳动产品已成为商品),以此满足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将目光完全集中在了物与物间的相互交换关系上,原本在商品交换中所体现的买卖双方之间人与人的关系便逐渐被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所以,“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83)商品的拜物教由此得以产生。 由此可见,“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并且“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84)“因为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85)然而拜物教的发展并不会永远停留在商品拜物教这一阶段上,而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剖析商品的属性才能看到商品拜物教的历史阶段性,才能发现商品拜物教向货币拜物教过渡并进一步向资本拜物教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二)货币拜物教 “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货币的权利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86)在日益发展的人类社会中,货币作为商品交换之媒介,作用也愈发重要,以至于“货币万能”的拜金主义盛行不衰。对此,尽管凯恩斯也注意到并论述了“流动性崇拜”现象,(87)但他并未觉察到或者是刻意忽视了掩盖在货币背后的社会关系。“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当它考察资本时,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88)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89) 值得一提的是,货币拜物教的特性在货币资本的增殖公式中表现得更为直观。因为透过G—G’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此时,“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90)作为生息资本,“资本取得了它的纯粹的物神形式,即G—G’,……货币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91) 还应看到的是,纸币的出现非但没有消除货币拜物教,反而使人们“货币万能”的“信仰”更加固化。“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92) (三)资本拜物教 资本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随着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之后,资本拜物教的观念便完成了。(93)在剩余价值率转化成利润率后,资本关系也就神秘化了。马克思在对商品和货币进行论述的那一刻起,就指出了拜物教这一神秘性质,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94) 应当看到的是,资本拜物教的兴起同样是与资本家的贪婪欲望如影相随的。“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95)马克思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资本的逐利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96) 由此可见,“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97)基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作为物化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拜物教有其自身的历史性。“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98)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出马克思在拜物教分析上所采取的历史唯物论分析方法。 五、拜物教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一)拜物教理论揭露了资本家的贪婪本性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有十分精辟而深入的探讨。具体到拜物教这一视角而言,马克思首先论述了伴随拜物教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信用现象,认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为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信用货币所代替”。(99)在信用基础上,拜物教的本能冲动促使了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银行制度的发展使其更易于吸收社会的闲散资金,从而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和种社会职能。然而这样一来,“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100)对此,西方经济学只是就信用崩溃这一现象本身来阐述经济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并未看到资本拜物教的疯狂发展致使信用膨胀直至崩溃的深层原因。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101)受拜物教贪婪本性的驱使,资本家会不遗余力地扩大生产规模,使得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物的因素较之于人的因素而言不断增加,进而导致相对剩余人口随之增加。随着总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102)“利润率下降,同时,资本量增加,与此并进的是现有资本的贬值,这种贬值阻碍利润率的下降,刺激资本价值的加速积累。”(103)这表明,一般利润率的下降会促使资本家进一步扩大资本投入量,以此防止总利润的大幅缩减。然而,资本投入量不断增加将会一方面使得原先规模相对过小的资本由于无法保证原有总利润的实现而被“淘汰”,由此产生相对资本过剩;另一方面,资本投入量不断增加还会进一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在产生相对人口过剩的同时,又进入新一轮的上述循环的过程之中。 由此可见,资本家的最终目的(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与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扩大资本投入量)之间具有无法调节的矛盾。基于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生产过剩仅是表面现象,其本质在于相对资本过剩与相对人口过剩,而这两种“过剩”并存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并且还是最荒谬的现象,因为这两者的结合便可形成生产力从而生产出新的社会财富。事实上,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最突出之处。故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104)并且“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105) 从而,“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106)这便在造成相对人口过剩与相对资本过剩的同时,还存在相对产品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对此,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则仅仅借助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幌子来掩盖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性因素。此外,他们试图用“自然失业率”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失业现象,而马克思对此早已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角度论证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失业大军”出现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西方经济学家不仅没有站在生产角度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分析问题,反而试图以此极力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 (二)拜物教理论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生产关系因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拜物教已逐步发展到金融资本拜物教。此时,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将进一步迫使资本大规模地脱离生产型企业,把实体经济外包到其他地区。这在致使工业出现空心化趋势的同时,还使得金融资本膨胀、投机盛行,进而破坏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导致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失调,由此引发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一切都是用“人”的“动物精神”、自发性、盲目性所难以解释的。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人”的本性,而是把人看作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从而是把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且认为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人的“本性”。马克思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发展中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一切重大现象(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必然性与相关特征。 只有看到资本所表现出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资本再生产就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方面再生产出资本家,另一方面则再生产出雇佣工人。“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末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107)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同这些资料隔离开来;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仅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来重建平衡”。(108)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就是资本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本身,就是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彼此分离”。(109) (三)拜物教理论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唯物史观的解释 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立场不仅能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内在必然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性,而且还能捕获到为拜物教冲动所驱使的资本家在拼命扩张生产规模并推动大工业发展的同时还为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级阶段过渡而创造条件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在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更具破坏性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110)并且,“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111)特别地,资本家“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112) 随着资本主义积累的不断增大,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最终将会撑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此时便会要求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13)由此可见,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属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人的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西方经济学根本就提不出也绝对不能容忍提出每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观点。(114)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马克思是在假设市场(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产品市场等)完全竞争、经济参与者(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完全理性、信息完全充分、供求彼此平衡等“理想”环境下深入剖析经济现象并由此把握经济规律的,从而这些假设同样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这对于准确认识与把握经济规律而言则能起到“去粗取精”的效果,进而是必要的。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与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其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得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115)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然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学中所涉及的“人”之主要特征的界定上大相径庭,由此使得两者在从“人”的因素来剖析经济危机的切入点上及其深刻程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大体说来,西方经济学的视域中的“人”被定义成抽象的、充斥着“动物精神”的理性“经济人”,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人”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这两者在探寻“人”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及对相关问题的解答方面迥然不同。就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而言,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力主从“动物精神”的视角阐述相关原因,然而“动物精神”概念不仅是立足于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的,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释力度亦是乏善可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的拜物教理论出发不仅能够捕获作为经济范畴人格化的资本家们的贪婪本性,而且还能深入挖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及其内在机制,甚至还有助于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性以及朝着更高级阶段过渡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应归结于意识形态的差别和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需要,这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具有截然不同的哲学立场。与西方经济学所采用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相反,马克思经济学采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116)所以,与西方经济学家想方设法地渲染资本主义社会之完美性的做法不同,立足于辩证法的马克思不仅“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117)而且“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18)正是马克思经济学采用了辩证与发展的观点研究经济问题,其研究结论才更加深刻并更为科学,同时也更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的诸多理论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相比均可谓相形见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与全面爆发是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作为资本人格化且受拜物教驱使的资本家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用人的本性“自私自利”说明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当今西方经济学用人的本性为“动物精神”也说明不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是资本主义历史存在暂时性的确定证明,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全面、完整、系统地阐明了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原因和必然性,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三卷《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中。(119)故而,“资本主义已经造就了一个真正的人类世界的可能性,但不超越资本主义我们就不能达到那个世界”。(120) ①吴易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4页。 ⑩胡钧、杨静:《“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经济人”与“人格化资本”两种不同规定的本质区别》,《经济学家》2005年第6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8-849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3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3页。 (20)胡钧、杨静:《“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经济人”与“人格化资本”两种不同规定的本质区别》,《经济学家》2005年第6期。 (21)纳索·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46页。 (22)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杨砾和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23)Maslow,A.H.,"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vol.50,no.4(1943),pp.370-396. (24)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9页。 (25)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1-19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1页。 (27)Güth,W.et al.,"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ium Bargaining",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vol.3,no.4(1982),pp.367-88.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1页。 (3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3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页。 (34)胡钧、杨静:《“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经济人”与“人格化资本”两种不同规定的本质区别》,《经济学家》2005年第6期。 (35)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7页。 (36)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和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页。 (3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8页。 (38)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4-125页。 (39)胡钧、杨静:《“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经济人”与“人格化资本”两种不同规定的本质区别》,《经济学家》2005年第6期。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163页。 (41)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7页。 (42)Mas-Colell,A.,D.W.Michael & J.R.Green,Microeconomic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5,pp.5-122. (43)Novales,A.,E Fernandez & J.Ruiz,Economic Growth:Theory and Numerical Solution Methods,Springer,Heidelberg,Dordrecht,London,New York,2010,p.471. (44)Blanchard,O.J.& S Fischer,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The MIT Press,Cambridge,London,1993,pp.334,355. (45)Kupiec,P.H.& S A.Sharpex,"Animal Spirits,Margin Requirements,and Stock Price Volatility",Journal of Finance,vol.46,no.2(1991),pp.717-732. (46)Peter,H.& R.P.McAfeex,"Animal Spiri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2,no.3(1992),pp.493-509. (47)Middleton,E.,"Adaption Level and ‘Animal Spirits’",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no.17(1996),pp.:479-498. (48)Grauwe,P.D & P.R.Caltwasser,"Animal Spirits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 & Control,no 36(2012)pp.1176-1192. (49)Hasselmann,K.& D.V.Kovalevsky,"Simulating Animal Spirits in Actor-based Environmental Models",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tware,no.44(2013),pp.10-24. (50)Farmer,R.E A & J.Guo,"Real Business Cycle and the Animal Spirits Hypothesi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63,no.1(1994),pp.42-72. (51)Dos Santos Ferreira,R.& F.Dufourt,"Free Entry and Business Cycl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imal Spirit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no.53(2006),pp.311-328.Dos Santos Ferreira,R.& T.Lloyd-Braga,"Business Cycle with Free Entry Ruled by Animal Spirits",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 & Control,no.32(2008),pp.3502-3519. (52)Velasco,A.,"Animal spirits,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vol.15,no.2(1996),pp.221-237. (53)Cozzi,G.,"Animal Spirit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Innov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no.49(2005),pp.627-637. (54)Kindelberger,C.,Manias,Panics and Crashes,5th ed.,Wiley & Sons,2005. (55)Harris,M.& A Raviv,"Differences of Opinion Make a Horse Race",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vol.6,no.3(1993),pp.473-506.Morris,S,"Speculative Investor Behavior and Learning",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1,no.4(1996),pp.1111-1133. (56)陈彦斌、唐诗磊:《信心、动物精神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金融研究》2009年第9期。肖欣荣:《金融投资理论:一种基于动物精神和宏观对冲的框架》,《南开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林树、俞乔:《有限理性、动物精神及市场崩溃:对情绪波动与交易行为的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57)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廖理、施红敏译,20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8)Akerlof,G.A &-R.Shiller,Animal Spirits: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162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162页。 (6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 (6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8页。 (64)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9-343页。 (65)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5页。 (66)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5页。 (6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6页。 (6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1页。 (69)Koppl,R.,"Retrospectives:Animal Spiri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no 5(1991),pp.203-210. (70)Schwartz,H.,"Does Akerlof and Shiller's Animal Spirits Provide a Helpful New Approach for Macroeconomics",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no.39(2010),pp.150-154. (71)隋建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与应用》,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72)Bidder,R.M.& M E Smith,"Robust Animal Spirit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no.59(2012),pp.738-750.Bofinger,P.et al.,"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n a Model with Animal Spirits and House Price Booms and Busts",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 & Control,no.37(2013),pp.2862-2881. (73)Gintis,H.,"Animal Spirits or Complex Adaptive Dynamics? A Review of George Akerlof and Robert J.Schiller Animal Spirits,Princeton(2009)",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no.30(2009),pp.511-515. (74)Schwartz,H.,"Does Akerlof and Shiller's Animal Spirits Provide a Helpful New Approach for Macro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no.39(2010),pp.150-154. (75)Schwartz,H.,"Does Akerlof and Shiller's Animal Spirits Provide a Helpful New Approach for Macro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no.39(2010),pp.150-154. (76)西蒙·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健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页。 (77)西蒙·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健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 (7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7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8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6-997页。 (8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8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8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8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8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101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1页。 (8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8-159页。 (8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 (8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2-113页。 (9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2页。 (9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2页。 (9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0页。 (9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9页。 (9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6页。 (9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9页。 (9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9页。 (9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9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4页。 (10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6页。 (10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 (10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 (10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7页。 (10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8页。 (10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6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1-292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7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2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7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1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1页。 (114)胡钧:《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几个关键问题的看法》,《改革与战略》2011年第12期。 (11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4页。 (1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1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19)胡钧、沈尤佳:《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区别》,《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120)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宋萌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191页。标签:凯恩斯论文; 经济人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经济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商品拜物教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