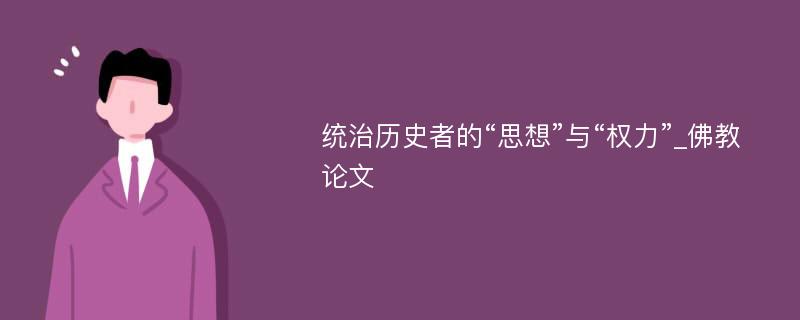
治史者的“思想”与“权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思想论文,治史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初是从《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一、二期上,获知葛兆光先生撰写了《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即《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当时便对他的立意、构思颇有好感,日后拜读,的确获益匪浅。在此,笔者只想就书中个别章节凸现的观点及方法论问题谈点杂感,所涉及的主要是第四篇第六节的第四部分。
看来,葛先生在这部分是要总结性地讨论一个问题,即“佛教进入中国”后对华夏原有“话语权力”的“回应”。既然要讨论,那么也就必然会发生“讨论者”对“历史”的介入,从而也就有了讨论者究竟应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去介入的问题。相对而言,“介入方式”无疑是更根本的。依笔者的体会,葛先生的介入方式或“话语”逻辑,也即所谓“本来,佛教……可是,中国……”例如,他写道:“本来,佛教并不需要悠久的历史依据作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的基础……可是,在一切都需要‘有史为证’或‘古已有之’才能使人信服的中国,历史时间的长短似乎与真理价值的高低相关甚至决定真理价值的高低……”又如,“本来,佛教也不需要从宇宙空间位置上来为自己宗教的真理寻找价值的基础,可是……在中国人看来,中国是宇宙的中心……”再如,“本来,佛教在世俗社会中坚持宗教独立、追求精神超越的理由,是从它关于人生的大道理中来的……可是,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中……其实,如果这一讨论的思路深入,使得佛教关于人生的理论真的取代了古代中国人生论,那么,古代中国人那种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追求目标的价值体系将崩溃,中国古代人那些以血缘亲情、家庭伦理、社会责任为评价基础的传统准则将失去意义……但是,这种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争论的目的也很快就具有了现实的、具体的实用性……”
在这部分“本来,佛教……可是,中国……”的集中出现,使作为读者的我颇感诧异:葛先生怎么改变了此前章节那种比较平实的“写法”?而随后的疑惑,则首先集中在一个看似简单却颇为要害的问题上:“本来,佛教……”中的“佛教”,指称的是何种意义上的佛教?它到底是指“原有的”印度佛教,还是指华夏历史中演化着的“先前的”中国佛教,抑或是指葛先生在其个人今之体悟中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被看成“普遍主义的宗教”(580页)的佛教(为了叙述方便, 此义佛教有时将以“GF”代之)?对此,葛先生并未点明,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做些推断:这里的“佛教”,如指“原有的”印度佛教,则“本来,佛教……”并无“中国思想史”意义可言。在概念上,它尽管可以指称某种原生的整体意义上的佛教,但实际上却只具有某种外在的、形式上的涵义,不过像张“出生证明”,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在此如指“先前的”中国佛教,则又显得不合逻辑,因为此义佛教即是华夏历史中的那个佛教,原无所谓“本来,佛教……”可言;如此看来,这里所指称的“佛教”,就只能被推断为葛先生自己的体悟。笔者冒昧地做此推断,实不知葛先生以为然否。如果这种推断属实,那么葛先生的这部分讨论也就难免不出现问题。
问题在于,葛先生一旦写下“本来,佛教(GF)……”那么实际上就已把他本人的GF,当做了某种对他的讨论具有决定意义的预设、起点乃至尺度;而一旦用这种方式介入历史,实际上就把他所要讨论的“先前的”中国佛教,把这个“中国思想史”中真正的历史性话题,置于他本人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GF的笼罩、“统治”之下,从而也就会严重“消解”这个话题本身的历史性以及相关讨论的历史意蕴。其实,葛先生如果在此不是以“治史者”的身份出现,那么他本人之GF是否达于“真知真觉”,本无关宏旨,充其量也不过是他个人的“兴趣”及“参悟”问题。然而,既然他在此扮演着治史者的角色,既然他要讨论的对象是“中国思想史”意义上那个“先前的”中国佛教,那么,最好还是尽可能淡化乃至抑制对自己的GF之恰当性的自信和热情,以便能够更自然地“接近”与“体验”,更平实地“述说”与“阐释”他的对象,无论这个对象,较之那个即使佛祖本人“现身”恐怕也说不清的“原有的”印度佛教,它已变得如何如何(低劣?),或者,较之葛先生本人“觉悟”的GF,它已因所谓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与普遍主义的宗教之间的冲突”(580页)、 因华夏原有的“话语权力”而变得如何如何(卑俗?)。不因史“喜”,不为史“忧”,乃治史者应有之心态,或曰境界;至于治史者本人“思想”的介入,尽管实属必然,但理应慎之又慎。所谓“春秋笔法”,本非通则,自不可滥用。记得何兆武先生说过:“一个历史学家不但同时也必然是一个思想家,而且还必须首先是一个思想家,然后才有可能谈到理解历史。”(《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385 页)这种说法的确会使一些“有思想的”治史者感到某种快慰和自信,有时他们还可能变得有些自负。然而,这种说法也有过于罗曼蒂克的一面,因为在某种意义或很大程度上,“历史”或“思想史”之“真谛”,很像个不通情理的怪物,像个怪诞不经的家伙,治史者越有他自己的“思想”、“热情”乃至“权力”,它反倒会越快越远地逃逸。当然,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治史者本身应是怎样的思想家,以及,他们能否较自觉地厘清并处理自己的“思想”与“历史”或“史实”之间的关系,而要真正达于会通兼得之境界,又何其难也!
不言而喻,要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讨论“先前的”中国佛教问题,就要有一定的预设、起点及尺度,而这套东西,也是任何一位称得上是“思想家”的“历史学家”所不能不去思考的。因此,问题仅仅在于,他究竟应该从哪里引出、把什么作为这套东西?一般而论,既然要研究的是具体的“思想史”而非纯粹的“经义”、“学理”,那么治史者就应更多地注重“历史性”原则、更自觉地坚持“历史主义”立场。殊而言之,这里所要预设的,既不应是“原有的”印度佛教本是、曾是怎样的,也不该是葛先生本人的GF之“理所当然”,而只能是:无论“先前的”中国佛教是怎样的,它都必然历史地不同于“原有的”印度佛教和葛先生本人的GF。这听起来很像是“废话”,然而在方法论上却极为重要,它至少提醒并要求治史者:时时对上述三者的历史性差异之必然存在,保持一份清醒的自觉;处处对自己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具体介入方式之恰当与否,保持一份冷峻的警觉。惟其如此,在治史时,他才有可能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什么当说”以及“该怎么说”,才有可能比较自然而平实地去“体验”、“述说”及“理解”历史中的中国佛教。至于在此能够作为起点与尺度的东西,也只能是那些已被治史者恰当地意识到并被确证了的“先前的”中国佛教之历史事件及实际演化。依上述立场来看,通常所谓“佛教进入中国”,就只能算是一种很外在的皮毛说法。因为,一方面,并非“原有的”完整而纯粹的印度佛教(有吗?事实上,即使在“进入中国”前,它的“部派”及演化就已十分庞杂),而是被统称为“佛教”的那种宗教的一些东西,哩哩啦啦地渐入华夏;另一方面——这才是更根本的,我们在“史学”意义上对佛教的理解,固然不能忽视原生于印度的高僧与经籍向华夏传了些什么或有些什么,但更重要的应看,那些原已成为华夏“话语权力”之“承担——行使者”的中国人,他们历史地实际接触、选取、接受以及转化了些什么。严格地讲,这种意义上的佛教,才真正构成了“佛教”之在中国的历史性具体内涵;而且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也正是这种浸透着历史性内涵的具体佛教,才构成了讨论佛教问题的真正“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起点。说起来总让人感到有些遗憾,葛先生尽管对所谓“佛教进入中国”做了大量而极有意义的“追溯”,但他对这里的“佛教”之于华夏所必然浸染的历史性具体内涵及其历史生成,却因为引入了所谓“本来,佛教……”这种“话语”,而未能在他本人的“思想”中达到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总体性把握。
不难理解,在“本来,佛教……”这种非历史发生学的“话语”中,内含着葛先生对佛教的某种非历史的抽象理解;而这,实质上又与他那种把“佛教”看成所谓“普遍主义的宗教”的理解,与他对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与普遍主义的宗教之间的冲突”的看法不无关系。其实,就历史本身看,这个“冲突”问题,以及诸如“宗教普遍理想是否能够超越民族狭隘立场”(577页)之类的问题, 不过是一些非历史的“虚假问题”;而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上去谈论所谓“普遍主义的宗教”,也只是治史者本人的一种抽象的“思想虚构”。即使撇开“世界三大宗教”的同时存在、深刻差异以及它们各自庞杂繁复的“教派”分化这些“史实”不谈,一种宗教(这里指佛教)是不是“普遍主义的”,或者说,它的“教义”、“理想”以及“真理”(580 页:“宗教真理普遍性”)等是否具有“普遍性”,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原有的”它曾是怎样的,也不在于“自在的”它会是怎样的,更不在于它的“经、律、论”等抽象地看当是怎样的,而是在于,它在华夏这个特定的民族、文化或国度中历史地是怎样的,也即恰恰取决于,那些必然有着各自具体的前信佛生成史的“赵、钱、孙、李……”们,他们对它的具体接受方式以及具体接受了什么。这个道理,以今之解释学抑或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看,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和理解所谓“民族主义的情绪”、“民族狭隘立场”这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呢?其实,较之生成于外域且渐入华夏的那个佛教的那些成分,在中国本土,恰恰是华夏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及“立场”,才是本然的、必然的及主导的,当属华夏民族及文化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与最根本的“对话方式”,因而,无论对外来宗教显得如何“狭隘”、“激烈”、“过分”,也只有它们,在华夏才真正是“普遍主义的”,尽管在与外来宗教的交往及“冲突”中,它们也会历史地调整或改变自己。综言之,华夏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及“立场”,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与那个外来“佛教之间的冲突”,但葛先生所谓的它们与“普遍主义的宗教之间的冲突”,则是一个非历史的“虚假问题”,一种抽象的“思想虚构”。
可是,在葛先生这部分的讨论里,他对佛教的那种抽象的“普遍主义的宗教”理解,不但构成他本人之GF的一项实质性内容,而且还构成他借以展开讨论的一种基础性解释框架与语境。这使人不禁会问:如此这般,“史学”或“思想史”意义上的那段历史及那个佛教又在哪里、又会怎样呢?结果是,这里进行的讨论,很像是葛先生本人也以自己的GF而闯入其中的一场“论辩”或“冲突”。或因此故,在讨论中国的信佛者与反佛者之间的“论辩”时,他才会写下了诸如“这本来也就足够了”(582页)之类的断语。
从深层看,当葛先生以“本来,佛教……”这种“话语”展开其讨论时,一方面,依福柯之言,他是在不恰当地建立并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力”,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抽象“话语”,去“消解”他作为治史者本来要讨论的历史性具体话题,可谓“事与愿违”;而另一方面,按伽达默尔之说,作为治史者,他又有把自己的“历史性”当做某种“绝对”而强加于“先前的”中国佛教的“历史性”之嫌,因而实际上又排斥着他与后者“视界融合”之可能(同时也在排斥“消解”的功力),可谓“南辕北辙”。也就是说,在“思想史”及其研究的意义上,“本来,佛教……”这种“话语”,已经内含着某种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或矛盾,其结果是,“史学”从而“历史”本身,被弄成了“思想家”的“独白”。而葛先生“消解”缺陷或矛盾的技法,又像是“以拙补拙”:把真正该说的、应深入讨论的东西,抛入了同样不恰当的“可是,中国……”这样“话语”之中,进而还引出了“其实,如果……那么……”之类的“虚拟式”议论(见前引片断,另见572页)。这样一来, 便使华夏历史中演化着的佛教之历史性及复杂性,使治史者本应尽可能予以“呈现”和“理解”的历史内容本身,反而又成了他批评的对象。毋庸赘述,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可是,中国……”这种谈论或介入方式,显然是极不恰当的;“往事已矣”,“七世纪前”的中国及其演化着的佛教,看来也没有再去做“虚拟式”议论的必要。不过,这类“话语”的出现,倒是确证了:这里的“视界融合”尚待时日。应该说,从葛先生撰写这部著作的立意看,他对这类“写法”是否弃的;笔者的印象是,他在别的章节尽管也有“走神”的时候,但还是相当警觉的。可在这部分,他好像再也耐不住性子去“追溯”了。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历史当其成为过去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就是定命的了”(《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125页)。在这个意义上, 治史者如能说清“定命”之所以然及其过程的复杂性,就已算是尽职尽责了。细而言之,对华夏历史中演化着的“先前的”中国佛教的总结性讨论,应尽可能完整地说明其基本历史脉络是怎样的,而不是去构想它应是怎样的;应尽可能如实地揭示那原创于印度的佛教为什么在华夏必然会演化成中国式佛教,而不是去批评它为什么没演化得更纯更好;应尽可能深刻地理解那个佛教在中国“话语权力”背景下之被华夏接受、转化过程的复杂性,而不是去抱怨当年“更多的佛教信仰者仍然希望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与传说中寻找证据”(582页),或“他们依然滑入中国思路之中”(583页),如此等等。要做到这些,自然是难之又难,然而一旦有意无意放弃了这种努力,那么治史者又何以立身呢?这当然不是说,葛先生淡视了这些历史及史学内容,而只是说,他在此尚未用一种恰当的方式去历史地“追溯”与“重构”之。
或许换一种“话语”逻辑,譬如换成“本来,那时中国……可是,那个佛教……”我们会更好地接近并理解在华夏历史中演化着的中国佛教。但无论怎么讲,瑕不掩瑜,葛兆光先生的力作《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毕竟给我国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新气息,带来了新气象。而这,不也正是它值得人们“吹毛求疵”的“本钱”吗?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版,42元。)
标签:佛教论文; 思想史论文; gf论文; 华夏民族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华夏论文; 中国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