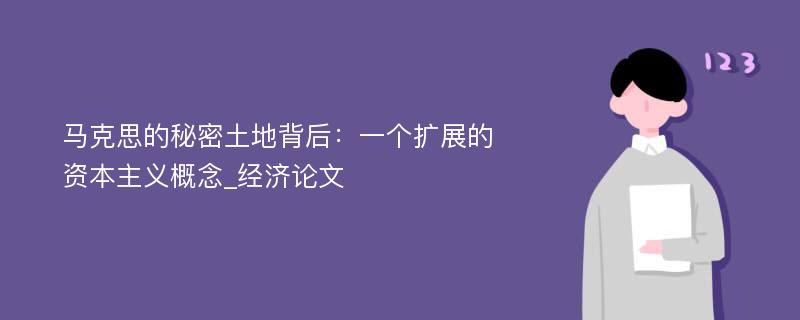
马克思隐秘之地的背后:一个扩展的资本主义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之地论文,隐秘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资本主义”回来了!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个术语,如今不同领域的评论者都公开地对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各个学派的学者争相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化批判,而且全世界的活动分子都动员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实践。①“资本主义”的回归是当前危机的深度展开,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对系统化资本主义论述的渴望,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不过,当前有关资本主义话题的急速扩展更多地表征了一种对系统化批判的渴望而非实质性贡献。其结果就是我们生活在一种十分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之中,却没有一个能够阐释这种危机的批判理论,同样也缺乏与当今时代相称的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危机的概念。在本文中,我的目标就是指出一条能够弥补这一空白的道路,这一道路由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所指引。同时我也提议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在一般的概念性资源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然而没有能够将性别、生态以及政治权力系统性地考虑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构化原则以及不平等的轴心,更别说考虑为社会斗争的风险和前提。因此,需要从这些视角重新建构马克思的思想。本文将重新审视一些老问题: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如何使之最好地概念化?我们应该视之为一种经济体制、一种伦理生活的形式,还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我们应该如何描述其“危机趋势”的特征,以及我们应该将其置于何处? 典型特征 为处理这些问题,我将从回顾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四个核心特征开始。这一路径乍看起来非常正统,但我打算通过表明这些特征如何以其他特征为先决条件,从而使之“去正统化”。这里所说的其他特征,实际上构成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四个核心特征之所以可能的背景性条件。为了发现资本主义的秘密,马克思的视线越过交换领域,进入生产这个“隐秘之地”,而我将进一步在更具隐蔽性的领域中,即生产领域背后,探寻生产之所以可能的背景条件。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它预示了所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划分。这一划分的出现是早先社会世界瓦解的结果,在早先的社会世界中,不管境遇如何不同,绝大多数人都可获得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资料,换句话说,不必通过劳动力市场就可获得食物、住所和衣服,就可获得工具、土地和工作。资本主义彻底颠覆了这种机制。它封闭了公有物,废除了大多数人惯常的使用权,并将共享的资源转化为极少数人的私有财产。 这直接导向马克思所说的第二个核心特征: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因为大多数人现在为了工作以及获得他们维持生计、抚养小孩之所需而不得不屈服于这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这里,劳动力在两种含义上是“自由”的:首先,在法律地位方面具有流动性的自由——不是被奴役,成为奴隶或农奴,不是被束缚在一个既定的地点或依附于特定的主人——并能够订立劳动合同;其次,“游离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之外,包括游离于土地和工具的惯常使用权之外,从而丧失可以使一个人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资源及权利。 接下来是同样特殊的自我增值的价值,这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核心特征。资本主义特有一种客观的系统性推动力或指向性,即资本积累。原则上,所有者以资本家的身份所做的一切都指向资本扩张。而且每个人为了满足自身需求所做的努力都是间接的,都是为其他东西服务——这里所谓的“其他东西”即指资本本身无止境地自我扩张的需要。马克思说,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资本本身即为主人。人是其卒子,沦落到计算如何能够在资本的缝隙中通过服务于资本积累从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第四个特征详细说明了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众不同的作用。市场的存在贯穿于人类历史,包括非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功能具有以下两个更深层次的特征。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负责将主要投入配置到商品生产中。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生产要素”的这些投入,起初被确定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除了配置劳动力之外,资本主义也利用市场来配置不动产、资本品、原材料以及信贷。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这些生产性投入,继而将它们转化为商品。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功能:它们决定着社会剩余如何被投资。马克思认为,社会剩余指的是超出再生产某种既定的生活方式以及补充生活过程中的耗费所需资金之外的集体性社会资金。一个社会如何使用其过剩的生产力至关重要,它提出了人们想如何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他们选择将集体性力量投往何处,在平衡“生产性工作”与家庭生活、休闲与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意见如何,以及他们如何渴望与非人的自然建立关联,他们想要留给后代的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将这样的决定留给“市场力量”。这也许就是资本主义最重要也最有悖常理的特征——这等于将最为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计算货币化价值的装置来处理。这与第三个核心特征紧密相连,即资本固有但却盲目的指向性、自我扩张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资本将自身建构为历史的主体,取代使其成为现实的人,并将人变成它的奴隶。 通过强调市场的这两种作用,我意在反驳如下被广泛持有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本身推动生活世界的日益商品化。我认为这样的观点会走向一条完全商品化世界的反乌托邦幻想的死胡同。这样的幻想不仅忽视了市场的解放性面向,而且忽略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强调的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往往在“半无产阶级化的”家庭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在允许所有者付给工人较低工资的制度下,许多家庭从非现金工资的其他来源中获得一部分重要的生计支持,包括自我供应(种植园地、缝纫)、非正式的互惠(互助、实物交易)以及国家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公共产品)。②这种制度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活动和物品置于市场的范围之外。它们内生于福特制,在那些主要经由将男性雇佣劳动与女性家务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家庭进行生产,同时在外围抑制商品消费发展的国家,这种福特制能够促进工人阶级的消费主义。半无产阶级化在新自由主义中更为明显,通过将数以亿计的人从正式经济驱逐到资本从中汲取价值的非正式的灰色地带,新自由主义已经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积累战略。这种“原始积累”是资本从中获利并对其深度依赖的持续不断的过程。 那么,关键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化与非市场化并存,这是深入资本主义骨髓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共存”这个词不足以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化与非市场化方面之间的关系。更好的术语应该是“功能性的鳞状重叠”,或者是简洁明了的“依赖”。③市场的存在恰恰依赖于非市场化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为市场的存在提供了背景性条件。 背景性条件 接下来,我要看看生产这个“隐秘之地”的背后,还有什么更为隐秘的领域。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隐藏在如上四个核心特征之后并使得这些核心特征成为可能的东西是什么?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处提出了类似的问题。④资本从哪里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生产者如何与其相分离?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以抽象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这种方式抽离了对使资本主义生产成为可能的背景性条件的分析,这些背景条件被假定为简单的给定。然而,关于资本本身从哪里来有着一个完整的幕后故事——一个相当暴力的剥夺和侵占的故事。此外,正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曾强调的,这个幕后故事并不仅仅存在于过去,即资本主义的“原点”。⑤侵占是一个进行中的——虽然是非正式的——积累机制,它与正式的剥削机制——这可谓马克思的“台前故事”——持续并行。 从剥削的台前走向侵占的幕后,这种变换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转变。它类似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始部分所做的转变:他使我们离开市场交换领域以及与之有关的资产阶级常识性的视角,深入到更具批判性视角的生产的隐秘之地。由于这首次的转换,我们发现了一个肮脏的秘密:经由剥削进行的积累。换句话说,资本扩张并非如市场观点所暗示的那样是经由等价物的交换,相反,恰恰是通过其对立面,即通过不补偿工人的部分劳动时间。类似地,当我们在第一卷末尾处从剥削转移到侵占,会发现一个更为肮脏的秘密:在升华了的对雇佣劳动强制的背后,是公然的暴力和彻头彻尾的盗窃。接下来需要转向另一个视角,即剥夺。这种向“隐秘之地”背后的转移也是一种向历史的转移,并且也是转向剥削的“可能性条件”。 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当中也暗含着其他同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转变,只是马克思本人并未进一步展开。其中一个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转变就是从生产到社会再生产——一种产生并维持社会联系的供应、看护和交互作用的方式。不管被赋予何种不同的称呼,“照料”“情感劳动”或“主体化”,这种活动都形塑着资本主义的人类主体,支撑着他们作为具体化的自然人的存在,同时也将他们建构为社会存在,形成他们的习性和社会伦理本质,或伦理性,并且在这种伦理性中展开行动。比如,使年少者社会化、建立社群、产生并再生产对共享的理解、培育构成社会合作之基础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不是全部,但至少绝大多数这类活动是在市场之外发生并进行的,比如在家庭中、在邻里之间以及在大量的公共机构当中,包括学校和儿童托管中心;而且尽管不是全部,但至少绝大多数这类活动不采取雇佣劳动的方式。然而,社会再生产活动对于付薪劳动的存在、剩余价值的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的功能而言绝对必要。缺少家务劳动、儿童抚养、学校教育、情感照料,缺少大量其他有助于产生新一代的工人,同时有助于维持社会联系和共享理解的活动的话,雇佣劳动就不会存在。因此,与“原始积累”极为相似,社会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可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性条件。 此外,在结构上,社会再生产和商品生产之间的划分对资本主义而言至关重要——事实上,这种划分是资本主义的人为产物。正如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所强调的,这种区分深刻地性别化了,再生产与女性相连,生产与男性相连。历史上,“生产性的”付薪工作和无薪的“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分裂巩固了现代资本主义女性的从属地位。如同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划分,这种社会再生产和商品生产之间的划分也依赖于先前世界的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被打碎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女性的工作尽管有别于男性,但却是可见的、被公开承认的,是社会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相反,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再生产劳动被分离出去,移交给一个单独的、“私人的”家庭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再生产劳动的社会重要性被掩盖了。而且在这个金钱是权力之首要媒介的新的世界中,无报酬的事实揭示了问题所在:从事再生产劳动的人在社会结构上从属于那些挣现金工资的人,即便他们的工作也为雇佣劳动提供着必要的前提。 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划分是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历史性地出现的。不过这种划分并非一劳永逸。相反,这种划分经历了历史性的突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20世纪,社会再生产的一些方面被转化成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去私人化而非商品化。如今,随着新自由主义将某些此类服务(重新)私有化以及(重新)商品化,这种划分再次突变,与此同时,连社会再生产的其他方面也首次被商品化。此外,通过命令紧缩公共供给,同时大量招募女性从事低工资的服务性工作,新自由主义重新绘制了先前区分商品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性边界,并由此重新配置了这个过程中的性别秩序。而且,通过对社会再生产不断增加的重大打击,新自由主义将这种资本积累的背景性条件转变成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导火线。 自然和权力 我们还需要考虑另外两种更深层次的、在认识论视角上同样重要的转变,它们将我们引导到其他的隐秘性领域。第一种转变非常好地体现在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之中,目前他们正在书写着有关资本主义凌驾于自然为所欲为的另一个背景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资本对自然的吞并,对土地的殖民化占领,自然既被视为一种“投入”到生产之中的原始资料,又被视为一种吸收生产废弃物的“污水坑”。在这里,自然被变为资本资源,其价值既被预设,同时又被否认。在资本的账目中,自然被视为免费的,因而,自然被征用、剥夺而毫无补偿或再补给,并且被暗中假定为是无限的。如此一来,自然界维持人类生活的能力以及更新其自身的能力就构成商品生产和资本累积的另一个必要的背景性条件。 从结构上说,资本主义假定了自然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截然区分,自然领域被设想为提供可使用的、免费的、非生产性的“原材料”,经济领域被设想为一个价值的领域,由人类创造并且为人类而生产。伴随这种截然的区分,预先存在的人——被视为是精神性的、社会文化的和历史性的——和非人的自然——被视为物质性的、客观给定的以及与历史无关的——之间的区分也被强化。这种截然的区分也依赖于先前世界的瓦解,在先前世界中,社会生活的节奏在很多方面顺应于非人类的自然的节奏。资本主义野蛮地将人与自然、季节性规律分离开来,将人征召到由矿物燃料所驱动的工业生产之中,以及被化学肥料所养大的利益驱动的农业之中。借用马克思所谓的“代谢断裂”,资本主义开始了如今被称为“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在其中,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和大气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⑥ 这种划分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突变。当前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圈地,例如水的商品化,它将“更多的自然”带到经济的台前。同时,新自由主义承诺模糊自然与人的边界——以新兴的生殖技术以及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机器人”为证。⑦这些发展不但没有促成人与自然的“和解”,相反更加剧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商品化和吞噬。与马克思和普兰尼(Polanyi)所谈过的圈地不同,那种圈地“只是”将已经存在的自然现象商品化,而新的圈地则深深渗透到自然的“内部”,改变了自然内在的“文法”(grammer)。最后,新自由主义正在将环境保护主义市场化——以活跃的碳排放许可和碳补偿贸易以及“环境衍生品”贸易为证,这类贸易转移了资本对转变以矿物燃料为前提之不可持续生活方式的长期、大规模的投资。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种对现存生态环境的侵犯正在将资本积累的自然条件转变成资本主义危机的另一个核心节点。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最后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转变,这个转变指向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政治条件,即资本主义依赖公共权力来制订并实施其基本规范。如果没有一个支撑私营企业和市场交换的法律框架,资本主义终究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的台前故事主要依赖于公共权力来保证财产权、执行契约、裁定争端、平息反资本主义的叛乱,并且——用美国宪法的语言来说——维持构成资本命脉的货币供给之“十足的信用”。在历史上,这种公共权力主要被固定在领土国家的范围之内,包括那些作为殖民势力来运作的权力。正是这种国家的法律体系构成了貌似去政治化的领域的大概框架,在这个领域中,私人的活动者能够追求他们的“经济”利益,一方面免于公然的“政治”干涉,另一方面免于来自于亲属关系的资助义务。同样,动员“合法性力量”镇压对剥夺——通过剥夺,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得以生成并维持——的反抗的,也正是领土国家。最后,对货币进行国有化以及认购的也正是这样的国家。⑧我们可以说,国家历史地“建构了”资本主义的经济。 这里,我们遭遇到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划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划分。伴随这个划分而来的是公共权力从私人权力中、政治强制力从经济强制力中的制度性分化。正如我们曾讨论过的其他核心划分,这种划分也是作为先前世界之瓦解的结果而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废除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例如,在封建社会中,对劳动力、土地以及军事力量的控制权力无一不根据权威和隶属制度来授予。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如艾伦·伍德(Ellen Wood)所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彼此分离;每种权力都被指定了其自身的领域、表现方式以及独特的做法。⑨然而资本主义的台前故事也拥有地理政治学层面上的可能的政治条件。这里所讨论的是领土国家植根于其中的更广泛的空间组织。在资本扩张的推动下,这将是一个资本流动非常频繁的空间。资本的这种跨国界的运行能力依赖于国际法,它促成大国之间及超国家政权之间的协议,这些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以对资本友好的方式)使这一空间处于安定状态。纵观历史,资本主义的台前故事依赖于一连串全球霸权主义的军事和组织能力,正如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的,这种全球霸权主义力求在多国体制的框架内逐步促进积累。⑩ 这里,我们看到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更进一步的结构性划分:一方面是“国内”和“国际”之间“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划分,另一方面是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帝国主义的划分。不论哪种划分,其前提基础都是另外一种更为根本性的划分,即被组织为一种“世界体系”的不断增长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和被组织为一种领土国家的国际体系的政治世界之间的划分。随着新自由主义对政治能力——历史上资本曾在国家层面和地理政治学层面上依赖于这种政治能力——的掏空,这些划分目前也在发生着变化。作为这种政治能力空心化的后果,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政治条件现在也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重要场所和导火索。关于这些内容有更多可以讨论的内容,不过,我论证的着力点很清晰:资本主义台前的“经济”特征依赖于“非经济的”背景性条件。通过私有制、自我扩张的价值积累、自由劳动力市场以及商品生产其他重要投入的市场、对社会剩余物的市场分配等因素加以界定的经济体制,可以通过社会再生产、地球生态以及政治权力三个至关重要的背景性条件加以描绘。因此,为了理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将资本主义的表面特征与这三个幕后故事相结合。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与女性主义视角、生态视角以及政治理论的视角——国家层面的理论、殖民地/后殖民地的理论以及跨国理论——结合在一起。 制度化的社会秩序 那么,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我这里阐述的图景远远不同于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常见观点。的确,乍一看我们所认定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似乎是“经济的”。但这个表象是误导性的。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之一就是它将其结构性的社会关系处理为好像它们是“经济的”。实际上,我们很快就发现,讨论使这种“经济体制”得以存在的“非经济的”背景性条件是必要的。这些特征并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而且我们已得出结论,那些背景性条件切不可被排除在资本主义图景之外,而必须被概念化、理论化为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的一部分。因此,资本主义的内容远不只是经济。 同样的,我所描绘的图景也不同于将资本主义物化为一种以普遍的商品化和货币化为特征的伦理生活形式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正如卢卡奇(Lukács)在其著名的文章《物化和无产阶级的意识》(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中所阐述的,商品使得所有的生活殖民化,在诸如法律、科学、道德、艺术以及文化等各种不同的现象中都打下其烙印。(11)在我看来,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普遍。相反,凡其所在之处,都恰恰依赖于非商品化地带的存在。社会的、生态的以及政治的非商品化地带不只是商品逻辑的反映,而且体现着其自身与众不同的规范性“文法”和本体论“文法”。例如,指向再生产(和生产相对)的社会实践易于产生关怀、相互责任以及团结的理想,尽管这些理想也可能是等级化的和地方性的。(12)同样,指向政治的实践,常常涉及民主原则、公众自主的原则以及集体性自决的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可能是受限制的或排他的。最后,与资本主义在非人类的自然方面的背景性条件相连的实践倾向于培育诸如生态支持力、无支配的自然以及代际正义之类的价值。当然,我的重点不是要将这些“非经济的”规范理想化,而是从与资本主义前景相连的价值出发正式提出它们的分歧,这些价值中最重要的有:增长、效率、平等交换、个体选择、消极自由以及精英提升等。 这种分歧对我们如何概念化资本主义关系重大。资本主义社会远不是产生出一种单一的、无孔不入的物化逻辑,而是存在着规范性的差异,包含多种彼此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社会本体。这些彼此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规范性差异相互冲突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将拭目以待。不过,这些差异的基础已经非常清晰:资本主义独特的规范性生成于我们已经辨明的台前与背景的关联之中。如果打算发展一种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我们就必须用一种更为差异化、结构性的观点取代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物化的伦理生活形式的观点。 如果资本主义既不是一种经济体制,也不是一种物化的伦理生活形式,那么它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它最好被视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比如和封建社会一样。以这种方式理解资本主义强调其结构性划分,特别是我前面已经指出的那些体制性分离。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构成性的本质,在于“经济生产”从“社会再生产”中的体制性分离,这是一种以男性支配的资本主义形式为基础的具有性别意味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使得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和积累模式成为可能。另外,资本主义还是“经济”从“政治”中的制度性分离,这种分离将被确定为“经济的”事务从领土国家的政治议程中驱逐出去,与此同时释放资本,使其自由漫步在一个跨国的无人地带,在那里,它在从霸权秩序中获益的同时,逃离了政治的控制。最后,对资本主义而言,同样具有根本意义的就是本体论的划分,这是预先存在然而已被大规模强化的划分,即其(非人的)“自然”的背景和(表面上非自然的)“人”的台前之间的划分。因此,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以如此的分离为前提的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就是在暗示资本主义与性别压迫、政治统治——民族国家层面的和跨国层面的、殖民的和后殖民的——以及生态退化之间非偶然性的、结构性的鳞状重叠,当然,与其同为结构性的、非偶然的、动态的劳动剥削相结合。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划分就是简单的一劳永逸的给定。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哪里及如何确定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和政治、人和非人的自然之间的界限是根据积累体制而历史地变化的。实际上,我们恰恰能够基于这些差别将自由放任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概念化为三种历史上特殊的划界方式,对经济与政治、生产与再生产以及人与非人的自然之间的界限进行划分。 边界斗争 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精确配置在任何地点和时间都依赖于政治,即依赖于社会权力的平衡以及社会斗争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划分远非简单的给定,而是常常成为冲突的焦点,特别是当社会活动者动员起来挑战或捍卫已确定的经济与政治、生产与再生产、人与非人的自然之间的边界的时候。为了在绘制资本主义制度性图谱的争议性进程中重新定位,资本主义的活动者们开始借鉴其他多个规范性视角。例如,为了反对教育的商品化,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汲取与再生产相关联的关怀、团结以及相互尊重的理念。其他人则呼吁与生态相关的自然治理的观念以及代际正义的观念,以促进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还有一些人援引与政治相关的公共自治的理念,来倡导国际资本管制以及扩展超国界的民主问责。这样的主张,与不可避免会激起的反对主张一起,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斗争的内容——这些社会斗争与马克思特别强调的在控制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分配上的阶级斗争一样重要。这些我称之为边界斗争,决定性地塑造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13) 聚焦于边界斗争应当预先避免给人留下任何错误的印象,比如认为我所提出的观点是功能主义的。的确,我着手于将再生产、生态、政治权力的特征描绘为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台前故事之必要的背景性条件,强调它们对商品生产、劳动剥削以及资本积累所发挥的作用。然而这种结构上的瞬间并不能捕捉资本主义台前幕后关系的所有故事。毋宁说,它与另一个“时刻”共存,这个时刻同等重要,它源自于“非经济”规范之来源的社会、政治及生态表征。这意味着,尽管这些“非经济的”秩序使得商品生产成为可能,它们却不能被归结于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此外,这些“非经济的”理念中孕育着批判政治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它们能够用以反对与资本主义积累相连的核心的经济实践。在这样的时刻,在其各个制度性领域中隔离各种不同规范的结构性划分趋向于减弱。当这种隔离无法保持,资本主义的主体将经历规范性的冲突。他们会利用资本主义自身复杂的规范性来批判资本主义,而非从“外部”引入什么理念,他们反对不稳定地共存于一个以台前幕后划分为前提的制度化社会秩序之中的多重性理念。由此,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制度化社会秩序有助于我们理解从资本主义内部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然而,这种观点也暗示着将社会、政治以及自然浪漫地解释为“外在于”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固有的反对都是错误的。这种浪漫主义视角如今被相当多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以及左翼活动人士所坚持,包括女性主义者、生态学家以及新无政府主义者,也被许多“多元”“后增长”“休戚相关”以及“大众的”经济的支持者所坚持。这些潮流过于频繁地将“关怀”“自然”“直接行动”或“共同性”视为在本质上反资本主义的。他们忽略了如下事实:他们最喜欢的实践不仅是批判的来源,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秩序不可或缺的部分。毋宁说,社会、政治以及自然与经济同时出现并在与经济的共生中得到发展。它们实际上是后者的“他者”,并且只是在与后者的对比中才获得其独有的特征。因此,再生产和生产配成一组概念,每个概念都凭借作为对方的他者来定义,离开对方,自己也就毫无意义。政治/经济、自然/人也是如此。作为资本主义秩序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哪个“非经济”领域能够提供一个全然外部的、绝对纯粹、全然激进的批判形式的立足点。相反,诉诸被设想处于资本主义“外围”的政治计划通常以重复资本主义的陈规而告终,因为它们还是将女性的养成与男性的攻击性、自发的合作与经济核算、自然的整体有机主义与人类中心的个体主义相对立。在这些对立的基础上引出斗争并不算是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化的社会秩序,而是于不知不觉间反映着这样一种社会秩序。 从上文可以推断出,一种恰当的资本主义台前一幕后之关系的论述必定将三个各不相同的理念结合在一起。第一,资本主义的“非经济”领域作为背景条件使经济成为可能,后者的存在恰恰取决于从前者而来的价值和投入。第二,资本主义的“非经济”领域具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和特征,它们能够在某种情况下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资源。第三,这些领域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历史地与经济同构的领域,而且打上了与经济领域共生的显著印记。 还有第四点,这一点将我们带回我开始提到的危机问题。资本主义台前—幕后的关系隐匿了社会不稳定的内生性源头。正如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自足的,而是搭了社会再生产、自然和政治权力的便车,而且其追求无止境积累的倾向威胁到这些条件的稳定性。就其生态条件而言,维持人类生活以及为社会供应提供物质输入的自然过程处于危险境地。就其社会再生产条件而言,为社会合作提供基础的团结一致的关系、精神气质、价值观,以及为造就恰当社会化并掌握熟练技能的“劳动力”提供基础的社会文化过程处于危险之中。就其政治条件而言,被妥协掉的是保障财产权、执行契约、裁定争端、平息反资本主义的叛乱以及维持货币供应的公共权力,不论是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 这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三种“资本主义的矛盾”,生态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对应三种“危机倾向”。不过,与马克思所强调的危机倾向不同,这些危机的来源并非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毋宁说,这些危机植根于经济体制与其背景性条件之间的矛盾——经济和社会之间、经济和自然之间、经济和政治之间。(14)如前所述,这些危机的影响就是激起资本主义社会中范围广泛的社会斗争:不仅有位于生产这个中心点的阶级斗争,而且有围绕生态、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的边界斗争。相对于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倾向,这些斗争对于将资本主义视为制度化的社会秩序的扩展性观点而言是特有的。 从上文描绘的概念出发能够引出何种资本主义批判呢?将资本主义视为制度化的社会秩序的观点需要多重形式的批判性反思,很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发展的批判。根据我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交织了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倾向的系统批判,对其内置的(阶级)统治动力学的规范性批判,以及对内生于其(阶级)斗争典型形式之中的解放性社会变革之潜能的政治批判。系统性危机的批判不仅包括马克思所讨论的经济矛盾,而且还包括我这里所讨论的三种领域间的矛盾,通过危害社会再生产、生态以及政治权力,这三种领域间的矛盾破坏着资本积累之必要背景条件的稳定性。同样,主导性的批判不仅包括马克思所分析的阶级主导关系,而且包括性别主导关系、政治主导关系以及对自然的主导。最后,政治批判包括多重主体——阶级、性别、身份群体、国家、人民(demoi),甚至可能还有物种——以及多种斗争:不仅有阶级斗争,还有基于社会、政治、自然与经济之分离的边界斗争。 因此,被视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远比马克思传统意义上所假定的斗争要宽泛得多。一旦看到台前故事背后的幕后故事,我们会发现,劳动剥削的所有不可或缺的背景性条件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冲突焦点。不只是位于生产之中的劳资双方之间的斗争,而且还有基于性别支配、生态、帝国主义、民主的边界斗争。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后者目前呈现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斗争、围绕资本主义自身的斗争,以及某些情况下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斗争。 原文题为“Behind Marx's Hidden Abode:For an Expanded Conception of Capitalism”,刊登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2014年第86期,第55~72页。 注释: ①这些观点是在与拉埃尔·杰吉(Rahel Jaeggi)的交谈中形成的,而且将呈现在我们的《危机、批判、资本主义》(Crisis,Critique,Capitalism)一书中,该书即将由Polity出版社出版。感谢布莱尔·泰勒(Blair Taylor)在研究方面的协助,感谢剑桥性别研究中心(Centre for Gender Studies,Cambridge)、全球研究所(Collège d'études mondiales)、人文科学研究会(Forschungskolleg Humanwissenschaften)、“正义”高级研究中心(Justitia Amplificata)的支持。 ②Immanuel Wallerstein,Historical Capitalism,London,1983,p.39. ③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New York,2002; Nancy Fraser,Can Society Be Commodities All the Way Down? Economy and Society,Vol.43,2014. ④Karl Marx,Capital,Vol.I,London,1976,pp.873-876. ⑤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2003,pp.137-182. ⑥Karl Marx,Capital,Vol.Ⅲ,New York,1981,pp.949-950; 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5,No.2,September 1996. ⑦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Socialist Review,Vol.80,1985. ⑧Geoffrey Ingham,The Nature of Money,Cambridge,2004; David Graeber,Debt:The First 5000 Years,New York,2011. ⑨Ellen Meiksins Wood,Empire of Capital,London and New York,2003. ⑩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London and New York,1994. (11)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London,1971. (12)Sara Ruddick,Maternal Thinking:Towards a Politics of Peace,London 1990; Joan Trento,Moral Boundaries: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New York,1993. (13)Nancy Fraser,Struggle over Needs:Outline of a Socialist-Feminist Critical Theory of Late-Capitalist Political Culture,in Fraser,Unruly Practices:Power,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Minneapolis and London,1989. (14)See James O'Connor,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1,No.1,1988,pp.1-22.标签: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