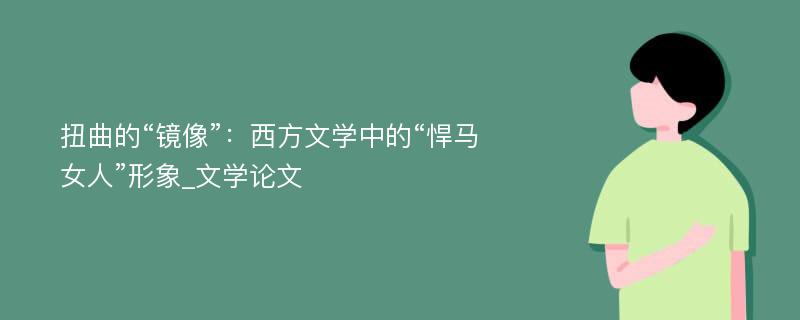
扭曲的“镜像”——西方文学中的“悍妇”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悍妇论文,镜像论文,形象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悍妇”,古今中外均有不少轶闻掌故流传。在中国,最知名的要算是宋代的“河东狮吼”故事。而在西方,声名赫赫的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家有悍妻,恐也无人不晓。“悍妇”,这一令人闻之色变的不雅之称,很早即进入了文学作品,成为标举女性品格、地位及社会意义的重要文学个性,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学景观。我们注意到:大凡可归入泼辣、凶悍一类的“悍妇”型文学个性,均是男性作家笔下的造物。而女作家以同等理由指斥同胞姐妹的现象则极为鲜见。在19世纪英国妇女文学的黄金时代,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等的笔下可以出现一系列自强不息、桀骜不驯甚至惊世骇俗的主人公,但她们和“悍妇”的指称是毫不沾边的。可见,性别的差异甚至对峙,确实是造就不同文学个性的重要因素。“悍妇”形象,是男权文化思维一手捏造出来的。
一、寻找“悍妇”的原型
在西方文学史上,“悍妇”文学类型可谓源远流长。“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在其著名的三部曲《奥瑞斯提亚》中,塑造了一个具有强悍的个性与魔鬼般意志的女性——迈锡尼王后克吕泰美斯特拉的形象。在三部曲的第一部《阿伽门农》中,她暗藏杀机,却花言巧语地迎接丈夫的凯旋。在引导他走向地狱之门的过程中,她始终泰然自若,雍容自处。亲手刺杀了丈夫之后,她手执利剑,昂然立于阿伽门农和卡珊德拉尸体的血泊中,冷眼笑对长老们的叱骂。在第二部《奠酒人》中,奥瑞斯提亚为父复仇,克吕泰美斯特拉的第一个冲动便是和儿子较量武器。当儿子的利剑直逼她的前胸,她有胆量袒露胸口说:“孩子,看你曾在这里睡过,你吮着我的乳头哪!”第三部《福灵》中,她的幽灵从地狱一跃而起,厉声呼唤复仇女神向儿子讨还血债!这位无所畏惧的女人,是埃斯库罗斯最精彩的杰作之一。但就其道德品格而言,克吕泰美斯特拉自古迄今是被否定的,原因即是她弑君篡权、谋杀亲夫!因此,克吕泰美斯特拉堪称西方文学文本中最早的“悍妇”原型。另一出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具有近似的品格内涵:美狄亚为了帮助爱人伊阿宋获得金羊毛,不惜残杀并肢解了自己的亲兄弟;她又煽动珀利阿斯的女儿们将父亲碎尸万段,放在锅里烹煮,以泄伊阿宋心头之愤。当伊阿宋别有新欢,意欲抛弃她时,她用巫术烧死新娘及其父亲,还亲手害死自己的一双爱子,以达到让伊阿宋绝嗣的目的。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使美狄亚成了魔女的化身。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同样亦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女人。麦克白夫人的野心比丈夫更甚,心肠比丈夫更狠,在使丈夫从国家的功臣堕落为血腥的弑君僭主的过程中,麦克白夫人的邪恶怂恿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在此列举的,是西方文学早期三位著名的“反面”女性典型。她们的身份、个性、遭际不尽相同,但在下列方面无疑是相似的:即都工于心计、强悍无畏、残忍狂暴,有强烈的报复欲,是对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的、具有毁灭性的力量。通过与西方文学肇始时期其它女性文学类型的比较,我们发现,她们的社会学意义是异曲同工的。作为欧洲社会进入父权制时代之后的产物,她们均体现了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是男权文化为女性提供的“镜像”:以希腊美人海伦为代表的“倾国”、“倾城”型女性,概括了长久以来女性作为男性渔猎对象的历史地位,并反映了男性对“女祸”的恐惧;《荷马史诗》中那忠贞无二、苦苦等候远游的丈夫的珀涅罗珀,则是男权文化为了维护私有财产的神圣,确保子嗣血统的纯正为女性树立的道德楷模;而以克吕泰美斯特拉、美狄亚、麦克白夫人为代表的“悍妇”形象,则是珀涅罗珀这类家庭天使的另一极,代表了男权文化对胆敢逾越尊卑常轨,试图颠覆主流文化的异己势力的贬斥、压制与打击。假若男权文化关于“笔”是“阴茎”的隐喻能够成立的话,在女性作为受压迫的群体潜入历史地表,患了“失语症”之后,“悍妇”便成了男性话语独霸的必然产物。
二、“悍妇”的文化生成
“悍妇”文学类型,可谓自塑与他塑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女性的自塑而言,“悍”,成了表现女性在江山失落后,对屈辱的历史地位进行抗争的手段。克吕泰美斯特拉生活的时代,希腊的母权制已日渐失落其昔日的辉煌。黑格尔曾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父权制因其“合理”的因素,正逐渐走向“现实”。《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曲终处,雅典的长老法庭判奥瑞斯提亚为父复仇杀母无罪。父系神阿波罗在法庭中对复仇女神是这样抗辩的:“母亲决不是生产她的所谓‘世系’,而不过是抚育新播的种子;父亲才是生父,养育出新的芽苗,……”(注:《奥瑞斯提亚·福灵》灵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20页。)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三部曲的社会历史意义:“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7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因此,家庭复仇故事的表象下,实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性政治冲突,而女性遭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恩格斯语)。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克吕泰美斯特拉的行为,是预感自己的性别“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后的一次垂死挣扎。为了挽救女性日后数千年被压迫的屈辱命运,她甚至不惜采取了“杀夫”的极端手段。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克吕泰美斯特拉当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同样建立于性别压迫基础上的母权社会也决然不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结构模式,但我们不能不叹服于她无所畏惧的挑战精神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绝望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克吕泰美斯特拉堪称是希腊母权大厦颓然轰塌之际最后的一位斗士。
如果说克吕泰美斯特拉母狮的余威犹在,美狄亚的命运则展示了女性已被打翻在地的严酷现实。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期间,希腊经过土地立法,私有财产的发展使家庭制度巩固下来,婚姻制度逐渐固定为一夫一妻制。但这种婚姻制度只单向对妇女发生约束。雅典妇女必须严守贞操,甚至被禁锢于闺阁中,不得参予公共生活,更享受不到政治权利。而男子则可以有外室而不受法律或道德的束缚。欧里庇得斯虽然是以擅长妇女题材并同情妇女而著称的,他的悲剧《阿尔刻提斯》却同样强调了单方面的“妇德”:斐赖城国王阿德墨托斯命中注定要短命而死,包括父母在内的亲人无一人愿当替身,唯有妻子阿尔刻提斯自愿替死。在这一要求妇女作无条件牺牲的文化背景下,美狄亚的处境是艰难的:伊阿宋为了财富和权势可以别有新欢抛妻弃子,社会却要求美狄亚忍气吞声甚至强作欢颜。但来自野蛮国度、较少受希腊文明濡染的她起而抗争了。她的对手不仅是伊阿宋,更是他身后那个压迫妇女的男权社会,这就注定了她的抗争是一场力量悬殊、结局注定的悲剧,由于无法倚靠社会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美狄亚的反抗是一种孤军奋战,具有孤注一掷的性质,采取的是绝望的甚至变态的复仇手段。她以扼杀爱子的自虐行为试图达到报复伊阿宋的目的,代价是惨重的。因此,无论是克吕泰美斯特拉还是美狄亚的残忍狂暴和破坏欲,都是在不公正的社会压迫下爆发出来的一种过激反应,是在别无选择的两难中疯狂而绝望的行为,她们擎起的是一面“逼上梁山的旗帜”。(注:语出彭兆荣文《“被缚的妻子们”——古希腊文学中女性性格的分离与原型辐射》,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同时,笔者所说的他塑,指的是男权社会对这种威慑与解构社会秩序的异己充满了戒备和敌视,因此利用话语霸权给她们扣上了泼辣、凶悍、阴鸷、充满危险性等等帽子,捏出了“悍妇”文学“镜像”,供人们借鉴。其实,正如苏珊·格里芬一语道破的:“男人害怕面对女人的肉体时失去对女人和自己的控制,所以他们抗拒女人的形象。或者将女人视作物,玷污或损害她的肉体,将她毁灭,或者将她塑造为邪恶的化身和毁灭的根源加以防范。”(注:苏珊·格里芬:《自然女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页。)耐人寻味的是:中西男权文化不约而同地将这类不受欢迎的女人称为“狮”。中国宋代苏轼诗中谑道:“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明代梅鼎祚《玉合记·砥节》中亦有“吼动河东狮子,惊回海底鸥儿”之语。《美狄亚》一剧中,伊阿宋称美狄亚为“可恶的,凶杀的牝狮”。在入赘王宫的美梦被美狄亚粉碎后,他更是气急败坏地骂道:“我所娶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只牝狮,天性比堤耳塞尼亚的斯库拉更残忍!”(注:《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美狄亚》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6页。)所以,“悍妇”文学个性是男权文化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在对妇女实施教化的过程中他塑而形成的一个反面典型,这和忠贞温驯的珀涅罗珀们,起到一个殊途同归的作用。但对“家庭天使”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文献记载,远游了20年归来的奥德修在确认了对财产(包括王位和妻子珀涅罗珀)的所有权后,又弃家而去了。关于他塑,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由于女性被逼到了文化的边缘,遂与同样被逐出正统文化圈外的妖魔鬼怪产生了认同,因此,“悍妇”们往往沾上了鬼气或歪气。不是和巫术有关,就是与鬼魅为伍。现存文本中,男性被视作“巫”或“妖”的极少,而这些几乎成了女性的“专利”。克吕泰美斯特拉被形容成“阴险的诱惑神”、“可恨妖精”、“两头蛇”、“狂暴的母夜叉”;美狄亚是一个标准的女巫,会妖术和魔法;《麦克白》中,荒野上那形容枯槁、奇形怪状、不男不女的三个女巫,正是麦克白夫人蛰伏的野心的形象外化。至于童话中面目可憎的“巫婆”形象,更是比比皆是。这些女巫,被剥夺了女性一切美好的特征。概括起来说,以“女巫”和“天使”为两极的“镜像”,浓缩了西方男权传统文化的女性观。
三、“悍妇”的历史延伸
“悍妇”这一在西方文学肇始期便形成的文学品格,作为一种基本原型,深深影响了后代的女性形象塑造。在男权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她们虽有衍生和变形,但其中透出的基本价值取向则是一致的。
18世纪号称英国小说之父的笛福,在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海外历险张目,创造出原始积累时代的高尚英雄鲁滨逊的同时,笔下也出现了欲与男性争一杯羹的奇女子摩尔·弗兰德斯的形象。表面上看,《摩尔·弗兰德斯》是一部女性视角的自陈式作品,但其道德内涵依然经过了真正的男性作者的检查与过滤,这就使作品依旧框定在男性教化者的霸权话语中。(注:可参王亦蛮文《对抗与包涵——论十八世纪英国妇女的价值观》,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3期。)体现在文本中的女主人公具有情人、小偷、妓女、老鸨、骗子、女强人等多重身份。小说冗长的副标题构成了她传奇生涯的一个梗概:“她生于伦敦纽盖特监狱中。一生命途多舛,60年中,成人后12年过娼妓生活,5次嫁人(其中一个和她异父同母),当小偷12年,因罪流放美洲吉尼亚8年,晚年致富,为人正直,临终对自己罪愆表示忏悔。”这和清教主义时代男权文化对女性勤劳克制、贞洁自守的企盼是多么的天差地别啊!摩尔因自己的离经叛道和诡计多端,确立了自己在英国清教时代的“悍妇”地位。笛福塑造她,无疑是为当时的正经妇女们现身说法的,无怪他安排了他的女主人公晚年的“忏悔”,以自我的清隐为代价,达到了和主流文化的和解。
进入19世纪,在个人奋斗成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时,凭借自己的妖媚外表,以性作手段,在男人的世界里兴风作浪的女冒险家更是比比皆是。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名利场》中的蓓基·夏泼,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这位长袖善舞的女子,在名利场中道貌岸然的上流绅士们面前,无往而不胜。哈钦森出版公司英文版《英文小说》第一卷引言中这样评价道:“她不屈服于家庭女教师的奴隶地位,而蒙受耻辱。不择手段,有意识地运用男人为武器,再加上自身的天然财富——性,到处卖弄风情,在男人的世界里掀起狂风恶浪。”(注:阿莫尔德、凯特尔:《〈英文小说〉第一卷引言》,哈钦森出版公司1977年,第153页。)我们看到,这里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均采取了一种典型的男性立场。同样的类型还有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贝姨》)、德莱塞笔下的嘉莉妹妹(《嘉莉妹妹》),以及20世纪法国作家让·莫里亚克《黛莱丝·德斯盖鲁》中的同名主人公。尽管作家们对她们被损害、被欺骗的遭际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揭示了她们被禁锢的欲望和被剥夺的话语,然而,还是将她们处理成颠覆者的形象,具有不同程度的“悍”性:贝姨阴险恶毒,工于心计,黛莱丝更是因“杀夫”被推上了法庭。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使我们不禁想起了以自己的身躯为母权制祭旗的克吕泰美斯特拉。这些自不量力的女人们,如飞蛾扑火,在这场亘古至今而又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充当着性别压迫的历史见证。
四、《驯悍记》——父权文化心态的佐证
在这场“性政治斗争”中,父权心态在莎士比亚早期喜剧《驯悍记》中,得到了鲜明的凸现。这出轻喜剧显然是具有男权文化的霸气的。霸气就霸气在把溅在受难妇女斑斑血泪的悲剧处理成一出得意洋洋的喜剧。绅士巴普提斯塔之女凯瑟丽娜不惟“长得又难看”,而且“脾气非常之坏,撒起泼来,谁也吃她不消”,男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葛莱米奥老爹说他:“宁愿每天给人绑在柱子上抽一顿鞭子,作为娶她回去的交换条件。”霍坦西奥说:“即使我是个身无立锥之地的穷光蛋,她愿意贴一座金矿给我,我也要敬谢不敏的。”但凯瑟丽娜最终还是被新婚的丈夫彼特鲁乔驯服了。这位绅士声称:“我是天生下来要把你降伏的,我要把你从一个野性的凯德变成一个柔顺听话的贤妻良母”,他对她施以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虐待,依据的正是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总结的“金科玉律”:“好娘子,坏娘子,都需要一根木棍子。”令人费解的是身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薄伽丘,在呼唤人性解放的同时,却又宣扬了这样一条血腥的法律。凯瑟丽娜收敛起她的锐气和傲气,归入到低眉顺眼的“贤妻”行列之中。不仅如此,“归队”了的她还向其他女人现身说法:“一个女人对待她的丈夫,应当像臣子对待君王一样忠心恭顺;倘使她倔强使性,乖张暴戾,不服从他正当的愿望,那么她岂不是一个大逆不道,忘恩负义的叛徒?”又一位有棱角有锋芒的女性在挥舞的大棒下沉默了。因为她别无选择,她不可能做出走的娜拉。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曾虚构了莎士比亚出走的“妹妹”的凄惨结局。(注: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第三章,王还译,三联书店1992年。)即便是19世纪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在社会尚未为妇女的真正解放提供条件的前提下,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向“傀儡之家”妥协。凯瑟丽娜的被驯服,体现了一个僭越的女人被强行纳入父权轨道的心路历程。作为男权文化代言人的莎士比亚,通过这个虚构的御妻故事,再次扬起了得胜的大旗。然而,19世纪末,英国戏剧大师肖伯纳毫不掩饰他的反感,气愤地说道:正派的男人陪着女伴看这戏,简直要羞愧得无地自容。(注:转引自方平先生《历史上的“驯悍文学”和舞台上的〈驯悍记〉》,载《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五、结论与思考
概括起来说,后代西方女性文学品格在文化摇篮的希腊已能找到端倪。无论是以克吕泰美斯特拉、美狄亚等为代表的“悍妇”或“女巫”,以珀涅罗珀等为代表的家庭天使,或是以潘多拉、海伦为代表的“尤物”、“祸水”,均是欧洲社会进入父权制时代之后的产物,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希冀和篡改。它们是不能代表女性在本真意义上的情感和欲望的。我们透视“悍妇”文学类型在文学史上的虚假镜像,就是为了从性别视角重审女性在男权传统文化中的角色意义,使女性从扭曲、割裂的人格中走出来,重新整合为不再是道德符号,而是具有真正意义的自我。那么,自我何在?能否说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能代表真实的女性自我呢?事实上,在长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代代承袭、潜移默化的背景下,女性作家很难完全突破男权价值判断的框架。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另文中有进一步的阐发,因不是本文重点,恕不作深入展开。而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作家在创作中,也势必会受到来自于主流话语、传统批评尺度、自我心理乃至语言手段的缺乏诸方面的束缚而陷入困境之中。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人性阐扬,还有赖于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伴之而来的男女两性的进一步理解、尊重和合作。只有在充分尊重男女独立人格的基础上扬弃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偏见,才能完善和发展健康的人性,建立一种双性文化,从而达到“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注:李小江语。转引自刘慧英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5年,第215页。)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到了那样的阶段,“悍妇”文学现象将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