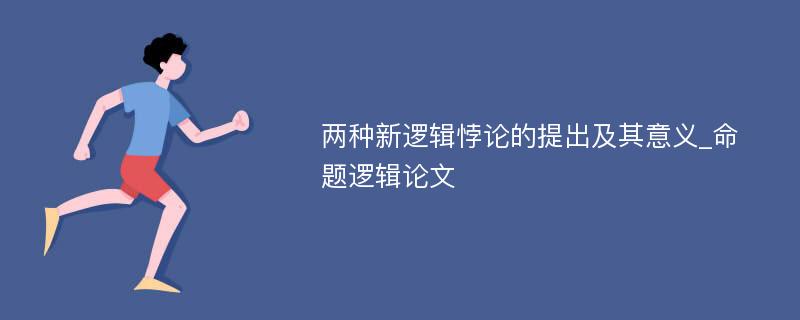
两类新型逻辑悖论的提出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两类论文,逻辑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类新型逻辑悖论即认知悖论与合理行为悖论的发现和研究,是当代西方逻辑悖论研究中的重要进展。但从近期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讨论文章看,国内学界对此尚缺乏了解和重视。本文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简要述介,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探讨。
大家知道,尽管说谎者悖论出现于古代,中世纪逻辑学者也已研究了它的许多非直接自指式变体,但我们所知道的多数语义悖论,如著名的理查德悖论、格里灵悖论、贝里悖论以及它们的各种变体,都是在集合论悖论出现以后于本世纪初年陆续提出的,它们的出现表明诸如“指称”、“描述”、“满足”、“可定义”等基本的语义学概念同样存在说谎者悖论向“真理”概念提出的问题,这对推动悖论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对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等一系列新成果的获得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然而,由于解决说谎者悖论的各种方案均可自然推广到其他语义悖论,人们在一段时间里对构造新的语义悖论不抱热情。直到40年末期英国MIND杂志开展有关“知道疑难”的讨论,人们才开始关心能否为在认识上与“真理”概念平行的“知识”概念建构悖论的问题。经过反复研讨,终于使这种疑难经美国著名学者蒙塔古和卡普兰(D.Kaplan)之手而改造成为一个严格的货真价实的逻辑悖论,并由此进一步构造出一个与说谎者语句类似的语句K:“某认知主体(知道者)知道K是假的”,由它在三个明显合理的假定之下,能以与建构说谎者悖论同样的严格性建构一个“知道者悖论”。这三个合理假定为:(1)凡被知道者知道的东西都是真的。(请注意区分“真知道”和“伪知道”)。(2)知道者知道(1)。(3)如果知道者知道A,而他又由A合乎逻辑地推出了B,则他知道B。蒙塔古和卡普兰指出,这三个假定在严格构造的知道者悖论中的地位,就相当于塔尔斯基的(T)型等价式在严格构造的说谎者悖论中的地位。知道者悖论所依赖的直觉和逻辑两方面的力量,都不亚于说谎者悖论。[①][②]
知道者悖论所涉及的问题显然超出了语义学领域,因为它本质地使用了“知道”这样的命题态度概念(拒斥“命题态度”这一概念的学者通常称之为“认知态度”、“心理态度”或“态度”)。但由于其所依赖的合理假定(1)的存在,许多人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去解决说谎者悖论对“真理”概念提出的疑难,并认为知道者悖论未必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蒙塔古本人开出的药方是,“知道”与真势模态词一样,不能处理为语句谓词,而必须处理为语句形成算子,这种观点与克里普克建立的新型可能世界语义学恰好合拍,由此他致力于一般内涵逻辑的建构,而未再深入探讨悖论问题。直到克里普克的文章掀起悖论研究的新热潮之后,关于命题态度的悖论才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许多学者指出,把真势模态词作为语句形成算子确是合乎人们的日常直觉的,但“知道”这样的命题态度词并非如此。在自然语言中,它们通常都是作为语句谓词来使用的。而且人们发现,若只把它们视为语句形成算子,则有两种可能情况:若不允许命题量化,就使得某些在自然语言中显然要表达的东西(如“甲知道乙知道的某些事情”,“丙承诺了某团体中其他人都不承诺的东西”等等),成为不可表达的;而如果允许命题量化,则悖论仍可循严格的逻辑途径得出。至于命题态度悖论之独立研究价值问题,则可以由“相信者悖论”说明。“相信”并不是如“知道”那样的“事实性命题态度”,相信者相信P并不蕴涵P为真。然而仿照知道者语句构造一个语句B:“相信不相信B”。在某些明显合理的假定之下,同样可以严格地建构B与非B互推的矛盾等价式。相信者悖论的严格刻划1978年由美国哲学家伯奇(T.Burge)公之于世。它的提出有力地说明了研究有关命题态度的悖论的必要性,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关于其他各种命题态度(如“认为”“期望”“猜测”“承诺”等)的悖论被纷纷构造出来(有些悖论的构造需要如克里普克所说的那样诉诸经验事实的风险性),并展开了各种哲学的或形式技术的讨论,使之成为悖论研究的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
关于命题态度的悖论的构造均不能脱离语义概念,故按照人们所熟悉的莱姆塞型二分法(即把逻辑悖论分为集合论—语形悖论和语义悖论),自然应归入语义悖论。但有鉴于命题态度概念本质地引入了“认知主体”因素,有人早在MIND讨论知道疑难时就建议称之为“语用悖论”。或许由于在语用学与语义学相互关系上存在一些针锋相对的争议,这个称谓没有流传开来。“认知悖论”的称谓是伯奇提出来,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笔者亦曾撰文认为:“把关于命题态度的悖论统称为认知悖论是恰当的,它不仅有利于与(本质上不涉及认知主体的)语义概念相区别,而且可以体现其与认知逻辑的密切关联”。
合理行为悖论是一种最新型的逻辑悖论,迄今在国内学界尚未见到任何反映。我们这里陈述其最简单同时又是最基本的例子:
甲向乙提出:乙可以选择盒子A(它是空的)或盒子B(它有1000元),但不能两者都选。甲保证:如果乙就此作出一个不合理的选择,他将给予10000元奖励。那么乙应如何选择呢?如果我们假定乙取盒子A是不合理的,则取A将使乙比取B多得9000元,从而使得取A成为合理的行为;反之,如果我们假定取A是合理的选择,则取A将至少比取B少得1000元,所以取A终究又是不合理的。从而有:乙取A是合理的,当且仅当乙取A是不合理的。
这是美国学者孔斯(R.C.Koons)于1992年出版的《信念悖论与策略合理性》一书的导言中所表述的一个悖论,对该悖论的研究构成他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孔斯指出,使这个“故事”可以构成一个严格悖论的条件,除了假定甲和乙都是理想的理性人且甲总能遵守其诺言并且这两点构成甲和乙的共识之外,尚需如下四个合理假定:(1)可辩护的语句集合,相对于任一认知情形而言,至少在终极意义上均是演绎封闭的。(2)所有算术定理都是可辩护的。(3)已证明的东西在任何认知情形下都是可辩护的。(4)如果某种东西不可辩护是可辩护的,则它就不是可辩护的。其中所谓某种东西是“可辩护的”,是指支持它的证据强于与它不相容的任何证据。这样,当我们说“乙取盒子A是合理的”时,其意即为对乙来说取盒子A是最合适的(即具有最大期望效益)这一点是可辩护的。孔斯在书中给出了四条合理假定的形式刻画,由此严格地导出了上面以自然语言陈述的矛盾等价式。
由于该悖论的一个完整变体最早由以色列学者盖夫曼(H.Gaifman)于1983年发表,故孔斯称之为“盖夫曼悖论”,又由于它明显由纽科姆疑难(1969年由物理学家纽科姆(Newcomb)提出,在对策论基本理论领域已被热烈地讨论了多年)改造而来,也有人称之为“纽科姆—盖夫曼悖论”。孔斯强调指出,盖夫曼悖论决不是一个人为地刻意制造出来的东西,有许多非常类似于该悖论情景的迄今仍未解决的难题,一再出现于当代对策论和对策论经济学研究之中。他举出了著名的“囚徒疑难对策的有穷系列问题”,“塞尔登连锁店疑难”等例子,并说明盖夫曼悖论为阐明这些难题的本质特征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没有这个悖论的发现,这些问题都仍将会分别地而且在一种不可避免地特设的形式上处理”[③]。正是基于对盖夫曼悖论的细致解剖,孔斯把这些疑难分别地造成了一些严格意义的悖论,从而形成了可以和语义悖论、认知悖论相并列的一个新的逻辑悖论群落。
居于这个新的悖论群落的核心位置的“合理性”概念,显然是相对于认知主体的“行为”而不是相对于语言或命题的。为区别起见,孔斯把这些悖论统称为“置信悖论”(Doxic Paradox)并与认知悖论并列使用。我认为,这个名称难以表征这个悖论群落的特点。受英国学者森斯伯里(R.M.Sainsbury)用“合理行为问题”概括纽科姆疑难和囚徒疑难[④]的启发,我主张将这组悖论直呼为“合理行为悖论”。
两类新型悖论的发现对于哲学逻辑(尤其是认知逻辑和行动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其价值又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些新悖论的发现提供了检验以往各种解决悖论方案的新的试金石。若一种方案也能够同时解决两类新型悖论,说明其具有较强的相对合理性,自然比只能解决语义悖论的方案占居优势。孔斯在其著作中对此作了详细的比较分析,指出一系列语境迟钝方案对某些认知悖论和所有合理行为悖论无能为力,而新兴的语境敏感方案面对新悖论却游韧有余,这个结果确立了语境敏感方案的地位。从而强化了回归自然语言,在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中研究悖论问题的大趋势。
其次,新型悖论的发现进一步显示了悖论研究的哲学价值。对于集合论悖论和语义悖论,笔者曾经试图自然而严格地说明它们与辩证真理观的对应关联。[⑤]新型悖论的发现,显然又可与辩证知识观、辩证信念观、辩证行为观等建立对应关联,从而可以构成与辩证哲学某些基本范畴相对应的链条。显然,基于这种对应关联的辩证分析,可为统一把握各种不同类型的逻辑悖论提供一条重要途径,而反过来,对这个悖论链条的探讨无疑有益于当代辩证哲学与辩证逻辑研究的发展和深化。
再次,新型悖论的发展更加凸显出悖论研究的应用价值。由克里普克倡导的回归自然语言的逻辑悖论研究,无疑会引起以自然语言理解为重要内容的人工智能理论界的兴趣,而认知悖论探讨又与知识处理等前沿理论问题相关,因而备受重视。一个重要的象征是,从1986年开始,美国IBM Almaden研究中心每隔两年召开一次有多种不同领域专家参加的“关于知识的推理”大型研讨会,认知悖论一直在会议话题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笔者看到的三次会议论文集中,许多长期致力于逻辑悖论研究的学者都在会议上发表了有关成果。合理性行为悖论所触及的“策略合理性”概念,是当代对策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与出现于对策论经济学和其他有关社会科学学科之中的“理性经济人”(或“理性政治人”等等)模型的研究本质相关。“这种理论或合理性模型的初步运用,是在给定有关局中人的适当的证据及价值、目标、需要等信息的情况下,预测局中人的选择和行为。这无疑使得悖论研究成果的应用又进入了一个广阔的领域。
最后,两类新悖论的发现历程,表明了人们在悖论观上的历史性进步。本世纪初年集合论悖论不期而至,人们惊呼数学基础乃至整个数学大厦的危机。而现在,新型悖论是人们千方百计地去发现、去建构的,人们普遍把一个新型的严格悖论的发现看作件好事,认为它往往预示着一种新思想的诞生。有些学者甚至把发现新悖论作为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伯奇曾就此总结道:“悖论应视为弄清我们的语言和概念的深层精妙特性的手段,而不应看作它们的矛盾或不相容的病状。至于有些悖论尚未能解决,它们不过是我们关于语言和概念的假定中混乱或错误的病状。正因为这些假定看上去是明显合理的,这些悖论便成为理论启发的一个源泉”。[⑥]这样的认识已为众多学者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