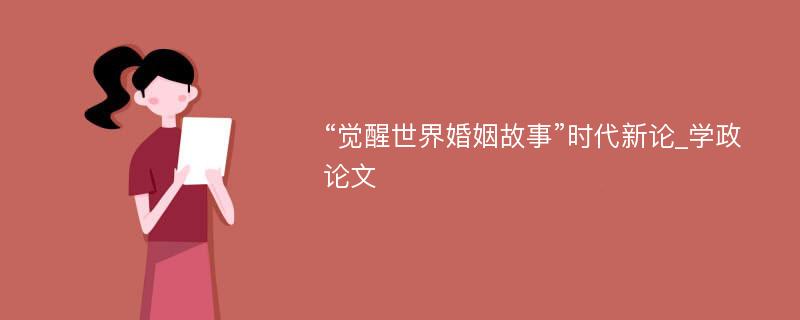
《醒世姻缘传》成书年代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书论文,姻缘论文,年代论文,醒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51(2004)02-0088-05
在我们把《醒世姻缘传》(以下称《醒》)的成书年代推至雍正四年后之前,先要确定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研究的立足点应该是在“清代说”的基础上。有些学者提出了“明代说“,尤其是“崇祯说”,其实用以论证的根据都是模糊和不确定的。比如“除夕雷雨”、“内官儿”等,关于自然灾害,雍正三年后的山东地区有很多旱涝大灾与书中所说相符,而且既然我们可以证明该书是雍正后所作,那么它完全可以记叙之前任何朝代发生的事件,实在不足以证明什么。即使有人指出作者所叙事件离他生活的年代太远,不是亲历之事,但就如蔡义江先生论《红楼梦》是曹雪芹写他祖辈的事一样,虽然没有经历,但完全可以是“道听途说”,根据祖辈人的记录或口述加工而成,所以灾害与事件并不是唯一可靠的证据。
曹大为先生曾在《〈醒世姻缘传〉作于明末辨》一文中说:“除非从这近百万字的篇幅中哪怕找出一条为清代,……特有的名物、事典、服饰、风俗,否则就无法动摇基本成书于明末的结论。”以下就试论证出现在清代的此类事物。
一、廪生保结
《醒》第三十七回,县里考试:
“薛如卞入籍不久,童生中要攻他冒籍,势甚汹汹。程乐宇的妻兄连单人,叫是连才,常到程乐宇书房,看得薛如卞清秀聪明,甚有爱敬之意,家中有一个小他两岁的女儿,久要许他为妇,也只恐他家去,所以不曾开口,只背后与程乐宇说了几遭。这连春元的儿子连城壁,是县学廪生,程乐宇将这几个徒弟托他出保;……(程乐宇说)“外边攻冒籍的甚紧,连赵完又不肯出保的意思,我再三央他,你可将这结状送到他家。”薛如卞拿了结状走到连家,门上人通报了,……薛如卞有了这等茁实的保结,那些千百年取不中的老童,也便不敢攻讦。”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中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冒籍现象。所谓“冒籍”,即不是本县人而冒充本县来参加考试。因为每县学校每次考试录取人数各有定额,而投考的童生各县多寡不等,额少人多者录取难,额多人少者录取易。故额少人多处之童生,往往跑到额多人少的县参加考试,以期易于录取。若外籍人多录取一名,本籍人就少录取一名,这对本籍人不利,故为定例所不许。清代乡试中廪生的保结非常重要,廪生所保的内容之一就是“冒籍”问题。若有廪保卖情,或受贿而保送非本籍人应考者,准考生或他人检举揭发,证实后廪保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称为“攻冒籍”。《醒》中薛如卞参加县试时就是因为被人“攻冒籍”,怕考不成,才去求自己老师的外甥出保。清代县、府、院、乡各考试都要有廪生保结,明代却没有此制。
比较明清两代科场弊端及其改革可以明显的看出,虽然两朝都为科考中长期存在的冒籍案所困,但明代除了对已发生的冒籍事件进行善后性的惩戒工作外,并没有出台具体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致使明成祖以降冒籍案频出,以至愈演愈烈。如《万历野获编》[1]卷14《科场》举景泰、成化、嘉靖、万历各朝冒籍现象,但除“发回原籍”“不许今科入试”和严惩执政官的亡羊补牢之法外,并未提及预防措施如保结一事,更没有廪生保结之说。
又有《弇山堂别集》[2]卷82《科试考二》:
“(景泰四年)礼部祠祭司主事周骙之奏:‘……今顺天府景泰四年乡试取中举人尹成、汪谐、陈益、龚汇……,俱系冒籍人数,于例不该入试。似此之徒,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乞明正其罪,以警将来’。命锦衣卫俱执送刑部问,未发露者,许出首逮问,同学知而不首者同罪。今后科场知贡举、监试、提调等官,务在防范严切,不许容情。……”
《弇山堂别集》卷82《科试考二》世宗朝冒籍情况:
“初,顺天乡试,岁多冒籍中者。……(嘉靖二十二年)礼科给事中陈棐劾奏之,因力陈京闱之弊。其劾谓曰:‘……或因本地生儒众多,解额有限,窥见他方人数额少,逃奔如京,投结乡里,交通势要,钻求诡遇者有之;……请令所司核究顺天府学冒籍生员,俱遣回籍,降等肄业……庶乎前弊可革’。得旨,钱仲实、张和下法司逮治,冒籍生员,提学御史复勘,余俱下礼部会议。”
以上两例奏疏说明明代冒籍现象虽多,但始终苦于没有应对之法,臣下多方建议,期望“前弊可革”,但后来屡禁不止的状况证明,仅仅是发现后重罚严惩并不能缓解该现象之严重性,于是当政者也实施了具体的办法进行预防,如《弇山堂别集》卷82《科试考三》记嘉靖四十三年曹栋上疏言科场冒籍案:
“疏下礼部查议,独黜冒籍陈道箴、吕祖望回籍充附,礼等各行原籍勘实,……于是罢部僚与试,而行提学御史徐爌通查在京冒籍生员,斥遣有差。复诏增拓举场前地,临入场时,增遣监场御史二员先于场门外检阅以进,著为令。”
《春明梦余录》卷40《礼部·贡举》崇祯六年礼部尚书黄汝良疏:
“……其童生入试,须令州县教官革取保结,无过犯方准进场,有败伦而失简举者,教官与州县官有罚。”
以上两例是明代实施的比较积极的控制冒籍的措施,从中可以看出明统治者对生员冒籍几乎是束手无策的,使用的也是比较愚笨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制定考试制度者的眼光很短浅,总是等事情发生后将责任全部归结给考官和生员,而且权利和责任都显得十分集中,都掌握在最高执政官手中,没有作到权利和责任的下达,所以才导致明代政府面对冒籍现象表现出的软弱及其科考中混乱不堪的局面。
明末虽然开始实行让教官与州县官取保以防冒籍的措施,但终不若清政府把责任下达到生员中,实行廪生保结和互相保结,承担责任的人多了起来,问题也就自然会少很多,不仅防止冒籍,而且可以防止各种考试弊端。再者,单看被追究责任方就可以区分明清两代保结制度的不同。明代追究的是教官与州县官的责任,而清代却明确提出还要追究“廪保”的责任。据《清稗类钞·考试类》[3]“廪生保童生”条载:
“各州县文童武童应试时,必由廪生领保,谓之认保。又设派保,以互相稽查而慎防弊窦。如孩童有身家不清,匿三年丧冒考,以及跨考者,惟廪保是问;有顶名抢替,怀挟传递各弊者,惟廪保是问,甚至有曳白割卷,犯场规、违功令者,亦惟廪保是问。”
《清会典》卷32《礼部》载:
“童生考试,以同考五人互结、廪生认保初结。府州县试,查照格眼册式,令童生亲填年貌、籍贯、三代、认保姓名,并各结状,黏送府州县。试毕造册申送学政。……”
《钦定礼部则例》卷60《童试事例》亦有与上相同之记载:
“童生考试,以同考五人互结,取行优廪保出结识认。查照格眼册式,令童生亲填年貌、籍贯、三代。每名下仍开廪生认保姓名,……不得有顶冒、倩代、假捏姓名、匿丧冒籍……容隐者五人连坐,廪保黜革治罪。其府州县考时,亦令本籍廪生一体保结识认。”
从清代的廪生保结制度可看出清代已汲取明代科考经验,对冒籍现象及各种弊端、隐患给予充分重视,也提出了相对严密、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清代科场冒籍案和由它造成的不良影响比明时都大大减少。通过对明清两代典章制度的考察发现,在处理冒籍这一猖獗于两代的科场弊端时,明代政府及其制定的相应制度表现出了明显的粗陋和没有经验,政策跟不上事态的发展就造成了只能事后自我批判而来不及事前预防的论乱局面;清代政府相比之下则稳健老成得多,清朝各种有关考试制度的典章、章程都对各种可能发生的舞弊现象列出相应的处理措施,尤其是对冒籍问题,其处理的手段、方法似乎已经十分成熟了,并有着它近乎约定俗成的独特的严密性,与明代自上而下的慌乱与束手无策的窘状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醒》中明确说出廪生保结制度,这应该可以证明他的最早成书年代不会是在明代,而一定是在清代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同时考察出其最晚成书年代不会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以后。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4]之“童生之院试”条载:
“(童生参加院试)报名、填写履历、取五童互结、廪生保结等,与县府试略同。院试于认保外,再加派报廪生,系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湖南学政张姚成奏准,所以杜认保廪生之或有舞弊。由府、州教官依长案先将派报名次,榜示署前,考生于府试、院试时请其加保,谓之派报。”
《醒》第三十七回对县、府试的描写和记载可谓详尽,但对派报一事却只字未提,试想如果作书前或当时就存在此例,那么作者在叙述从报名到考试全过程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什么都说了,只单单把这一项落掉了的,这只能证明在当时的科考中还没有实行这个政策,也就是说作者作书的年代应该不在乾隆五十七年以后。
二、服装颜色
《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一部典章制度书,其中记录贵族女装用料均为“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而平民女服用料受限制,即便是礼服,也限用紫色租布(即“絁”),并且禁止用金绣,袍衫也只限用紫色、绿色和桃红色等浅淡颜色,禁止用大红色、鸦青色和明黄色等浓艳色彩。明洪武十四年还规定,商贾之家只能用绢布制装,农家可以用紬纱和绢布。(《中国历代服饰史》191页)
《大明律·礼律2》[5](P386-387)疑制199条:
“官吏军民人等但有僭用玄、黄、紫三色及蟒龙飞鱼斗牛器皿,僭用硃、红、黄颜色及亲王法物者俱比照僭用龙凤纹律拟断。服饰器物追收入宫。”
明代法令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平民穿着的颜色,但《醒》中大量涉及服装色彩方面事宜,多处提到明代禁用的颜色:
1.《醒》第一回:珍哥大摇大摆穿着禁用的艳色服装出外打围狩猎“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莽挂肩,……一件天青……一根金黄…”
2.《醒》第三回:“将一只裹脚面高底红缎鞋都跌在三四步外……”
3.《醒》第五回:“……红鞋绫袜……”
4.《醒》第六回,晁大舍为珍哥置办年货“又买了些玉花玉结之类,又买了几套洒线衣裳,又买了一匹大红万寿宫锦……”“集”、“会”、“庙”等都是古代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百货交易的场所,出售的大都不是平民被禁止使用的东西,晁大舍买回的“大红万寿宫锦”也应是逢年过节中市面上的寻常货色,说明大红色非民间禁用色。有人说《醒》成书于明代,既然明代禁止平民用大红色制装,又为何被自称该书是“其事有据,其人可征”、以实录市井民生为本的作者将其一次又一次的“录”入书中呢?
5.《醒》第七回,珍哥穿着“大红缎裤”。更有甚者,也是该回,珍哥到晁大舍家拜见二老“两乘大轿,许多骡马,到了通州,进到衙内。珍哥下了轿,穿着大红通袖衫儿,白绫顾绣连裙,满头珠翠,走到中庭”。珍哥此时还没有正式成为晁家媳妇,她本人的身份还是平民,却在进一个诺大的通州衙门时公然穿着禁装,而晁大舍之父、通州知州晁思孝竟然视若无睹,这只能说明当时政府并未有明令限定平民着装颜色,大红乃喜庆色彩,合当在重大场合使用,珍哥如此打扮实属正常不过的事,所以作者一笔坦然写过,毫不见藏首露尾之情。这里还有一点有必要说明:任何朝代中明文禁止的事物到实施起来总会有违禁的行为出现,象唐代王维就曾因属下伶人私自舞黄狮,被人揭发而获罪。像这样的违禁私举在唐代必然不止王维一人,只是无人告发而已。尤其到了下层百姓中间,比如明代小说中描写女子家居偶着禁用之明艳色衣服,也一定是常有的事,只要没人告发,又兼仅在自家宅眷中穿着,也不能以此断定该作品不是创作于那个有禁令的朝代。但是场合的不同,使得《醒》中珍哥作为一个平民女子着禁装进宫家府第这一行为的性质不能与其他单纯描写家居着装违禁的小说相提并论,加之这里的行文气势和叙述的流畅自然,使我们看不出作者面前有一大堆的官府禁令要避讳。可见,平民女子进官家、着大红装,绝非明代女子所为,实是清人无疑。
6.《醒》第八回,计氏衬了件“小黄生绢衫”。
此类用法很多,由于篇幅就不一一枚举。无论从小说中人物所处场合(如牢狱、衙门、狩猎场等)、各自身份都可以看出,如果成书于明代,在还没有规定平民可以穿红、黄、青的时代,作者怎会预想到将来的清代会对服装颜色没有禁令呢?既是如“崇祯说”所说,书写于那个对着装有禁令的年代,那么身边百姓的穿着色彩对作者的写作就没有产生一点影响吗?怎么会写起来如此毫无顾忌呢?似乎也是解释不通的。
三、“提督山东学政”
《醒世姻缘传》第四十六回:
“学道将次按临东昌。原来那学道宗师姓徐,名文山,江西吉水县人,甲戌进士,原任武城县知县,十六年前,打那晁思才与晁无晏、替晁梁起名字的,都是他。由武城知县行取工科给事中,因谏言削职为民,又丁了两遍艰,奉恩诏起了原官,升了参政兼副使,提督山东学政。”
在明代,掌管学校政令和科考的官员称为“提督学道”、“提学御史”,《明史·志第五十一·职官四》[6]:
“按察司副使、佥事分司诸道。提督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十三布政司俱各一员,惟湖广提学二员,浙江、山西、陕西、福建、广西、贵州清军兼驿传,江西右布政使清军。”
《弇山堂别集》卷82《科试考二》:“冒籍生员,提学御史复勘,余俱下礼部会议”,《弇山堂别集》卷83《科试考三》:“提学御史徐爌通查在京冒籍生员”,《春明梦余录》卷40《礼部·贡举》:“提督御史董,以失觉察调用”《明会典》卷77,礼部35,《贡举·岁贡》对督学官的称呼都是“提学官”,并无“提督学政”之类语。《中国历代职官辞典》第994条“提学”的解释是:‘提举’、‘提督学道’、‘提督学政=学政’、‘提学使’。宋代置提举学事司,掌地方学政。元代改为儒学提举司提举。明代由提刑按察使司之按察使及副使、佥事等任各省提督学道。清代改为提督学政(简称学政),各省一名……清末改为提学使。在对“提督”的解释中提到:其它官职亦有名为提督者,如明代之提督东厂,清代之提督学政、提督会同四译馆等。这些都说明明代的督学官名均称之以“学道”而非“学政”。
清人黄本骥所编《历代职官表》[7]卷五·学政(第四十六表)中的“提督学政”一栏里注明,从三代到五季都没有该官职,五季以后历代执行督学任务的官职具体名称分别是:宋代称为“提举学士司”;金代称为“提举学教官”;元代称为“儒学提举司、提举、副提举”;明代称为“提学御史、提学副使、提学佥事”。该书的《出版前言》说该书是道光年间黄本骥以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七十二卷本《历代职官表》[8]为底本编撰而成,而清乾隆时为编修此书曾颁布《上谕》说:“将本朝文武内外官职阶级,与历代沿袭异同之处,祥稽正史……分晰序说”因此批评说“官修本的表文,……存在体例上以历代职官强行比附清代官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黄本骥时也没有进行严格的考订和修改。这一现象正为我们的清代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中的纵列只列出了从三代到明代的官职,并没有列清代的官职,而横行所用的官职名称显然都是清代才有的,正因为把清以前没有的官职强行与清代的官职相对应,以至于很多时候不仅名称不符,连官员所行职责也大相径庭,才招致《出版前言》中的批评,这个批评侧面的证明了明清两代官名及其职能并不能一一对应,比如,明代虽有提学官,但没有“提督学政”这一具体称谓,更没有明确规定提学官全名是“提督某省学政”(该全称是雍正四年后才在全国通行),且官员责任范围也比清代小得多。为了便于了解历代职官的沿革和表中所列职官的执掌、演变的情况,书中还附有瞿蜕园先生撰写的《历代官制概述》,瞿先生在明代官制的概述中说:
“关于地方学校考课之事,自宋代设提举学士司始,元则设儒学提举司,皆为地方高级督学之官职。……惟考选生员入学之事,明初本未设专官,中期以后,始以御史提督两京学校,以按察司副使、佥事为各省提督学道……”
《历代职官沿革史》也说:
“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始设提督学校官,……至于考选生员入学之事,明初本未设专宫,中期以后,才由御史提督两京学校,以按察司副使、佥事为各省提督学道。不仅生员,连府州县教官也归其考核”。
但到了清代官制的概述中,瞿先生就多次使用“学政”一词(限于篇幅,也不逐句列举),可见瞿先生对于“学道”与“学政”的区分也是很审慎的,这更证明了名实相符的“学政”应出现在清代。更明显的使得两个官名得以区分的依据是该书还附有一个《历代职官简释》,对各种官名进行详释,其中“提督学政”的解释是:
“古代无专司教育文化之高级地方行政官,宋代始置提举学士司,然仅管学校,而不管考试。明代始分别差御史为两京提学御史,以按察使、副使、佥事为各省之提督学道。清代初亦沿明制,后乃一律定为提督学政。……”
对于清初沿用明制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史实:施闰章(1617-1683)是清代曾在山东任学政的官员之一,但他是顺治年间人,《山东通史·明清卷》说:“清世祖推崇文学,……施闰章名列第一,擢山东提学佥事。”书中又特别在“山东提学佥事”的官职后加括号补充道:“相当于后来的学政”。这说明,“学政”在顺治年间还未被作为山东督学官的官名使用;而且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后来”指的应该就是雍正四年废“学道”,改为“学政”的法令颁布之后。
《清代地方官制考》在学政的设立与沿革的考证中也明确了到康熙时才有学政官职,而且也仅在几个地区设立,也就是说山东督学仍称“学道”:
“清沿明制,顺治初年,于各省并设督学道,带按察使司佥事衔……称为‘学道’。又于顺天、江南、浙江(为康熙二十三年定)设提督学政,均以翰林官充任,称为学院……至雍正四年定,各省督学皆改为学院,……”(按,学院的行政长官为“学政”)
把“提督某省学政”这种官衔中包含的地方名“某省”与官名“提督”、“学政”间有固定排列顺序的特殊称谓,用在对山东地区学政官的称呼上,是以雍正四年为始的。
《历代职官沿革史》:
“宋祟宁二年(公元1103年),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所属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简称提学。金有‘提举学校官’,元有‘儒学提举司’,都属同一性质。明初没‘儒学提举司’,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始设提督学政。两京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佥事充任,称为‘提学道’。清初相沿,各省多设‘督学道’。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改称‘提督学院’,长官称‘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政’。清末改设‘提学史’。”
对于“提督”这一官名的演变和具体功用《历代职官沿革史》还有详细记录:
“明代驻防京师的军营没有提督。中叶后,巡抚多兼提督军务衔,亦间有总兵称提督的。万历时始专设提晋,但不常置。清设‘提督军务总兵宫’,简称‘提留’,为地方高级的军事长官,从一品,下设镇、协、营、汛四级。其直接统辖的绿营兵,称‘提标’。有水师之地,或专设水师提督。又为领导监督之通称。清代学政的全衔为‘提督某省学政’。”
《清史稿·志91·职官制》[9](P3345):
“初,各省并置督学道,系按察使佥事衔,各部郎中进士出身者补用。惟直隶差督学御史一人,后称顺天学政。……雍正三年,析置江苏、安徽各一人。称学院。……康熙元年,并湖北、湖南提学道为一,更名湖广提学道。雍正二年复分置。……二十三年,停督学论俸补授例,并定浙江改用翰林官,依顺天、江南北例称学院,其各省由部属、道、府任者,仍为学道。三十九年,定翰林与部属并差。雍正四年,各省督学并更名学院。凡部属任者俱加编修检讨衔。至是提学无道衔”
《钦定礼部则例》卷54《学政事例》更是用专章31条规定提督学政官的各项职责权限。另外,对清代科举制度很有研究的商衍鎏先生,用了30年的时间终于在1956年,完成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书中说:
“雍正四年废学道,各省督学一体成为提督学院,官名则曰钦命提督某省学政,加提督衔者,以学政兼考武生之故。”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提学”条:
“明初置儒学提举司,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置提督学校官两京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使、佥事充任,称提督学道,惟直隶与江南、江北派督学御史,称学院。雍正四年(1726年)各省督学道皆改提督学院,长官称提督学政,简称学政。”
以上种种说明,清康熙二十三年前督学官均称为“学道”,二十三年后除顺天等地区称“学政”外,其余地区包括山东仍称“学道”,而雍正四年(1726)的法令颁布后,各省督学均更名“学院”,学院的行政长官就是“学政”,从此再没有“学道”衔。《醒》中徐宗师的官衔是“提督山东学政”,与雍正四年所立官职名称“提督某省学政”相同。说明此时是雍正四年后了,山东省的“学道”也已改为“学政”。假设不是在雍正四年政令变更以后,作者又如何想出要用这样一个名称,即使想出来,又如何能与政令上规定的名称顺序完全吻合呢?在这个名词出现之前,书中一直都在用“学道”,即使是上述引出的段落中、在叙述徐宗师的经历时还用了两个“学道”,既然如此,就应该沿用同一个名称以保证作品内容的统一和前后一致,又何必要把用得好好的“学道”突然改为“学政”呢?唯一的解释是这个官职的名称在作者居住的地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前后曾发生过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官或儒界影响很大,有必要、也必须真实而鲜明地反映出来。这个变化给了作者很深的印象,或许作者写书之时正在经历这个变化,他的朋友、宗师恰逢此时升任该职就遇上了官名的变更。另外,作者用如此郑重的叙事口吻对一个官衔特地全名加以强调,除了写实,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这一段在小说中起到连贯上下文的巨大作用。短短的一小段,就要把—个百回煌煌巨著中出现的本不多见的几个好人之一的一个官员在16年间的经历交代清楚,这一段的意义可谓重大。16年前,徐宗师任武城县知县,平息了晁氏家族的内讧,并为新出生的晁氏继承人起了名字,16年间,徐宗师宦海沉浮,几起几落,16年后终于奉诏起了原官,“升了参政兼副使,提督山东学政”。他的重出在他个人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部作品,就是借助他仕途的起落引领出一个新的叙事时间与空间。这16年的前前后后就是一段完整的历史,而沧海桑田的变化最后全部通过一个崭新的官衔展现出来,它好像要告诉读者:以往的屈辱和不公总算可以化解,以前那段故事中晁家小主人的幼年已结束,一个好官的复出有着令人可以预想的要干一番新事业的前景,那么推动故事发展的势能也就产生了。这两个名称一看就知道是专有的职务名称,它们的突然出现,打破了“学道”的特定称谓,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说,当叙述时间和空间要发生一个大幅度的飞跃时,作者不会不注意到要处理好飞跃的起点与落点中间的环节,而环节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明显而广为人知的时间特征,这里的核心就是“提督山东学政”一词的出现,它是真正分割16年前后新旧环境的历史性标志。作者的目的是要强调此时山东地区的“学道”已更名为“学政”,无疑是暗示读者这是雍正四年后的事了。这种以当朝人或近朝人悉知的官名统更的史实作为作品中时间暗示的创作方法比只是简单叙述时间推移更有历史层次感。
通过考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醒世姻缘传》成书的上限应该是雍正四年,而下限则是乾隆五十六年。
收稿日期:2003-0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