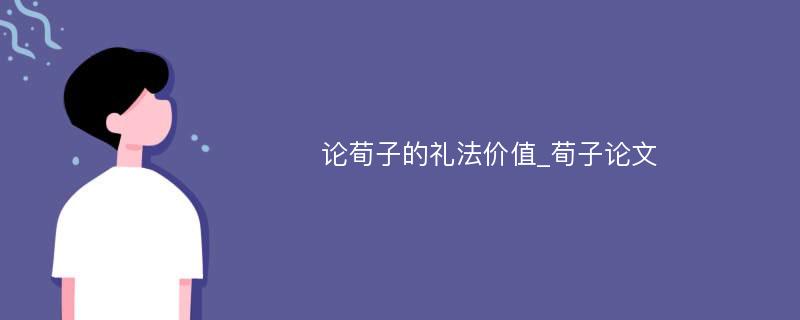
论荀子的礼法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礼法论文,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有着相对于法的价值优先性。作为由三代社会政治文化模式中升华出来的价值准则,礼对于工具性的法具有一种涵摄作用。在荀子看来,礼包含着形上层面的终极关怀意义,而法则不过是实现礼的工具而已。即使同为治理国家的手段,礼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也是法所不能比拟的。荀子的礼法价值观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儒家文化何以被称为礼乐文化的原因之所在。
一、荀子对礼、法概念之界定
(一)礼之概念界定
荀子礼学思想中的礼,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双重含义。
第一,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礼表达了荀子对社会等差秩序的追求。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针对当时人们对三代之礼的混淆和僭越,荀子进行文化重建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厘定由礼所承载的社会等差秩序,实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1] (p178)的价值目标。荀子从两个方面论证了社会等差秩序的必要性。从人性的角度看,因为人的自然欲望可能导向恶的行为,所以必须以礼来划分等级尊卑秩序,满足不同等级的不同欲求,或者是根据不同的等级来控制不同的欲求。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看,“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1] (p179)也就是说,人和禽兽的不同,就在于人能“群”而禽兽不能“群”,而群居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能够各自恪守自己的本分。如果超越了这种欲望享受的分界,就会产生争夺,群居的生活就不能维持。因此,必须以礼来“明分使群”。他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使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1] (p152)在这里,荀子试图站在人类生活的高度来证明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在他看来,社会上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非齐维齐”。惟有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名分制度,才能有效地维系社会群体,使社会处于整合状态。
第二,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礼是维护社会等差秩序的主要手段。荀子说:“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存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1] (p490)又说:“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1] (p232~233)在这里,荀子试图通过礼对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人的义务进行设定,以实现维护社会等差秩序之目的。
(二)法之概念界定
据《说文解字》解释,法即刑。《尔雅·释诂》曰:“刑,法也。”[2] (p15)《韩非子·难三》说:“法者,编著之图籍。”[3] (p381)可见,在我国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法是刑的成文的表现方式。战国时期,法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尔雅·释诂》说:“法,常也。”[2](p15)由此可知,法又指度量行为的尺度。有学者认为,从时间顺序来看,中国古代法的称谓,在三代称之为刑,春秋战国时期称之为法,秦以后称之为律。但是,无论是法、刑还是律,其内在规定性都不外乎一种通过肉体惩罚使人屈服的工具。在这里,法即刑,律也是刑,法、律、刑有着相同的本质。
法字在《荀子》一书中出现的频率高达170余次,仅次于礼。[4] (p241)这些众多的法字,主要有以下几种用法:一取效法之意,如说“法先王”(《荀子·非相》),说“不法先王,不是礼义”[1] (p93),说“上则法舜禹之治,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1] (p97)等。二取一般意义上的规范制度之意,如说“礼者,法之大分”[1] (p12)等。三取政治性国家制定的法律规章之意,如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1] (p151),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1] (p392),说“若是则百官莫不畏法而遵绳矣[1] (p228)。以礼法关系为视角,荀子的法主要是指第二和第三层意思。在大多数情况下,荀子的法更接近于今天所说的刑。
二、礼作为工具理性的价值优先性
在我国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的根本对立在于确立社会等差秩序的价值合理性的依据不同。法家以“竞力”作为理想社会建构的根本原则,而儒家则将价值理性意义上的礼作为理想社会建构的根本原则,尽管儒家也运用刑罚这样的工具措施,但却把它们置于礼的框架内,使它们在现实中的运用获得某种超越其本身之上的更高的神圣性。[4] (p247)作为一个“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1] (p236)的思想家,荀子继承了孔子思想,把礼置于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他曾提出“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1] (p202),这同孔子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梁治平说:在先秦时期,“理、义或礼乃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只是在有的场合,它以其精神贯注于律、令等专门的法律形式之中;在另一些场合,它直接被援用作为判决的依据。”[5] (p180)这充分说明了礼在包括荀子思想在内的儒家思想中的价值优先性。
荀子认为,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礼足以治天下。他说:“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势矣,致忠信,著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1] (p214~215)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荀子认为虽然结束战乱离不开战争,但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式。他说:“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1] (p289)“以德兼人”就是以德行去治理国家。它“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1] (p289)“以力兼人”就是用武力统一天下。它“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衅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1] (p289)“以富兼人”就是用财富去统一天下。它“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比发夫掌禀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三年,然后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1] (p289~290)荀子认为,用德行去统一天下,会得到百姓的顺从和拥护;用武力去统一天下,虽然能够得到土地和百姓,但是得不到人心;用财富去统一天下,虽然能得到百姓的归附,但是国力难以应付。因此,荀子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1] (p290)
由此可见,荀子是在礼治的框架内阐述重法思想的。他认为,“礼义者,治之始也。”[1] (p165)“法者,治之端也。”[1] (p230)在荀子看来,礼法相比较,礼具有更重要的地位,是起着指导作用的一般原则,而法则是为了实现礼的目标而运用的手段,礼具有价值理性,而法只具有工具意义。比如,《荀子·君道》篇把法分为“法之数”和“法之义”:“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1] (p230)“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1] (p232)在荀子看来,“法之数”是具体的法律制度,在械数之上还有更高的“法之义”,即礼。而“法之数”要受“法之义”的规导和制约。荀子始终恪守着“国家无礼不宁”的思想宗旨,而将法安排在礼的框架之中。如他认为:“礼者,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也。”[1] (p12)“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1] (p281)这说明,作为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并没有将礼和法等量齐观,更没有将礼和法混为一谈,而是表达了礼本法末的礼法价值观。
三、荀子礼法价值观的学理依据
(一)逻辑上的礼包含法
虽然礼、法各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但是,礼在荀子这里有包含法的意思。如在《劝学》篇中,荀子认为礼是唯一的学习对象,即学至乎《礼》而止。但是他又说:“学也者,礼法也。”[1] (p34)在这里,礼显然有时等同于礼法,法涵盖于礼的概念中。
作为最普遍的社会规范,礼在国家形成之初就有涵盖法或者刑的意思。《尚书·吕刑》说:“伯夷降典,折民惟刑”。[6] (p344)“《大传》引此句作‘伯夷降典礼,折民以刑’”。[6] (p345)《尚书·舜典》又说:“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6] (p17)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制礼是可信的。结合历史上“伯夷作五刑”的说法,可以推测礼和刑在上古是相通的。西周社会被称之为礼乐盛世,但是礼乐之中也有许多严厉的刑罚。既然礼包含了刑,那么,违反了礼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则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7] (p250)《左传》还列出了对违礼行为的具体刑罚制裁措施,主要有:讥讽、责让、诘难、卑贬、夺邑、放逐、杀戮、征伐、取灭等11种。由于礼是最普遍的社会规范,它涵盖国家的政治、外交、战争以及个体人生的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因此,凡是这些方面的严重违礼行为都要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如《礼记·王制》记载:“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8] (p412~413)
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礼法二分现象,礼不仅从内容上包含了法,而且在发生作用的方式上也统摄了法,前者主要表现为法的规则同时也是礼的规则,后者主要表现在违礼的行为要受到刑罚的制裁。
荀子在《荀子·王霸》篇关于礼法的论述中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1] (p220~221)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1] (p214)
从这段探讨礼法的基本含义和纲领的论述中,我们看出礼法既是礼又是法,这里的礼具有传统的礼和法的双重含义,具有“儒家之礼和法家之法的双重属性”。[9] (p127)也就是说,荀子的法在一般情况下包含于礼的概念中,只有当法是指刑罚禁令时,法才成了与礼相对称的概念。后来的儒学思想家一直沿着这样的路径思考礼法关系,如王充在《论衡·谢短》中说:“古礼三百,威仪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条三千,出于礼,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数也。”[10] (566)《后汉书·陈宠传》中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11] (p545)章太炎说:“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12] (p399)
(二)产生顺序上的礼先法后
与探讨礼的起源一样,荀子也是从人的欲望和社会财富之间的矛盾来论述法的起源的。他认为,人生来就有贪利、嫉恨和耳目声色之欲望,求得这些欲望的满足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但是,如果任由这些原始的本性去发展,就会发生争夺、残杀、淫乱等罪恶行经,社会就会失去良好的秩序。因此,需要制定礼义法度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1] (p346)。他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1] (p440)
由此可见,“礼义”和“法正”是用来制止“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的。这是礼的起源,也是法的起源。虽然礼法同源,但是,圣人在纠治偏险悖乱时所运用的礼义和法度是否同时产生呢?荀子说:“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1] (p437);“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1] (p438)。由此可以推断,在礼法产生的顺序上,荀子显然是认为礼在先,法在后。这里的礼先法后表达的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更重要的是,它隐含着礼本法末的价值评判。
(三)功能上的礼本法标
荀子虽然肯定了法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但是,他却认为礼、法发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是不同的,法探究的重点是如何施以刑惩,以借助重刑来控制社会,而礼则十分注意对犯罪原因及犯罪预防的思考,它从根本上“收拾人心”。首先,荀子为礼和法规定了不同的地位,认为“礼”是“治之始”,而“法”是“治之端”。他以秦为例说明,统治者专用刑罚和功赏治理国家并不是最好的方法:“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1] (p273~274)其次,荀子为礼和法划定了不同的适用范围。他主张:“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1] (p149)第三,在礼法发挥作用的方式上,荀子认为,礼以德教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法则以刑罚制裁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但是,两者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其发挥作用的程度是否一样呢?对此,荀子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1] (p291)也就是说,为政以礼可以治天下,为政以法只能霸天下。所以,礼是比法更根本的政治原则。
四、荀子礼法价值观评价
荀子礼本法末的礼法价值观,表达了儒家的总体价值取向。对此,历史上许多学者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13] (p983)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六也认为:孔墨同称,始于战国,孟荀齐号,起自汉儒。荀学以隆礼为要。
荀子的礼法价值观表达了儒家对礼这种软性规范的推崇。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说,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势、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社会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14] (p349~350)刘丰认为,福柯这里说的虽然是现代社会规范对人的制约,但是,如果把它对应在中国古代社会,这样的“监狱网络”就是作为社会控制的礼。他认为,这样的对比是恰当的,并没有“历史错位”的感觉。古代社会的礼也含有惩罚的一面(刑),但它更重视从正面来引导、规劝,这也相当于福柯所说的“新型惩罚策略”。福柯认为,“新型的惩罚策略”以一种谆谆教诲的姿态出现,它的主要特征在于对正面的惩罚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把免除刑罚作为惩罚的主要手段,以一种“反常”的名义对人进行“正常”的教化。显然,这种“策略”正是古代社会礼的特征。古代的礼以一种弥散性的社会控制把社会中所有的人都纳入其中,对其进行规劝、教导,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自觉接受礼的要求,服从礼的规范,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5] (p187)
荀子的礼法价值观使得法具有了某种道德属性,使法律成了“伦理规范的法典化”(韦伯语),造成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和法虽然有一定的冲突,但是终究没有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得中国古代法律表现出伦理法规和风俗习惯含混不清,进而使得“伦理的责任和法的义务的模糊混杂,伦理的告诫和法律的命令在形式上没有严格的界限:即一种尤其无形式的法(non-formal law)。”[15] (p139~140)马克斯·韦伯是在分析中国何以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时说这番话的。事实确实如此。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支配了一切古代法典,这是中国法系的一大特色。汉代以后,“礼本法末”、“德主刑辅”一直是历代社会立法的基本原则。如《唐律疏议?名例》遵循“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16] (p3)的原则。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法律始终与道德相互胶着在一起,共同为维护社会等差秩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