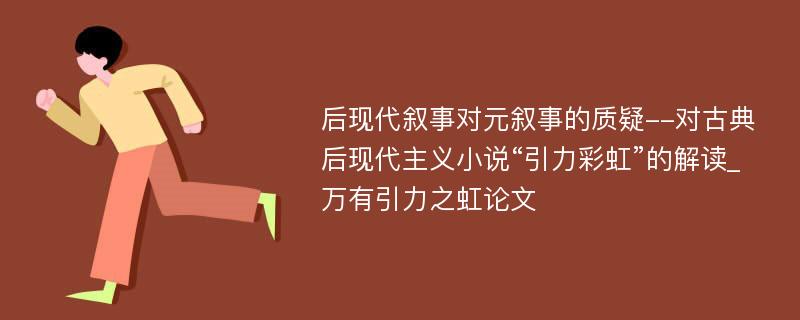
后现代叙事对元叙事的质疑——解读后现代主义经典小说《万有引力之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万有引力论文,后现代论文,经典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马斯·品钦是一个谜。他很少抛头露面,却备受关注;他的作品尽管深奥晦涩,却连连获奖,畅销不衰。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V》(1963)于当年获“福克纳最佳小说处女作奖”;第二部长篇小说《拍卖第49批》(1966)于1967年获美国全国艺术与文学院的罗森塔尔基金奖;第三部长篇小说《万有引力之虹》(1973)先后获1974年全国图书奖和1975年美国艺术与文学院的豪威尔斯奖,但品钦拒绝领奖;第五部长篇小说《梅森和迪克森》(1997),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全美五部最佳小说之首;品钦于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了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必读作品,《万有引力之虹》更是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小说长达887页(Bantam1974年版),人物有400多个;故事发生地遍及欧、美、亚、非各大洲;情节纷繁离奇,如梦如幻,支离破碎;内容涉及火箭工程、现代物理、高等数学、弹道学、性心理学、化学、音乐、电影等等五花八门。难怪著名的批评家爱德华·孟德尔逊(Edward Mendelson)把《万有引力之虹》和《唐吉诃德》《浮士德》《尤利西斯》《白鲸》等著作并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叙述作品。”[1] (P161)该小说1974年获普利策奖提名,但最后却被评奖委员会否决了,其原因是作品“太过晦涩”。[2] (P15)许多文学研究者读不过百页就放弃了,更别说普通读者了。
《万有引力之虹》之所以晦涩难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蔑视了读者习以为常的“经典叙事秩序。”在品钦的世界里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人可以顺着下水道和污物一起流动;火箭可以先爆炸,随后人们才会听到其飞行的声音;人的性欲竟和火箭落点有着神秘的联系;肉体居然可以像气团一样分解消散……这是一个理性和秩序遭到无情嘲弄的世界。
追求秩序是千百年来人类一贯的思维模式,理性主义更是西方文明的基础。然而,物极必反,理性秩序的发展也具有两面性,与高度工业文明和绝对理性主义相伴的是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和人性的严重异化。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在给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的个性带来了严重的压抑和扭曲。人的个性与创造性被生产过程中的理性原则所排斥,从而失去了主体地位,沦为生产过程中被动的客体。物原本是人所创造的,现在却掉过头来压抑人、支配人、排斥人、约束人,人越来越被物所同化,变得越来越像机器。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3] (P96)技术理性和官僚政治及资本集团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的异化力量,牢牢地掌控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绝对理性带来的危机决不是某一方面的危机,而是政治、经济、信仰、道德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总体危机。
看到了绝对理性给世界带来的危机,后现代思想家们开始着手消解理性那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指出,由于当代社会现实和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变异,现代社会中理性已经堕落成为了权力的代名词,而绝对理性的无限权威是建立在其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剥夺和扭曲基础上的。利奥塔1979年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科学为了证明自己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制造出了哲学这种元话语来,而元话语又制造出“宏大叙事”也就是所谓“元叙事”。“元叙事”就是指那些能够为科学立法的哲学话语。“元叙事”被认为具有普遍性,可以用来表述绝对真理,是理性和秩序的代言人。后现代作家们把表述绝对真理的“元叙事”当作抨击和瓦解的对象。在利奥塔看来,所谓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4] (Pxxiv)
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是后现代的代表性文本。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品钦运用后现代叙事对元叙事的消解,即用混沌来对抗秩序;用天性来瓦解理性;用“鄙俗”来蔑视权利。
一、秩序——混沌
自从人类开始探索自然规律以来,秩序受到了特别的青睐。人的目光一直盯在那些稳定的、有序可循的事物上面,混沌无序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忽略。人类似乎已经忘记,和宇宙中那无垠的混沌相比,秩序只能算得上是九牛一毛。然而人们对无处不在的混沌却视而不见,只把注意力放到秩序上,认为混沌是无法理解的怪物。拉普拉斯(1749—1827)于18世纪,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动力学决定论,认为自然事物都是受客观的力学原因和力学规律支配,无论是最大的天体还是最小的原子,只要知道了它们在某一时刻的一切关系和作用力,就可以推断它们的状况。这样一来,秩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混沌完全被边缘化了。到了20世纪,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秩序并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于是,混沌开始进入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视野。利奥塔宣称,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决定论危机”[4] (P53)的时刻。后现代理论家们指出,不确定性、开放性、异质性和多元化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
《万有引力之虹》是一部拒绝秩序的小说。小说结构松散,缺乏主线,甚至很难归纳出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情节;这是一部用片段拼贴出来的作品,书的四个部分包括73个用小方框隔开的片段,没有顺序和章节的标记,片段与片段之间的跳跃性很大,根本无法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理解;小说的视角大部分是第三人称,但有时突然会转向第二人称,作者直接面向读者说话;有时在叙述一件事情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细节,作者会不厌其烦地追踪这个细节,而把正在叙述的事情放到一边。其实品钦所做的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消解读者所习惯了的秩序,以引起读者对既有思维模式的反思。品钦把那种认为万物之间都有联系的想法称为“偏执狂”。[5] (P820)所谓“偏执狂”实际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那些与其格格不入思想的称谓,而此处品钦所说的“偏执狂”实际上也指那些持决定论观点的秩序维护者,因为他们习惯于在纷繁复杂的事物背后寻找关联。用统治者称谓其异己的词来称谓统治者他们自己,让读者看到统治者本身并不是无懈可击,他们所压制的东西也存在于他们自己的身上。作者在这里所用的叙事策略正和解构主义者常用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如出一辙。
小说中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心理学家坡因兹曼(Pointsman)。他是一个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的信徒,把有机体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认为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对人的身体和心理进行控制。他身上的人性已经完全让位给了所谓的理性,他虽然在盟军的心理情报部门工作,但是其冷酷的程度不亚于法西斯分子。人体在他这里成了实验品,他希望在斯洛思罗普身上进行的实验能成为他通往诺贝尔奖大门的敲门砖。他企图要弄清楚斯罗斯洛普和火箭之间的关系,他想:“当我们发现了这种联系时,我们就会又一次证明一切事物、每个灵魂之间的铁一般的确定性。”[5] (P99-100)他的思维模式是典型的两极化模式,非此即彼。因果关系对于坡因兹曼来说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坚信凡事必有前因后果,“我们科学的理想,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发现真正的机械意义上的解释。”[5] (P102)但是发生在斯洛思罗普身上的事例却让他大惑不解,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火箭还没有到来之前斯洛思罗普就出现了性欲反应,这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
“如果有一个坡因兹曼的对立面存在的话,麦克西柯(Mexico)就是这个人。”[5] (P63)作为一个统计学家,罗杰·麦克西柯所感兴趣的是概率。概率论是以偶然事件出现的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迥异于坡因兹曼的决定论。和坡因兹曼的两极化思维模式相比,麦克西柯的思维模式是多元化的,“在○和一之间,无和有之间,坡因兹曼只拥有○和一,他不能像麦克西柯一样在中间地带生存。……但是麦克西柯属于○和一之间的地带——坡因兹曼从他的信仰中排除了的领域……”[5] (P63-64)麦克西柯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经历了真爱的人物之一,他和杰茜卡(Jessica)的爱情虽然作者着墨不多,却是感人至深的。他对坡因兹曼的决定论不屑一顾,他觉得因果论过于狭隘:“如果我们有勇气摒弃因果论,能换个角度看问题的话,也许伟大的突破就会到来”[5] (P103)。品钦在秩序中看到了压抑,在混沌中看到了希望,在秩序和混沌的对峙中期冀着“伟大的突破。”
二、理性——天性
《万有引力之虹》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然而,品钦并没有去着力描写战争,也没有着力描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是把叙述的重点放在了V-2火箭上。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战争,而是看到了绝对理性和自由人性之战。“政治只不过是战争的舞台,只不过是用来分散人的注意力……然而在背后,是对技术的需求控制着战争。”[5] (P607)正如托洛利安(Tololyan)指出的那样:“品钦想让我们把德国看作是技术社会最极端的一个代表,”[6] (P52)是绝对理性发展到极致而趋于疯狂的体现。V-2火箭是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从小说开始的一声尖啸,到小说结束时火箭的下落,以及书中人物的活动,都是围绕着火箭来进行的。而火箭作为技术的成果,是人类科学理性的产物,它实际就是人类理性的代表。在小说中,品钦再三提醒读者,在绝对理性的时代,火箭作为技术理性的象征,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那洁白的火箭就像那“教堂顶上挺拔的尖塔一样”,[5] (P33)威严神圣,它“像幼儿耶稣一样……你看到它的第一眼就不得不对它产生臣服之心,它的确具有马科斯·韦伯所称的领袖魅力。”[5] (P541)当它飞行的时候,在天空中画出一道绚丽的彩虹,让人想起了上帝的彩虹。在《圣经·旧约》中,上帝和诺亚以彩虹为约,允诺再也不会毁灭人类。然而火箭——这个新时代的上帝手中的彩虹却是死亡之虹、毁灭之虹[7],那美丽的彩虹将把成千上万的灵魂送入地狱。把人类理性附着在这样一个杀人武器上,其本身就是对理性的一种嘲弄。
和绝对理性相对应的是天性,也就是自然的、非人为的东西,在《万有引力之虹》中主要指地球的引力、万物的生命力和人性的自由。作为理性代表的火箭,从设计、制造和发射都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程序进行的,是理性的力量使火箭升空的,火箭上升的过程实际上是克服地球引力的过程。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升空最终会屈服于地球引力”。[5] (P885)火箭飞行的抛物线轨迹恰恰是天性瓦解理性的最形象的注解,火箭的升空受理性支配,然而它的下落和爆炸却是地球引力的结果,理性对此无能为力,不管火箭飞得多高,它终究会“再一次飞下来,不受控制的爆炸。”[5] (P847)显然,理性并不能控制一切,在飞行中,火箭要服从地球引力的召唤,服从自然的规律,于是他从理性的产物变成了自由落体。在它降落的过程中,制造者、发射者的意志已经无影无踪,它的归宿永远是大地,它永远也不能摆脱地球引力作用。品钦在此似乎在暗示我们,一切违背自然规律的对大自然的所谓征服行为永远也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和死亡之虹——火箭相对应的,是皮瑞特·普雷蒂斯(Pirate Pretice)种植的香蕉。香蕉的形状和火箭的飞行轨迹一样,也是抛物线状的。普雷蒂斯的香蕉早餐很有名气,“在这战争的早晨,香蕉的芳香飘散着,充溢了整个空间。”[5] (P11)纽曼(Newman)指出,那些形似男性生殖器的香蕉就像抵御死神的符咒一样,在V-2火箭奸污着伦敦的时候,它们在一片战争的废墟中生机勃勃,显示着大地的生殖力。[8] (P93)这些长在房顶污泥中的大香蕉泛着翠绿、橙黄的生命光辉,透着对钢铁死神的蔑视。
绝对理性企图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人性自由是它所不容的。《万有引力之虹》中的主要人物泰洛尼·斯洛思罗普(Tyrone Slothrop)出生于一个清教徒家庭,继承了他家庭中“因果论”的思维模式,一心想解开围绕在自己周围的谜团。他从小被父亲卖给心理学家进行性学研究实验,体内被注入了一种化学物质,而这种物质后来又被用于火箭制造,这使他和火箭有了神秘的渊源。性欲是人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绝对理性特别想加以控制的东西。作为实验对象,斯洛思罗普从小受到监控。另外,当发现他的性欲和火箭有直接联系时,他更成了各方面跟踪、控制的对象。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来到了“基地”(Zone)——战争刚结束的德国。这里一片混乱,秩序还没有建立。然而这种混乱正好为斯洛思罗普摆脱控制、舒展自由的人性提供了机会。在基地,斯洛思罗普终于逃脱了控制。他仍然扮演着一个实验品的角色,不过这一次他成了检验人性自由的试验品,他要证明:“就在某个地方,在这个世界的垃圾堆中,隐藏着那把将让我们回家的钥匙,这把钥匙将把我们归还给大地,把我们归还给自由。”[5] (P612)就是在这里,自然的力量和人性的自由汇聚到了一起,共同来对抗那疯狂的绝对理性。在大自然中,斯洛思罗普找回了被剥夺的人性自由,找回了失去的自我,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的肉体居然分解消散,完全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心中充满了激情,站在那里哭了起来,脑子里毫无杂念,只有自然的感觉……”[5] (P729)普兰特(Plater)指出《万有引力之虹》是“关于自然力与人为力量的对抗,人企图将人为秩序强加于自然之上。”[9] (P28)
三、“鄙俗”——权力
《万有引力之虹》中关于废物和垃圾等“鄙俗”的描写随处可见,品钦好像比别的作家更热衷于描写那些破旧的床垫、“成千上万的旧牙膏皮”。他作品中的人物许多也属于社会的“废物”和“垃圾”:流浪汉、无业游民、失败者、妄想症患者、吸毒者、偏执狂,性变态者等等。这些都是主流文化所不齿的、被边缘化了的人物。品钦显然是这些边缘人物的代言人,他要通过作品把这些本来被社会忽视的人群重新推到读者的眼前,推入社会的视野。
“选民”和“弃民”的对立是品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根据加尔文教义的预定论,上帝在创世时,既已选定了一部分人得救,这些人被称为上帝的“选民”,而另一部分人上帝没有选定,他们不能得救,上帝任由他们沉沦,这部分人被称作“弃民”。那些“选民”们往往自诩为“社会的精英”,“优等民族”。他们高居社会的上层,手中握着权力,对那些下层的“弃民”压迫、排挤、甚至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二战中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就是这方面极端的例子。那些“选民”们表面上优雅得体,内心却藏污纳垢,《万有引力之虹》中描写了一些盟军军官的变态性行为,让读者注意到那些道貌岸然的上层社会人物骨子里的肮脏。
品钦对那些占据着统治地位、掌握着主流文化的“选民”们的作为厌恶至极,他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弃民”联系在了一起。作品中每当提到那些拥有权力的统治者时,往往使用人称代词“他们”,而指代那些下层“弃民”的代词则多是“我们”,这表明了作者对“弃民”的身份认同。小说中,斯洛思罗普为了追逐他那掉进厕所下水道的竖琴,自己也掉进了下水道,和下水道中的污秽一起漂流。在这厕所的下水道里他竟然发现了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弃民”的世界,是主流文化所不容的世界,只有在这厕所下水道中,他们才有安身之地。哪些东西是废物和垃圾,哪些是有价值的,这并不取决于其本身的性质,而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建构。对于这种“选民”和“弃民”的等级制度,作者深恶痛绝,他借斯洛思罗普之口喊道:“在荒芜内部的什么地方,应当有一种和谐共处,我们一同从这和谐中前进。没有选民,没有弃民,甚至连他妈的国家也没有……”[5] (P648)这里,品钦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美国社会文化中的清教传统。
在权力控制的等级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服从严格的等级秩序,充满了恐惧、教条和僵化,这是“选民”社会的生活。与其相对立的是“弃民”社会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对一切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着不敬和猥亵。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显示着自己的存在,释放着生命的活力,“鄙俗”是他们对抗权力的武器。
小说中的一个片断描写麦克西柯的恋人离开了他,他非常痛苦,而这时坡因兹曼等一批人正在开会。想起了坡因兹曼以前利用了自己对他的信任,麦克西柯怒火中烧,他闯进会场,跳上桌子,对着与会的那些“精英”开始撒尿,并对坡因兹曼劈头一通臭骂。[5] (P741-742)这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场面。像麦克西柯一样,品钦也以一些“鄙俗”的描写,表现了他对权力、对“选民”、对“精英”们的蔑视和不屑。在他的笔下,既有高雅的叙述,也有“鄙俗”的描写,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消失了。
《万有引力之虹》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文本,以“不确定性”的后现代叙事对元叙事所表述的理性和秩序进行了消解。通过瓦解秩序,混沌进入了读者的视野;通过批判绝对理性,天性——也就是自然秩序和人性自由,得到了关注;通过对权力的蔑视,僵化的等级制度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在后现代的叙事文本中,品钦呈现给我们一个异质性、多元化的后现代世界。
真理、理性和秩序本来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然而,万物有度,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走向了谬误。理性一旦被供奉成了君主,秩序一旦被绝对化成了教条,人性就会惨遭压迫和摧残。后现代主义叙事文本通过以不确定性、开放性、异质性和多元化为武器,向以稳定性和整体性为特点的宏大叙事发起了进攻,从而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有利于解放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人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