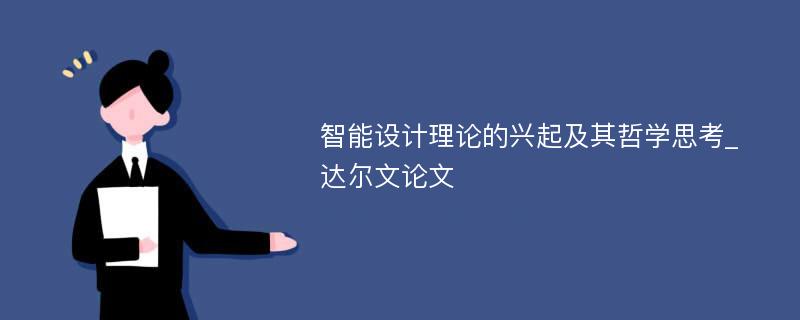
智能设计论的兴起及其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智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9)09-0008-07
强调在精致有序的自然界背后有一个设计者,这决不是智能设计论的首创。自西方文明诞生以来,诸如此类的论证不绝于耳。其实,这一现象也不难理解——人的天性之一即表现为擅长于追因溯果,面对一个外在于自己,又无时无刻不生活于其间的自然界呈现出来的和谐有序,他总想找到一个原因,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的智力探索。从试图解释自然界所呈现出来的秩序出发,我们看到了设计论思想的萌芽。设计论思想最早可以直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在自然神学中更是达到顶峰。自达尔文理论诞生以来,物种及其适应性状的起源乃至整个生物界的和谐有序无需再借助上帝的出场——自然选择理论就可以解释这一切现象。然而,由于神创论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因此,尽管设计论在学术界已经难觅知音,但它却依然影响着许多普通人的心灵,特别是那些希望在生命世界的构成中看到上帝神迹的信徒们。在他们眼里,只有诉诸某种智慧的设计才能解释生命界纷繁复杂的现象,而这就是上帝存在的最好证据。鉴于传统的神创论几乎就是宗教教义的一部分,显然它难以与货真价实的科学理论——自然选择理论相抗衡,于是在当代美国,神创论以一种新的面目——智能设计论——出现。据说,这是一种科学理论,甚至可以替代自然选择理论。本文即围绕此问题而展开。
1 什么是智能设计论
说起来,智能设计论还很“年轻”,1991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詹腓力(Philip E.Johnson)出版的《“审判”达尔文》一书,标志着智能设计论正式加入反进化论的行列,这是它在美国的首次亮相。智能设计论主要关注生物的适应性状及物种在地球上如何形成以及上帝在此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由于智能设计论出现的时机恰逢“要求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开设创世论课程”的一系列官司的败诉,这一时间上的巧合使得有些进化论者把智能设计论称为“地下创世论”或“创世论2.0版”。人们普遍同意,智能设计论的重点不在于关注最早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体如何产生,而在于指出进化论在解释后来生命的惊人复杂性时所具有的缺陷。
如前所述,詹腓力是智能设计论的奠基者。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身份是一位法学教授,而并不是一位科学工作者。他之所以提出智能设计论的观点,与其说是出于要理解生命的复杂性这一科学愿望,还不如说是为了捍卫上帝的地位这样一种使命感——因为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公众正在逐渐接受一种纯粹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样的忧虑在宗教界内部引起强烈反响。詹腓力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也许是出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兴趣,詹腓力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审视现有的科学证据,从而质疑“进化乃事实”的观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位研究学术的教授,专长是分析辩论中所用的逻辑并且辨识辩论背后的假设……我的目的是考验科学本身的证据,并且审慎地明辨证据本身的意义和宗教或哲学方面的偏见……我要明察的是达尔文思想是否基于公允客观的科学证据;达尔文主义是不是另一种变相的原教旨主义”[1]。他把智能设计论比喻为能够劈开木头的“楔子”,寓意智能设计论能把科学从“无神论自然主义”的枷锁之中解放出来。其目的是“要把社会公益事业(主要是教育)置于宗教教义的基础之上,从而复兴美国文化”。因此,公正地说,智能设计论在其诞生之初,就并非源于科学传统。
自然界的纷繁复杂暗示了一个设计者的存在,这个观点源远流长,在威廉·佩利的自然神学中达到高峰。达尔文在提出“自然选择”之前,他本人也曾被设计论的论证吸引。然而,对于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们来说,“设计”这一视角已被用“皇帝的新衣”装扮一新,这件“新衣”就是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迈克尔·J·贝希(Michael.J.Behe)在其著作《达尔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论对进化理论的挑战》一书中,表达了他对分子机制“不可降低的复杂性”的敬畏。贝希强调:从纤毛到凝血机制直至人的眼睛,都是复杂的生化系统,要使其发挥功能,必须有若干部分的相互配合,而自然选择显然无法解释作为一个系统起作用的生化现象。因为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看,生物的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功能却只能处于“有”或“无”两种状态。所以在贝希眼里,自然选择学说难以解释一个具有不可降低的复杂性的系统。为了使他的观点更加具体生动,贝希举了老鼠夹的例子。为了使一个老鼠夹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它必须由若干部分组成:①做底托的木质底板;②起着关键作用的金属锤杀棒;③支撑捕杀器时起固定底板和金属锤作用的弹簧;④稍加施力就扣杀的捕杀器;⑤暂时支撑捕杀器时可与捕杀器相连并可钩住金属锤的金属棒。贝希认为:老鼠夹任何一个部件失效,都会使系统的基本功能丧失。与老鼠夹的例子相似,生物系统也具有不可降低的复杂性,而这不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可以解释的。因为某个系统要经受自然选择的考验,就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说,具备在现实生活中完成某项工作的最基本的能力[2]42。贝希由此断定:如果一个系统具有不可降低的复杂性,则这个系统就不能用自然选择理论进行解释,于是只能求助于智慧设计。“这些系统的设计并非依据自然法则,也不是出于偶然性或必要性,说得确切些,它们是计划的产物,设计者知道系统完成后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然后采取步骤将其生产出来,地球的生命从其最基本的水平,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讲是智能活动的产物”[2]182。
威廉·邓勃斯基(William Dembski)是一位受过信息论训练的数学家。在其《理智设计论——科学与神学之桥》一书中,邓勃斯基发表了他对智能设计论的看法:“智能设计论(在该书中,被翻译为理智设计论)是为了说明复杂,富有信息的生物构造,智能原因是必不可少的,且智能原因是可经探测的,即存在明确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根据世界的观察特征可靠地区分智能原因和无目的的自然原因。每当这些方法探测了智能的因果性时,它们所揭示的隐含实体是信息。信息成为智能原因的可靠指示剂,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合适对象。于是智能设计论成为一门探测和衡量信息并说明其具体来源跟踪其理想的理论。因此智能设计论并不是对智能原因本身的研究,而是对智能原因所引起的信息路径的研究”[3]104。与贝希的不可降低的复杂性相似,邓勃斯基的立足点是“具体的复杂性”。他指出:我们无论何时推断设计,都必须确定三件事:偶然性、复杂性和具体性。“偶然性确保所述物体不是无法选择其结果的自动且非理智过程的产物。复杂性确保该物体并没有简单到可轻易加以解释的程度,具体性确保该物体表现智能的范式特征的典型”[3]132。用复杂性——具体性标准的方法推断设计,等价于探测复杂具体的信息,为了使他的观点通俗易懂,邓勃斯基以有序有意义的树叶作类比。如果你看到一堆树叶,它们排列组合成一些有意义的单词,句子,段落,甚至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时,那就是一种具体的复杂性。因为只有具体的复杂性才能产生信息,才具有意义。而这些传达出某种特定的信息的树叶显然不是一种随机、盲目的组合,只有通过智能设计论才能得到解释。问题是,如何证明复杂性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呢?也许是出于邓勃斯基的职业兴趣,他构造出了一种数学模型“解释过滤器”,用来区分三种类型的进化原因:偶然的、必然的和设计的。他还试图通过计算概率说明偶然突变和自然选择不能解释进化过程的“具体的复杂性”。
2 智能设计论的特点:披着科学外衣的新自然神学
20世纪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当然不会像19世纪的威廉·佩利那般直接,他们不会说生物界的纷繁复杂预示着某个钟表匠的存在。他们会说,难以相信这样的复杂性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通过这样一种逻辑推理,自然界的复杂性直接指向了某种智慧的存在。人们有理由追问:这种智能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们到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威廉·邓勃斯基甚至强调:智能设计论既不预设创造者,也不预设奇迹,智能设计论是神学最低限度论的,它探测智能,但不沉思智能本身[3]104。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能使科学界感到满意——如果智能设计论一定要标榜自己是科学理论的话。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科学家的工作,主要集中于“能说,并且应该说清楚的部分”,即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自然。在科学的蓝图中,引入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智能设计论,这无疑是对科学的巨大亵渎。所以,智能设计论虽然没有把“智能”直接归之于上帝名下,但是,这改变不了其神秘主义的性质。一些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强调“如果说人类的词语尚不能描绘咖啡的芳香,那么他们又怎么能捕捉像上帝这样的微妙之物呢?”需要说明的是,想要描绘咖啡沁人的芳香,人类的语言的确略显贫瘠,但科学家对于咖啡何以香如许的原因已经给出解释——科学家们在对咖啡的香味进行气相色谱法成分分析时发现其主要是由酸、醇、乙醛、酮、酯、硫磺化合物、苯酚、氮化合物等数百种挥发成分复合而成。其中,脂肪、蛋白质、糖类是香味的重要来源。而且这些香味很多并非咖啡豆的原始成分,而是在烘焙的过程中,咖啡中含有的其他成分彼此发生反应,形成的新的化合产物,最终产生出独特易挥发的物质——咖啡的香味由此而来。上帝和咖啡的浓香显然不具可比性,上帝是远在人类的经验之外的,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科学的底线就是对自然现象做出解释时,不能引入神或者说超自然原因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以詹腓力、贝希、威廉·邓勃斯基为代表的智能设计论的鼓吹者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了最新的生化理论,如细菌鞭毛、人类的凝血机制等,强调自然选择理论在解释诸如此类的问题时的苍白无力,从而声援自己的智能设计论。细读他们的作品,颇有“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味道。要知道,这些最新进展,无一不是科学家们(主要是生化学家们)的科研成果。当他们强调“自然选择难以解释这些生化现象,只能诉诸某种智能设计”的时候,与其说这显示智能设计论的地位,还不如说这显示了当今时代科学的强势。因为就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初,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们都要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寻找神学的理由。哥白尼把自己的著作奉献给教皇,伽利略在教廷的权威面前退缩了;笛卡尔的反对者指责他设计了一个十分有效的宇宙机器,没有给上帝的控制留下余地,但他仍然认为自然界的数学定律是上帝创立的,通过思维可以接近上帝;牛顿的一生对化学好像比对天文学更感兴趣,对神学好像比对自然科学更感兴趣,正是他提出上帝是“第一推动”,而且他本身就是个宗教徒。即使当他们的学术观点遭到神学方面的谴责时,科学家本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信仰,虽然他们的信仰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看来未必正统。其实这些现象不难解释:当科学还未能与技术,与工匠的实用领域相接触时,对社会的福利还不能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和承诺时,科学只能是少数有闲的社会精英人士的思想活动。“本质上它满足的仅是人类对宇宙奥秘的强烈求知欲望。这样的欲望必须贴上神圣的标签,才能被社会及从事者心安理得地认同。而上帝作为造物主的形象早已是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这时,对宇宙奥秘的揭示自然就成了对上帝本性的揭示、理解乃至赞美。这就是从事科学的最好理由,其神圣性不容置疑”[4]。
今天的科学早已取代了神学昔日如日中天的地位,当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们都在引用现代科学的最新知识为自己辩护的时候,科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说哥白尼、伽利略这些科学家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某种设计,是因为科学发展自身的限制——只有等到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理论之后,自然界的纷繁复杂才不再需要借助上帝的出场。那么,在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之后,如果还满足于做一个智能设计论者,就需要一些特别的理由了。如果认定某物是被设计的,那还有什么工作能留给科学家做呢?退一步讲,假如威廉·佩利“正确”地指出了哺乳动物的眼睛无疑地表示了智能原因的标记,这一认识对于科学家更好地理解眼睛的结构一点帮助都没有;相反,科学家也许连研究的动力也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旦认定自然界的纷繁复杂是出于某种智能的设计,这就会使一切科学探究陷入停顿。尽管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总是不由自主地引入目的因,因为目的显示了功能。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在其《心血运动论》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血液循环理论,这一理论被恩格斯誉为使生理学成为科学的标志。哈维的这一重大发现,与他对静脉瓣膜功能的揭示密切相关。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静脉瓣膜的重要作用正是阻止血液的离心运动,使血液只能做向心运动,故血液的流向具有一定的方向。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底,血液循环的思想也就呼之欲出了。实际上,早在哈维之前,他的老师法布里修斯(Hieronvmo Fabricius,1537-1619)就已经发现了静脉瓣膜的存在,但是,他对此的解释是“瓣膜的存在纯粹起制止和延缓血液流动的作用,以避免血液因受自身重量影响而太多地流入手足并在那里过量聚集”[18]。哈维宣称:“当我分析我的资料,……来自研究心室和进出心室的脉管,研究这些脉管的对称和大小——造物主不会无的放矢,不会无目的地使这些脉管具有大小的形态——或者来自对瓣膜位置及结构的专门研究……我想是否有可能存在一种循环运动,现在我发现确实如此。”[5]55是的,正因为哈维坚信静脉瓣膜肯定有其存在的目的,所以他才会在这方面孜孜不倦地努力,最终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难怪有人会半开玩笑地说,目的论是科学家的情人,在公共场合不能出现,但私底下科学家却少不了它。需要强调的是,在科学工作者最终给出的科学解释中是丝毫没有目的论色彩的。因此,像智能设计论这样一种理论即便从智力上也难以打动人,而科学解释往往能带给人一种智力上的满足。
智能设计论最引人瞩目的地方莫过于它与科学界的几场官司。进化论者和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都借助法律程序捍卫自己的论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国家法律来限制或捍卫一个具体的理论。法律在此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需要指出的是:法律之所以在这场争论中如此重要,与智能设计论起源于美国这一背景密切相关。美国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在美国人眼里,法律只规定底线——某些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否则就是触底,除法律明令禁止的事情之外,什么都能做。这也正是智能设计论和科学界都试图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立场的缘起。科学界试图通过诉讼,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智能设计论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宗教。美国是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一旦智能设计论被定性为宗教,它就不能走入公立学校的科学课堂。智能设计论的诉求恰恰相反,它试图借助法律手段谋求自己与进化论的同等地位,从而名正言顺地成为公立学校科学教育的一部分。要强调的是:讨论智能设计论的地位问题并不是说不能让智能设计论进公立学校的课堂,更不是说要取缔这种观点本身,作为一种观点,或者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如果它在人文学科的课堂上出现无可厚非,在宗教场所出现更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问题是,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们的要求显然不会这么简单,他们的目标直指科学课堂,最终目的是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分庭抗争。于是,有关智能设计论到底是不是科学理论的争论就变得尖锐起来……
3 为什么智能设计论不是科学
(1)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理论的划界标准
一方面,智能设计论认为自己是科学理论,其严谨性足以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相抗衡;另一方面,科学界一致认为,智能设计论是宗教信仰,不是科学。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科学理论呢?
何谓科学理论,学术界至今尚未取得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定义。但大家一般能够同意科学理论代表了这样一种框架,在这种框架内的观察和实验才有意义。而且,一个合格的科学理论不仅要面向过去,还要展望未来—科学理论应该能预测其它发现,并且还要为进一步的实验验证提供指导。因此,预测是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反进化论者攻击达尔文进化论不是科学理论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进化论不能进行预测。比如说100年以后,会有什么新物种出现?而物理学家却能预言76年之后哈雷彗星的准时回归——哈雷正是根据牛顿的引力定律用数学方法测算出这个结果,并预言了这个具体现象。当哈雷彗星如约光临地球,科学理论的威信凸显。
初看之下,进化论确实不如物理科学那样具有预测性,但事实上,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时间。什么是时间?虽然我们每日生活于其间,但大都没有好好琢磨过这个问题。时间首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内在时间,它源自我们内心深处对时间的体验,所以它和个人的心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常说的度日如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内在时间的真实写照。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对内在时间做过一个精彩的概述:时间是灵魂的内在度量。与此相对应的是外在时间。这是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在这样一种时间观里,未来和过去是不加区分的。爱因斯坦在悼念好朋友贝索(Bessel)时写道:“对于像我们这些信仰物理学的人而言,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顽固持续的幻象。”通过我们的日常经验可以知道,显然还有一种时间与上述两种时间观有所不同——时间明显地表现出某种不可逆性和方向性——它意味着变化。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戈金(I.Prigogine,1917-2003)有句名言:时间意味着新鲜事物源源不断地出现——是对这一时间观的最好概述。
现在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预测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科学预测中涉及到的时间呢?哈雷彗星在 76年之后会准时造访地球,这里的“76年之后”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未来吗?要知道,按照我们刚才对时间的分类,未来就应该意味着变化,而哈雷彗星的回归显然和变化没有关系,彗星的运动轨迹,是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了的,就天体的运行而言,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这里的“76年”对哈雷彗星来说只是一个循环的周期而已。就此而言,这里的过去和未来是一个完全对称的过程,只要间隔76年,哈雷彗星就会光临地球上空,往前推76年和往后算76年,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差别。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牛顿力学中无所谓“时间”,尽管在运动学公式中会出现“时间(t)”,但这里的时间却是可逆的,过去和未来是不可区别的,它只是一个物理学参量而已[6]。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瓦雷(Koyre)把力学的运动称为“与时间无关的运动,或者说得更离奇一些,在没有时间的时间中进行的运动”。
一旦这个论点确立,我们就可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具有预测功能。进化论预言了始祖鸟的存在,因为根据进化论,在所有灭绝和生存的物种之间有过渡型和中间体的存在。1861年在德国的苏郝芬(Solnhofen)石灰石矿场,出土了第一块始祖鸟化石。如果在预测中过去和未来不可区别的话,那么预言在遥远的过去有始祖鸟的存在,与不久的将来哈雷彗星的回归,完全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哈雷彗星所代表的将来,和始祖鸟所代表的过去,在预测那里完全同构。
但是另一方面,进化论不能预测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物种,也不能预言物种走向、进化趋势。问题是这决不构成进化论的软肋,其他科学理论事实上也没有这种意义上的预测功能。科学预测仅指本来就存在的物体(大到始祖鸟、哈雷彗星,小到分子、夸克),只是这些物体暂时没有被发现而已。重点在于“没有被发现”,而不是“不存在”。——换句话说,科学预测的对象是本来就存在着的,这一点确凿无疑。“未来会出现什么新物种”,意味着要求进化论对一种本来并不存在的新物种进行预测,这显然超越了进化论,或者说所有科学理论预测的能力范围。
由此可见,进化论的确是一门严格的科学理论,它预言了始祖鸟的存在,而且这一预言已被证实。反观智能设计论,强调进化论不能解释生命的惊人复杂性的同时,预言有某种“智能”的存在,却对这种“智能”语焉不详,更不要说提供如何证明这种“智能”的方法了。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们是在没有经过确立一种理论所必须经过的科学论证的情况下断然宣布其为科学理论的。
其次,科学理论总是显示出某种“简单性”,正如“奥卡姆剃刀”原理警示我们的: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科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就是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概括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爱因斯坦对此作过精彩的表述;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7]。达尔文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在给当时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的信中,达尔文说道:如果我的自然选择理论必须借助这种突然进化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为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理论就不值分文了[8]。在达尔文看来,自然选择理论存在的意义在于,它为解释自然界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当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可以有效解释自然界的复杂现象时,智能设计论所暗示的设计就成了一种多余,因为它马上引起这样一个问题,是谁设计了设计者?这就会使问题陷入了无穷倒退之中。当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们一再强调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只能是出于某种智能的设计时,这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理论应有之义。
在判决“科学创世论”不是科学而是宗教的时候,阿肯色州的法官威廉·奥弗顿引用科学哲学家的说法,指出了一个合格的科学理论的五项基本特征:
1)科学被自然定律所指导;
2)科学被有关的自然定律所解释;
3)科学可通过与经验世界的相对照而得到检验;
4)科学的结论是暂时性的,亦即它们无需是最终的表述结果;
5)科学是可证伪的[9]。
言下之意就是一个科学理论应该与可观察的经验证据联系在一起,可以用自然规律加以解释,并且它永远等待被检验。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与上述要求一一对应,它有丰富的证据,历经无数科学家的苛刻验证,最终才确认其科学理论地位的。而智能设计论永远都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检验——因为“智能”不可能被证实或证伪,从这点来看,它完全是自封的科学理论。
(2)对于复杂性的解释
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们经常用这样的方式指责进化论:首先指出自然界是如此的复杂,然后说难以相信这样的复杂性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于是,自然界的复杂性就暗示了某种智慧的存在。问题是,自然界或者说生命界呈现出来复杂性,难道只有用智能设计论才能得到解释?
著名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对“复杂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古尔德曾经举过一个“醉汉走路”的例子。一个醉汉烂醉如泥地从酒吧走出来,站在酒吧前面的人行道,人行道的左边是酒吧的墙壁,右边是排水沟。如果走向水沟,那么他会摔进水沟,昏迷不醒。假定他每次不是朝向水沟就是朝墙壁直线前进。如果让他有足够的时间,随机蹒跚前进,结果会怎么样?稍加考虑,我们就能得出结论——他一定会摔进水沟。理由很简单:每次朝两个方向之一前进的几率是50%,而左边的墙壁可以视为“反弹界限”。他如果走到墙壁处受到阻挡,停一停,一定又朝另一方向前进,也就是说,只剩下一个前进的方向——朝向水沟而已。古尔德解释道:在直线运动中,一边是墙壁,没有特定方向的随机运动,都会使位置偏离起点处的墙壁。醉汉每次都会掉进水沟,然而他的动作并不蕴含朝向毁灭的任何趋势。同理,生理平均值或是极端的例子,在甚至对进化没有任何好处时,也会朝特定方向前进;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天生的趋势,偏爱这个方向[10]168。在“代表最不复杂的左墙”,即在复杂性的最低点,进化更可能是向上而不是向下发展。这时候的变化不是随机的,只有向变得更复杂这一个方向。因为如果突破复杂性的最低点,这个物种就不可能存在。但是,一旦离开左墙,复杂性的趋势就不再只是“向变得更复杂”一个方向——物种的复杂性趋势可以随时停止,因为谁也不知道醉汉什么时候会掉进水沟,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只是很走运地走到了最后而已。正如古尔德指出的:“生命以细菌的模式,从代表最不复杂的左墙衍生,将近40亿年之后的今天,仍然还在原来的地方,显示着同样的生命模式。虽然最复杂的生物,可能随着时间变得更为精致,但是这一小小的右尾端,不足以代表全部的生物,也不能和繁荣丰富的整体混为一谈。而人类则可能因为目前所居的地位,而非常珍视这个尾端”[10]165。
为什么说当进化离开古尔德所说的生命左墙之后,向上变化和向下变化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呢?在自然界有这样一种肝吸虫,它最终以占据羊的肝脏为目标,但是它的生命周期却极为复杂:它的受精卵生长在池塘或者小河中,当长成一团球状细胞时,用球体外部表面的纤毛慢慢在水中游动。这个细胞团能够探测到水中的田螺,一旦找到目标,就能刺穿田螺的防御机制,寄生在田螺体内,然后形成许多自身的复制体。这些子代最终又变成另一种形式,离开寄生的田螺,游到水边的草叶上,然后进入潜伏期,直到被羊吃掉,进入羊的肝脏,变成肝吸虫。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生命周期啊。但对肝吸虫来说,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进入一个倒霉的羊的肝脏。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几百万年之后,羊在进化中改变了,它不再吃草了,有些羊以田螺为食,其他羊都开始吃兔子,那情况会怎么样?在吃田螺的羊面前,自然选择会迫使肝吸虫失去寄生于田螺之后的几个生命阶段,即离开田螺和寄居水草的阶段,从而降低了它的复杂性。但是在只吃兔子的羊面前,肝吸虫不得不增加一个生命阶段,寄生于兔子体内,然后指望这只兔子有朝一日成为一只羊的美食,它因此而进化得更加复杂。由此可见,复杂性在进化中的变化可以是随机的:复杂性可能会增加,也可能会减少,取决于物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对肝吸虫来说,只要能进入羊的肝脏,复杂和简单都不是问题。因此,当离开最低限制,即古尔德所谓的左墙之后,复杂性向增加或减弱方向进化的可能性是相同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尔德会说,如果把一切推倒重来,让生命再重新起源一次的话,人类就未必有这个好运了。
但是在自然界,我们的确看到了“复杂性增加”这一事实,这怎么解释呢?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那里,我们能找到很好的依据:“在一个物种复杂性的顶端,有一额外的力量在驱使复杂性增加,而不是减少。超越现存物种,就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因为在那里还没有任何竞争者。如果一个物种能进化得比现存的任何物种都复杂,它就能找到尚未被占据的生存的生态空间”[11]52。达尔文在他的私人笔记本上有这么一段描述,是对上述观点的最好概括:“复杂性本身能滋养自己,因为复杂形式的进化,为更为复杂的形式开辟新的生存方式”[11]52。要强调的是:正如古尔德所认为的,在设定的一个比较低的限制之上,生命复杂性的范围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稳步增长。但正如“醉汉走路”理论所暗示的那样,生命的复杂性向右尾的延伸,是随机的,它随时都有终止的可能,因此右端的出现只是结果,不是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复杂性也有自己的顶端。复杂生命比简单生命含有更多的基因,它们的DNA信息更长,因此,复杂生命在复制它的DNA时更容易出错。这就好比抄写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独白比抄写一条生动形象的广告语出错的概率更高一样,复杂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会面临维持自身稳定性的问题。“随着越发复杂的生命进化中DNA信息的不断增长,复制错误也越来越成为问题。当DNA信息太长,每次复制都要出错误时,生命的复杂性就到达了自己的最高极限。当生命接近这个上限时,复杂性也就不能向上进化了”[11]69。这也正是为什么生命的右端非常细小,占据右端的物种——我们人类,在整个自然界所占比例不高的原因(在自然界中,80%以上的多细胞动物都是节肢动物,而这一门在我们人类眼中是原始而未演进的)。在这个意义上,古尔德不无幽默地说到:生命的右端只不过是尾巴,摇动不了整只狗。
这是从科学角度对自然界所呈现出的复杂性的解释,层层深入,让人心悦诚服。反观智能设计论,把自然界呈现的复杂性作为攻击进化理论的法宝,却不去寻找其中的机制,把其中的原因设想为出自某种智能的设计,然后不了了之,这显然不是一种实证的科学理论应有的态度。
问题还在于:即使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确实不能解释某些生物现象,是否一定意味着智能设计论的出场?注意这里的基本逻辑:如果理论A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遇到障碍,理论B必定就是正确的。稍加考虑,我们就会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逻辑谬误,因为在逻辑上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智能设计论连自然选择理论的补充说明都谈不上,因为正如前文所探讨的那样,它够不上科学理论的资格。
4 结语
值得庆幸得是,智能设计论的思潮尚未波及到我们国内学术界。虽然有关智能设计论的书籍慢慢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詹腓力、贝希、邓勃斯基的作品正陆续被翻译过来,但智能设计论更多是被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加以介绍,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以一种确凿的科学理论的面目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内就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可以高枕无忧了。近几年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八卦似乎一下子“热”了起来,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某些高校要开设“风水”课程的传闻不时见诸于网络、报刊的显著位置。和我们对智能设计论的态度类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如果在人文学科的课堂上出现无伤大雅。但问题在于:不论是风水还是八卦,无一不打着“科学”的招牌招摇过市。这就使得国内学术界有关“科学——伪科学”的争论陷入白热化,与智能设计论在美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讨论智能设计论的由来、现状,及美国学术界对其的种种反思,对我们的科学——伪科学之辨无疑是一剂清醒的丸药——智能设计论在美国的艰难处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风水热,八卦热的惨淡将来。
收稿日期:2009-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