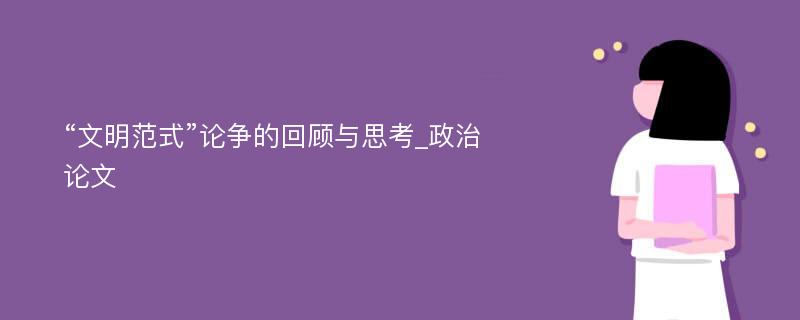
“文明范式”论争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6—0045—03
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作为十余年来国际政治学界最具有争议的理论一直备受关注。此论虽经中外学者口诛笔伐,却在“9.11事件”之后更加耀目。耀目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文明冲突论”具备了某些预见性,实则说明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其合理的内核主要集中在“文明范式”上。“文明范式”是构筑“文明冲突论”这座大厦的基石,这一基础性研究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因人们多忙于批判“冲突论”,以至学界明确针对“文明范式”的论争却不多见。本文愿就此问题作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思考。
一、对“文明范式”的批评
回顾十余年来中外学者对于“文明冲突论”的种种批评意见,可谓汗牛充栋,但专门明确针对“文明范式”的评论却不多见,我们只能从对前者的评论中提炼出一些对“文明范式”的批判观点。
(一)国家利益范式。这是影响最大的也是最普遍的批评意见,此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文明,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间的利益政治和权力政治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如钱乘旦教授认为,人类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由利益引起的,而且物质利益始终是基本的利益,完全的非物质利益(如文明)的冲突是极为罕见的,国家的利益恐怕目前还没有被超越,还没有形成超国家的“文明”的利益。[1]
(二)过简范式。以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为代表,认为亨廷顿为了追求范式简约的美德而去刻意精简范式,是将“婴儿和水”一同泼了出去。[2] 但这种简化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只收集对自己当事人有力的证据,不可避免的遵循了律师法则而实行双重标准。他认为亨廷顿所提炼出的“文明范式”正是这种患了“简单狂热症”的“政治学摩尼教”(摩尼教相信世界分为对立的两极一光明与黑暗)。
(三)冷战范式。这一派则认为亨廷顿所谓的“新范式”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罢了,所谓的文明冲突包括美国借反恐之名对阿富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等等都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虽然亨廷顿的理论表面上是七、八种文明。但是其核心仍然是“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这种“西方与非西方”、“我们和他们”的划分乃是意识形态作祟的结果,故而亨廷顿被视为新时代的乔治·凯南。
(四)封闭的范式。还有批评者认为“文明范式”无视文明的融合和正在形成的普世性的文明的事实,以封闭的、静态的、稳定的观点来看待文明。如汤一介列举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融入中国的事实,批评亨廷顿忽视了文明融合的可能性。[3]
二、亨廷顿对批评者的回应
面对如潮的批评,亨廷顿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并在1996年出版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进行了系统地回应。他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毫不动摇,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也在不断的回应过程中完善自己的理论。
亨廷顿把第一种批评意见概括为“国家范式”(statist paradigm),“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便是典型。他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替代性”(pseudo-Alternative)范式,它人为地制造了国家和文明之间毫不相干的对立。对于有人认为,“冲突的是国家而不是文明”,他认为,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所以文明并不去“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任何的其他事情。”[4] 也就是说,文明只是冲突的原因,而不是冲突的具体组织形式。
对于第二种批评意见,亨廷顿承认“文明范式”所描绘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地图的确“是非常简单化的”,“它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但是,人们研究国际政治需要这样的“简单地图(simple map)”。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反映现实,但是过分详细的地图会妨碍人们从复杂的信息之中掌握主要的东西。正如,40年来人们就是应用了非常简化但是非常实用的“冷战范式”来思考和行动的。
对于第三种批评意见,亨廷顿认为这是冷战结束后学者们提出的四种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的一种范式:“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的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就大多数目的而言,这样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他并不赞成用两个世界的范式来解释冷战后的世界政治,而且自认为“文明范式”已经完全超越了这种两个世界的范式,从而回应了第三种批评意见。而对第四种批评意见,亨廷顿似乎没有认真应对,只是大致的提了一提“文明是动态的”、会“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
亨廷顿坚信:“文明范式”可以避免当时四种政治地图的缺陷,它以七八种文明来看待世界,不像一个世界或两个世界范式那样,为了简化而牺牲现实;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它提供了一种比较简明和准确的“对于学者有意义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他甚至还反击道: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文明范式(civilizational paradigm)和观察角度(approach),那么你们能够提出什么新的范式,来取代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冲突和三个世界范式?的确,让我们去建构一个冷战后新的范式至少在目前可能性还不大。也难怪李慎之先生半似调侃地说。亨廷顿的回应使得“衮衮诸公的各种评论统统无异于废话”。[5]
三、对论争的思考
在对论辩双方观点的不断梳理后,我们仍无法为“文明范式”下一个“对”或“错”这样简单的结论。我们认为,作为一种观察视角而言,“文明范式”虽也存在缺陷,但其本身并无对错之分。有必要对“文明范式”进行重新的思考。
(一)论辩双方对“文明范式”的概念模糊不清
从文献的检索中可知,不仅是批评者,就连亨廷顿本人也未对“文明范式”进行明确的概念上的界定。这一论争基础的缺失是论争过程中的首要缺陷。那么,我们的首要工作便是对它进行界定。何谓“文明范式”呢?我们从亨氏的著作中归纳认为,冷战结束后,国家主权不断受到削弱,影响世界政治中的文化因素在上升,亨廷顿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为了给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或称地图),在研判了当时四种不理想的框架之后,他提出以现存的七、八种文明来分析世界政治,这种分析框架即“文明范式”。它实际上是一种观察世界政治的新视角——多个文明的视角。
那么,何谓“冲突论”呢?我们以为,亨廷顿依“文明范式”观察。发现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有利于非西方的转变。非西方的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加之西方的普世主义把自己引向了和其他文明冲突的边缘,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同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冲突。为此西方人必须重新肯定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并为避免文明战争而彼此合作。这一部分推论被视作为“冲突论”。
(二)范式和结论的混淆
有些批评者对“文明范式”的误读来自对范式和结论的混淆。“冲突论”是亨廷顿站在其非理性、保守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运用文明范式所得出的结论,对其结论的批判不应和“文明范式”本身混为一谈。如前文提到的第三种批评意见,因为亨廷顿得出了“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结论,便认定文明范式是新的冷战范式,这种推论是不严密的。“文明范式”是以七、八种文明来观察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分析框架,而“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是亨廷顿戴着“保守的现实主义”的有色眼镜对七八种文明均势进行分析得出的带有冷战意味的结论,这属于结论而不是范式本身,是混淆范式和结论造成的误读。还有,遭到中国学者猛烈轰击的所谓“伊斯兰——儒教联盟”也不过是亨廷顿非理性错觉下的结论。而并非“文明范式”之错。如此,则当范式本身和结论分开之后,便使得作为学者的亨廷顿和作为谋士的亨廷顿分开了,范式体现了其学者的一面,结论却让我们看到其谋士的另一面。我们不要因其结论的缺陷而把污垢连同孩子一起泼掉。
(三)一元范式论的误区
从对“文明范式”的论争中可以看出,有些批评者和早期的亨廷顿都陷入了一元范式论的误区而不自知。最常见的是第一种批评意见,他们认定“国家利益”才是世界政治的真正动力和“根源”所在,据此认为亨廷顿的观点不值得一驳,对此我们赞同王缉思的评论:“亨廷顿如此突出精神因素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确实缺乏实证分析,有失偏颇。但是说各个民族的文化、文明价值观以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通通不过是争夺利益的工具和幌子,我以为比亨廷顿偏离真理更远。”[6] 他认为,对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追求,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对物质利益和资源的争夺,都是世界政治的动力。如果认定政治冲突多起于经济矛盾,就象说谋杀案大多是谋财害命一样,缺乏科学根据。[7]批评者从国家范式出发把国家和文明对立了起来,实际上是把利益(权力)因素同文明(价值)因素对立起来,造成了“利益”和“价值”的对立,这是最常见的误读。我们以为,这种对立没有必要。按王缉思的说法:“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只能是国家、民族内部各种利益的交织,也只能是领袖和精英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认识到的利益。”如果用亨廷顿的话来进一步解释就是:“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这个认同就是价值的认同。所以,孙相东认为亨廷顿并不想否定利益政治的本质,只是想表明文明在界定和认识利益中的过滤作用。[8] 如此,则这种对立是没有必要的,但这种误读却很普遍,如上文提到的“冲突的是国家而不是文明”的批评即是如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价值和利益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文明范式”也并不必然和国家范式水火不容。
早期的亨廷顿也坚持一元论,认为“文明范式”是国家范式的替代,我是而你非。和第一种观点坚持利益是“根源”一样,其早期的论文也认为文明的差异是导致冲突的“根源”(source)。从语义上分析,“根源”一词具有排他性,如果利益是根源,文明则必然是从属,反之亦然,这实际上又造成了价值和利益的对立。但是到后来,亨廷顿在专著中却始终回避这一用词,可见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还进一步缓和了“文明范式”和国家范式的关系,他认为“文明范式”不是对国家范式简单替代。前者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无用,它们是相容的。我们也认为,文明虽然日渐重要但也不至于是“根源”,其早期的“根源论”,未免夸大其词。实际上,如果非要讨论到底谁是“根源”。是经济利益还是文明价值,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也许永远没有答案。
既然“文明范式”和国家范式并非水火不容,那么。我们对“文明范式”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国家范式的否定。尤其在解释如此复杂的世界政治时,运用任何单一的范式都难以圆满,需要从多元的视角来观察。如亨廷顿认为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失败,是因为西方国家把票投给了同一文明圈的澳大利亚;但对于台湾拒绝给同为“儒教文明”北京的投票却避而不谈,亨廷顿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双重标准的尴尬之中。其原因并不是如哈拉尔德·米勒所批评的“文明范式”过于精简,而是因为范式的单一所致。台湾不给北京投票,显然是无法用“文明范式”来解释的,而用利益论却迎刃而解。所以,“文明范式”并不能包医百病,多种范式并用才能更好地解释世界政治。如同市场经济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的争论一样,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都将是有害的。当世界需要多元范式的时候。“文明范式”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不错的选择。从多元范式的观点视之。文明和利益都是世界政治的推动力,都是解释世界政治的需要,这是亨廷顿和他的批评者都需要注意的。
(四)亨廷顿化的“文明范式”及其局限性
可以看出,亨廷顿对第四种批评意见的回应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在于亨廷顿化的“文明范式”存在着自身的先天缺陷。“文明范式”之所以受到批评,主要因为在为“文明冲突”论证服务的过程中“文明范式”被亨廷顿化了。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它只强调差异性,于是“文明冲突”变成为理所当然的结论;对普世性的拒斥,又使其对于解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对话与合作显得无能为力。这样,给人的印象便不是“文明范式”而是“文明冲突范式”了。
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人们最大的文化认同,其主要的因素是宗教和语言。这倒并不为错,但是为什么在他的笔下,文明就必然会冲突甚至会发生“文明战争”呢?我们认为,这是亨廷顿对文明的狭隘理解所致。他戴上了保守的现实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有色眼镜,为了论证“冲突”的需要,以最富悲剧色彩和最悲观的习惯对文明进行了理解。在他的笔下,文明被视作一个不动的板块,文明即便在发展当中也始终保持着其纯洁性,具有恒定不变的性质,也就批评者所说的“静态的”、“封闭的”文明观。“文明范式”就这样被亨廷顿化了。如此,则伊斯兰文明具有不变的“好战性”等。于是,在亨廷顿看来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文明间的融合和交往变得没有可能,那么好战性等等特性使得“文明冲突”的结论便水到渠成了。这种认为各个文化具有先天固有的、不变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认识,常被视作为“文化本质论”而受到批评。[9] 再由于他对文明的这种亨廷顿式的理解,也使他和批评者在普世文明的概念上分歧巨大。他认为批评者所提出的几种普世文明概念,都是一些不恰当或不深刻或二者兼具的认识,对于解释文明冲突毫无意义。因为,亨廷顿所理解的普世文明实际上是指的宗教大融合的普世文明,这显然是难以看到的。据此,他断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存在一个所谓的普世文明。然而。当今世界广义的普世文明(即他所批评的普世文明)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毕竟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存在,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化政治现实,他的“文明范式”却视而不见,不能够有任何作为,说明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对亨廷顿的文明概念进行改造,不把文明看作为狭隘的、封闭的板块,则可以使我们看到文明既冲突又融合,既有相对稳定的形态,也一直向前发展变化。即不仅体现着差异性。还在另一个层面上看到普世性,差异性与普世性达到了统一。这样来理解“文明范式”,不仅能够解释世界的冲突。也能促进全球化带来的合作与对话,从而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那么,“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无从发生。这样难道不更好吗?
总之,“文明范式”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范式,但由于中国学人的兴趣多集中于对“文明冲突论”的讨论,却对这一理论问题少有人问津,在此提及“文明范式”只为抛砖引玉。以使其研究更加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