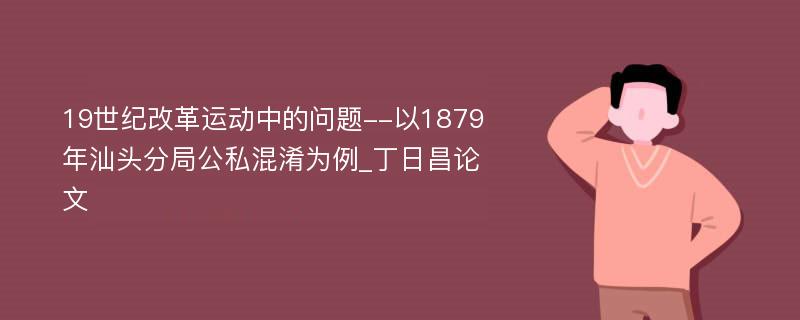
19世纪改制运动中的难题:1879年招商汕头分局公私混淆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汕头论文,公私论文,分局论文,难题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初以来清朝的改制运动涉及政府内外的许多范畴,诸如官制、税制、洋务等,其意义深远。但是对这些改制运动的评价,学者们从来都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两种观点:一是以费维恺为代表的否定论。该论认为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任何社会改革的根本,而洋务改制运动少的就是政治改革,因此是注定要失败的。用费君的话来说,没有政治改革,再多的坚船利炮也无济于事。(注:Feuerwerker, Albert, China' 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New York, Atheum, 1970) , P59.)这种观点源于冷战时期,虽然年深日久,在学界依然有影响,尤其能迷惑刚入门学习中国历史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最近以罗威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从“社会—国家”这个新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与上述的否定论大相庭径。在他们看来,改制运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新兴事物,如商业的发展,对原有的国家架构形成的压力,以及清统治者自身的调整。罗君的观点在他的“公共领域”这么一个概念里得到了集中的阐述。(注:Rowe, T.William, Commercial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lso see "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rn China" , in Modem China, July 1990, P309-322.)上述两种观点无疑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各自也都有盲点。如果洋务自强真像费君说的那样一无是处,那又怎么解释那时打下的近代工业基础呢?如果改制是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那又为什么无法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呢?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剖析1879年招商汕头分局“公私混淆案”,来试图解释19世纪改制运动中的难题。本文的重点,则是清朝财政政策及其改革和执行,而最终要证明的观点可以表述如下:正是纵横交错于清政府内外的“非正式财政体系”,把19世纪改制运动置于两难之境。
一
清政府的财政改革,可以说是整个改制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尤其在19世纪财政收入日落西山、危机迭起之际,财政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所有的其他改革。有关清朝财政的资料可以说是太多了,同时又太少了。有清一代中央集权,地方政府的所有财务处理都必须上报户部审批,再由户部造册以备谘皇帝天聪。由此留下来的册、表、章、奏、批,可谓汗牛充栋。另一方面,由这些文件反映出来的政府财政的实际运作却又微乎其微,因为这些公开的文件,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用语甚至内容,做出来让皇帝和公众看的;在实际运作中的种种具体过程,尤其是有违章嫌疑的细节,则不会包括在这些文件里。因此,研究财政改革不仅要基于这些政府的文件,还要考虑到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卷入这件事情的人员,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品味出文件中没写出来的奥妙。这些奥妙比任何规章制度都更确切地反映出清朝财政运作的真实面目。
为了更好地展开对19世纪财政改革的讨论,让我们先来看看1879年轮船招商汕头分局“公私不分案”的始末。广东汕头厘金局的蔡伦书,长期把收上来的厘金税款存在一家叫做乾泰的私人钱庄里吃利息。1877年乾泰破产,蔡血本无归。为了弥补损失的税款,他从另一家叫顺泰的钱庄里以12%的高利息借了一万两银子。此后每当蔡收取了新的厘金税,都饥不择食地存到其他钱庄里,来挣取更高的利息,以偿还顺泰的本和利,并希望有朝一日弥补此前损失的厘金税款。这些公私款项的所有转移和交割,都通过招商局汕头分局的钟循来处理。钟循把蔡的厘金税款存在一家由香港人吴绮云开的和记贸易行里。吴是香港永同兴贸易行的东主的公子,来汕头扩展生意时与钟循成了好朋友,此前钟多次在他那里存款生息,没失过手。这次除了蔡送来的厘税11000两以外,钟还把2880两招商局款和3900两商局代收的赈灾款,一起存在和记贸易行里。像往常一样,吴答应一旦需要,钟可以随时取款。但是在1878年初,香港永同兴贸易行因资不抵债而宣布破产,吴无法偿还钟循的存款,便于当年6月不告而别,逃往香港藏匿起来。这样,归还蔡的厘款、招商局的局款和赈灾款共18000多两的重大责任,便都落在了钟的头上。钟循纵然有三头六臂,一时也无法筹措这么一笔巨款。1879年6月,福建巡抚丁日昌突然发难,就此案指责招商局的财务混乱,并对钟循穷追不舍,要求严加惩办;并扬言说,如果商局不认真办理,他就会同南北洋大臣,务必弄个水落石出。在丁的压力下,商局开始对钟案进行调查。可是调查并不顺利,拖泥带水地折腾了好几个月。最后由官府行文,通缉首犯吴绮云;既然吴已经逃跑,何记贸易行在汕头的财产全部没收入公;钟循被永远踢出招商局,并勒令其归还所损失公款的一部分。(注:钟循供词,招商局档案#468(2)/41,中国南京第二档案馆藏。)从1880年以后便再也没人提到这个案子,钟循是否按规定偿还公款也不清楚,整个“汕头招商分局公私混淆案”于是便不了了之。
1877年和1880年之间发生在汕头招商分局这件案子的真相,也许再也不会大白于天下了。但是此案发生的前因后果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公款的损失会发生在“公款生息”这一政府行为上?考虑到这种行为并非偶然,这个问题就更有意义了。第二,既然香港永同兴贸易行早在1878年初就倒闭了,从那时起钟循存在那里的公款肯定就已经没有了着落,那么为什么直到一年以后该案才曝光呢?其中的猫腻不言而喻。第三,汕头在广东省的管辖之下,出了事该由广东巡抚来处理,为什么实际上是福建巡抚丁日昌出面?诚然,招商局不同于一般政府行政部门,从来都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禁脔,但是不论是从名义上的管辖权还是实际上的责任,都轮不到丁说话。第四,既然丁一开始就大张旗鼓,颇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最后怎么又不了了之呢?对钟循的处理是不是依法办事?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就可以管中窥豹,略见当时财政及其改革之一斑;改革中怎样遇到难题,为什么解决不了等问题,也随之释然。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公款会在“公款生息”过程中损失?公款生息作为政府行为由来已久,到了清代已经非常普遍了,比如说内务府,就经常在私人钱庄里存钱。(注:关于内务府的功能及其在清代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地址和作用,请参看Torbert, Preston M., The Ch' 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 1662-1789,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北京政府对公款生息的控制一贯很严,所有的款项来往必须造表报给中央的户部,生出来的息款也规定要用在公共事业上。由于清帝国疆域辽阔,政府部门多如牛毛,对公款生息进行管理肯定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公务。不过在国家机器运转还良好时,公款生息似乎还没有给中央造成太多的麻烦。但是从19世纪以来国库渐空,1840年以后的10年里,政府每年的赤字高达900万两,大概是正常收入的四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与太平军的战争可以说是清代财政管理的一个转折点,厘金制度的启动及其运作典型地表明了中央的财权如何逐渐落入了疆臣手里。(注: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在这种大气候下,公款生息的管理也成了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范围。这种财权下移的趋势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以后,疆臣们就是靠这条财路来发起洋务自强运动的,如兴办招商局。与此同时,上述财政改革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央的管理逐渐削弱甚至不再存在。原则上,只要地方政府向户部造表申报,就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开发财源,就地使用。这就几乎等于放任各级政府部门巧立名目来致富。由于当时捐纳制度已经蔚然成风,许多商人用钱开路进入权力结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政府里捐个一官半职不仅是为了光宗耀祖,也是为了赢利。一旦中央的约束少了,就给他们造就了捞钱的广阔天地。在这种大环境下,公款生息也就成了官府中以公谋私的重灾区。钟循在汕头招商分局任内干的那些事,不过是沧海一粟。
作为洋务运动的早期工业之一,招商局本来也是按照集权模式来管理的。局里的所有财务都由上海的总局控制,赚了钱归总局,亏了本也由总局来填补。刚开始规模小时这种集权式的管理还可行,可是在1876年兼并了美国旗昌公司之后,问题就来了。各分局连年亏空,让总局补不胜补。于是从1878年开始,招商局顺应当时全国性财政改革的潮流,把财权下放到分局。总局先根据各分局的财产和市场定出一个数目,由分局包干,此外盈亏都由各分局自负。(注: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年版,第850页。)就像全国性的财政改革一样,商局的改革表面上好像还是挺成功的。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商局的官员声称全局的开支少了,生意多了。(注: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但是这一改革也像全国的财政改革一样弊端百出。由于权力下放了,局员们便撒开了竞相以公谋私。全局上下都在商局之外有别的生意,如徐润在上海有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并且和唐廷枢、叶思贤等人合伙办钱庄。(注:徐润:《徐愚斋自述年谱》,文海出版社台北1978年版,第33-34页。)当时招商局高息向钱庄举借了大笔债务,债主中自然少不了他们。唐廷枢办了一家揽载行,据说生意极其兴隆;不过这根本不奇怪,因为每当货运旺季,唐的揽载行是从来不必担心舱位的。(注: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1948年版,第8页。)这种公私之间的模糊不清导致了一连串的腐败案。1880年天津分局的叶显祖因为中饱公款而被开除;1883年上海房地产危机中,徐润挪用的大量局款被套牢,不得不以自己的股份填补,市价高达48万两。(注:张厚权:《招商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204页。)相比之下,钟循折腾那么一两万两银子,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二
钟循的案子固然很小,可毕竟也涉及了公款,一旦出了事,也不是说要脱身就能脱身的,可是为什么钟循出事整整一年以后才引起注意呢?这是我们前边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清代官僚机制和财政运作入手。财权一贯是北京的禁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官员们的薪水也定得极低;堂堂一品大员年俸仅180两银子,而最低的从九品,则低到33两。(注:《大清会典》,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6-177页。)这些集权措施同时也给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打了很大的折扣。日益繁杂的政务加上僵硬的管理,甚至使得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也束手无策。因此从康熙中后期起,中央对财权逐渐网开一面,允许地方官员在正赋以外加收附加税,美其名曰“耗羡”,用于地方行政来提高效率。于是在正式公开的财政运作体系之外,逐渐发展起另一套非正式不公开的体系,是为“非正式财政体系”,(注:Zelin, Madeleine, The Magistrate' s Tea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 ing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颇似今天的计划外收支。雍正初登宝鼎时雄心勃勃,进行“耗羡归公”的改革,却苦于开网容易收网难。乾隆继位后,自誉要在其祖之宽与其父之严之间取其中,更使得改革不了了之。到了19世纪,这一以耗羡收取为中心的非正式财政体系成长壮大,一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以致于如果没有这一体系的参与,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便不可能。正如墨子所说的,“令公私两便”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决策和运作的原则。(注:Metzger, Thomas A., "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Ch' ing Bureaucracy in the Field of Commerce, the Lianghuai Salt Monopoly" , 1750-1840, in W.E.Willmot( ed.) ,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这样,清朝的财政其实由两套体系来运作。一套是按照《大清会典》设计的公共体系,官员们公事公办时上宣下报的官样文章自然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另一套则是非正式财政体系,也就是在公事公办的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满足各级各式办事人员的内部及私人需要。前者是公开的、合法的,而后者是隐蔽而又人人都心中有数,不完全合法而又为上下所共同接受的。这种不公开的运作极其容易滋生弊端,由半合法滑向非法。在现有的官僚体制中对这些非法行为的唯一控制,是上级官员的慧眼。但是由于这一体系已经浸透于整个官僚结构,几乎所有的官员在仕途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从中有染,成为既得利益者,其“慧眼”也就为尘所蔽,对非法行为视而不见,见而不管,管而不严。一旦有事,肇事者的上司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照公共体系的法规行事,而是通过非正式财政体系对各有关方面进行通融,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这正是1878年汕头钟循案发以后招商局内外的反应。和记贸易行关门,吴绮云远逃香港后,钟循自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在公共体系下全权处理这件案子的是他的直接上司,商局总办唐廷枢。如果要按照法规办事,唐应该立即惩办钟。但是维系唐与钟的并不仅是这套公共体系,还有另一套非正式财政体系。由于这套体系的不公开性质,两人之间关系到底如何今天是无法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猜想到,此前唐很可能从钟的不义之财那里分过一杯羹,这样,钟唐两人就绑在了同一条贼船上。这套不公开的体系有另一套办事规矩,而不是简单地对钟法办了事。唐就是按照这套不同的规矩来办事的,他利用自己在香港的社会关系,跟永同兴的合伙人罗鹤平接洽,希望让罗赔偿钟循2000两来私了此案。(注:《丁日昌致唐廷枢信》光绪五年九月,招商局档案#468(2),中国第二档案馆藏。)很清楚,只要钟能够归还部分损失的公款,唐就可以利用职权大事化小,把整个事件摆平。这就是为什么钟案发生以后的一年里,表面上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
钟循损失的公款中很大一部分是招商局的局款,作为招商局的总办和主要持股人之一,唐廷枢应该严惩钟循,才是维护自己的实际利益之道。问题是唐既在公共体系中有利益,也在非正式财政体系有利益。如上所述,非正式财政体系刚开始是作为对公共体系的补充发展起来的,可是19世纪以来公共体系越来越为这种体系所侵蚀,两者在分量上的对比逐渐向后者倾斜。更重要的是,对公共体系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在局部上进行补救的,而一旦对非正式财政体系造成了损失,则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虞,因为在这个体系中决不仅仅是唐钟两人,而是一个贯彻上下的庞大系统,其中很多人唐既不愿意得罪,可能也得罪不起。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唐只有舍鱼而取熊掌了。
三
1879年6月,招商汕头分局的钟案在捂了一年之后终于被揭了盖子。有趣的是揭盖子的人是与招商局没有直接关系的福建巡抚丁日昌。为什么呢?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简单地说,这正是非正式财政体系运作的结果。这一体系通常由一批政府内外的人员组成,通过半合法甚至非法的财务运作共同得益。一般而言,投身某一个非正式财政体系的最普通的途径,是所谓的“三缘”,也就是血缘、地缘、学缘;中国许多其他社会组织都是以这“三缘”为脉络形成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但是与中世纪印度的等级和欧洲的阶级不同,在非正式财政体系中个人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维系这一体系的并不是这三缘,而是共同的利益和风险。这个吐故纳新的过程,遵循的几乎是适者生存的原则。同时,共存的诸色非正式财政体系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也长期争斗。
丁日昌是广东人,早期由帮助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中兴大业而发迹。办轮船之议一开始,他就大力支持并勇于自任。要说他是曾左李集团的中心人物之一,是公共体制中的一位出色的“公务员”,实不为过。可是他早期与曾的关系和对近代技术的热情,并没能保证他在以李鸿章为中心、以招商局为主体的非正式财政体系中的地位。其原因想必是非常复杂的,而肯定与丁不能很好地按照这一体系的规矩办事有很大关系。据说他有一次连夜从前线回来向李通报紧急军情,门房要红包,他偏不给,在门口大吵大闹起来。如果真有此事,事后李肯定会想:不就几个钱吗?给了该省多少事儿啊!因此,1872年招商局成立以后,考虑到作为经济实体要在宦海里浮沉和丁在办事上不够灵活,李没有让他介入。不过丁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在肥得流油的招商局里分一杯羹,他一开始就努力把广东的买办、四品顶戴叶廷眷往商局里插。丁叶之间的关系如何,从现有的资料也看不出来;既然丁如此器重叶,可以相信他们之间形成的是另一个非正式财政体系,铆足了劲儿要跟李鸿章为主的体系在招商局一争长短。只是在自己的床榻之上,李岂让他人酣睡?好几年里丁对着招商局直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口。直到1878年商局总办之一朱其昂去世,恰逢好事的御史董隽翰又为收购旗昌的事对李指桑骂槐,说他有了好处独吞,一直闹到北京,折腾了好几个月。(注:《董隽翰光绪三年九月十八日奏》,《洋务运动》,北京中国史学会1959年版,第6卷,第19-20页。)为了封住众人之口,李才勉强接受叶入局,接替朱其昂的工作,专管漕运。
叶廷眷于1878年8月开始成为招商局的总办之一,但是他在局内的工作并不愉快。局里各总办之间虽然一直矛盾重重,可到底都出自李鸿章的门下,因而形成一个臭味相投的小圈子,只有叶是外人。不过他也不肯逆来顺受,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的本家叶显祖曾主持天津分局,几年前因为涉疑中饱局款被赶出局。至此叶廷眷一力承担,把显祖运动回到天津分局任上。偏偏显祖又不争气,刚回来不久又让人抓住把柄,由李鸿章亲自画圈再次赶出局。廷眷不甘心,亲自上书李,要求对商局进行人事和组织上的全面改革,李还是不为所动。相反,在对叶的工作考评上,李说他不谙商情,又与同事合不来。(注:《李鸿章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奏》,《洋务运动》,北京中国史学会1959年版,第6卷,第51-52页。)这样入局还不到一年,叶就准备辞职了。必须重申,详细的内幕今天已经不可得知。不过李上面的说法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说了真话,叶无法胜任商局的工作。如果是那样,就说明了叶和丁日昌一样,因为没能按照圈子里的规矩办事而被淘汰了;另一种可能是李在撒谎,叶本来是胜任的,辞职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如果是那样,这种压力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李本人,因为他不愿意看到叶在商局里扎根。不论是哪种可能,都只说明了非正式财政体系运作起来能量非同小可。
不用说,丁日昌坚信的肯定是第二种可能性。愤怒之余他开始反攻了,而机会有的是,汕头分局的钟循案就是其中一个。由于丁一直都盯着招商局找破绽,钟循案发之时他很可能就已洞悉,之所以没有马上发难,是因为叶廷眷正在局里,投鼠忌器,为了自身利益甚至帮着遮羞也不是没有可能。到了1879年6月,叶出局成了早晚的事,丁拍案而起的时候也就到了。在他给南北大臣的谘文中可以看出来,当时他可以说是怒发冲冠。(注:大清会典,中华书局北京1991年版。)钟案发生时他装聋作哑,一年以后又大张旗鼓,就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对这种离谱的反差的最佳解释,就是两个不同的非正式财政体系之间折中的结果。
四
丁日昌发难以后,钟循终于吃了苦头。不管丁的动机如何,一旦抓住了李鸿章和唐廷枢的小辫子,非正式财政体系运作中的种种猫腻毕竟还是上不了台面的。这也说明了这种体系再强大,还是没能完全取代公共体系的合法地位。但问题是,对钟循损失18000两公款的惩罚,是不是罪得其所呢?清代对贪污公款的惩罚之严是有目共睹的,此前为数不少红顶子曾经为此人头落地。而钟循只是被勒令赔偿部分公款并开除公职而已,几乎等于是无罪释放。那么其中有什么文章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大清律令的原则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清代政府官员的犯罪有两种:一曰公罪,二曰私罪。公罪者,官员在执行公务时无意犯法也;私罪者,官员的犯罪动机是有意谋私也。清律对私罪的惩罚远远比对公罪的惩罚要严厉得多。(注:Metzger, Thomas A.,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Ch' ing Bureaucracy,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137页.)公私罪之间的这种区分无疑是要表明,在以儒家道德为准则的政治结构里,无意识的犯法都是可以宽恕的,也就是一般人常说的好心办了坏事。墨子可锁定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动机的不同,(注:Guy, R.Kent, Rule of Man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the Cas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of Provincial Governor during the Qing, Paper for 1992 International Study Seminar on Chinese Law,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而盖博坚进一步指出,在实际运作中这种区别很难把握,因为时势、人缘、官品,无一不对动机的定位有重要的影响。(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新华出版社1950年版,第24页。)只要犯法的人能够设法证明自己的动机是为公的,就可能逃避应有的惩罚。招商汕头分局钟循案的处理,就可以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清律从没有把公款生息的活动列为非法,前提是所生之息必须用于公。可是除了钟本人,恐怕谁也无法证明他当时的动机到底是为公还是为私。只要他坚持说本来是想赚了钱归公的,只是没想到会受骗,他的罪就会按公罪处理。可以想象,在这上面摔了跟斗的每个人都会这么说,可并不一定都得到公罪的待遇。所以另一关键是仲裁者,也就是犯罪人的上级,是否愿意接受当事人的解释。在钟循的案子中的直接仲裁者是唐廷枢,而隐隐约约坐在其后的是李鸿章,这两人无疑都选择相信钟的说辞。所以丁日昌挑战的对象绝不是区区钟循,而是一个庞大的非正式财政体系;这个体系可不是丁单枪匹马所能动摇得了的。
当然,丁日昌也还不是没有希望,因为他总还有上诉的选择。不过他和李鸿章同为疆臣,再往上就是皇权了。从理论上来讲,皇权是儒家伦理社会次序的最后把关者,是天下为公的终极保障。可是实际上,清代的皇权也是非正式财政体系的受益者。通过捐纳制度,滚滚财源流进皇上的腰包。鸦片买卖和吸食在雍正时就是非法的,可是此后一百多年居然禁而不止。对此范文澜先生早就敏锐地指出,皇帝一只眼看到鸦片走私的恶果,另一只眼则看到其带来的好处。(注:Spector, Stanley,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of the Regionalism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5) , P118.)一旦皇帝成了这种体系中的一部分,就很难指望他真会拿它来开刀了。在非正式财政体系大行其道的当时,钟循捣鼓那么一两万两公款非常微不足道。案子之所以公诸于众,完全是由于分赃不匀给了丁日昌一个意气用事的借口。皇上妻妾成群又日理万机,哪有功夫管这种小事?不过再退一步说,皇上真地接了丁的上诉,升堂对钟循问罪了。真相大白后龙颜大怒,想必要砍钟循的头;那没问题,因为钟不过是个买了个七品衔的满身铜臭的商人。揪出了钟,势必要牵连出唐廷枢来;那也问题不大,唐某的四品顶戴也是用银子捐的;不过端坐在唐后边的,可就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正二品中兴名臣,拥兵数十万、门生满天下的李鸿章了。皇上如果真地要跟李对放,胜面还是会大些,但肯定不会没有代价。所以不到迫不得已,皇上不会那样做的。
以上臆想的场景只能建立在龙廷上坐着的是个尧舜皇帝这么一种假定之上。但是当时的西太后并不是尧舜,她有自己的小算盘。众所周知,李鸿章大业之成离不开太后的支持;而李的大业既成,她也不是个输家,因为从那里得到的好处,不管是合法的、半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绝对少不了太后的一份。甲午战后盛传的政治谣言之一,就说到李动用了中央拨给北洋水师买军舰的公款来给太后祝寿。真相如何至今也还是个谜,但是当时原定从德国购买两艘一等军舰的四百万两,最后只从英国买了一艘二等军舰,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处理钟循案时能够把钟赶出局,可能就是丁日昌力所能及的最佳结果了。可怜的倒是吴绮云,财产入公,人被通缉,即使也是罪有应得,到底有几分冤枉:因为从太后到李鸿章到唐廷枢,都需要一个替罪羊来祭祀公共体系,哪怕这个公共体系只剩下了空壳一个。这个替罪羊自然非吴莫属。
1880年初,叶廷眷给退休在家的前兵部侍郎广东巡抚郭嵩焘写信,抱怨说在洋人的竞争下招商局每况日下。而郭可没把此话当真。他在日记中写道,“此非洋人之所能攘夺也。招商局诸人自怀攘夺之心,相与谋利而不顾其害。”(注:《郭嵩焘光绪六年二月十三日日记》,《郭嵩焘日记》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郭本人没有参与过商局的运作,所以不可能知道详细内幕;但是他在宦海里浮沉了多年,这时凭直觉作出的论断却是非常精确的。1879年招商汕头分局的那件案子,真相也许永远也不会大白了。但是从其来龙去脉和其中心人物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的改制运动,既不像费维恺说的是由于政治上保守而全面失败,也不像罗威廉说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变迁。改制的得失,更多的是受制于与公共体系并存并日益侵蚀该体系的非正式财政体系。不论是什么样的改革,只要触犯了这种体系的利益,就注定要困难重重,甚至半途而废。换句话来说同样的意思,如果改革同时也照顾这种体系的利益,就会一路绿灯,皆大欢喜。因此,公共体系与非正式财政体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像中世纪末西方的社会与国家之间那种简单的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更多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长共消的关系。
藤原时代的日本,大化维新的影响日趋消亡之际,在中央皇权的架构里逐渐成长起来了一种半合法的“家政府”体系,由各大家族垄断和世袭政府里的职务。到了12世纪末,这种家政府的体系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开启了日本封建时代。19世纪中国的非正式财政体系与藤原日本的家政府体系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只是由于中国的皇权远比日本的完善,这一体系始终没能完成从半合法到全合法的飞跃,而只能以“寄生虫”的形式,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与公共体系共存。因此该体系的能量释放,不是基于西方经验的种种理论所能适当解释的,因为它有时会是对公共体系正常运作的干扰,有时又是它的前提。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每逢改制,都是各非正式财政体系之间进行利益重新分配的时机,该体系的能量释放也会格外激烈和不可琢磨。这才是19世纪中国改制运动的难题:固然不一定成功,却也未必注定失败。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时势和人事,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