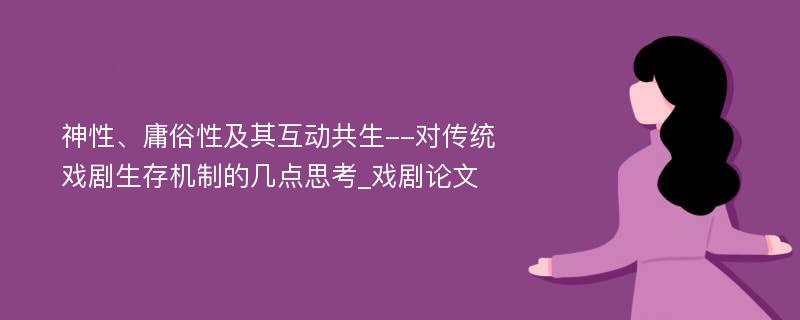
神性、俗性及其互动共生——关于传统戏剧生存机制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戏剧论文,性及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14)04-038-08 在当下,生存仍然是传统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传统戏剧是指在我国境内形成的、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的、以故事性的角色扮演为本质一切戏剧①,既包括古代,也包括现代的;既包括汉族的,又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既包括城市的,又包括农村的;既包括人戏,又包括傀儡戏;既包括所谓成熟戏剧,又包括所谓不成熟戏剧,等等②。 传统戏剧的生存,既是指宏观层面上的戏剧整体的生存,也是指具体的某个特定时间、空间、样式、功能的戏剧的生存。离开具体戏剧的生存,讨论整体戏剧的生存就没有意义。 那么,为什么要把生存作为传统戏剧研究的重要问题?一者,传统戏剧是民族文化一个活的纽带,它生在古代,仍活在现代,是一种活的遗产。对待遗产,黑格尔一段话讲得很好:“这些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他们很熟悉;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一度存在过”,“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的事物必须和我们现在的状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是我们的。”③二者,传统戏剧的研究,不应只为了还原、解释对象,还应服务、帮助对象,让对象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样界定,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④。 笔者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戏剧究竟是怎样生存的?生存机制是什么?从古代戏剧到近现代戏剧、从不成熟戏剧到成熟戏剧,从农村戏剧到城市戏剧,从汉族戏剧到少数民族戏剧,从祭祀戏剧到娱乐戏剧,他们在生存上是否有统一性?如果有,这个统一性又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笔者尝试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如《山陕会馆与秦腔的传播》试图从戏剧史学界经常探讨的“商业发展与戏剧繁荣”的问题入手,揭示戏剧生存与商帮的内在关系,指出:“山陕商帮建设会馆戏台、神庙及其相关的演戏活动、祀神活动,与建设会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借‘义’谋‘利’,但他们在实现‘利’这个目标过程中的演戏祭祀活动本身,却对文化传播尤其是戏剧文化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影响。”“……保持着农耕时代乡土情结、宗教情结的同乡会馆,使戏剧在城市化、商业化过程中,仍然保持了它的乡土性、宗教性,从而为地方戏的传播、交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⑤显然,山陕商人的会馆演戏,遵循了以戏祀神,以神明义,以义谋利的逻辑的,这为我们探索戏剧商业功能的发生机制创造了条件。《城市化、市民社会与城市演剧》从戏剧史学界经常提及的“市民发展与戏剧繁荣”的问题入手,探讨了城市化、市民、市民社会的内涵,指出我国的城市演剧其实有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基于市民(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戏剧,一种是基于非市民(以血缘、地缘、宗教信仰为存在基础的农村与城市居民)、非市民社会(以宗法社会为主)的非城市戏剧。目前城市演剧的衰落,主要是指城市中的非城市戏剧的衰落。“因为非城市戏剧不是因市民及市民社会存在,其在城市中的命运自然会受到市民化及市民社会化程度的影响。”⑥也就是说,非城市戏剧与城市的市民、市民社会的错位,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从供养关系看传统戏剧的城市化》从戏剧“供养”角度探讨戏剧的生存问题,认为戏剧作为一种民俗、艺术或文化,它不能独立地存在,总是依附于人的供养。戏剧的供养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与宗教供养相似,即奉献的意义;二是一般的养活的意义。戏班及其演员所从事的演剧活动,本身并不能为他们提供生存保障,必然依赖于供养者的供养。弄清楚什么人因什么目的来供养戏剧,是了解戏剧因何生存的一个重要途径。供养者与戏剧的关系或者是宗教性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商业性,或者是审美性。“供养关系的变化,不仅决定了戏剧形态从仪式到艺术再到文化的变化,决定了戏剧演出从乡村到现代城市再到后现代城市的变化,还决定了戏剧功能从维系地缘、血缘的传统人际关系到建设契约式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变化”⑦。《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海陆丰“戏窝”研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指出传统戏剧具有非物质性、活态性、价值性和生态性等特点,具有复杂的生态系统。传统戏剧的生存既与其剧本、音乐、舞蹈、演员、服饰等内在因素及其构成的内在系统有关,还与其所处特定时空的外在系统有关,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⑧。 当然,上述研究局限于视角的限制,仍然有很多问题无法得到明确回答。比如在山陕商帮以戏祀神,以神明义,以义谋利的逻辑中,以戏祀神是逻辑的起点,也是把戏剧与商业相关联起来的关键环节。那么,为何要以戏剧祀神,戏剧如何能够祀神?就是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再如,城市演出的非城市戏剧衰落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观众和演出环境已经从非市民、非市民社会发展为市民、市民社会,二者之间发生了错位。那么,城市戏剧与非城市戏剧是绝对不同的吗?市民、市民社会与非市民、非市民社会是绝对无关的吗?非城市戏剧与非市民、非市民社会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就根本不存在契约式关系吗?如果是这样,该如何理解传统非市民社会中人们利用戏剧来沟通神灵的行为,难道那不是一种契约关系吗?再如,人们对戏剧的供养既有奉献的意义,又有养活的意义,那么,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供养者往往因某种需要来供养戏剧,那么,戏剧是如何满足供养者的需要?戏剧与其供养者的需要满足之间是一种必然的关系还是可能的关系?换句话说,不同时空、不同民族的戏剧与其供养者需要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其中是否有共性?最后,如果说传统戏剧是由其生态系统决定的,那么,把传统戏剧内外生态系统及其各自的要素贯穿起来、构成系统的主线是什么?它是如何实现贯穿系统的功能的?这个主线对传统戏剧的生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对传统戏剧提出了神性与俗性的概念。所谓神性,就是指传统戏剧可以打破世俗常规的、超自然、能够沟通人神、祭祀神灵的性质。所谓俗性,就是指传统戏剧基于世俗社会的、自然的、满足人的世俗需要的性质。传统戏剧是一种混合了神性与俗性的文化形态,既是祀神的仪式,又是娱乐的艺术,还是代际传承的遗产。探讨神性、俗性及神性与俗性的互变关系,有可能回答戏剧生存研究中的上述问题,也有助于发现戏剧生存的共性规律。 一、起源:因俗入神,神俗交通 对传统戏剧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话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巫觋说⑨、乐舞说⑩、俳优说(11)、傀儡说(12)、外来说(13)、民间说(14)和综合说(15)等。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不足,归根结底,是由于大家对戏剧、起源概念理解上有差别造成的。就戏剧概念而言,有的以元杂剧为标准界定戏剧,有的以唐戏弄为标准界定戏剧,有的以人演的戏剧为标准界定戏剧,有的以剧本为标准界定戏剧,有的以音乐为标准界定戏剧,有的以脚色为标准界定戏剧等,标准不同,戏剧的概念就不同;概念不同,戏剧的起源也就不同。就起源的概念而言,有的理解为事物最初的主要的源头,有的理解为事物所有的源头,有的理解为事物胚胎和基因,有的理解为事物的某一个元素的来源。起源概念不同,戏剧的起源也就不同。 在所有关于戏剧起源的讨论中,被多数人认可的说法是巫术说(或称原始宗教)。人们之所以把戏剧起源与巫术、原始宗教联系起来,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巫术是人类最早的文化形态,是原始人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为了控制自然现象或他人的行为而进行的一种活动。巫文化或原始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戏剧与音乐、舞蹈、文学等文化形式就是在巫文化母体中孕育并独立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巫术作为戏剧之源与唐古拉山雪峰作为长江之源并无两样。戏剧以巫术为主源,身体里流淌着巫的血液,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要以巫的形态呈现,正如长江以唐古拉山雪峰为主源,流淌着雪峰溶化的水,但并一定要以雪峰的形式呈现一样。其二,巫术中有巫扮神的活动,与戏剧演员装扮角色十分相似。而从时间上,巫又早于戏剧,所以戏剧是模拟巫术而来,是巫术世俗化的表现。这个观点包含了一个先验的判断:巫和戏剧是各自独立的,巫是神性的,戏剧是俗性的,俗性的戏剧从神性的巫术中发展而来。所以,脱离神性走向俗性是戏剧自我独立的先决条件。其三,巫术有娱神的功能,戏剧有娱人的功能,二者相似且有关联,戏剧的娱人功能从巫术娱神功能发展而来。英国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在《金枝》中指出,巫术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把结果和原因看作同类相生,叫做相似律;一是接触过的事物在脱离接触后仍然继续相互作用,叫做接触率或感染率。根据相似率,人们通过模仿,可以对对象施加巫术,这种巫术就是模仿巫术或顺势巫术;根据接触率,人们可以对对象施加巫术影响,叫做接触巫术。(16)巫术娱神就是顺势巫术的一种,模拟俗世娱人活动以娱神,以达到模拟神、支配神的效果。在这样的思维中,娱乐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巫术的一个重要手段、重要功能,由此与戏剧的娱乐功能相联系,于是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个由彼及此,由神及人的逻辑链条。这个逻辑是建立在神与人都有共同的娱乐需求,巫术与戏剧都有娱乐功能这两个相似性上的。 传统戏剧起源于巫的理由主要归纳为以上三类,至于人们从戏剧的化妆、服饰、道具、音乐、动作、演员、观众以及演出时空等因素来探究二者渊源关系的论著,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大都跳不出以上三类的范围。 当然,鉴于人们关于戏剧起源的讨论都是基于认识即对戏剧起源事件的反映而来。所以,有的学者主张对戏剧起源的认识,应该避免使用容易引起误解的起源学的“起源”概念,而应当使用发生学的“发生”概念。起源学研究的是事件在历史中出现的源头,强调实证性、经验性;发生学研究的是有关事物的知识结构的生成,也就是事物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性的过渡不以事件和时间进行实证,而以观念进行推理,强调逻辑性、历史性。所以,人们所有关于戏剧起源于巫的观点,实际上是研究者所认知的起源,并不是戏剧事件在历史的起源,只能反映研究者所理解的、推理的戏剧的逻辑起源。这样,我们就不必过于拘泥戏剧起源于巫这个结论是否符合事实本身,而应该重视的是人们为何及如何提出这个观点?支撑这个观点的逻辑是什么?是否存在问题?能否通过这些审思来揭示传统戏剧的生存机制,为解决传统戏剧的当代命运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如果说戏剧起源于巫(实际上是发生于巫)说法能够成立,那就意味着承认戏剧在源头上是有神性的,或者说,戏剧是有神性基因的。那么,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 第一,传统戏剧的神性是如何获得?如何表现的?能否从人们关于戏剧起源于巫的三个理由来解释,即“以戏剧为代表的各种艺术形式都从巫文化孕育出来的”、“戏剧与巫一样都有角色扮演”、“戏剧与巫一样都有娱乐功能”?从逻辑上讲,这三个理由都是十分粗糙的。第一个理由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人类许多文化艺术与早期的巫有关,是有道理的,但具体到戏剧而言,并不是必然的、绝对的,从巫中发展出戏剧、发展出音乐与继续沿巫的道路发展,具有相同的概率。第二、三个理由则都是按照“前后相似”就等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得出的,在逻辑上显然是不够严密的。但人们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判断,除了在经验中相似有时确实会产生因果关系外,还在于巫术、宗教与戏剧并存共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巫中有戏,戏中有巫的现象,不仅在古代文献中有记载,在今天城乡的民间生活中依然存在,这是人们把戏剧与巫术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依据。所以,人们总是试图从文献记载中、从偏僻封闭的乡村祭祀活动中,寻找材料以证明戏剧源于巫、与巫共生及与巫分道扬镳的依据和逻辑。 今天,我们要重新检讨上述戏剧源于巫的观点和理由,要从巫与戏剧并存共生的现象中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巫术与戏剧并存的原始生活中,人们是如何理解戏剧的?戏剧的神性是由戏剧与巫并存共处而获得的?还是因为在当事人眼中,巫就是戏剧,戏剧就是巫,戏剧神性就是其自性的呈现?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在今天所谓巫术与戏剧独立并存的生活中,戏剧与巫术其实是一体的,戏剧不是巫术的分化物,而是巫术本身,即人神沟通的方式。 传统戏剧如何实现巫术,实现人神沟通的呢?事实上,在巫术及由其演变而来的宗教中,人神沟通的方式很多,有音乐、有舞蹈、有文学、有符咒、有幻术等。这些方式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帮助巫师或僧侣由人向非人转换,即人神转换,使自己“脱凡入神”,获得与神对话的资格。即所谓要成为“非常”之人,须借“非常”之手段,巫师、僧侣等是“非常”之人,音乐、舞蹈、符咒、幻术正是其所用“非常”之手段。手段越复杂,常人越难以模拟,就越能显示巫师、僧侣之神力,亦愈能蛊惑俗人之心。戏剧正是巫师、僧侣实现人神沟通的一个“非常”手段。 第二,传统戏剧如何“因俗入神”,“出神人俗”的?一方面,巫术和宗教是以俗世功利为目的,食物、安全、后代繁衍等需要是巫术和宗教得以发展的基础,传统戏剧在帮助巫师、僧侣实现人神转换的过程中,也促使了俗世愿望和实践活动的巫术化和宗教化,如原始的打猎舞、拟兽舞,既是现实实践活动的再现,又为巫术、宗教的角色扮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源于巫术、宗教的传统戏剧,在帮助巫师、僧侣实现人神转化、出俗入神的同时,也发生着“出神入俗”的演变,使其与俗世的现实政治、经济和娱乐需求走得更近。于是在戏剧学界,对传统戏剧就有祭祀戏剧(或称仪式性戏剧)与娱乐性戏剧(非仪式性戏剧)的二分法,从定义看二者的边界很清晰,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关联。但是,从传统戏剧的历史和现实状态来看,二者其实有内在的关联,只是大家尚未找到二者关联的中间环节而已。确实,离开具体戏剧样式和时空环境,把不同时、空和不同形式的戏剧放在一起,来找较晚的娱乐性戏剧与早期的祭祀戏剧的关系,当然是不合适的,也是无法揭示传统戏剧出神入俗的发展规律的。对这点,我以为仍然要从传统戏剧实现其神性的方式入手,了解传统戏剧的神性如何影响俗世生活,如何在俗性生活体内潜伏并发挥影响,才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关于这点,本文在探讨戏剧形态、戏剧功能的神俗互变、共生时,将进一步论述,此不赘谈。 第三,俗性是传统戏剧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然结果吗?诚然,对科学与艺术的推崇,消解了神性在传统戏剧中的地位,凸显了俗性。传统戏剧被赋予文学、艺术等光环,成了远离神、远离神性生活的俗世艺术,成了政治、经济的工具和娱乐、审美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戏剧存在的必要性开始受到怀疑,被喜新厌旧的人们抛弃成为可能。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可以轻易抛弃一个徒具娱乐、审美光环而缺乏神性的艺术,但不能离开可能不美、娱乐性不强但具有神性的文化,因为它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依托。 二、形态:出神入俗,俗神兼备 传统戏剧的神性、俗性及其互变共生,不仅存在于它的源头和发生之中,而且存在于它的发展过程所呈现的各种形态中。传统戏剧的发展正如长江一样,是一条长而宽的不停流淌的河流,在它流过的不同时间、不同地段都有新的支流注入,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在传统戏剧那漫长而宽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许许多多被后世称为“戏剧”的角色扮演形式,如从远古的拟兽舞蹈、周朝的宫廷傩戏、秦汉的百戏、隋唐的参军戏,宋代的滑稽戏、歌舞戏,金元的诸宫调,宋元明的南戏,元明清的杂剧,明清的传奇,清和近现代的地方戏及少数民族戏剧。从乡村祭祀演剧、民间路歧演剧,到城市勾栏瓦舍演剧,再到士绅富商的堂会演剧、商帮行会的会馆演剧、官府宴会演剧、军队的幕府演剧、王室宫廷演剧,等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场合、不同形式、不同功能的演剧,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那么,它们的统一性是什么,是否与我们所说的神性、俗性及其互动共生关系有关?如果有关,那么神性与俗性是以何种方式呈现于其中? 对于戏剧形态的时、空关系,多数学者认为后世戏剧、城市戏剧、文人戏剧、汉族戏剧、世俗戏剧要较前世戏剧、农村戏剧、民间戏剧、少数民族戏剧、祀神戏剧更加成熟、复杂、发达,二者之间存在的演变、进化关系。所以,从成熟、复杂、发达戏剧向不成熟、不复杂、不发达戏剧逐层剥笋式逆推、还原戏剧的演变、进化历史,是戏剧史研究者常见的做法。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为地设定一个框架,把时间、空间上两个现象的相似性等同于因果关系,容易导致对戏剧形态之间的关系单向度判断。实际上,戏剧形态间的关系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是多向度的。 从神性、俗性及其关系来看,戏剧形态既有神性的,又有俗性的;既有神性戏剧向俗性戏剧的纵向演变和横向传播,又有俗性戏剧向神性戏剧的纵向演变和横向传播,还有神性戏剧与俗性戏剧的共存、共生和互动。大量有关传统戏剧与民间宗教、佛教、道教关系的研究,发现了大量有关神性戏剧与俗性戏剧互动的证据,范围几乎涉及了戏剧的各个方面,脚色、服饰、道具、音乐、舞蹈、故事、场地、剧本和演出形式、习俗等。康保成《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一书,用大量材料证明了古代戏剧剧场、脚色、演唱、剧本、表演与佛教的关系,表明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传统戏剧发生了深远的影响。(17)倪彩霞《道教仪式与戏剧表演形态研究》一书,则对道教与戏剧的音乐、舞蹈、舞台、服饰、化妆、演出习俗的关系做了探讨,揭示了道教对传统戏剧的影响。(18)至于俗世戏剧影响神性戏剧的证据,在有关我国各地民间祭祀戏剧、傩戏调查研究的论著中也有充分的反映(19)。 所以,传统戏剧形态,既有来自巫术的神性,又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掺入祭礼、宗教的神性,还有来自演员、观众、编剧者所赋予的俗性,呈现为出神入俗、神俗兼备的特点。因为俗性,戏剧才获得在文学、艺术上的长足发展;因为神性,戏剧才有了难以磨灭的魅力,才能成为几千年来不断被传承与发展的遗产。 三、功能:因神而俗,亦神亦俗 戏剧功能是戏剧满足人的需要关系的能力的反映。戏剧功能的类型既取决于戏剧的,也取决于人对戏剧的需求类型。在戏剧历史上,人们对戏剧功能的认识和追求是不断变化的。总体而言,传统戏剧的功能主要有祀神功能、娱乐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交际功能等。 一般认为,祀神功能主要存在于早期的、民间的戏剧中,这些戏剧还不是成熟戏剧。独立的成熟的戏剧,才发展出来真正的娱乐、政治、经济和交际等功能。所以,戏剧的成熟、独立过程,就是戏剧去神性、去魅化的过程。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传统戏剧的祀神功能是如何实现的?是戏剧本身所固有的,还是从戏剧所派生的?也就说,祀神功能是由戏剧直接实现的,还是间接实现的,如娱神、供奉神?如果是前者,那么戏剧是实现人神沟通的唯一方式,还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如果是后者,戏剧通过什么中介来实现祀神活动?是通过它的娱乐、政治、经济和交际等功能中的一种或多种吗?有些人认为,戏剧的祀神功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由其娱乐功能为中介实现的。戏剧能够娱人,也就能娱神,人以己及人,把能够使自己快乐的戏剧奉献给神,以讨好神,神就自然会答应人的各种请求了。在今天的民间祭祀演剧中,很多人持这种看法,从他们献给神的戏剧,就大概知道他们的戏剧喜好了。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戏剧与祀神的关系,就不是先有祀神,后有戏剧,而是先有戏剧,后有祀神,戏剧娱神是由戏剧娱人发展而来的。这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戏剧源于巫术的观点相矛盾。由此,也可能陷入到鸡生蛋、蛋生鸡的矛盾循环逻辑之中。 笔者以为,早期传统戏剧在本质上是巫术或祀神活动的一种,与通过音乐、舞蹈、幻术或其他使巫师、僧侣具有异于常人表现的方式一样,是实现人神沟通的一种手段、证明。至于现代民间以娱神来祀神,则是在戏剧发展出娱乐功能后才出现的。所以,祀神、沟通人神是戏剧的基本功能。 戏剧的娱乐、政治、商业和交际等功能是戏剧的俗性功能,与祀神功能是什么关系?前者是否从后者发展而来的?一般认为,戏剧是一种文学、艺术,以娱乐、审美为基本功能。所以,戏剧能够将各种功能联系起来的中介就是娱乐,由祭祀到其他功能的发展,就在于戏剧的角色扮演给神和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满足——娱乐。由娱神到娱人,由娱人到交际、政治和经济,是戏剧功能转化、发展的一个逻辑。但这个推论是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解释祀神活动中戏剧存在的必然性。如果仅仅从娱乐角度认识戏剧在巫术和祀神活动中的作用,那么就无法解释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戏剧祀神现象。娱神的方式很多,为什么非要选择戏剧?今天的民间祀神中的演剧固然有娱乐性,但其之所以被人们所热捧,应该与它的角色扮演有关系,角色扮演是人模拟神,实现人神转化的重要途径。正因为如此,传统戏剧具有神性,是传统戏剧的本质使然。 那么,传统戏剧的神性、俗性及其互动共生是如何在戏剧功能中得以体现的?巫术、祭礼和宗教活动的祀神戏剧,是通过模拟神、扮演神、娱乐神,以建立人、神契约的方式来实现其功能,方式是神性的,目的则是俗性的,祀神戏剧是因俗而神,以神践俗的。俗世的娱乐、政治、商业和交际功能的戏剧,在实现其功能的途径和方式上,与祀神戏剧有相通相关之处。前文所述,由娱神到娱人,再以娱人为手段,实现政治、商业和交际功能,是戏剧神性功能到俗性功能的表层轨迹,不能真正解释祀神戏剧存在的必要性。 所以,俗世的娱乐、政治、商业和交际功能的戏剧与祀神戏剧有一定内在的联系机制,这个机制只能从角色扮演与建立契约关系等共性中去认识。戏剧祀神功能实现的本质是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关系的建立,巫术、祭礼、宗教活动中的歌、舞、角色扮演、幻术、祭品、仪式等,是帮助建立人神契约的手段。这种人神间的契约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商业和交际关系中得到投射。 就以古代山陕商帮会馆演戏来说,山陕商人在各地经商,建立山陕会馆,其中多修有庙宇和戏台,供奉关公和演戏。商人会馆主要在四种情况下演戏:一是会馆落成或修葺竣工时;二是会馆神灵诞辰、纪念日;三是商人店铺新开张;四是商人违反会馆行规,要受惩罚出资演戏(20)。前两种是典型的祭祀演剧,后两种是世俗演剧,都是服务于商人经商的,是以谋利为最终目的的,只是在方式上前两种比较间接,后两种较为直接罢了,说明祀神戏剧与商业戏剧共存于山陕商帮的商业活动之中。 那么,为什么商人商铺新开张或违反行规时要演戏呢? 北京西四北大街四十六号真武庙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猪行公义条规碑》记载:“……每年公财神献戏一天。新开猪店者,在财神圣前献戏一天,设宴请客,同行之人方许上市生理。此议论之后,俱各遵守,并无异说。今年北张羊王两家,开张之时,并未献戏请我同行。此皆年远日久,议规未申,亦故废饬。今同行公议,重整行规,以申旧制。自议之后,如有新开猪店,必须在财神圣前献戏一天,设宴请客,方准上市生理。如不献戏请客,同行之人,该不准其上市生理”。(21)新开商铺开张对同行商帮而言是一件大事,意味着有新会员要加入行会,必须明确其与其他会员之间的契约关系(行规),才能确保行业的和谐发展。那么,如何让新会员与旧会员建立新的契约关系呢?就是演戏,让新会员给神演戏、设宴请客,这其实就是通过与神灵沟通、建立人神契约关系的方式来建立新会员与旧会员的新契约关系,使得新、旧会员的契约关系因得到神的支持、见证而具有神性和强大的约束力。 成都洛带湖广会馆康熙九年(1670)碑文记载:“因王明浩不肯附会,辄罚令唱戏酬神,以致余人皆停工观望”(22)。北京《糖饼行北案重整行规碑》记载:“……如有帮案、烧炉,散去徒弟、伴脚接作活者,工价送钱一律照旧;如不照旧,赚者罚该柜神戏一台”(23)。违背会馆或行业规范,对商帮、行会而言也是一件大事,是对大家所认可并被神所见证、支持的契约的破坏,必须重建契约的严肃性和神圣性,所以必须让违约者受到惩罚。之所以选择罚戏方式,其实与建立契约是演戏一样,也是通过人神沟通以告知神灵,让神灵见证、支持契约的重建,赋予这次重建以神圣性和正当性。 如何确保传统戏剧具有可持续的生命力,是当下“非遗”保护重点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戏剧研究者应该重视的问题。 目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功能、不同形式的戏剧生存状况各有不同,有的依然十分繁荣,有的则日渐衰落。从整体而言,城市的、国营的、剧院的、审美的传统戏剧在衰落,农村的、民间的、广场的、祭祀的、自娱的传统戏剧依然活的较好。对这种状况,我们值得反思。由此,我认为我们可以跳出之前对传统戏剧概念、分类、发生、发展的思维定势,重新回到传统戏剧所赖以发生、存在和发展的生态中,从中探索传统戏剧是什么、如何生存等内在问题。 从上述思路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戏剧对我们而言,至少有三种意义,一是宗教性戏剧,既指具有角色扮演的巫术、祭礼或宗教活动,也指独立但服务于巫术、祭礼或宗教活动的戏剧;二是艺术性戏剧,指以满足人的娱乐和审美需要为主的戏剧;三是遗产性戏剧,指被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遗产的、代际传承的戏剧。不同的戏剧意义,展现了人们看待戏剧的不同视角、不同的优势,也暴露了各自的盲区。那么,能否找到一种可以联合三个视角来全方位、立体透视传统戏剧生存机制的方法呢?本文提出的神性、俗性及其互动共生,就是一个新的尝试。 神性、俗性是指传统戏剧的两种属性。神性是指戏剧通过角色扮演以沟通人神的、服务巫术、祭祀和宗教仪式的性质。俗性是指戏剧通过角色扮演以满足人的世俗需求的性质。神性与俗性既体现在戏剧从起源到发展、成熟的各种历史形态上,也体现在戏剧的各种空间和功能形态上;既表现为二者为共存、互动的情况,又表现为二者各自独存、分化的情况;既有显性状态,又有隐性状态。 从传统戏剧的起源看,原始巫术(原始宗教)是一种因俗(为满足俗世需要)而神、人神沟通的戏剧,其以歌、舞或模拟装扮形式扮演神、展示神、与神沟通的方式,不仅影响了后世的祭礼、宗教仪式,而且衍生了后世俗性戏剧。 从传统戏剧的形态看,从远古一直延续至今的巫术、祭礼到宗教的戏剧,与秦汉百戏、隋唐戏弄、宋杂剧、金院本、宋元明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清及近现代京剧、地方戏、少数民族戏剧,一神一俗,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条独立的河,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神入俗、神俗兼备的汇流。在所谓纯粹的文学性、艺术性戏剧中,从剧本、脚色、音乐、服饰、道具、故事到表演,保存了大量巫术、祭礼或宗教的因子,成为二者互动、演变的证据。 从传统戏剧的功能看,戏剧的祀神功能与娱乐功能、政治功能、商业功能、交际功能分别代表了戏剧的神性与俗性两个方面,看似分离、各自独立的,实则是密切关联的。祀神功能在实现方式上由模拟神、扮演神再到娱乐神发展,体现祀神戏剧从形象上认同到情感上认同、从庄严的神性向轻松的俗性转变的痕迹。俗性的娱乐功能、政治功能、商业功能和交际功能虽然价值指向各有不同,但与神性的祀神功能有着或明或暗、或紧或松的联系。由娱神到娱人,再以娱人为手段,实现政治、商业和交际功能,是戏剧神性功能到俗性功能的表层轨迹。内在的机制则是:戏剧祀神功能实现的本质是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关系的建立,巫术、祭礼、宗教活动中的歌、舞、角色扮演、幻术、祭品、仪式等,是帮助建立人神契约的手段。这种人神契约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商业和交际关系中得到投射。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政治、商业和交际关系的确立,不是直接建立的,而是通过与共同信奉的神灵关系的建立来间接实现的。正如天主教信徒的婚姻誓言要在教堂神甫的见证下才有效一样,戏剧在政治、商业和交际中的功能正是通过人神关系的建立而实现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地方的民间政治、商贸、人际纠纷等要通过在神前罚戏方式来解决了。 当然,神性、俗性及其互动共生也只是考察传统戏剧生存机制的一个新视角,说明了传统戏剧不仅仅是一种有着俗世功能的艺术,而且是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宗教和遗产,正是文化内涵在传统戏剧中的消长,才造成了传统戏剧潮涨潮落的盛衰变化。当然,与其他视角一样有自己的优势,本文也有盲点。加之,把不同的戏剧形态整体纳入考察范围,时代、空间、形态跨度都很大,甚至把前人归于巫术、祭礼和宗教的一些活动都作为考察对象,其中难免存在以偏概全、不能周详的问题,望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①关于戏剧概念和本质,笔者基本认同康保成老师关于戏剧本质是角色扮演的观点,但不只是演员在假的环境中进行的以娱乐为主要目的角色扮演,还包括那些有故事性、非娱乐性的角色扮演。康老师的观点,参见康保成《试论戏剧的本质与中国戏曲的特色》,《古代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6-96页。 ②对传统戏剧的边界,基于不同的戏剧概念就会有不同的理解。笔者以有故事性的角色扮演为本质,以我国境内为范围,以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为形式等标准来进行限定,试图从宏观、整体的视觉来看传统戏剧,而不仅仅局限于从南戏、杂剧、传奇戏、昆剧、京剧等所谓成熟戏剧(戏曲)为对象。 ③[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6页。 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参见宋俊华、王开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附录1”,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⑤宋俊华:《山陕会馆与秦腔的传播》,《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 ⑥宋俊华:《城市化、市民社会与城市演剧》,《文化遗产》2007年创刊号。 ⑦宋俊华:《从供养关系看传统戏剧的城市化》,《戏剧艺术》2013年第6期。 ⑧宋俊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海陆丰“戏窝”研究》,《西安艺术》2013年第1-2期。 ⑨宋代苏轼、近人王国维均持此说。详见苏轼:《东坡志林》(卷二);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⑩清代纳兰性德、近人刘师培、常任侠、周贻白、张庚、郭汉城均持此说,详见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刘师培:《原戏》,北京:北京景山书社,第5页;常任侠:《中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学术杂志》1943年第1期: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 (11)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俳优》、清代焦循《剧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均持此说。 (12)孙楷第:《傀儡戏考源》,上海:上海出版社1952年,第122页。 (13)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原载《小说月报》1927年第17卷号外,李肖冰等编:《中国戏剧起源》,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也持此说。 (14)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 (15)周贻白:《中国戏剧发展史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16)[英]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页。 (17)康保成:《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 (18)倪彩霞:《道教仪式与戏剧表演形态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9)如田仲一成以《中国祭祀戏剧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为代表的关于中国传统祭祀戏剧的系列研究著作,还有如台湾王秋桂主编《民俗曲艺》丛书(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3-2007年)对我国各地民间祭祀戏剧的调查与研究。 (20)宋俊华:《山陕会馆与秦腔的传播》,《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 (21)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51页。 (22)成都洛带湖广会馆康熙九年《鲁祖会馆》碑文。 (23)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