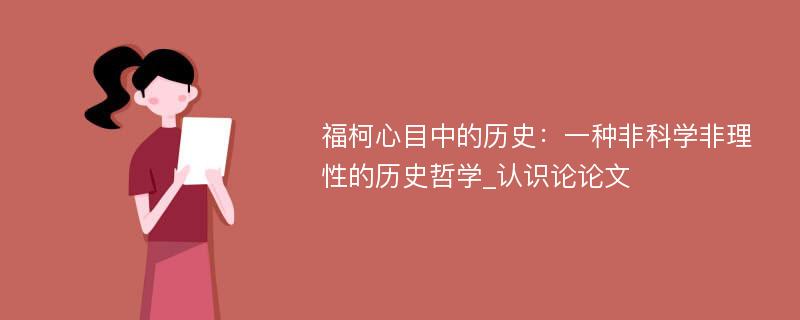
福柯心中的历史: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历史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哲学论文,心中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409(2008)04-0039-07
著名的荷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曾说过:“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是,抽去科学和现代主义的根基。这里,对于后现代主义论题的最好说明实际上是由历史学提供的。”[1](P184)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开山大师之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代表性著作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安克斯密特的这一论断,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是十分准确的。因为福柯的几部代表性论著,如《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1961)、《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和《性经验史》(1976、1984),都是通过历史题材立论的。本文从这几部历史学论著人手剖析他的历史观,进而揭示出他的历史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以及直接受到这种历史哲学强烈影响的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性质。
福柯的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
在史学本体论或历史观方面,福柯主张摒弃“全面历史”(histoire globale),而代之以一种“概要历史”(histoire gé né rale)(谢强、马月翻译的《知识考古学》中把此词译为“总体历史”,我认为,从该书中福柯对它的解释来看,这种历史展开的是一个离散的空间,它研究的是在这个空间中出现的“遗迹”和“断裂”。可见它绝不可能是一种总体的历史,因此法文单词“gé né rale”在这里应取“概要的、概括的”之意。)在《知识考古学》中,他把历史学家通常致力于研究和写作的历史称之为“全面历史”,认为那种“全面历史”是力图以“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2](P10)而如今“全面的历史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概要历史的东西已初步形成。”[2](P9)福柯所说的“概要历史”,就是从杂乱无章的历史“遗迹”中找出若干个“不连续”的“断裂点”组成的历史。福柯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在一个不断展开的离散(dispersion)空间中,即“话语”的范围内去探寻并描述这些“遗迹”和“断裂”。“话语”在福柯那里有特别的含义。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当关注的并不是人们所说的话,也不是那些隐藏或暴露于话语中的思想、表述、主题、成见,而是“作为实践的话语”。那么,福柯所说的“话语”到底指的是什么?在《知识考古学》一书的结束语中,当被问到“您近十年来坚持不懈地从事研究而又从未考虑详细介绍的话语究竟是什么”时,福柯回答说:“目前我还不能为我的话语确定一个字眼,远不能确定它说话的出发点,勾画它可能依附的土壤。它是关于话语的话语。……它并不试图使自己成为起源的追忆或者真理的回想。恰恰相反,它要制造差别,即把差别作为对象来构建,分析这些差别和确定它们的概念。……它不断地进行着区分,这种话语是诊断器”。[2](P228)这样的回答是很模糊的,始终让人看不清楚所谓的“话语”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们能够从福柯的几部主要作品中反复使用的几个具体的“话语”——“疯癫”、“人”、“惩罚”和“性”——中看出,他所说的“话语”实际上指的恰恰是“话语”表达的“观念”,他并不是用那些“话语”论述疯癫、人、惩罚和性本身的历史,即人们的实际作为的历史,而是论述人们对待疯癫、人、惩罚和性的观念、态度的历史。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作为实践的话语”的含义。
除了福柯所说的“话语”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观念”之外,我认为他所说的“知识型”(l'é pisté mè,也译作“认识型”)说到底也是一种“观念型”。在《词与物》中,福柯主要探讨了三种“知识型”:
第一种是从文艺复兴到16世纪末的“知识型”,它以相似性为组织知识的基本原则。相似性形式主要有四种[3](P24~35):首先是“适合”(la'convenientia),当两个物彼此充分靠近,处于并置之中,而且它们的边界彼此接触,一物的末端意味着另一物的开头,这两个物就是彼此“适合的”,比如“身”和“心”。其次是“仿效”(l'aemulatio),这种相似性形式不受位置的束缚,它可以使并不邻近的事物通过某种“映象”作用而彼此“仿效”。比如,“人的两只眼,以及它们的有限的明亮,是太阳和月亮散播在天空中的巨大的照明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双眼及其明亮与太阳和月亮的照明具有相似性。再次是“类推”(l'analogie),这种相似性并不是事物本身之间的可见的实体的相似性,它表明的是从一个点拓展到无数的关系。“例如,星星与星星在其中闪光的天空的关系也许可以在这样一些东西中找到:在植物与土地之间,在生物与生物居住的地球之间,在诸如矿石之类的钻石与埋藏钻石的岩石之间,在感觉器官与因这些器官而富有生气的面孔之间,在皮肤雀斑与隐藏这些标记的身体之间。”最后是“交感”(des sympathies),交感可以激发世界上物的运动,并且能使最遥远的物相互吸引、相互接近。比如,向日葵的巨大黄色花盘总是随着太阳的运动轨迹转动就是交感作用的结果。在福柯看来,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这四种相似性只是告诉我们“相似性路径是什么并采取什么方式”,但“没有告诉我们相似性在何处,人们怎样看到相似性,或者凭什么标记,相似性被人认出”。为此,福柯认为必须要有某个标记,使我们能注意到这些相似性。而这些记号就是“讽刺诗、符号、数字和晦涩的词”[3](P37),即语言本身。语言的价值在于它是物的符号,它指称物并与自己所命名的物相似。这就是福柯所说的16世纪的知识型,说到底,它就是指人们用怎样的“词”去把握“物”的方式。
福柯说的第二种“知识型”是17、18世纪所谓“古典时期”的“知识型”,它以同一性和差异性为组织知识的基本原则。福柯认为,这个时期的“知识型”不再以寻找相似性为目标,语言(即符号)在这个时期不再是获取知识的钥匙,而是具有新的力量,即表象的力量,它处于表象内部,但又贯穿表象的整个范围。在《词与物》一书中,福柯对17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第雅各·委拉斯开兹(Diego Vé lasquez)创作于1656-1657年的著名油画作品《宫中侍女》所作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对这种以表象为特征的知识型的具体诠释。[3]
福柯说的第三种“知识型”是19世纪以来所谓“现代时期”的“知识型”,它以历史范畴为组织知识的基本原则。福柯认为,在这个时期表象理论作为所有可能的秩序的普遍基础消失了,语言作为表象与存在物之间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的特权地位也丧失了,“人”(l' homme)第一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由此,现代时期的知识型转向了对人的关注。《词与物》就描述了“人”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诞生到正走向消亡的历史过程。但福柯所说的“人”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的人,而是作为他设定的那种观念的体现者的“人”。
那么,福柯所说的“知识型”究竟指的是什么?他自己认为它是属于认识论领域的,并解释说:“我设法阐明的是认识论领域,是认识型(l'é pisté mè),在其中,撇开所有参照了其理性价值或客观形式的标准而被思考的知识,奠基了自己的确实性,并因此宣明了一种历史,这并不是它愈来愈完善的历史,而是它的可能性状况的历史;照此叙述,应该显示的是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les configurations),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3](P10)可见,福柯所说的“知识型”是指用观念把握世界的方式。
由此可见,无论是福柯的“话语”还是他的“知识型”,指的都是一种观念和作为观念的外在表现的“态度”,他的“概要历史”实际上就是人们对待各种事物的观念、态度的历史,而且是那些观念、态度的不连续的、断裂的、无规律的历史。
在史学方法论方面,福柯摈弃了传统史学确定文献真伪和解释文献的方法,提出寻找“遗迹”、“断裂”的“考古学”方法。他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他的“考古学”方法共有四大特性:第一,关于新事物的确定。“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思维、描述、形象、主题,萦绕在话语中的暗藏或明露的东西,而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福柯这里所说的“规律”,是指能描述各个对象的离散状况、把握分割它们的间隙以及估量它们之间的距离的那些话语的“分布规律”,而决不是我们所说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恰恰相反,福柯指出他的“规律”不是要重建某些“推理链”,也不是制作“差异表”,而是描述“离散”的系统。第二,关于矛盾的分析。“考古学不试图发现连续的和不知不觉的过渡”,“相反,考古学的问题是确定话语的特殊性;指出话语所发挥的规则作用在哪些方面对于其他话语是不可缺少的;沿着话语的外部的边缘追踪话语以便更清楚地确定它们”。第三,关于比较的描述。考古学不涉及创作主体的层次,相反,它“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而这些话语实践横贯个体的作品”。第四,关于转换的测定。“考古学不试图重建人们在说出话语的一瞬间的所思、所愿、所求、所感受、所欲的东西”,“考古学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仅仅只是一种再创作”。它不是“向起源的秘密本身的回归”,而是“对某一话语——对象的系统描述”。[2](P152~154)总之,福柯的“考古学”不再以探寻起源、连续性为目标,而是转向强调断裂和非连续性,寻找到各个知识领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巨大断裂点”。
在史学认识论方面,福柯持一种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在他看来,既然历史是一个无规律的、不连续的、有着“巨大断裂”的过程,历史学家只能根据一些“遗迹”和“断裂点”来对历史进行考察,因而人们也就不可能获得客观性的、愈来愈完善的历史认识,只能获得一些永远不可能确定其准确含义的、模棱两可的认识。福柯本人一直在“实践着”他的认识论,他要求人们无论是对他的思想理论还是对他本人,都不要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要期望从中获得对历史的一以贯之的认识。在他的几部主要作品中,他把人们对待“疯癫”、“人”、“惩罚”和“性”的观念、态度的变化时而解释为是由于某种“深层结构”的变化所引起,时而又解释为是受到某种“情感”的影响所致。当有人质问他:“您是不是对您所讲的没有把握?您是不是又要针对人们向你提出的问题改变观点,变换立场,说这些驳斥并没有针对性?您是不是准备重复说您从来就不是人们谴责的那样?您已经在安排退路,以使您在您的下一部书中再次出现,并像您现在做的这样嘲弄我们说:不,不,我并不在你们窥测我的地方,可我却在这里微笑着注视着你们。”福柯对此的回答是:“无疑,像我这样,通过写作来摆脱自我面孔的,远不只我一人。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2](P19)至此,福柯的这种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倾向已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它试图从根本上阻止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使人们不敢作出明确的判断或结论。
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历史哲学
福柯的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互相联系,构成了他的历史哲学,其中他的史学本体论居于主导地位,决定着他的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他的“三论”充满了自相矛盾,凸现出非理性特点。
我们首先来分析福柯的史学本体论。福柯否认有一个从古至今渐进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在他看来,历史就是由杂乱无章的历史“遗迹”及其中若干个不连续的“断裂”所组成的,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去探寻并描述这些“遗迹”和“断裂”。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福柯在他的几部主要作品中费尽心思地去考证和描述人类关于“疯癫”、“人”、“惩罚”以及“性”的“重大历史遗迹”和“巨大断裂点”。但也正是在这里,他陷入了无法解脱的自相矛盾的泥潭:他为了否定连续的客观历史的存在而竭力去寻找“断裂点”和断裂的“遗迹”,不得不去追溯有关“疯癫”、“人”、“惩罚”以及“性”的观念的漫长历史,这样就实际上承认了它们有那么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例如,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在前言中就表明要从有关“疯癫”的历史“遗迹”中探寻“断裂点”,并认为这个“断裂点”造成了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与断裂。最终,他把这个“断裂”定在了18世纪末,在他看来,正是在“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4](P2~3)再如,在《词与物》中,福柯通过对有关“人”的历史“遗迹”的考证,提出“人”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西方文化认识型中的“巨大断裂期”。
由此可以看出,福柯在完成他的历史研究任务,即考证和辨识“重大历史遗迹”和“巨大断裂”时,却正是以人们对待“疯癫”、“人”、“惩罚”及“性”的观念和态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为其立论依据的,这个事实本身恰恰说明了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存在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福柯否认历史发展进程中有因果联系。在《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前言里,他申明,他所进行的疯癫史研究是不遵循任何理性的因果逻辑的[4](P3)。但是,他对因果关系的否认却是通过如下的过程进行的,即先试图寻找原因,进而论证这些原因根本无法最终解释他的那些历史“遗迹”和“断裂”。例如,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在考察古典时期的疯癫史时关注到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一个是1657年(法国)总医院建立和对穷人实行‘大禁闭’;另一个是1794年解放比塞特尔收容院的带镣囚禁者。”[4](P4)福柯认为,这两个历史事件前后呼应,但它们的意义却截然相反,一个标志着“禁闭”的开始,另一个则代表着“解放”的到来。为什么会是这样?福柯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实际上,在这两种相反意义的背后,有一种结构正在形成。这种结构不仅没有消除这种歧义性,反而决定了这种歧义性。正是这种结构导致了中世纪和人文主义的疯癫体验转变为我们今天的疯癫体验,即把精神错乱完全归结为精神疾病。”“但是,从一种体验到另一种体验的转变,却是由一个没有意象、没有正面人物的世界在一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中完成的。这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作为一种无声的机制,一种不加评注的行动,一种当下的知识,揭示了一个庞大静止的结构。这个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4](P4~5)这些话表明,福柯一面否认因果关系,一面却承认存在着一种推动人们的疯癫体验不断发展变化(即从人们对疯癫实行“禁闭”到“解放”疯癫者,从人们把疯癫看作“精神错乱”到看作“精神疾病”的过程)的动力,这就是“一种结构”,一种“庞大静止的结构”。福柯在理解18世纪人们的疯癫意识是如何转变时,再次承认需要从“结构”中去寻找原因。他认为这种意识既不是在人道主义运动的背景下,也不是在某种科学需要的压力下演变的,“疯人逐渐被分离出来,单一的精神错乱被划分为几种基本类型,这些与医学进步和人道主义态度都毫无关系。正是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禁闭本身去寻找对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说明。”[4](P208)那么,福柯所一再强调的这种“结构”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按照福柯上文中的解释是“这个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可是我们看到这种解释既模糊又带有一种神秘性,仿佛“结构”就是某一个神秘的“地方”,最终人们仍无法弄明白它到底是什么。其实,福柯自己已解释不清了,因而就干脆下结论说,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的,历史研究是不能遵循任何理性的因果逻辑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固执地坚持非理性立场使福柯自己陷入了多么尴尬的处境。
事实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性的因果逻辑”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就以福柯自己专门考察过的法国人对待“疯癫”、“人”、“惩罚”及“性”的观念和态度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他实际上已经不得不承认那些观念和态度都有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非理性到理性的逐渐推进的过程,他只是固执地拒绝承认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力量推动着那个过程的前进,那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5](P494)这里揭示的“理性的因果逻辑”就是:人们的观念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而相应的发展和改变。由这样的“理性的因果逻辑”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所说的法国人对待“疯癫”、“人”、“惩罚”及“性”的观念和态度的“断裂”性的改变,都发生在17-19世纪之间,绝不是偶然的。正是在这个时期,法国劳动大众奋力摆脱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束缚,向着社会化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方向迈进;成长中的市民—资产阶级依靠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以所谓“第三等级”代表者资格,日渐鲜明地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向封建制度和贵族等级特权发起进攻。福柯追溯到的法国人对待“疯癫”、“人”、“惩罚”及“性”的观念和态度的“断裂”性的改变,不过是这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中的一些侧面的转折性标志点。福柯固执地否认促成那些“断裂”点出现的符合“理性的因果逻辑”的真正动因,而把那些动因归之于自己也说不清的“庞大静止的结构”的变化。这充分表明,他坚持的那种非理性的、虚无主义的史学本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再看福柯的史学方法论。我们知道,每位历史研究者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性质和特点的观点或理论,即他的史学方法论,实际上是由他的社会历史观—史学本体论转化而来的,他持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史学本体论,就会采用什么样的历史研究方法。既然福柯把历史的演变过程视作是一个断裂的、不连续的、无规律的过程,说到底也就是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那么,他的所谓“新史学方法”也就不可能揭示连续的、有规律可循的历史演变过程,更不可能运用因果必然性规律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作出解释,而只是去寻找历史过程中的一些“遗迹”和“断裂”,并对它们进行描述。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实际上就是通过描述那些断裂的、不连续的“历史遗迹”来实现他所说的“重新考察历史”。他的“考古学”虽然也强调要确定“服从于某些规律的话语本身”,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他所说的“规律”其实是指能描述各个对象的离散状况、把握分割它们的间隙以及估量它们之间的距离的“话语”的“分布规律”,而决不是我们所说的“因果必然性规律”。用福柯自己的话说,他的“分布规律”决不是要重建某些“推理链”或探寻事物的起源,而只是用来描述事物的“离散”、“断裂”和“非连续性”。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福柯的史学认识论。福柯否认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认为人们不可能获得愈来愈完善的历史认识,而只能获得一些永远不可能确定其准确含义的、模棱两可的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永远不可能被人们所认识。的确,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相比,历史学的认识对象有其独特性。其他社会科学虽然也都不免要涉及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情况,但它们首要的对象是现实社会生活中这些领域的现象及其规律。与此不同,历史学要研究的主要是人类社会中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以往的过程和现象,研究者对此已不可能亲身感受或直接地观察,而只能凭借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去认识它们。由此,历史学的认识对象便具有如下的特点:它是以往的客观历史,而能直接进入对它的认识过程的,却只是它留下的遗迹——历史资料,历史认识者只能通过研究这些历史资料去认识客观历史的原貌。这样,历史认识者的认识对象便表现为双重客体:一个是历史认识者所要认识的客观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原本客体,另一个是直接进入历史认识者认识活动过程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称之为中介客体。这双重客体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甚至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承认,这种不一致或距离确实给历史认识者正确认识历史的原本客体——客观历史过程增加了困难和复杂性,但不能因此就认定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相。这是因为,尽管历史资料有限,而且不可避免地渗进某些主观成分,但历史认识者可以从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出发去认识人类社会以往的过程和现象,并在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中去检验其历史认识的真实度。也就是说,历史认识者除上述双重客体之外,实际上还面对着第三重认识对象,那就是现实社会,它是历史原本客体的延伸体,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原本延伸客体”。其实,历史学家在探寻原本客体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以今推古”或“抚今追昔”的方法,马克思把这种认识方法形象地比喻为通过人体的解剖学结构的认识,达到更好地认识猴体的解剖学结构的方法,这就表明历史学家实际上总是把现实社会作为他的认识对象的一部分的。也就是说,历史学最终实际上是面对着三重认识对象,即原本客体、中介客体和原本延伸客体。[6](P329~332)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三重客体,所得出的看法可能各不相同,但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某些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那些反映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的认识,总会逐渐趋于汇合和升华,成为比较全面的认识,就像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真实全貌的认识过程那样,总会越来越接近于对历史的真实全貌的认识。[7](P375)福柯把人们对待“疯癫”、“人”、“惩罚”和“性”的观念、态度看作源自于某种“深层结构”或“情感”,认为这种“深层结构”或“情感”决定着人们对“疯癫”、“人”、“惩罚”和“性”的历史认识。在他看来,由于“深层结构”或“情感”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某一个神秘的地方,因而人们所获得的历史认识只能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完全取决于自身感受的认识,不可能具有任何客观性。然而,人们的认识只能来自他们的实际生活体验,无论是“结构”还是“情感”最终都是由人们的现实生活体验所决定的,而且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增加,人们的“观念”会不断发生变化,认识可以越来越接近于揭示历史的真实全貌。实际上,福柯在史学认识论上所持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观点,其根源还是在于他的史学本体论,他否认历史的发展演变有客观规律,而且否认连续的历史过程本身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可能承认通过历史研究获得客观真理的可能性了。
由此可见,福柯的历史观使得他的论述(“文本”)充满了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并决定了他的历史哲学凸现出非科学、非理性的特点。他的这一套“抽去了科学和现代主义的根基”的非科学、非理性的历史哲学对当代西方历史学思潮的影响是很大的。当今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如荷兰历史学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英国历史学家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等,他们的历史哲学理论都与福柯的历史哲学理论有直接联系。在史学本体论方面,他们主张“文本本体论”,就是把一切认识对象,包括物质和精神的认识对象,都归结为“文本”,认为一切“文本”本身都没有确定不变的内涵。这里的“文本”概念实际上同福柯的“历史遗迹”概念相近。怀特主张把文本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并认为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把历史当作文本来谈论。詹京斯也认为历史只能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文本解读(解释),而且就逻辑上来说,这样的解读必然是无休无止的,不可能有一个公认的最终结论。这种“文本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本体论,历史研究在他们那里变成了见仁见智、无休无止的文本解读,没有任何科学结论可言,只能凭研究者个人感受描绘出福柯所说的那种由一个个离散的、没有规律的“遗迹”和“断裂”构成的“概要历史”。在史学认识论方面,他们持一种具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特征的认识论,强调对文本含义的解读总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或任何他人的解读或认识宣称为唯一真理。怀特提出“情境主义认识论”,认为所有的历史作品都是作者根据个人的想象对过去的历史情境作出的情境主义解释,因此人们无法认定哪一部史书是更“真实的”,更“可信的”。詹京斯也认为,由于历史是历史学家各自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叙述和解释,而“过去已经一去不返,没有任何叙述可以向过去本身查证,而只能向其他的叙述查证”[8](P65)。由这种史学本体论和史学认识论进而推导出所谓“诗意性的(Poetic)”治史、写史方法论,后现代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研究和史书的写作都不可能运用追求客观真相的科学的方法,而只能运用艺术的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福柯的历史哲学还是直接受其影响的怀特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都是一种“抽去了科学和现代主义的根基”的非科学、非理性的历史哲学。当然,这种历史哲学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历史哲学的破坏性,那就是它把一切已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统统加以否定,从而否定一切科学理性,否认历史学揭示历史真相和科学真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最终否认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品格和存在价值,这是一切有志于追求历史真理的人们所不能赞同的。
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上述历史哲学的破坏性。轰动美国乃至全世界学术界的“索卡尔诈文”事件就是对后现代主义反科学倾向的有力回击。1996年4月,美国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了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的文章《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一种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该文被发表的当天,索卡尔当众声明他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诈文,其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事实证明,该杂志的五位主编都没能识别出作者有意捏造出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也没能识别出作者在他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所谓“联系”,而是一致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这一事件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的渗透,知识界充满着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怀疑倾向的相对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者向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及其客观真理性发起挑战。面对这种挑战,美国生物学家保罗·葛罗斯(Paul R.Gross)和数学家诺曼·李维特(Norman Levitt)1994年发表《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一书,率先发起了捍卫科学真理的反击战,获得了许多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暴露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装”。索卡尔读了这本书之后,也对后现代主义反科学思潮的泛滥深感震惊和不安,于是才有了上面提到的这篇诈文。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也对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性给予了客观冷静的评论,他指出,“由于不受科学规范的限制,后现代主义者可以如其所愿地进行自由研究,自由地‘玩弄’范围广阔的各种观念(有时候甚至以一种荒唐滑稽的方式)。”与现代科学不同,后现代社会理论事实上只不过是由“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种观念组成的大杂烩罢了。”[9](P338)
标签:认识论论文; 考古学论文; 福柯论文; 科学论文; 知识考古学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疯癫与文明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词与物论文; 哲学家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