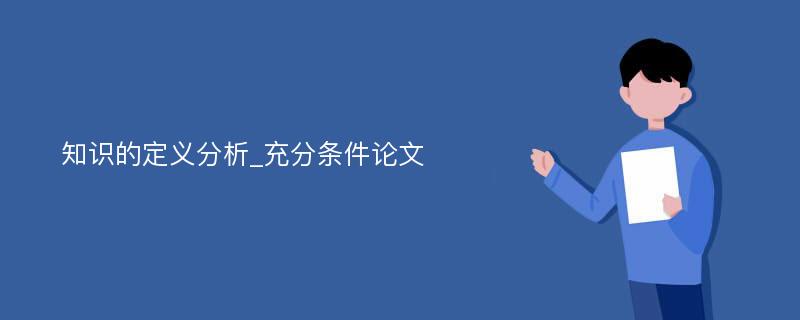
关于知识定义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义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8)04-0013-11
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老问题。但我们现在未必人人都知道究竟什么才算是知识。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一、传统知识定义
知识的定义是指“知识”这一概念的定义。知识的概念与知识当然并不是同一的。概念是思维的最基本的单位,它是内在于认识主体的思维之中的。而知识并不完全是内在的。知识是认识主体对外在事物正确把握后形成的信念。知识的概念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必须能够反映知识的本质的特性。分析知识概念的定义,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明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资格说,我们是有知识的,或者说我们能够宣称我们是知道的。知识概念与知识的区别还在于从定义上说,知识必须是真的,而在实际上我们认为自己当下把握的知识未必就是符合知识定义要求的。
知道(to know)是与知识(knowledge)同义的。说你知道某物,就是说你拥有关于这一事物的知识。同理,说你拥有关于某物的知识也就意味着你知道了这一事物。
在此所谓的知道或知识的确切含义,不是某种技艺,如你知道如何驾车,你知道怎么样打篮球,你知道如何能够考上研究生,等等。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知识的对象是什么,知识的种类有多少,而是要问知识本身是什么,知识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知识论的讨论要能够寻找出存在于一切可能的知识中的共同的本性。
真实的意见与知识在实用方面可能具有同样的指导的作用。比如你参加智力测试,虽然你并不知道哪个才是正确的答案,但你很幸运都答对了,这就是说,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你不具有知识或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回答,但事实是你都猜对了,这就表明你对于这些问题,拥有真的信念。就实用的目的讲,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上述的智力竞赛中,真的信念与知识一样,都可以使我们达到同样的结果。考试时,我们也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形,很幸运,很多题我们都蒙对了。于是我们高分通过了考试。可见,蒙对了或真的意见与知识或知道似乎都能够给我们不少的益处。在智力竞赛、考试的例子中或者其他的实际生活的场合中,既然正确的意见或猜测与知识起着同样的指导作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知识与正确的意见之间加以区别呢?
应该承认,这两者之间是有着很大的或本质的区别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在于有知识的人会一直获得成功,而没有知识仅仅具有正确意见的人,虽然也可能极其幸运,蒙对了或猜对了不少,但他们只能在有的时候获得成功,在大部分的时间却总是不成功的。而且即便取得了成功,这样的成功也是极其飘忽不定的。为什么呢?
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举雕像为例对美诺说,代达罗斯的雕像是伟大的杰作,是很值钱的雕像。但如果你不把它们捆绑起来,它们就会逃跑。如果把它们捆绑起来,它们就会在原地呆着。如果你有一个未加捆绑的这样的雕像,那么它是不值钱的,因为它会像奴隶一样的逃跑。但是如果你把它捆绑起来,那就非常值钱了。知识与正确的意见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被捆绑的雕像与未被捆绑的雕像之间的区别。在苏格拉底看来,正确的意见如果能够固定在某一地方不动,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东西,可以用它来做各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加捆绑,那么它随时都有可能逃走,会从人的心灵中逃走。比如一个刚入学的新生,选了有关中国哲学的两门课程。在一个课堂上老师如胡适主张老子先于孔子,他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你看来显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于是你也就不得不跟着他走,成了胡适派了。但在别的课堂上,另一位老师,如梁启超却主张孔子先于老子,当然他的这一主张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他有很多的理由,也有相当丰富的史料来佐证他的观点。你发觉自己也不得不跟着梁启超跑,于是不知不觉间又成了梁启超派。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历史上的孔子和老子究竟哪位在先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只是由于历史悠久,资料缺乏,现在竟成了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了。现在不谈这一问题能否最终解决,我们关心的是,在此一问题上,胡适与梁启超所具有的看法,至少在他们本人看来,不仅是正确的意见,而且是被理性“捆绑住”的正确意见。而那位新入学的学生所具有的显然仅仅是正确的意见,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断地被胡适与梁启超牵着鼻子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他所具有的仅仅是意见,而不是所谓的知识。知识与正确的意见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苏格拉底所谓的要把正确的意见捆绑起来,是说正确的意见本身还不是知识。正确的意见必须再加上些什么东西才能构成知识。在他看来,用来捆绑正确的意见的是人的理性。正确的意见一旦被我们的理性捆绑住了,那么它们就不仅仅是正确的意见了,而成了知识,成为了稳定的东西,对于我们真正具有无上价值的是被“捆绑住”的正确意见。
在苏格拉底看来,运用理性捆绑正确意见的过程是回忆的过程。他认为:“如果关于实在的真理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中,那么灵魂必定是不朽的,所以人们必须勇敢地尝试着去发现他不知道的东西,亦即进行回忆,或者更正确地说,把它及时回想起来。”[1]此一看法,现在很少有人赞同。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特色在于运用其精神助产术帮助别人生下思想的胎儿。如果胎儿是假的,他要把此胎儿拿走。如果这一胎儿是受孕的,那么这就是真实的思想。我们看到,他特别注重的是思想的论证,更重视论据的充分性。凡是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东西,他都不屑一顾。
《美诺篇》讨论的主题是美德的性质及美德是否可教,知识并未成为讨论的中心。但通过这一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格拉底认为,正确的意见需要运用理性来捆绑,或者说正确的意见应该得到理性的说明或解释。于是,知识概念的定义中应该包括这样三个成分,它们分别是:1.真;2.意见或信念;3.理性的解释。对于我们讨论和理解知识性质最为重要的是《柏拉图全集》中的《泰阿泰德篇》。因此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又经常被称之为“泰阿泰德问题”。
苏格拉底问泰阿泰德“知识是什么”。泰阿泰德想了想说:“我想,说某人知道某事就是觉察到他知道的事情,因此,就我现在的理解来说,知识无非就是感觉。”[2]664显然,这样的回答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事物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他人就是它向他人呈现的样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事物向我们所展现的表面的特殊的现象,而我们看不到事物的真实的一面;第二,如果用感觉来定义知识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然会碰到这样的困境,即我们如何来区别我们的正常的感觉与虚假的感觉之间的差异,如何来区分正常人的感觉与由于疯狂或心理失调所引起的错觉,又如何来区别睡眠与苏醒之间的不同。泰阿泰德承认,他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在它们之间作出明确的划分;第三,如果感觉是知识,而感觉显然是指视、听、触、闻等感觉器官的活动及其对象,那么我们就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些奇特的现象,如我看见一本红色的书在我眼前,如果看就是知识,我睁开眼看见红书,我就知道这本红书。如果我闭上眼,那么我在心里肯定记得这本我已看到的红书,但这时我却不能够说我知道这本红书,仅仅因为我已经闭上了眼睛。如果说知识就是感觉,那么只有当我们在听、看的时候才能说我们知道了某物或对某物具有知识。因为在这里看或听与认识或知道是同义的,所以不看或不听意味着不认识。从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识一事物并仍记得它的人并不认识它,因为他没有看见它,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因此,苏格拉底的结论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知识并不存在于印象,而在我们对印象的反思。似乎在反思而非在印象中,才有可能把握存在与真理。”“不能在感觉中寻找知识,应当到心灵被事物充满时发生的事情中去寻找。”[2]713,714
苏格拉底的诘难把泰阿泰德从感觉现象引向了认识主体的反思或所谓的判断。这就引导泰阿泰德“把知识定义为真实的判断”。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真实的判断。在苏格拉底看来,真实的判断是与虚假的判断紧密相连的。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判断的性质,就得知道什么是虚假判断的性质以及虚假判断产生的可能的途径。
要回答上述的问题必然会涉及什么是“知道”的确切含义。所谓“知道”是指,当我们说我们知道的时候,无非说的是这样的两种情况:第一,我们知道某些事情;第二,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某些事情。具体说,当我们知道某物,我们就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某物。同理,如果我们不知道某物,我们就不能说我们知道某物。如果上述的两种情况是所谓的真实判断的含义的话,那么虚假判断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说我们在思考虚假的事物,那么情况可能会是如下的几种:
第一,我们错认了事物,比方说我们知道两件事物甲和乙,我们有时候会把甲当作乙,或者是将乙当作甲。这就是所谓的误判。这时候我们会做出虚假的判断。
第二,有时候我们会对不存在的事物进行思考。但此时的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事物不存在,而是坚信我们所思考的事物是存在的。于是,我坚信某物存在,但此事物又是不真实的。
苏格拉底认为,上述的第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第一,如果我们正在思考两样事物都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么虚假判断是不可能的。因为既然这两样事物都是我们所知道,我们也就不可能将其中的一物误判为另一事物。第二,如果两样事物中的一个是我们知道的,而另一个是我们不知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误判也不可能出现。因为既然我们认识其中的一个,而不知道另一个,那么我们必然没有误解这两者的机会。
在第二种情况下虚假判断是否可能出现呢?似乎也不可能。苏格拉底认为,想不存在的事物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这一说法似乎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根据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经常在想像那些似乎不存在的事物。但是知道与想像并不是一回事。知道是对存在着的事物的认知。所以如果一事物不存在,那么我们对这一事物的认识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第二种情况下,虚假判断也是不可能的。
在苏格拉底看来,虚假判断不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之中,也不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之中。那么还有什么可能的情况下会出现虚假的判断呢?这样的可能的情形就是,我们对我们所获得的感觉的反思有可能出现误判。苏格拉底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发问等于又回到了上面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即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两样事物而我们把其中已知的一个误认为是已知的另一个。而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苏格拉底认为虚假判断是存在的,但我们寻找虚假判断的努力是失败的。而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这样的努力探讨的前提有问题。因为我们是在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知识的情况下来寻找虚假判断的。既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知识,我们当然也不会了解什么是知道。这就是说,我们所积极努力寻找的东西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好比我的朋友要我去机场帮他接一个朋友,却忘了告诉我他的朋友长的具体模样。其结果可想而知。这表明,把知识撇在一旁去寻找虚假判断,是错误的。这就是说,我们只有在知道了什么是知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知道什么是虚假的判断。于是,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的对话也就再次返回到了“什么是知识”这一正题上,即“知识就是真正的信念”。但前面的讨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对知识性质的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苏格拉底指出,当时的那些智者、律师和演说家鼓动如簧之舌就可以蛊惑人们相信他们的说辞,以为这些就是真实的信念。因此我们必须在真实的信念之上再加上些条件或要素使它们成为知识。那么应该加上些什么东西呢?泰阿泰德说:“真实的信念加上解释(逻各斯)就是知识,不加解释的信念不属于知识的范围。”[2]737解释可以有三种意思,第一种是指说话声音中的思想的影像,第二种是列举所有元素而达到的整体,第三种是要能够指出一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相区别的标志。但苏格拉底明白地指出,真实的信念即便分别地加上这样的解释还是不能够构成知识。
我们知道《泰阿泰德篇》的主旨是讨论什么是知识,但整篇对话却没有向我们揭示关于知识的完整定义。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了解了苏格拉底对于知识的看法。他坚定地指出知识不是感觉。他认为真实的信念加上解释也同样不能够构成知识。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虽然苏格拉底认为真实的信念加上解释仍然不能够构成知识,但他并没有否认,真实和信念是构成知识的两个必要条件。他所以说真实的信念加上解释不能构成知识,是因为“解释”本身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在解释之外去寻找构成知识的第三种要素或条件。
现在,绝大多数的哲学家认为,知识除了必须是真实的意见之外,还应该加上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证实。所谓证实是说你应该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或证据表明你所拥有的意见或信念是真实的,而不是仅仅根据猜测、想像或其他的什么途径就断言你的意见或信念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知识构成的三个条件分别是信念、真和证实。
二、传统知识定义的要素分析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信念是知识的第一个条件。这就是说,知识一定是信念。就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的知识而言,知识是人类的知识,或者说任何知识都必须是认识主体所能够把握的,或相信的。知识要成为知识就蕴涵着这样的思想,即它必须成为认识主体的思考内容或对象。因此,你要知道某一个东西,首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你必须让这一东西成为你的思维或思考的对象。比如说,我们知道太阳系有九大行星。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科学常识。但是,如果我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太阳系有九大行星这一事实,相对于我而言绝不是知识,因为它首先不是我的信念。要使这一事实成为我的知识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我要相信这个事实,要使它成为我的信念。总之,知识必须是信念。
但信念却不一定是知识。信念是构成知识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说信念是构成知识的必要条件是说,如果没有信念,那么就没有知识;说信念不是知识的充分条件是说,有了信念,但却不一定有知识。这也就是说,没有信念就必然没有知识。所以,信念是形成知识的第一个条件,或者说是构成知识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信念必须加上其他的因素才能够构成知识。这就清楚地表明,信念与知识有区别。
信念通常为某一特殊的认识主体所持有,是认识主体内在的一种心理状态,或是在自己的思维活动中对某一思维内容的断定。信念或相信可以经由言或行表达,也可以不借助于言或行而进行。因此我拥有什么样的信念,你很难断定。同理,你拥有什么样的信念,我也难以裁决。要断定其他人的信念,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听其言,观其行”。人的言行并不总是真实地反映内在的思想或动机。所以“听其言观其行”必然设定某人是可信赖的,是忠诚的,是不会欺骗人的,其言行是一致的。但一个忠诚、言行一致的人也经常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说错了自己的看法或心思等。所以言行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并不总是能够真实地反映内在的信念的。至于那些借助于言或行而进行的信念或相信,我们更是难以诠释。
一般而论,信念也是容易发生变化的。比如你今天可以说:“我相信我的朋友对我是忠诚的。”但是明天却可以说:“我不再相信我的这位朋友了,他对我背信弃义。”知道和相信具有不同的含义。你知道某东西,你必须说明你是知道这一东西的,你必须提供“知道”的充分条件。但当你说“我相信某一件事物”的时候,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相信某一事物,完全是我内心的一个认定,我不需要提供什么理由或证据。正因为不需要理由或证据来捆绑我自己的任何信念,所以信念就容易变化或飞走。
人们却也经常会相信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物,当然这样的信念也不是知识。比如,有些人坚定地相信,鬼是确实存在的。你不相信,就要问他,请他告诉你鬼在什么地方存在。他当然是说不清楚的。虽然他说不清楚鬼在何方,但对鬼之有却坚信不疑。这样的信念不是知识。又比如基督教的信徒是相信上帝存在的。上帝的存在当然是无法经由理性的方式证明的。但他们却确信无疑。他们确信无疑是因为他们信仰上帝。因为信仰上帝,所以他们认为上帝是存在的。这样的信念也不是知识。可见,知识只是信念中的一种。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此处所谈的信念决不是纯粹主观的或与主观相类似的信念,而是指与认识的客体密切相联的那些信念。如我们相信太阳系有九大行星这样的信念就是这样性质的信念。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信念只是形成知识的第一个条件,而不是形成知识所需要的充分必要的条件。
知识所需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信念必须是真的。
在这里,我们现在不必急于来讨论究竟怎么样证实某一信念是真的这样的技术性的难题。而是要探讨真或真实与知识之间应该具有什么样性质的关系,即知识是否蕴涵真。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知识是信念。但并不是所有的信念都是知识。因为信念有真实与虚假的区别。只有真的信念才有可能成为知识。而虚假的信念决不可能是知识。
于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知识必须是真的信念。或者说,知识是否必然地蕴涵真的信念。
我们先来看,虚假的信念有无可能被称为知识。在此,我们不讨论虚假信念是如何形成的,而是讨论虚假的信念有否可能成为知识。一般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信念是虚假的,那么它们便不可能转化为知识。假如你正在寻找一本书,而且没有找到,于是,我对你说:“我知道这本书在什么地方。它就在我左手边的书架第二层上。”你当然相信我的话,就去那个书架的第二层找。翻遍了第二层,就是找不到。我说:“我知道。”就是说,所谓的“知道”的对象应该是一个事件或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在上述的场合下,我所知道的应该是“那本书在我左手边的书架第二层”这样的客观事实。但你寻找结果是那本书并不在我所说的地方,或者我所说的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非常自然的反应就是:“你事实上并不知道这本书在什么地方。”我说我知道,你说我不知道。我们两人的对话在逻辑上预设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即“知道”这一概念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含义,这就是“知道”必须指向一特定的客观事实。如果这个特定的客观事实存在,那么我就有资格说我知道。否则,我就没有资格说我知道。因此,评判认识主体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的一个标准就是,有还是没有相应的客观事实与我们所已经拥有的信念符合。如果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知道。如果没有,那么回答就是否定的。如果一个人相信他所熟悉的一个朋友去世了,但过了几天在一个社交场合发现他的这位朋友居然在舞场翩翩起舞。这说明几天前他“不知道”关于他的这位朋友的情况,而现在他“知道”了关于这位朋友的真实情况。以前的信念是假的,而现在的信念是真的。真的信念指向一客观的事实。虚假的信念并没有这样的事实与之相符合,所以它不能转化为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只能说,他事实上并不真正知道他朋友近来的情况。既然不知道,他也就不具有关于他的朋友的知识。这就说明,知识应该蕴涵真或真实这样的含义。
那么,我们能否“知道”虚假的事实呢?所谓虚假的事实是指那些不存在的事实;或指错认了的事实。比如我们要知道事物甲,但我们却错认为是乙;或指通过想像等途径所产生的场景等等。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知识蕴涵真。而所谓真是指我们对事实认定或看法是有依据的。事实就是认识或知识或判断为真的依据。如果虚假的事实是指的上述第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认识虚假的事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既然虚假事实不存在,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在此情形下,说我们认识了虚假的事实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虚假的事实是指错认的事实,而错认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这是指我们主观认识方面的错误。这样的错误经常发生,在此意义上的虚假事实是有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发生,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说我们“知道”虚假的事实,而只能够说我们不知道。至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事实与我们此处所说的客观事实并不等同,所以它们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是不同于相信、惊奇、思考、希望这些心理状态。当然你相信某种信念是真实的时候,你无疑会有某种心理状态。但是知识并不仅仅描写或摹状人们的某种心理状态,它还必须要指明人们所拥有的某一信念是真的。这也就是说,信念的真意味着信念与信念对象的一致或符合。这样的真实际上便是大部分哲学家所坚持的信念和外在世界之间的符合。这种真理符合说固然有好多理论上的问题,但是在讨论和研究知识理论时是断然少不了它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实在是关于外在实在的知识。
知识是真的信念,但是真的信念却不一定是知识。假如一个人并不具有任何的充分理由,但是他却坚定地相信明天将会下雹子。在他所生活的这个地区自有史以来就一直没有下过雹子,而且现在的天空也异常的晴朗,同时天气预报也与他的看法截然不同,报道说明天天气将是晴朗的。然而第二天却天公不作美居然下起了雹子。于是,这个人的信念得到了印证,可以说是真的。而且他本人也坚定地相信这一信念是真的。在此情形下,他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看,我的预言不是胡说八道,不是信口雌黄,而是有根据的。今天不是下了雹子了吗?”但是,我们在这里却可以明确地指出,尽管这个人的这一信念是真的,然而很遗憾的是这一信念仍然不是知识。在他预言明天会下雹子的当下,他并不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会下雹子。因此,这个人的信念缺乏充分的理由或材料的支持,所以这一信念仅仅是一种幸运的猜测。当然,我们会承认他是很幸运的,因为他的猜测是正确的,或者说他关于第二天要下雹子的信念是真的。但是,我们知道信念的真,仅仅是成为知识的部分条件,而不是构成知识的全部条件。换句话说,知识必定是真的信念,但真的信念却并不一定是知识。如在数学考试中,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是,有些题目从直观判定某个答案是对的,但我们就是不知道究竟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去求出这一答案。如果真的信念就是知识的话,那么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们的真的信念也都是知识了。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对知识做这样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这也就表明要使真的信念转化为知识,我们还必须要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信念是真的。我们不但要知其然,还要进一步知其所以然。因此在信念和真这两个条件之外,我们还需要第三个条件。那么,什么又是形成知识的第三个条件呢?
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表明我们所拥有的信念是真的。
证实是我们说某一信念或判断或知识为真时所能够提供的充分的理由或根据。说某一信念为真时,我们必须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或根据说明它为什么说是真的。这里所说的理由或证据当然是指知识或判断有还是没有对象与其符合。所谓的对象是指在知识之外的客观事实。如果知识或信念与外在的客观事实有相应的符合的关系,那么我们便有资格说,知识或信念得到了证实。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事实,那么信念或判断也就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证实是指,信念或判断或我们所说的“知道”与外在客观事实之间的符合的关系。
真的信念必须要得到完全的证实才能构成知识。在这里,完全的证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部分的或不完全的证实是不够的或不充分的。比如,我相信我的某一本书在我的书房的书桌上放着,因为我每天都放在同样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它是不会有错的。现在我不在书房里,但是我还是认为并且相信这本书还仍然在老地方放着。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本人亲自到书房去看一看,我仍然不能完全证实此书还仍然在原来的地方放着。
在形成知识的三个条件之中,证实的问题是一个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问题。这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证据本身就是一个有程度上高低之分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究竟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断定什么样的证据是完全的、是充分的?而什么样的证据又是不完全、不充分的?这一问题可以说是知识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此详细讨论,而只能从大体上对知识证实的理论的种类作一介绍。而且我们在此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对“知识”这一概念要素的分析揭示出了知识与知识的证实之间的关系。由知识的证实又进一步地过渡到各种不同的知识证实的理论。所以,知识这一概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分析知识这一概念,我们就会形成一完全、系统的知识理论系统。
经验知识的证实理论共有三种:
第一种是基础主义的证实理论(foundation theory of justification)。根据这种证实理论,知识的证实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这一基础就是证实的初始前提。这些前提向我们提供了某些基本信念,而所有其他的信念都要依据这些基本信念才能得到证实。
第二种证实理论是融贯论(coherence theory of justification)。融贯论的倡导者们坚决地反对基础主义者的证实理论。他们从根本上就否认了基本信念的存在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应该将证实(justification)和论证(argumentation)、推论(reasoning)加以区别。对于他们而言,根本不需要什么基本的信念,因为所有的信念都将由它们与其他信念,将由所有这些信念相互之间的一致的关系,而得到证实。所以在他们看来,证实过程的确立是由于信念和信念之间的和谐和一致的关系及其彼此支持的方式,而绝对不是由于这些信念是建立在所谓的基本信念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种证实理论叫做外在主义(externalist theory of justification)。这种外在主义的证实理论反对上述的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的证实理论。这种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我们为了获取知识,既不需要基本信念,也不需要信念之间的融贯。我们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只是信念与实在之间的某种关系。因果关系就是这里所需要的外在关系。在某种既定的场合下,使我看见了一红色的东西这一信念转化为知识的既不是所谓的基本信念,也不是这一信念与信念系统之间的融贯,而是我的这一信念是由我本人看见了某一外在的红色东西而引发的。持外在主义立场的哲学家们甚至进一步认为,证实对于知识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认为,我们真正所必需的只是信念和外在事物之间的某种外在关系。外在主义者的这种理论或许可以称之为外在主义的证实理论。
上述的三种证实理论之间虽然有种种的差异,但是这三种理论之间也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如外在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基础主义,但是外在主义本身实际上也是基础主义的现代变种,因为这种理论实质上把信念和外物之间的外在关系看成是使信念转为知识的基础,所以其理论基本上还是落在了基础主义的框架之内。由于这三种证实理论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所以解决知识理论中的最困难的证实理论问题的出路似乎是将基础主义证实论、融贯主义的证实论和外在主义的证实论结合起来,由此而形成完全的证实理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哲学家对什么是证实以及如何证实等问题充满着激烈的争论,但是有一点是完全清楚的,这就是,真的信念要能够称为知识必须得到证实。总之,知识就是证实了的真的信念(knowledg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三、质疑传统知识定义
但是传统的知识构成论在1963年却遭到了致命的挑战。爱德蒙·盖特尔(Edmund L.Gettier)在1963年第6期《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首先对传统的这一知识定义发起了攻击。他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很富有挑战的意味:《证实了的真的信念是知识吗?》
盖特尔在文章中首先列举了对传统知识定义的三种大同小异的表述方式:
1)S知道P
如果①P是真的;②S相信P;③S相信P得到了证实。(在此,我们以S和P分别表示认识者和命题)
2)S知道P
如果①S接受P;②S有充分的证据接受P;③P是真的。
3)S知道P
如果①P是真的;②S确信P是真的;③S有权利相信P是真的。
对知识定义的这三种传统的表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第一种表述是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的201页和《迈农篇》98页中提出的。第二种表述是取自齐硕姆(Roderick M.Chisholm)在《察见:哲学研究》(1953年)一书中对知识所下的定义。第三种表述是艾耶尔(A.J.Ayer)在《知识问题》(1956年)一书中对知识所下的定义。
盖特尔认为,上述对知识定义的第一种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它并没有形成充分的条件来指明“S知道P”这一命题的真值。第二种表述和第三种表述虽然分别以“有充分的证据”和“有权利相信”置换了第一种表述中的“相信P得到了证实”,但是,它们同样也都没有构成知识定义的充分而又必要的条件。
接着盖特尔又指出了如下的两点。
第一,如果“S相信P得到了证实”是“S知道P”的必要条件。那么在这种证实的意义上,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就是,一个人相信了某一命题并且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一命题却是一个假的命题。
第二,对于任何一个命题P,如果S相信P并得到了证实,而且P蕴涵着Q,所以S从P演绎出Q,并接受了这一推演的结果的Q,这样S相信Q也同样得到了证实。
以上两点对于盖特尔反对传统的知识定义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因为根据这样的两点,盖特尔列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传统知识定义的失误。
[例证1]假定斯密思和钟斯同时在某一公司申请一项工作,并且进一步假定斯密思对于下列的联言命题有充足的证据。这一联言命题如下:
a.钟斯将会得到这一项工作,而且钟斯有十枚硬币在他的口袋里。
斯密思关于这一联言命题的证据可能是公司经理曾向他私下示意钟斯将有可能最终得到这份工作。而且就在十分钟前斯密思还亲自数了数钟斯口袋里的十枚硬币。上述的联言命题a蕴涵着:
b.将得到这一份工作的那个人有十枚硬币在他的口袋中。
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斯密思看到了从联言命题a到命题b的蕴涵关系,并在联言命题a基础上接受了命题b,并且他对命题a有充分的证据。在这一例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密思相信命题b为真确实是得到了明白无误的证实。
但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定,斯密思本人并不知道,是他而不是钟斯最终将得到这一份工作。而且同样凑巧的是,斯密思自己的口袋里也有着同样多的十枚硬币,对此他却全然不知。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联言命题a是假的,但是从这一虚假的命题a却推演出了真命题b。
在上述的例证中,1)命题b是真的;2)斯密思相信命题b是真的;3)斯密思相信命题b为真得到了证实。但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却是,斯密思并不知道命题b是真的。因为命题b的真是根据于斯密思口袋里的硬币的数量,但是斯密思本人却并不清楚他自己的口袋里到底有多少硬币。他相信命题b的真却依据于钟斯口袋里的硬币的数量。这就是说,证实了的真的信念并不一定构成知识。
[例证2]现在也让我们假定斯密思有强有力的证据使他相信下列命题a:
a.钟斯有辆福特车。
斯密思的证据得自于下列事实,即据他记忆所及,钟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确实有辆车而且就是福特车,就在前几天钟斯还让他坐过福特车兜风。
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假定,斯密思还有另一位朋友布朗,但是他并不清楚布朗现在究竟在何处。斯密思于是随意选择了三个地名,构成了下列三个命题:
b.或者钟斯有一辆福特车,或者布朗在波士顿。
c.或者钟斯有一辆福特车,或者布朗在巴塞罗那。
d.或者钟斯有一辆福特车,或者布朗在布雷斯特——立陶宛。
上述三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蕴涵在命题a中。现在我们又进一步假定,斯密思看到了他根据命题a构造的命题间的蕴涵关系,而且根据命题a去接受命题b、c、d。斯密思从自己有充分证据的命题a推导出了命题b、c、d。于是,斯密思也就完全证实了自己可以相信这三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命题。当然,斯密思并不知道布朗的行踪。
但是,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假定另外两个条件。第一个是,钟斯事实上并不拥有一辆福特车,他现在驾驶的是一辆租用来的车。第二,由于完全的巧合,而且斯密思本人也并不知道,命题c提到的巴塞罗那正是布朗现在所在的地方。如果假定了这两个条件,那么斯密思并不知道c是真的,尽管1)命题c是真的,2)斯密思本人也相信命题c是真的,3)斯密思相信命题c为真得到了证实。
于是,盖特尔的结论也就是,证实了的信念并不是知识。
盖特尔的文章发表之后在知识论研究领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至今在关于信念究竟应该具备多少条件才能转化成知识这一问题上仍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仍无定论。
许多哲学家肯定了盖特尔文章的价值,认为他的文章是一篇经典性的文章,有重大的意义。自60年代末期至今英美哲学界的许多哲学家都在倾其全力研究,在传统的关于知识定义的三要素中还应该补充进什么样的新的要素,我们才能够成功地构成一个关于知识的必要而又充分的定义。
当然,有些哲学家不同意盖特尔的论点。他们认为,盖特尔的反例证是依据于一种虚假的原则,即人们以假命题为证据相信并证实某一命题原则是假的。既然这一原则是假的,那么盖特尔的反例证也失效。他们认为,作为证据的命题必须是真的,它才能用以证实某一人去接受或相信某一命题。所以他们还是与传统的知识是证实了的真的信念的看法相同。
又如阿姆斯特朗(D.M.Armstrong)也反对盖特尔的反例证。他在其《信念、真理与知识》(1973)一书中指出,盖特尔的反例证有缺陷,因为这些例证完全依赖于如下的假的原则,即假命题能够用来证实人们对其他命题的信念。他认为,只有当命题P被认为是真的时候,它才能够用来证实另一命题h。
其实,对盖特尔反例证的上述批评并不具有充足的理由,因为许多类似于盖特尔的论证的论证并不依赖于上面所讨论的虚假的原则。我们可以对盖特尔所举的论证稍加修改,来进一步申述我们的观点。
假定詹姆士在告诉斯密思他有一辆福特车之后,并给斯密思看了他的驾驶执照。我们可以这样来进一步假定,詹姆士在与斯密思的交往中一直是诚实可信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上述的证据组成一个联言命题,这个联言命题叫做m。这样一来,斯密思相信詹姆士有一辆福特车的信念得到了证实(这一命题为r),结果当然也就是,他关于他的办公室的某一人有一辆福特车的信念得到了证实(这一命题为h)。
通过上述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到,命题m和命题h是真的,而命题r却是假的。因为斯密思相信命题h并且得到了证实,然而事实是他却并不知道命题h。
我们在这一例证中用来证实命题h的是命题r。但是既然命题r是假的,所以这一例证就与这一有争议的原则是相互冲突的。由于命题r是假的,这样它也就什么都没有证实。可见,原则是假的,那么反例证也就随之无效。
现在,我们也可以把上面的例证再做一下修改。通过这样的修改后,为斯密思证实命题h的命题是真的,而且斯密思本人也知道这一命题是真的。下面让我们假定,斯密思从命题m推演出下面这样的命题n:
办公室中有人告诉斯密思他有一辆福特车并且给斯密思看了他的驾驶执照,而且此人在与斯密思的交往中始终是诚实可信的。
由于斯密斯是从命题m正确地推出了命题n,而且他也知道命题m是真的,所以命题n是真的,同样斯密思知道命题n是真的。正是在命题n的基础上,斯密思相信了命题h,即他的办公室中有一人有一辆福特车。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密思对于命题h的信念是已经得到了证实的真的信念。而且他本人也知道使他相信命题h的证据也是真的,然而,事实上他仍然并不知道命题h。
总结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尽管一个命题能够得到证实,并且用以证实这一命题的证据也是真的,或者说,被知道是真的,但是对于传统的知识定义即知识是得到证实的真的信念仍然有能够反驳它的例证。所以,盖特尔反对传统知识定义的看法并未被推翻。于是,在知识论的研究中,对于盖特尔的挑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采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应该接受盖特尔的挑战,分析他所提出的问题,从而尽可能正确地解决问题。
盖特尔的论文在知识论的研究领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于是,许多文章都企图来分析和解答盖特尔的挑战。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在绞尽脑汁思考着,如何在传统的知识构成的三要素之外来增补第四个条件,以使知识的定义趋于完善。
由于在盖特尔的例证中,认识主体得到的经过证实的真的信念是从假的信念中推演出来的,所以关于知识的第四个条件必须是这样的,即认识主体相信命题p的证据就不应该包括任何假的信念。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关于知识的这样的新的定义:
S知道P
如果①P是真的;②S相信P;③S相信P得到了证实;④S证实P的证据不应包括假的信念。
然而,对于这一新的定义,我们仍然可以提出反对它的例证。假设你驾驶车向某一社区驶去,你看到了许多所谓漂亮的别墅,你是在不太远的地方,且光线非常好的情况下看到它的,事实上它看上去就是与真的别墅一模一样。于是,你就认为你得到了经过证实了的真的信念:它们就是别墅。但是,事实上,其中有些根本不是别墅。由于拍摄电影的需要,为了使别墅的数量显得更多些,所以制作电影的人想法建造了不少十分酷似于真的别墅模型。这样,你从公路上一眼望去,根本不可能把这些模型和真正的别墅区别开来。准此,你就不能说,你知道你所看到的就是别墅,尽管你有了经过证实的真的信念。
于是,怎么样来修改和补充传统的知识定义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理论问题。
我们认为,似乎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是要对盖特尔的例证作更深入的分析,然后再来寻求解决问题可能的方向。既然盖特尔反对传统知识定义的两个反例证都是以假命题为证据来证实另一命题,那么修补传统知识定义的一个较为理想的途径似乎是在知识证实过程之中设法排除以假命题为证据的可能性。
同时,盖特尔反对传统的知识定义的例证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比如在第一例证中,命题a蕴涵着命题b,因为命题a真,所以命题b亦真。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盖特尔进一步假定,斯密思不知道是他本人,而不是钟斯将得到这份工作。他同样也不知道,他自己的口袋中也有这十枚硬币。这就是说,命题a是假的,由于命题b的真是从命题a推出来的,那么这也就说,命题a的假蕴涵着命题b的真。至少对斯密思说,情形是这样的。这在方法上似乎是讲不通的。因为盖特尔这一论证并不是同一层次上展开的。他首先是从形式上假定了命题a是真的,并以命题间的蕴涵关系推出命题b是真的。接着又从经验层次上假定命题a是假的,但斯密思本人不知道此命题是假的,仍然认为是真的,而盖特尔认定命题a是假的。于是,盖特尔的结论是,1)命题b是真的;2)斯密思相信命题b是真的;3)斯密思相信命题b为真得到了证实。根据传统知识的定义,斯密思应该“知道”命题b是真的。但盖特尔却指出,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尽管上述三个条件得到了满足,但是斯密思仍然不知道得到工作的是他而且他自己的口袋中也有着同样数量的硬币。所以传统的知识定义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盖特尔是从一虚假的命题出发,并且经过一真的命题,最后却导出一同样的假命题。
在这里,还需我们进一步讨论下列问题。
第一,证实的确切含义应当是什么?当盖特尔说,斯密思有充分的证据相信命题a为真时,他实质上是在说,命题a是真的。也就是说,一命题为真是说有一对象与此一命题相对应,它们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当我们说,某一命题为假时,是在说没有与此一命题相对应的客观事实。按通常的理解,这后一种情况不能称之为证实,而应该叫做证伪。证实是积极意义上的。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前述的[例证2]中,我们就不能说斯密思相信命题b得到了证实。但盖特尔所反对的传统知识的三个定义说的都是证实,而不是证伪。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盖特尔反驳传统知识定义的理由不是充分的。
第二,盖特尔对传统知识定义的反驳是在一种孤立的语境之中做出的,他将知识的定义完全与经验内容隔离开来。所以他能否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设定出发命题的真或假?能否从假命题导出真的命题?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在一种纯粹的语言分析中,我们可以随意设定某一命题的真假,但在经验知识体系中,任何一关于经验知识的命题的真假都必然与经验知识体系中的其他命题密切相关。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例证确实有随意性,但在有关经验科学的知识体系中,我们不能够随意说某一命题的真或假。在此情形下,命题的真或假既与经验科学体系中的其他命题密切相关,也与外在的经验事实相关。方法是假设了命题间的逻辑关系。
第三,蕴涵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在上述的第一个[例证1]中,当盖特尔是从命题a和命题b之间的蕴涵关系,即从前一个命题推出后一个命题的时,他注重的是命题的蕴涵关系,此种蕴涵关系当然不是经验性的。而当他说,命题a蕴涵着命题b并从前者导出了后者的时候,他着重的是这两个命题间的逻辑性的关系。但当他说命题b真而命题a假时,他所诉诸的不是两命题间的蕴涵关系,而是两命题的经验性的内容。既然盖特尔注重的是对传统知识定义的纯粹的语义学的分析,所以他能否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又诉诸经验内容呢?
第四,“斯密思将得到这份工作且口袋里有十枚硬币”与“将要得到这份工作的人的口袋里也有十枚硬币”尽管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下,从外延上说是等值的,但从内涵上讲是不等值的。从逻辑推导的形式讲有其道理,但结合着经验内容来讲却是完全不可以的。
第五,在文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强调,关于知识的定义与知识本身是有区别的。定义要求知识一定是得到了证实的真的信念。但这一定义并没有规定我们在实际经验生活中所得到的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知识一定是知识,或者说必须是得到证实的。完全有可能,在实际经验生活中,我们认为是知识的东西可能不是知识,可能没有得到证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知识定义中要求知识是得到了证实的真的信念。盖特尔文章的核心错误就是混淆了知识定义与知识之间的区分。
第六,更为严重的是,盖特尔的反驳例证都是在当事人并不知道的情形之下得到的。如斯密思并不知道,不是斯密思而是钟斯本人将得到工作且自己口袋里也有十枚硬币。如此等等。如果这样的例证不为认识主体把握,认识主体又怎么能够以此来表明某一命题是真的或假的呢?盖特尔如此讨论已经完全逸出了知识论的范围。
总之,根据上述的理由,我们认为,盖特尔的文章并未对传统知识定义构成威胁。信念要成为知识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而我们自认为是知识的信念不一定就是知识。
标签:充分条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