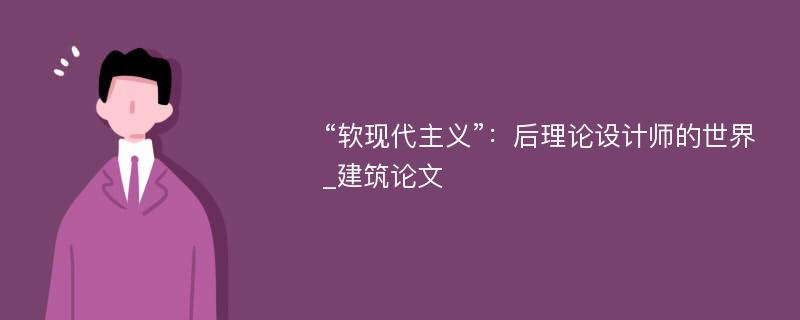
“软现代主义”:后理论设计者的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设计者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设计师和模仿者曾试图在后现代的折衷主义内创造出一种现代主义。然而,这是一种只信奉在尼采主义的强力意志和秩序误解中所固有的极权主义的现代主义。
失序成为再现的形式
虽然人们可能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理论对物质的胜利,但这是对一种马克思主义导出的现代主义的颠倒:现在一切烟消云散的东西都凝固了。失序成为再现的形式。像一种正在融化的物质一样,看似短暂的东西成为附属的东西,有时是有机性的,有时像一种装饰形式的拚贴画一样。
为了理解现代性的伦理,平民主义理论往往只走回到密斯·凡德洛(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格言“少就是多”那种程度上。这已经产生了一种我称为极少主义的生活方式审美。这并不是对密斯和现代主义发表沃尔夫式的谴责,而是说明需要把密斯及其简约主义的现代主义审美放置到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这样做,需要参考为现代主义伦理制定出基本原则的一篇演讲: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的“装饰与罪恶”。卢斯宣称,多余的装饰是被抑制的文化发展的一种信号,一种原始景色的表述,一种犯罪趋势的信号或没落贵族的标记。这产生了被贴上“不正常”标签的多余装饰。对卢斯来说,儿童或“巴布亚人”可能会随心所欲地乱涂或装饰,因为他们在生理和文化意义上都尚未“成年”。然而那些生活在一种成熟的、文明的文化之中的人,那些已经成年的人通过不正常的东西将只会打乱自己世界的秩序。
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失序,这种多余的装饰包括上帝。虽然尼采早就预言了上帝的死亡,马克思使上帝成为一种鸦片,但现在卢斯把上帝变成了一种多余的装饰。上帝不再是造物主,那个赋予世界秩序的造物主。相反,上帝被视为人性的扰乱者。平顶的密斯式摩天大楼无需大教堂指向天空的尖顶,它的水平平顶象征一种可以企及的超验性,而不是指向远处的手指。
人道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是一种世俗主义的行为,一种赋予上帝制造的无序状态以秩序的企图,一种战胜和反对宗教的人道主义行为。同样,现代主义既是乌托邦的,也是进步的——必要的世俗化。正如20世纪60年代“上帝死亡”的著名拥护者阿尔泰泽尔(Thomas.Altizer)所宣称的那样:“如果20世纪有一个清晰的人口,就它就是经过上帝死亡的一个通道,就是位于现代人新发现的根本内在之外的任何意义或现实的坍塌,就是一种消解超验之影记忆的内在。”阿尔泰泽尔声称,从此之中产生了一种尼采预言式的虚无主义“新混沌”。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际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兴起结束了芒福德(Mumford)格言的前一部分。装饰的放逐、上帝作为不正常之物的符号、一种内在性超验的平顶和纯粹主义的白墙全都试图消除世纪末炫耀的混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而且也都试图拥抱新的技术希望和一种有未来主义灵感的机器时代。正是这改变了现代主义的本质。在非理论的实践中,那些遵循纯粹主义宣言的人开始走向一种亚尼采主义(sub-Nietzschean)的虚无主义形式。密斯主义的审美是少,纯粹主义的审美是强加的简约。卢斯希望消除多余的东西,一种以文化和文明为名的简约,一种人道主义的、现代的、进步的伦理声明。相反,纯粹主义者为简约而简约,是一种认为技术是存在的理由的机器审美。纯粹主义的风气就是白色纯度(控制)的风气。
“纯白”的崇拜
在1927年斯图加特住宅展览会上,白色性与萌芽状态中的国际风格之间的缠结集合成一种集体的纯粹主义影响的未来想像。16位建筑师建造了一个小规模的住宅,在那里“惟一的限制是他们应该使用平顶和白色的外墙。”正如威格利(Wigley)所指出的,“认为现代建筑是白色的思想成功地展现在国际观众面前”。这种白色性不仅是对装饰的驱逐,而且是对一种新宗教审美原则的表述。在1922年,杜斯堡(Theo van Doesberg)宣称:“即将到来的风格应当详细说明‘宗教的活力’,而不是‘信念和宗教权威’”。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对纯粹主义的重申更具有天启性:“对美丽材料的信仰现在只是一种极度痛苦的最后痉挛。”直到20世纪30年代,杜斯堡仍愿意把白色宣称为人性发展的最高阶段,并认为白色性是存在理论意义的:“白色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颜色,洁白指引着我们的行为。这种白既不是灰白,也不是象牙白,而是纯白。白色是现代时代的颜色,这种颜色散失在整个时代之中,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完美、纯洁和确实性的时代。白色包含一切。我们已经驱除了堕落和古典主义的‘褐色’,而且也驱除了分色主义的‘蓝色’,一种对蓝天、绿胡子上帝和光谱的崇拜。”
同样,景象的澄明被固定成存在。由于未被标为是一种过去的装饰,白色建筑物想成为一种内在世俗王国的新耶路撒冷。在卢斯主义对装饰所引发的挑战和白色性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希望之间所捕捉到的东西,是被称为密斯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东西。这产生了鲍豪斯简约主义的人道主义、潜在石匠的技艺和重新制定秩序的乌托邦的、进步的欲望。密斯景象的核心是“大厦”、建筑艺术、建筑工人的技艺和建造技术。密斯把自己视为第一流的建筑工人,而不是一个艺术家或工匠。在他的景象的核心中存在着简单、秩序和纪律。
重构世俗环境
在现代主义思潮和审美中发生的是国际风格企图以一种证明自己超越环境的方式来建造新的耶路撒冷。普世的、国际的、现代主义的世俗之城想成为一座秩序和纪律之城。玻璃塔——新的世俗教堂反映的不是超验性上帝的荣耀,而是在它们反射性的平顶上反映出人类建造者的荣耀。消除多余的装饰重构世俗环境,其中现代社会可以进行反思。如果房屋就像柯布西耶所说的那样已成为一种用来生活的设计,那么密斯已把它转换成一种用来在其中进行思考的设计。密斯主义审美把整个城市变成一种用来思考的设计,一种其内在力量寻求人类精神对神圣的胜利的思考设计。
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努力在消除多余装饰的预言之外进行生活。世俗之人的兴起、世俗之城和对“上帝之死”的哀悼在一种都市背景的衬托下发生,而都市环境已经使这些情感成为现实了。对建筑来说,问题变成了:下一步是什么?虽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把现代建筑的死亡时间确定在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22分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摧毁普律特-伊果(Pruitt-lgoe)住宅区的那一刻,但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纯粹主义表述,类似于它对误用“新精神”的破坏性。走出秩序或超越秩序或秩序之后——一种后秩序——就是在后现代性实质中的东西。而且关键的是它在另一种塔中发现了自己最有潜力的象征。
软现代主义浮出水面
当今,由于全球化的世界似乎在无批判地拥抱被其称之为后现代的东西,由于我们在穿孔和纹身中以及在精神性和基础主义的兴起中看到了“多余装饰”的回归,所以建筑已经扔掉了后现代主义的装饰。在最近几年里,我们看到了走向被称为“软现代主义”(soft modernism)的东西的端倪。这被视为现代主义盒子的人性化更新,或许被视为对过去秩序的参照,是一种空间的包围,但现在是一种用来生活的空间。秩序、控制、纪律——但人性化,这就是一种即时性的现代主义。然而,某种“多”的东西(而不是“少”)正在产生。现代性取决于两个重要的轴心:简约(少/丧失/秩序/控制)和进步。后现代主义表现为相反的极端:过度(折衷主义/装饰物/混沌/多样性)和相对主义。如果现代主义为一种国际风格奋斗的话,那后现代主义推动了本土性。如果现代主义寻求一个尚未到来的终点,那后现代主义声称终点已经到来,因此让我们在狂欢中来庆祝它的死亡。
为了理解软现代主义的兴起,或许我们需要根据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来思考。在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中,现代性是正题,后现代主义是反题,软现代主义或许是合题。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则是一种没有理论、没有背景的现代主义,作为风格而独自存在。极少主义内部的简约常常发生在那些带有折衷主义的超验精神性形式的住房之中。缺少装饰发生在那些本身被不必要地装饰起来的住房中。这种软现代主义的参照点不是某种未来的乌托邦,也不是某种计算机时代的未来主义,而是在对后溯现代主义的盲目迷恋中放弃现代主义的进步。真实性变成一种仿真之物的商品。前后现代的“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的后现代之后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光环。在软现代主义、极少主义和后溯现代主义中生活就是过着向后看的生活,而不是向前看的生活。这并不是现代主义,但也不是庸俗艺术。设计师、二流的制图师和进行复制的建筑师已经终结了全息博物馆的设计。简约现在来自折衷主义的现在,从本土退却到一种未经思考的、强制的、时空混乱的后溯现代主义(retro-modernism)。“少”现在是在场在眼下的减少。
“毕尔巴鄂主义”
极少主义的设计师就是极少主义的本性之所。制图员/人性化现代主义的建筑师现在生活在芒福德格言的第二部分之外。他们在一种真实性的永恒循环中生活,而人们认为这种循环取决于后现代性的另一面。他们内部的临床性、把过去复兴为新进步的企图、生活风格的宣扬以及那种值得生活和仿效的生活风格导致了时空的混乱。它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后现代的,它仅仅是不真实的。同时,指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把技术缅怀主义的有机事物称为虚假之物在后现代性之后的另类、公开的表述。后溯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一种追求技术化生存的本土表述。然而,没有指出的是后溯现代主义与诸如弗兰克·盖里在毕尔巴鄂的古根汉博物馆这样的新反讽作品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些新的公共和公司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无意识地模仿了路易斯·沙利文的原初现代主义(proto-modernism)建筑表面。这样一些建筑物的虚假性在于公众对建筑物表面的兴趣和争论远远超过对它实际所展示出来的东西的关心。在这个意义上,毕尔巴鄂博物馆实际上是对自身的展示,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内在意义的存在形式。如果后溯现代主义的内部空间模仿了一种混有某种电子人未来的想像性过去,并因此使其不再是现代的,那么电脑辅助设计就混乱了现在与历史和本土性。这样一种后溯未来主义已经被注明了日期和划分了类别——查尔斯·詹克斯称之为“毕尔巴鄂主义”的东西。
詹克斯在这个方面上强调的是似乎天生自指(self-referential)的建筑。然而,电脑复制设计的重点实际上把诸如“毕尔巴鄂”这样的原型建筑基准转换成把外部事物当作是纯粹装饰的软件和新材料的可能性。虽然詹克斯可能把“令人心醉神迷的建筑”归为这种形式的建筑——这种建筑物似乎如此的过度,以致于使旁观者处于恍惚状态。
因为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企图把世俗的人道主义平面确定为权威和身份的基础。多余装饰的消失被当作是希望、自由和真实的标志。“毕尔巴鄂主义”追求“有机之物”的人造表象,这种表象就如同纯表面的表象一样是可以辨别和期望的东西,在这种追求中,“毕尔巴鄂主义”就是基因修改在建筑上的对等物。自然就被技术重构为“自然”本质主义形式的表现。
因此,即使密斯式的现代主义者把“当代之物”的表达设定在人类体验之中,但“毕尔巴鄂主义”所做的事情是使“当代之物”脱离技术机体的复制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人性本身成为“多余的装饰物”。同样,这种技术机体外形的存在形式是回溯现代主义存在形式缺失的侧面。电脑辅助设计的“毕尔巴鄂主义”把功能完全分解为形式,或者分解为如同“多余装饰物”那样的技术表象。换句话说,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是一种超存在——在那里“多即少”就是全部:把缺失之物斥为不相关之物。虽然马克·C·泰勒(Mark C.Taylor)把这些变化视为“新兴网络文化”的证明,藉此特别是在毕尔巴鄂,“形式变成了复合体”,而且现代主义的栅格变成了“动态性的”和“有机性的”,这里就有一种把网络技术视为“真实之物”的场所的本质主义误读。因此,就像教堂指的是被认为在世俗体验之外存在的一种规范性现实那样,电脑辅助设计的“毕尔巴鄂主义”也是如此,现在技术完全取代了上帝作为那种独自存有人性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