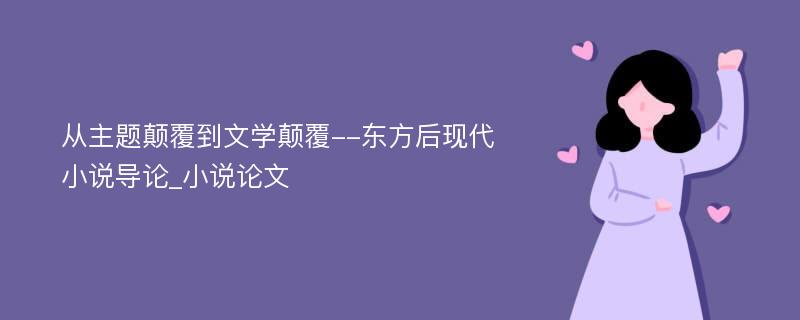
从主题性颠覆到文类性颠覆——东方后现代小说概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概论论文,主题论文,小说论文,到文类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东方后现代文学中,小说的后现代特征无疑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1991年11月,在墨西哥莫雷利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小说研讨会上,来自20多个国家的近百名小说家、评论家一起讨论了“小说的危机”。墨西哥作家埃尔南·拉蜡教授的发言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小说的技巧已经掘尽,主题已经写绝,等待小说家们的将只是前人留下的残羹剩饭。”[①a]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显然也面临着这种危机。小说如何摆脱困境?80年代以后,中国一大批中青年小说家为此作了种种不懈的努力,其中大大的热闹过一回,并且卓有成效的实验和探索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一、彻底颠覆传统小说主题和文类;二、小说叙述方法的转换与变革。本文拟就前一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般说来,19世纪小说或者说前现代主义小说是精心建构主题和充分完善文类的小说。这时小说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是明确的。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是为了证实、表达、宣讲某种观念、原则或者真理,最后达到对读者进行陶冶和教化的作用。马克思在1859年曾批评拉萨尔的剧作“最大的缺点就是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但是,马克思非但没有否定文学的倾向性,反而十分强调文学的倾向性。不过,这种倾向性不是通过大段大段的说教特别地指点出来,而是“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因为文学可以“真实”地再现现实,所以有认识作用;通过认识,进而发挥教育的作用;最后,在教育的同时,寓教于乐,文学又有了审美作用。由于文学具有如此巨大而又多重的作用,所以自然要求文学主题鲜明,语义单一、明晰,故事生动完整等等。巴尔扎克的小说可以说是这类文学发展到尽善尽美的标志。
20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即现代主义小说是重构主题和重构文体的小说。这时的小说的主题和作者的意图已不再是明确单一的。小说已由再现转向了表现,由注重外部世界转入内省、反思。小说的主题开始走向多义、模糊、分裂,甚至荒诞,因为现代主义作家认为,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原本就是如此。这正如爱尔兰诗人叶芝所揭示的:“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②a]现代主义否定了前现代主义的所谓“再现”的真实,强调内心,那怕是已被扭曲变形的内心的真实。他们并不反对文学的认识、教育、审美作用,他们反对的是传统文学认识的内容、教育的方式以及审美的局限,譬如他们强调潜意识、变态心理、象征、暗示、审丑等等。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家。
20世纪下半叶的小说,即后现代主义小说是颠覆主题和颠覆文体的小说。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意义根本就不存在,真实不可能具备任何客观性。一切都是符号,是失去了所指的能指。小说是人类自欺欺人的虚构。小说的重心转向了语言,创作小说变成了小说的创作。昔日现代主义作家尽管反叛、质疑了传统小说(包括对传统小说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彻底的变革),但却并没有反叛、质疑小说本身。现代主义从反传统开始,最后自己也成为了传统的一部分,所以,它的反叛并不彻底。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传统,它自己决不再成为传统,因为一旦形成传统,它就不再是后现代主义的了。后现代主义对小说这一形式、小说的写作过程以及叙述本身进行了彻底地解构、颠覆和嘲弄性模仿,这导致了传统的“小说和叙述”被彻底解体。萨特将这种后现代小说命名为“反小说”,他在概括这种“反小说”的特征时指出:“反小说保留了小说的外表和轮廓;给我们介绍虚构的人物和讲述故事的是想象的活动。可是,我们大失所望:小说自己否定了自己,人们似乎在建树小说时,小说在我们眼中毁灭了;作者是在写一部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小说中之小说。……这些难以归类的怪异作品的出现,并不证明小说这种体载的缺陷,仅仅表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思索的时代,小说正在作自我反省。”[①b]如此看来,这种“反小说”与其仍然被称作小说,不如说是对“小说”的颠覆和破坏。
以上我们对西方近百年来小说形式和观念的发展和变化作了简要的概括。如果我以此来比照中国80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我们发现它们颇具后现代主义的颠覆主题与颠覆文体的特征。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在经历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之后,最后进入了小说创作本身的危机。他们不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先验的、客观的真理,也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价值标准,更没有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目标。生活中没有什么主题,或者说生活本身就是主题。写作的意义就在于写作本身,写作之外或作品之内没有意义。写作与其说是一种事业,不如说是一种游戏。小说担负不起,也没法担起认识世界、教育人民的历史重任。不仅小说的创作,而且小说的阅读和阐释,乃至小说的理论批评都是游戏,不过,这是高智商的精神游戏。
在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中,余华可算是对意义和文体解构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一些人誉为“中国新时期的鲁迅”。他对主题的颠覆首先表现在他对历史的解构。因为历史通常总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中“意义权威”的最高文本。中国是一个史官文化十分发达、历史精神十分强大的国家,这一点我曾专文作过论述。余华以此为突破口,开始了他对整个传统文化的解构和颠覆。他在小说《往事与刑罚》中这样对历史施以酷刑:
他是怎样对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进行车裂的,他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撕得像冬天的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他施予宫刑,他割下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的沉甸甸的睾丸,因此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没有点滴阳光,但是那天夜晚的月光却像杂草丛生一般。而一九六○年八月七日同样在劫难逃,他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钢锯,锯断了一九六○年八月七日的腰……[②b]历史及其崇高意义被一系列的酷刑肢解后,还原为一连串随意排列的能指符号,它的昔日的光辉消失殆尽。余华在消解了历史后,又开始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颠覆。他的《世事如烟》、《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现实一种》等小说均可说是这一类作品。在《世事如烟》中,90多岁的《算命先生”为了自己增寿而克儿子,并且他奸幼女为的是给自己采阴补阳;60多岁的职业哭丧婆为了怀孕而与自己的孙子同床;另一个人物为了自己获利而将六个女儿卖掉……如此等等,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在这里被无情颠覆。
余华在完成了他对传统主题进行颠覆后,又开始了他更深刻的颠覆活动——对文类的颠覆。《河边的错误》是对公案/侦探小说的颠覆。小说情节复杂曲折:一再发生在河边的离奇的谋杀案,警方经过多方侦查认定一位工程师是本案的嫌疑犯,读者对此也几乎深信不疑。但是小说最后揭示出:凶手原来是一个疯子,他的杀人毫无动机,他为了杀人而杀人,杀人是一种仪式;工程师因为多次目击谋杀,最终把想象当做了现实,他发狂自杀了。小说完全模仿公案/侦探小说的写法,但却抽去了这类小说最重要的杀人动机和因果关系,因此,小说成了抽象的叙述形式本身,不具备任何具体实在的意义。作者正是这样在模仿这种叙述程式之后再将其颠覆。
《古典爱情》是对才子佳人小说的颠覆。这里有进京赶考的士子柳生,有绣楼里伤春的小姐惠,有热情、机敏的丫头,有姹紫嫣红的后花园,有缘绳而人闺房的冒险,有一见钟情、一夜风情、剪发送别……并且,这里还有历史沧桑,杀人卖肉,人鬼不分,总之,才子佳人小说的一切文类特征这里似乎应有尽有。但这里却没有这类小说的核心,即忠、孝、爱情。小说徒有传统小说的程式和情节,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空壳,读者在这里得到的只是叙述形式的震惊和叙述内容的虚幻,传统小说模式由此被消解。
《鲜血梅花》是对武侠小说的颠覆。小说开篇写道,“一代宗师阮进武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已是十五年前的依稀往事。在阮进武之子阮海阔五岁的记忆里,天空飘满了血腥的树叶。”[①c]这里,武侠小说所有的悬念、武功、复仇等基本要素都已具备了。接着小说按照武侠小说的程式缓缓叙述:十五年后,阮妻拿出丈夫留下的梅花剑,嘱托儿子去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寻问杀父仇人,为父报仇,母亲随即自焚身亡。阮海阔于是开始了漫无目的的寻找。他遇上胭脂女,她托他向青云道长打听刘天;以后遇到黑针大侠,他也托他向青云道长打听李东。阮海阔遇到了白云潇,但他忘记了问自己的问题,他只记得胭脂女和黑针大侠托他打听青云道长。他终于碰到了青云道长,道长告诉他:刘天和李东都去华山参加十年一度的剑会了。青云道长只回答两个问题,阮海阔没有问出自己的杀父仇人。他往回走将刘天和李东的去向告诉了胭脂女和黑针大侠。三年后,他再次遇到白云潇时,他才知道他的杀父仇人就是刘天和李东,并且,他们三年前在去华山的路上已分别被胭脂女和黑针大侠杀死。阮海阔听后“感到内心一片混乱”,他那漫无目的的漫游行将结束,他不知道自己余下的生命将如何度过。在这篇小说里,有复仇却没有仇恨;有追踪却没有目的;有机会却总是放弃;复仇后却没有任何欣喜。这里只有武侠小说的程式和情节,却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无意义的程式和情节最终自然会走向对自身的彻底否定。
洪峰是一个善于制造距离的作家,他善于制造隐含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以及隐含读者之间的距离。通过对这四者之间不同的距离的自由运用,洪峰的小说的内部充满了紧张和矛盾,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反讽。这便彻底地消解了传统小说明晰统一的主题思想,并使小说出现了多种价值的交汇与动荡,进而形成小说内在价值多元化趋势。譬如在小说《极地之侧》中,叙述者“洪峰”与另两个人物章晖和小晶以及隐含的读者之间是有距离的:叙述者“洪峰”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互为矛盾的所见所闻所想,并且不揭示其中的任何意义;章晖不停地讲着死人的故事,他自己最终没有发疯却自杀了,但小晶证实他讲的故事大多是假的;而小晶却来历不明,他是“洪峰”在街上闲逛时凭直觉从一歹徒手中救出的受害少女。这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隐含的读者只有在完整地接受了这一切之后,才有可能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是,因为这里是多种声音同时独自发言,是多声部合唱,所以,“正确”的判断却是困难的,或者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或许可以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个莫名其妙正是它的全部意义所在。”
叶兆言的《关于厕所》已很难将它归入小说类了。“小说”第一部分,叙述美丽青工杨海龄在上海淮海路上大庭广众之下尿裤子,基本上是传统写法。接下来作者故意中断以上叙述,插入一段作家的“创作谈”:“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厕所的小说,当我开始打算成为一名小说家的时候,有一个叫高晓声的小说家,谆谆教导我说,要写小说,首先要从自己感受最深的问题着手。”在取消了叙事的连贯性后,小说干脆采用了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对古今中外关于尿溺的记载和议论旁征博引、对照分析。这里涉及了清代李渔的牢骚,《南华经》、《内经》、《悟真录》、《养生杂记》中的记载,毛泽东当年起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西方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的《文明与野蛮》,以及《域外万花筒》、《科技经验导报》、《百花洲》上的报告文学……随后由一则美国发明“女尿厕”的文章又过渡到十七年前杨海龄尿湿裤子。然后又插入叙述者下乡、考大学、文化大革命时父母扫厕所等以中断叙述,这以后又有《说文》、《释名》、《汉书》等对“厕”的解说,夹杂着《扬子晚报》上的长篇报道。总之,这篇“小说”力图打破一切文类的界限,使小说不再成为小说。这就不再是像余华所乐意做的那样,只对某一种小说模式进行颠覆,它实际上是对小说本身进行颠覆。
李晓的《相会在K市》与其说是在写作小说,不如说是对小说的写作。小说展示的是作者写作的过程,即作者写作的缘由、动机、遗憾以及他的采访、调查、思考、争论、想象和虚构。小说写作过程的结束也就是小说的完成。而小说的故事是什么?主人公刘东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他的死究竟是因为什么?这些在传统小说中至关重要的内容这里均语焉不详,甚至连小说的作者也不能确定。小说终于演变为一个过程,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过程中的愉阅,一种形式中的游戏。潘军的《流动的沙滩》“自然就不属于小说了”,它是“一本说不好的书”。“你可以把它看作更换电话号码的通知或者使用新型卫生巾的说明。”这里除了“读物”之外,不再有通常的文类上的区别。
王朔几乎是在颠覆主题的同时将文类也颠覆了,这便是他的“虚无主义嘲谑”。他不仅以嘲谑铲平一切,而且是一无所有的、无任何依凭的进行嘲谑,不仅如此,而且是没有目的、无所肯定地进行嘲谑。他不仅嘲谑他人,嘲谑客体,而且嘲谑自我,嘲谑自我分裂,进而还嘲谑文学本身。王朔曾非常刻薄地说,“19世纪产生的所有文学作品对今天的作家毫无补益,在技术上都是过时的”[①d]。他对于19世纪的伟大的文学大师,譬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从来就不恭维,对于他们的大部头的作品没有一部看完过。
总之,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从颠覆主题走向颠覆文体,走完了他们的探索和实验。他们从颠覆传统的主题和意义,到颠覆一切的主题和意义;从颠覆传统的小说观念,到颠覆小说本身;后现代主义小说在消解一切的同时,也将自己消解了。这样,后现代主义小说非但没有拯救当代小说的危机,反而加深了这种危机,这使得读者不仅要问,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之后,小说还有可能、有必要继续存在吗?
注释:
①a 陈众议:《拉美作家谈“小说危机”》,《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②a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①b 萨特:《〈陌生人肖像〉序》,《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页。
②b 余华《往事与刑罚》,《橡皮爱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①c 《鲜血梅花》,《橡皮爱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①d 王朔:《欣赏与摒斥》,《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