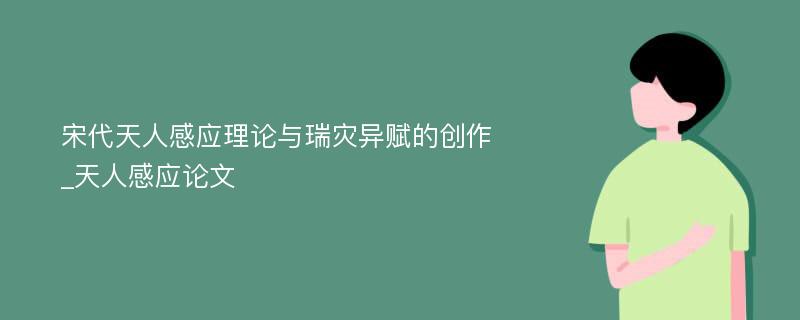
宋代天人感应学说与祥瑞灾异赋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祥瑞论文,宋代论文,天人论文,感应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4.04.009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4)04-0055-06 祥瑞灾异赋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学说基础上,以自然界异常现象为描写对象的赋。宋代祥瑞灾异赋比前人更加深化了学理内涵,现象反映和问题提出也更加尖锐深沉。 一、天人感应学说在宋代的波折与发展 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天人感应观念由来已久,“天人感应”思维模式甚至成为汉代儒学的显著特色①。宋以来,人们对这门古老的学问既怀疑又倚重,随着思想解放、政治变革而几经波折,天人之学的发达也推动该学说继续丰富发展。 (一)天人感应学说在宋代经受怀疑与挑战 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始终动摇感应学说的基础。宋代对日月食的成因,解释已十分准确;对于五纬退留现象,甚至认识到了轨道差异②,与古星占大相径庭。在感应学说里被视为首灾的日、月食甚至一度被剔出,“徽庙朝曾下诏书,言此定数,不足为灾异,古人皆不晓历之故”③。北宋中叶,《新唐书》打破了《汉书》以来延续近千年的传统,只记灾异而不著事应,要求对未知事物心存敬畏而不胡乱联系。对于雷火把室内坚钢熔化成汁却无损于它物的怪现象,沈括说:“欲以区区世智情识,穷测至理,不其难哉!”④司马光又说:“世人之怪所希见,由明者视之,天下无可怪之事。”⑤ 道学思想的冲击也是重要因素。“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也。”⑥谶纬学说成为被冲击的对象,遭到欧阳修、叶适、魏了翁等的强烈反对。鉴于汉易与谶纬的密切关系,宋代易学也竭力与之划清界限。宋人还要求理性看待历史现象,欧阳修首起指责“幽赞生蓍”、“河出图、洛出书”等说为怪妄,薛季宣承之,大力反对五德始终说。王观国例举了“五运”说既无法解释国家分裂时的历史实际、历朝也没有一定之论,认为“彼图录谶纬之书,皆虚怪不可必信之语也”⑦。邵博认为,刘邦能当皇帝,“其取之无一不义,虽汤、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称‘断蛇著符,协于火德’,谬矣”⑧。五行难知难验,而以此起家的五运、谶纬学说却林林总总,宋儒甚至责怪起子思和孟子多事:“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⑨李纲就明确反对五行推配。 宋代政治变革对天人感应观念起到明显抑制作用。一是对变法阻力的突破。神宗初发生了日、月食及全国性地震,吕公著、曾公亮、富弼、司马光借灾变反对变法,王安石反击。熙宁八年彗星出,邓绾、王安礼、吕公著、张方平等再谈天变,王安石例举晋武帝在位十八年与《乙巳占》不合的典故,指出:“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不无偶合。”⑩他作《洪范传》,抛开天人相感的直接作用,又在科考中废除了书写怪异的《春秋》。由于王学在北宋后期的官学地位,使得感应学说处境不利。二是因物极必反。徽宗对祥瑞的痴迷动摇国本,造成了重大的社会负担和逆反心理。《齐东野语》载,政和年间上奏灵芝动辄二三万本,山石变的玛瑙以千百计,山溪生金数百斤,“皆以匣进京师”,“祥瑞盖无虚月”(11)。时人非议。对所谓符瑞等,南宋人始终保持了清醒的戒备意识。 (二)“为人事”目的对天人感应学说的强化 “神道设教”是天人感应学说存在的基本理由。无论是真宗虚张声势的“降天书”和“封禅”闹剧,还是仁宗“欲自以身为牺牲”(12)的求雨过程,都力图发挥它在凝聚信心、巩固政权中的强大作用。南宋草创期尤为明显,皇帝以之安抚民心,主战派以之激扬士气。张浚、胡铨,其来往书信“无一语不相勉以天人之学,无一念不相忧以国家之虑也”(13)。许多儒者坚决反对取缔对灾变的神学解释,“使君天下者,视天灾时变,不务德以禳之,但委其数而已”(14)。石介极力反对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经书星陨、日蚀、水灾、螟伤稼,皆偶然也?”(15)熙宁初,有人对皇帝讲灾异与人事无关,宰相富弼深不以为然:“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16)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杨时、陈闲乐、陈瓘至魏了翁等都是王安石的尖锐批评者,杨万里举十二大罪状,首条就是“天变不足畏”(17)。陆九渊虽然说了好话,仍为其治国不取“洪范”九畴抱憾。程朱嫡系王柏在《喜雨赋》中就借天人逆感对王安石进行了嘲弄。而南宋末君臣对天变的戒惧更是达到了恐慌。 据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的研究,宋代是我国气候变化五个重要时期之一,气候多变,灾异频发。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适当放开舆论,使借灾变言事成为政局变革的先兆。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底发生大规模地震,死伤惨重,此后连年灾异,又发生宋夏战争。庆历二年(1042),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以灾变为题求直言,“此乃自有殿试以来,数百年间最美之事”(18),受到了社会盛赞,不但成为庆历新政的开始,对灾异赋创作也有解禁意义。在借天人感应参议政事上,即使强硬如王安石,也不敢公然对抗(19)。淳熙八年(1181)大旱,这年科举,刘大誉就凭一篇巧用天人感应的《闵雨有志乎民赋》荣登榜首,并致使赵温叔罢相。 (三)天人之学的发达对感应学说的推动 谶纬学说其实是天人之学的一个分支,但是没给出系统有力的解释。宋人对天人之学的高度热情,为继承和发展感应学说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 很早以前,人们就以阴阳解释天地变化的原因,使得“论道经邦,燮理阴阳”(20)成为政治家的主要职责。宋代延续这个传统。首先,加强了阴阳与人事对接。刘敞论日食:“明其阴侵阳,柔乘刚,臣蔽君,妻陵夫,逆德之渐,不可长也。”(21)欧阳修说:“盖阴为小人与妇人,又为大兵与蛮夷。”(22)杨万里应用了他对“乾刚”的强调,指责淳熙十二年地震为小人在侧。朱熹更是从先天卦气上查找依据:“阳生于北,长于东,而盛于南;阴始于南,中于西,而终于北。”(23)故阳为生育长养,其类刚明公义,君子之道;而阴常为夷伤惨杀,其类柔暗私利,小人之道云云。薛季宣把易、历结合,认为同是圣人“易教”内容,“法象于阴阳而和顺于吉凶,通理于人而遂物”(24),从而较宏观地为人事吉凶提供依据。其次,提出“致中和”的变燮理念。这与“燮理阴阳”乍看没甚区别,其实标志了宋人新的执政理念。田锡论端拱二年旱灾原因:“此实阴阳失和,调燮倒置。上侵下之职,而烛理未尽;下知上之失,而规过未能。”(25)司马光说:“圣人所以制世御俗,犹天地之有阴阳,损之益之,不失中和。”(26)华镇称:“故圣人善政事以和人物,变阴阳以弭灾变。”(27)显然并非一味地崇阳逐阴,不是把作为阴戒的“小人”全断送了,而是以“广生”的姿态大搞政治平衡。在宋代频繁党争和社会矛盾前,这种观念显然有积极意义。欧阳修一反《夬》五阳决一阴的说法,提出“去小人者不可尽”(28),并从物极必反发出警告。陆九渊则意味深长地说:“知天灾有可销去之理,则无疑于天人之际,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29)再次,加强对天地间现象的阴阳分析。邵雍用阴阳刚柔解释复杂的天气现象,且同一气象在不同的时间场地呈现差异,受制于五行的偏颇。张载以阴阳凝散解释气象,如“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阴为阳得,则飘扬为云而升……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30)等。从卦象解气象,蔡渊推究地甚密,如坎之阴为阳所得,则升而为云;以阴包阳为雹为坎,离交坎为雪,坎交离为霜等。既为认识天象、气候提供了建设性理论,也深化了感应学说的合理必要性。 《尚书·洪范》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来源,古人以为治国之要。沈括、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提出过重要见解,陆九渊极其重视,说:“《春秋》之书灾异,非明乎《易》之太极、《书》之《洪范》者,孰足以知夫子之心哉?”(31)王炎称《洪范》为“圣人经世之大法”,以之统领易学以及《素问》研究,把“五福六极”与“五运六气”进一步结合,使得气候、星象变化与政治修为联系更加紧密。对《麟德历》《大衍历》等对岁星运转的推算不合前验,宋人批判前人仅凭了单调的科学知识,而不知天人感应之理。更神奇的是北宋刘羲叟,天文历学专家兼占卜高手,曾作《春秋》《洪范》休咎十数篇,驳斥古人牵强附会处,所占日月星辰无不验。欧阳修称他“学通天人祸福之际”(32)。这些都使在阴阳五行支配下的天人感应观念在宋代得到了理论充实,愈加复杂化了。 (四)宋代天人感应学说的基本形态 1.天监说。北宋初期有突出地位,基本特征是重视天文示象,认为天降赏罚,一切人事活动的好坏都会反映到自然意志里。早在《无妄》象辞就有:“天下雷行,物与无妄。”董仲舒说:“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33)持此说的人笃信上天有尊严威德,善赏罪刑,昭昭著著,无分毫侥幸可言。宋初田锡认为君主“位至尊而心至谨”,则天降其祜;“身妄动,令妄施,则天降其咎。”(34)星象说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真宗大臣宋祁称“天所以垂戒者寓乎象”(35),可为代表。南宋杨万里更以星象教导皇子,“天监不远,岂诬我哉!”(36) 2.运气说。这是种寻找外在依据却含有点宿命意味的天人理论。较新颖的是石介的说法,天地气有正邪,正气生时为真运,真运时君明臣贤民良,阴阳顺序,风雨时降,昆虫草木没有变怪。所以要使至正之气充塞天地,邪气无隙干之,也就是他“夫天生时,圣人乘时,君子治时”(37)的根据。更多人仍坚持了传统的五运说。如王观国通过五行之性相违而不相用解释灾异发生;曾巩认为,“雨、阳、燠、寒、风”时至则和,过则为沴,代表着五行的克当,体现着人事休咎,所以“为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己之得失于天也”(38)。当然也包括借鉴《素问》的“五运六气”说。 3.德行说。主张气象与政治之象相侔,人君道德才是感召天变的根本,代表者欧阳修。他否定三统五运说,指出天下有至公大义,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实际上变相提出了有德者才有位的观点。《新唐书》肯定了五行是万物精气,王者取用得当则物阜民安,否则物夭民愁、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起为天地灾异,在感应的面目下寓含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刘敞也说:“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阴阳不和也;所以致阴阳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也”(39),“人和则天地之和致矣”(40)。苏轼反对“五行六沴”,一反阴盛的普遍看法,别出心裁地从阳气泛滥之象解释淫雨,进而对仁宗朝散缓的政治风气提出批评,是对德行说的灵活运用。 4.召感说。召感是天人感应学说的本质,不过宋人给出了更清晰的因果律内容。石介说:“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应善;人不能行大中至道,则是为恶,恶则降之祸。”(41)比董仲舒“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42)多出了许多学理内容。邵雍把天地看作阴阳刚柔运动的大系统,之间连通呼应,所以环境的顺逆也在于人心向背,人心或感来顺气成美,或来逆气成恶。北宋后期,华镇写过一篇《浑天论》,认为天气不和,人物感之则饥馑夭阏;人气不和,阴阳感之则日月错行、星辰离次。南宋周密考究到,雷电为阳激而欲破阴而出,人之恶气感召了天之怒气,以致雷震之灾等。神宗时,吕大均已经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较内在的角度关注天人感应,认为人心不安则易变故,人心一于道心则自然不危。心学出现后,个体的力量备受关注,陆九渊强调每个人都有内在的感召能力。他发扬《洪范》,认为人心与天地同受理于五行,故相感通,其结果不可限量:“是极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43)为天人感应说辟出新径。为救时弼世,南宋末学者们将理、心自觉结合为一体,感应之谈愈加苛刻。同是告诫皇帝,魏了翁说:“天地是我去做,五行五气都在我一念节宣之。”(44)大学士李曾伯说:“一念敬忽,休咎响应”。(45)方大琮则劝告:“若一念之歉横于胸中而不化,则一气之戾郁于两间而不消。诚能宣明洞达此歉不留,将见精诚感召此戾自弭。”(46)这种一触即发,达到了类似心电感应的程度,真切反映出南宋朝廷里的危机感。 5.民意说。民意即天,这种声音每逢在历史的转折期响起,特别具有反思意义。李纲《证兆志序》称:“天之所为,即人之所为;人之所欲,即天之所欲。”(47)换句话说,民思安则国家兴,民思乱则国家亡,北宋实亡在失去民心。杨万里在《旱暵应诏上疏》里发挥道,天地之气通畅则为丰年、为太平,若有隔塞则致水旱之灾。“戾气”使天地阴阳之气互不相接,“然则孰为戾气?斯民叹息之声,此至微也,而足以闻于皇天;斯民愁恨之念,此至隐也,而足以达于上帝”(48)。它贯通了三才学说,充分地表达了民本思想。南宋末,文天祥上《御试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为喜怒者也。”(49)以天人一体,说明天人之交不容穟,也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政治关系的紧张被动。 总之,天人感应学说在宋代既怀疑又发展,学理深化,思想多样,对祥瑞灾异赋创作带来了直接影响。 二、天人感应学说影响下的宋代祥瑞灾异赋 天人感应为赋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祥瑞灾异赋创作源远流长。最早可见的是汉代贾谊《旱云赋》,以大旱阴阳不相得,批评“政治失中而违节”。东汉初杜笃的《众瑞赋》已不可窥其全貌,三国魏刘邵的《嘉瑞赋》可能与之比较接近,陈列了盛世出现、代表祥瑞的物种。杨修、钟会的同名《孔雀赋》、晋顾恺之《凤赋》等均借外国进贡的吉祥物歌颂时代政治。魏晋时期,少量以苦雨、苦暑为题材的赋开始从抒写羁旅之苦转向天人感应,如魏国缪袭的《喜霁赋》写君王罪己止雨,晋傅玄的同名赋、傅咸《喜雨赋》写祷雨得应等。南朝时期祥瑞灾异赋的范围有所扩展,出现了周渭《齐七政赋》这样的星象赋,不过气象赋中仍十分有限,如傅亮《喜雨赋》等,数量很少。唐代因为制科的需要,以天人感应为题材的赋骤然增多,蔚为大观。尤其是祥瑞赋极大丰富,其中又以各种星象赋为盛。次如以五色卿云、风不鸣条、紫气、晴虹等为题的各种气象赋,还有珍禽异兽、瑞麦神鼎等各种物类赋。只有个别赋敢寄寓个人观点。如沈瑱《贺雨赋》给出处理灾变的“应急机制”,包括移寝、减膳、恤狱缓刑、惩治奸人等,也是老生常谈。王邵《商霖赋》以雨拯救生灵、沾濡裔夏的天泽与治政者休兵育民相对应,表达出强烈的和平愿望。而唐代灾异赋十分罕见,能见到的有李观《苦雨赋》写水灾,无名氏《骄阳赋》写旱灾。 纵观宋以前赋史,天人感应赋的缺点:一是敷陈经学,远离时代;二是缺少独立思考,对自然界异常现象没有学理上的发挥;三是缺乏大胆犀利的理论建设与批判,灾异现象入赋比较少见。这些正是宋赋所要弥补的。 宋代祥瑞灾异赋现存31篇左右,规模约为唐代1/4。祥瑞赋主要集中在真宗到神宗时期,以仁宗时为最多。作者有著名文臣王禹偁、宋祁、夏竦,乃至以正直著称的大臣宋庠、文彦博等,内容从天文星象、气象、宝鼎、灵芝、瑞麦、瑞竹到贡入的珍禽异兽,种种不一。而出于对北宋末政治的反省,南宋祥瑞赋较少,只出现在孝宗登基初年。相比之下,宋代灾异赋却无代无之,地震、气候异常、风灾、旱涝灾害等在赋中常有反映。在宋代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祥瑞灾异赋创作面目一新,极具挑战性和时代特点。 (一)突出的怀疑精神,理性思考自然界中异常现象 著名经史学家刘敞的《罪岁赋》是篇怀疑星象之文。序说,岁星所在分野应五谷昌盛,且不可对其发动战争,否必受殃。但自去年岁在翼轸(对应楚地)后,不但相继洪灾旱灾,而且又兵祸。黔中、长沙等地的少数民族叛乱,不但未损及他们自身利益,反而宋朝的将士民众遭受杀掠,死者数千。作者不禁责问天道之不仁而岁星无诚验。《奇羊赋》里不断发问:若说四时节气平分、五纬周转,如何能出现双头之羊?若说离卦为火明炎上,为何羊的视力那样差?《说卦传》里兑为羊,兑卦象征了愉悦,若说羊代表了吉利,为何这羊看起来那样令人反感?若说天地间规则已定,但是在伟大的规则下怎能出现这样不合规则的产物?这两篇赋充分体现了刘敞的怀疑精神。类似的还有苏轼的《飓风赋》。 (二)更加重视警示意义,突出了“为人事”的目的 真宗、仁宗时代,夏竦《封中起白云赋》写封禅的山上白云聚集,文彦博《玉鸡赋》写白气如虹等,歌颂时大都有所劝诫。宋祁《陈州瑞麦赋》提醒君王“知稼穑之艰难”,文彦博《汾阴出宝鼎赋》机警地表达出“鼎取新而革去故”的强国愿望。刘敞《化成殿瑞芝赋》大胆说出“见瑞而怠者,虽与灾变无以异矣”的惊人之语。无论司马光作《交趾献奇兽赋》还是薛季宣《灵芝赋》,都摆出了一副“虽无此芝(瑞),何损于治”的态度,劝勉君王努力政事。 《宋史·五行志》载,宋初多次沙尘暴。就天禧四年(1020)而言,暴风两起西北,出现“昼晦数刻”“折木、吹沙、黄尘蔽天”等,因此诛杀了内侍周怀政等人。梅尧臣《风异赋》记叙了宋仁宗宝元三年(1040)的一次沙尘暴。它“亘天接地”(50),威力极大,据说经历地域还非常广大。序说:“岂常哉?若应人事之变,则余不知。”赋尾又说:“言变咎,则非愚者之能议。”实是深疑朝政将有变故。隆重记叙,本次沙尘暴却不见载于史册,突出说明作者对政治人事的关切。 钱惟演《春雪赋》作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指出“春阳已中”而“阴冷而忽兴”是阴阳违和的表现,对农事“顾沃若之待收,罹此暴殄”、国家命运“始蒙蔽于阳乌,遂潜藏于天幕”那些隐藏的祸患表示深深的忧虑。貌似关心国家、怜悯农人,然而,先前他挤兑寇准及丁谓,仁宗即位,他本应加官晋爵,宰相冯拯恶其为人,将他逐出朝堂,即日远赴河阳任职。钱大失所望,本赋借春雪指摘朝臣,来排解自己仕宦道路大打折扣的失落情绪。 钱惟演可以这样写,徐仲谋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类说》载,皇祐中,徐仲谋献《秋霖赋》指摘阴阳失序,忤怒宰相贾文元、陈恭公,贬绍武酒税。这是一个触犯忌讳的典型例子。宋赋写灾异还都比较谨慎,如不写苦雨而写喜晴,不写干旱而写喜雨等。张耒《喜晴赋》就对朝政进行了深刻的嘲讽。而南宋王柏《喜雨赋》对熙宁以来的政治讽刺堪称系统,其赋借祷雨成功从地方骂到中央,有强大的喜剧感和尖刻的讥刺力。 薛季宣《春霖赋》呈现了春天的一副凄惨景象,深刻反映出北宋的覆灭不仅是天时,更是人祸,表达了作者无奈、愤怒、嘲讽和哀伤的复杂心绪。 (三)强烈的道德精神,构建修平学说 一些赋通过气象变动来要求当政者提高责任意识,或贡献对国策制定的意见、建议。云在感应学说中有重要地位。《周礼》载保章氏观云物知水旱凶吉;《汉书·天文志》称庆云“喜气也”(51);《新唐书·百官志》把它升为仅次于麟、凤、龟、龙等皇家专享的“大瑞”,是天下大治、贤人在世的体现。应孟明《夏云赋》以五色云喻贤人,提出了修身的理念。赋末风姨、月姐戏问为何不与之绸缪,则道出了作者赋夏云的初衷——不酬风月而酬云,无富贵之意但求解旱之功,是所以心忧天下,体现了一个儒者的高尚情怀。 范纯仁,仲淹之子,一代名臣。《喜雪赋》写在了穷偏山县,却荡漾着春光和气。其中提到做官本分:要有职业操守,才对得起俸禄;就算所辖土瘠而民穷,也不因官小而不作为;就算地方治理得不错,也不要沾沾自喜,而应心怀天下,忧乐与共:“嗟一人之余庆兮,赉亿兆以何丰!”史载,他因仗义执言,两遭连贬,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当地治理得风调雨顺,民望极高。这篇赋便是他虽遭不公正待遇,始终不弃不馁、不为名利、勤勉如初、爱民如初的动人写照。王炎的《喜雨赋》则对官吏切实的责任感和忧乐精神进行褒扬呼唤。 宋代试赋常以重大时事为题,考察对时局的观察把握能力。“五星同色”与“岁星所在国有福”就是两个“国考”级命题。《史记·天官书》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52)并载汉高祖建邦时,五星聚于东井。据《宋史·天文志》,宋代三百年,五纬聚会的年头有七,“庆历三年十一月壬辰,五星皆见东方”(53),时为1043年底。还真是凑巧,自1041年西夏战争,北宋连战惨败,不得不继续与辽国修好,且于1044年与西夏签下和约,以后近百年太平无事。刘攽《五星同色赋》反映了北宋停战的意愿。且五星相聚以黄色为吉,原因是从填星之所居,赋中特别强调本次聚于填星之舍,来夸赞国君英明,体现对和议政策的赞同。楼钥,南宋名臣。他“隆兴元年试南宫,有司伟其词艺……考官胡铨称之曰:‘此翰林才也。’”(54)《岁星所在国有福赋》就是他应试之赋。岁星兆国运昌隆,在五行为木,五常为仁,此年分野恰在南宋,且无盈缩。孝宗太子时便以仁孝主战闻名,与秦桧不和,大得民心。此时南宋建国已三十余年,国力恢复,新君登基,锐气风发,国民翘首,欣然之情可知。赋中充满对君明臣贤的期待,有着南宋人少见的高调自信。 陈造《听雨赋》是他任地方官期间忧旱而辛苦祷雨的记述。除了说明官吏的安否系于民之安否,一场解旱大雨,使“憔戚叹咤者,生意之顿回;奔骛跼蹐者,舞踊而经营。洗襁子之昔忧,歘春台之共登”,实在指出了四民生计以农为重心,农业不兴,则士、工、商百业俱废,整个社会阶层都会起动荡。 (四)深掘学理,表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欧阳修《应天以实不以文赋》把灾异都归因为阴盛,对《洪范》以君王德行不足导致五行乖错的灾异观念悄悄地作了改变。此赋上,受到仁宗褒奖。王炎《喜雨赋》为淳熙三年(1176)的大旱祷雨成功而作,融会了作者所学。赋中说道,初夏“值亢阳之为沴”,郡守“谒梵王之莲宫,羞苹蘩之洁清”,以助阴的方式祈雨。在感动神灵的表象之下,其实满含细致的气象观察,潜藏了“五运六气”说的诸多背景:起初风弱且霾、云郁不兴以及太阳刚刚向北回归就那样明亮炎热,是木气不足的表现;后来石柱基座潮湿、鼓面软潮声哑,表现了厥阴风木虽郁但没有勃发为暴雷,而是回复舒展,于是风凉云兴,终至大雨。熙宁初,孔文仲引日食反对变法,被黜,哲宗初再上书痛诋,指出导致日食的五件事。《三阶平则风雨时赋》里继续发扬“天监说”的威力,称:“君道修于下,则瑞为之证;人事失于此,则变从而作”,体现了他硬朗的个性。李曾伯《避暑赋》则是其“一念敬忽,休咎响应”学说的放大,进一步提出,要改变世风,必须息心清净,不煽性与情。 以上可见,在政治、学术活跃,思想开阔的前提下,宋人对异常现象和天人感应学说的思考都更加理性深入。在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和理论带动下,宋代祥瑞灾异赋境界阔大、学理精微、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篇篇生命蓬勃,饱含张力。它们密切联系时代,敢于表达个人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学术。不但对自然现象的发生原理进行过深入探究,对社会政治的批评和对社会秩序的建构追求也发人深省,取得了杰出的思想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