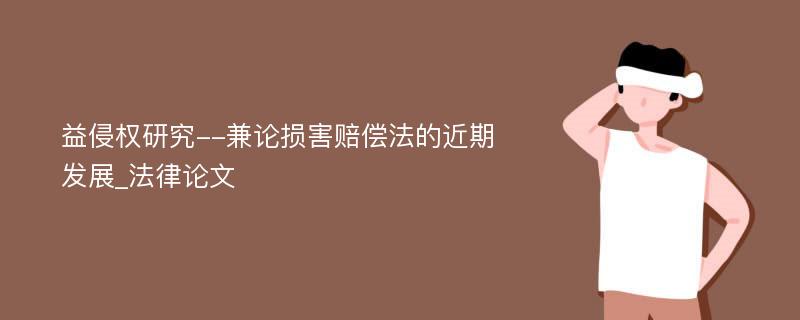
受益型侵权行为研究——兼论损害赔偿法的晚近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赔偿法论文,侵权行为论文,晚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社会中侵权行为种类众多,形态各异,不胜枚举。从罗马法时期的私犯与准私犯,到日耳曼法时期的个人侵权与团体侵权,及至晚近之积极侵权与消极侵权,皆贯彻行为主义之进路,惟自侵权行为性质角度观察,其规范目的均着眼于行为过程之客观评价,对行为后果一般在所不问。上述侵权行为形态的分类,固然揭示了侵权行为的存在意义,但其从行为到行为的理论归纳模式,显示了行为效果意识的缺失,似有违侵权法从行为到责任的应然逻辑结构之嫌。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损害及损害赔偿制度关注度的提升,特别是国外学术界对损害赔偿与返还请求权(restitution)研究热潮的持续,一种以责任主义为价值导向的侵权行为形态——笔者称之为受益型侵权行为(gain-based tort)——逐渐浮出水面。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受益型侵权行为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汇,有关研究比较薄弱。但对于国外学术界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学术界来说,围绕受益型侵权行为损害赔偿(gain-based damages)这一主题,早已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① 这昭示着侵权法乃至债法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具体到侵权法领域,受益型侵权行为可谓是侵权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连通了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两个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并与债法的其他分支特别是不当得利法产生了众多交结点。对受益型侵权行为本质的具体澄清,寻求恰当的规范模式与解释路径,进而阐明损害赔偿法的现代发展及其对我国侵权法立法的影响,将是笔者努力完成的任务。
二、受益型侵权行为的基础理论解析
所谓受益型侵权行为,是与损害型侵权行为(loss-based tort)相对应的侵权行为形态,两者均系理论概括之产物。简言之,受益型侵权行为是指产生损害后果且行为人从中获利的侵权行为;损害型侵权行为则是指只产生损害后果且行为人未从中获利的侵权行为。以行为人是否受益来区分侵权行为之要义,旨在对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复杂关系的梳理与提炼,以构筑行为联结责任的学术通道。与传统侵权行为形态分类不同,受益一损害型侵权行为分类的关注点不在于侵权行为本身,而是掩藏于侵权行为精致外壳下的损害结果。具体到受益型侵权行为之结构,侵权行为为因,受害人受损与行为人受益为果。传统理论对何种侵权行为造成行为人受益,在所不问;学术界的争议一般主要集中在行为人受益与受害人受损的关系上。行为人受益究竟是受害人受损的判断标准还是受害人受损的计算标准呢?对此在学术界形成了两种观点:“损害判断说”和“计算标准说”。“损害判断说”是指行为人受益这一事实是侵权损害存在的客观标准,原告无须单独举证证明损害的发生,换言之,行为人受益本身就意味着侵权损害,“受益”与“损害”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计算标准说”则是指仅仅根据行为人受益这一事实不足以判断侵权损害的发生,原告仍须就侵权损害的存在单独举证,亦即行为人所受之利益只是在侵权损害无法直接依据原告的实际损失进行确定的情况下的一种替代计算方式。“计算标准说”被不少国家的立法所采用,如《荷兰民法典》第6篇“债法总则”第104条、《德国著作权法》第97条第1款、《希腊著作权法》第65条第3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都采用了以行为人因侵权行为所获之收入或利润作为侵权损害计算标准的方式,此学说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而“损害判断说”看起来则要激进许多,行为人就其因侵权行为之获利承担的侵权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侵入了传统不当得利法的“获利返还责任”领域,以至于很难对受益型侵权与不当得利做出泾渭分明的界定。事实上,不只是侵权法开始渗透到不当得利法领域,不当得利法也逐步扩展到了侵权法的原有领地。例如,《日本民法典》第704条规定,恶意受益人应于其所受利益上附加利息返还之,如尚有损害时,亦负其赔偿之责。日本学者圆古峻指出:“第704条规定了恶意不当得利者的利息返还义务和损害赔偿义务,传统通说认为这已经超越了不当得利的返还而课以其侵权行为责任了”。② 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182条也规定了“附加利息,一并偿还;如有损害,并应赔偿”。有学者担心,鉴于不当得利法非以受益人之行为为评价对象的特质,在以利益回复为目的的不当得利法内部隐藏着无过失归责之损害赔偿,如果突破现行法律制度既有的衡平,将混淆不当得利法与损害赔偿法各自之目标功能以及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利益衡平机制。③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过度禁锢于民法体系化和概念化思维之中,往往不利于法律的成长。④ 私法是一个整体,其法律体系和所有的基本范畴归根结底都是相互交融的。私法的任何分支都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自我欣赏的法律部门,相反,在现代私法体系下,“每一个制度都是另一个制度的要素”,⑤ 我们只有查明和掌握了私法制度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相互交融,才能认识到私法的真实状态。要想准确理解受益型侵权行为及其对侵权责任体系的影响,仅从侵权法的视角进行论述恐怕是不够的。要想廓清受益型侵权行为的理论边界,我们就必须检视整个债法体系,我们的眼光必须不断游弋于侵权法与不当得利法之间。
传统民法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的救济方式通常是责令行为人支付给受害人一定数额的损害赔偿金,而损害赔偿金的计算依据,一律是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⑥ 至于行为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由于并非侵权法的关注点,因而一般无法直接追偿。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受害人转而借助不当得利法的救济渠道,也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如大陆法中的请求权竞合禁止和英美法中的诉因选择制度等。难怪有学者慨叹:“‘任何人不得从其不法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具有充分的伦理依据。但为什么民法对其回应却是如此之少呢?”⑦ 面对这种理论上的困惑,英美法晚近之学说、判例做出了积极回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对受益型侵权采取赋予受害人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方式的做法,其制度寓意在于将损害赔偿建立在行为人的受益而非受害人的损失上。诺斯(Nourse)勋爵评论道:“对英国侵权法特别是所谓的财产侵权法而言,有意识地将损害救济建立在被告的不当得利而非原告损失的基础之上,也许才是正确的方向”。⑧ 尼科尔斯(Nicholls)勋爵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确定损害赔偿时,法律并不痴迷地固守可计算性财产损失的赔偿观念。当情况需要时,损害赔偿可以依据不法行为人所获之利益计算而得”。⑨ 英国法律委员会在其新近发布的关于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的报告中也确认了这种救济方式。⑩ 尽管基于行为人获利的损害赔偿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但有关法律术语和规则定位之争却从未停止。对于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的称谓,英美法学界素有“restitution”与“disgorgement”的分歧。传统主流观点主张使用“restitution”一词,强调“restitution”是独立于传统侵权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后来英国学者戈夫(Goff)和琼斯(Jones)将其提高到独立的请求权基础的高度,并将其适用范围拓展到各种受益型侵权行为。(11) 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restitution”仅适用于名义上的侵权,如强占、侵入等,但不适用于过失侵权;(12) 其他针对受益型侵权的返还则应使用“disgorgement”一词。有学者更是强烈呼吁应以“disgorgement”的表述来代替“restitution”,并支持对“disgorgement”的排他性使用。(13) 埃德尔曼(Edelman)尝试对两者进行了澄清。他认为,“restitutionary damages”与“disgorgement damages”是基于受益型侵权行为的两种财产救济方式,前者主要针对不法行为导致的原告财产向被告的不当转移,后者则旨在剥除被告因不法行为而获得的利益,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转移财产的客观方式和被告财产的不当增加方式之不同。(14) 申言之,“restitution”所返还的利益源于原告的损失,在法律渊源上隶属于普通法,遵循损害赔偿的填补原则;“disgorgement”所返还的利益则源自于侵权行为本身,原告甚至没有受到传统侵权法上所谓的损害,其被视为一种衡平法上的救济方式,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尽管“restitutionary”与“disgorgement damages”内在基本原理迥异,但总体上可以统一于损害赔偿(damages)这一概念之下,服务于剥除行为人因侵权行为导致的不当增加之利益的共同目标。不管上述关于返还请求权概念和功能的争议是否有最终的结论,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将请求行为人返还侵权所得视作一种救济方式的做法已不为传统不当得利法所独有,它逐渐成为侵权法救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并且在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侵权法的传统观念。
在对受益型侵权行为的侵权法保护和不当得利法保护作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对“受益”这一关键术语作必要的阐释。受益型侵权行为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形态,“受益”这一前缀语无疑是最重要的节点。而侵权法与不当得利法之所以出现交融,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受益”这一事实。按照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的构造,行为人之受益不仅是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而且还决定着返还请求权所要求的损害赔偿数额,其制度功能毋庸置疑。所谓“受益”,应限于财产利益,无论此种财产利益是以积极受益抑或消极受益的形式出现均可。而行为人因侵权而产生的单纯精神满足、心情愉悦等非财产利益,则不在此列;否则,受益型侵权行为的适用范围将被扩大到难以控制的地步,从而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理论价值。对“受益”理论的释义,至少要完成以下两项工作:(1)受益事实之判断,亦即受益与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探查。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发生于侵害行为之后的行为人受益均可确认两者之间存在其因果关系,依赖于侵权行为的受益与行为人独立的受益必须被严格区分开来。有学者富有智识地提出,只要受益是“行为人的技巧、努力、财产和资源以及投入的资金与本不属于其财产应承担的风险”(15) 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这些受益就应当被法律所许可。(16) 申言之,只有那些在侵权行为直接作用下产生的行为人获利才能被视作“受益”。(2)受益数额之确定。王泽鉴先生认为不当得利中之获益“系指因某项事由(给付或非给付)而受的个别具体利益而言,非以受益人整个财产作为判断标准”。(17) 此观点虽针对不当得利而言,但对受益型侵权行为亦有参考价值。该观点贴切地诠释了受益型侵权行为的本质,便于区分依赖于侵权行为的获益与行为人独立的获益,殊为可取。如果参酌普通法上“一般损害赔偿”和“具体损害赔偿”的区分思路,将侵权行为人的受益划分为“一般受益”和“具体受益”,那么受益型侵权行为所指的“受益”毫无疑问将属于“具体受益”,行为人总体财产的增加这一事实不得作为行为人侵权受益的初步证据,原告须对行为人的“具体受益”进行举证。
三、比较法视野下受益型侵权行为的法律规范路径选择
按照传统侵权法学者的研究思路,要实现对受益型侵权行为的准确理解,可以围绕归责原则、因果关系、违法性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展开论述,以明晰受益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及法律责任体系。这一解释思路将学术视角集中于独立的侵权法,可称为内部性解释。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仅在侵权法体系内讨论受益型侵权行为就能揭示出受益型侵权行为的私法全貌,那么这一断言无疑过于轻率,其论证也将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从本质上看,受益型侵权行为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其行为形态在事实层面上与侵害权益型不当得利并无不同,差别仅在于两者在规范层面归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在不同的私法体系中,受益型侵权行为在法律规范路径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一些特定的受益型侵权行为在某些国家专属于侵权法的规范对象,但到了另一些国家则成了不当得利法规范的客体,有些国家甚至确立了受益型侵权行为的侵权法规范与不当得利法规范竞合的模式。规范路径的不同,反映了根植于私法制度背后的立法理念与法律精神的不同,特别是各国侵权法基本观念(如损害概念、损害赔偿观念)的差异。由此可见,要想全面阐明受益型侵权行为制度,仅仅依靠内部性阐释是不够的,还必须转向对侵权法和不当得利法的比较分析——又可以称之为外部性解释——才能达成目的。
在对各国债法体系及其司法实践进行比较观察后,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侵权法作为一种外在的因素始终伴随着不当得利法发展的全过程,而反之亦然;两者呈现出彼此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不过,这种休戚相关的依存关系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我们在侵权法与合同法的互动中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况。(18) 以下笔者将以侵权责任的三种解释性类型为切入点,讨论受益型侵权行为规范路径的选择。
(一)以法国法为代表的侵权责任放任主义体系
1804年《法国民法典》承袭罗马法的衣钵,将不当得利视为准契约的一种类型,而未设立不当得利的概括条款,仅在“准契约”一节规定了“非债清偿”的返还责任。《法国民法典》第1376条规定:“因错误或故意而受领不当受领之物者,对给付人负返还其物的义务”。第1377条规定:“因误认自己对他人负有债务,而清偿者,对债权人有请求返还的权利”。从条文来看,《法国民法典》上的不当得利仅限于非债清偿,尚未成为独立的制度,甚至连“不当得利”的正式表述也没有形成,其体系零散杂乱,与受益型侵权行为紧密相关的侵害权益型不当得利更未囊括在内。《法国民法典》颁布后不久,法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就意识到缺乏不当得利概括条款的弊端,并试图通过学说和判例来拓展不当得利法的适用范围。起初,法国最高法院尝试类推无因管理的规则来解释不当得利案件,但将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债因混淆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诟病。法国最高法院终于在1892年的“布艾迪案”(19) 以衡平为依据肯定了原告对间接接受利益的第三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不当得利制度创建上前进了一大步。法国民法由此正式确立了不当得利的一般原则。此后,学者们很快就发现,如果直接适用此原则,原告可因被告的侵害权益型不当得利之事实而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则侵权责任制度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区分体系将有分崩离析之虞。为此,以奥布瑞和饶为代表的法国学者提出,应当对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一般原则加以限制,以避免其范围过分扩大,遂创设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辅助性理论,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只有在没有侵权请求权或契约请求权时才能适用。(20) 至此,法国不当得利法终于找到其应有的位置。不过,总的来说,从晚近法国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状况来看,法国不当得利法始终处于欠发达状态。受此限制,受益型侵权行为至今无法在法国不当得利法中找到存在的空间。
法国不当得利法的存在空间之所以受到挤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因为法国民法采纳了侵权责任放任主义立法模式。侵权责任放任主义,又可称为非限定原则,是指在民法典中以侵权一般条款的方式对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提供原则性保护,不限制侵权法保护利益范围的立法模式。采用侵权责任放任主义体系的国家主要有法国、比利时、希腊、意大利等。侵权责任放任主义体系的特点是侵权法的适用范围极其宽泛,包括了引起他人损害的任何行为,在客观上只关心是否有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由此将所有侵害他人利益而使自己获益的行为都视为侵权行为,纳入侵权法的调整范围。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作为侵权请求权辅助性措施,可见诸于这些国家的法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042条;希腊则通过判例确立了这一原则。“在那些不当得利请求受到怀疑的法域里有人热衷于将损害概念扩张到不当得利。这些国家总是力图适用侵权行为法的原则。”(21) 为了使原告获得侵权损害赔偿救济,这些国家在各类涉及行为人受益的案件中采用了多种技术,大大拓展了损害概念的范围。在法国,只要满足确定性、个人性、直接性和法定性四个要件,任何损害都是可予赔偿的。(22) 在这四个要件中,确定性、直接性和法定性都是弹性很大的标准,法官们在适用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很大。通常他们也愿意作出宽松的解释,于是很多时候即便被告没有实际损失也被视作遭受了侵权损害,而这些情形在其他国家往往被认为构成了不当得利。例如,在“使用丧失”(loss of use)一类的案件中,原告虽然没有因物的使用丧失而额外支出费用,但仍被认为遭受了损害而享有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官们将这种损害称为“精神上的损害”,并将之解释为原告遭受了“不便”。(23) 此外,在那些仅仅涉及名义上侵权或者原告机会利益丧失的案件中,法官也毫不费力地确认了侵权损害的存在。而颇具启发性的是,这些采取放任主义体系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将行为人受益这一因素作为考察损害的重要指标。在法国,对于受害人是否受到损害的问题,法官通常是用侵权构成的标准来进行判断的,因为这一标准能使加害人受到惩罚。(24) 换言之,在计算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如果行为人因侵害行为的获利超过被告的实际损失时,赔偿的水平将被提高到相当于获利数额的水平。在出版物侵害人格权的案件中,比利时法院将有过失的出版商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润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以此赋予判决一定的阻吓功能。(25) 而意大利法院在对侵害知识产权案件中的财产损失进行评估时也会考虑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并参考一些其他因素。(26) 综上所述,在采取侵权责任放任主义体系的国家,宽泛的侵权损害概念使得行为人返还产生于侵权行为的不当获利成为可能,只是这种救济方式仅局限于侵权法。
(二)以德国法为代表的侵权责任保守主义体系
受罗马法个别返还诉权的影响,1794年《普鲁士普通法》仅列有非债清偿的规定,而无不当得利的一般原则性规定。在《德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学者们对《普鲁士普通法》的规定展开了猛烈的批评,最终促使不当得利的统一规定被纳入其中。在《法国民法典》颁布近百年后,《德国民法典》中的不当得利制度以改革创新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德国民法典》第812条规定:“(1)无法律上的原因,因他人的给付或以其他方式使他人蒙受损失而自己取得利益的人,对该他人负有返还的义务。即使法律上的原因后来消失,或依照法律行为的内容而用给付来追求的结果并未出现,该项义务也存在。(2)以合同就债务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所进行的承认,也视为给付”。《德国民法典》施行后,鉴于其第812条的抽象性,学者们尝试通过学理解释来明晰不当得利的各种基础原因及其体系。1934年奥地利学者维尔贝格(Wilburg)提出“非统一说”,即应区分给付得利和非给付得利的观点。后来冯·克默雷尔(Von Caemmerer)在继受维尔贝格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对各种不当得利情形进行了综合考察,主张除给付不当得利外,侵害型权益不当得利(Eingriffskondiktion)也应是一种重要类型;“‘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类型的发现,扩大了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及规范功能,强化对权益的保护,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7) 以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为的区分为线索的全新的现代不当得利法体系得以建立。可以说,德国民事立法和学说判例的发展为不当得利法对受益型侵权行为的适用提供了充分依据,也确立了不当得利法在现代德国民法上的优势地位,不当得利法由此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
德国不当得利法适用空间的释放,与德国民法采纳的侵权责任保守主义立法模式是密不可分的。保守主义,也可称为限定性原则,是指在民法典中对侵权法保护的利益进行完全地列举,侵权法保护对象的范围被明确规定的立法模式。采用保守主义体系的国家有德国、奥地利、瑞典等。这种体系的特点是侵权法的适用范围狭窄,许多本应属于侵权法的调整领域和规范功能都由其他私法部门来分担。在德国,侵权责任的成立除了具备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三个要件外,还要符合违法性的要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将侵害的权益限定为“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也就是说,只有上述权益受到侵害时违法性要件才具备,其侵害结果也才能构成可赔偿性的损害,否则只能构成单纯的事实上损害。因而损害的概念受到了极大地压缩,在诸如侵害人格权、债权、纯经济损失或没有实际损害的场合,如果从侵权法角度出发就难以确定损害的存在。聪明的德国人遂求助于合同法、不当得利法等私法其他分支,以弥补侵权法调整范围狭窄的不足。对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利的行为进行规范的使命,就落在了不当得利法头上。在那些存在侵权请求权的案件中,不当得利法以竞合者的身份加入到调整这一法律现象的队伍。例如,涉及物的所有权的消费、使用、处分等行为就可能意味着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侵害,如果行为人在此过程中获得利益,就构成“以其他方式取得利益”,原告就可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由于不当得利责任的成立无须原告证明加害人有过错,而且在诉讼时效上更为有利,(28) 因此以不当得利为诉由提起的诉讼受到司法实务界的肯定。在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有疑问的案件中,不当得利法的补充功能表现得尤为突出。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当得利法的适用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在所有权之外还有其他与物无关的权利,如姓名权、商号权、一般人格权、专利或者标记。此外,还有类似权利的,如占有。侵害这些权利或者准权利,是否或者在何种前提条件下会引发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请求权,尚存在诸多疑问。”(29) 对于这些疑问,德国学者遂创设了“权益归属说”进行了解释。持“权益归属说”的学者认为,“权利归属内容决定了对权利或权益的侵害是否会导致侵害权益型不当得利请求权:如果受到(不一定是违法)侵害的权益并不属于此项权益的归属内容,或该项权益的归属内容未被侵害所波及的,则不成立侵害权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认定侵害权益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时认为,债务人应当是将债权人受保护的权益纳为己有,而其以合法方式、未经侵权人同意是不能利用此种权益的;其中侵害必须是,‘侵害了本应归属于债权人的、对权益变价的权益归属内容’”。(30) 尽管学者们对不当得利法的适用持乐观的审慎态度,但在司法实践层面,不当得利法适用领域的不断扩张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例如,在侵害营业权、债权等所有权以外的领域,特别是在侵害商品化人格利益的案件中,不当得利法更是已经取得了真正的实践意义。(31) 不当得利法所蕴含的剥夺行为人没有法律原因获得的额外财产的民事责任,已经超出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的“损害”含义。有关事实表明,上述趋势已经影响到所有受德国侵权责任保守主义立法模式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瑞典法院起初没有考虑不当得利在涉及“纯经济损失”案件中的适用,但后来立法者改变了这种做法,在关于以广告目的使用他人姓名和肖像的法律中规定,在姓名、肖像无过错利用之场合,行为人应当向受害人支付适当的对价,如果证明被告有过错,应当判决等于或者大于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奥地利法院甚至通过判例扩大了不当得利法的适用范围,认为获利一方必须返还使用所得之物的价值,而无须以所有者受到损失为条件。(32) 归纳而言,在采取侵权责任保守主义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救济方式有效填补了适用范围狭窄的侵权法留下的空白,同时也折射出未来侵权法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侵权责任实用主义体系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英国只接受了早期罗马法上的“程序诉讼制度”的影响,而长期游离于罗马法后期成文法编纂运动的影响之外,发展道路有别于欧陆国家。因此,英国始终未能发展出类似罗马法准契约那样的成文法制度,不当得利从一开始就是以零散难辨的诉讼形式出现的,此后一直沿袭这种发展模式。缺少了成文法的引导,学说判例则成了英国不当得利法发展最重要的原动力。传统上,英国法恪守“无救济即无权利”原则,习惯从救济方式而非权利性质的角度对诉讼进行分类。在中世纪,有些“指令令状”(praecipe writ)虽以返还原物或其价额为救济方式,但其实际上既有执行合同之债的效力,又有返还不当得利的功能。这些令状主要针对“借债之诉”(action of debt)与“会计之诉”(action of account)这两种诉讼。(33) 这些实用色彩颇浓的诉讼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罗马法中作为一种对人诉讼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变形和发展。后来的“允诺赔偿之诉”(assumpsit)、“金钱失而复得之诉”(action for money had and received)、“已付金钱之诉”(action for money paid)、“支付合理服务费之诉”(quantum merit)、“支付合理价格之诉”(quantum valebat)等“默示合同”诉讼形式的出现,则进一步完善了返还不当得利诉讼的体系,同时也催生了独立的准契约制度。1760年,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在划时代的“莫塞斯诉麦克弗兰案(Moses v.Macferlan)”(34) 中,确立了不当得利准契约制度。(35) 伴随着1852年《英国普通法诉讼程序条例》的颁布,传统诉讼形式被废除,禁锢不当得利制度发展的诉讼限制得以解除,不当得利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1937年《美国返还请求权重述》的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不当得利理论的发展。1966年,英国学者戈夫(Goff)和琼斯(Jones)共同发表了《返还请求权法》,标志着不当得利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他们关于准契约或其他请求权均系建立在不当得利原则基础之上的观点,成为英美不当得利法的金科玉律。
尽管如此,受法律传统的影响,根植于大陆法系的不当得利概念至今仍为大部分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所陌生。虽然不少学者极力论证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独立性,但认为它作为一种法律效果或救济方式,目的在于请求回复对方所取得的客体或价值的传统观念仍是英美法系国家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观念。英美法学界对不当得利理论的争议和困惑,也许可以从返还请求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关系中找到答案。与普通法的其他私法部门相同,英美法中的侵权法也是从各种具体诉讼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大量具体的侵权诉讼形式及其责任规则,没有形成形式统一的成文法,而是由法官在个案中通过运用各种法律技术进行具体裁判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侵权责任实用主义体系。侵权责任实用主义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不关心什么是可予赔偿的损害,也不对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做出任何理论上的自我限制,只要有对应的诉由和救济方式且符合违反义务标准的判断,就可以确认成立侵权责任。易言之,实用主义侵权法的命运始终无法摆脱救济方式的影响。对于受益型侵权行为来说,传统法律责任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请求损害赔偿与返还不当利益,此两者均为侵权法所承认的救济方式。可见,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来就是适用于特定类型侵权行为的。在历史上,作为不当得利原型的“允诺赔偿之诉”就是从“类案侵权之诉”(trespass on the case)发展而来的。这印证了一个事实:如果不考虑过错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等因素,不当得利法与侵权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源的。但学者却常常漠视这种同源性,在他们看来,原告要想行使返还请求权就必须放弃其在侵权法上的请求权,而且这已经得到司法实务界的普遍遵循。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统一澳大利亚公司诉巴克莱银行(United Australia Ltd v.Barclays Bank Ltd)案”(36)(以下简称“统一澳大利亚公司案”)中,“侵权之诉放弃(waiver of tort)”理论被首次提出。在该案中,原告在上议院判决之前,申请将初审时提出的侵权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变更为“允诺赔偿之诉”,上议院同意了这一请求。由此确立了这样的规则:原告放弃侵权之诉只意味着他选择以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非损害赔偿请求权为诉由进行起诉,原告有权择一行使,但侵权行为并未因此而消失。因此,所谓“放弃”只是一种词义上的误读。事实上,无论原告选择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抑或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都必须首先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37) 所谓“侵权之诉放弃”,在学者看来,只不过是“从前同一程序中无法整合两个不同诉讼形式时期的粗糙的技术”。(38) 无怪乎戈夫和琼斯直言:“‘侵权之诉放弃’是一个错误的标签”。(39) 说到底,“侵权之诉放弃”只是法律禁止受害人就同一损害得到双重救济理念的体现,它不是一种诉由上的选择,而是一种救济形式的选择。这是一种不同于侵权责任保守主义体系中不当得利法与侵权法的竞合,两种体系中的竞合虽然在法律效果上相同,但在本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在侵权责任保守主义体系中,返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是一种程序上的竞合,原告必须在起诉时对两种诉由进行选择,但两者分别对应不同的法律范畴,返还请求权归属于不当得利法,损害赔偿请求权归属于侵权法,诉由的不同意味着法律规范的不同;在侵权责任实用主义体系中,返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是一种实体上的竞合,由于原告的诉由是受益型侵权行为,因此无论原告选择哪一种救济方式都必须遵守侵权法的规则,并接受侵权法的调整。返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竞合方式的区别在形式上表现为当事人选择时机的不同。在“统一澳大利亚公司案”中,上议院法官就明确表示,虽然原告享有返还请求和损害赔偿的选择权,但这种选择在判决最终做出之前是没有强制性的。(40) 在晚近的案例中,法官们再次重申,被告获利计算与原告损失赔偿可以针对同一行为,两种救济方式是相互冲突但又可选择的,而且这种选择在判决形成之前不是必需的。(41) 这种选择自由无疑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辨清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英美法系国家理论界和实务界始终有意识地接受这样的立场:无论是否作为一种独立的请求权基础,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都可以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在侵权法范畴内进行讨论。对于数量日益增多的受益型侵权行为,如侵害知识产权、不法使用他人肖像权用于商业用途等,传统侵权法以受害人损失为基础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已很难给权利人以周全的保护,以行为人受益为基础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完善和发展,正好弥补了这种制度缺陷,与此同时,它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拓宽着英美侵权法的领域。
四、受益型侵权行为对损害赔偿法发展之影响
从不当得利法与侵权法在各国私法的持续互动中可以看到,不当得利法所蕴含的“行为人获益返还”之法律精神已渗透到侵权责任体系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侵权法的原有面貌。(42) 在现代社会,传统侵权法固有的以受害人损失为基础的责任评价体系在很多时候已不能满足权益保护的需要,面临着功能性失效的制度风险,此时以行为人获益为基础的责任评价体系则成为损害赔偿法重要的替代选择。因迥异于传统的侵权立法模式,“行为人获益返还”原则在各国损害赔偿法上的确立与适用,主要是通过拓展损害概念和损害赔偿概念两种方式进行的。
(一)损害概念的现代发展
传统损害赔偿法关于损害概念的界定,无论是“差额说”、“组织说”,还是范围最广的“损害事实说”,均着眼于受害人,甚少关心行为人获益因素。晚近的学说判例主张应从行为人获益角度思考和拓展损害概念。在“斯托克特伦特市议会案”中,尼科尔斯勋爵就做了前瞻性的评论:“一个人不当使用了他人的财产,即使没有造成任何财产上的损失,仍须承担高于名义上的损害赔偿之责任,这是衡量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性原则。(43) 一般而言,他须支付合理的金额作为不当使用他人财产的赔偿金。法律是通过赋予损失或损害概念比以财产所有人在损害行为发生前后的财产状况比较为准所确定的单纯财产上损失更为宽泛的含义而得出上述结论的”。(44) 尽管通过行为人获益这一要素来扩大损害概念范围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但这毕竟超出了损害赔偿法的传统领域,在理论解释上面临着不少困难。有学者主张,可以通过“许可费丧失说”所主张的法律拟制手段来理顺这种逻辑混乱。(45) 所谓“许可费丧失说”,是指将行为人的获益拟制为受害人本应获得的合理许可费用损失,行为人财产积极增加的部分可视为因侵权行为而不当获得的许可费,行为人财产消极增加的部分则视为因侵权行为不当节省的本应支付给受害人的许可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本质上是一种机会利益损失,损害的数额可根据行为人的获益来计算。(46)
“许可费丧失说”在人格权的商业利用领域中的运用尤为广泛。(47)“相关声誉可能存在于一个人通过广告或商业化或者授予第三方许可使用其形象的辅助性经营中。这是有关人格上商誉的更狭义的概念,虽然并不具有吸引力,但它有助于聚焦到原告可能遭受的损害的本质上。因此,如果原告能够证明侵权的前两个构成要素,那么他就能够主张他授权使用其形象的业务可能会由于丧失要求被告为使用其形象而支付一定费用的机会而受到损害。换言之,当原告暂时不能就其形象进行许可经营时,他可以主张被告侵害了他未来许可使用其形象的潜在机会。”(48) 德国在以“许可费丧失说”来拓展侵权损害概念方面的实践颇具启发性。或者,更确切的说法是,采用侵权责任保守主义立法模式的德国是通过对“其他权利”的解释来拓展损害概念的。透过深化对“其他权利”这一兜底条款的规范解释,德国司法界创设了“一般人格权”,排除了侵权责任违法性要件的障碍,使得损害概念范围得以扩大。在德国法院的法律解释过程中,“许可费丧失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在最初,德国法院的观点与现在的主流看法截然相反,否认从许可费的支付中推导出人格侵权财产损害的可行性。在“达尔克案”(49) 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未经许可在一个机械单脚滑行车广告中公开使用一位名演员达尔克的照片,构成了对其人格权的侵害。不过,认为此案的判决主要是建立在对《德国艺术版权法》第22条的违反上的法官,作出赔偿判决的理由是应当对照片使用支付适当的许可费,而不是基于对此种人格权的损害赔偿。有学者对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达尔克案”中表现出来的保守态度提出了批判,指出:“认为非物质性损害不可以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条款的情况下产生一项金钱损害赔偿的决定,是不同寻常的,因为那个案件事实透露了可以根据一项使用许可费而估算出来的金钱损失”。(50) 在此后的“骑士案”(51) 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仍未能转变其立场,虽然判决了一项对非物质性损失的赔偿,但其理由不是因为原告受到传统理解的纯粹经济损失所致,而是原告受到《德国基本法》和《德国艺术版权法》保护的人格受到了侵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不能假设被告可能事先与原告达成一个照片付费使用协议,因为实际上原告没有受到任何金钱损失,而设想一个具有原告这样的社会身份的人会为答应此照片的使用而接受多少钱也纯属臆想;类似的,基于不当得利的权利主张也被排除了,因为原告没有受到金钱上的损失,所以也不存在《德国民法典》第812条规定的金钱返还的适用空间。在随后的案件中,德国法院终于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迪特里希案”(52) 中,柏林上诉法院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保护的一般人格权不仅保护非物质性的人格利益,也保护物质性的或经济性的人格利益。许可费丧失可视为侵害人格权导致的财产损害之原则终于得以确立。“一项权利的性质可以从基本上是一项人格权转化为一项经济性权利,例如商标被归为人格权范畴,但其与企业家个人的业务和人格的关系已经完全脱离。变化的技术和经济环境提供了新的营销机会,使名气大的人格可以创造经济价值……这些保护办法必须超出已有的对纯人格进行保护的非金钱性救济手段。”(53)
“失去许可机会”的法律拟制技术则反映了侵权法的进化方式。事实上,借助行为人获益来证明或推测侵权损害存在的做法并不限于人格权商品化类型的案件,它在侵害所有权等传统侵权案件中开始得到有限度的适用。对于物的毁损或灭失导致的使用丧失,“如果所有人一时不能使用自己的住房,即使其并不因此而发生附加费用,这仍然应当意味着是一种可以赔偿的财产损害。理由是,使用权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拥有’,其还包括使权利人获得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可能性。即使说这种目标有时不能够取得成功,也不应单纯从货币性的财产增加或减少的角度来看待”。(54)
大体而言,拓展损害概念的方式主要为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那些损害概念范围狭窄的侵权责任保守主义立法模式的国家所采纳,英美法虽然也对“失去许可机会”等损害进行了积极的探讨,(55) 但并未触及英美侵权法理论的根本。对以义务为导向的英美侵权法来说,讨论某种类型的事实损害是否属于可予赔偿的损害并无实质意义,它们在更多时候只是关注注意义务而不是损害本身。(56)
(二)损害赔偿概念的现代发展
英美侵权法对注意义务等义务标准的讨论,以保障权利救济为最终目标。因此,将议题集中在作为私权最主要救济方式的损害赔偿之上,也许是最符合英美侵权法内在精神气质的做法。从理论和实践来看,“行为人获益返还”的法律精神在英美侵权法中的扎根与传播,正是通过损害赔偿概念及其功能的拓展来实现的。
一般来说,英美侵权法是在填补受害人损害的意义上使用损害赔偿这一概念的。在传统法律观念中,损害赔偿与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赔偿受害人损失是损害赔偿的唯一功能,“没有实际损害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损害赔偿”(57) 规则被当作“一般原则”(58) 或“绝对肯定的原则”(59) 来对待。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成为“行为人获益返还”损害赔偿方式在侵权法中推广的主要理论障碍。近年来,容易引发各种制度化痼疾的狭隘的损害赔偿观念开始为学者们所诟病。麦格雷戈(McGregor)以名义上的损害赔偿(nominal damages)与惩罚性损害赔偿(exemplary damages)为例驳斥了损害赔偿是严格建立在填补受害人损害基础上的观点,认为除了基本的填补功能外,损害赔偿还应具备其他功能。(60) 按照埃德尔曼的说法,损害赔偿只是“对不当行为的金钱给付”,(61)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62) 损害赔偿功能的多元化,为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的引入铺平了道路。作为以受害人损失为基础的传统损害赔偿的对立面,以行为人受益为基础的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主要是针对原告没有遭受实际损失或者至少实际损失小于被告获益的情形。(63)
虽然将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作为损害赔偿法的一个重要分支的理论已经日渐成熟,而且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多地展现了它的制度魅力,但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和学者并没有过度痴迷于损害赔偿法的这一历史性变革,而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学者们纷纷仿效德国理论界创设侵害型权益不当得利的做法,提出了各种理论以对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的适用做出适当限制。彼得·伯克认为,相关的侵权行为必须具有“防止不受许可的获利方式的目的”;而乔治·帕尔默则提出,在原告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时,被告的获利必须是“法律上受保护的被侵犯利益的产物”。(64) 戈德雷认为:“当被告侵占了原告的土地或动产,侵犯了他的专利或版权,或者将其姓名或肖像用于商业用途时,他就可以要求恢复性的损害赔偿(restitutionary damages)。当他是非法侵犯(battery)、过失行为(negligence)、妨害行为(nuisance)或者诽谤行为(defamation)的受害人时,纵使被告因这类行为而受益,他一般也不能得到那种赔偿。现代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种区分是根本性的”。(65) 他以水泥厂排放烟尘妨害农夫土地所有权的非法侵入案件为例作了深入剖析。(66) 在他看来:被告仅干涉所有权人那些可以获得利益的权利是一回事,他侵占所有权人有权获得的这些利益则又是一回事。根据公平原则,以水泥厂所得数百万美元利润中的一半或者更多赔偿给土地价值仅为25000美元的农夫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却不能据此认为因非法侵入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限于干涉行为所引发的损害。这是因为,如果允许获利大于必须支付的损害赔偿数额,将会鼓励行为人侵害他人再做出补偿,这样所有权人实际上就可能被强迫以低于其权利对他所有的价值而出售该权利。也就是说,法律必须让行为人支付多于补偿性损害赔偿的赔偿金才更公平。正是在此意义上说,英国法院在“罗萨姆公园不动产公司案”(67) 中所确定的损害赔偿数额可能是最合适的。这种损害赔偿数额是高于补偿性损害赔偿数额但又低于行为人获得的全部利润的合理数额。这种损害赔偿既不是补偿性的,也不是惩罚性的,严格来说也不是恢复性的,而是“鼓励你代之以合同约定”的损害赔偿。(68)
恢复性损害赔偿或日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的发展,预示着英美损害赔偿法功能的拓展,其在法律效果上类似于大陆法传统民法中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至此,以受害人损失为基础的责任评价和以行为人获利为基础的责任评价这二元对立的侵权责任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五、代结语:受益型侵权行为理论对中国侵权立法的启示
私法的发展和进步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各个部门法之间在任何时候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以多样化的相互依赖形态而存在。我国侵权立法注定不能摆脱合同法、不当得利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影响和制约。将眼光局限于侵权法本身,是目前我国侵权法起草和研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也许,远距离地观察和思考与侵权法相关的其他私法制度,展示它们与侵权法之间的微妙关系,从而使侵权法乃至整个民法典体系结构和具体规则得以真正的科学化与合理化,才是我国侵权法理论研究和立法起草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受益型侵权行为问题的提出,不仅涉及侵害他人权益使自己受益这种行为形态在未来我国侵权法体系中的定位与规制,还牵涉到我国民法典中侵权法与不当得利法的体系安排与制度衔接。作为后发型的成文法国家,我国在侵权法立法过程中应当积极吸收和借鉴两大法系关于调整受益型侵权行为的有益经验,把握受益型侵权行为所表现出的侵权法发展趋势,为将来的司法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引。基于我国民法理念继受德国民法的传统,在我国侵权立法中引入德国民法拓展损害概念之方式来体现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法律理念无疑更为妥当。同时,英美侵权法和荷兰民法中的返还请求权之损害赔偿与我国民法所承认的恢复原状民事责任形式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而有必要加以借鉴以丰富损害赔偿法的责任体系。在侵权立法过程中,我国除了要对民法各个领域之间的交融保持高度的敏感性,还要时刻牢记保持民法各部门的基本界限的重要性。尽管侵权法与不当得利法在受益型侵权行为规制方面有许多互通之处,它们也各自借用了彼此特有的法律技术,但从整体上看,保持两者的区别仍很重要,(69) 也惟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民法典的体系化得到了真正的尊重。
注释:
① 这些研究,常常涉及返还请求权法(不当得利法)与侵权法的跨部门的比较和检讨,其中不乏有代表性的作品。See James Edelman,Gain-based Damages:Contract,Tort,Equi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Hart Publishing,2002; Steve Hedley,Restitution:Its Division and Ordering,Sweet & Maxwell,2001; Gerard Mcmeel,The Modern Law of Restitution,Blackstone Press Limited,2000; P.Birks,Unjust Enrichment and Wrongful Enrichment,79 Texas Law Rev.1767,2001.
② [日]圆古峻:《判例形成的日本侵权行为法》,赵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87页。
③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债法总则编·合同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9页。
④ 参见[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⑤(18)(21)(24)(26)(32) 参见[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0页,第504页,第611页,第640页,第642页,第642页,第643—644页。
⑥(12)(38)(40)(45) See Gerard Mcmeel,The Modern Law of Restitution,Blackstone Press Limited,2000,p.324,p.325,p.326,p.344,p.327.
⑦ Steve Hedley,Restitution:Its Division and Ordering,Sweet & Maxwell,2001,p.85.
⑧(43)(57) Stoke-on-Trent City Council v.W.& J.Wass Ltd [1988] 1 WLR.
⑨ Attorney General v.Blake[2001] 1 AC 268(HL) 285.
⑩ See Law Commission,Aggravated,Exemplary and Restitutionary Damages(Law Com.No.247,1997).
(11) 包括利益源于受害人、利益源于第三方、利益源于不当行为本身三种形态。See Goff & Jones,The Law of Restitution,Sweet & Maxwell,2007,pp.81-83.
(13) See Lionel D.Smith,The Province of the Law of Restitution,71 Can.Bar Rev.672(1992).
(14)(16)(61) See James Edelman,Gain-based Damages:Contract,Tort,Equi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Hart Publishing,2002,pp.1-4,pp.104-105,p.5.
(15) Warman International Ltd v.Dwyer(1985) 182 CLR 544(HCA) 561.
(17)(27) 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第139页。
(19)(20) 参见霍政欣:《法国不当得利法律制度研究》,《法国研究》2006年第1期。
(22)(23)(25)(56) See U.Magnus,Unification of Tort Law:Damage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80,p.87,p.47,p.58.
(28) 《德国民法典》第852条规定:“赔偿义务人以侵权行为使受害人蒙受损失而自己取得利益的,在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损害的赔偿请求权完成消灭时效后,赔偿义务人也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负有返还的义务”。
(29)(30)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78页,第579页。
(31) Vgl.BGH NJW 1995,861; BGHZ NJW 1987,128.
(33) 参见肖永平、霍政欣:《英美债法的第三支柱:返还请求权探析》,《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3期。
(34) See(1760) 2 Burr.1005.
(35)(39) See Goff & Jones,The Law of Restitution,Sweet & Maxwell,2007,pp.3-11,p.801.
(36) See(1941) AC 1.
(37) See Commercial Banking Co.of Sydney v.Mann(1961) AC 1; Chesworth v.Farrer(1967) 1 QB 407,417.
(41) See Tang Man Sit v.Capacious Investments Ltd(1996) 1 All ER 193; Island Records Ltd v.Tring International plc(1995) 3 All ER 444.
(42) 侵权法对不当得利法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有学者就提出要限制“被告不再得利是不当得利诉讼中一项抗辩理由”的规则,赋予了不当得利法近似于侵权法的效力。See John P.Dawson,Restitution without Enrichment,61 Boston U.L.Rev.564(1981).当然,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值得商榷。
(44) (1988) 1 WLR 1406,1416.
(46) See Sharp & Waddams,Damages for Lost Opportunity to Bargain,2 OJLS 290 (1982).
(47) 参见郭明龙:《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侵权人获利”因素》,《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48)(50)(53) 参见[澳]胡·贝弗利—史密斯:《人格的商业利用》,李志刚、缪因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16页,第265页,第268页。
(49) Vgl.BGHZ 20,345(1956).
(51) Vgl.BGHZ 26,349; BGH GRUR 1958,408(1958).该案的原告是一家酿酒厂的共同所有人之一,也是一位业余艺术家、绅士、骑马障碍爱好者,而被告把一张从第三方的广告代理商处获得的原告照片用于增加性能力的药品广告中。
(52) Vgl.BGH 1,12,1999(1999).该案被告根据一位已故女演员的生平制作了一部音乐剧,注册了“Marlene”商标,并将商标使用在与音乐剧有关的商品上,并将商标许可给一家汽车生产商使用。
(54)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475页。
(55) See Stringfellow v.McCain Foods(GB) Ltd(1984) RPC 501; Henderson v.Radio Corp.Pry Ltd(1969) RPC 218; Tot Toys Ltd v.Mitchell(1993) 1 NZLR 325.
(58) British Transport Commission v.Gourley(1956) AC 185(HL) 197,212.
(59) Skelton v.Collins(1966) 115 CLR 94(HCA) 128.
(60) See McGregor,McGregor on Damages,Sweet & Maxwell,2003,pp.3-4.
(62) 在英美法以外,也可以见到损害赔偿法类似的发展。例如,在《荷兰民法典》中,损害赔偿一词的含义就不限于对损失的补偿,该法第6:104条赋予法官就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方式的选择权。
(63) See McGregor,McGregor on Damages,Sweet & Maxwell,2003,p.4.需要澄清的是,这里所说的损失,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损害,不包括通过法律拟制手段解释和拓展的诸如“失去许可机会”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损害。
(64)(65)(66)(68) 参见[美]詹姆斯·戈德雷:《私法的基础:财产、侵权、合同和不当得利》,张家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29页,第729页,第727—748页,第745—748页。
(67) See(1974) 1 WRL 798.
(69) See Gething,The Action in Unjust Enrichment to Recover the Proceeds of a Tort,3 Tort Law Rev.123(1995).
标签:法律论文; 不当得利论文; 返还原物请求权论文; 债权请求权论文; 法律救济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