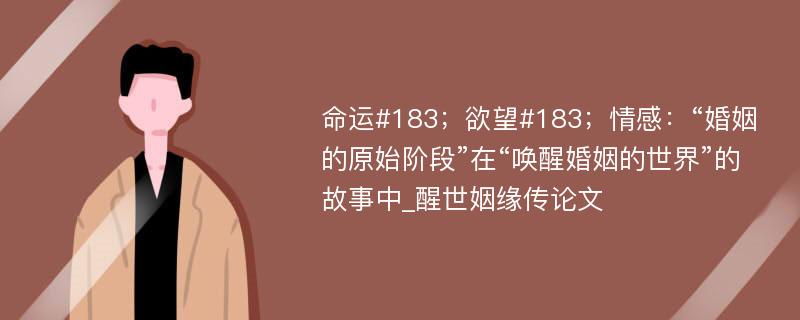
缘法#183;情欲#183;情分:《醒世姻缘传》中的“婚姻本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相论文,情分论文,姻缘论文,情欲论文,婚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醒世姻缘传》中,婚姻问题始终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作为序言的《引起》,首先简单阐释了孟子提出的“君子三乐”(注:《孟子·尽心上》。),并以此为基础广泛讨论了人类的职责以及履行这些职责的方式和途径。接着迅速将焦点转向五伦之中的“夫妇”,郑重其事地指出,要成就孟子所说的“三乐”,“第一要紧”的是“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只有妻子贤德、夫妇和顺,才能真正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不愧不怍、潜心学问。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婚姻具有非常神圣的意义,男女婚姻乃承天地阴阳之性配合而成,所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易·系辞》)。后儒据此发挥渲染,进一步以婚姻为契合“天地之道”的“人伦之本”,伦常礼义、社会组织都基于婚姻,所谓“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所措”(《易·序卦》)。西周生在五伦之中特重“夫妇”,提出“贤德妻房”“第一要紧”,隐含婚姻为伦常之本的传统观念,具有严肃的伦理学意义。
夫妇为人伦之本,应该是人世间最为亲密无间、最能曲致情意的关系,可是,正如西周生所说,现实却让人沮丧,理想中的贤妻像“王者兴,明世出”一样难以“遭着”,现实生活中的夫妻“十个人中倒有八九个不甚相宜,或是巧拙不同,或是媸妍不一。或做丈夫的憎嫌妻子,或是妻子凌虐丈夫,或是丈夫弃妻包妓,或是妻子背婿淫人。种种乖离,各难枚举。而人世间的仇恨,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际,还有逃躲的时候,“唯有那夫妻之中,就如脖颈上瘿袋一样,去了愈要伤命,留着大是苦人”(《引起》),就像是一把累世不磨的钝刀在颈上锯来锯去,其苦楚胜过阎王的十八重阿鼻地狱。天涯相隔的男女为什么会凑合拢来结成夫妻?天意凑合的夫妻为什么有的恩情美满有的势如水火?吴越寇仇一般的夫妻为什么要厮守终生?西周生对这些至今仍让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一、无法躲避的缘法
人生的种种际遇的确有不可捉摸不可预测的一面,婚姻关系的缔结尤其充满了偶然性因素。对于宿命观念很强的传统中国人来说,“缘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最方便的解释”。(注:杨国枢:《中国人之缘的观念与功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婚姻是人伦关系的起点,是血脉关系与非血脉关系的交界处,它使原本可能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人或两个家庭产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因此,缘的观念在这方面也强调得最多。(注:参见王鸿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1994年,第68页。)
宿命的婚姻观在中国起源很早,大概始于周文王娶太姒(注:见《诗·大雅·文王之什·大明》:“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汉儒以阴阳五行之说解经,姻缘天定的观念更加明确(注:《汉书·外威传》:“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填欤。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至唐代,宿命观念广布民间,《太平广记·定婚店》中“月下老人”的故事更是影响深远。在《太平广记》中,“结缡之亲,命固前定”(注:《太平广记·卢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的故事还有《琴台子》、《崔元综》、《卢承业女》、《武殷》、《卢生》、《郑还古》、《秀师言记》、《李修行》、《灌园婴女》,《侯继图》等等。此类故事广为流传,婚姻乃命中注定的观念遂成为一般人信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唐德宗时宋若昭著《女论语》曰:“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元明清以降,有缘千里相会、无缘对面不逢的宿命婚姻观经小说戏曲反复渲染,更加深入人心。元王实甫《破窑记》正旦唱:“夫妇取今生,缘分关前世”;《醒世恒言》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卷首词曰:“自古姻缘天定,不由人力谋求。有缘千里也相投,对面无缘不偶。仙境桃花出水,宫中红叶传沟。三生簿上注风流,何用冰人开口”。(注:《三言》《二拍》中类似的说法还有《喻世明言》卷5:“姻缘本是前生定,不是姻缘莫强求”;《警世通言》卷22:“不是姻缘莫强求,姻缘前定不须忧。任从波浪翻天起,自有中流稳渡舟”;《初刻拍案惊奇》卷5:“诗曰:‘每说婚姻是宿缘,定经月老把线牵。非徒配偶难差错,时日犹然不后先。’话说婚姻事皆前定,从来说月下老赤绳系足,虽千里之外,到底相合,若不是姻缘,眼面前也强求不得的。就是姻缘了,时辰未到,要早一日也不能够,时辰已到,要迟一日也不能够,多是氤氲大使暗中主张,非人力可以安排也”;《二刻拍案惊奇》卷2:“百年伉俪是前缘,天意巧周全”等等。另外,《喻世明言》卷4,《警世通言》卷23,《初刻拍案惊奇》卷5、9、10、12、34等篇目则在情节安排上体现了姻缘天定的观念。)清袁枚《续子不语·露水姻缘》则称,露水姻缘亦有神道掌管。姻缘天定思想与佛教的轮回观念融合,遂成根深蒂固的因果报应之说,人世间的“恶姻缘”都是前世冤业无法躲避。
西周生深受这一传统观念的浸染,他在《引起》中对夫妻之间的因果有一个总的解释:
这都尽是前生前世的事,冥冥中暗暗造就,定盘星半点不差。只见某人的妻子善会持家,孝顺翁姑,敬待夫子,和睦妯娌,诸凡处事井井有条。这等夫妻乃是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友,或是恩爱相合的知己,或是义侠来报我之恩,或是负逋来偿我之债,或是前生原是夫妻,或异世本来兄弟。这等匹偶将来,这叫做好姻缘,自然恩情美满,妻淑夫贤,如鱼得水,似漆投胶。又有那前世中以强欺弱,弱者饮恨吞声;以众暴寡,寡者莫敢谁何。或设计以图财,或使奸而陷命,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
《醒世姻缘传》的主干故事演绎的是无法躲避的三世“恶姻缘”:第一世姻缘,计氏为男是丈夫,晁源为女是妻子,而且夫妻关系中是妻子欺贱丈夫(注:见第3回晁源公公梦中所托之言。不过,30回计氏托梦给晁夫人说自己前世是个狐狸,90回高僧胡无翳说狄希陈“三世前是个极肾极善的女子”,前后矛盾。)。第二世,晁源为男,计氏为女,再结夫妇。按前生之因,应该是计氏欺凌晁源,报完冤孽,然后好合好散。因此,在晁父还是寒酸秀才时,“计氏恃宠作娇,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1回)。可是,随着晁父的发迹,晁源也就渐渐地对计氏有了厌心去了畏敬,终至纵妾凌妻,逼死计氏。同时晁源又射杀狐仙,剥皮弃骨,种下新的恶因。第三世,晃源转世为狄希陈,狐仙转世为薛素姐,计氏转世为童寄姐,双双嫁与狄希陈。至于晁源的宠妾施珍哥则转世为丫鬟小珍珠,被寄姐虐待至死。素姐和狄希陈本来有“六十年的冤家厮守”,才能“报复前仇”(100回),经神僧胡无翳超度,才得以提前消释冤愆。素姐病死,狄希陈与寄姐和好成家,并因“有善待庶母,存养庶弟,笃爱胞妹之德”而得以“延寿一纪,考福善终”(100回)。
除了妻妾之外,狄希陈与孙兰姬之间的露水情缘也是“前缘宿定,赤绠系将来”的“缘法”。李姑子对狄母说,他们俩是前生同在船上订了盟未曾完得,所以“这辈子来还帐”,“还不够,他也不去。还够了,你扯着他也不住”。李姑子甚至说“但凡人世主偷情养汉,都是前生注定”,而且,“若是那应该的缘法,凭你隔着多远,绳子扯的一般”,挣也挣不开(40回)。连廉耻丧尽的程大姐也相信“要嫁人家,也无论老少,只要有缘法”(72回)。这些显然都是对“姻缘天定”的传统观念的演绎。
《醒世姻缘传》对婚姻的果报解释历来受到非议。我们认为,对此应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以科学的唯物的观点来看,它的确属于无稽之谈。但是,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俗信仰,它主要给男女遇合的机缘一种神秘的解释,并给婚姻不如意者一种宿命的安慰。周景杨就曾劝狄希陈说:“尊嫂如此悍戾,不近人情,这断不是今生业帐,必定是前世冤仇,今世寻将来报复”(98回)。据杨国枢先生的调查,在台湾现代大学生中,对一些关于“缘”的成语与谚语持赞成态度的比例相当高,“遇合有缘”90%,“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88%,“千里姻缘一线牵”81%,“一日夫妻,百世姻缘”56%,“千年修来共枕眠”56%,“百年修来同船渡”54%,“不是冤家不聚头”43%。就具体的婚恋关系而言,认为男女一见钟情是“有缘”的占92%;认为婚姻美满是“缘分很好”的占72%;认为夫妻不和而离婚是“没有做夫妻的缘分”的占47%;认为婚姻不幸是“没有做夫妻的好缘分”的占44%,杨先生同时指出,大学生是现代化程度最高、偏离传统最远的群体,普通民众相信“缘”的比例应该更高。因此,虽然现代人所说的“缘”,相对于古人来说,迷信与宿命的色彩已经明显减弱,但是,“这样高的百分比总可显示缘并未成为历史的陈迹,还是存在于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注:参见《中国人之缘的观念与功能》,《中国人的心理》。)
德国19世纪历史文化学家狄尔泰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注:钱钟书:《管锥编》,引文为钱钟书的译文,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第166页。)陈寅恪先生吸收这一解释学原则,提出了著名的“同情”说,强调对历史材料解释中的生命体验。(注:“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分,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7页。)狄尔泰以及陈寅恪的观点,不仅适用于思想史哲学史,同样适用于文学史的研究。
西周生深信男女遇合以及婚姻都是无可逃避的“缘法”,而“恶姻缘”是“前生怀宿仇,撮合成显报”,因此奉劝世人“顺受两毋躁”(《引起》)。我们如果能够“遥体”西周生“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并考虑到缘的观念在现代中国依然广泛存在这一事实,那么,就对西周生的“迷信”就不应该过分苛求。
二、无法抗拒的情欲
在狄希陈暗无天日粗俗不堪的婚姻生活中有两个具有亮色的片段格外引人瞩目,一是在情窦初开的少年时代与妓女孙兰姬萍水相逢的姻缘;一是在远离凶神恶煞的素姐到京城坐监时与童寄姐无忧无虑的恋情。
狄希陈在济南府趵突泉西边一座“花园”里“溺尿”,无意中被妓女孙兰姬看见并大声嚷嚷,狄希陈羞得脸绯红提着裤子跑了。一来二去,彼此留情。第二天狄希陈偷偷跑到孙兰姬家里,两个斗了一会嘴,孙兰姬就主动“梳笼”了狄希陈(37回)。从此,狄希陈寻找一切机会与孙兰姬“鬼混”(38回)。命定的“缘法”结束之后,孙兰姬被当铺老板秦敬宇娶走,两人恋恋不舍地分手。各自婚嫁之后还匆匆见过一面,不禁“销魂”“落泪”,此后“便都彼此茫茫,再难相见”(50回)。花园相遇的方式显然是对自《史记·司马相如传》以来的千古文人津津乐道的“才子佳人”模式的戏拟;书生与妓女的身份则又是对《李娃传》以来的“妓院爱情”的戏拟。
“花园”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固定意象,可是“溺尿”这一粗鄙且极具性暗示意味的动作,不仅消解了“花园”意象的浪漫和诗意,而且将男女关系中潜在的原欲和盘托出。接下来情节的发展强化了这一构思。狄希陈和孙兰姬之间,没有美妙的琴声,没有缠绵的情诗,甚至也没有一般意义上嫖客与妓女之间的金钱关系,两个偶然相遇的年轻人在本能的驱使下毫无阻碍地遂其情欲。作者评价说:“情欲已开,怎生抑遏得住?”(40回)强调的是欲望层次的冲动与不可抗拒。在“玉人不见”(50回)之后,狄希陈珍藏着孙兰姬赠送的“汗巾”和“眠鞋”,“但遇闲暇之时,无人之所,就拿出来再三把玩,必定要短叹长吁,再略紧紧,就要腮边落泪”(52回)。这种由于阻隔而产生的“相思”,隐约有了一些“诗意”,可是,叙述者再一次不动声色地弱化了“情”的因素。他说:“若是少年夫妇,琴瑟调和,女貌郎才,如鱼得水,那孙兰姬就镇日矗立在面前,也未免日疏日远。争奈那素姐虽有观音之貌,一团罗刹之心。狄希陈虽有丈夫之名,时怀鬼见阎王之惧,遇着孙兰姬这等一个窈窕佳人,留恋爱惜,怎怪得他不挂肚牵肠?”(52回)也就是说,狄希陈对孙兰姬的“相思”,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对方可爱而是因为自己婚姻不幸。狄希陈与孙兰姬的“相爱”时的情形已为这里的“琴瑟调和”、“如鱼得水”作了注脚,他“短叹长吁”地向往的是肉欲层面的和谐美满。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补充证明狄希陈对孙兰姬主要是“欲”而不是“情”。狄希陈恋着孙兰姬不肯回家,可是听说家里请了几个神仙般的姐儿,就乖乖地回去了。
作品多次重复“溺尿”的情节(注:第一次是叙述者正面叙述,详写;第二次是孙兰姬当着狄希陈的一班朋友打趣他:“你对着我溺了尿去……”,“你极了尿,可再来这里溺罢”;第三次是孙兰姬私下里打趣狄希陈:“你怎么不再去我家溺尿呢”(以上均见37回);第四次,孙兰姬对狄婆子复述,详写(40回);第五次狄婆子对薛婆子复述,略写(41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才子佳人模式的浪漫与诗意。而作为妓院爱情故事,作者又巧妙地消解了情欲与礼法的对立。
在中国古代,自春秋初叶齐管仲设“女闾”始,娼妓就已成为一种国家制度(注:参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21页。),与此相适应,妓院成为不受礼法禁锢的化外之区。在世俗观念中,少年男子嫖妓,从妓女那里获取性经验,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对狄希陈嫖妓一事,狄员外“一些”也“不恼”,狄婆子只是担心他“长出一身疮来”(40回),甚至连素姐的母亲听了狄希陈与孙兰姬“溺尿相遇”的故事后也是“又笑又喜”(41回)。在狄希陈新婚时,薛三省娘子还打趣他:“府里孙兰姬没教给你?”(45回)。
狄希陈与孙兰姬的关系是青年男女“情种欢逢,娇娃偶合”(40回)的欢愉。如果作者从这种“欢愉”之中正面导引出“情”,并让当事人为这种“情”走出妓院踏入现实而付出努力,则势必面临礼法的非难。具体地说,如果狄希陈因为爱情而坚持要将孙兰姬娶回家,甚或为之反叛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则会产生自由爱情与父母之命之间的冲突。可是作者的兴趣显然不在这里,他借着“缘法”的观念轻而易举地避开了这种潜在的冲突。狄婆子亲自前往府里找寻狄希陈,一见孙兰姬的面。“那一肚皮家里怀来的恶意如滚汤浇雪一般”(40回)无影无踪了,不但不责备反而体贴地成全他们最后两天的缘法。如果说母命代表礼法,在这里,礼法主动成全了化外的情欲。
如果说狄希陈与孙兰姬的故事还只是对潜在的情礼冲突的逃避,狄希陈与童寄姐的故事则是对现实的情礼冲突的消解。
狄希陈第一次到京里“坐监”,住在童奶奶家里,宾主相处有如“至亲”,狄希陈与童家十岁的小姑娘寄姐以“哥哥”“妹妹”相称(54回)。再见面时,寄姐已“长成了个大大的盘头闺女”,两个仍像兄妹一样无拘无束地“斗嘴雌牙”“掷骰赌钱”。在“玩耍”过程中,彼此胳肢脖子拉扯胳膊,寄姐不禁“脸红”。到后来,一个说“你倒好性儿,我娶了你罢”,一个说“你这们好性儿,我嫁了你罢”(75回)。当狄希陈托人向寄姐的母亲童奶奶提亲时,童奶奶对寄姐说:
姑娘,你听见来?这是你终身大事,又没了你爹爹,你兄弟又小,我终是个女人家,拿不定主意,说不的要你自己几分主张。
母亲主动把婚姻自主权交给了女儿,意味着礼法对情欲的退让。可是,这对自由恋爱的情人,婚后不久即吵闹不休。卢棱有一个有名的论断,他说夫妇共同生活六个月以后,美貌就不再被重视,甚至于不会令人留意。(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商务印书馆,1995年,1996年2次印,第114页。)推而广之,当进入婚姻、感官的享受得到满足之后,男女之间由于性意识而产生的互相吸引、若即若离的“激情”会渐渐平息。寄姐婚后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激情”平息之后的真实表现。相对于那种有情人成了眷属之后必定百年好合的恩情美满的浪漫故事来说,西周生的观察也许令人沮丧,却的确更具人性的真实。
书中两个最具亮色的片段已经对男女遇合的浪漫情怀以及外力对男女情欲的阻隔都进行了消解,作者关注的是男女之间尤其是婚姻关系中的情欲。
《醒世姻缘传》对情欲的描写,并没有走《金瓶梅》、《如意君传》、《绣榻野史》之类的“以淫戒淫”、满纸“艳情”的套路,它对性场景的控制处理非常引人注目,“尽管这部小说的主要素材将其焦点极富规律性地带入闺房之中,但作者在处理这些场面时表现了明显的控制。与此相反在叙述和对话中却充满了粗俗的色情表述,常常到了极端细节化的程度,因此就使这种对性场景描述的控制更令人注意”。(注:浦安迪:《逐出乐园之后:〈醒世姻缘传〉与17世纪中国小说》,见乐黛云等主编《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在接触到性场景时经常以“枕边光景不必细说”、“吹灯以后的事体可以意会不屑细说”(72回)等隐语一笔带过,这表现出作者对“情欲”的严肃态度。
作者注意到了情欲在夫妻关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狄希陈乘机取鼎”一节是全书有数的“色情”描写之一。狄希陈连续两夜被关在新房门外,甚为恼怒。第三夜乘着素姐酒醉成就了姻缘之后心满意足,甚至连素姐也有了些“温柔”。作品通过叙述者和小玉兰两重视角补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狄希陈和素姐之间的“初夜”,其目的并非“宣淫”,而是为了表达一种深刻的内涵,这一情节对狄希陈和素姐日后婚姻生活极具象征意义。狄希陈曾对劝他休妻的术士邓蒲风说:“我几番受不过,也要如此。只是他又甚是标致,他与我好的时候也甚是有情,只是好过便改换了,所以又舍不得休他”(61回)。当太守得知素姐的恶行要为狄希陈“断离”“除害”时,素姐平生第一次向狄希陈求情:“小陈哥……你想想那使烧酒灌醉了我的那情肠,你没得不疼我的”(98回),“初夜”的爱欲,成了素姐用来向狄希陈“乞怜”的最重要的资本。
狄希陈贪恋素姐的“标致”而舍不得休妻,素姐同样为了自己的“人欲之思”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素姐被那酒香触鼻,欲火攻心,明知与狄希陈是前世冤仇,到此田地,不得不用他一用。既要用他,便也只得假他个颜色”(61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对前世冤家的夫妻关系正是靠非理性的原欲来维系,双方互相厌憎互相仇恨却又互相吸引互相需要。
与狄希陈和素姐比起来,晁源和珍哥的夫妾关系中肉欲的成分更加突出。小珍哥本是娼家出身,毫无德操和羞耻之心,却“风流伶俐”,作品多次写到她与晁源“纵欲”,甚至造成了“崩胎”的严重后果(4回)。与此形成对照,计氏却是个“正经人”,“争妍取怜、媚惑人的事”“一些不会”(8回)。晁源宠爱珍哥而厌弃计氏,说明他追求的是淫荡的性伴侣而不是守贞的妻子。这一点还可从他与珍哥的“誓盟”中看出,晁源许珍哥扶正,珍哥则许晁源寻一个美妾“大家取乐”;当媒婆来提亲,晁源有可能娶到比珍哥更年轻漂亮的富家小姐时,就恨不得“一木掀把那珍哥掀将出去才好”(18回)。婚姻关系至此,除了“欲望”还有什么?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淫荡的受宠,守贞的却被诬以不贞的罪名要被休掉,“贞”与“淫”都成了借口和可利用的工具,已经毫无道德上的意义可言,这足以说明礼法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分离的现象。
此外,作品还从反面说明了性爱的重要性。狄希陈惧怕寄姐还有一个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的原因,那就是狄希陈不能很好地尽“丈夫”的责任,以至于半夜三更不是被揭了被子挨冻,就是被踢下床来不许同睡(91回)。郭总兵是一位可以让“百万官兵神钦鬼服”的武将,居然也怕老婆,似乎不可思议。在权奶奶和戴奶奶争风吃醋不可开交时,这位丈夫解释说:“我们做大将的人,全要养精蓄锐,才统领的三军,难道把这些精神力气都用到你们妇人身上?”由此看来,他的问题也是不能很好地尽“丈夫”的责任。第八十七回写到郭总兵、狄希陈两家在船上都闹得天翻地覆,在幕客周景杨的提义、安排下游了一天山,“只因遣兴之后,不止狄希陈与寄姐和好如初,权奶奶与戴奶奶也暂时歇气”。游山可以调剂婚姻的矛盾,是因为妻子们旺盛的精力在性爱之外有了排遣的途径。
西周生对性爱在婚姻中的作用基本持肯定态度,不过,他以反讽的方式主张婚内情欲同样应该有所节制,尤其是中年之后。
西汉枚乘《七发》说:“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浩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1624年出版的春宫画册《鸳鸯秘谱·小引》中说:“奈何世人不能惩欲,竟以此为欢娱之地,而使生我之门,为死我之户”;略早于《金瓶梅》的医学著作《养生四要》卷一《寡欲》引吕纯阳诗曰:“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髓骨枯”,三者都强调色欲的恐惧而主张节欲。这一类观念在古代小说中广泛存在,不过绝大多数在警戒色欲的同时交织着对“浩齿娥眉”、“二八佳人”的恋慕。《醒世姻缘传》中晁源贪恋唐氏的“娇艳”而死在小鸦儿刀下,重复了“纵欲身亡”这一司空见惯的主题。对此,叙述者引用了一句套话来评价:“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以诙谐的口吻突出了“风流”的欢愉而消解了“死亡”的恐怖。与此相对照,西周生关注的似乎是另一种“恐惧”——“老夫少妻”型婚姻中“老夫”生命的迅速枯竭。晁思孝娶妾之后触了风寒,头疼发热,不到两个月即“考终了正寝”(18回);汪为露为了“小新人”,弄得“肾水消竭”,不久即“佯长去了”(39回);周龙皋娶了妖冶的程大姐,“弄得精空一个虚壳”,不到两年即得伤寒病症而死(72回);类似的还有晁无晏,续娶的郭氏虽然不是“少妻”,但他“饿眼见了瓜皮,扑着就啃”,几个月之后即跟着“(阎王的)差人去了”(53回)。作品通过“形象迭用”(注:参看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0页。),将同类的故事均匀地穿插在作品中,似乎在持续地提醒读者,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中,同样需要节制欲望,对中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从这一点来看,西周生对色欲的态度,接近于道家的“养生”说。
如前所述,狄希陈与孙兰姬的欢愉在当时的社会不触犯任何忌讳,所以叙述者对它持欣赏的态度。狄希陈与薛素姐、晁源与珍哥的关系则说明了情欲在婚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仅有情欲,不可能有和谐美满的婚姻。更何况,就像婚前的激情会逐渐平息一样,随着年华渐老,情欲对婚姻的维系力势必日趋减弱,如果这时还一味迷恋肉欲,甚至会断送生命。这也许就是西周生在情欲问题上给予我们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放纵情欲导致身亡的“老夫”基本上都是道德上的小人和恶人,他们的“纵欲”是贪婪、不知节制的本性的延伸。这样,对婚内情欲的关注在更深的层次上与对道德的关注联结到了一起。
三、无法弃置的情分
胡适先生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中曾经提出:为什么狄希陈不离婚呢?这的确是一个有趣而又值得思索的问题。
《礼记·檀弓》、《列女传》均有言:“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大戴礼·本命篇》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概言之,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盗窃等,皆可成为男子出妻的理由。礼法既言夫妇无义则去,又为男子提供了出妻的种种理由,因此历代律法都允许离婚。《大明律》甚至规定:“若犯义绝应离而未离者,亦杖八十”,这已不止是允许离婚,而是强制“义绝”者离婚。更有甚者,律文还规定:“凡妻妾殴夫者,杖一百。夫愿离者,听。至折伤以上,各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素姐除了淫和盗窃之外,“七出”中占了五条(注:素姐本来貌美,后来被猴子抠瞎了一只眼、咬掉了一个鼻珠,见76回。);在成都府里,打了狄希陈六百棒椎,又用一熨头炭火烧烂了狄希陈的脊背,这已不仅应该“断离”,而且应该受到律法的严惩。可是,狄希陈还是没有“出妻”,这是为什么呢?
成都府太守知道素姐的暴行之后,逼着狄希陈递呈子由官府“断离”。狄希陈与寄姐商量,寄姐提醒他考虑两点:第一,“只怕断的不伶不俐,越发中了深恨”;第二,“你见做着官,把个老婆拿出官去,当官断离,体面也不大好看”(98回)。狄希陈一时顾不得“后来仇恨”和“眼前体面”,要周景杨替他写呈稿。周景杨却说:“天下第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是与人写休书,写退婚文约,合那拆散人家的事情”,然后说了一大堆写休书或休妻损阴骘、得恶报的事典。再加上素姐得知了风声,假意认错乞怜,狄希陈终于打消了休妻的念头。
如前所述,自先秦始,礼法和律文都不以离婚为非,因此,离婚易而流于滥。孔氏三世出妻(注:《礼记·檀弓·家语·后序》。);曾子因蒸梨不熟而出妻;晏子车夫之妻因夫胸无大志而“求去”(注:《史记·管晏列传》。);朱买臣之妻因夫贫贱而“请绝”。(注:《汉书·朱买臣传》。)自春秋战国而至隋唐,有据可查的离婚事件不绝如缕。唐代公主离婚改嫁者,不胜枚举,有的甚至再离而三嫁。从唐高祖到代宗,出嫁的公主九十三人,其中再嫁和三嫁的达二十八人,有夫死再嫁,亦有夫在改嫁。当时社会离婚之易于此可见一斑。唐时佛教盛行,冥报观念深入人心之后,为人所鄙的无故弃妻行为辗转附会酿成阴谴之说,宋人渐以离婚为丑事,士大夫遂不敢轻言出妻。士人应科举者,恐遭阴谴致误进取,故多视离婚以及替人写休书为可畏。(注:参见《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1-595页。)周景杨所说的孙举人和陆秀才的故事,即是对流行的报应故事的附会。(注:《南部新书》卷10(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1036册,“子部”342“小说家类”第259页)、(宋)李昌龄《乐善录》(见《说郛》)均有载。这类故事在古代小说中被广泛引用。)
胡适先生根据寄姐所说的第二点,认为狄希陈之所以没有休妻,主要是考虑面子的问题。我们认为,周景杨不肯写呈稿,是畏惧阴谴;狄希陈最后放弃休妻,“阴谴”和“面子”观念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情分。狄希陈对太守说:
薛氏嫁经历的时候,父母俱全;如今他的父母俱亡,这是有所往无所归。且自幼都是先人说的亲,由先人婚嫁,两处先人俱已不在,又不忍背了先人之意。且是机事不密,被人泄漏了消息,他却再三的悔罪,赌了誓愿,要尽改前非,自许如不悛改,任凭休弃。于是衙中众人再四的劝经历在老大人上乞恩,且姑止其事。(98回)
这里,狄希陈求太守“姑止其事”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追念两家先人;二是薛素姐自己悔过认罪的态度。先看第二点。素姐在小浓袋的点拨下,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小服低”,向狄希陈道歉认错、立誓悔改,并含嗔带娇地搬出了他们“初夜”的情爱,由不得狄希陈不心软。这是夫妻情分。
再看对两家先人的追念。狄希陈与素姐的婚姻原本是地道的“父母之命”,在他们八岁的时候由父母作主定亲,而且是换亲,即狄希陈的妹妹巧姐许配素姐的弟弟薛如兼。这时候,两家已“相处了整整的十年,也再没有这等相契的了”(25回),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和二姓之好”(注:《礼记·昏义》。)的婚姻。在他们婚后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父母之间的情分始终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素姐逆姑殴婿,薛夫人拿着礼品亲自登门“千赔礼,万服罪”,“求亲家担待”,“倒也教狄婆子无可无不可的”(48回);狄婆子被素姐气成瘫症,薛夫人和两个管家娘子时常往来问候(56回);薛教授则同样被女儿气得中痰风瘫(56回)。这样相契的儿女亲家,怎么可能休妻?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七十回。素姐与程大姐一起,在上庙途中被一群流氓无赖将衣裳剥了个精光,连绣鞋和裹脚都拿走了。据说自从缠足的习俗风行以后,女人的小脚成为身体最隐秘的部分。(注:“从宋代起,尖尖小脚成了一个美女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并围绕小脚逐渐形成了一套研究脚、鞋的学问。女人的小脚开始被视为她们身体最稳秘的一部分,最能代表女性,最有性魅力。宋和宋以后的春宫画把女人画得精赤条条,连阴部都细致入微,但我从未见过或从书上听说过有人画不包裹脚布的小脚。女人身体的这一部分是严格的禁区,就连最大胆的艺术家也只敢画女人开始缠裹或松开裹脚布等样子”,“春宫画上的女人凡在席子上或有侍女可以看得见的地方性交,总是穿着鞋子和扎着裹腿,鞋子和裹脚只有在遮有帐幔的床上才脱下,裹脚布也只在浴后才更换”,分别见高罗佩著,李零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版,第286、290页。)素姐狼狈至此,可谓脸面丢尽。可她非但不自责不羞愧,反而将狄希陈的胳膊咬掉核桃大的一块肉。这时,薛教授夫妇和狄母都已离世,一向忠厚本分、委曲含忍的狄员外羞恼至极,“皇天爷娘的大哭”,要儿子休妻。当素姐的生母龙氏来“理论”时,狄员外说:
要我说你闺女该休的罪过,说不尽,说不尽!如今说到天明,从天明再说到黑,也是说不了的!从今日休了他也是迟的!只是看那去世的两位亲家情分,动不的这事。刚才也只是气上来,说说罢了。(73回)
如此羞恼之下,尚要顾及去世的亲家的情分,在此之前,狄家为两家的情分而对素姐百事含忍就更不难理解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儒家社会秩序的基本骨架是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它假定人是生存在各种人伦关系之中,而人伦关系靠种种情分来维持。在文化价值体系中,中国和西方都有适合于一切人的最高的普遍法则,在西方是“公平”,在中国是“仁”(后来是“理”)。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人一直重人伦之情,孟子的著名假设“瞽叟杀人”和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都说明“法”在中国价值系统中不是最高原则而是次一级的观念。明白了情分在中国社会运作中的重大作用,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狄员外如此看重去世的亲家的情分,为什么狄希陈最终未能下决心按律法休妻。
狄希陈尽管从小刁钻古怪、顽皮促掐,可是与他的前生晁源相比,还是有本质的不同。他有“善待庶母,存养庶弟,笃爱胞妹之德”,而且,他基本上是个顺从父母的儿子,有较强的孝道观念。他自己曾说:“娘教道我,甚么我没听来?我正好好的在府里住着,娘只去,我没等娘开口,我就跟着娘来了”(45回)。“蒿里山哭母”(69回)一节则说明了他对亡母的怀念。所以,他追念先人、“不忍背了先人之意”应该是真诚可信的。从他的说辞以及他实际的处境来看,与夫妻情分比较,两家先人的情分应该是更主要的因素。
中国古代的婚姻,既以“父母之命”为常格,那么,像这样因为两家的情分该离而不能离的情形无疑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在西周生笔下,婚姻与精神层面的爱无关,这种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有人认为,“为爱而结婚成了一种奢侈,要等在某些文化上的变革发生后才会出现,即要等到对个人尊严有更多的敬重、男女平等的观念出现、财富大量增加和生活闲适时才有可能”。(注:安东尼·华尔士著,郭斌等译:《爱的科学》,团结出版社,1999年,第22页。)在中国古代,婚姻的目的是奉祭祀、繁子孙、求内助,“为爱而结婚”当然无从谈起。文学作品中那些“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爱情,大多是文人浪漫的理想。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关系”。(注:马克思:《1844年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夫妻是由两个互相吸引的一半组成的整体,而整体中的两部分虽然互相不可或缺,却始终存在着“一种时而敌对时而和睦、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注: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央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69页。),因此,婚姻是“一种两极间的张力”。(注:霭理士著,潘光旦译:《性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1页。)“缘法”是对婚姻超验的解释,“情欲”与“情份”无疑是维持“张力”的重要因素。有的论者认为,西周生笔下的婚姻悲剧“莫不是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所造成的恶果”(注:北大中文系:《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89页。),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的确是封建婚姻的痼疾。可是,在“一夫多妻”、“父母之命”早已成为历史,为爱情而结婚早已成为现实的今天,类似西击生笔下的婚姻悲剧依然存在,徐志摩就曾经说过,在他的朋友们家里,不乏“出过大洋念过整本皮装书的”“素姐”(注:徐志摩:《〈醒世姻缘传〉序》,亚东版《醒世姻缘传》附录,广州出版社,1996年。);在我们的身边,也不乏“同床睡大虫,共枕栖强盗”的夫妻。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父母之命”和“一夫多妻”。由“缘法”、“情欲”和“情分”来解读《醒世姻缘传》所描写的婚姻,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