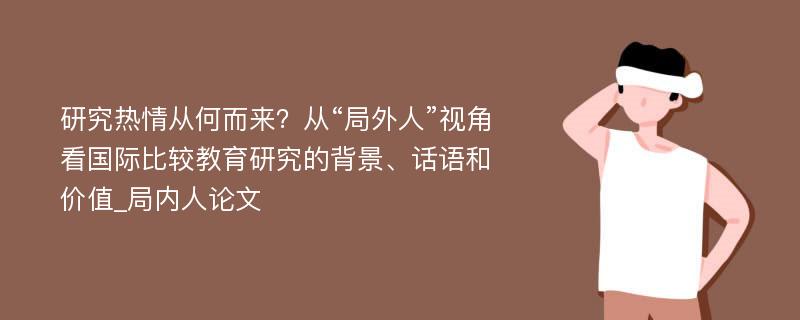
研究热情从何而来?——以“局内人—局外人”视角看国际比较教育研究的背景、话语与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内人论文,而来论文,局外人论文,视角论文,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2)02-0008-05
在本研究中,我将使用“局内人”与“局外人”这一对概念来阐明我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局内人”与“局外人”概念并不等同于“局内人主义”或者“局外人主义”,这一组概念的建构充满了复杂性,并且与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密切相关。这一组概念在学术研究领域并不陌生,比较教育自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后,就多次使用其进行研究。鉴于此,或许我应该把论文的题目改成“再次启用‘局内人—局外人’视角”更好些。
我在题目中使用了“热情”(passion)一词。“热情”在英语中有多重含义,在基督教中,这一词意味着耶稣受难,是一个带有消极意向的词。在诗歌、文学、音乐、电影和西方媒体中,这个词又意味着“爱、强烈的情感以及我们非常在乎的东西”。比如表达“我们对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怀有极大的热情”时,就可以使用"passion"。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强调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公平、教育质量与社会变革问题。这都是比较教育研究者所关心的或者说投入极大热忱关注的问题。我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说不同的语言,没有多少可以共享的生活经验,但作为教师和比较教育研究者,我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非常关注这些与教育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
“我们的行为表现与我们的旅行有关,我们去过什么地方,我们就会具备那一方水土的特质”。
——19世纪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米歇尔马契》。
上面所引用的这句话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和我们进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经历。以我自己为例,我的人生旅程的起点是我的双文化特质。我在德国出生并在德国接受教育,而成年后在英国定居,开始研究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在研究过程中跨越多个文化领域。有时候我作为单个研究者独自进行研究,有时候又与许多欧洲国家的同事一起合作。我在说英语和德语的国家开展研究时,能够准确地理解研究的文化背景,而在官方语言是非英语和非德语的国家进行研究时,我需要通过专业知识去克服研究中所遇到的障碍(Arthur,2007)。我的个人经历和研究体验使我能够游刃有余地使用“局内人—局外人”视角去研究纷繁复杂的国际比较教育问题(Arthur,2001)。
我把今天的演讲内容置于高等教育教学背景下,从我对世界的理解角度,对国际比较教育的四个方面进行阐述:(1)英国国际与比较教育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简称BAICE)视角;(2)全球视角;(3)“局内人—局外人”连续统一体;(4)共享意义与价值观。
一、英国国际与比较教育协会视角
我曾经担任英国国际与比较教育协会(BAICE)会长,同时我也担任BAICE学术期刊《比较》的编委。大家从BAICE的英文标题就可以看出,BAICE没有很好地解决“国际”与“比较”二者的矛盾关系,到底是先有比较,后有国际,还是反过来呢?现在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非从BAICE名称实用性的角度出发,而是更多地强调两个概念历史根源的模糊性(Bray,2010)。“国际”和“比较”两个关系密切的领域虽然可追溯的历史根源是不同的,但是却有许多共同点。比较与国际教育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有丰富的发展历史、多样化的目标和理论基础、完善的全球性组织网络以及诸多优秀专著(Crossley,Watson,2003)。
BAICE与其他比较教育组织机构一样,富有活力,执行力强。现在BAICE的发展状况是:(1) BAICE有300名会员(Lee,Mak,2010)。(2)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3)定期开展研讨会、承担科研项目以及为学生提供奖项资助。(4)与其他比较教育组织保持良好关系。(5)为母语是非英语,但想在《比较》投稿的作者制订发展计划和开展讨论会。(6)创办学术期刊《比较》,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
《比较》接收和发表的文章来自世界各地,中国研究者的文章也在《比较》期刊中占据一定比例。该期刊通过纸质版和电子版的方式发送给世界范围内数量庞大的订阅者。目前《比较》期刊的线上服务和全文下载服务发展迅速。在2005年,全文下载的文章达到8,000篇,2010年则增加到25,000篇,2011年更是达到31,000篇。在《比较》期刊中,许多发表的文章关注的是英联邦国家的教育问题,这些文章反映了英国的殖民历史以及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这些文章都以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传统学术风格进行发表,反映了批判性的、建构主义和后现代的研究范式(Stromquist,2000)。
2010年,《比较》创刊40周年。在2000年,《比较》杂志每年发行3期,但是随着世界各地投稿量不断增多,现在《比较》每年发行6期,发行数量的增多标志着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比较教育研究者对全球化问题、新自由主义对教育的影响以及教育市场化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多。
《比较》编委埃文斯(Evans)和罗宾逊-潘特(Robinson-Pant)在《比较》40周年特刊中撰文指出,近几十年中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主题的变化,即与跨文化研究相比,学者更加关注理解不同文化间学习和互动的过程以及新的教学和学习方式。同时指出,研究者对比较教育的研究兴趣有了复苏的趋势,比较教育主要被当做提高各国国际竞争力和国际竞赛名次的副产品(Evans,Robinson-Pant,2010)。但是,“比较”的边界仍然非常模糊。因此,我们建议有潜力的作者在投稿时要对不同的文化群体、时间阶段或者教育体系进行比较性反思。
二、全球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几年,《比较》的学术文章中对低收入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以及这些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国际发展问题研究有了显著增多。I-Hsuan Cheng(2010)认为,国际发展问题应该纳入更广阔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中。我们在报纸、电视或者学术期刊上所读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民众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其中辍学问题、识字与扫盲进展缓慢、性别不平等、可持续发展、儿童营养不良、教育与暴力冲突等是讨论最多的话题。
最近刚刚发布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2011)——《隐性危机:武装冲突与教育》(The Hidden Crisis: Armed Conflict and Education)记录了武装冲突对教育的破坏性影响。报告考察了迫使学生辍学的诸多反人权的行为。此外,我们经常读到一些令我们内心非常不安的数字。如在发展中国家,1.95亿年龄小于5岁的儿童营养不良问题非常严重,这对儿童的身心发展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此类儿童占发展中国家同年龄段儿童总数的1/3。又如世界上17%的成人缺乏基本的识字技能。但是,让我们更加遗憾的是,国际上对教育的关注度已经有了下滑的趋势。2009年国际教育援助只占世界人道主义援助的2%(GMR,2011)。值得注意的是,21个发展中国家对军事的投入要高于对基础教育的投入(GMR)。这引起了我们的质疑:难道在西方国家的眼中,有利可图的军事贸易关系比人道主义援助或者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发展性目标更加重要?(Smith in Arthur,2011)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辍学或挨饿的人来说,以上列出的数字是非常空洞的。我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与责任,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们只对全球问题有一个模糊的认识,更多的是从吉登斯(Giddens,1990)提出的“非嵌入”(disembededness)或者“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视角去理解。也就是说,作为研究者,我们确实对全球问题非常关注,但是研究者个体与全球问题之间存在着遥远的时空距离。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或者“局外人”,很难将自身置于全球问题之中去把握问题的实质。
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是使用“局外人—局内人”视角进行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默顿通过“局内人—局外人”视角观察美国白人占主导的社会中被压迫的黑人群体以及与文化、社会结构、机会与限制相关的压迫者(Baert,1998)。默顿指出,研究者应该超越自身所在的组织和文化背景观察权力关系。成为一个“局内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成为被研究对象文化群体中的一员,成为“局内人”或者“局外人”主要取决于对研究所在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群体的了解程度。
克莱恩·索迪安(Crain Soudien,2009)把“局外人”、“局内人”概念和南非前殖民主义历史结合在一起。他把“局外人”概念与理性和个人主义挂钩,把“白人”霸权与全球话语范围内的权力与压迫挂钩。索迪安说:“如今,与‘局外人’概念相关的全球化话语中的权力、等级、种族隔离和他者化的问题饱受诟病,因为在许多人看来,权力与等级将会加快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分裂而非融合。”(Soudien,2009)这些激烈而强有力的观点激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世界。
三、“局内人—局外人”连续统一体
关于这一对概念的已有研究有:
(1)人类学从观察者学习不同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社会学则从权力关系的动力、治理、获得社会流动机会的视角进行研究;(2)心理学对群体行为和人际互动进行研究,尤其重视文化间研究;(3)哲学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个人、自我、现象学与自反性等术语。
以上研究都通过教学、学习、科研方法论等多样化的形式对学生、教师和学习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产生影响。
但是作为独立的学者或者研究者,我们通过何种途径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很少会通过对立的概念来研究教育现象。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局内人”或“局外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也不是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并列的两个概念。从个体角度来说,作为“局内人”会让人感觉非常舒服,会自然地形成一种归属感,而如果作为“局外人”,则意味着不能很好融入研究对象群体。另一方面,一个人可以是“局内人”,同时也可以是“局外人”。但是,圈内群体可以使用的权力范围有时超出想象,就像“局外人”有时也可以成为掌握权力的压迫者。陌生人则不会真正成为圈内的一分子,也就是“局内人”,他们只是旅行者、新来移民或者努力成为“局内人”的定居者。不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有权力将陌生人驱逐出群体,也可以把徘徊在群体边缘的陌生人吸纳进来。
在英国教学环境中,“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概念一般通过与语言和文化相关的多元文化教育来理解。刚来英国的移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但当他们学会英语以及认同英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后,就成为了“局内人”。多元文化教育学与跨文化教育学的概念有明显差异。多元文化是指不同文化群体共同生活,他们有相同的权力和特权。而跨文化教育学尝试在文化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以促进社会和谐和多样性。在英国,具备会说英语的能力仍然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并且对期望在语言种类多样的英国永久居住的移民来说是一个障碍。在英国伦敦的学校中,学生每天使用的语言超过300种,说得较多的语言有孟加拉语、吉吉拉特语、旁遮普语、粤语、中国普通话和闽南语等。
如今,每年有50万国际学生来英国留学,中国是英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2008~2009学年有47,000名中国学生来英国留学,紧随其后的是34,000名印度学生,而德国学生只有14,000名(HEFCE,2011)。几乎所有的学生在英国完成学位后就选择回国。
顾、施韦斯弗思和戴(Gu,Schweisfurth & Day,2010)对在英国留学的国际学生的留学体验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绝大部分留学生在经历了最初的文化适应期后,都能较好地适应英国文化和学业生活。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过没有归属感以及在两种文化间游走的感受。一个学生说道:
我有两套文化价值观:一套价值观用于英国,一套价值观用于中国。我认为这两种价值观都很自然地在我身上体现出来。我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当我回到中国后,我就会变成我来英国之前的样子。但是英国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一个过客,而过客就意味着弱势。
一个在中国居住很长时间的英国研究者也写了一段话:
当我审视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时,我把自己看做是英国的“局内人”,中国的“局外人”。然而,在中国,我逐渐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我非常努力地尝试理解中国文化,观察中国的社会习俗。我非常喜欢中国,和我共事多年的中国人把我当做是半个“局内人”。但是现实是什么?现实又在哪里?(Hellawell,2006)
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调查了移民美国的陌生人现象。他用象征主义描述了一个新来者在来到一个新国家后作为一个陌生人、边缘人、旅居者和中间人之后经历的不同阶段。他写道:
这里讨论的陌生人有两类,第一类是今天来明天就走的游荡者,第二类是今天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出于好奇等原因,选择留下来的人。(Simmel,1958,p.509)
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看似是陌生人,但我们并非四处游荡、居无定所的陌生人。由于我们自身的优势或者经验,我们选择留下来,开始去认识和理解彼此。全球化和科技力量正在使这一过程变得轻而易举。
在网络问世之前,比较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贝雷迪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一个人如果不具备以下条件,是不能进行比较研究的:(1)对研究对象国进行充分地调查和了解;(2)在研究国家居住很长时间,并学习该国家语言。在贝雷迪看来,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全身心为研究工作做准备。因此,游荡者不会一直是一个“局外人”、边缘人或者旅居者,与研究国进行多年的磨合后,游荡者将会成为“局内人”,只有在这个时候其才会有资格进行比较研究。显然,此种研究方式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非常奢侈而且难以实现的。
考基拉·罗伊·卡特娅(Kokila Roy Katyal)和马克·金(Mark King,2011)描述了其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多年的经历和感受。在香港,他们可以称自己为“局内人”,因为他们非常熟悉香港的生活,同时他们也是专业研究领域的“局内人”。然而,他们两个人都不是中国人(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美国人)。他们在香港这座西化城市中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工作,但是香港居民的社会文化态度又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个案的背景环境是中国传统文化占主导的香港学校。因此,卡特娅和金的西方价值观使他们难以准确理解儒家文化中的领导和管理内涵。
许多学者赞赏超越文化背景的深度个案研究,在这些个案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的是细节性的内容和具体的比较性反思,并勇于对“局内人—局外人”视角提出挑战(Crossley,Vulliamy,2006)。研究者之间尽管存在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但他们可以分享同为教师的职业兴趣与经验。作为个体研究者或者在与“局外人”或“局内人”组成的研究团队中进行研究时,他们可能更多关注研究所发生的国际与国内的历史背景,以更好地推进研究进程。
四、共享价值观与共同关注之事
作为研究者,我们与一个或多个国家建立工作上的跨文化或文化间合作关系的机会不断增多。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大学学者争取大笔跨学科和跨国研究资助经费的压力同样很大。此种科研任务要求研究者使用新的模式和知识框架以迎接新的挑战。我最近参与了一项欧洲资助的科研项目,该项目涉及14个不同的国家。因为多样化的工作语言会降低研究团队的科研效率,所以项目合作者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此外,对专业术语的准确解释非常耗时,并且很难实现。例如"job"和"occupation",甚至是"profession"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都有不同的含义(Arthur,Little 2010)。在参与国际发展问题中采用“北—南”视角逐渐被看做是提升研究能力和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改善科研对政策与实践的影响的潜在因素(Barrett et al,2011)。全民教育目标可能在2015年会部分实现。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讨论进而更新对“局内人主义”和“局外人主义”的认识。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要求“局内人”和“局外人”用全新方式共同研究的全球化智力环境中,在不同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中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一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同时又会对未知的冒险非常期待。
因此,在此种环境下,作为一个“局内人”或“局外人”,与我们不断增进的专业知识、学术水平、已有经历和成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有很大关系,也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如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和所经历的事情有关。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点。
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够与被研究者感同身受,也就是“共情”。这一状况的达成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亲疏远近关系不大,最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够尝试理解他人或者不同的文化背景。此外,很普遍的一种情况是,在研究过程中,同一个研究者能够不只是在一个“局外人—局内人”统一体中游走(即指有时是“局内人”,有时是“局外人”——译者),还可以同时作为“局外人”和“局内人”。(Hellawell,2006,p.489)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共情”。“共情”是指能够认识和共享他人所经历的想法或感受。作为教师,我们会对学生的需要感同身受。作为国际比较教育学者,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不同文化体间搭建桥梁,充当媒介,在局内和局外之间建立不同文化间的意义。作为教师,我们可以同时在教学环境的内外。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同时在调查事物现象的内外。我们在做研究时需要远离,同时又要沉浸其中。当我们在思考环绕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时,我们既不是纯粹的旁观者,也不是纯粹的参与者。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已经不允许简单事物的存在。比较教育研究者的任务是不断适应愈加纷繁复杂的研究背景和问题,同时还要坚守住内心恒久不变的力量(如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对全球教育问题的关注),因为这些力量是我们坚持进行研究的基础。作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比较教育研究者来说,我们能够达到的是互相理解和共享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用哈贝马斯(Habermas,1984)的话来说,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达成理解,而且要达成共识。我们需要在对彼此的信任中寻找有共同意义的知识和价值观。这是国际比较教育中一种特别的力量——也是我们研究者真正应该为之着迷、为之痴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