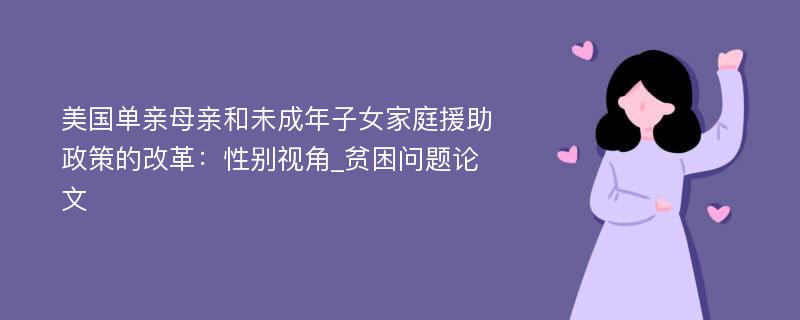
美国单身母亲与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政策改革——社会性别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性论文,美国论文,视角论文,子女论文,单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妇女与福利国家关系议题 传统的社会政策研究将福利国家作为一个性别中立的概念,忽视妇女及其妇女运动对社会政策构建的影响,也无视社会政策带来的性别分层效果。这种性别盲视的倾向在1990年代得到彻底地扭转,形成了社会政策研究的性别视角。从此,妇女与福利国家的关系议题成为社会政策研究的三大重要版图之一。它将性别——家庭议题作为影响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因素,分析妇女的社会政治活动对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探讨福利国家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性别角色关系及其不平等、单亲家庭的贫困等问题产生的直接效果。[1]换言之,性别视角的社会政策研究将性别作为自变量,考查妇女及其组织化运动对社会政策的推进与社会福利模式的塑造作用,或将性别作为因变量,考查社会政策对性别关系及其角色分工的影响。从美国的实践来看,社会政策与妇女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紧密且双向的互动。一方面,妇女关于社会权利议题的斗争无论失败还是成功,都对社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社会政策项目对女性尤其是单身母亲的就业状况、贫困率产生了直接影响。为了清晰地勾勒美国社会政策与妇女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其最重要的社会福利制度——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政策(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以下简称AFDC)为例,讨论这一社会福利项目与贫困单身母亲的关系,并分析199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福利改革中,以贫困家庭临时救助政策(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以下简称TANF)取代AFDC,对贫困单身母亲就业状况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及这一转变的社会性别意义。 二、AFDC的建立及其社会性别意义 在美国社会政策体系中,AFDC是历史最悠久的社会福利项目,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的母亲津贴(Mother Pension)。同时,它也是美国最重要的社会救助项目,对维持贫困家庭的生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与实施AFDC是为贫困单身母亲抚养未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虽然减少不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是社会福利制度追求的理想目标,但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这一社会政策项目从满足单身母亲被赋予的母亲、家庭主妇、儿童照顾者的角色出发,只是对她们照顾未成年子女给予经济支持,在一定的意义上只是促成她们实现并继续实现既有性别角色要求,完成传统角色的生产与再生产。因此,AFDC成为巩固既定的男女角色模式和扩大现实的男女性别差异的制度性安排与政策模式,具有鲜明的性别化(gendered)特征。 (一)从母亲津贴到AFDC 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核心家庭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家庭结构类型,而男主外、女主内是其典型形式。对于那些因为战争、工伤或其他意外事故导致男性家长死亡或者长期缺席的妇女来说,失去了丈夫就意味着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会直接影响到自身及其子女的生计维持。1909年1月,在白宫第一届儿童会议上,联邦政府主张各州制定母亲津贴法,以支持丧偶的单身母亲抚育其子女。1916年,密苏里州制定了第一部寡妇年金法。这一法案规定,对丧亡服役人员未再婚的妻子及其未成年子女,由地方政府提供现金补助。在1911~1920年间的“进步运动”中,由于改革者、妇女组织及其政治联盟的共同推动,全美所有州都推行了寡妇年金制度。1921年11月,作为第一部联邦政府福利项目,《谢泼德·托纳母婴保护法案》(Shepard Towner Infancy and Maternity Protection Act)在国会通过,标志着联邦政府建立了美国最早的社会福利项目——母亲津贴。[2]它要求州政府对失去男性养家者的寡妇或者丈夫长期不在家的妇女提供经济援助,使她们能够继续抚育未成年子女。 母亲津贴成为美国现代社会政策的第一个组成部分,为AFDC的创建提供了准备。相对于欧洲大陆先进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来说,美国社会政策的建立不仅严重滞后,更重要的是,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社会保险制度优先保护男性为主的劳动者,美国残补式的社会福利制度首先考虑保护贫困的单身母亲及其儿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达·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认为,1920年代,美国建立了母系主义的社会政策。[3] 保护贫困母亲及其未成年子女不仅是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源头,也是美国社会福利体制建构和扩张过程的重要内容。1935年,在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联邦政府颁布了《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奠定了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法案的Title Ⅳ中引入了“儿童救助”项目(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以下简称ADC),授权州政府以现金支付的方式给贫困母亲及其子女提供公共援助,它要求联邦政府给州政府提供资金以帮助贫困单亲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联邦政府根据州政府提交的用款计划,由议会授权财政部门拨款,最初的拨款需达24 750 000美元。[4]它还规定,由州政府的公共福利部门负责管理贫困家庭及其儿童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服务,这标志着对贫困母亲及其子女的福利工作从私立志愿性转向政府公立性。1962年,ADC更名为AFDC,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拨款对因丧偶、离婚、分居、遗弃等原因导致家长长期缺席的贫困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给付经济援助和福利服务传递。 (二)从社会性别视角看AFDC AFDC的建立,表明美国政府对妇儿福利领域的干预力度大大增强,家庭领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领域,而是受到政府干预和影响的公共领域。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最重要的机构和儿童照顾的主体,AFDC体现的政府干预必然影响到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分工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总体来看,AFDC及其前身是一个具有强烈性别化特征的社会政策项目。从政策预设、文本及其实施上看,它将贫困的单身母亲及其未成年子女作为目标群体,强调这一社会福利项目是资助贫困的单身母亲抚养其未成年子女。 首先,在政策预设上,无论是母亲津贴,还是AFDC,都假设一个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工作的人(主要是男人)和不能工作的人(包括女人尤其是母亲、身体残障者)。假定参与社会性劳动的男性才是有经济能力的养家糊口者,当一个家庭没有男性家长时,因为母亲无法从事有酬劳动、无力抚养未成年子女,所以政府才扶助她们照顾未成年子女。AFDC理所当然地将母亲作为天生的家庭照顾者,强化了女性的照顾者角色。更进一步,无论是母亲津贴,还是ADC或AFDC,都不是直接针对单身母亲的贫困问题,而是针对贫困的单身母亲如何抚养未成年子女的问题,政策设计的目标和理念是帮助贫困单身母亲抚养未成年的子女,使其顺利承担母职。 其次,在政策规定上,AFDC及其前身ADC主要是针对贫困的单亲家庭,尤其是女主家庭。《社会保障法案》第406条款将失依儿童(Dependent Children)定义为失去父/母抚养的儿童,包括父/母死亡、长期离家或者身心残障。除非母亲死亡或者残疾,母亲的优先抚养权使得未成年子女多由母亲抚养,这预示着ADC及其之后的AFDC目标群体基本是贫困的单身母亲及其未成年子女。 第三,在政策实践中,AFDC及其前身ADC将贫困的双亲家庭排斥在给付范围之外,并为了控制福利津贴支出,限制受益对象是没有父亲的儿童及其抚养人。[5]作为社会救助项目,所有ADC或AFDC申请者必须通过严格的资格审查。1950~1960年代早期,一些州将合适的住所和同居男性作为资格审查的条件,采取半夜突袭的方式检查申领救助的贫困母亲是否有同居男伴,认定无关男性的存在使家庭不适合儿童居住,其经济需求也不存在。1960年,路易斯安那州以此为借口终结了6281个个案,涉及23 549名儿童。[6]4-5直到1960年代末期,这些限制性的资格条件才因与侵犯隐私的宪法性条款相冲突而得以废除。毋庸置疑,这样的资格条件和甄别机制具有鲜明的标签化特征和耻辱化效果。 AFDC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责任完全归于单身母亲,将儿童的家庭照顾等同母亲照顾。尽管这一政策对缓解单身母亲的贫困状况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主导的价值理念不是帮助妇女实现解放和追求性别平等,不是打破而是强化既定的性别角色分工,不是缓解而是巩固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既有地位。可见,这一社会政策项目不是性别中立的,而是深深隐含着父权主义假设和男女不平等的性别观念。 三、AFDC与贫困的单身母亲 196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婚育模式的变化、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和未婚生育率的上升,美国出现了大量女主家庭(female—headed household),其贫困问题也不断凸现。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贫困家庭中,女主家庭占大部分,她们不得不依赖AFDC津贴维持生活。 (一)美国单身母亲的贫困问题 在美国家庭结构形式变迁过程中,女主家庭数量不断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1974年,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单亲家庭占17.4%,女主家庭和男主家庭分别占15.7%、1.7%;1996年,单亲家庭所占百分比上升到了29.6%,包括24.1%的女主家庭和5.5%的男主家庭。[7]1这意味着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有近四分之一是女主家庭。单亲家庭的大增与婚育模式的转变有关。美国总人口的结婚率从1950年的11‰下降到1996年的8‰t,而离婚率则从2.6‰上升到4.6‰。[8]同时,婚外生育大量出现。在1962~1996年间,15~44岁的已婚女性生育率从150.8‰下降到82.3‰,而同一年龄组未婚女性生育率从21.9‰上升到43.8‰。非婚生儿童所占比例也呈明显增长态势。1962年,非婚生儿童只占5.9%,而1996年这一比例高达32.4%,这意味着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儿童是非婚生儿童。[9]概言之,离婚率的上升和非婚生育的蔓延导致单亲家庭的数量和比例大大增长,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近三分之一是单亲家庭,而在单亲家庭中,近80%是女主家庭。 美国女性的贫困化首先表现为单身母亲的贫困。事实上,贫困不是个人特征,而是由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的家庭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单身母亲的贫困是女主家庭的贫困,它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贫困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以1996年为例,美国人口普查局“当前人口报告”(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显示,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41.9%的女主家庭是贫困家庭,远远高于双亲家庭7.5%的贫困率,也高于男主家庭20%的贫困率。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6 131个贫困家庭中,双亲家庭占32.0%,女主家庭占61.3%,男主单亲家庭占6.7%。[7]8见,女主家庭是抚养未成年子女贫困家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二是在1960~1996年期间,女主家庭的贫困率一直高居不下,保持在40%~55%左右的高位[10],而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贫困家庭中,女主家庭所占比例从28%上升到了60%左右[11]。 大量的研究将贫困问题与女主家庭联系在一起。韦茨曼(Weitzman J.)在《离婚革命》一书指出,离婚后妇女与子女的生活水平平均下降了73%,而丈夫提高了42%。[12]一些研究表明,女性在成为单亲后经济状况恶化或陷入贫困的概率明显高于男性;与健康稳定的双亲家庭相比,单亲家庭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照顾的双重压力,更容易陷入失业困境,在经济安全、社会与心理支持和儿童照顾上面临着重重困难,尤其是女主家庭。[13-14]未婚生育的少女妈妈更是面临着中断学业和职业培训的风险,甚至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成为备受谴责的底层阶级。[15]因为很多单身母亲的工资收入非常微薄,公共援助成为她们重要的经济来源,虽然美国还有相对慷慨的遗属保险,但主要是支付给寡妇。因此,对大多数的女主家庭来说,AFDC及其之后的TANF是她们能够得到的最主要的政府现金援助。 (二)AFDC最主要的领取者——贫困的女主家庭 为了扶助贫困家庭抚养其未成年子女,政府在AFDC这一社会福利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根据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DHHS)的统计数据,1962年,联邦政府对AFDC支出和管理投入7.8亿美元,1994年则达到141.92亿。在1970~1994财年期间,AFDC津贴总支出从40.82亿上升到227.97亿。[16]总体上,在1962~1996年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AFDC上的支出一直保持明显的上升趋势。 AFDC支出的持续上升,不是由于津贴水平的提高,而是因为领取者人数的高速增长。1962年,享受AFDC津贴的家庭数是92.4万个,领取者总人数达到359.3万个;而在1994年,受助家庭数上升到504.6万个;领取者总人数达到1 422.6万个,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贫困女主家庭已然成为AFDC最主要的给付对象。1962~1994年间,单亲家庭领取者的数量从87.6万个上升到468.3万个。以女主家庭为主的单亲家庭一直在AFDC津贴领取家庭中占绝大部分,其占比高达90%以上。[17]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女主家庭一直占AFDC津贴给付对象的大多数,但早期的领取者主要是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寡妇家庭,而1960年代以来,因离婚、分居、未婚生育的单身母亲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贫困女主家庭成为AFDC津贴的主要领取者。 (三)AFDC遭到批判 1962~1996年间,虽然政府在AFDC上的支出不断增长,但单亲家庭的贫困率仍然稳步上升。在一定的意义上,AFDC并没有改善而是滋长了单身母亲的贫困状况。因为AFDC不能给贫困家庭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持,这种事后补救型的社会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虽然AFDC及其前身ADC有利于维持贫困单身母亲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共同生活,但其潜藏的福利意识形态鲜明地体现了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强化,因为它将母亲角色直接定位为儿童照顾者,强化了妇女的传统性别角色。保守主义者指责AFDC冲击和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间接鼓励男性家长放弃养家糊口者的责任,最终导致家庭的解体和功能的弱化,助长了单亲问题。[18] 以贫困单亲家庭为主的AFDC领取者备受非议,单身母亲更是被打上了耻辱化的烙印,被贴上了双重标签:一是不工作,不参加劳动力市场;二是不结婚和不道德的婚育行为。在强调工作伦理和个人独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和保守主义福利意识形态下,那些领取津贴的单亲家庭被视为不劳而获、不负责任、独立意识薄弱的福利依赖者,长期领取AFDC津贴的单身母亲被称为懒惰、放荡的“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以贫困的单身母亲为主的AFDC津贴领取者积极参加劳动力市场、依靠工作收入以脱离福利、实现自立,成为AFDC及其改革的重要取向。 四、AFDC改革——从福利到工作 作为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范式的典型代表,美国的社会政策强调市场对个人福利的作用,相信市场是个人福利最重要的来源,鼓励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因此,美国的劳动力去商品化程度在OECD的18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位。[19]52美国主流的福利意识形态强调新教主义的劳动天职观和个人主义的独立精神,而不是集体主义的互助互济。这些使得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尤其强调工作福利(workfare),并贯彻与体现在AFDC及其改革中。 (一)AFDC中的工作要求与工作刺激 工作要求与工作刺激计划一直伴随着AFDC及其转变,并成为这一福利制度的重要内容。在AFDC的实施过程中,将愿意寻找、接受工作或职业培训作为待遇给付的前提条件,同时,通过工作激励方案,推动与维持工作积极性。1962年,联邦政府要求,AFDC津贴接受者如果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职业登记、职业培训或职业介绍,就要从福利名单中清退。对于抚养6岁以下学龄前儿童的母亲,鼓励她们自愿参加职业登记并接受职业培训和其他支持性服务。[20]同时,议会授权拨款支持“社区工作和培训”项目(Community Work and Training),给AFDC津贴领取者提供免费培训和就业服务。它规定,所有年满18周岁的受助对象必须参加这个项目,参加社区劳动也可获得与同类工作相当的工资。为了维持工作积极性,使福利领取者不因工作带来家庭收入的提高而丧失领取津贴的资格,在家庭财产状况调查计算家庭收入时,扣除与工作相关的支出,如上下班交通费用、工作所得税等,还扣除为满足未成年儿童潜在需要的储蓄,如入托、教育和医疗费用等。 AFDC在给贫困的女主家庭提供必要经济支持时,也要求和激励单身母亲参加工作,推动她们从依靠福利转向依靠劳动力市场。历届美国政府都将AFDC项目与工作联系在一起。1968年,议会要求各州政府建立《工作刺激法案》(Work Incentive Act,简称WIA),由健康、教育与福利部和劳动部通过州政府福利部门和就业服务部门共同管理。一是要求所有的单身母亲必须参加《工作刺激法案》规定的就业和培训登记,只有抚养6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可以豁免。二是加大工作刺激力度,即在家庭财产状况调查时,工作所得的第一个30美元及其剩余的三分之一都不计入家庭收入内。[6]52这意味着,只要总收入不超过150%AFDC基本津贴,加上30美元,加上150%工作相关支出,就不会丧失领取津贴的资格。 1980年代,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泛起,大力鼓吹市场的作用,批判全民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能力,助长了依赖性。此间,关于单身母亲与福利依赖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引起了学界和公众的持续关注。保守主义者甚至颠倒单身母亲与福利之间的关系,认为慷慨而宽容的福利抑制了她们的工作动机,甚至诱导她们追求依赖福利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话语背景和削减福利开支的压力下,里根政府大力推行从福利到工作(welfare-to-work)的工作刺激项目。1981年,议会授权州政府资助津贴领取者找工作,在“社区工作经验项目”(Community-Work Experience Programs,简称CWEP)中,为她们提供工作救济(work relief)和工作补贴(work subsidy)。在家庭财产调查时,头四个月的工作收入不计入。1988年,《家庭支持法案》(Family Support Act)取代《工作刺激法案》,推行“工作机会和技能培训计划”(Job Opportunities and Basic Skills Training,简称JOBS)。联邦政府要求各州尽其所能地推动3岁以上儿童的母亲参加教育、工作或者培训,这意味着只有3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可以赦免,这是社会立法第一次要求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必须工作。[20]总体上看,伴随AFDC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刺激方案,旨在推动包括单身母亲在内的津贴领取者积极参加劳动力市场,以最终结束福利依赖,实现经济自立。 在工作要求的推动和工作刺激的激励下,申领AFDC津贴的单身母亲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有了一定的提高,工作加福利成为她们维持生计的基本模式。1968~1979年间,对女主家庭福利依赖的跟踪研究表明,领取AFDC津贴母亲的长期经济来源是福利和工作所得,她们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从事兼职工作,每周的工作时间是5.4小时,微薄的工资收入使得她们无力养家,也无法完全退出福利。[21]虽然她们也有工作的意愿,但自身人力资本的缺乏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分化使得她们难以找到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二)工作福利——从AFDC到TANF 1990年代中期,降低福利开支、结束福利依赖成为美国社会政策改革与重组的重要目标。1994年的《福利指标法》(Welfare Indicators Act of 1994,简称WIA)明确指出,促进依赖福利转向依赖收入。1996年8月22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福利改革法》(Welfare Reform Act,简称WRA),即《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简称PRWORA)。在这个法案下创建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取代了实施60余年的AFDC,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废除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部分条款的一次。TANF旨在推动职业培训、就业和婚姻,强调从福利到工作,要求福利接受者积极参加劳动力市场,通过工作收入实现生活自立。 TANF中的工作要求条款对州政府和受助者提出了明确规定。一是州政府必须大力推动津贴领取者参加工作,使其工作参与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具体来说,1997~2000财年间,单亲家庭的工作参与率要从25%上升到50%,双亲家庭的工作参与率要从75%上升到90%。二是要求津贴领取者在受助期内必须工作或者寻找工作,否则就减少津贴水平。它规定,双亲家庭每周的工作时间不低于35小时,单亲父母每周的工作时间或参加职业培训的时间不低于20小时,少女妈妈要通过受教育来折抵工作时间;对抚养不满3岁儿童的单身母亲,是否豁免工作要求,或者抚养不满6岁儿童且无法找到托儿机构的单身母亲,是否放宽工作要求,由州政府自行决定。[6]57总体来看,TANF的工作要求更加严厉,更强调工作福利。 TANF的工作要求带来了双重性的效果。一方面,领取津贴的个案数量大幅下降,成年女性的工作参与率大大提高。2001年,TANF的个案规模比起1996年的AFDC领取者数量降低了56%,比1994年高峰期下降了63.2%;同时,单身母亲的就业率从1995年的64%上升到2000年的75.5%,女主家庭的贫困率从42%下降到28.5%,儿童贫困率从22.2%下降到15.6%。[6]59另一方面,工作和家庭照顾的双重压力使得一部分单身母亲更容易陷入失业或贫困境地。研究表明,将单身母亲在TANF前后的经济状况进行对比发现,相当规模的女主家庭比起她们依赖福利时生活更加贫困,在退出TANF的女主家庭中,贫困率高达50%以上。因为在TANF严格的给付资格和领取条件下,一些单身母亲虽然走进劳动力市场,但她们所从事的工作稳定性差、报酬低,实际收入反而比福利津贴低。[22]总之,TANF取代AFDC后,虽然贫困单身母亲的就业率有一定上升,但那些无法正式就业或者工资收入低下的单身母亲处于一种更加边缘的地位。 (三)工作与福利——两难困境中的贫困单身母亲 AFDC及其改革后的TANF对美国贫困女主家庭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的社会政策。第一,推进工作结束福利依赖的政策,假设如果有工作就有收入来源,则能实现经济独立,则无需福利支持。这忽视了贫困的单身母亲有强烈的工作意愿,不是她们不愿或者不想工作,而是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机会和就业质量方面有现实的障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她们只能参加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低劣的非正式工作、兼职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作穷人”。[21]她们缺乏的不是工作动机,而是缺少足以维持家庭开支的工作机会。第二,政策实践表明贫困的单身母亲面临工作和家庭照顾的两难困境。一方面,AFDC及其后的TANF潜在地强化了单身母亲承担儿童照顾者的性别角色;另一方面,又推动单身母亲积极参加劳动市场,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这意味着要求单身母亲兼任母职和父职。她们在家庭生活和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母亲、儿童照顾者与养家糊口者、劳动者这一双重角色的矛盾之中,承受着家庭照顾的重任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压力。第三,工作福利是以男性为参照标准,以与男性无差异的单一就业形式来判断单身母亲的就业状态,将女性等同于男性,忽略了男女的差异和性别角色的实际处境的差异。对于贫困的单身母亲来说,依靠福利会带来耻辱标签,但工作又意味着自己无法全力照顾家庭,由于缺乏普遍性的公立儿童照顾体系,参加工作的单身母亲不得不承担高额的儿童照顾支出。在一定意义上,从AFDC到TANF的改革,片面强调工作福利,试图将单身母亲从福利领取者队伍驱赶到劳动力市场,忽视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和角色承担上的现实障碍。这无益于单身母亲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更不利于推动性别平等。社会政策应该从重构性别角色、推动性别平等的角度入手,切实改善单身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 五、从社会性别视角看AFDC和TANF 社会性别理论不是片面地强调两性之间的一致,而是从两性之间的差异出发,承认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认同两性的需求、经验以及实际利益也有不同。莫林诺克斯(Moleyneox M.)和摩塞·卡罗琳(Moser Caroline)分别提出了性别利益(gender interests)和性别需求(gender needs)概念,并将其区分为现实性和战略性两类。前者是从妇女地位的实际条件与现实需求出发,在现存的性别角色分工下,妇女因既有的社会角色,如母亲、家庭主妇、儿童照顾者等所产生的实际需求;后者则是从妇女的从属地位以及作为他者的存在方式来演绎的,基于两性关系的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性别分层和劳动的性别分工而形成的需求。[23]现实性别需求和战略性别需求的区分为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AFDC及其之后的TANF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维度。 福利国家将女性作为家庭照顾者,男性作为养家糊口者,使得男性往往享有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相关的社会保险,而女性则不得不依靠具有耻辱化效果的社会救助和选择性的社会福利服务。AFDC即是从基于传统性别分工的现实性别需要出发,旨在协助单身母亲顺利承担传统性别角色——母亲和儿童照顾者的职责,使她们有效完成并继续完成既有性别角色要求。简言之,满足现实性别需求的社会政策项目只是强化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不会提高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能为她们赋权。因此,1962~1996年间,虽然AFDC津贴支出猛增,但抚养未成年子女单亲女主家庭的贫困率及其在贫困家庭中所占的比例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而在这一社会政策影响下完成性别角色再生产的单亲母亲还被标签化为“福利母亲”。 从性别需求的维度来看,社会政策不仅要关注单身母亲基于社会性别分工的现实性别需求,还要满足她们的战略性别需求。应看到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对她们造成的影响,努力改变她们在公民身份上遭遇的社会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的歧视、在性别关系中遭到的压迫。概言之,社会政策不仅要满足单身母亲的现实性别需求,更要满足她们的战略性别需求。第一,要健全公立性的儿童照顾体系,缓解单身母亲遭受的工作与家庭照顾的双重压力。事实上,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不是无力作为或无所作为。“二战”期间,美国为了推动妇女在战争工厂中工作,为学前儿童提供公共性日托服务。但战后,联邦政府停止了对日托服务的财政支持,使得工作母亲不得不依靠价格高昂的私立性托儿服务。而在以瑞典为原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政府通过综合性的家庭福利将儿童照顾和亲职工作的成本社会化,建立庞大的公共部门提供社会服务,不仅为妇女获得有酬工作给予最主要的机会来源,而且为她们将儿童照顾和有酬工作结合起来提供支持。[19]223-224美国单身母亲的经济状况远远低于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的单身母亲,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尚无普遍性的儿童津贴或家庭津贴制度,也没有普惠型的公共性儿童照顾体系,而是一直片面依赖残补性的社会救助制度。[24]第二,要改善单身母亲的工作机会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层。对于包括单身母亲在内的女性而言,劳动力市场参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工作为她们参与社会生活和实现经济独立提供机会和途径,有助于实现男女平等、摆脱福利依赖;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化又是性别取向的,职业的性别隔离通过教育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使得女性在求职时面临累积的障碍,导致女性被分配到工资低的行业和职业中,形成所谓的“女性职业”,或者在给定的行业和职业中,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即“同工不同酬”。这不利于妇女解放和单身母亲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TANF取代AFDC尽管提高了单身母亲的就业率,但忽视了这一群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化,使得单身母亲陷入严重的工作贫困状态。社会政策要从战略性别需求的角度,批判与反思现存的性别不平等结构,挑战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改善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