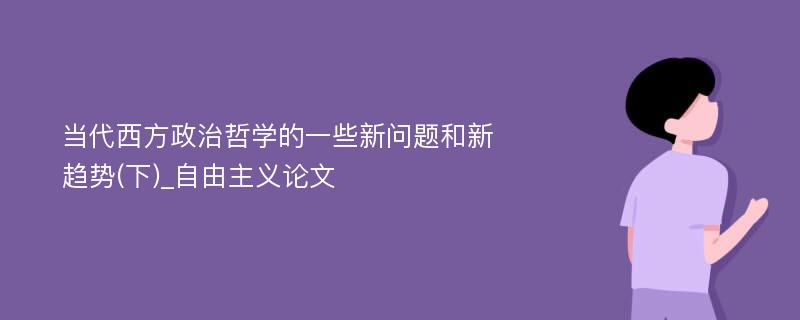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若干新问题和新动向(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问题论文,新动向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中立性和道德
从穆勒(J.S.Mill)到罗尔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正统立场是主张国家对于公民的道德持中立态度,因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本不涉及对个人道德的探讨和争论。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权力的起源和界限,明确区分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强烈主张国家不干涉个人生活。穆勒的学说有明显的“反至善论”(anti-perfectionism)倾向,认为政府不能运用自己的权威来使公民在道德上完善。罗尔斯的《正义论》严格区分权利(right)和善(good),要求国家在善的问题上中立。他的《政治自由主义》更是极力避免所谓的“完备性学说”,即有特定形而上学、道德、宗教内容的学说,主张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来源于不同人群的“交叉共识”。德沃金把中立性原则表述得最明确,他认为立法者“对于那些可以称之为美好生活或什么东西使生活有价值的问题,必须保持中立。因为一个社会的公民对于什么使生活有价值具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政府对一种看法的喜好超过另一种——不论是因为政府官员认为其中一种本质上更优越,还是因为更多的人或强有力的人群主张其中一种——政府都是没有将公民作为平等的来对待”。(注:Dworkin,R.,1985,p.191.)
社群主义兴起之后,对自由主义的中立性原则进行了猛烈批判,作为回应,自由主义者开始重新思考中立性问题,重新探讨自由与道德生活的关系。
一种思路是重新理解和阐释自由主义传统,认为它没有主张或不应该主张中立性,它本身包含了道德倾向性和内容。比如马塞多在《自由主义的德行》中认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看,中立性是幻想,自由主义在坚持以自由为核心,坚持正义的优先性的同时,完全可以提供关于社群和美德的主张,特别是自主(autonomy)这个概念,它在各种生活理想中具有普遍性。(注:Macedo,Stephen,1991,p.234,p.263.)帕特里克持相似的观点,认为罗尔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没有充分表达自由主义精神的丰富性,应该看到,中立性并非国家可以达到的目标,而自主本身就是善,它的作用很大。(注:Patrick,Neal,1997,p.4.)布林克主张,自由主义理论家应该承认他们的学说对于什么是美好生活并不是中立的,这些学说实际上促进了个人自主和多元主义的理想,并与其他理想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自由主义不能靠中立性来回避和克服冲突,而应公开偏向某些道德观念。(注:van den Brink,Bert,2000,p.5.)
在自由主义者的回应中,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三人的观点,这些观点代表了对传统的偏离,被视为一种新动向。
约瑟夫·拉茨在坚持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同时反对中立性原则,赞同至善论。他认为,政府的责任之一是促进道德,虽然一般说来自由主义者警惕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是对的,但同时应该看到,政府也可能是自由的源泉,它可以创造条件使人得到更多的自由。国家对其公民负有一系列义务,它如果未能帮助其公民获得幸福,就是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因此,要想以什么都不做来实施中立是空想。他说,自由主义者强烈地提倡中立性原则,是因为他们把个人自主视为最基本的价值,对强制保持高度警惕。但在仔细分析之后可以看到,自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程度问题,虽然强制常常对人的幸福产生不利影响,但并没有人们通常想得那么严重。应该看到,比起人们经常遭受的罪恶与不幸,强制的罪恶很容易被夸大。另外,为了实现确保个人发展自主生活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有时不能不使用强制。发生在理想的自由国家里的强制和发生在其他情况下的强制有很大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强制可以是真正为了被强制者的利益,甚至可能为他们所希望。他还说,人们反对至善论有一种认识上的深刻原因,即认为至善论会将某种生活方式强加于人。拉茨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可以采取是否鼓励、给予荣誉、增税等等手段,可以通过社会体制作出法律或行政方面的安排来促进某种价值。(注:Raz,Joseph,1986,p.415,pp.18~19,p.124,pp.156~161.)
德沃金的立场在90年代有明显变化,他声称在伦理学的抽象层面上,即对于如何生活的基本立场问题,自由主义不能够也不应该中立。人们可以大力宣传、提出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争取别人采纳同样的价值标准;在适当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对青少年进行家长式的教育,以塑造其正确的道德观。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做,不能靠法律和强力,不能违反他人的意志与信念,不能依伏自己的道德观与多数人一致。(注:Dworkin,R.,2000,pp.238~239,282~283.)他力图为他的平等理论以及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奠定伦理基础,为此,他作了两种区分:一是意欲性利益(volitional interest,主观上想要的好处)和批判性利益(critical interest,使人的生活更美好的东西),二是两种不同的价值模式,效果模式(model of impact,认为生活的价值在于对世界产生的作用和结果)和挑战模式(model of challenge,价值在于对生活与环境的挑战作出技巧性的回应)。他说,追求批判性利益将自然地把人们引导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实践,批判性利益意味着生活中的挑战模式,接受这个模式就必然会坚持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平等标准:资源平等。(注:Dworkin,R.,2000,pp.243~245,251~254,277~278.)
高尔斯顿称自己的观点是自由主义的,因为它与自由主义的以下基本立场一致: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坚持个人自由。但他明确地反对中立性原则:“把自由国家理解为‘中立’的是不恰当的,它和任何其他政治社群一样,信奉一种人类善的观点,赞同某些生活方式,抨击某些生活方式。”“不能把自由国家理解为不受限制地表示‘差异’的竞技场,恰恰是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自由主义式的统一性制约着多样性”。他说:“至少有三种理由说明中立性主张不能成立。第一,它代表了对于洛克的观点的深刻误解,而这一观点体现并且要求对于诸如最大程度地减少暴力这类人世间的至关重要的善的实质和重要性的共识;第二,它不符合自由主义政治的现实,这种政治如果不诉诸于对善的理解就难于前进。最后,这个主张不能自圆其说,每个支持它的人都不言而喻地依赖不仅是形式上的和不仅是工具性的善的概念来发挥其主张。”(注:Galston,William A.,1991,pp.3~4,p.8.)
高尔斯顿证明了自由主义的鼻祖如洛克和亚当·斯密是很讲究德行的,还简单地说明了自由主义关于个人道德的一些要素:(1)生命;(2)基本能力的正常发展;(3)实现利益和目的;(4)自由;(5)理性;(6)社会;(7)主观上的满意。至于公共的道德,除了每个政治社群都要求的勇气、守法、忠诚等等之外,他特别分析了自由社会所要求的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道德。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德行是工具性的话,那么有没有非工具性的,作为目的、内在的德行?他的回答是有,这些自由主义的德行是:(1)理性或自我反思;(2)根据责任戒律行动的能力;(3)充分伸张个人性。(注:Galston,William A.,1991,pp.173~177,215~216,228~230.)
五、各种平等理论
在当代,关于平等问题的讨论和争论进行得十分热烈,其核心问题是“什么东西的平等?”(equality of what?)阿马蒂亚·森对此解释说,如果把争论看成是有些人赞成平等,有些人反对平等,就会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各种人——收入平等主义者、福利平等主义者、古典功利主义者、纯粹的自由至上论者都是平等主义者。从某个方面出发的平等,从另一个方面看可能就是不平等。比如,诺齐克(R.Nozick)主张权利平等,就会产生结果的不平等。森还进一步解释说,“什么东西的平等”会成为核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1)人类的多样性,勤快的人和懒人报酬一样,对前者就不公平;(2)判断平等的相关空间的多元性,比如有收入、健康、功用、自由、基本物品、能力等不同方面的平等。(注:Sen,Amartya,1999,p.iv,p.129.)
罗尔斯和德沃金主张的平等观是资源的平等(equality of resources)。罗尔斯的《正义论》中的两个正义原则具有很强的平等主义含义,他认为人们应当平等地占有最基本的资源,他将其称为“起码的好处”(primary goods,中译本为“首要善”),包括自由、自尊、个人权利、机会、职位、收入等等。他的差异原则把人生而有之的才能都视为社会共有的资源,认为有才能的人不应由此得到好处。另一种平等叫幸福的平等(equality of welfare或equality of well-being),这里说的幸福,指人们成功地满足了自己的喜好、目标、抱负,实现这种平等,就是把资源分配和转移到这种地步,使得人们在这方面没有差异。德沃金批评了这种平等标准,他主张的资源平等,即每个人都得到相等份额的东西。他说,要满足有奢侈爱好的人的幸福感,需要耗费超常的资源,这对只有平常爱好的人是不公平的。爱喝啤酒和爱喝香槟酒的人要得到同样的满足,花的钱会大不一样。(注:Dworkin,Ronald,1981,What Is Equality? Part 1:Equality of Welfare,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0,No.3; What Is Equality?Part 2:Equality of Resource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0,No.4.)
阿马蒂亚·森说,他深受罗尔斯的影响,但认为罗尔斯的关注点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拥有同样多起码好处的两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能力去追求他们各自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因为由于主观和客观情况不同,人们把起码好处转换为幸福的能力是不同的。设想一个孕妇和一个同龄男子在收入和其他基本好处方面完全相同,但孕妇应该对营养、住房等条件有特定的额外要求,而这个男子则不是非如此不可,所以从相同条件出发,他们最终的幸福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关心的是最后结果,而不止是为达到结果的条件和手段。比如,重要的是人的营养状况,而不是人们有多少食物可吃;重要的是人们学到了多少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家长或政府把多少钱用于孩子的教育,特别是如果不顾效果大手大脚花钱的话。所以,森主张用能力(capability)来代替资源、机会、收入等等作为衡量平等的标准。(注:Sen,Amartya,1999,pp.8~38.)
阿尼松认为,不论是用幸福,还是用资源,以及用其他概念来作为衡量平等的准则,都有缺点。他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森的看法,他说,确实,人们把起码的社会性好处转化为他们最珍视的东西的能力和效率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关心大家应当得到相同份额的资源,不为别的,是我们要考虑他们用这些资源份额去做什么,这些资源能使人是什么。他提出自认为是最恰当的概念,即“对于幸福的平等机会”。假设人群之中的每个人都与别人同样地面对一系列选择,每种选择的结果是对不同喜好的满足,作出一种选择并得到一种结果之后,当事人又面临一系列选择……如此等等,这就形成了一棵决定之树,它给出了一个人可能的、完整的生活史。如果每个人都面对相同的决定之树——即每个人最佳、次佳……直至第n佳的选择都是相同的,而且,如果后来出现机会不平等是因为人们的志愿选择或行为疏忽因而要由个人负责任,那么在这些人之中就实现了对于幸福的平等机会。(注:Arneson,Richard J.,1989,pp.77~91.)
科亨在很大程度上赞同阿尼松的“对于幸福的机会平等”观,但认为它对人们并非有意造成的不利或不平等注意不够,所谓并非有意的即是并非当事人选择因而应当负责任的。此处,他认为“好处”(advantage)这个词比“幸福”(welfare)更宽泛和恰当,所以他把自己赞成的观点叫作“对于好处的平等机会”或者“平等得到好处的机会”(equal access to advantage)。他设计了一个颇为奇特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反驳其他平等观。设想一个人有双重不幸,首先,他两腿瘫痪,按平等主义原则,应该补偿他一架轮椅。给他轮椅仅仅因为他是残疾人,而没有考虑他的幸福量减少了多少,这就驳斥了“幸福的平等”观。又假如这个人天性乐观,知足长乐,人们没有理由说他有许多机会幸福而不给他补偿,这就驳斥了“对于幸福的机会平等”观。再假设这个人有一种怪病:他的双臂可以像其他人那样活动,但动了之后会剧痛,需要昂贵的药物,按平等主义原则,应当无偿地给他提供这种药物,这就驳斥了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观,因为德沃金只是认为残疾人不能行动可算作资源缺乏而应得补偿,而这个人是可以活动手臂的。按照科亨的标准,这个人的两种疾患都是他本人不应负责的不利条件,因此他应该得到补偿。(注:Cohen,G.A.,1989,pp.916~920.)
德沃金在回应科亨时说,科亨驳斥资源平等的上述说法是出于误解,他举的例子是典型的资源缺乏的事例,从原则上说当然应该给予补偿。德沃金同时回应了阿马蒂亚·森,森在驳斥资源平等论时举了这样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的代谢水平与常人大不相同,就算他占有同等的资源(食物),他还是会感到饥饿,这并不平等。德沃金说,从理论上说,资源平等会把代谢水平的差异列为个人资源之一,从实践上说,就这种事例进行再分配要考虑多种因素,十分困难。他在评价森的“能力平等”观时说,按照自然的方式理解他的主张,就会看到它与“幸福的平等”观没有区别;而如果按另一种方式理解他的观点,就会发现那不过是以另一种词汇表示的资源平等观。(注:Dworkin,R.,2000,pp.296~297,300~303.)
六、多元论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多元论(pluralism)愈来愈成为政治哲学中的热门话题,并渗透到各个分支学科、各种主题中。比如,针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和再分配平等观,迈克尔·沃尔泽在其著作《正义的诸领域》中提出了一种多元论的复合平等观,认为需要平等分配的社会性好处或利益既不是单一的,也没有一种是主要的,而是有多种;分配正义原则既不止一个,也没有一个是基本的,而是应该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平等原则和标准。又如,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和维尔·基姆里卡在该国种族、语言、文化分歧对立,分离主义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写出了一系列有关多元论、多元文化论和少数民族权利的著作,基姆里卡甚至力图探讨西方的多元化理论和前苏联东欧种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与冲突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注:Kymlicka,Will & Opalski,Magda,2001.)
一般认为,当代多元论最深刻的表述,是由英籍犹太裔思想家伯林在其著作《自由四论》中,尤其是其中的“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作出的。伯林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作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重要区分,但据一些人的理解和解释,对他来说,多元论比自由主义更重要、更基本,自由主义可以从多元论中推导出来。伯林认为人类的价值观和文化是多元的,这指的是,它们各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它们彼此是冲突的,而且我们不可能把它们统合为一个综合的体系,也不可能对它们比较高下,加以排序,列出最优者加以推广,它们是没有公共尺度可以衡量的。
伯林的思想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一位作者所说,道德多元论是伯林著作的核心观念之一。伯林提倡消极自由,是因为他相信多元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他只是坚持个人自由;伯林认为承认个人自由的政治秩序最符合我们道德状况的多元性现实,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自由秩序对差异是宽容的。以下重要哲学家受到伯林的影响,并对多元论的内涵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和发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拉茨(Joseph Raz)、格雷(John Gray)、汉普夏尔(Stuart Hampshire)、卢克斯(Steven Lukes)、拉莫尔(Chares Lamore)。(注:Galipeau,Claude,1994,p.2、58、68、111、168.)
在当代关于多元论的讨论和争辩中,下列问题成了一条主要线索:伯林是否认为多元论支持自由主义,或者,不管伯林如何看,多元论是否支持自由主义?认为多元论与自由主义有一致性是颇为自然的,因为多元强调差异,尊重和保持差异需要宽容——这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因素。另外,各种价值不分高下,意味着不能强制,而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这就直接导向了自由。
但对伯林有全面、深入研究的格雷不这么看。他认为,虽然初看起来有三项主要理由使人相信价值多元论会支持自由主义,特别是与消极自由和宽容相关的方面,但仔细考察之后可以看到,二者不但可能有矛盾,而且事实上冲突不可避免。如果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和秩序以普遍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西方的普遍价值为前提,那么多元论对其有消解作用。如果它的理论基础是特殊主义,它就不会倡导惟一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它把特定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人民,不会说这是惟一合理或最好的,它会说,尊奉某些价值,贬抑某些价值对于现存的、有意义的生活是必需的。说到底,如果多元论成立,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推断:当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其他价值冲突时,人们没有公认的标准证明自由主义的价值更优。(注:Gray,John,1995,pp.151~155.)
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还可以通过中立性问题来考察。人们易于认为,既然不可能在各种文化、价值、生活方式中区分高下优劣,那么国家的态度和政策就只能是在它们之间保持中立,而这正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但这种初看起来顺理成章的观点却遭到一些人的否定,比如纽威说:“我认为多元论和中立性的联姻最好也不过是权宜之计,这种结合很可能没有好结果。多元性是否支持中立性,这是很可怀疑的,在某些情况下,信奉多元论会要求非中立的政策。我还要进一步主张,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诸如拥护宽容,反对书报检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因为拥护中立性而得到伸张。有意使中立性建基于多元论之上的论证可以与一元论的价值形而上学调和。”(注:Newey,Glen,1997,Metaphysics Postponed:Liberalism,Pluralism,and Neutrality,Political Studies,No.XLV,p.296.)
克劳德对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作了长期研究。他曾说,伯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中的主张广为流行,即认为若接受多元论为真,就有理由拥抱自由主义,他认为这是错的。价值多元论并不支持自由主义,也不支持任何政治学说的规范性主张,它并未告诉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价值中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多元论不仅不支持自由主义,而且还损害了它,它总是可以这样发问:为什么不选择非自由主义呢?(注:Crowder,George,1994,Pluralism and Liberalism?Political Studies,No.XLⅡ,p.293,pp.303~304.)克劳德的批评意见引起了伯林本人的反批评,在与威廉姆斯合写的答辩文章中,他们指责克劳德思维混乱,只在极其抽象的层次上进行论证,这种形式的风格无助于讨论问题,应该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层面上,而不是在逻辑可能性方面谈问题,才能使自由主义的弱点和多元论的自我意识问题浮现出来。(注:Berlin,Isaiah & Williams,Bernard,1994,Pluralism and Liberalism:a Reply,Political Studies,No.XL Ⅰ,pp.306~309.)克劳德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他认为从多元论到自由主义的论证有可能成功,比如他的两步论证:(1)多元性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多样性有价值;(2)多样性与自由主义最相适应。(注:Crowder,George,1998,From Value Pluralism toLiberalism,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Vol.3,No.1,p.3、9.)
高尔斯顿在2002年出版的新书《自由多元论》对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多元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作出了全面的阐述。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力量多半得自于伯林所阐发的价值多元论,他的“自由的两种概念”有助于发动价值多元论运动,这场运动在当代已经达到羽翼丰满的程度。他提出,对多元论的理解应把握以下要点:(1)价值多元论不是相对主义,好与坏、善与恶的区别是客观的;(2)没有衡量客观善的共同尺度,它们性质不同,因此不可能对它们区分高下,按优先性加以排列;(3)某些善是基本的,它们是任何有意义的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4)除了极少数基本善,关于个人对美好生活,对公共文化和公共目的的理解,存在广阔的、合法的多样性空间;(5)多元论与各种形式的一元论对立,一元论要么按一种共同尺度把各种善还原为一种,要么把它们纳入无所不包的等级体系。高尔斯顿举出三条理由说明多元论比一元论可取:(1)一元论会导致道德的强求一致与扭曲;(2)人类经验证明,没有一种价值能够完全压倒另一种价值;(3)他在白宫工作(1993~1995年任克林顿总统的国内政策副助理)的经验说明,不存在对面临的选择作衡量和取舍的单一标准。他在这本书中还批判了格雷的观点,认为多元论和自由主义之间有一致关系。(注:Galston,William A.,2002,pp.4~7,48~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