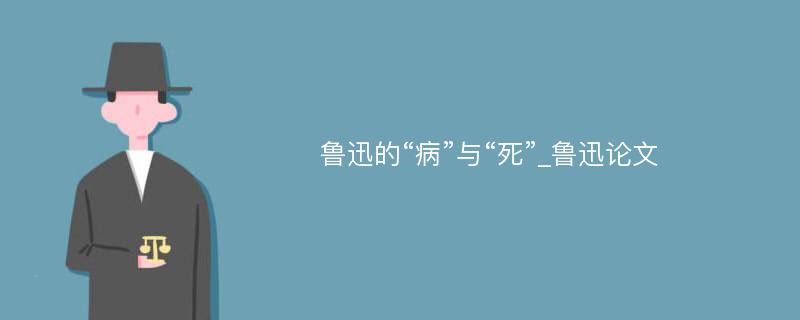
鲁迅的“病”与“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家,鲁迅受人崇仰最多,也议论最多。鲁迅的早逝并未如其所愿的“埋掉,拉倒”,也并非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谓的以死解救了对立,消泯了论争(《鲁迅》第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实际上,后世学人在慨然而生“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浩叹之时,对其生前身后的命运也一直有“是非蜂起”的论争与猜测。作为鲁迅的后人,周海婴的新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以大量亲闻亲见的一手资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隐情,破解了一些困扰鲁迅研究的历史谜团,意义甚殊。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史料问题(周海婴在资料方面自然具有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事实”的揭示与如何揭示本身就包含着“求是”亦即真理求索的严肃意义。比如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题目,就需要思想的勇气。在我看来,周著更重要的价值就体现在一种“抛弃顾虑”、大胆直书的精神,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周海婴真正承续了乃父最基本,也最可贵的精神原则。但同时,我们亦须注意,秉笔直书虽然是历史书写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和原则,但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完备的事实考证。而且,事实也不等于结论,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与论证过程,否则,即使列举很多的事实,也可能得出有偏差的结论。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我觉得周著的些许欠缺就在于个别地方的“大胆假设”似乎多于“小心求证”。比如在对鲁迅之死的解释上,认为给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有谋害的嫌疑就显得思虑不周,情感臆测的成分大于事实分析。不过应该看到,著者毕竟不是学者,其“抛弃顾虑”的“实事实说”的勇气,表明只是“怀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的坦诚,已殊为不易。周海婴根据个人的意愿来回忆往事,书写自己心目中的鲁迅,罅漏难免,他人可以批评,却没有权利苛责。因而,本文只算是对周著的一种补充和发挥。
鲁迅的猝然而去是许多人所意料不及的,这甚至也包括鲁迅本人。在耳闻目睹了多次打着民主、共和旗号的“抢夺旧椅子”的革命游戏后,种种漂亮名头下的黑暗现实使鲁迅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切的观察,也使得他对中国未来充满了深刻的悲观。但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以悲观的勇气否定了虚妄的“黄金世界”后,又同样以一种深沉的勇气来承担和挑战心内心外的死亡与幽暗。所谓“自家有病自家知”,学过医的鲁迅对自己严重的病情当然更应该有所了解。但那种“反抗绝望”的亢奋心态与刚毅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自己病情的看法。早在1934年,社会上就风传过鲁迅患重性脑膜炎的消息,鲁迅戏拟一诗作为答复:“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谣言虽然是谣言,但鲁迅嘲弄性的反击却的确洋溢着一种战斗的乐观气息。因之,到了1936年,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已不断出现“发热”的危险记录,而史沫特莱请来的美国肺病专家邓恩医生又确诊其病情严重后(“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云云),鲁迅虽然“受了些影响”,但又“不怎么介意”,再加之医生又有“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的话,他反而增强了医生所誉的“最能抵抗疾病”的信心。所以当茅盾、增田涉等几位朋友看望他时,鲁迅是笑着将自己的X光片指给他们看,一面还不免将美国医生赞誉的话得意地重复一番。鲁迅在病逝前所写的《死》,被许多人惊叹为先知的绝唱,但如仔细品味就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其实充满了惯常的冷嘲热讽,那种幽默与乐观洋溢可见。这种“乐观”并非超然于死的“达观”,正如鲁迅的自我调侃:还“未曾炼到‘心如古井’”的地步。鲁迅在文末也说:“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换言之,如果真的意识到死亡,恐怕写不出这样乐观、从容的文章来,可惜人们的注意力多放在戏拟的几条“遗嘱”上,而忽视了这条重要的幕后说明。鲁迅的这种乐观似乎也感染了亲属,在给曹白的信中,许广平就把“再活一二十年”当成了一个可信的“好消息”。也许正是这种乐观,鲁迅的忽然去世就让人难以接受,也在亲人们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
就像周作人在爱女若子死后对日本医生痛加指责一样,怀疑医生误诊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就此认为是谋害就有些过头了。周书提到,日本医学界的泉彪之助先生后来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查阅资料,做出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这就否定了周建人在1949年《人民日报》上的公开质疑。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怀疑呢?其实,诊断、用药这些医疗上的怀疑,最终都归结到了对须藤这个人的怀疑上,理由是有人说须藤是日本在乡军人团体“乌龙会”的副会长。姑且不论这个“听说”来的故事是否和有关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皇军”猎犬的传言一样可靠,鲁迅在犹豫后还坚持“叫他看下去”,可见对其是极为信任的。在《死》一文中,鲁迅称其为“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既可看出鲁迅态度的尊敬,又可看出两人能说得来、非常熟识的深厚交谊。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查鲁迅日记,1932年10月20日有“寄须藤医士信”的记录(但鲁迅日记的注释称其于1933年方在上海设立须藤医院,疑误,待考),其与兼任内山书店医药顾问的须藤的交往最早应该是在这一时期。两者最初的交往完全是书信、“邀客夜饭”之类的朋友关系,并没有看病的往还。鲁迅在初期主要请篠崎医院的坪井学士为周海婴治病和高桥医院的医生为自己治齿。和须藤有了看病的往来,始于1933年的6月2日,不过第一次是代为冯雪峰的夫人(即日记中的“何女士”)延请的,但从此以后须藤几乎就成了鲁迅家的私人医生和常客。先是频繁地给周海婴看病拿药,后来又出现了多次父子并诊的情况,及至1934年与1936年两次持续“发热”、“肋痛”的大病,两者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仅从1934年算起,鲁迅日记提到须藤的地方就有近二百处。长达四年的交往,两人的交谊即便不如与内山完造深厚,至少已经相当亲密了。在鲁迅日记中,与须藤的关系除了提到治病,还有“邀客夜饭”,多次互赠荔枝、糖果、书画的这种朋友性交游的记载。鲁迅与须藤也是无话不谈。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书所说的完全销声匿迹了,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他描述了鲁迅的病因,并深情地回忆了与鲁迅“为朋友”的日子。在平日的叙谈中,他们不仅谈中日关系和文学批评、外国科学的大问题,还谈到孩子的身体与教育,“虔心地祷祝着海婴康健地长大”,有时还开一些玩笑(《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载《作家》1936年11月号)。须藤对鲁迅“正直”、“坚强”由衷的钦佩之情在这篇文章中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师从鲁迅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的增田涉在回忆中印证了这个事实。他说,我认识须藤医生,在大陆新村鲁迅最后住过的地方,“时时在旁边听来诊病的须藤医生和鲁迅关于德国文学或日本文学的杂谈”。鲁迅对须藤所说的“最讨厌的是假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这类推心置腹的话,同样出现在增田涉的回忆文中,也证明了须藤对与鲁迅之间朋友关系的描述是真实的(《鲁迅的印象》第5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如果再联系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的须藤经常出入鲁迅家中,“连老娘姨对他都是尊敬”的情况,两人超乎普通医治与一般朋友关系的互相尊敬、信任的亲密程度已足见一斑。从这一点看,须藤谋害鲁迅的猜测不大可能成立。
史沫特莱请美国肺病专家给鲁迅诊病是一个事实,但周著倾向鲜明的陈述方式也导致其与所述事实有一定出入。书中提到,邓医生认为“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修养,至少可活十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60页)。而实际上,鲁迅、许广平等当事人即使表示乐观,也没有这样夸张,而是相当谨慎的。首先,邓医生在诊断出鲁迅的病情极重后,不可能有“无须我亲自治疗”这样轻描淡写、不合逻辑的说法;而鲁迅拒绝了邓医生的开方,理由是不相信欧洲的医学一定会有“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也至少说明治疗方法不会“极简单”。萧红回忆说,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相信药是没有用的”,也与周书的陈述有异。同样,许广平在提到“再活一二十年”的“好消息”时,是有“如果拖得巧妙”这样小心的假设,而前提也是对“经过几次必死之病状”的严重事实的认证。姑且不论医生的话是否是一种安慰,增田涉在1936年专门去上海看望鲁迅时,看到“先生已经没有希望了”却的确是一个悲哀的事实。因为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看问题(这种观念由转述周建人的看法所致,但周建人是在内山完造最后认识到鲁迅“病势很重”,为“顾虑万一”才让许广平打电话将其叫来的,应该不是当事人),作者对一些事实的分析甚至已不近情理。对邓医生提出的休养方案,作者深以为是,而对须藤在很早就提出的同一方案,却认定是个阴谋。须藤提出转地疗养从医学角度来说是无可怀疑的,错就错在地点定到了日本。实际上,到日本疗养的并非自鲁迅始,早在此前,左联作家蒋光慈就因肺病去日本休养过一段时间。况且劝鲁迅赴日疗养的也并非须藤一人,日本友人山本实彦(鲁迅曾为其主办的《改造》做《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在回忆中说,他曾三次敦请鲁迅“来东京一游”,而鲁迅也是“有意来日本”的(《鲁迅的死》,载1936年10月《日日新闻》)。同样,在致茅盾的两封信中,鲁迅自己不仅表达过“决赴日本”的心愿,而且也有“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不成了”的惋惜,这表明周书中的“断然拒绝”一事显系误说。进一步说,如果请鲁迅去日本疗养是一种阴谋,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请鲁迅去苏联疗养的事?为什么后者偏偏被理解为朋友的关心而就不可能是一种“阳谋”?鲁迅最终哪儿也没有去,除了家族、经济等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山本实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愿意染上过厚的政治色彩”,害怕失去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吧。
至于对须藤不送鲁迅住院治疗,“拖延”病情的怀疑,看一看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就可明白,“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须藤每日数次往返诊视,不惮麻烦,应该说是从鲁迅身体的角度着想的。既然谋害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周书所指陈的一些医疗失误又是怎么回事,该做何解释呢?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因为想要请松井博士诊察一回,所以就马上把汽车驶到福民医院去接松井博士;但,偏巧博士今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问到了他的去处,须藤医生就亲自去接他。”这段表述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作为“老朋友”,须藤与内山一样,对鲁迅的病是极为尽心的,所以有“马上”、“亲自”的举动。但是,尽心未必能够尽力,从要亲自请福民医院医生的另外一面看,须藤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坦率一点说,须藤的医术是有限的(但不能因此怀疑须藤的医品)。由是之故,先前请美国医生和拍X片都是在福民医院,后来在鲁迅病情凶险时首先想到的也是福民医院。所以,医疗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如鲁迅所说,须藤“不是肺病专家”;二,鲁迅日记中称呼医生多用学位,如最初给周海婴看病的坪井学士、后来的松井博士等,而独对须藤多称“先生”,可见这位退职军医学历并不高。日本女作家河野樱在《病床上的鲁迅》一文中,谈到过与鹿地亘夫人池田幸子一起拜访鲁迅时遇到的须藤印象:“这是一位在虹口开业的老年医师,他既不会奉承,又不懂得客套,完全是一个乡村医生的类型……鲁迅一面接受注射,一面和须藤先生谈着话,他们谈的完全是日常生活的事情。我心里却在暗忖:‘为什么不找一位更好些的医生来治疗啊!是不相信新的医学的进步吧!’我内心甚至还为此感到不满哩。”河野樱对“乡村医生”的“不满”,与内山完造此后不再让须藤给周海婴看病一样,都是从医术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因而,即使认为须藤对鲁迅的死负有责任,实在也只能从医术不高明来解释,蓄意谋害的说法则多少有些是妄做揣测。
如果不缠绕于具体人事的枝枝节节,不仅仅从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来看问题,而从诸如知识分子的命运、社会环境等更重大的问题背景来展开思考的话,也许对分析鲁迅的“病”与“死”更有意义。鲁迅的病与死当然有先天的生理素质的问题。从鲁迅1912年的壬子日记查起,陆陆续续就有数百次“腹痛”、“胃痛”、“肋痛”、“齿痛”、“腹泻”、“发热”的记录,其中发病最频繁的有四次:兄弟失和后的1923年,“和章士钊闹”后的1925年,以及到上海后的1934年和1936年。正如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自己的肺病“已经生了二三十年”,“不会断根”,“全愈是不可能的”。那么,病根从何而来呢?无独有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书中提到父亲和弟弟的病“伯宜公的病以吐血开始,当初说是肺痈,现在的说法便是肺结核”;“椿寿则于六岁时以肺炎殇”(第29、593页)。周作人自己也在1920年大病了半年之久,“因为生的是肋膜炎,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第402页)。可以看出,鲁迅的肺病与家族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承认这个客观的前提,却不可过于夸大它。因为先天的生理问题虽然无法拒绝,但后天的环境可以完全对其进行排解和调节。比如周作人,选择西山碧云寺作为清休之地,而且也度过了危机。鲁迅也不是不想去休养,他在信中多次表达过“转地疗养”的意思,但最终实在是“非不为也,势不能也”。同样的病因,造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与其说是环境的原因,不如说是两人对相同环境的不同态度的问题。而后者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对待置身其中的环境(社会、文化),将决定着个体对自我的定位和人生命运的选择;这种定位与选择,也深刻影响着如何看待疾病与死亡的问题。对于病,周作人选择了寺庙的清休,这位苦雨斋的“老僧”在病后也果真大彻大悟,深悔过去的“满口柴胡”之气,而欲在十字街头筑塔,做平和冲淡的隐士文章。鲁迅在病初的日记即有“无日不处忧患中”的记录,这种不能忘怀于外在环境的敏感与忧虑显然不利于清养。所以我想,即使鲁迅真的去疗养,恐怕也不会有周作人那样的效果,因为他对环境的态度已深深地决定了冥神对“死”的这一安排。
在《“碰壁”之后》一文中,鲁迅屡屡“碰壁”而不悔,坦承自己有到处“看一看”的“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明白无论什么事,在中国是万不可轻易去‘看一看’的,然而终于改不掉,所以谓之‘病’”。直到生命末期的大病不起,鲁迅还是固执地让许广平“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就是出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现实关怀意识,出于只有这样方才心安与“切实”的“动作的欲望”(《“这也是生活”……》)。对于鲁迅来说,“病后”之于“病”,犹如静之于动,只是相对、暂时的现象。鲁迅也一度想“静一静”,但终于离开了“伏处孤岛”的厦门大学,就是因为那里“无刺激”,感觉如“死海”;鲁迅最后定居上海,明知“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信),“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信),就是因为一份能够“看一看”、介入社会现实的忧患之心。在索尔仁尼琴称为“癌病房”的制造迫害、屠杀的专制社会中,“夜正长,路也正长”,现实的黑暗盛满了鲁迅的内心,也剥夺了他的安适与优裕,愤怒与绝望的抵抗使他时时处在“战取光明”的“苦斗”的激昂中;而发热的胸肺愈是意识到病状,也愈是有“赶快做”的扑火飞蛾似的念头。这样,鲁迅似乎总是处于无日不忧患的“病中”,而不大可能有超然物外的休息与“病后”时候。因而,“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很难“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如周作人那样择寺建斋,修得“于瓦屋之窗之下,清泉绿茶”、“苦中作乐”的境界(《雨天的书·喝茶》)。
知识分子对病与死的态度,实际上也决定了他们对生存环境是回避、随顺还是直面、反抗的姿态与选择。庄子曾云,“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顺服环境,可得“养生”,反抗环境,则必“灭亡”。无论是庄子“明哲保身”的存身之道还是近代“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都是为鲁迅所深谙的,但他最后还是坚持“争天抗俗”的摩罗精神,“举起了投枪”,走上了“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的无路之路。深深影响了鲁迅早年思想的克尔凯郭尔的“人是精神”的命题,使他更深切地认识到“生存”之上还要“发展”的精神原则。这种自觉的选择与承担,同时意味着在此后的人生岁月中,“华盖运”将可能像鬼影一样无休无止地纠缠着他。关于这一点,我想鲁迅也不会不明白。
权势者要统一意识,就要消泯知识者异议、批评的精神,而知识者为了不让个体思想的声音消亡,就不得不直面肉身的“无家可归”:飘泊、流浪,乃至死亡。正是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刻画为“边缘人”和“流亡者”:“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因为“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知识分子论》,第48、53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与强大的专制权势相对抗,如同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所说的“苍蝇战大象”的斗争,不可能指望有“俟河之清”的胜利时候,而且“还要准备着为它步上尘垢扑面的死亡之路”,“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牲”(第11页)。因此,萨义德尽管乐观地肯定了流亡者的“解放”意义,但他也看到,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不被驯化”,坚持“对权势说真话”,必然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的悲剧命运。经历了从北京到厦门、广州、上海的辗转流徙,经历了政府的迫害与“友军”的暗箭,经历了威胁无日不在的病痛与死亡,鲁迅对此有着切实而清醒的体认:“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旗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通信》)。在《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两次探讨知识分子命运的演讲中,鲁迅指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因而“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是因为,道与势、文艺与政治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阅读鲁迅与萨义德相差近半个世纪的演讲稿,可以想见他们内心共鸣着的一种深深的悲凉。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深有意味地说:“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正因为见证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革命“风波”,被从现实与“梦境放逐”的鲁迅同时也放逐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革命之后“黄金世界”的虚妄幻想与浅薄的乐观(《在钟楼上》),也正因为怀着如此深刻的悲观和识见,鲁迅屡次提到叶赛宁等人的死,甚至表示出自己没有被杀而足见文章无力的观念(《答有恒先生》)。即使在因身中左联内部“一大把暗箭”而满心疲惫与创伤的生命后期,鲁迅对自己可能“充军到北极圈”和“穿红背心扫马路”的命运也做好了一定的精神准备。由此看来,鲁迅对自己“如果还活着”的命运其实早有所知,后世好事者实在没有必要再枉费思量。
陈漱渝在鲁迅的一次纪念会上曾发言说,鲁迅之死是不幸的,“但死得其时,避免了在中国‘寿则多辱’的命运,又是他的有幸”(《突然想起鲁迅之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4期),将很多学者私下的猜疑直接公开了。其实,流传于民间的鲁迅“如果还活着”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刘小枫就曾把它当做“笑话”讲过(《圣人虚静》,《读书》2002年第3期)。这倒不是有什么可笑之处,多半是这种可能性因斯人远逝,往事成尘,而难以求证吧。周著现在举出一例孤证,近来已有多人质疑,尤以陈晋文章考证最为切实(《“鲁迅活着会怎样”》,《百年潮》2002年第9期)。学者的考证自然更为严谨,但鲁迅已然“远行”,事实求证其实早已丧失了“鲁迅活着”的大前提,将文件与讲话一路罗列下去并无实际的意义,也难以说明可能性不会发生的问题。鲁迅身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铺天盖地的整体性思潮,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论是鲁迅的弟子胡风、萧军,还是扬鞭的“奴隶总管”周扬,最后都是同样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何用翻箱倒箧,字字求证?实际上,历史上的许多困惑是难以用考古得来的“事实”完全证明的,正常的思维与思想有时反而比知识更重要。
我想,用某种意识形态和人为界限来划分年代,切断时间之流,是不会有真正的历史之同情的。运用所谓现代、当代的分野,站在时代之外来看鲁迅,必然难以接受充满了死亡、杀戮、血腥与阴暗的鲁迅思想与文学,也不会真正了解鲁迅“病”与“死”的如何与为何。在鲁迅时期,世界上最大的流亡现象出现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凑巧的是,在刘半农戏赠鲁迅并博其首肯的“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联中,鲁迅所心仪的学说正是出产在这两个国度;而其所深慕的魏晋风度,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最深的黑暗时期。也许,这不仅仅是一种偶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