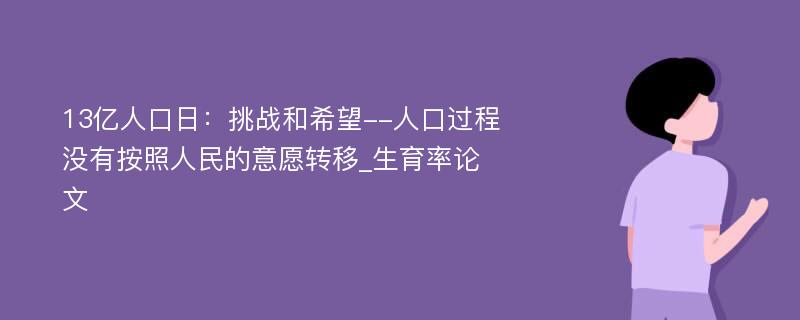
十三亿人口日:挑战与希望——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意志论文,过程论文,十三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2年的人口普查是我国第一次用现代人口统计方法进行的大规模人口调查。几乎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了我国年度的人口动态监测制度。20多年来,经过3次普查和2次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20多次年度抽样统计监测结果的不断调整、磨合,我国统计部门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口统计体系。按照我国人口统计体系的测算,2005年年初全国大陆人口达到13亿。这一测算结果,是建立在2000年人口普查12.6亿基础上的。1980年,我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只生一个”的政策和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的人口目标。但是,即使按照人口普查公告2000年11月1日我国总人口12.6亿计算,我国大陆妇女在1982~2000年其间,也平均生育近2.3个孩子。因为大中城市的妇女基本上是每人生育了一个孩子,所以,农村妇女在此其间实际上平均生育了2.5个以上的孩子。要求“只生一个”,实际生育接近2.3个;目标是12亿,却得到了13亿。
人口过程乃是一种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口过程,是这个国家或民族所有人的生命过程的总和。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则是这个人由出生获得生命到其死亡的全部历程。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由出生到死亡要依次历经幼年、青年、壮年、老年几个阶段。从人类社会之初至今的各个历史上,人的幼年和老年阶段的生命过程都是通过家庭或者家族的帮助完成的。每一个人在其生命历经青年、壮年阶段时,都要生育(复制)可以替代自己的新的生命,抚养和培养这一可以接续自己的新生命,抚养曾经生育自己和替代他、现在已经进入老年阶段从而丧失或者部分丧失生存能力的人。只是由于如此,人类社会才得以正常延续。一个个人的这一周而复始的生命过程的集合,就是人口过程。生儿育女和养儿防老,既是个人生存的需要,也是每一个民族的人口过程的具体内容。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过程要受到这个国家平均条件下的单个人的生命过程的更替规律的制约。在传统社会里,不仅经济活动是以家庭形式进行的,每个人的生活也是以家庭的方式实现的,个人的生命过程几乎全部都是在属于他的那个家庭里面进行的。一个个家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就是这一民族的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缩影。保持适当的家庭规模,是维持单个人的生命的保障。在已往的历史上,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和人类的生存条件比较差,无论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延续都需要有较高的生育率。
工业革命提升了人类活动的社会性,改变了传统的人口过程。首先是社会生产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家庭生产,传统家庭的许多职能被社会替代,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生命过程中的许多活动被转移到社会上进行。在这一改变历史的进程中,特别重要的是以下两种现象的出现了。一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化的发展,只要一个人在劳动年龄攒到足够的钱,他的老年生命过程也可以不通过家庭帮助来完成。这样一来,生儿育女和养老第一次在历史上可以成为没有必然联系的两件事情。加上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提高,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的降低,人们普遍产生了少生孩子的愿望;二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先进的避孕工具,从而使人类实行节制生育成为可能。想一想1960年代开始推广的安全套,即方便又安全;70年代使用的避孕药丸,一天一粒,简单、有效。性也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可以成为与生育没有因果联系的行为,从而使越来越多希望少生育、甚至不生育的家庭把愿望变成为现实。在人类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鼓励生育以延续种群,提高人的生育行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从而使人足以把生育当作一种本能,人类通过遗传逐渐获得了这样一种生理功能即在性活动过程中因刺激感官而产生一种特殊的快感和愉悦。也许上帝担心人类会逃避生育和繁殖后代的责任,才给人一种人人都希望得到的、永远也不会满足的、只有通过性活动才能获得的、与生育密切联系的特别享受。经过许多万年以后,现在人们终于能够打破上帝的最初设计,把性和生育分开了。人终于可以做到有性、有愉悦、有享受,而不要生育。性不再是少数人拥有的一种享乐行为。从这一方面讲,计划生育不过是工业革命和科学进步奉献给人类的一种更符合人性的新的生活方式。
即使如此,人口过程仍然是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仍然要由个人的生命过程的总和来构成。社会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生活方式、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变化也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每一代人都必须慎重对待自己的生育等生命现象和人口行为。1979年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首先将人口老化概念引入研究我国人口趋势,提出“一胎化”可能带来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和兵源匮乏、人口年龄倒金字塔和家庭三代人的“四二一”结构等问题。会后有关部门组织了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小组,该小组反驳说,即使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在本世纪内我们不可能碰到这些问题,在21世纪头20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也不严重”(宋健等,1980)。这是一个答非所问的做法。人口老化这一概念的本质就是反映进入老年时期的人口当年是如何处理自己的生育问题的。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头20年的老化问题“并不严重”,是由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几十年里人们保持了较高的生育率。用当时的老化状况证明当时的生育政策,不是一种科学和严谨的作风。在传统社会里,家庭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规模大意味着生产能力强、经济收入高。生儿育女是维持和扩大家庭规模的基本途径。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生产越来越多地在许多领域取代了以手工为主的生产方式。但是,即使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水平比较高的今天,社会化生产和社会服务有了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生育态度仍将取决于生命过程的各阶段能够获得的状态,特别是取决于生儿育女付出的成本和养儿防老两个方面的权衡与搏弈结果。对于每个家庭的生育行为来说,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只是给人类提供了愿意少生孩子的手段,至于每个家庭生育几个和在什么时候生育,那纯粹是家庭的私事,要由各个家庭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在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里,社会养老迅速取代家庭的养老职能,养儿防老的观念也逐渐淡薄,人们可以根据个人的条件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在农村,虽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了生育率。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家庭仍然是大多数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由于农民家庭的养老职能在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是社会其他机构无法取代的,养儿防老就仍然是决定农民生育观念的主要因素。这些情况说明了,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城市妇女的生育率可以降低到接近1.0的水平,而广大农村却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主要原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生育率水平,这一原理仍然在人口过程中顽强地发挥作用。
许多国家的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观点。西方发达国家由传统到现代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也经历了上百年。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到现代所用的时间短,其妇女生育率的下降又要快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引用的例子,被联合国经常用来说明同一个道理。早在1979年,中国的妇女生育率为2.8,印度的克拉拉拉邦3.0,到1991年中国降到2.0,该邦已经达到1.8;印度的另一个邦——泰米尔纳都邦的妇女生育率在1979~1991年则由3.5降到2.2。印度的这两个邦的计划生育成就都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后,政府并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取得的([印]阿马蒂亚·森,2002)。其实,我们自己有更为生动和辉煌的例子。1970年以前,我国妇女生育率在6.0左右,到1979年就下降到2.8,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水平在10年里下降了3.0,这在古今中外的人口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注:按照当时的统计报表,仅1971~1976年,我国每年净增人口由1950万减少到1100万。《陈慕华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6日),载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53页。四川省的计划生育工作在上个世纪一直是全国的先进省份,但提出“只生一个”和在工作中普遍出现强迫命令,也都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据陈慕华副总理在几次讲话和文章中引用说,1970~1977年,四川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31.21‰下降到8.67‰,1978年上半年有进一步下降到6.06‰。陈慕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197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调查数据推算,陈慕华引用的这几个数据都不是那么准确。在无政府主义还很严重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对公民生育问题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强制性也远没有80年代之后那么普遍,但人口生育率却下降得很快,这些都应该是不争的事实。)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政府在那10年里的作用。根据80年代之后的一些调查,1971年政府重提计划生育时,我国妇女生育率已经有了数年明显的下降。同时,我们还可以想象,“文化大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政府的意图肯定难以贯彻,更没有一个象1979年年底以后提出的“只生一个”的具体生育政策。1980年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干部都深以计划生育工作为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南部一个县里担任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由于公社书记请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病假,我还主持过公社的全面工作。但是,在任职其间我没有象现在的乡镇干部那样做过计划生育工作。那时的县和地区的领导机关,每年都要召开几次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也都没有给我们布置过计划生育工作。我任职的公社机关所在地曾经是一个老县城,公社医院实际上是东边半个县的中心医院。公社医院的支部书记是一位转业军人,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由他带领一支医务人员组成的队伍到各个村子里给妇女做“四术”。那时公社的中心工作就是抓生产、搞政治学习和社会主义教育,基层干部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计划生育方面,县和乡镇的党政“一把手”对计划生育工作甚至于不闻不问,但那10年的妇女生育率却下降得最快。
相反,上个世纪最后20年,我们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社会资源,希望妇女生育率有较大的下降,结果却强差人意。经过20年的努力,妇女总和生育率充其量也只下降了0.5左右。(注:198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生育率抽样调查1980年妇女生育率为2.24,2000年前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认为妇女总和生育率大约为1.8。)1980~1985年前后是我国执行极为严厉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时期,按照当时的统计报表和我们的感觉,全国也都几乎实现了“一胎化”。可是,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所做的几次大规模人口调查,譬如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1988和1992年的调查,以及1982、1990年两次普查和国家统计局1987年的抽样调查,(注:我对所有这些调查都持保留态度,特别是越到后面的调查,则遗漏越为严重。)我国妇女生育率在1981~1987年的绝大多数年份里都保持在2.5左右,明显比1980年已经达到的2.24还要高。人口过程中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情况,说明其自身具有的客观规律性。
既然客观存在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还有必要讨论和研究吗?当然有必要。正确认识客观性的目的在于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试想,按照1980年提出的“只生一个”的政策,2000年我国总人口仅只有10.6亿;到90年代初期实行“女儿户”政策,届时也超不过11亿。但是,在2000年前后我国总人口实际已经达到了13亿。这超过政策规定的2亿多人口是如何出生的呢?在那些计划生育工作不是很认真的地方还好一些。在执行政策坚决的地方,当农村妇女怀孕以后,或迟或早要被基层干部发现。通过干部三番五次地做工作,怀孕妇女必然地跟上干部去做流产。在过了一年半载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妇女又一次怀孕,干部再做工作再做人工流产。如此反复多次,当不符合政策的孩子终于生下来后,干部又上门收取社会抚养费。农村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主要工作,和谐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如果制订一个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接近农民生育意愿的宽松政策,不仅可能比实际出生的孩子还少,更重要地是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由于人口政策是政府为了直接干预人口过程才制订的,所以,有必要就此再说几句。20多年前我在写《人口学》时,不理解人口学在西方已经经过了200多年的发展,但西方学者却从不研究人口政策。(注:其实,这对于西方法制传统的国家公民或者具有希腊哲学和罗马法背景的人来说,都不成为问题。渊源于自然哲学和自然法的现代国家法律认为,婚姻和生育是属于公民个人领域的事情,在公法和私法分明的国家里,任何一后开明的政府都不愿意染指家庭生育这类极为隐私的问题。所以,只有我们国家、也只有在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我们国家能够制定出一套具体到每一个人能生几个和不能生几个的所谓人口生育政策。)所以,我那时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几乎是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耕耘。当时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明确提出过象我们国家那样规定老百姓不能生几个和只能生几个的人口政策。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并不意味着有些国家政策不对该国的人口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譬如,发达国家的教育政策、经济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卫生政策,从其制订者的意图讲虽然不是为了影响人口过程,但这些政策却直接导致了该国生育率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些名义上并不是人口政策但事实上已经影响了人口过程的政策,可不可以视之为人口政策?相反,有时为了影响人口过程的人口政策却不一定奏效。大家都知道,前苏联、欧洲共同体各国几十年来都有一些徒有其表的人口政策,旨在鼓励自己的妇女多生孩子。所以,不能仅仅从名义上区分什么是人口政策。我那时认为,只要是影响了人口过程的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就应该称之为人口政策。为此,特别创造了“广义人口政策”和“狭义人口政策”两个概念。说到底,政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属于主观意识。判断主观意识能否对客观过程产生影响,就要看这种主观意识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和适应客观存在。人口行为说到底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无论广义或者狭义的人口政策都只有在充分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符合人口运动状态的实际时,才能起到政策制定者希望起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