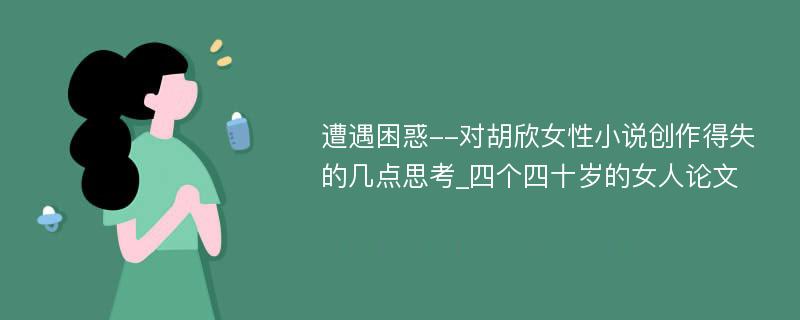
遭遇困惑——对胡辛“女性小说”创作得失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困惑论文,几点思考论文,女性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胡辛的上一部长篇小说《蔷薇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至今已经整整五年了。当然,没有理由说胡辛进入了许多作家一年都经历过的“创作潜伏期”,她依然笔耕不辍,只不过这一时期她施展手脚的场所是传记文学这个圈子,起初只想略作尝试便罢,不料从《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台湾台北新潮社,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却有一发难收的势头,连续推出《最后的贵族——张爱玲评传》(国际村文库书店,江西21世纪出版社),《陈香梅传》(国际村文库书店,作家出版社)。三部传记,皆为海峡两岸同步发行,都有既叫好又叫座的记录,一时之间如此风光,是胡辛始料不及的。然而,飘飘然只能是一瞬间的事,显然,很多关注她的批评者和读者似乎没有和她一起欢欣鼓舞,而是对这三本传记显示出不应有的沉默,仿佛是基于一种顺理成章的阅读期待,他们在等待胡辛下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的诞生,他们还记得胡辛十二年前的迷惑:“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一切的一切,是多么复杂,处处是问号,女人啊,答案在哪儿?”(《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现在,他们的迷惑是:在《蔷薇雨》之后,胡辛还有多深的潜力来写一部高质量的小说——它可能为胡辛自己的“女性小说”创作历程,也为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添上浓重的一笔?
胡辛无疑是新时期较早的一位具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80年代初中期,正是反思文学兴盛,寻根文学初萌的时候,这时的大多数女性作家依然在以中性的眼光描写社会生活,反映社会问题,她们的所思所写,以及表述的方式,和男性作家几乎没有多少区别,只有极少一部分女作家发现并认识到,在她们所处的语境中,“女性”只是一个被书写和被符号化了的概念,“女性”作为主体的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它被赋予的意义又充满了偏见和扭曲。如果说,在封建时代的写作传统中,“女性”的被排斥完全来自男性权势的硬性压制的话,那么,现在“女性”在写作中的缺席则是因为女性自身的原因了。认识是行动的前奏。不安于沉寂的女作家和她们在二三十年代的前辈一样开始了女性自己的写作。她们在创作上的最初选择是十分现实的:写女人的心理、爱情、家庭、事业、追求、写社会中存在的妇女问题。随着后来认识的延伸,她们逐渐具备了一种自觉意识:从女性的角度关注女性的传统,审视女性的文化内容。胡辛便是这些初具自觉意识的女作家中的一位,1983年,她在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的题首,进行了极富意义的发问:“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十分新鲜,但是它却表达出女性对女性文化进行反思的努力,正是在这种努力之中,女性文学曙光初露。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获得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使胡辛一下子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但这之后的几年,胡辛虽然仍有多篇中短篇小说写出,并结成《地上有个黑太阳》(作家出版社,1986年)。《这里有泉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两个集子出版,但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平淡的,与处女作相形之下似乎难以为继。而偏偏就是在这几年,一大群优秀的女作家带着一批令人瞩目的作品,在文坛上声名鹊起:张洁的《方舟》,《祖母绿》,谌容的《懒得离婚》,王安忆的“三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还有铁凝、残雪、方方、池莉……她们的群体性写作,形成一幅灿烂的风景,在这个背景中,人们迅速提高了对女作家的期望值:在荒漠里,有几株绿草就不错了;到了花园,姹紫嫣红也难让人满足。这种氛围既让人兴奋,又充满了压力,对任何一位女作家而言,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没有自我超越,就难以立足。
1990年,胡辛洋洋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蔷薇雨》出版,作品以巨幅民俗,女性“风景画”的形式,描摹出半个世纪前后三代十多位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场面壮阔前所未有,女性主题一如往昔。这部“写足了女人”的小说随后连获华东地区和江西省的多项创作奖。对胡辛来说,这是一座里程碑。然而,这部不乏精彩处的小说给人的整体印象正如王蒙在序中所言,既“充满魅力和激情”,又有许多“不准确不成熟乃至芜杂浅薄的地方”。五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我们的遗憾愈加明显。我们认为,胡辛没能写成一部“女性史”式的作品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女性文学语境中,作家对女性文化核心的把握,作家的写作观念、表述手段、思维方式都存在着超越的不足。
二
胡辛是个写民间风情的好手,《蔷薇雨》的开场便颇为不凡:写六眼井、三眼井、大井头;写驼子娶妻、干家嫁女……活色生香,令人难忘。胡辛对这种民间风情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她熟悉洪城的市井风貌,她把这一方水土缓缓展开在我们面前她对洪城的了解痴迷甚至欣赏并不亚于贾平凹之于商州,李杭育之于葛川江,池莉方方之于武汉三镇。然而,我们认为,单有对民俗地域的直观描绘是不够的,景观只能是个背景,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只有真切地展现出与这个背景融为一体的人,并达到揭示出普通人性的深刻,民间风情才是完美的。人无法逃脱地处于历史和传统中,人“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余秋雨语),人的思想、行动和言语,都可以看作文化的符号,都打上了传统的烙印。人,就是蕴含着文化密码的民族的精灵。在民间背景中凸现出富有质感的人才是创作的最大成功。葛利高里(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斯第芬(乔伊斯:《尤利西斯》)……他们,就是一个民族的化身。贾平凹笔下的韩玄子、李杭育笔下的福奎,都是因为文化的象征意义而具有了历史的深度。
胡辛却令人遗憾地错过了这条本可以继续行走的路,在进行了精彩细致的民俗描绘之后,在营造出颇有民间风味的情境之后,她转向了一个现代生活故事,而故事及其中的人却缺乏与文化情境相得益彰的质地,深沉不足、从容不够,最终减弱了作品的整体力量。
说到底,胡辛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型作家”。在那种气息浓郁的民间情境戛然而止之后,我们就开始面对她笔下人物无休无止的问题,现实世界立刻把我们淹没了。而这时,胡辛就和“她们”合为一体,一起受苦,一起倾诉,这是一颗女人的心对另一颗女人的心的体验,胡辛注入的是全部情感,她把一扇一扇的心灵世界之门打开给我们看。这种叙述有时确实有出人意料的效果,如对章亚若(《蒋章之恋》)、张爱玲(《最后的贵族——张爱玲评传》)的心理和情感流动的细腻描画,写来得心应手,纤纤动人。但有时,它又显得捉襟见肘。很明显,叙述者的分身术毕竟有限,而多个被叙述者却要展现千差万别的面貌,这就使叙述者在写作时陷入了一个不利境地,造成被叙述者间的角色错乱:叙述者的影子可能同时出现在多个被叙述者的背后。在《蔷薇雨》中,许多人物都不约而同的具有一种焦躁倾向,便是作家自身介入过多的结果,这种不断的角色置换,也必然地导致“体验疲劳”,于作者读者都极为不利。当这种以体验为内容的角色融合成为一种叙述惯性时,另辟蹊径、超越现实,便不但不是一句空话,而且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必要性与急迫性。
胡辛,以及和她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热爱生活,描写生活又容易囿于生活。在她们看来,正常的生活秩序,业已成为不可逾越的规则,所有的行为,都是已经发生过了的,充满了合乎规范的理由,对此,阅读者无需过多地行使思考和提问的权利。于是,“生活”二字仿佛一柄锋利的双刃剑,稍不留意,便把作者——作品——读者这个三维空间削成了一个平面。这种极度生活化的写作方式不由得令人想起另一种写法的残雪。残雪首先粉碎的就是循规蹈矩的生活观,她的世界不是我们周围呈本真状态的世界,其中充满了无法捉摸的行为、飘忽不定的心绪、难以解析的谵语梦呓……一个又一个“意义空白”突如其来,给阅读设置了重重陷阱。即便她写的只是倏忽间的感受,阅读者却不得不调动成倍的智力去思考。残雪正是属于那种“即令在他感受的时候,也总是在思考”(艾米尔·路德维希语)的作家。两种写作趋向两个极端:前者赋予了作品过多的感性,后者却逼迫你进行精神角斗;前者缺乏让人顿悟的空间,后者则极易诱人进入意识和语言的迷宫。
在此,我们更加关注前者,并试图加以检讨。我们以为,一个作家倘若不能驾驭生活,便可能成为生活的俘虏。日常生活的经验只能是创作的起点而非终点,超越生活并高高飞翔于天同深入生活并深深扎根于地同等重要。
也许,所谓“极度生活化”的倾向,并不能完全而准确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如果要把它作一点更明确的表述的话,可以说,它是按生活的过去式写,而不是按生活的可能性写,我们可以举方方为例来比较胡辛,从生活观念和写作心态来说,二者都已经像是两代人了。我们观察方方《白驹》中的一段对话:
夏春冬秋说:“那与我无关吧。女人又不是出租车,挥手即去,招手即停。”
麦子笑了,说:“好吧,那你还是当巴士吧,该停时自己去停。”
夏春冬秋亦笑,说:“若想上车,你得自己找个站等着。”
说罢两人均嘎嘎大笑,笑得咖啡厅的人均怒目而视……
这是一对年轻夫妻的对话,丈夫离开他公开的情人,要求回到妻子身边。不论是试探中显露出来的两性观念,还是试探本身的言语方式,都是《蔷薇雨》中的女人们所不可能具有的。这种洒脱、轻松、似现实又非现实的氛围,和胡辛的写作也相去甚远。
胡辛这一代作家的写作心态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她们的写作是严肃的,她们自动承载着沉重的文学使命;另一方面,她们又认识到文学正在经历着的转型,她们也竭力试图变革自己的写作。然而,写作面貌往往沉淀着作家的文化心理机制,形而下地与实际生活相关照的思维摸式,以及再现现实现念,已经成为她们写作中的某种集体无意识。这些似乎都注定了她们的创作是沉重而艰辛的,面对各种围困,轻松的写作、快乐的文本,对她们而言,只能是一种奢侈。
三
胡辛曾以“女人写,写女人”这个口号来概括她(以及不少的女作家)的写作。“写女人”并不难理解,胡辛创作生涯贯穿着的女性主题已经为此作了注释。“女人写”则非易事,它不仅仅标示了写作者的性别,从深层上说,它还指向运用女性特有的视角、心理、意识,来建构女性的写作世界。这一口号的内容以及提出口号这一行为本身,共同显示着女性写作的自信和独立,它试图形成一种影响力,来达到女性文化的自我强化。
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指出,现代社会既是“菲勒斯(男性)中心”社会,又是“逻各斯(语词)中心”社会。“男性”和“语词”都可认作“权势”的代名词。而由女性主义批评者埃莱娜·西苏提出的“女性写作”观点则首先是对男性中心的反动。但是“女性写作”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打上了男性烙印的语言,该采取何种态度?这时,“妇女只有两个选择:(1)拒绝规范用语, 坚持一种无语言的女性本质;(2)接受有缺陷的语言,同时对语言进行改造。显而易见, 所有的女性主义批评者都采纳了第二种选择。”(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写作一方面必须接受语言这一传统方式,另一方面又要摒除语言传统中的父权制象征系统,才有可能保持一种区别于男性范畴的独立性。女性写作也才最终可能具有一种策略性:有条不紊地建立一套女性话语系统。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当然无法框定中国女性作家的写作。但是我们发现有一点二者是一致的:进行有别于男性的女性自己的写作,其努力方向正是形成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大陆女作家的写作中,进行策略性写作的意识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女性作家对语言的运用大多属于一种本能的审美行为,如果说在形成独立的女性话语中还有一些成果的话,也只是个人努力的偶然。在向目标前进的路上,她们走得并不远。
胡辛在她的创作宣言式的论文《我论女性》(《创作评谭》1991.3)中,表述过一种颇为典型的思考。
女性的独立首先是从男性强加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等待释放是消极而不切实际的,只能运用自身的力量去打碎枷锁,这种近于暴力式的反抗动机自然要导致与男性传统的剧烈冲突;其次,女性的独立必须要对另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传统在女性自身沉淀下来的心理机制,诸如自卑、顺从、安于天命……任何手段对这种心理机制的改变都将是缓慢而艰难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救世之人焦虑又无奈的一种反映。“反男性中心——女性独立”这一行动,在处于焦虑状态的知识女性身上,呈现出一种激烈的姿态。语言往往折射出写作者的观念和心态。在《我论女性》中,胡辛对某些男权象征使用的是“最痛恨”、“最厌恶”、“最反感”这样的情感极度强烈的词语。这些都使人想起张洁在《你有什么病》,《鱼饵》中的“恶语”。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女性文化研究之后,胡辛又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女性和男性根本上应该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如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人是由男女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的,“世人除了女人就是男人,女人独立,又能独立到哪里去呢?”(《我论女性》)直接地把女性同男性对立起来,无疑是违背了人类规律。女性独立不是女性自我孤立,不是打倒男性,颠倒角色,而是与男性和谐共存。值得庆辛的是,这种两性关系的理想模式已经在一些女性作家的笔下有过表现,如舒婷的《致橡树》,在女诗人看来,女性不是缠绕大树”的“青藤”,而是与“橡树”并肩而立亲密相处的“木棉”。还有青年女作家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中的“我”,更具有一种坦白的心境,承认在心理上需要男性,但绝不自怜自艾,刘西鸿的一种温和的方式,对男女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淡化。
胡辛试图以激烈的姿态来获得最终的平等与和谐。然而,这种选择显得相当冒险。
胡辛对女性自身的反思,明显地带有她们这一代人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驱动,她们渴望拥有能使她们内心和外部世界之间达到平衡的价值观,但是其涵义究竟是什么,她们自己也无法作出判断。为什么知识女性,尤其是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女人,她们在思想上代表了值得肯定的方向,然而一进入生活,便要遭遇无穷的挫折?从《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的淑华、叶芸,魏玲玲、柳青,到《蔷薇雨》中的徐氏姐妹,都没有摆脱命运的阴影,似乎女性意识的强烈程度总是与女性的幸福生活形成背反,事业、追求又总是对立于爱情、家庭,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在胡辛心中,前者是女性独立的具体体现,没有它,女性就丧失了现代的存在意义,而后者又是女性的文化天性,妻子、母亲的形象与女性不可分割,没有这些,女性是不完整的,这一矛盾面前,价值判断显得软弱无力。细读胡辛的小说,我们常常在这种背反面前,为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涌出心酸和怜悯的复杂情感。
我们注意到,在对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反思之后,有一种观点值得玩味:女权主义的诉求往往只是有利于那些上层的、精英的、处于传统婚姻模式之外的职业女性,而大多数生活型妇女所得到的利益并不比遭受的损害更多,女权主义要改造原有家庭结构的行动,最终却粉碎了生活型妇女试图巩固家庭的愿望。作为一个生活型知识女性,胡辛正是陷入了这一思想困境之中。虽然胡辛内心深处对女性意识作用的模糊怀疑,并没有冲淡她坚信女性意识具有思想上的意义这一想法。但是已然成型的形而下思维方式,自然而然地诱使她在生活中对思想进行检验,而生活却总是提供相反的证据:女性意识必然地要付出情感和家庭的代价。在无可奈何之中,胡辛只好在两者之间寻求最大可能的平衡。胡辛最初选择了柳青这位女性作为回答:她“已经爱过了”,而且她还有另一种支撑——来自她的学生的“人世间最崇高,最纯真的爱,”然而,这就是女性和女性意识的最好结果吗?胡辛依然没有说服自己,她表述了她的迷惘:“我塑造了不多也不少的女性形象,可我不知道我是高扬还是失落了那原本就模糊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价值?”(《我论女性》)八年的创作似乎使胡辛绕了一个大圈,对女性文化的反思愈持久,反而愈觉得迷惘,犹如陷入了“无物之阵”,不知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作家找出的每个答案,都被随之而来的怀疑否定掉了,这是一种疲劳而难于获胜的战斗,因为它的结果最后是女性作家对自我和写作目的的怀疑。胡辛曾说,对女性怪圈的思考,“相信不至于周而复始,而会取得螺旋式的升华。”(《我论女性》),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可是如果在怀疑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进行女性话语建设的策略意识,女性写作恐怕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
四
应当看到,胡辛写作的十多年,正是西方女权主义介绍进入中国的时代,西方女性话语对大陆女作家的影响是广泛而有力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言“给我一间房”便是胡辛深有感触并经常重复的。不过更值得女性思考的不仅是:“房间”的含义?如何获得?而且还有:“房间”是最终目的,还是仅仅是个手段?有了”房间“之后怎么办?正如几十年以来一直难以解决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前面还有无穷的问号,它们给女作家提出了要求:具有面对它们的勇气、具有终极性思考的能力。
进入了多媒体时代,写作的一些传统功能,诸如描绘生活,展现场景,表达情感,沟通交流,在电子科技面前,已无任何优势可言,然而,高层次的写作却是无法替代的,因为它们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描述,给人的思考以巨大震撼和提升,它们走向形而上,使人仿佛在聆听神祗的声音……这样的深刻,只有写作才能带给人类。对今后和未来的每一个写作者来说,生活都只能是起点而非终点,超越现实穿透物象的终极性思考,才是写作所要抵达的彼岸。
中国女性写作的前面依然关山万里。女性在民族文学传统中长期缺席,女性面对男性话语体系的巨大的压力,都给女性写作造成了先天性局限。但另一方面,优势和动力也存在于局限之中。女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有独特的视角和情感,有特殊的表述方式和语言感悟,这些必然地会同男性写作相互区别。在现AI写作作语境中,女性在阐述和探讨人与自然的许多奥秘,尤其是两性关系时,似乎比男性更有发言权;同时,在人们已经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各种定论进行怀疑之际,女性写作也具有提供人们更新的观念和思考的可能性,并进而出现人类认识自身的一个全新视野,这些无限的可能性,也许正是属于女性写作策略中值得更深入探讨的内容。
近十多年,中国大陆女作家群体写作已是繁花渐欲迷人眼。如果说,花满枝头必然预示着秋天的丰硕,那么,自喻为“一篷野草”的胡辛,在“写足了女人”的《蔷薇雨》之后,将要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并呈现隐藏其后的心路历程呢?也许,她的三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传记文学都是一种准备,一种飞跃前的力量积蓄吧!我们期待着她的力作,“女人啊,答案在哪儿?”12年前的诘问至今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我们坚信,胡辛将以其毕生精力来努力回答,因为一个充满了激情的执著的作家,永远会向心中的圣地进发。
标签: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论文; 小说论文; 胡辛论文; 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