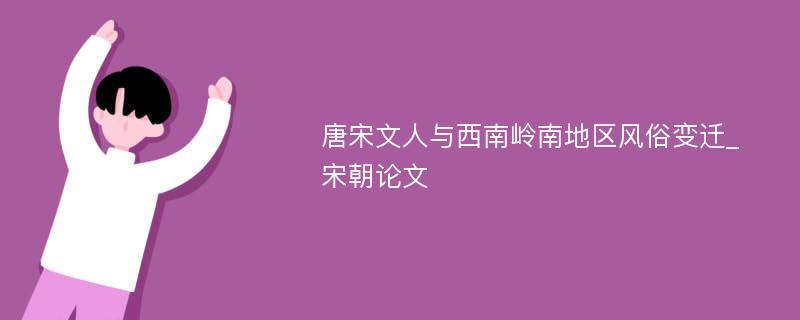
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移风易俗论文,士大夫论文,唐宋论文,岭南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6)02 —0039—06
古代西南、岭南地区群山险江纵横交错、气候炎热,地理环境复杂而封闭,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相对偏远;同时西南地区也是古代“蛮夷”分布最多的地区,众多夷族部落散居在崇山峻岭间。直到唐宋,许多地方仍然处于极其原始的社会组织形式,民俗习尚也大多停留在原始落后状态,儒家礼乐文明在这些地区影响甚微。同时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獠人入蜀”、蛮族内迁的民族迁徙,曾经在秦汉时西南开化较早地区如川北、三峡地区甚至又经历了第二次“蛮夷化”过程①,甚至汉民族高度聚集的成都平原也有不少蛮、獠人居住,经济、文化均有所倒退。从民间信仰看,西南地区普遍流行着诸如“杀人祭鬼”、“信巫不信医”及其杂祠淫祀多神崇拜现象,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西南、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唐宋对西南地区的控制除了政治上设立大量羁縻州、军事上重兵防守剑南、山南、广右的成都、汉中、渝州、桂林等西南中心城市外,思想文化上推行儒家礼义教化也是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岭南这些偏远地区推行儒学教化者实际上大多系文人士大夫,移风易俗是其地方理政的重要层面,而且具有很大的自觉性,因为移风易俗的推行者很多是受朝廷贬谪远赴西南地区的士大夫和致仕回乡官员,如唐代的陆贽、李德裕、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欧阳修、黄庭坚、李复、苏轼、文同、王十朋、冯时行,直到晚宋孟琪、李曾伯等,优良传统代代相承。他们的这些文化行为一方面对改变西南地区的落后野蛮习俗、普及儒学教育、倡导进步、文明的生活方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典型体现了古代文人士大夫自觉践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无类”政治教育思想的良好风范。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学术界对唐宋时期全国范围的杂祠淫祀及其治理已经开始予以关注,并有一些文章发表②。但对这同一时期原始巫文化甚为盛行的西南地区及其文人士大夫在该地区所进行的移风易俗活动却缺少专题研究,本文试作探讨。
一、唐宋西南、岭南地区民俗时尚及特征
民俗作为最具普遍意义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顽强的承袭性,而民俗的生成与流行与一定地区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的著名命题就深刻揭示了民俗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与黄河中下游文明开化较早地区相比,古代西南、岭南地区与“天下之中”的长安、洛阳、开封距离偏远,且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天然封闭性特点,蜀地北有秦、巴高山屏蔽,东有三峡之险,西接青藏高原边缘,西南隔大渡河与云贵高原相望,除成都平原、汉中盆地、遂宁平原、昆明滇池周围地区外,西南地区大多为丘陵山地,山民散居于群山崇岭间;岭南两广地区距中原更是山水迢遥,五岭横亘,海南岛孤悬海外,居民以“百越峒蛮”统称,散居山林溪洞,儒学礼义影响甚微。所以直到唐代,西蜀与岭南在时人心目中的地理意象仍然常常以“僻远”、“瘴蛮”等描述③。从诸多历史文献来看,唐宋时期广袤的西南、岭南地区民风民俗仍然呈现出典型的原始状态。尽管古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称,表明即使在一定区域内民俗文化也有地方差异,但就唐宋时期的西南、岭南地区来说,由于地理环境的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与经济文化的共同落后性特点,民俗风尚仍然具有很大的共同特征,这就是中原儒教文化在这些地区积淀淡薄,生活方式普遍原始落后,在祭祀、婚姻、节庆、治病、丧葬等方面保留着诸多陋习乃至恶习传统。巴蜀地区在整个西南地区而言,自战国秦汉时就开始汉化过程,文明程度相对较高,但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獠人入蜀”、蛮族内迁的二次“蛮夷化”过程,民间信仰文明又普遍出现逆转倒退,到唐朝初年西南地区许多地方盛行以鬼神崇拜为主的杂祠淫祀,儒学礼义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落后。唐贞观年间,高士廉赴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任,发现“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亲扶侍,杖头挂食,遥以哺之”[1]卷65,《高士廉传》,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礼教孝行淡薄、民风落后;成都平原如此,其他地区情况就更甚。汉中郡房州(今湖北房县),初唐时也是“州带山谷,俗参蛮夷,好淫祀而不修学校”[1]卷,185上《韦景骏传》。可见蜀地东部山区汉夷混杂,教育落后;唐代后期,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还发现成都平原盛行女口买卖,民削发为僧却娶妻妾的丑陋现象④,遂大加整治。唐代湘西南与岭南地区则盛行人口买卖,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旧唐书》载:“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1]卷,160《柳宗元传》《新唐书》也说“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2]卷168,《柳宗元传》。岭南人口买卖更加严重,并发展到强盗掠夺人口买卖程度。孔戣任岭南节度使时奏报“南方鬻口为货,掠人为奴婢”[2]卷163,《孔巢父附孔戣传》。
唐代蜀南巴渝一带民风更是落后,流行自然神崇拜。如剑南东川的合州璧山县有闻名遐迩的“壁山神”,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五征引晚唐孙光宪《北梦琐言》一则故事说:“合州有壁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宋代四川民间祭祀更为繁杂,据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一书统计,当时川南的雅州、嘉州、泸州、戎州、渝州长江沿线盛行祭祀三使者神;而合州有壁山神,雅州、嘉州、邛州、眉州供奉劈海揭帝神,除此之外,蜀人还普遍信仰东岳神、嘉陵江神、梓潼神、城隍神、表衣神、蚕丛神、大江神、田神等[3]。唐云南南诏国也普遍盛行巫神信仰,《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说乌蛮“一切信使鬼巫”,鬼神崇拜十分普遍;《新唐书·南蛮传》也记载云南“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说明云南鬼神祭祀已经家族化,以家族为基本祭祀组织;《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四裔考七》则说:“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复仇云。”唐南诏王异牟寻受到中原封禅文化影响,也赐封点苍山等神山为四渎五岳。据段玉明先生统计,隋唐时贵阳、成都、合州、姚州、丽江16个州县有神祠建筑,其中鬼神祭祀占75%以上[4]。
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于北方中原地区,原始巫文化有很大市场。四川此风甚盛,以致成为全国典型淫祠区。《全唐诗》卷二四九皇甫冉《杂言迎神祠》诗序说“吴楚之俗与巴渝同风,日见歌舞祀者”,足以说明川南地区“淫祀”现象在全国的影响,以至于成为时人心目中南方杂祠淫祀的参照中心。宋代川峡四路,除了成都府路文化相对发达外,其他地区文化教育普遍贫乏,民俗文化的落后显而易见,与唐代比并无多大进步。如利州路兴元府洋州,南宋时犹“信鬼不信医”[5]卷68。即使成都平原,民间文化中的巫术迷信也同样突出,且酝酿有社会动乱隐患。赵抃为成都转运使时,曾向朝廷奏报“所部诸州,每年有游惰不逞之民,以祭赛鬼神为名,敛求钱物,一坊巷至聚三二百人,作将军、曹吏、牙直之号,执枪刀旗旛队仗,及以女人为男子衣,或男子衣妇人衣,导以音乐百戏,三四夜往来不绝。虽已揭牓禁约,然远方风俗相沿,恐难骤止。请具为条制。诏所犯首领,以违制论,仍徙出川界”[6]。宋代川东三峡及汉水上游一带地近荆楚,受楚俗影响显著,巫神信仰盛行。夔州,宋人的记载明确说“其俗信鬼”[7];南宋人马永卿甚至说三峡地区“峡中人家多事鬼,家养一猪,非祭鬼不用。故于猪群中特呼乌鬼以别之”[8]。“杀人祭鬼”是流行于荆楚、巴渝地区一种古老而野蛮的祭祀习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巴地“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此乃以生人为祭品祭祀神灵。因其残忍非人道性,与儒家“仁政”严重相悖,唐宋中央皆曾严加禁止⑤,这一习俗在西南湘、桂一带同样十分严重,据柳宗元说,“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俪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9]卷28。其负面影响不仅有违人道,而且也直接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凋敝。三峡一带杀人祭鬼恶俗一直到宋代仍然存在。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夔州地方官员向朝廷奏报“夔路有杀人祭鬼之事,乞严禁止之”,此事曾引起南宋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因之决定在夔峡地区大力治巫⑥。
二、唐宋士大夫在西南地区的移风易俗
唐宋时期在西南、岭南地区的士大夫可划分为三类人,一是朝廷正式遣授的府、州、县各级官员,二是因上层集团斗争失败而贬谪西南、岭南的所谓“罪臣”,三是致仕官员与地方乡绅。由于西南地区民间信仰问题的复杂性已经严重影响到该地区经济生产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杂祠淫祀也与儒教礼义严重冲突⑦,因而唐宋士大夫们把移风易俗作为地方理政、推广儒家教化的一项重要使命。归纳起来考察,这些易俗教化活动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大力兴办学校,倡导儒学教育,用教化手段提高人们文化认识水平
唐初,“是时承隋大乱,风俗薄恶,人不知教”[2]卷98。刚刚结束魏晋南北朝与隋末战乱,全国经济凋残、百废待举,维系国家政治伦理的纲常名教也尚待重振。任职西南的官员针对当地文化落后、科举不兴的局面,大多从开办学校、诱导乡民习经应举入手。贞观年间王义方贬为岭南儋州吉安丞,“蛮俗荒梗,义方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清歌吹龠,登降有序,蛮酋大喜”[1]卷187。这是初唐在岭南少数民族间推行礼义教化的典型事例;开元时韦景骏任汉中郡房州刺史,面对房州“俗参蛮夷,好淫祀而不修学校”的状况,“始开贡举,愁除淫祀,又通狭路,并造传馆,,行旅甚以为便”[1]卷185。将“开贡举”作为破除“淫祀”的有效策略。同时整修道路,发展交通,改善鄂西山区的文化经济状况;郑余庆、郑澣父子两代皆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在兴元府地区兴办学校教育。《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余庆传附郑澣传》载:“始余庆在兴元创学庐,澣嗣完之,养生徒,风化大行。”揆诸史志,这应是历史上汉中地区创立最早的府学,对于开创汉中地方官办教育功不可没。所以,宋代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四十八《成都府学讲堂颂张俞》说:“昔郑正公之镇兴元,创立儒宫,开设学校。其子宣公复居其位,继成前烈,殆将三百年。江汉之人,诵其遗风若前日事。”刘禹锡贬迁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积极倡导地方教育,鉴于西南地区地方学校普遍废弛状况,上书宰相,大声疾呼:“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不扬,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叹廪庚之无余可乎?”倡议振兴中央国子监与地方州县学,“其他郡国,皆立程督,投绂怀玺,棫朴华华,良可咏矣”[10]卷20。虽然刘禹锡是否曾致力夔峡一带的学校教育实践史无明载,但从刘氏自连州(今福建连县)北迁夔州伊始即上书朝廷呼吁振兴教育来看,其在夔州间对夔峡一带的地方教育应该是曾有所作为的。此外,唐代士大夫还常以儒家孝悌思想来感化土人,改变夷人血亲情感淡漠、兄弟争讼残杀的现状。唐高宗时,韩思彦任监察御史巡察剑南,利用“高赀兄弟相讼”这一案件,在蜀推行孝道,整顿民风。史载韩思彦“廵察剑南益州,高赀兄弟相讼,累年不决。思彦救厨宰饮以乳,二人寤,啮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识孝义,公将以兄弟共乳而生邪。’”[2]卷112 虽然《新唐书》的这条记载难免有溢美之嫌,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孝悌思想在西南地区移风易俗中的作用。一些在南方边远地区为官的士大夫还试图在当地建立符合儒教价值观念的民间祭祀,以劝农重本,抵御淫祀习俗。唐高宗永徽年间,张文琮出任建州(今福建建瓯)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农,今此州废不立,尚何观?比岁田亩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于是始建祀场,民悦从之。”[2]卷113 看来经过张氏的努力倡导,作为祭祀农神的“春秋二社”最后是建立起来了,并且建州百姓最终也认可接受了这种带有中原儒家礼义意义的民间祭祀。宋代赴任西南官员,一般下车伊始,先视察教育,庆历七年杜应之为浔州(今广西桂平)刺史,刚到任即“大相厥土,而营学宫……以齐鲁周孔之教而为政”,其上司广南西路安抚使余靖高度评价杜氏此举“上以宣朝廷向学之意,下以成州里兴贤之本,能使远邦学者,异时取名爵于朝,当自今始,真善教者可记也哉”[11] 卷6。南宋荆湖南路永州(今湖南永州市)东安县“在西重山复岭间,境与峒獠接,其风俗鄙陋”,知县上官阐走马上任后,也是首先从建立学校教育入手整治风俗,“乃修崇黉宇,饬簠簋俎豆之事,帅儒其衣冠者,使进而舍奠瞻想温厉恭安之容,退而游处沉酣诗书礼乐之意”,其儒学教化效果显著,深得时人好评,著名学者胡寅由此大发感慨:“东安风俗鄙陋,无足怪也,然号名为人,灵于群动,则其鄙陋,非天之降才矣!是故仲尼有教无类,盖欲居乎。”[12]卷20 唐以来三峡地区教育一直极为落后,直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全国兴学时,在地方官员的积极推动下才有起色,北宋人蒲宗孟说:“惟夔为西南之陋,当天下学者翕然向劝之时,此邦之人尚不识书。至庆历诏郡县立学,今龙图阁直学士庐江何公郯为郡别乘,始能用文章理道,感悟其俗。于是人渐知读书。逮十余年,方有进士,后又有以进士得科名者。”[13]卷36 由于地方官员的不断兴学,到北宋末年,夔州已经出现“业儒者日益于前,登名士版者方兴未艾”[14]卷181 的可喜局面。应该说,宋代三峡文化教育开始起步,何郯们实为有功之臣。
(二)打击人口买卖恶习
虽然唐宋法律对人口买卖都曾制定不同程度的禁令,并且在《唐律疏议》、《宋刑统》、《庆元事法条类》等法律典籍中均有严禁买卖奴婢的条文,但实际上唐宋两代人口买卖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在西南、岭南边远落后地区常常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打击人口买卖也就成为这两大地区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重要政务。元和十二年孔戣任岭南节度使,鉴于“南方鬻口为货,掠人为奴婢”现象猖獗,以严刑峻法打击之。以至于“亲吏得婴儿于道,收育之,戣论以死。由是闾里相约不敢犯”[2]卷163。虽然有矫枉过正之弊,连收养弃婴也在处罚范围,但也可谓治乱世用重典。唐文宗太和年间李德裕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曾对成都社会风气大加整治,把禁止女童买卖作为治蜀之首策。史载“蜀人多鬻女为人妾,德裕为著科约,凡十三而上,执三年劳,下者五岁,及其则归之父母”,同时下令“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经过治理,“蜀风大变”[1]卷180,收到良好的效果。唐代柳州民间长期盛行借债以男女儿童作抵押,即所谓“以人质钱”。柳宗元贬谪柳州后,对此传统陋习大力革除,《旧唐书》一百六十《柳宗元传》载:“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柳宗元死后之所以能深得湘南人民的长久怀念,与此善行有密切关系。
(三)引导民众弃巫信医
唐宋西南、岭南地区气候炎热,瘴气弥漫,疾疫频发,是疟疾、伤寒、瘿疾疾病的多发区,严重威胁着汉夷人民的健康,但由于这些地区医学的落后与受原始荆楚巫文化的影响,民间普遍存在着有病“信巫不信医”的古老习俗。北宋邕州(今广西南宁市)“俗好淫祀,轻医药,重鬼神”,范旻知邕州时,“下令禁之,且割己俸市药,以给病者,愈者千计。复以方书刻石置厅壁,民感化之”[15]卷249。 尽管范旻以自己的俸禄买药给患者接济范围是相当有限的,所谓“愈者千计”难免有所夸大,对邕州大部分人来说无济于事,但一州最高长官的身体力行,必定发生良好的垂范意义,对改变当地“轻医药,重鬼神”的陋习当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峡忠州、夔州是唐宋瘴气重要分布地区之一,唐德宗时名臣陆贽贬官忠州时,潜心钻研医书,探求治瘴良方。史载陆氏“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2]卷157。陆贽是因忠言直谏忤怒皇帝,加之受政敌排挤流谪西南三峡荒蛮之地忠州(今重庆忠县)的,其心情的忍辱负重可想而知。但这位唐朝贤相贬迁三峡后并没有消沉颓废,而是为有助于当地人治疗瘴病而认真搜集古今医案验方,惠泽于一方之民,反映了唐代士大夫关心民瘼、“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可贵情怀。这方面最典型者当推北宋李复,其在夔州刺史任上所作的《夔州药记》是一篇反映宋代士大夫在西南地区引导民众弃巫信医、努力挖掘地方药材资源重医治病的典型文献,这里择其重要者节录如下:
夔居重山之间,壅蔽多热。又地气噫泄而常雨,土人多病,瘴疟头痛脾泄,略与岭南相类。他处药材皆不至,市无药肆,亦无学医者。其俗信巫而不求医,人无老幼,不问冬夏,饮茱萸茶一两杯,以御山气。予到郡,悯其多病而不知治疗,博为询访,欲求土产药,区处以疗之。凡累月,闻山有采药者,命呼来,得十余人。与之酒食数日,熟问之,其所说药品种甚多,皆在本草外云。其采之,各有用。凡治性味,有毒无毒,相得相恶,皆能道之云。荒山僻远,土人皆如此服食,病皆良愈。异乎哉。真古之良医用药也。古之医者于药,皆就其所出之地。按其节候之早晚,及运气所宜,率自采之,故其药多效。今医率求药于市,市肆听于贩夫,真伪尚且不辨,况于其它乎?时予家有乳婢,患疮周体,甚苦。问治以何药。有黎千挽者云,此甚易。次日将紫蔓有如山芋苗来,云此青云膏也,但烂捣傅之必愈。从之而验。遂厚赠之。因令尽条其药名,使各归散,求欲移植后圃,命工写其枝叶花实之形,绘而为图,录其治疗性味畏恶相得之性,详而为经,择乡民之可教者,命学之,以成一方之医,庶救其土人之疾。方讲此而予遽得罢。予少亦留心于医家,人辈疾病未尝呼医,率多自疗,然亦未尝使人知之。至夔得此事颇合素志,若讲而得成,岂曰小补。今非惟不满予心,而郡之士民莫不怃然也。谨书以告后来之能有志者。[16]卷6
李复,字履中,祖籍开封府祥符县,因生于其父仕宦陕右间,又称长安人,登元丰二年进士。李复事迹《宋史》失载,从其文集可以管窥其曾先后在四川、陇右为官,在夔州刺史及熈河转运使任上颇有政声。李复任夔州刺史大约是在北宋末期哲宗绍圣或徽宗崇宁年间。从这篇《夔州药记》看,李复对传统中医颇有造诣,针对夔州一带“壅蔽多热,又地气噫泄而常雨,土人多病”的地理环境疾病,不是束手无策或漠然视之,而是积极采访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当地药材资源、药性特点与对症药方,认真地“写其枝叶花实之形,绘而为图,录其治疗性味、畏恶相得之性,详而为经”,整理成篇以为医书,同时还以此为教材,“择乡民之可教者,命学之,以成一方之医”,为当地培养医疗人才,以此来革除当地由来已久的“信巫而不求医”落后习俗。
西南、岭南地区杂祠淫祀作为历史习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未可一朝去”[17]卷3。历史上移风易俗向来并非易事,革除旧俗自然不可能全是以下达政令雷厉风行、短时间大见成效,如果强制性“热处理”,不仅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可能容易激生民变。因此在唐宋西南地区的移风易俗活动中,一些官员常常采取变通策略⑧。这方面,如前所述,发展地方教育,用儒家礼义文化濡浸民风,诱导土人习读诗书,鼓励学子应该科举,用教化的手段移风易俗是唐宋士大夫对西南、岭南地区最大的贡献;其次因势利导,改造民风。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刘禹锡贬谪此地后发现本地“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作为诗人的刘禹锡,以自己善诗之长,从改良地方辞曲入手,“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卷160。起源于湘西南与川东南巴渝地区的民歌艺术《竹枝词》,之所以在唐宋文学史上盛行一时,与刘禹锡等人的挖掘、改良不可分离。可以说,西南蛮夷民歌给刘禹锡等诗人提供了创作生活新题材,而诗人则利用当地民歌“作为新辞”改良民风,互为交流,相得益彰,产生了积极的教化作用。在革除“信巫不信医”、“杀人祭鬼”落后野蛮习俗方面,唐宋士大夫们也是结合地方社会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实际,殚精竭虑,进行民俗改良。柳宗元贬为柳州刺史时,鉴于“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的严重社会问题,利用佛教戒禁杀生、普度济众思想改革当地有病信巫而杀人祭鬼的恶习,劝导人们“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趋于仁爱”[9]卷28。柳宗元在柳州推行的以儒学教化为主的移风易俗活动,初步改变了湘西南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状况,深得柳州人民的爱戴怀念。史载柳宗元死后,“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2]卷168。当地人对柳宗元的纪念甚至神化了。
三、结语
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在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儒家“以夏治夷”、“有教无类”政治文化思想的具体实践,而且在西南、岭南地区推行移风易俗者大多是遭朝廷贬谪、仕途人生遭受挫折、“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如唐代的陆贽、王义方、张文琮、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欧阳修、黄庭坚、李复、苏轼、何郯、王十朋、冯时行等,他们在这些偏远地区进行的教化易俗活动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为官职责的“分内”范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文化理性的自觉。他们这些文化行为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对儒家使命的终极关系和可贵的人生观念,典型体现了古代士大夫政治失意、“处江湖之远”的儒家文化自觉践履关怀民生的可贵文化理念,他们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努力,对改变唐宋时期西南、岭南地区贫穷落后的文化生活,促使民风民俗摆脱野蛮愚昧向健康文明迈进发挥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也对后世西南、岭南地区的文化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以后,西南、岭南地区的文化逐渐纳入了华夏文化的主流文化之中,儒家文化开始广泛传播到西南、岭南边远地区,唐宋士大夫的教化之功不可忽略;同时儒家忠义观念也在西南地区逐渐深入人心,南宋后晚期蒙古已经占领大部四川的危难岁月中,四川、贵州军民能同仇敌忾、英勇抗击民族强敌半个多世纪,成为南宋王朝西部的中流砥柱,应该与唐宋士大夫们的儒家教育大有关系。
收稿日期:2005—10—30
注释:
① 如蜀地北部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地区)历史上开发较早,在秦汉时已是西南地区公认的文明开化之地,农业发达,儒学兴盛,人才辈出,《华阳国志·汉中志》称此地为“郡守冠盖,相继于西州为盛,盖济济焉”,是为东汉至三国初的情况。但到南北朝后期至隋,川北、川南地区却逆转至一片“獠蛮化”景象,魏收《魏书》卷一○一《獠传》:“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隋书·地理志》也称梁州之地“多事田渔,……傍南山杂有獠户”;《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九《山南西道七·巴州·清化郡》引《四夷县道记》说:“李特孙寿时,有群獠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流布在此地,后遂为獠所据。”都说明魏晋南北间蜀地因獠人入蜀出现了经济文化的倒退现象。
② 参见王永平《论唐代民间的淫祠与移风易俗》,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杨倩描《论宋代禁巫》,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参见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出版。张文重点探讨唐代人区域地理意象及其差异性,与文本旨趣不同,但其对唐人蜀地与岭南感觉地理的揭示仍有一定启发意义。
④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李德裕传》:“蜀人多鬻女为人妾,德裕为著科约,凡十三而上,执三年劳,下者五岁,及期则归之父母,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夏四月壬子载,宋真宗于天圣九年曾下诏,“如闻荆湖杀人以祭鬼,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之。募告者,悉畀以罪人家赀;官吏捕获者,其赏与获全伙刼盗同。”
⑥ 熊克:《中兴小记》卷三十绍兴十二年四月庚戌条。宋高宗对夔州地方官员的奏报颇为重视,《中兴小记》本条纪事后紧接着又记载了高宗赵构对此事处理策略:“己未,上谓宰执曰:‘此必有大巫唱之,但治巫,则此自止。西门豹投巫于河以救河伯取妇,盖知此道也。’”
⑦ 赵璘《因话录》卷五:“若妖神淫祀无名而设,苟有识者,固当远之。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祀也。”这表明在唐人看来,除了国家正统祀典外,其他各种民间祭祀均为“淫祀”。
⑧ 参见王永平《论唐代民间的淫祀和移风易俗》,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