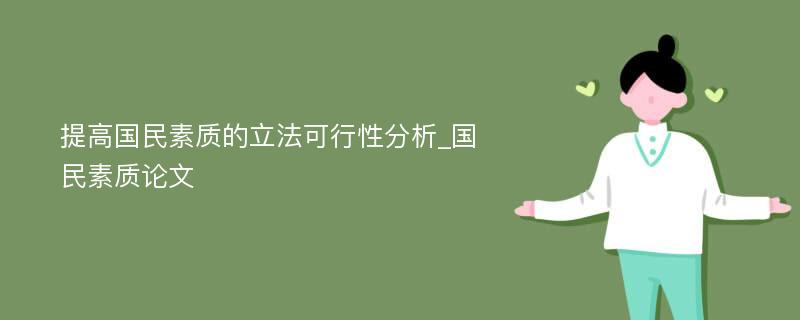
立法改善国民素质的可行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行性分析论文,国民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初,上海,第一次来中国的日本青年冈田在地铁车门前毫无秩序的“混战”中手足无措。随后,她疑惑地向本刊记者发问:中国的小学里有没有德育课?会教孩子排队吗?
冈田的疑惑是正常的反应,因为日本实在是个太有序的社会。当年麦克阿瑟初到日本,看到战后粮食紧缺的日本人在领粮时根本不需要维持秩序,很自然地排成一条长龙,曾感叹道:这个国家很快就会复兴。
与有序又有教养的邻邦国民相比,中国国民的整体素质显得比较让人失望。而且,虽然政府与媒体一直在宣传和倡导,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将种种陋习“发扬光大”到了世界各地。国民素质难以取得突破性提高的事实让部分人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宣传和倡导是不是唯一的办法?我们能不能动用法律的手段?
上海议案与新加坡经验
4月底,上海在这方面亮出了一个带有创新意义的动作。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审议了由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国弟等13位市人大代表提出的“出台《上海市民行为规范暂行条例》的议案”。这份议案建议,在加强市民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用法律手段约束、规范市民某些不文明行为,加大处罚力度。议案列举了七项需要规范的行为,包括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损坏公物、破坏绿化、乱穿马路、在公共场所吸烟和在公共场所讲粗话脏话等。
像任何一种新鲜事物一样,这则新闻也引起了正反两方的辩驳。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最后一条——在公共场所讲粗话脏话上面,认为“如果把人们说脏话粗话一事提到立法高度,势必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况且法之所以为法,其特点之一就是它所面对的主体要尽可能明确,以便于人们更好地遵循、适用法律。而脏话粗话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法律要给脏话粗话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非常困难。这种语意含混不清的法律规章制定出来,又有何意义?”
事实上,在这则新闻引起讨论之前,立法部门已经注意到了上述七项不文明行为之间的微妙区别。上海市人大表示,要将这七项行为作一下分类,法律的问题归法律管,道德的问题归道德管,再尽快制定相应的法规或市民公约。
相比之下,对于能否将前六项行为列入法律调整的范围,舆论的认识比较一致。有评论指出,要杜绝不文明行为,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当然很重要,但同时还需要进行必要的管制。因为对一些已经把不文明行为固化为自身习惯的国人来说,言辞说服难以发挥足够的警戒和抑制作用,改变习惯往往需要借助外力的强制。外力有助于人们对自身行为的理性检点和社会公德意识的提高,有助于根治一些积重难返的行为痼疾,值得期待和肯定。
用法律来规范国民的不文明行为,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在中国,这个问题被提出来过,但可以说从未得到过认真而深入的探讨,更谈不上实行。所以,这次上海的新动作,颇有它吸引眼球的一面。
之前,我们对这种想法的感性认识,最多的来源于新加坡经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新加坡经验并不陌生。
在新加坡,政府明文规定,行人过街闯红灯或不走斑马线,罚款20新元;在地铁车厢内和公共汽车内吸烟,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罚款70新元;乱丢废弃物或罚款500新元、或罚扫大街半日;如在建筑物上乱涂鸦,可处以数月的监禁和鞭刑这样的重罚,等等。
全球舆论普遍认为,新加坡在这方面的严厉法律,对打造著名的“花园城市”功不可没。但同时,新加坡也遭到了一些法律过于严厉的指责。
事实上,邻邦韩国也曾经动用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国民素质问题。1988年举办汉城奥运会时,当时的汉城市政府为了解决随地吐痰的问题,加大了罚款额度并增派大量警察监督,结果,只一年时间,随地吐痰的现象就几乎被杜绝了。
在中国,类似的想法曾星星点点地出现于地方政府的立法实践中,但却常常不了了之。这其中的一点重要原因,是因为反对的声音还比较大。例如,去年杭州市政府曾出台过对随意丢弃垃圾等行为的处罚规定,就有评论认为这是将道德的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的错误做法。反对者们认为,类似新加坡的做法不是一个法制社会的正常做法,而是“严刑峻法”的表现。
通常,反对者的观点如下:一、公民不文明行为的问题更多的是道德问题,不应该用法律来规范。二、用重罚的办法,是解决不了国民素质问题的。
一个江南城市的探索
重罚的办法是否有益于公民素质的提高?或许,江南某城市曾经走过的路是对这个设问的中国实践版回答。
这座城市曾经因为其卫生状况之好而闻名全国,许多到过这座城市的人都表示,“那里很漂亮、很干净。”但不熟悉情况的人并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干净与重罚有脱不了的干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座城市自行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惩罚措施,直接针对各种破坏环境的不文明行为。市民李某向记者回忆:“当时罚得还是很严的。例如随地吐痰,罚50元钱不说,还要把痰迹处理掉,抓到下一个人才能走。有时候还要穿个黄马甲站在那儿,很没面子的。所以的确见效,很快就没什么人乱吐痰、乱扔烟头了。”
如今,这座城市早已不再实行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有关部门也表示,当时的措施现在看来的确是法律依据不足。但近几年以来,被罚出来的好习惯得到了延续,城市依然保持着干净的外貌。
“就是一种习惯、自觉,我们都觉得这里的人素质比其他地方人高。看着那么干净的环境,谁都不好意思去破坏它。”市民陈某颇为自豪地向记者表达了她的看法。
这座城市的有关部门向记者表示,目前该市杜绝不文明卫生习惯的方法,主要是靠一个良好的环境来暗示人,让人不好意思破坏它。但显然,良好的环境维护离不开历史上曾经采取的措施所养成的市民习惯。
也许,市民郭某的看法更中肯。“我不觉得这里的市民天生素质有多好,制度环境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欧美国家的人也不见得天生素质就有多高,关键还是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制度环境在约束个人行为。”据他介绍,该市目前已没有罚款现象,但在主要街道上还经常有城管队员巡逻监督。而在非主要街道上,不讲卫生的人也还是不少。
这说明,罚不是一种最根本的办法,但肯定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办法。这座城市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对“罚不出文明”说法的有力反证,它告诉我们,罚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它不能治本,就连它治标的意义也给否定了。更不必说,治本与治标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仅靠罚当然不能罚出文明,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没有罚,就更不会有文明。其实,罚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道德教化,所不同的是它具有“言教”没有的约束力,是在规范中让人潜移默化,在强制中使人“习惯成自然”,从而从不自觉迈向自觉的境界。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高家伟就这座城市的经验评价,尽管当初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但的确有其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