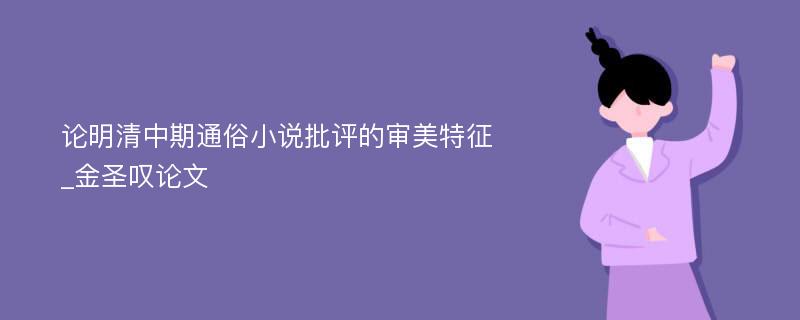
论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通俗小说批评的美学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清代论文,美学论文,通俗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古代小说批评,以评点为主要形式,序跋等次之,专题论文到后来才出现。评点起源于古代学者对古籍的笺注,而把评点用于小说,则滥觞于宋代,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实开小说评点的先河。到明初,蒋大器用评点的方式来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长篇小说评点的开山。但不论是刘辰翁生活的南宋时期,还是蒋大器所在的明代初年,对小说的批评都是偶有一二人为之,此前更没有专人从事小说批评,有关的内容往往只是见于对其他文体的论述,或是稍带有所提及。明代中叶到明末的李贽、冯梦龙等一批小说批评家的出现,使小说批评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他们的理论,得到了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清中叶的张竹坡、脂砚斋等小说批评家的继承和发展,使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不但规模空前,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体系。
以序跋、评点为主要形式的我国通俗小说批评,到明代中叶得到了著名的“异端”思想家李贽的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为《水浒传》作序并进行了详细的评点。在他的影响下,焦闳、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凌濛初等一大批人,先后积极为通俗小说作序、作跋, 有时还进行点评,掀起了小说批评的热潮。
明代中叶到明末小说批评的兴盛,一方面是由于小说批评理论的积累和当时“四大奇书”等通俗小说的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手工业、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冲击了封建机体,思想界进步人士鼓吹的启蒙思想和小说反映的新观念、新意识,影响了小说批评家。作为产生很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李贽及同时和稍后的许多文学家们,自然注重到反映时代特点和社会生活的通俗小说。他们积极发表见解,出现了比较一致的小说批评理论,小说批评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深刻,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代中叶以前的小说批评家只是把小说作为史的附庸,这与起初小说被视为“稗官野史”的“小道”相比,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提高。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通对小说的审美功能和传道功能的探讨,通过把小说与经史比较和对小说价值的探讨,把小说的地位抬高到了同“六经”、国史一样的高度。
这一时期,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日益被批评家们所认识。他们认为,小说较之其它文学样式,有更易于传道的特点。
李开先(1520~1568)在谈到《水浒传》时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词谑》)对《水浒传》的艺术价值作了大胆而充分的肯定。汪道昆(1525~1593)更认为《水浒传》“真千秋绝调矣”(《水浒传·序》),认为《水浒传》叙事记人的精湛艺术完全可与《史记》相比。袁宏道(1568~1610)则完全突破了尊经史为正统的观念,提出了更为大胆的看法:“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宋先生说〈水浒传〉》)这时的批评家们极力肯定《水浒传》等通俗小说的艺术成就,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小说争得一席之地。
同时,小说的审美功能日益被批评家所认识。他们认为,小说较之六经国史更利于传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袁宏道还说,读书者读史“忽忽欲睡”, 而一读起小说来则“捧玩不能释手”。 汤显祖(1550~1616),在《点校虞初志序》中对小说也是备加推崇。他认为小说能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因为它“婉缛流丽”,有审美的“真趣”。正因为小说具有通俗、形象的特点和审美的功能,所以它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更具有感染力,因此更易传道。冯梦龙对这点认识得更透彻,他认为小说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有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
小说的审美教育功能的发现和阐述,成了小说传道主张的理论依据,批评家们抓住这一点而充分肯定小说,以驳斥统治阶级和正统文人轻视小说的谬论。这是批评家们发唱小说传道的又一原因。袁宏道就曾针对有人指责小说家“调脂弄粉,耽恋簪珥”的说法,理直气壮地指出,小说“丽词绮言,种种魂销。暇日抽一卷,佐一觞,其胜三坟五典,秦碑汉篆,何啻万万”(《花阵绮言·题词》)。这种小说传道的理论对后来的小说虽有消极的影响,如小说中出现过多的说教、议论等,但在当时对于抬高小说的地位,推动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的批评家所肯定的小说传道的含义远不只是宣扬封建正统的伦理观、道德观,几乎包括了小说所表现的一切在当时值得宣传的观念,同时也包括了小说家的创作意图、倾向和小说的思想内容、意义,等等。批评家通过对小说传道的内容的阐发,来肯定小说巨大的社会作用,通过把小说与经史并提,来肯定小说的价值,从而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这是本期小说批评突破前人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李贽(1527~1602)一生竭力抬高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有明一代文学的代表。相传李贽批评的小说很多,今存主要有容与堂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和袁无涯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云:“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此传之所为发愤矣。”他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书,是施耐庵、罗贯中发愤之作,其意图在肯定“忠义”、张扬“忠义”。他说,《水浒传》宣扬的是正道,“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认为《水浒》远超《史记》、《汉书》、进与《左传》齐肩,深得《春秋》之神韵。李贽批评小说的根本思想在于反对正统思想观念,同时与谩骂《水浒》“诲盗”的谬论针锋相对,虽然他仍然没有摆脱儒家的道德思想。冯梦龙对他的观点则加以继承和发挥。他指出“小说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序》),他认为“六经”、典籍,诲人无非为忠孝节义之士,而这一宗旨,小说家完全能实现。
署名“修髯子”的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说:“史氏所记,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懦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囤睡。”他认为史志的作用和社会效果极其有限,而演义小说则能使“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张尚德通过阐述作者旨在传道的创作动机,揭示作品传道的积极意义。这样,小说的价值也就得到了肯定。
这时期的小说批评家虽然只是以史鉴功能或诗文功能来评论小说的作用,只是从小说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着眼,还不能从小说自身具备的独特功能进行阐发,但也能看出,他们视小说为一体,已形成了小说观,他们对小说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的肯定,正是对轻视小说的观念的否定,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人的小说批评,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是明代中叶以来经济繁荣、启蒙思想萌芽,小说创作繁荣的必然结果,又是清代我国通俗小说创作发展到高峰的必要准备,同时也为清初到康熙期间通俗小说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并达到体系化打下了基础。
明代中叶到明末,李贽、冯梦龙等人通过对《水浒传》、“三言”、“两拍”等通俗小说的批评,肯定了小说的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清初至清中叶的小说批评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挥。从使小说批评逐渐形成了体系。
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形式异彩纷呈。明代小说批评的形式重要是序跋和笔记,回评方式只见于署名李贽的两种《水浒传》批本和一种《西游记》批本,且后者评语没什么价值,而《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只有眉批、夹批,没有回评。清代初期至清中叶的小说批评,除序跋和笔记而外,回评、凡例、读法、眉批、弁言、题辞、论赞、杂说、例言等形式纷纷出现,而以回评、读法和序跋运用最广,影响也大,出现了不少影响较大的小说批评家,如金圣叹、毛宗岗、“天花藏主人”、张竹坡、脂砚斋等。他们大都自成一家,各自对某一作品所作的批评,无人能出其右。金丰、刘廷玑、蔡元放、“闲斋老人”、王希廉、哈斯宝等人在这一时期也有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小说批评的重要特点是渐趋体系化,而以写实理论的充实和典型理论的形成为其主要特征。
写实理论的充实是这一时期批评的重要收获。随着《金瓶梅》等写实小说的崛起,批评家对小说创作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一方面反对演义小说皈依史籍,不能放手进行艺术虚构,另一方面又批评神魔小说太幻,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因而对刚刚崛起的人情小说则格外推崇,他们虽然没有对写实理论作过完整的解释,但各自都根据自己对写实小说的认识而强调某一方面,使写实理论不断得到充实。
首先,批评家们继承明代李贽以来的“发愤著书”的理论并加以发挥。张竹坡在《竹坡闲话》中认为,《金瓶梅》作者是“愤已百二十分,酸又百二十分,不作《金瓶梅》又何以消遣哉”。张竹坡认为作者作此书以泄其“愤”,是“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是“自云寒酸”,所以能注意到作者所泄之愤是有社会内容和现实针对性的。“天花藏主义”在《女才子书·凡例》中评论这类才子佳人小说时,认为作者不能在现实中实现所愿,因此“不得已借写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并认为“凡纸上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他注意到,由于作者的抑郁、愤懑来自社会的不公平,故而作品的各种描写,都在不同程度上抨击、揭露了社会,表现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脂砚斋”等人认为《红楼梦》同样是基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同样是有所怨,有所叹,有所感。他说:“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庚辰本,十七、十八回眉批)又说:“况此亦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故迥不同与小说之离合悲欢窠旧(臼)相对。”(同上,七十七回夹批)可见,张竹坡、“天花藏主人”和脂砚斋等人都强调小说创作需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积累,需要有作家对于社会的洞察、思考和感叹。
其次,批评家们认为小说要“描摹世态”,这是写实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时期的批评家进一步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探讨,认为能“透彻世情才是真文人,亦惟真文人,方能透彻世情”(孟汾《孝义雪月梅》第二回回评),充分肯定了小说对社会的揭露、针砭,褒扬小说对世态人情的尽相摹绘。“憬园退士”《儒林外史·序》云:“《儒林外史》一书描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对小说描摹世态的充分肯定,意味着主张小说面对社会,使小说创作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第三,批评家们主张小说要深入人情。只有写得人情出,作品才能真实感人。他们认为,小说的艺术世界必须接近现实的日常生活,艺术形象必须体现出常人的一般特征。《金瓶梅》之前的小说并没有真正达到这一点。“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指出:“其书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然则真千百化身,现各色人等,为之说法者也。”(六十三)“其各尽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六十二)张竹坡指出了作品展现的生活画面,细腻逼真,非常接近生活。“似有一人亲曾执笔”,“一一记之”(同上),张竹坡还认为,《金瓶梅》中的描写“各尽人情”,“文字俱于人情深浅中,一一讨分晓,安得不妙”(第二十回回评)。这既是对作品的高度赞扬,也是对写小说塑造人物的经验总结。脂砚斋对此与张竹坡持相同看法。他在批点《石头记》时,多次指出作品的优点就在于深入人情。在十八回夹批中,他说:“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减,入情入理之至。”(庚辰本)第二十九回写清虚观一场闹剧,他又批道:“清虚观,贾母、凤姐原意,大适意,大快乐,偏写出多少不适意事来,此亦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同上)脂砚斋已认识到小说人物形象的言谈举止必须合乎特定身份和特定情景,小说描写的事件应当尽可能地写出生活的实际情况。
张竹坡等人提倡写实,反对不合情理的描写,主张再现生活,深入人情,同时又肯定艺术创新,这些都充实了写实小说的创作理论,对当时及后来的小说创作及小说批评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清初至清中叶小说批评体系化的又一特征是典型理论的形成。写实理论强调作家深入生活,深入人情,可以说是典型理论的基础。写实理论一出现,典型理论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典型理论的构成主要是从金圣叹的性格论,到张竹坡的情理理论,最后到脂砚斋对《石头记》的批评,逐渐形成。
金圣叹(1608—1661)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30岁以后开始批书,崇祯十四年(1641)刻成《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四年后,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便为清朝所取代。其小说批评的影响主要在清初,如顺治十四年就有醉耕堂刻本《第五才子书》。嗣后,经金圣叹删改评点的《水浒传》、《西厢记》便广为流传,几乎淹没了其他版本。
金圣叹的思想带有个性解放的性质,与李贽等人有一致之处。他的性格论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他将《水浒》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合称六才子书,称《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性格论是金圣叹小说批评理论的精华。此前,李贽在容与堂本《水浒传》回评中早有“各有家数、各有身份”和“同与不同处有辩”等说法,已经涉及到了人物个性化理论。金圣叹继承和发挥了这一观点,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阐释。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他认为,《水浒传》之所以百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同上)。金圣叹把是否塑造了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看作是小说创作成功的关键,在理论上是一大进步。他进一步指出,人物性格化的特点和要求应是“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序》)。他认为《水浒传》塑造的各类人物既有个性特点,又有典型的代表性。“第一豪杰,即居然豪杰”,“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写一淫妇,即居然一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居然一偷儿”。(《第五才子书》五十五回回评)这里,金圣叹已隐隐约约认识到,小说人物应该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他还说:“《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写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金圣叹认识到,作者虽写同一特征“粗卤”,却表现出个人迥异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互不混淆,决窍就在于抓住了人物各自的“性格”、“气质”、“形状”和“声口”。金圣叹的论述,涉及了人物性格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理论,这点对稍后的毛宗岗、张竹坡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金圣叹关于人物性格化理论的不足之处,是认为小说人物的性格是单纯的。毛家岗继承了金圣叹的人物性格化理论,认识到《三国演义》塑造了孔明、关羽和曹操这三个性格理论中的单纯化发展到绝对化,而忽视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现实性以及人物形象丰富的性格内容,因而有些偏离了通俗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
张竹坡(1670~1698)充分发挥了金圣叹的人物性格化理论。他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四十六中指出:“《金瓶梅》于西门庆不作一文笔,于月娘不作一显笔,于玉搂则纯用俏笔,于金莲不作一钝笔……,此所以各各皆到也。”所谓“各各皆到”,即指作者写人能够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落笔,无任何雷同之处。张竹坡不象毛宗岗为了强调人物性格鲜明忽略了写实的原则,指出刻划人物性格必须合于“情理”。他说:“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同上,四十三)张竹坡所说的“情理”,包含了真实与个性的特点。“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同上)他认为,塑造人物个性,就得把握住笔下的这一人物不同于其他一切人物的、独特的“情理”。如果从言谈、举止等各方面都能准确地表现出“这一人的情理”,“这一人”的性格必然鲜明,而绝不会出现雷同。这一点很接近恩格斯在论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理论典型论的“这一个”的说法。
“脂砚斋”在这方面的认识比张竹坡又进一层。除了张竹坡涉及的理论,“脂砚斋”在批评《石头记》时还注意到了作者描写环境的真实典型,如十四回写秦可卿丧葬的排场,“脂砚斋”在回末批云:“此回将大家丧事详细剔尽,如见其气概,如闻其声音,丝毫不错。”又批道:“写秦死之盛,贾珍之奢,实是却写一个凤姐”。(良辰本)可见,“脂砚斋”已注意到典型环境的描写,必须基于生活真实而又达到艺术真实的境地。
同金圣叹、张竹坡一样,“脂砚斋”也谈到典型人物塑造理论,但他往往能从所批评的具体作品上升到一般创作理论来认识,并联系其他小说加以说明。从他对《石头记》的许多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如:
看他写黛玉只用此四字,可笑近来小说中满纸天下无二、古今无双等字(甲戊本第三回夹批)
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鼠耳鹰腮等语。(甲戊本第一回眉批)
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四十三回夹批)
脂砚斋认为,典型人物的描写应平实自然,切合性格,又要高于情理,典型人物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脂砚斋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理论已经非常接近于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可以说,脂砚斋的小说批评理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典型化理论,虽然还没有出现“典型”一词,但它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了典型化理论的各个方面,和写实理论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批评的主要特征。
除上述而外,本期的小说批评理论还涉及到了小说理论的许多其它方面,对艺术手法、创作动机、文学语言以及鉴赏方法等几个主要方面都有较深刻的阐释。中国小说批评理论到此初步形成了体系,而以评点为主要形式、以典型化理论和写实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批评方式直到晚清才被思辩式的专题论文为主的批评方式所取代。
明代中叶到清代中期的小说批评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小说批评理论形成的关键时期,小说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通俗小说日渐深入人心。尽管这时的批评家们仍然只是将小说方之于经史,还不能完全深入小说的本体,尽管他们的小说理论还没有从随笔评点和序跋中独立出来,但他们取得的成绩还是令人瞩目的。至此,小说批评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为后来的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标签:金圣叹论文; 脂砚斋论文; 水浒传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金瓶梅论文; 读书论文; 红楼梦论文; 张竹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