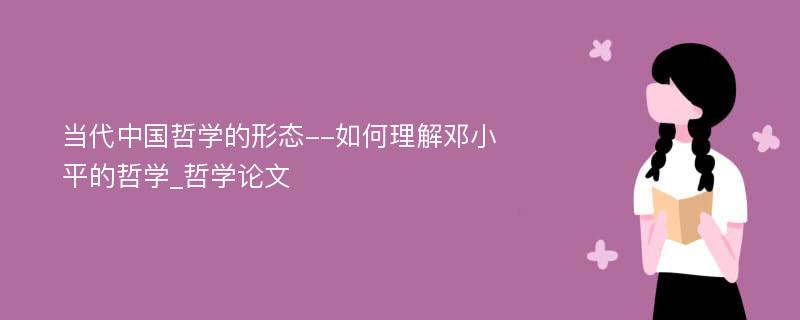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如何理解邓小平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形态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究竟有没有哲学或者说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究竟有没有相对独立的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哲学或者说是不是改革开放前曾经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模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直接延伸?对于邓小平或邓小平理论中的哲学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央领导的讲话多次郑重地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1] 13“邓小平同志的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从实际出发反映事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尤其要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的。”[2] 3但毕竟没有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哲学那样对邓小平哲学作出具体的阐述。这种情况客观上给人们如何看邓小平哲学或者对它产生各种不同的认识留下了空间。弄清这些问题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哲学形态有内在联系。
一、邓小平哲学传承了马克思哲学的品性,属于哲学思维运动
从传统的“概念哲学”或“纯哲学”标准看,自从1847年马克思哲学公开问世即《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几乎没有留下一篇像恩格斯的《路德维稀·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样的哲学专文,他的哲学似乎“消逝”了。其实,马克思的著述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哲学形态即实践型哲学,或准确地说这种新型的实践哲学形态开始生成。(注:王南湜等在《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根据理论活动或思维方式的不同,把哲学分为“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所谓“实践哲学”,是认为理论思维是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生活,并不能在生活之外找到立足点,因而理论理性要从属于实践理性。)这种新哲学形态关注的重心不是“批判的武器”,不是坐而论道的书斋哲学,不是学院哲学或教科书型的纯哲学,追求学说体系本身的完美,而是注重人世的生活与实践,注重于当世普遍性问题——“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3] 230的追问与求索,关注的是“武器的批判”。
前苏联、中国改革开放前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模式适应当时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把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纯哲学”化或“教科书”化,在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过程中确实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与此同时,它在相当程度上特别是在后来的长期流行过程中严重地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品性和本真精神。而邓小平哲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鲜明地传承并光大了马克思哲学的品性和本真精神。
邓小平哲学似一块蕴藏无价之宝的“玉石”而不是被刻意雕琢的“纯玉”,是马克思式的“实践型哲学”。邓小平长年身居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线”,其精力、思维和哲学睿智倾注于那些事关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刻不容缓”的实际问题的思考与决策之中,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刻意去把这些理论思想、哲学智慧搜理、归纳成学理性专文或哲学专文。
从原生形态看,邓小平文选三卷(包括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党和国家的决议文件),没有一篇带“论”字的纯学理性文章,没有一篇纯哲学专文如毛泽东的“两论”、陈云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很少独创新的纯哲学术语而往往借用前人的哲学命题、话语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全是有关国是的报告、讲话、批示、题词和决议等,类似于马克思1847年后的著述的情形。这种情形或“假象”的确给人们准确地、深刻地把握、估量邓小平哲学及其特色造成了困难。如果人们固守“概念哲学”或“纯哲学”标准,那就必定断言邓小平哲学没有什么哲学上的独创,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如果拓宽我们的哲学视野,拓新我们的哲学标准如纳入实践哲学的标准,就能透过“假象”把握真相。思想家葛兰西说得好:“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4] 85
邓小平哲学的直接“存在形式”表现为“问题意识”,一种对当代实践问题锲而不舍的哲学“追问”。长期以来,世人包括不少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惯性地预先假定或自以为然地断定这个问题属于马克思主义的“ABC” ,在“老祖宗”那里早就解决好了,后人“按图施工”就是了。虽然客观效果不理想,那也不是“图纸”问题,而是“施工”问题或“施工”经验不足。邓小平却发人深省地反复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5] 137,“这个问题不光我们有,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6] 369-370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三次重大历史关头(即1958年“三面红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所导致的整个国家严重困难、“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模式所导致的中国社会徘徊不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导致的苏东剧变)都一次比一次更鲜明、更严重地把这一现代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展现在世人面前。邓小平以他思想伟人、哲学伟人的敏锐适时地作出回应,先后发表了著名的“猫论”讲话、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和“南方谈话”。
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与求索决不是小题大做或老调重弹,而是对牵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乃至当代世界的一个最高最大的普遍性问题——社会主义世界每个人生存发展问题的追问与求索,是对关涉到如何看待经典马克思主义或经典社会主义即基础理论问题的追问与求索,从而在社会主义世界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或哲学思维运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这种思想解放运动。
这种对普遍性问题所作的及时反应、追问、决断,本身就是一种致思性极强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况且邓小平对这个当代世界的普遍性问题所作的追问与求索“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的书本”。[7] 180
二、邓小平哲学既有隐性哲学思想,也有显性哲学理论;不是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模式的直接延伸,而属当代中国哲学形态。
就表达形式看,邓小平哲学既有丰富的、深厚的隐性哲学思想,也有相当的显性哲学理论。邓小平的隐性哲学思想体现在字里行间,属于“无型”的哲学思想或哲学智慧,类似于人们常说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大哲学”。
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普遍性问题进行追问与求索的过程中,邓小平所提出的命题或论断如“对外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和平与发展”、“三个面向”、“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新观念,的确不是“小哲学”命题或纯哲学形态,不是那种显性哲学理论,而属于隐性哲学思想。因为它们是邓小平像当年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层面追问、求索社会主义为何可能(使之由空想变为科学)那样,从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规律层面进行追问、求索的科学结晶,体现着人类哲学的本性即对既有成果、既有结论的“超越性”或批判性;这类“大哲学”命题或论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本本”里“找”不出来,超越了这些前辈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结论甚至基本思路,刷新了曾经长期盛行的社会主义观念。正如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的意义时所说,“是书本上所没有的”。[5] 130“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5] 258
邓小平这类隐性哲学思想体现了时代的鲜活性,体现了邓小平实践型哲学的特质,不是改革开放前曾经长期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模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直接延伸,而颇具当代“中国特色”。邓小平理论中蕴藏着丰富的的这类隐性哲学思想。
邓小平提出的诸如“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5] 6、“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7] 16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 274等等就属于显性哲学理论。
作为显性的邓小平哲学理论,首先是邓小平的思想核心即“精髓”层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虽然他本人没有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他的理论精髓,况且这八个字前人也多次使用过,但他往往是以“六经注我”的形式如人们常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语词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联系当年邓小平提出的“领袖是人不是神”[7] 165、“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7] 266、“实行开放政策”[7] 133、“三个面向”[5] 35的语境,就不仅仅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有结论的问题。就哲学的话语而言,不是要恢复前苏联和中国“文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模式,不是一般地重复前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而首先是要突破长期以来主要是1957年后党内存在的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或经典社会主义观念绝对化(当然也包括照搬本国历史上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做法)即“左”的思维定势的问题。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范畴,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哲学或哲学思维的品性——对既有结论或既有成果的“超越”或“批判”。
邓小平显性哲学理论的另外一个直接体现,是他旗帜鲜明地支持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制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哲学“常识”,然而这位思想伟人、哲学伟人视之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7] 143,属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基本建设”。[7] 191把思想路线问题视作“基本建设”与马克思当年把哲学视作“解放的头脑”[8] 32-33相似,同属哲学层次。这表明在他的视野中,他把思想路线问题首先置于哲学思维方式的层面,而不仅仅限于政治学层面。因而,他注重从人们思维定势方面反思党在实际工作中曾经出现的挫折特别是“左”的思维所酿成的灾难,提出“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5] 375他在1980年2月科学制定的党的“思想路线”[7] 278正是用以克服各种思维偏向特别是“左”的思维定势的“杀手锏”。
邓小平显性哲学理论集中体现为邓小平在基础理论层面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的创建“工程”。所谓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不在于邓小平哲学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恩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创立的一系列“方法论”,更不在于邓小平哲学是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模式的直接延伸或仅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释义、对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模式的纠正,而在于她在事关社会主义社会生存发展问题上所提出的带原创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观,在哲学思想史上具有当代中国优势或中国人独创的始原性。
他当年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权威的现实前提是:“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5] 237正是中国这种严峻的社会形势迫使中国人毅然打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并在这一“旗帜”下提出了事关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带原创意义的理论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论断。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社会主义本质”概念是由邓小平首次提出的新哲学概念。“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世界最高最大的普遍性问题,刷新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及其价值标准。
又如“社会主义改革”论。经典唯物史观把解决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的重心放在上层建筑领域,以“社会革命”范式(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处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它社会问题: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8] 32-33。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就其一生而言)在处理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都持这种理念。鉴于在社会制度上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中国生产力落后,邓小平强调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7] 182,并首次“铸剑戟为锄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对这种理念实现了超越或转型,着眼于“把蛋糕做大”。他提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从历史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7] 311主张区分社会制度与体制模式,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体制特别是采取市场经济机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基本范式。
邓小平哲学不是一般地“恢复”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在中国一般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有结论,而是在反思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观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方面的前提的基础上,在基础理论层面实现了从马恩一般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到特殊的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民的“解放的条件的学说”的转向,从马恩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到事关世界社会主义社会兴衰存亡特别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兴衰存亡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转向,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的创建,远远超越了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模式,尽管这一“工程”远未竣工。可以说,邓小平哲学集中表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或具有中国相对优势的当代哲学形态的开创。
三、不要再贯性地把当代中国特色置于前人或别人的影子下
一些西方哲学家基于其“概念哲学”标准、欧洲文化标准,对中国哲学不以为然:“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当他们过渡到具体者时,他们所谓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9] 132“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10] 139有国人也看不起自己的学问,特别是看不见自己学问的“中国特色”,往往无视自己的特色即相对优势、强点,或者贯性地把自己的特色置于前人或别人的影子下。比如在如何看邓小平哲学的问题上,国内舆论界、学界及有关此类的论著长期以来几乎存在这么一个“成规”:把邓小平哲学仅仅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有人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创造性运用、体现和发展”。[11] 365甚至有人认为:“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了哪些新的哲学观点、哲学概念,而在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化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化为思维方式、领导方式、管理方式、工作方式”。[12] 15
尽管这类对邓小平哲学的“定位”从主观上或字面上看都强调了邓小平哲学的“发展”性或“创造”性,但不仅客观上“抹掉”了邓小平哲学对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模式的超越性,而且导致这么一个印象:邓小平哲学仅仅限于在中国“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有结论。这类对邓小平哲学“定位”的思维贯性或“成规”固然正确地把邓小平哲学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族”内,主观上把邓小平哲学放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平起平坐”的位置,实际上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泛化”了,不利于人们领悟其个性和本真精神,而且遮蔽了邓小平哲学的个性和特色,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十几亿中国人民26年来改革开放的新成果和理论思维上的创新。这与其说不利于在世界文化面前彰显邓小平哲学的特色和中国当代思维的特色,遮蔽了邓小平哲学在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中的独特价值,不如说不利于邓小平哲学特色和中国当代思维特色的进一步“发育”,从而不利于当代中国事业的发展。
“文革”时期的“顶峰”论曾经严重地阻滞了自己民族的发展。但不要因噎废食,应该区分中西文化各自的个性,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哲学理念层面的得失长短,区分实践型哲学标准与“概念哲学”或纯哲学标准之间的差异。
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实效上而且在理念上都在世界上获得了自己的相对优势,中国人民深刻地汲取了历史上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教训,中国人民比之过去更深刻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实践家中西结合、承传文明、知己知彼、扬长补短,构建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中国当代哲学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当代中国人在哲学理论上应该有也确实有自己的“品牌”。因为当“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即在于它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是有普遍性的”时,就“进到真正哲学的基地上了”。[9] 98-99邓小平哲学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哲学形态之一,正是中国“进到真正哲学的基地上”的标志。尽管邓小平哲学不等于中国当代哲学的全部,但代表了中国当代哲学的方向。
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中国特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