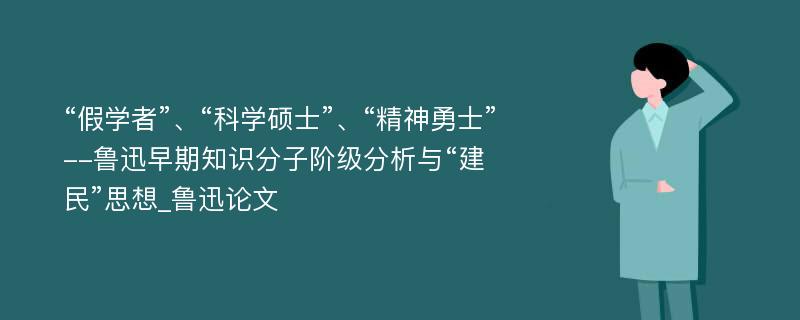
“伪士”、“硕士”、“精神界之战士”——鲁迅早期对知识阶级的分析及其“立人”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阶级论文,战士论文,硕士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知识阶级的分类
“智识阶级”作为外来词进入在中国,至1922年3月6日《晨报副镌》载俄国盲作家爱罗先珂名为《智识阶级的使命》的演讲词才发生普遍影响。此前,鲁迅对这部分人群使用传统的称谓,如早期著述的各类“士”,“士人”,《新青年》时期的“鸿儒”,“文士”。“智识阶级”一词被引进后,鲁迅采用的同义语有“知识阶级”,“智识分子”,“智识者”等,如《坟·春末闲谈》的“特殊知识阶级”,《华盖集·通讯》的“智识阶级”,同时解释了该词的舶来性质及其与中国相应人群特征存在的差别。后鲁迅多用“知识阶级”,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
早期鲁迅关注的对象即知识阶级。《摩罗诗力说》、《文化偏执论》、《破恶声论》三篇虽各有偏重,而要旨皆在揭示知识阶级对社会文化思潮趋向的影响,重心是中国知识阶级的问题。
针对知识阶级里的各色人,鲁迅使用寓褒贬于其中的称谓词语,以示区分。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对中国知识阶级尤近代人士多用贬义词。《摩罗诗力说》的“文士”,“哲士”,“爱智之士”,“思士”,“后贤”,“儒服之士”,“崇实之士”,“诗宗词客”等;《文化偏执论》的“辁才小慧之徒”,“奔走干进之徒”,“无赖之尤”,“识时之彦”,“识时之士”,“操觚之士”,“狡狯之徒”,“评骘之士”,“学者文家”等;《破恶声论》的“妄行者”,“知者”,“人士”,“浇季士夫”,“妄惑者”,“志士英雄”,“士人”,“士大夫”,“伪士”,“志士”,“中国桢干”等称谓反复出现。把这些词语从上下文里抽出,已减损了它们的恰切程度,且不能完全显现它们实际贬义之所在,但罗列的必要在于,突出鲁迅使用各种修饰限制语是对知识阶级问题的批判方式。若从中选取一个典型,则“伪士”可传达其贬义。
与以上称谓不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有相应的名称词语:如《摩罗诗力说》的“诗人”,“性解”,“精神界之战士”,“神思之人”,“精神界之伟人”;《文化偏执论》的“先觉善斗之士”,“聪明英特之士”,“神思宗之至新者”,“大士哲人”,“卓尔不群之士”,“大士天才”,“超人”,“英哲”,“明哲之士”,“天才”,“新神思宗徒”,“社会桢干”,“绝大意力之士”;《破恶声论》的“硕士”,“觉者”,“独具我见之士”,“健者”,“性解”,“诗人”,“首唱之士”,“才士”等。这些褒义之词,同样表达了鲁迅的态度——赞扬乃至向往,即使脱离具体语境也能显示其含义。依据中国社会现实,“硕士”较可能产生;鲁迅赞赏曾在西方出现的“精神界之战士”。两者都是中国最需要又颇具力量的知识分子。这里且以“硕士”、“精神界之战士”为代表。
据鲁迅的典型词汇,知识阶级可分为“伪士”,“硕士’、“精神界之战士”,前者是中国已经且大量存在的文人,后两者是鲁迅正在发现的、呼吁在中国出现的知识阶级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形象,是现代知识阶级的代表。鲁迅对世界范围知识阶级的分类,彰显了中国知识阶级与西方知识阶级的差别——封建传统观念的“士”与资本主义民主、平等、自由观念的知识分子。事实上,鲁迅已使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尺衡量中国的知识阶级,因此有了对后者的批判和要求,批判来自鲁迅用价值相对主义重估传统文化—反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批判知识阶级固守的士大夫价值,同时,强烈的历史感使鲁迅考察过去、时下为着投向未来,在现实中促使知识阶级超越过去的囿限,进入新的价值领域。这种批判并非单纯的否定,是以肯定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为正面引导,提出对中国知识阶级的要求,该要求是鲁迅对传统价值、现代价值的反思并吸取后者的精神作为战斗的动力与源泉,以校正我国知识阶级保守派、改良派论者的偏至,抑或对其启蒙。
鲁迅对知识阶级分类的目的,也许在理论上并未明确,但在文学上的表现是相当明朗的。
2 “伪士”的表现
“伪”,一般解释为“欺诈,假装”及“虚假,不真实”之义,鲁迅所说的“伪士”之“伪”,有类似的含义,意在批判某些“文人”言行不一或表里不一的性质,也指“辁才小慧之徒”。
“伪士”首先是“妄行者”,是已经或正在推行自己的主张以及“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的人。“妄行”,似乎动机良好,至于后果如何,则出乎思虑之外。第一,“言武事”。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战争中显出军事装备的落后,洋务运动针对此弊进行救治;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实证了“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其惨败的结局是必然的。造成这样的局面,如果“仅见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且“文明亦不能无偏至”;遗憾的是他们“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第二,提倡“制造商估”。鲁迅亦揭露其大名词背后的真相:“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善于生存似乎是儒服之士的一个特长;这种本领的得来,鲁迅5 年后创作的《怀旧》仍在追问:“先生能处任何时世,而使己身无几微之痏,故虽自盘古开辟天地后,代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而仰圣先生一家,独不殉难而亡,亦未从贼而死,绵绵至今”?且“非从读书得来,必不有是”?博取名誉、“善自退藏”是传统知识阶级的本领之一。第三,持“立宪国会之说”。其“较善者”,“不得已,姑拾他人之绪余,思鸠大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其“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顾见诸实事,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搰,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捷径在目,斯不惮竭蹶以求之耳。”这里,鲁迅暴露了“伪士”假“多数”名义的最堂皇而隐秘的目的以及为赢得“多数”而包藏的双簧戏式的“瞒”和“骗”的技巧与手段。“故民中之有独夫,昉于今日,以独制众者古,而众或反离,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拒,众昌言自由,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鲁迅指出知识分子需保持的思想自由与政治手段须求的意见集中、管理统一乃至专制之间难以调和的牴牾。该观点在此后的二三十年时隐时现地存在,这种纠缠成为鲁迅无法摆脱的困苦。
总之,“妄行者”因“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是故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质言之,“妄行者”以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之鹄的对付甚至应付贫弱的民族文化现状,并无“根本之图”。其无法脱身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弊端,促使鲁迅寻找新的价值观并重估传统价值体系;他虽未说明“根本之图”为何物,但其时思考的“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问题,已涉及该范畴;且当时只能从国民中知识阶级入手,这是鲁迅批判并力图改造“国民性”艰巨任务的起步。
“妄行者”的优势在于有权力推行自认的主张,其条件是维护封建统治利益。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来由不感兴趣,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也不重要,而图谋自己的施展场地,并借此获得私利,扩大个人影响,成为时代主人。他们排斥知识阶级的自觉精神,只需盲从者,疾视歧见甚至不惜铲除异己,“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附,乃即以大群为鞭棰,攻击迫拶,俾之靡骋。”“妄行者”追求的不是真理,只是具体、浅薄的目标。
“伪士”的另一层含义是“妄惑”,“妄惑者”的言论往往与文化发展的方向相左,却不觉悖谬,企图占据话语霸权,以掩盖其他的声音并牵制民众的精神活动。“妄惑者”的言论分“破迷信也,崇侵略也,……”。“破迷信”是“伪士”欲破除“气禀未失之农人”、“向上之民”的“人心向上之需要”——宗教信仰。民间宗教是民众与世界之间的直接联系途径,是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方式,是长时期形成的民族习惯。然而,“妄惑者”多余地在民众与世界之间设立另一个“敕定”的宗教领域,妄图将民众诱入可奴役的领地,缩限民众自身活动的能力与范围;朴素之民的自觉范围变小,是将更多的自我权利移交精神主人,甚至以他人为皈依;精神依靠的存在,削减了普通人的尊严与价值。鲁迅力图破除的就是这一重幻影,呼吁知识阶级从驯化的道德枷锁下释放自己,也使民众解脱,直接投射于身外的世界。“朴素之民,厥心纯白,则劳作终岁,必求一扬其精神”,呈现其本身,发挥其至性,才能反映普通人的价值,并在与世界的协调活动中提升自我。民众的宗教活动即处理自身与客观存在关系的过程,应由民众自己的意识作用与认知活动体验、选择,不需要“伪士”的指手画脚乃至横加干涉。
鲁迅进一步揭露“破迷信”的“伪士”自身的精神状况:“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秘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不自知其谬,还“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造作躗言,必尽颠其隐依乃快”。“妄欲夺人之崇信者”的言论本身就带有矛盾,他们的破坏意在切断宗教信仰的习惯源流,在君权的传统势力下建构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以所谓最高的主宰为凭借,妄图使他们的理论系统更加完满。正像鲁迅后来揭示的,“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中国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① 鼓吹儒教的“伪士”与孔子对统治者有相似的心理结构。鲁迅暴露其费尽心机倡导“敕定正信”是为意识形态构想的动机,这在精神意义上恰与民众所供奉的神祉相抵触,“农人之慰”在于“稍息心体,备更服劳”,“伪士”之意在于“利力实其心”,其间的区分一在于精神的寄托,一在于功利的追求。故后者的恶行“烈于暴主远矣”!“妄惑者”企图以秽恶玷污“厥心纯白”之朴素之民。
“敕定正信教宗之健仆”破坏“农人之慰”的祸害还表现在,将宗教转化为统治阶层的御人工具,妄使儒教成为庞大的“群体宗教”,将民间宗教由一种底层阶级的活动转变为上层阶级的运动,图谋宗教与君权结合,诉诸统治者的体系来控制群众,让民众服从专制统治。将朴素的信仰之途沦为政治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破迷信”。如此,中国的宗教已被加入功利的因子而丧失信仰的涵义,“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② 因而“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有学者认为,“1895年康有为发动了一场著名的战役,要使儒学成为国家宗教,他和其他人顽强地追求这一目标,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去。事实上,这场战役的社会——政治目的大大超过了对精神的关怀。……它只是一个适应中国当代需要的社会调整,而不是坚信儒家之道需要这样的表达方式才构想出来的策略。”③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近代思想史也是一部与儒教斗争的历史。“伪士”充当卫道者的角色,他们从物质、制度层面进行的革新,以及标举儒教大旗以遂其导引民族文化潮流的初衷,是企图补救即将颓倒的封建专制之厦;但在世界文明“迫拶”之下,在中国民主文化演进中,封建专制秩序的颓势已无可挽回。鲁迅的批判,要使知识阶级里的“盲子”、“巨奸”等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状态醒悟。
“崇侵略”的恶声指“伪士”“祟强国”、“侮胜民”,并非“兽性爱国”,他们徘徊于“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祟侵略”与“人云亦云,不持自见”之间。鲁迅认为弱国之民应重在“收艳羡强暴之心,而说自卫之要矣”,他所批判的“崇侵略”是“伪士”奴性的另一种表现——就像阿Q怕赵太爷、 假洋鬼子,瞧不起小D、王胡,侮辱小尼姑一样——艳羡、惧怕强者,蔑视、欺侮弱者;只是“伪士”比阿Q多了一套迷幻的理论包装——“汝其为国民”?“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伪士”之所谓“中国”即皇帝的中国,而“皇帝”即儒家独尊逐渐形成的依傍势力,所有的问题都归于这个既实际又空泛的名称,“儒服之士”藏种种隐秘于皇帝名下。鲁迅曾揭露这古老的迷惑以减少其神秘性,“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贴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只有儒者们知道着。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④。掀开“愚君政策”面纱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皇帝失去存在性,还促使中国知识阶级及民众摆脱奴性;生活在对皇帝的幻想之中,人们适应从奴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其思路恰似“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里的后者,鲁迅要打破的正是各级奴才的逻辑。“伪士”不论妄行、妄惑,都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其“妄行”脱离时代,不顾念中国与世界文化思潮的差距,脱离现实,对国家的危机本质无甚认识,对民众的真正苦难茫然无知,“虽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而其心其术,违戾亦已甚矣。况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复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哉?”鲁迅反驳以封建道德、宗教禁地遏制人成为自己主人的“妄惑”的言论,力斥以虚构的价值体系掩饰真实意图的“恶声”,批判“灵府荒秽”的“伪士”依靠君权逃避知识阶级的责任及由此扩大的知识阶级的惰性。正因为“伪士”维护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道德伦理,“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造成“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的后果。鲁迅没有以任何形式的历史传统代替极力颠覆的封建秩序,而致力促使中国知识阶级的觉悟,彻底破除幻影,呼吁知识分子回归自己,发挥创造的潜力,逐步建造新价值的世界。
3 何谓“硕士”
“硕士”形象的出现,代表鲁迅对中国知识阶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破恶声论》里,“硕士”分两种情形。
其一,存在于中国现实的。
他们或许有救国救民于苦难之中的勇气和献身精神,“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贡献”,如邹容等;或许抱有高洁的志向,但“诸夏丧乱,外寇乘之,兵燹之下”,不忍目睹生灵涂炭,又无力改变现实,且不愿苟活,于是“赴清泠之渊”,以决绝的方式维护了“士”的尊严,希望以死警示国人,如陈天华等。在民族危难之际,这些“硕士”虽在志节等方面比“伪士”高洁且可贵,却未能充分发挥倡引民众的作用,遗憾地被淹没在“扰攘世”中。鲁迅既为中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欣慰,也为他们的“寂漠”惋惜,关于这类“硕士”的文字也属于“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写的”⑤ 罢。
其二,现实社会需要而仍未产生的“硕士”。他们可成为民众的精神向导,“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他们是民众的思想灯塔,“则中国之人,庶赖此数硕士而不殄灭,国人之存者一,中国斯托生于是已”。鲁迅渴盼的“硕士”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某个具体的形象,其具备的特征有:第一,在己身修成方面。首先,勇于向自己挑战,因最致命的对手常常是自己,故挑战的对象还包括甚至主要指向自身——停滞的或被动的存在,“英勇无畏之人,独立自强”,真实地直面自我,敢于扬弃昨日之我。其次,内在的信念不被外在的势力吓倒,“天时人事,胥无足易其心,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其言也,以充实而不可自己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以波涛之作于脑故也”,用至诚的心声做盾牌抵御随之而起的乱矢。他们“苏古掇新,精神闿彻,自既大自我于无意,又复时反顾其旧乡”,披厥心而成声,殷若雷霆之起物。”“返顾其旧乡”,即在“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的同时“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硕士”形象是知识分子在饱尝人世苦痛中积健为雄,保持奇伟悲壮的气概以驰骋人世。“硕士”的内涵是自我评价,不是社会工具价值;鲁迅重视民族文化的未来,故“硕士”的立说基于化价值。第二,处身知识阶级里,则“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谓之渐自省其内曜之成果可也”,有确信的人是“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他们在“伪士”之林永葆“神思之澡雪”,并将这一过程作为铸就自身的必由之路。故“硕士”的生命是动态的,他们不断地前进并且升越地推动自己,在不懈奋斗的途程中,提升本身便是目的,这种发展——重现人的最高潜能及自我超越的意志——乃是最高自由的表现。时代环境不仅不能囿限“硕士”,反而成为其展示潜能的必要场所;他们不是时代眼光的商品,不为他人所役,也不为传统价值所奴。在鲁迅眼里,“硕士”应成为知识阶级的主流,作为推动时代和变革环境的主力军。
鲁迅设计的“硕士”形象,重点在知识分子自我的张扬和对民众的启蒙。如但丁之于意大利,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果戈理之于俄国,“作至诚之声,致国人于善美刚健者;作温煦之声,援国人出于荒寒者”。尤其十九世纪“神思宗之至新者”,尽力宣扬个性主义思想,通过“文章”导引民众。“德人斯契纳尔(M.Stirner)乃先以极端个人主义现于世。……至勖宾霍尔(A.Schopenhauer), 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稀有;……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Kierkegaard)则奋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其后有显理伊勃生(Henrik Ibsen)见于文界,……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若夫尼采,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鲁迅盼望中国出现这样的“硕士”,以文章为载体,传达鲜明的思想,呼唤民众的觉醒。
尽管“硕士”有“超人”般的强力,但鲁迅发现现实中“硕士”难于出世的问题。“披心而叫,其声昭明,精神发扬,渐不为强暴之力谲诈之术之所克制,而中国独何依然寂漠而无声也?岂其道茀不可行,故硕士艰于出世;抑或众哗盈于人耳,莫能闻渊深之心声,则宁缄口而无言耶。”一种情况是勇敢地呐喊了,却未能将“至诚之声”、“自由之音”从“恶浊扰攘”中游离、凸现,如何使民众“为闻声而摇荡”?怎能使其声“深感后世人心”?另一种情况是前者的后果产生的负面作用——既未见成效,就不必呐喊了。此外,“硕士”的出现,需要“健者”在前方披荆斩棘,“嗟夫,观史实之所垂,吾则知先路前驱,而为之辟启廓清者,固必先有其健者矣”,然“顾浊流茫洋,并健者亦以沦没”,“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则中国遂以萧条”。“硕士艰于出世”的原因还包括,历史惯性推动下的强大旧势力使与之抗衡的“硕士”因新生而显得出头的力量不足;再者“硕士”的数量少,像“过客”那样执著追求理想、探索道路的艰苦卓绝的知识分子只是极个别的;还有整体文化氛围的问题,即缺少“培养天才的泥土”。
“硕士”本义指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之人,鲁迅既接取原有之义,复赋予崭新的内涵,“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而“硕士”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计划,面对“恶浊”的现实,鲁迅坚定地向“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强聒不舍”:“绍介新文化之士人”——“精神界之战士”及其影响力。这是改变中国知识阶级现状的一个必要步骤。
4 引介“精神界之战士”
“精神界之战士”与“硕士”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更坚定勇猛,更毅然决然,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不为顺世和乐之音”,而向所遇问题挑战,向思想的禁地探索,是“先觉善斗之士”,“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是战斗性思想家,是“说真理者也”;但在传统社会“非遂即人群之骄子,轗轲流落,终以夭亡”,成为“吾曹并时众恶之象”,是“失败的英雄”;尽管“精神界之战士”生平不幸,命运多舛,但他们不被旧价值体系阻挠,能承负艰难,展示知识阶级的现代职能,放射创造的辉光,是“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精神界之战士的精神,鲁迅后来还描述为:“有这样的一种战士——……他走进无物之阵……但他举起了投枪!”⑥ 他们所追求的也最重要的是,“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抗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逐渐产生社会效果:“往时去矣”,“旧习既破,何物斯存,则惟改革之新精神而已。”
拜伦等西方知识分子摆脱传统思维的桎梏,完全从自由、至诚、伟美出发,以坚定的确信和孤注一掷的行动“撄人心”:他们“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不同民族因有了这些“卓尔不群之士”的行动,一定程度改变了由群体组成的历史。
“精神界之战士”之“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鲁迅注重的是“反抗”、“动作”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
“精神界之战士”的“反抗”包含一种价值转换——对传统的道德伦理以及封建意识形态等价值的否定,“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凡正义自由真理以至博爱希望诸说,无不化而成醇,……现于人前,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也”。鲁迅热烈称颂刚毅果决的“反抗”精神,赞美“精神界之战士”的自主道德,因为这是积极的,奋进的,是知识分子自我肯定的表现。他们是知识阶级及民众“反抗”的动力。
“精神界之战士”的“动作”,是启迪民众在生活与思想方面发扬奋斗、进取与创造的精神,即意味着“战斗”:关心真理,重视发挥人的内在潜力,富有追求热情与质疑精神,“大都执兵流血,如角剑之士,辗转于众之目前,使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该“战斗”又不同于实际的参战,鲁迅向来反对不值得的“动作”,不论晚清时期参与革命活动的献身者,还是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因战斗被屠戮的生命,认为“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⑦。“战斗”意指不断超越以达到无限的自我及民众提升的行动。
赞扬“精神界之战士”体现了青年鲁迅的知识阶级理想,也反映了精英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图景。
5 “立人”思想的现实性
1906年立志从文的鲁迅力图改变麻木的国民精神状况,而中国的问题不仅在愚昧的民众,更在知识阶级,后者的蒙昧不只是自身的;再者,相较于民众,知识阶级易于改变;鲁迅将社会问题与知识阶级结合起来,试图从知识阶级走向社会文化。这就是青年鲁迅注重知识阶级的“个”对民族国家的作用而无暇顾及社会的共同基础以及人群共策共进一面的缘由。直到1925年鲁迅仍持此观点:“现在没奈何,也只有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说。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⑧。对此,鲁迅一面寻找知识阶级精神现状的历史原因,一面发现时代缺乏的虔敬、诚信、虞虑和理想主义精神,并把“伪士”普遍的“白心”缺失现象当作一个反抗的契机。
“伪士”的存在,不但延续了没落的传统文化,还进一步掺入近代的因素形成更其堕落的文化形态,“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⑨ 从“伪士”到“精神界之战士”的距离,就是维持现状的保守与除旧立新的创造之间的思想差别。也许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鲁迅通过比较,发现中国缺少“破坏”思想的知识分子,多的仅是封建体系文以载道的、惟为稻粱谋的、不见“白心”的“士”。这一发现,不啻暴露了中国在世界落后的真正的——人的——原因,而非物质或制度的原因;况且,这部分人在中国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是介于上层与底层之间的肩负民族文化改进重担的知识阶级。
鲁迅早期著述里“伪士”、“精神界之战士”的对立出现,是对世界范围的知识阶级思想的平行类比,是对不同思维模式的对照,是平等观念下的考察方式。这是鲁迅发现中国知识阶级存在的问题之枢纽,平行比较是手段,发生影响是指归。鲁迅一方面批判“伪士”,另方面塑造“硕士”;批判“伪士”与赞扬“精神界之战士”又成为鲁迅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种方法,批判是为了矫正偏颇,赞扬是为了树立楷模;两者的目标都是塑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事之两面。
鲁迅设计、引介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提出了知识阶级从封建体制的“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问题。鲁迅向颓废的文化价值挑战,希望树立新的价值观念——以强者的道德代替弱者的道德,以“硕士”、“精神界之战士”取代“伪士”,即“立人”的思想。鲁迅的最终目标,不仅是知识阶级思想的改进,还由此达到国家的现代化,民族的强大。
鲁迅注重的知识阶级导引社会文化思潮这一特点,是由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背景决定的。处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弱势位置,寻找被动挨打的原因以及追赶先进的心理特征定然突出,鲁迅的民族存亡危机感尤为强烈,属于日本学者尾崎文昭所谓的“追赶型的现代性”特征。在这种氛围中,强调知识阶级的社会文化功用是必然的,也是当然的;知识分子个体间思想的其他差别则从属于救亡、启蒙的主题。但知识阶级在将种种革新付诸实施的过程中,由于个人背景的差异和思想的变化,尽管具备良好的初衷,却不断出现与目标背离的现象,这就是知识阶级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知识阶级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论借鉴外来的什么思想、制度,都不会真正改变中国的现状。鲁迅批判“伪士”,赞扬“精神界之战士”抓住的正是该环节的关键——知识阶级自身的改造。
早期鲁迅“立人”观形成的一个原因是受卡莱尔“文人英雄”思想的感染,青年鲁迅崇信文章的社会作用。他不仅在《科学史教篇》里称赞卡莱尔,还在《摩罗诗力说》里赞同他的一番话:“英人加勒尔(Th.Carlyle)曰,得昭明之声, 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并借鉴卡氏诗人英雄所发心声的强弱对民族存亡作用的观点。现代印刷技术使得思想言论能更广泛地产生社会影响,这是科技进步使文人可能成为英雄的必要条件。要指出的是,卡莱尔的文人英雄观念对鲁迅熔铸自身“精神界之战士”的催化作用。
又受西方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浸染,如尼采等“新神思宗徒”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个人主义思想,“立人”观即大胆地向处于传统氛围的知识阶级发出“违言”。这种“违言”,在鲁迅就是对知识阶级启蒙的决心和信心,由于他们“妄行”、“妄惑”带来的危害,还没有完全被自身认识,这需要站得更高的知识分子呐喊,“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⑩ 就是针对无鉴别力的“宝赤菽以为玄珠”的智识者的启蒙。
处身于维护封建意识形态的“伪士”之中,“精神界之战士”是对付“扰攘”现实的一种可凭借的想象。青年鲁迅崇信“精神界之战士”整合理性与热情于一身的力量,即清醒的启蒙职责与从不消减的反抗斗志。在各种传统加速崩溃但仍对抗崩溃的世界,古老的文化传统,貌似坚固的社会结构,封建的道德伦理等,正走向边缘又垂死挣扎;鲁迅力图消解没落的文化,并找寻催促其崩溃的源泉,预见新声,以求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文化系统。“立人”思想即其可实行的线索,它糅合启蒙主义理性与浪漫主义热情,崇奉“摩罗诗人”和“新神思宗徒”的个人主义精神,注重对人的能动性的挖掘,以发现启蒙思潮的真谛;又以自由热情对付现实的昏暗,以浪漫的理想主义鼓舞启蒙的斗志。
鲁迅对“立人”观的实践,是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彻底决裂的代表,因为鲁迅没有像康有为等人那样,继承传统的价值——容纳过去以形成一个新的形式,而意在征服未来——创造新的价值,以强烈的责任感关怀民族命运。鲁迅的“动作”证明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历史文化的主要推动者。
“立人”观作为鲁迅思想发展的原点,融合了中外各种不同的乃至扞格的观念,形成可操作的步骤:“精神界之战士”是青年鲁迅发现的“新声”,它是最高人格力量和精神楷范的形态;“硕士”是鲁迅综合中西知识阶级特点设想的适宜于中国文化环境的理想知识分子形象。实际上,他们是超前于中国现实的精神产物,“真的知识阶级”的产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而此后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问题的观点是在“立人”思想之上的调整。即使在鲁迅“立人”思想提出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即“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竞争的规则,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途。从个人的角度看,“硕士”、“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是知识分子铸就自身的重要参照,鲁迅设定的“白心”、“寻新声”等标准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基本依据。
注释: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②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③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387页。
④ 《华盖集续编·谈皇帝》。
⑤ 《坟·写在〈坟〉后面》。
⑥ 《野草·这样的战士》。
⑦ 《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⑧ 《华盖集·通讯》。
⑨ 《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⑩ 《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标签:鲁迅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文化论文; 摩罗诗力说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