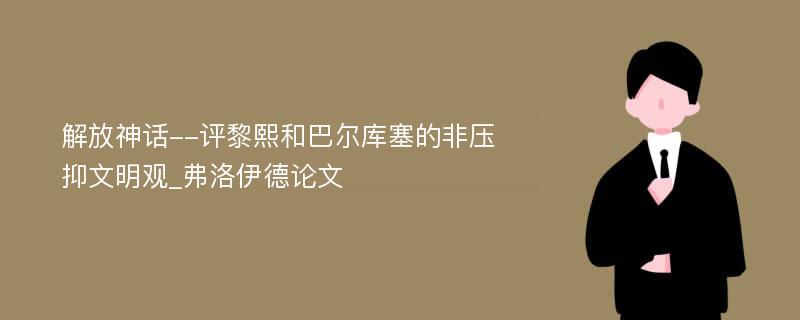
解放的神话——评赖希及巴尔库塞的非压抑性文明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话论文,评赖希论文,文明论文,巴尔库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论及的建立在非压抑性文明观基础上的所谓解放理论,曾在60年代的西方青年造反运动中成为反叛者的“圣经”,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由于这一“解放理论”的两个代表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性思想联系在一起,并且都认为自己的学说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本文便拟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开始。
一
早年马克思曾经对卢格说:“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其中之一,是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以其否定的哲学观念,揭示了黑格尔“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实体哲学在根据上的虚假性。
放眼于“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的马克思,着眼于人的解放,但他在资本主义“理想化的王国”中,却处处看到人的困境。他极具批判意识地指出,商品拜物教的物化的力量正在把人置换成物质的筹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饱满的人道情怀揭示出,体现着人自我创造的属人本质的劳动,正在由于它和它的生产者与产品的分离,而沦落为被动的、无意义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的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异化了的劳动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从而使人不幸地成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牺牲品:
社会生活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的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7页。)
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所造成的精神贫困直接把人类文化创造的英雄史诗篡改成商品拜物教的牧歌,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和艺术与诗歌相敌对,所以只有使人从异化所造成的精神贫困中解放出来,人类才能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自由地创造和发展自己及其文化;只有实现对私有制的扬弃,才能从根本上摆脱那种“史前史”的异化的阴影。
马尔库塞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判性的思想成果时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正是沿着“对这个社会的否定及转化变成了对解放的真诚展望”(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在此有必要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是实践的哲学,它不仅仅旨在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正是因为这种批判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由此产生的对人类命运的“真诚展望”才进入人类历史根本变革的社会场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理解为“历史的真正基础”,人类的物质的实践和革命的实践构成了真正的改造世界的解放力量,实践是人类“全体的活动”。对实践的重视甚至使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将实践看成最终将取代哲学本身的概念。在马克思不断地把思考的重心转向对阶级社会的历史进行批判后,正是实践的观念赋于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辩证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对应着人性——异化——人性的复归)以具体而真实的历史内容。
二
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在20世纪的理论结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文化既严肃又幽默的一个场面。在描述“解放”学说的发展时,我们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发的异化理论和人与自然的解放的观点,对于我们这里将要论及的“解放”学说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批判上所获得的深度与广度吸引着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的人们,他们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结合起来,从而把精神分析导向激进的“解放理论”。
早在30年代,赖希就较早地致力于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这种统一(尽管这种统一最后几乎被他所放弃)。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学说的深刻的革命性为揭示当代文明的弊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判的人类学前提,并由其获得了心理学的深度内省——这种内省的结果是对人的“性格结构”的审察,而“性格结构”的概念顺利地沟通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因为意识形态深深地内化在个人的性格结构中。在赖希看来,正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统一,才把冲突的社会学和冲突的心理学统一了起来。社会过程和心理过程的同一也进一步把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从非历史主义的定格中拯救了出来,从而为本能的解放留下了乐观主义的现代启示录。因为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家庭及宗教等通过对人的性的压抑,把意识形态锚定在人的性格结构中。社会和家庭作为制造驯化动物的工厂,是同人的性满足的需要根本相对的,而性的压抑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完成其对人们经济奴役的心照不宣的手段,并且社会通过性压抑把人沦为消极被动的牺牲品,使他最后磨损掉自由意识和人格的棱角,向外在的权威俯首称臣:
对性需要的压抑造成智力和情感作用的普遍衰退;尤其使得人们缺乏独立性、权力意志和批判能力……,正是通过强制的父权制家庭,性道德的固置以及它在人身上引起的变化,造成了一种特定的心理结构,这一心理结构就是任何权威主义的社会秩序的大众心理基础。(注:赖希:《性欲解放》,转引自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
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中,赖希指出,正是这种性的压抑和置换的机制的成功,才根本上导致了现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注: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性的压抑和性禁忌导致经济奴役、自由意识的消退和法西斯主义的膨胀,以此出发,赖希把性和本能的根本解放发展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论,这种性的解放是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相抗衡的一种特别的潜力。在描述性解放的乌托邦时,赖希批判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现实主义与悲观主义倾向。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的非历史主义的生物学困境和文明的发展与压抑的不可避免的悲观主义格调,否定了人类从压抑中解放的任何可能性,从而使精神分析同时面临着成为个人适应压抑性文明的改良主义命运的危险。因此,必须加强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立场,让精神分析理论在历史性的冲突不断加剧的时刻,成为性解放的进行曲和新的文化革命与性格结构革命的号角,从而将压抑性的社会文明改造成非压抑性的文明。
我们不否认赖希在其所开辟的独特的思路中对当代社会与文明困境的某些合理的揭示,特别是他对法西斯主义起源的社会心理思考,为人们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事实上,赖希的这种工作深深地启示了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以及阿道尔诺等人在《专制的性格》中对法西斯主义起源的杰出的探索。然而,赖希关于性解放的思想却由于倾向于把本能与文化简单地对立起来,以致于他所提供的乌托邦式的性政治学说同时也暗含着文化及其不朽性的新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意味。
三
同样一曲爱欲的田园牧歌,马尔库塞要比赖希唱得更富有诗意。马尔库塞把包括了一种新的情感和感觉上的美学片断的爱欲看得比本能的性欲具有更辽阔的意义,因而他的解放学说不至于被草率地认定为某种慌慌张张的性意识。它原则上也是一种乌托邦,只不过更多地是一个审美解放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为他的“非压抑性文明观”染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和赖希一样,马尔库塞也致力于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统一。作为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的异化和压抑的反抗,马尔库塞把人的主体性上升为一个本体论的概念,它既是内驱力、本能,而且也是通过对象化而越出自我之外的历史的社会的产物,因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的人是一种对象的存在物”。通过这个“对象化”中介,马尔库塞把世界和社会的存在这一根本的特征引入了感性的人的本质存在,并在两者的历史生成过程中去考察人的命运。如果说在这里,马克思所发现的异化与复归的人类学图式为马尔库塞提供了对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命运的考察坐标的话,那么,通过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则进一步认清了这种工业文明对人的本能和感性的压抑所造成的更加沉重的心理上的后果。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统一在他那里成为了解放人与自然的理论基础,并且也是他所高扬的“非压抑性文明”的乌托邦的真正的诞生地。事实上,无论是对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都没有跟随到底,他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实践性,抽象地发挥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异化与复归的批判思想,将他的批判哲学的使命界定为“通过抽象思维的工具担负着保证人的需要、恐惧和愿望得到解放的使命”(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289页。)。
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通过对弗洛伊德关于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对立的探讨,马尔库塞也像弗洛伊德一样指出,人的文明史就是他遭受压抑的历史。这种压抑的历史绝好地说明了在现实原则的支配下,人与文明的窘境。和弗洛伊德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并不把文明与人的本能看成是截然的永恒的对立面。弗洛伊德曾悲观主义地把压抑看成是文明必须偿付的代价,因此,弗洛伊德实际上否定了任何乌托邦存在的可能性,相反却认可了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英雄的苦役的意义。(注:参见拙著:《文明的阵痛与新生:西方现代反主流文化研究》,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63页。)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压抑性的文明在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它将粉碎一切生活的诗意,使人带上沉重的罪过感;弗洛伊德由于把文明的某一特定的、不合理的历史形式假定为文明本身,从而便否定了非压抑性文明的存在的可能性。
马尔库塞通过把弗洛伊德的范畴历史化,把它们从绝对的永恒真理转化为对某个特定的文化阶段的批判,作为解放理论阐发的前提。从这样一种前提出发,马尔库塞对现代大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总体异化展开了激进的批判。他首先为精神分析的批判性发展引入了两个重要的概念:“额外压抑”和“操作原则”。这样,作为一般文明所要求的基本压抑的现实原则与作为特定的历史文明的阶段所要求的额外压抑的操作原则之间的区分就成为了可能。在他看来,额外压抑为社会统治所必不可少,它与(基本)压抑的区别在于它是为使人类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对本能所作的必要的“变更”;而操作原则是现实原则的现行历史形式。
这个理论的提出,是马尔库塞结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一种尝试。在弗洛伊德那里,基本压抑是为了创造和保护文明所必需的对本能的一套限制,即对付物质需要所必需的劳动,这种劳动根本上是对人的快乐的抑制,但它是生物为了生存所必须的。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指出,生产的劳动组织形式与分配形式是社会强加于人的,在这里社会统治阶层发展出一套对人的本能的超出文化之外的额外的压抑,而现代社会正是在这里反映出它巨大的不合理性。在现实原则对人的爱欲进行抑制的时候,现代社会已以某种特殊的社会统治形式偷换了“现实”的名义,对人施加各种过度禁忌,这是操作原则对人的进一步非人化的暴力。他通过这两个批判性的概念,集中说明了文化与爱欲之间的对立——即压抑性文明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结果。
马尔库塞继续批判道,这种特定的压抑不仅造成了人的快乐原则被废黜,而且还导致了人性的根本异化和创造精神的消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工业文明所修饰的整个社会(如美国)反映了一种奇特的悖谬:它增加了人的资源和物质需要的满足,同时又以外部控制和官僚管理的现代社会的总体异化,反映了人已经不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相反,却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控制形式中不断地沉沦,沦为物化的牺牲品。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继续了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指出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以面包和牛排的小恩小惠把人改造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人,技术通过建立富裕的生活而成了一种对人的新型的控制方式,使那些不满和反抗社会制度的人得到了安抚,从而平平静静地用消费的平均化把人的激进的反抗抹平,这正是解放的障碍;而意识形态成为把人的丰富而特殊的灵性打制成“一个文化机器的齿轮”的工具。通过对广告语言、语言分析、实用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文化的保守性的批判,马尔库塞认为,压抑的方式已经以逻辑的规范的思想方式表现出来,而且断言以支配自然为基础的科学和技术根本上就是压抑性的;社会所认定的理性是一种远离解放、封闭反抗的门栓,它根本上把人类关闭在单向度的铁门中。(注: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在对额外压抑和操作原则的不合理性的考察基础上,马尔库塞顺理成章地指出了现存现实原则的历史局限性和压抑性文明的不合理性,并转而揭示了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马尔库塞指出,压抑性文明的成就本身似乎创造了逐渐废除压抑的前提,特别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提供了足够的资源,并把生产必需品的必要时间降低到了最低的限度,从而使苦役的时间转变为欢乐的时间成了可能。这是技术在被异化为官僚式的控制力量的同时所暗含的一种福音,这种福音也是把劳动从异化劳动中重新超度出来的力量。因此,现存的操作原则通过自己的成就,提供了否定自身的前提。
马尔库塞毫不迟疑地指出,这种力比多非压抑性的发展方向就是幻想的乌托邦。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的发展破坏了快乐原则与否定原则的前历史的和谐,以致于只能退居到幻想中反映出对压抑性文明的超越,这种幻想指示着一种新的现实原则的要求。因此,把弗洛伊德认为压制在潜意识中的前历史的和谐重新引回到现代文明中来,就意味着一种前进中的特有回归,这种回归是批判的力量,也是解放的形象。正是这种幻想,把过去、现在、未来编织成快乐与解放的交响。
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幻想及其所展开的“被压抑物的回归”展现了一种新感性的生命力,它也是对现行的统制框架的破坏与超越,因为它不顾一切理性的作用而保护了受理性压抑的人和自然要求全面实现的欲望。“幻想”的确把马尔库塞带得很远,带到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的河边,带到俄耳浦斯的竖琴旁。在这里,他否定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曾经认可的以忍受苦难、压抑的持久代价而换取人类进步的文化英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而诗意般地赞美着自恋和音乐的感性敞开中,尽情生活的那喀索斯和俄耳浦斯。对于已经消失了灵性的西方现代机械的日常生活来说,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是对现代人发出的诗意的解放的呼唤:
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对世界的经验否定了那种维系着操作原则的东西。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被克服了。存在被看作是满足,它把人与自然统一了起来,人的实现同时也直接是自然的实现。……“世界正在趋向于美”,在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的爱欲中,这种趋向得到了解放,自然物能够自由地成为它们所是的东西,但是做到这一点,必须取决于爱欲的态度。只有在爱欲的态度中,它们才获得自身的目标。(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21页。)
这种爱欲从自恋出发而扩展到客体中的力比多,最终意味着一种主客体相统一的一元论,它暗示着一种升华,这种升华不是基于对力比多概念的一种强制的置换与压抑,而是源于力比多的扩展。在马尔库塞看来,在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身上体现的自恋和同性恋,实际上并不是某种禁欲的理想,而是对传统的压抑性的生育性欲的抗拒。因此,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身上的爱欲意味着一种人与自然的彻底解放。解放自然界也意味着解放人自身的自然。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尔库塞这样指出:
人们发现(或者确切地说是再发现),自然界成了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因为在剥削社会中对自然界的损害加剧了对人的损害。发现解放自然界的力量以及这一力量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种新型的力量。(注:马尔库塞:《自然与革命》,见《西方学者论〈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我们有理由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思想最终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曾经与他分道扬镳的老师——的后期思想是相呼应的,而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则表现出和东方的自然意识的智慧的契合。
四
赖希及马尔库塞从独特的爱欲解放的角度,引申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及统治机制进行激进批判的“政治学”意向。然而他们对“非压抑性文明”的竭尽全力的呼唤,却是一种在历史性的退化中寻求对压抑性文明的治疗。他们倡导生活的英雄,而含蓄或公开地否定文化的英雄。然而我们相信,文化作为人类的英雄史诗,正是对人的有限性的一种特别的救赎。因此,我们认为,纯粹的爱欲乌托邦的神话最终将归于流产,因为爱欲并不是生命的一切,正像文化人类学家E ·贝克所指出的,当进化给了人一个自我,一个肉体之上的符号的经验世界,它就把人一分为二,给了人一个额外的负荷。
人类为了写下英雄诗,而必须承担这个负荷。我们相信,这不是人的进化历程中神的施予,并且根本上它也不是灾难性的一步。它似乎在不断地重复着这样一个隐喻的真理:人为了确证自己而必须走出伊甸园。人从自然中走出来,既带着自然给他的原始烙印,同时又不断地清洗和修正着这个烙印。他注定了需要在奋斗的痛苦中去寻找制胜这种痛苦的符号性的文化归宿。我们不能不被马克思为普罗米修斯写下的那句颂辞激励着——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上最伟大的殉道者!
非压抑性文明的乌托邦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它不仅意味着对文化英雄的背叛,更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实质性的颠覆。马克思主义以它对批判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号召人类担当起改造世界的使命,并强调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必须面对真实的社会历史的变革,人类解放的实践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质的实践和革命的实践。但是我们看到,赖希及马尔库塞的解放理论却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实践性抽象地割裂开来。他们抽掉马克思主义解放学说中具体的真实的历史内容,将实践的历史演绎为观念的历史,创造出一个非压抑性文明的语言乌托邦。
“非压抑性文明”的乌托邦及其在现代西方青年反主流文化行为中的影响和灾难由此不难理解。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这也许才是所有标榜为“解放”的学说应该回到的实践的起点。
标签:弗洛伊德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神话论文; 乌托邦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