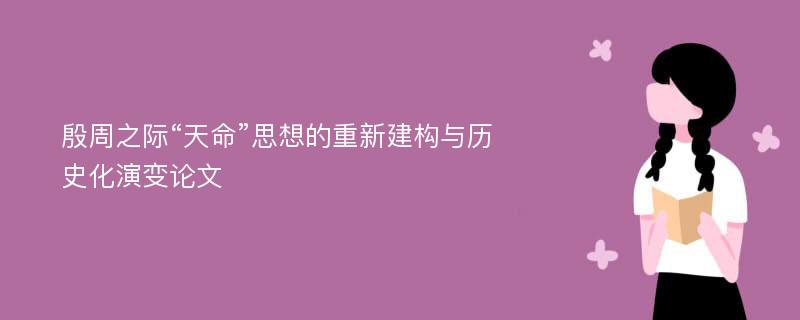
殷周之际“天命”思想的 重新建构与历史化演变
胡兆东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儒学院,北京 100080)
摘要 :殷周之际,中国的政治文化与思想观念发生剧烈变动,殷人的“帝”信仰被周人的“天”信仰所替代,周人赋予“天”以伦理属性和道德特质,“天命”的内涵也被德性化,注入了“敬天”与“保民”的内容,开启了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巫觋文化向人文主义的转型路程。周人通过天命的伦理化论证以及“文王受命”“文武受命”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强调了殷人的天命之终以及天命向自身的转移,论证了周兴殷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而奠定了两周天命思想的主基调,对春秋各家产生广泛影响。
关键词 :殷周;天命;帝;文王;武王
一、殷周的天、帝观念转变
王国维先生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231经过殷周之际的观念革新和政治重构,中国几千年政治与文化的基本范式被确立。该次变革中,天命思想的嬗变无疑是一个重大命题,在“绝地天通”余音未绝的殷周之交,时人的观念立足点和政治立足点仍然体现在下民与上天的交流之中。而在天命思想中,“帝”“天”是两个首先需要被界定的核心概念,天命思想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在这两个概念内涵与地位的转变之中。正如白川静先生所言:“殷周革命当然是政治的与军事的事实,但可以断定在这个古代王权更换的背后,有着作为帝之直系后裔的殷的王权观念与依据对天之信仰而来的君权神授的周族的观念之间的古代宗教战争。”[2]
那么何为帝?《说文解字》曰“谛也。王天下之号也。”[3]2《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称帝。”[4]53很显然,这都不是字源意义上的原本涵义。清末吴大澂认为,“帝”原始含义为花蒂,刘复、王国维、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皆从此说注 转引自石磊.先秦至汉儒家天论新探[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 。并且,郭沫若根据对殷商卜辞的研究,发现商王多称自己的父考为“帝”,如武丁称其父小乙为“父乙帝”,武乙称其父康丁为“帝丁”,称文丁为“文武帝”,“帝乙”“帝辛”之说更是数不胜数[5]321。按此,则“帝”为生命初始、祖先崇拜。詹鄞鑫则进一步认为,“‘帝’的语源义是生育万物的意思。”[6]裘锡圭则根据《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而断定“帝”与“嫡”通,下民之王实即“皇天上帝”之“元子”(嫡长子)[7]。无论如何,这种初始含义的“帝”自天上而运用到人间,以至天帝也被人格化,被赋予了自然神司掌天文、气象甚至人间吉凶祸福的权能。余敦康和张岂之都指出,殷代的天神信仰虽然已附上一定的社会属性,但仍然带有原始的自然崇拜的特点,“它如同一个没有理想的暴君,权威很大,而喜怒无常,人们只能诚惶诚恐地屈从它。”[8]163
柏拉图曾说过:“思维是灵魂的自我谈话”。有了思维的数学课堂才是有灵魂的课堂,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中思维才能变得更敏锐、更睿智、更理性。因此,在数学课堂上必须紧扣数学之“魂”,以探促“思”。当然,小学数学的思维训练,不仅要关注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还应该关注计算的过程,更应该关注计算的思维过程是否最优化,通过对思维过程的优化,探寻最佳的思维方法。
周人则将帝的自然力赋予“天”这一自然对象,同时“将天德性化和理性化,自然力不再狂乱无序,而是恒常地蕴含了正义的属性和德善的指向,灾异则在天人感应的模式下由君臣的失德承担。”[9]如殷商卜辞云“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10]表达了殷人对上帝操纵风雨的怖畏与期望。而在周人的叙述中,则变成“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诗经雝》)这不仅是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向,更是巫觋文化向人文主义的转向。
那么何为天?《说文解字》曰“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3]1《白虎通》曰“镇也,居高理下,为物镇也。”[4]499至高在上而居高理下,这与“帝”的功能有很大的重合,因此刘宝才等先生认为商代的天即上帝,帝本是自然天神[8]139。而这种生育万物、掌握天文气象乃至人间吉凶祸福的“帝”,在西周时期则转变为周人信仰的“天”。据郭沫若考证,把至上神称作天的用法应发生在殷周之际,故周初的彝铭如《大丰簋》铭文、《大盂鼎》铭文中,以天称帝的用法已屡屡出现[注] 《大丰簋》铭文载:“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大盂鼎》铭文载:“古天异临子,废保先王,□有四方。”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郑玄说:“据其在上之体谓之天,天为体称……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帝为德称也。”[11]766他认为“天”是从位置角度讲的,“帝”是从德性角度讲的,“天”“帝”同物异名。陈立在《白虎通疏证》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看法:“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4]5周人给“天”赋予了一定的理性原则与道德意志,如《尚书·酒诰》云:“天非虐,惟民自速辜。”[12]153下民的言行对自身命运改变上拥有了更高的权重,上天的无理性被大大降低。“天”虽然仍具主宰性,但其内涵在悄然变化,从无理性走向德性充盈,走向合于一定伦理准则的抽象存在——即从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向义理之天转化。
从思想与政治互动的角度看,周人对“天”的崇祀或是出于与殷商相区别的政治目的。殷人把上帝与自己的王族祖先紧密绾合为一,故在周人把“帝”普遍化的同时[注] 傅斯年说:“周人袭用殷商之文化,则并其宗教亦袭用之,并其宗神系统中之最上一位曰‘上帝’者亦袭用之。上帝经此一翻转,更失其宗神性,而为普遍之上帝。”见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0。 ,“天”把“帝”架空,这既是信仰理念的不同,也是政治旗号的更易,即是说,周人对“天”的崇祀一开始就打上了政治烙印。王震中先生从人类学的解释维度出发,认为“天”本姬姓族最大的图腾和宗神[13]。盖姬姓周人乃黄帝族裔,《国语·周语》云:“我姬氏出自天鼋。”[14]124所谓天鼋,乃周人族徽铭文,即是黄帝之“轩辕”。“天”由图腾走向部族宗神,最后发展为至上神。故知“天”的背后蕴含着周人的天帝信仰,在克商之后以“天”代“帝”也就不足为怪了。王和先生则从宗教源流的角度讲,认为殷人历代祖先战功卓著,高踞于各族之上,这形成了殷人强烈的祖先崇拜信仰,也是殷人“祖帝一元神”思想产生的原因;而相比之下周人历史则乏善可陈,作为一个“小邦”备受其他强大民族的欺凌,正因于此使得周人在强大起来之后,把功绩上归于“天”这个无形的至高神,而不是归功于弱小的祖先,故形成“天”与“祖”的二元神宗教观[15]。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也说过类似的观点:“殷代的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周代的帝王宗教观是二元的。一元的宗教观,指殷代的先王和‘帝’都统一到祖先崇拜。……在周人的手中,先王和上帝被分开来,但又在神秘的宗教观念上被结合起来。”[16]
二、周人对“天命”思想的重新建构
进入新世纪,信息技术、智能智造、生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人类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进入到创意革命的时代。创意、创新、创造成为时代发展的亮点。
然而文王伐商未果而中道崩殂,伐商的合法性危机和受命的重新阐释任务再次摆在周人面前。陈梦家认为周人受命有“文王受命”与“文武受命”两说,而现存金文仅有“文王受命”而无“武王受命”,故西周只是以文王为受命者,武王只是嗣文王作邦[36]。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云:“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唯)周文王受之,(唯)武王大败之,(成)氒(厥)(功)。”[37]174祭公为穆王时人,可知最晚到西周中期,周人仍只认为文王受命,而武王只是绍继文王的事业,克商定功。《礼记·中庸》亦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11]1436甚至在《逸周书·商誓解》中,载有周武王自己对于“受命”的看法,武王说:“上帝弗显,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纣!’肆予小子发,不敢忘天命。”[38]伐纣灭商的天命是文王承受于天的,武王只是“不敢忘”而已。一直到西周中后期,才开始出现“文武受命”的说法,如乖伯簋铭文:“不且玟、珷(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17]师询簋铭文:“不(丕) 显文武,膺受天令(命)。”[17]
西周天命观……肯定天命神意的主宰作用,但这种主宰作用不是体现为宇宙和人类安排了一个必然性的链条,而是根据事物的发展和人类的状况随时加以控制、干预和调整。……是伦理宗教面对社会历史、人类命运所产生的一种理解、要求、思想,并把这种要求诉诸天命论的形式。[18]224
IMF:亚洲需加强政策缓冲以应对不确定性。5月25日,IMF副总裁张涛在亚洲货币政策论坛上发言表示,亚洲需重建货币和财政缓冲,增强经济韧性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张涛指出,亚洲经济短期向好但面临潜在风险:如外债大幅增加,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46%上升到59%,私人部门债务高企;财政平衡继续恶化,平均赤字已达GDP的1.1%。
西周的天命观是“有常”与“无常”的统一。“无常”是指天所命赐给某一王朝的人间统治权不是永恒的,是可以改变的;“有常”是指天意天命不是喜怒无常,而有确定的伦理性格。[18]225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装机容量从2010年的30 GW增长到2017年164 GW,年均增长率为28%。根据我国“十三五”电力系统规划研究表明,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在2020年将达到33%,2030年将提升到50%。目前,我国的“三北”地区出现严重的弃风问题,2017年甘肃、新疆、蒙西、吉林弃风比例分别达到33%,29%,17%,21%。究其原因,风电消纳问题是新能源发展的主要挑战。为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我国已经在东北和新疆地区试点调峰辅助服务市场。针对风电并网后风电消纳所带来的备用问题,本文介绍并总结了备用容量的确定方法、获取方式以及费用分摊的方法和原则。
殷周之际的“天”从无理性演化为有理性,这种上天理性的确立其实也反映出下民理性的确立。盖自上古时代“绝地天通”后,统治者垄断了与上天的沟通权,商王既是政治领袖,同时为群巫之长,人间事务皆要通过占卜、祭祀请示上帝的意志;而周人则在敬天祭神的同时,把施政着眼点放在下民意志与自身德性身上,其宗教色彩趋于淡化。“酒神精神”的殷商信仰狂热,嗜祭虐民,仪式铺张,统治奢靡,不仅对牲畜、食物的浪费毫无节制,而且频繁采用人祭[5]241。而“日神精神”的周人敬天法祖,修德保民,这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前提下以人为本位的伦理体系的确立。“既然天是有伦理理性的可知的存在,人所要作的,就是集中在自己的道德行为上……而社会的统治者尤必须了解,天命即体现为民众的欲求。”[18]230《尚书·牧誓》云:“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12]118陈来先生认为,“恭行天罚”就是由人来执行天对某些人的惩罚。而武王列举的商王罪恶如“昏弃厥遗王父母弟”“暴虐百姓”等等,可以看作从反面表现出了重视善德的意识,因为天之罚是与商王的这些德行的罪恶联系起来的。[18]196-197所以周人认为,若要保天之命,必须以德治政,即“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
周人的“崇德”既是一种内在道德律,也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方式,它一方面表现为敬天,另一方面表现为保民,敬天与保民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与殷商的“残民事神”正相对立。所谓敬天,自是对至上神“天”(或曰天帝)的崇祀,即“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诗经·板》)而由于周人祖先神常伴随天帝左右[注] 《诗经·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所以这种对祖先神的祭祀往往与祭天重合为一,至上神始祖化,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完美而牢固地结合在了一起。所谓保民,即奉上天之命以安养、保护下民。如“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尚书·多士》)“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上天的意志不再高深玄虚,不再夐远难测,而是深藏社会与政治运行的全部过程中,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国民身上,统治者唯有保持忧患意识,唯有“明德慎罚”才可符合上天的意志,使自己的德性得到圆满,即所谓“以德配天”。清儒黄中松云:“所谓‘天命’者,天岂谆谆然命之哉,以行与事示之而已。虞芮质成,诸侯闻而归者四十余国。人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也。”[22]把天命归结为人心之所向,可以说是“以德配天”最好的诠释了。正如陈来先生所说:“在西周时代,虽然天帝被认为是人间王朝统治的终极合法性的决定者,但周代的政治文化不重视神灵崇拜,巫觋在政治结构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虽然周代鬼神祭祀具有更加完备的系统,但在政治实践上不具有中心的地位。……‘神’越来越成为形式上的合法性基础,而‘人’越来越成为实质性的合法性根据。在‘王’与‘民’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18]241-242自此之后,社会的主题从“神—人”关系转为“人—人”关系,“天命”彻底走上伦理化和政治化之路,它与社会和政治紧密联结,开启了后世几千年“天命—民意”的政治法理观念。
周人通过天命的伦理化论证,强调了殷人的天命之终以及天命向自身的转移,论证了周兴殷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尚书·多士》云:“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12]170也就是说,并非是周人觊觎神器,取殷代之,而是上天惩罚“允罔固乱”的殷人,把天命转交给周人代管而已。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周人以蕞尔小邦,国力远逊于商,居然在牧野一战而克商。周人一方面对如此成果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必须以上帝所命为解;另一方面又必须说明商人独有的上帝居然会放弃对商的护佑,势须另据血缘及族群关系以外的理由,以说明周之膺受天命。于是上帝赐周以天命,是由于商人失德,而周人的行为却使周人中选了。”[23]
三、周人天命思想的历史化演变:从“文王受命”到“文武受命”
虽然上天把天命转予周人,但并非直接施授于族群,而是对接族群之长——周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王受命”“文武受命”作为重要的思想概念在有周一代占据重要的文化位置。《诗经·文王有声》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21]250《尚书·君奭》云:“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12]179至于“文王受命”起于何时,千百年学者聚讼不断,或云起于“太姒之梦”,或云起于“平虞芮之讼”,此外还有“赤鸟”“嗣位”“得征伐”的说法[24]。前三说为受天命,后两说乃受商王命。而文王受谁之命、以什么形式受命,亦是一桩公案。
共产党人的哲学,永远都是在艰困中开拓,在阻难中前行,在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道路上,我们的哲理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定信念,奋发进取,矢志不移地奋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强化和凸显的,则也正是我们雄威壮美、如钢似铁的道路自信!
几个菜品,做得还算精致。辛娜终于放下了手机,屏却一直亮着,是微信聊天的界面。几口菜下肚,辛娜突然就说起了一个人来。现在回忆起来,辛娜当时的表情并无特别。辛娜说的就是老陆,她说,老陆你还记得吧?哪个老陆?陆正勇呵,我高中的同学。辛娜挑动着蚕眉,似乎在勾起王树林的记忆般。
或者,是否可以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方式:殷人之“帝”与“祖先”或为同一事物,而周人之“天”与“帝”又有莫大的联系,可否说明,周人所谓的“受天命”就是“受帝命”也就是“受殷人祖先之命”呢?此说亦有凭证,在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辞有文字言:
然而孔子曾赞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27]后世很多儒生将此言奉为圭臬,都认为文王至德,怎么可能自立为王,行僭越之事呢?宋儒欧阳修曾言:“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28]清儒姚际恒亦言:“小序‘谓文王受命作周’,非也。文王未尝为王,无受命之说。”[29]并解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周室得天下以后的辞令,虽然周室维新确肇始于文王,但并不能解为上天授命于文王。然而正如清儒陈启源所质疑的:“《诗》《书》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岂仅命为诸侯乎?……虽不显言称王,而其实已不可掩也。”[30]晚清以来,一种新的解释方式出现,其发轫者为俞樾。他认为:“唐虞五臣,稷契并列。商、周皆古建国,周之先君非商王裂土而封之也。”[31]即认为商、周为并列古国,并无清晰的、严格的臣属关系。王国维先生则利用西周金文提供的材料,证明了“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1]623这种解释既未违忤典籍记载,也维护了儒家道统及文王的至德形象。也有人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文王受命”,如郑玄根据《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将“中身”解作“中年”,因此“文王受命”为“受殷王嗣位之命”。而宋儒王十朋则根据《史记·周本纪》中纣王曾赐文王“弓矢斧钺”等物品、允许周文王专行征伐的记载,认为“文王非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文王自羑里之囚还而纣以弓矢斧钺赐之,使得专征伐。”[32]然而受命于商,继而伐商,于情理似不通。清儒陈奂则在《毛诗传疏》中言:“文王受命于殷之天子,是即天之命矣。”他将殷天子之命等同于天命,企图以此来弥合二说。
《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25]《史记·周本纪》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既让,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也’。”二书虽云文王受命,却并未名言受命为何。《大盂鼎》铭文谓“不(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17]《尚书·文侯之命》云:“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12]226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亦云:“大王自豳来……未有书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诸侯国名变而为天子国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26]这里明言文王受命即受天命,是“以诸侯国名变而为天子国名”,从此比列于殷商,有了翦灭商族的名义与可能。这也是周虽旧邦,而“其命维新”的题中之义。
贞王其□又太甲□周方白□甶正不嘎于受又又(凤雏H11:84)
彝文武丁□,贞王翌日乙酉其□爯中□武丁豊□□□嘎王(凤雏H11:112)[33]
周人重新定义了“天”的含义,然而高覆万物的“天”何以与人产生联系呢?只有当人格化的天施于下民以权威性的指示或敕命,才使上天与人建立起完整意义上的联系,这也是上古重要族群高度重视“天命”的原因所在。“天命”一词语出《尚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12]90在出土的西周甲骨卜辞与彝器铭文中,“受命”“受天命”也多次出现。如《大盂鼎》铭文:“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17]甲骨文中,“命”与“令”通,《说文解字》云:“命,使也。从口,从令。”[3]109所以“天命”之意“或指天的命令,或指天授予王朝的权命,或指上天的意志。”[18]223根据陈梦家的研究,天命概念最早由周人灭商后提出[19],殷商时期则只有“帝令”(“帝命”)而无“天命”,所谓“天命玄鸟”实即“帝令玄鸟”。这也反映了殷周之际神权从帝到天的转移。
笔者认为,《诗》《书》以及西周铭文、战国竹简都清晰指出“文王受命”是受天之命,而非是受先君之命或商纣之命。即使有受殷祖先之命的仪式,但仪式中的祖先仍是以超脱的“帝”的身份出现,而不是只保佑殷人的血缘性亲属。李忠林先生说:“文王既受天命,也受‘上帝’之命,两者是统一的。受天命是以‘太姒之梦’为标记,而受‘上帝’之命则是通过庙祭占卜的方式得到印证和宣扬。”[35]40这样的结果就是,不仅天命从殷纣转移到文王身上,而且殷人的邦国和民众也要转予文王统治。
李桂民、晁福林等先生皆认为,此“王”即是周文王。文王曾举行祭祀商先王太甲的典礼,祈请册命周方伯能够承商得到天命为天子,卜兆显示能够得到商先王的保佑。而祭祀于商王文武丁的宗庙,贞问周王在翌日乙酉祭祀武丁的典礼上是否可以建太常之旗,也属受命代商为天子而举行的典礼。[34]这表明,殷周之际政权的交接并非如后世朝代更替一般,毁其宗庙而迁其重器,至少在名义上,周人对殷代先祖还是保持着恭敬之心,在宣扬本族受命的同时也未否定殷人之命来自天授,只因帝纣失德于天,而致使天命之转移,故万千罪过皆“在纣一人”耳。
在《尚书·西伯戡黎》中,纣王闻周师西来云:“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12]106《史记·周本纪》则说得更清楚:“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20]118殷人认为天命不移,自有天帝与祖先神的庇佑。故当周以蕞尔小邦克大邦殷后,周人开始反省“天命”到底为何,在他们看来,有德是获得天命的必要条件,而修德保民则是永葆天命的唯一手段。《诗经·文王》云:“侯服于周,天命靡常。”[21]234《尚书·蔡仲之命》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12]185天命之靡常,皇天之无亲,故知天命轮转可易[注] 周人在克商之后一定程度上宣传过“天命不易”思想,譬如《诗经·敬之》云“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尚书·大诰》云“尔亦不知天命不易”,《尚书·君奭》云“不知天命不易”等。这主要出于政治宣传、维护政权稳定的目的,与“天命靡常”思想并不相悖。 ,上天不再是殷商伦理中只垂恩于一邦的宗神。然而“惟德是辅”一语,又表明上天辅佐有德者是确定不移的,天的道德意志支配着王朝的存续。所以陈来先生说:
“文武受命”一说虽为后出,但并非后人空穴来风,其实在克商之前即已显露端倪。如清华简《程寤》:
惟王元祀正月去既生魄,太姒梦见商廷惟棘,乃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告王;王弗敢占,诏太子发,俾灵名凶,祓。祝忻祓王,巫率祓太姒,宗丁祓太子发;币告宗祊社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烝,占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37]136
“太姒之梦”以及文、武“并拜吉梦”似为“文武受命”的理论来源,彼时武王虽为太子,但附于文王后共为受命的对象。王国维先生说:“《酒诰》之‘肇我民唯元祀’,是为文王受命之元祀。武王继位克商,未尝改元。”[1]617正因如此,当武王伐纣之时,必仍以太子自谓,而奉受命之君完成伐商的天命。这就是《史记·周本纪》所载的: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20]120
“为文王木主”“自称太子发”都表明此时的受命之君仍为文王而非武王。但文本中仍有两点值得注意,即“白鱼入舟”“王屋流乌”,这或可看作武王重新接受天命的标志性事件。《汉书·董仲舒传》曰:“《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39]《吕氏春秋·应同》曰:“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40]白为殷色,白鱼入舟,代表周革殷命。“流乌”者,即星相学所谓“柳宿西流”,形如朱雀之嘴又似古文之“火”,故名“鹑火”。《国语·周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14]123-125所以“王屋流乌”正是天授武王命,以星象而诰之[注] 杨宽先生认为:“至于西汉《泰誓》和《史记》所说:武王渡河中流有白鱼跃于王舟中,被武王取来作为祭品,又有火从上天飞到武王住屋,化为赤乌等。分明是战国以后五行相克学说流行以后的作品。商为金德,其色尚白,而周为火德,其色尚赤,因而把捉到飞来的白鱼和飞来的天火,化为赤乌作为周克殷的祥瑞。”见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87。 。因此,“文武受命”虽为晚出,但周初的记载已经有武王受命的迹象,通过上天对周人受命的重新确认,武王最终获得了克商的资格,从而替天行道,代商而厥有天下。
四方竹作为笋用林,由于常年挖取,对于土壤养分消耗大,导致竹林土壤肥力退化,施肥是改善这一现象的有效措施。试验结果显示,施肥能大大促进竹林的发笋,提高单位面积的竹笋产量。在施肥方案中,可以考虑以见效快的复合肥作为先导肥料保证当年生产,而以见效慢但持续性长、能改善土壤温度条件的有机肥作为长效肥保证持续生产,二者结合,作为最佳施肥方案。
四 结论
克商并不是周人一两代统治者的想法,而是长时酝酿、构思精密的政治谋划。《诗经·閟宫》云:“后稷之孙,实为太王,据岐之阳,实始翦商。”从太王时代起,周人就开始筹划克商大业,经过王季、文王、武王历代的努力,终于完成。与此同时,周人对自身天命的塑造(或者说是克商的舆论准备),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殷失其命”到“文王受命”再到“文武受命”,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天命构建脉络。所谓“受天命”,可以说是“周人发起的一场政治造势运动”[35]40,夏、商都接受过“天命”,那是因为他们的先人施德怀民;而随着统治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后代“不敬厥德”,久而失去民心,所以上天把“天命”转予了具有美德的文王、武王,即所谓“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尚书·召诰》)这就使周革殷命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至此,周朝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圆满的解释。
“天命”的构建复杂、精密而历时弥长,经过文、武、周公历代统治者的制定,周人形成天命与民意、敬天与保民相结合的德治传统,他们“以‘敬德’为‘受命’的根据,以‘保民’为‘天命’的体现;并把先王作为‘以德配天’的典范。”[41]通过一系列革命性的操作,周人终于建构起普遍主义的天下观与高度精妙的礼乐文明。在礼乐瓦解的两周之际,敬天保民的天命思想与理性主义的人文教化相交接,儒、道、墨、阴阳各家纷纷登场,至此,塑造文化原型的“轴心时代”浩浩荡荡拉开序幕,一个充满诗性与浪漫色彩的时代开始了[注] 当然,思想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并不必然为政治服务,二者往往互为因果,以历史的方法研究思想,最终还应回到思想本身。惟有兼顾“大传统”与“小传统”,综合各层级、各领域的细节演变,才能构建一种真实可信的思想史的叙述体系。 。
初中数学拓展性微课程,是以现有的初中数学教材为载体,借助微课“短小精悍、形式丰富、时空自由”等多种优势,结合资源内容,系统研发思维拓展型、学法指导型、数学文化型、操作活动型数学拓展型资源的微课程(图2),旨在拓宽数学教材的意义空间,挖掘数学独有的文化内涵,以此发展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目前已经重点开发3个系列微课程.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林集: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 白川静,袁林.西周史略[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17-18.
[3]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4] 陈立.白虎通疏证[M].新北:广文书局,2012.
[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47.
[7] 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00.
[8] 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 石磊.先秦至汉儒家天论新探[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
[10]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87.
[11]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 蔡沉.书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7.
[13] 王震中.商周之变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J].历史研究,2017(05):6.
[14] 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5] 王和.文王“受命”传说与周初的年代[J].史林,1990(2):5.
[16]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04-210.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9] 陈梦家.尚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5:207.
[2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8.
[21] 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2] 黄中松.诗疑辨证:卷五[O].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
[23] 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01.
[24] 陈颖飞.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J].清华大学学报,2013(2):137.
[25] 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M].北京:中华书局,1964:85.
[26] 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57.
[2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103.
[28]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135.
[29] 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262.
[30]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615.
[31] 俞樾.达斋丛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975.
[32] 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诗文前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660.
[33] 曹玮.周原甲骨文[M].北京:世纪图书出版社,2002:64,78.
[34] 李桂民.周原庙祭甲骨与“文王受命”公案[J].历史研究,2013(2):18-21.
[35] 李忠林.皇天与上帝之间——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说文王受命[J].史学月刊,2018(2):40.
[36] 陈梦家.西周年代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5:29.
[37]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
[38] 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82-483.
[39] 班固.汉书: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2500.
[40] 张双棣.吕氏春秋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349-350.
[41]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0.
Evolution of Thought of Heaven ’s Destiny
in Period of Yin and Zhou Dynasties
HU Zhao-d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nfucian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0,China )
Abstract :During the Yin and Zhou Dynasties,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and ideology changed dramatically. The belief in “emperor” of Yin people was replaced by the belief in “heaven” of Zhou people. The Zhou people endowed “heaven” with ethical attributes and mor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nnotation of “Heaven’s Destiny” was moralized; and the contents of “respecting heaven” and “protecting the people” were introduced. The transition from natural religion to ethical religion, from witchcraft culture to humanism was completed through the ethical demonstration of Heaven’s Destiny and the proposition of a series of concepts such as “King Wen was appointed” and “King Wen and King Wu were appointed”, Zhou people emphasized the end of Heaven’s Destiny of Yin and the transfer of Heaven’s Destiny to themselves, demonstrated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Zhou Dynasty’s prosperity and Yin Dynasty’s destruction, thus laid the main tone of Heaven’s Destiny thought of Zhou Dynasty, and produced extensive shadows to various school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ey words :Yin and Zhou Dynasties; heaven’s destiny; emperor; King Wen; King Wu
文章编号 :2096-1901(2019)04-0008-08
收稿日期: 2018-11-23
作者简介: 胡兆东,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E-mail:848691900@qq.com。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责任编辑:岳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