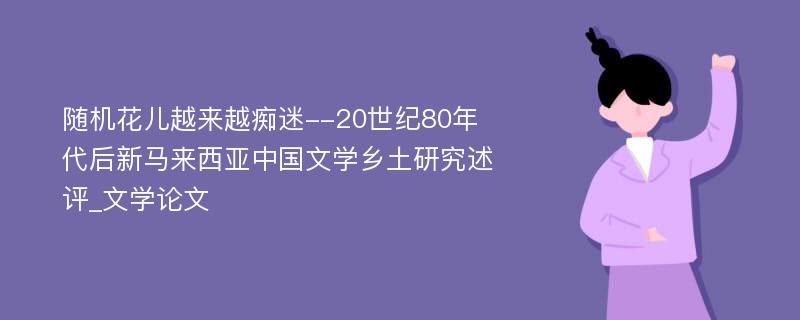
乱花渐欲迷人眼——20世纪80年代后新马华文文学本土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本土论文,乱花论文,年代论文,新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马两国本土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注:“本土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初步界定为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的作家、学者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其中包括留学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美国、欧洲等地的新马籍作家、学者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以下简称本土研究)随着创作的复苏而更加活跃起来,加上它们与世界各地的文学交流日益频繁,至20世纪末为止,短短20年里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足以傲视世人。粗略统计,这些研究成果中除了数以百计的单篇论文之外,研究专著也高达几十本之多,这里的研究专著泛指已出版成书的专论、单篇论文集、资料汇编、学位论文、文学史著、参考工具书和文学选集等。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新马华文作家批评家的努力以及新马两地华人社团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两国先后成立的新加坡作家协会(1970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78年)起了很好的领导作用,《蕉风》、《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联合早报》、《新加坡文艺》、《赤道风》等文艺报刊则充当了研究阵地。另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通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出版文集、提供发表园地等形式也为本土研究推波助澜并形成互动关系。
对新马本土研究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大致归纳一下,可分为下列几个议题:一、对新马华文文艺报刊的研究;二、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反思与展望;三、对中国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关系的论述;四、文学史的撰写与重写;五、其他论述。
一
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华文报刊密切相关。华文教育、华文报刊是华文文学发展的两大支柱。对华文文学发展而言,华文报刊既是它的发表阵地,又是它的资料保管所。因而,文学史家和资料搜集者非常重视华文报刊,在史论中,他们一般都将华文报刊纳入研究视阈。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卷)中将1919年至1942年即战前的马华文学发展分成四个时期:萌芽期(1920—1925)、扩展期(1925—1931)、低潮期(1932—1936)、繁盛期(1937—1942)。在论述每个时期的时候,必先评介当时的文艺刊物,如在扩展期里,他分节将当时的主要文艺刊物《南风》、《星光》、《荒岛》、《洪荒》、《椰林》、《瀑布》、《星火》、《荒原》、《曼陀罗》等等逐一作了介绍,为后面的作者与作品、文学运动与文艺论争的阐述作准备,文艺报刊成为他把握文学史实描画文学运动轨迹的基础材料。
20世纪80年代后,本土研究者对华文文艺报刊研究愈加重视,出现了专门研究文艺报刊的论著。如1980年,杨松年与周维介出版了他们的合著《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在此书里,他们先对1927年至1930年的新加坡报章文艺副刊作了综合论述,然后分别对南洋商报的《文艺周刊》、南洋商报的《洪荒》、新国民日报的《荒岛》、星洲日报《野葩》以及《草野》、《前景》、《文艺工场》、《现代青年》予以评介。其中,他们对1927年至1930年的新加坡报章文艺副刊所作的综合论述非常有价值。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文学史家对一段时期的文艺副刊作过如此宏观的把握。他们不但对1927年至1930年代出现的主要报章文艺副刊作一总的简介,而且还尝试着对这些副刊的编刊宗旨、编排方式、文艺的方向以及作品与作者的基本情况给予归纳总结。比如他们将“编刊宗旨”综纳为以下几点:1、替新加坡这块文艺荒地作点工作;2、建设南洋色彩的文艺;3、以文艺反映时代、服务大众;4、以文艺涵养娱乐;5、鼓勇前进,创造新生,有利于人们清楚地认识当时编者的编刊理念。而对“文艺的方向”把握上,他们认为有两方面值得注意:1、南洋色彩的提倡;2、新兴文艺的提倡。实际上就是对当时两大文学思潮“南洋色彩文学”与“新兴文艺”的阐释,并为这两大文学思潮找到了结合点,即都强调“地方色彩”。这本专著的后半部附录了十份文艺副刊的作品编目,如《绿漪》作品编目、《瀑布》作品编目、《曼陀罗》作品编目等等,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资料线索,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稍后出版的《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甲集)》(杨松年著)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的补充论述。在这本书里,杨松年择取了七种有特色且有重要文学史价值的刊物加以评介,例如新马新文学萌芽期的副刊《南洋商报》的《新生活》,新马第一份新文艺副刊《新国民日报》的《南风》,新马第一份戏剧副刊《新国民日报》的《戏剧世界》,北马第一份诗刊《南洋时报》的《诗》,早期中马文学的重镇《益群日报》的《枯岛》,北马卅年代初期的新文艺副刊《光华日报》的《绝缘回线》,新加坡卅年代初期的新文艺副刊《南洋商报》的《压觉》。杨松年为了挖掘这些文艺副刊的史料价值,做了大量的汇编、考证与分析的工作。
1988年,周维介出版了论文集《新马华文文学散论》,其中收集了三篇他对文艺刊物研究的文章,即《从〈南风〉看新马华文文艺的雏形》、《新马华文文学的温床——二十年代的学生文艺副刊》和《飘落热带的雪花——本地早期诗刊〈雪花〉》。与杨松年做法一致,周维介在此也主要是为了挖掘这些刊物的文学史价值。可以发现,杨松年与周维介的报刊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时段,这个时段的文艺副刊不是散佚就是尘封,对它们进行史料爬梳非常艰苦,然而其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却是不证自明的。
20世纪90年代后,方修出于对《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的修补,出版了《马华文学史补》一书,其中补充了战后初期以及紧急状态时期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杂志的介绍,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对新马华文文艺报刊的单篇论述也陆续发表了不少,其中马仑的《〈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1955—1993年)》[1] 和姚拓、小黑、朵拉三位《蕉风》的编者合写的《四十年来的〈蕉风〉》[2] 两篇文章值得重视,它们都是对新马华文文学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文学期刊《蕉风》的评述,虽然角度不一,但都分别概括了《蕉风》38年和40年来坚持多元化和开放性的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奖掖后进,扶植文坛新秀,并通过出版文学丛书和主办各种文艺活动、文学讲座,为新马华文文坛走向繁荣立下汗马功劳的历程。而张永修的《从文学杂志的处境谈末代蕉风》[3] 则从文学杂志的不景气联系到1999年《蕉风》的停刊,对末代《蕉风》的编辑团阵容、编辑特点、作者群像、版面构成以及它的附属刊物《少年蕉风》作了简要介绍之后,表示了对《蕉风》停刊的遗憾,期待着“蕉风出版基金会”的成立,早日盼回“老朋友”《蕉风》。
二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新马本土研究走向深入,从宏观方面或整体方面把握/总结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情况的文章日渐增多,这些研究文章或回顾或反思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展望新马华文文学的未来,为新马华文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总结/积聚经验,辨析/正名自身,并为其寻找恰当的历史定位。如方北方的《马华文学的起源及其发展方向——第三届亚洲作家会议专题演讲稿》、陈春德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马华文学》、杨松年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过去与现状》、骆明的《新华文学的过去现状及其方向》、黄孟文的《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王润华的《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阶段与方向》等论述分别回顾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虽然每个人的论述角度并不一样,但都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并将希望寄托于未来。他们的企图都非常明显,就是希望通过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过去及现状的梳理,作为前车之鉴,以尽快形成具有新加坡传统或马来西亚传统的新马华文文学。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九十年代以至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马来西亚工业化经济转型期,马华文学坚持走乡土文学的道路,应该是没有错的。”[4]
除了这些从整体上把握新马华文文学的论述之外,还有许多篇章或针对文学运动,或针对文学思潮,或针对某一文体发展状况进行梳理总结,择取一个角度切入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为新马华文文学进一步发展提供史的参照与借鉴意义。这类文章主要有:方北方的《谈马华文艺批评》、云里风的《文艺结社与文艺批评》、陈剑的《建国前后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概要》、戴小华的《八十年代马华文学的思潮》、马仑的《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脉络》、王润华的《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黄孟文的《新加坡华文小说的发展》、孙爱玲的《探索七十年代新加坡女作家崛起的原因》、吴岸的《马华诗坛的回顾与展望》、孟沙的《马华小说沿革纵横谈》、姚拓的《马华戏剧七十年来的回顾与展望》、甄供的《莫闲了春风词笔——谈理论批评、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爱薇的《永恒的童心——马华儿童文学的回顾与前瞻》、陈锦松的《追求“真善美”的报导文学》、陈应德的《马华诗歌发展简述》、陈蝶的《细雨狂飙含笑过——回顾与展望马华散文七十年》、钟怡雯的《从追寻到伪装——马华散文的中国图象》、潘碧华的《弹拨一根现实敏感的弦:听七、八十年代愤怒的声音》等等。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文章有谈文艺批评、理论史料的,有谈左翼文学运动和80年代文学思潮的,也有谈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以及儿童文学、报导文学的,从各个角度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作出总结与展望。如将这些篇章合在一起,几乎可以构成一部新的新马华文文学文学史。
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予以归纳总结的文章中,还有一类文章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关于马华文学的定义及定位问题的论述。新马分家后,两国的华文文学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目前新加坡华文文学已经被纳入到国家文学行列,这方面争议较少,而马华文学却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困境重重。马华文学的窘境主要是因为国家宪法明确规定马来语是国语,其他语种如英语、华语、淡米尔语只是马来西亚的使用语言,因而,只有用马来语写作的作品才是国家文学,其他语种写作的作品如“华文文学”、“淡米尔文学”则被看作是“移民文学”。据不完全统计,华人作为马来西亚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约是37%,如此众多的人口使用华语交际并创作,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的确是一件非常悖谬的事情。一直以来,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想修正国家文学的概念。例如60年代,汉素音在用英文写作的《马华文学简论》[5](由李哲翻译为华文)里面给马来西亚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马来西亚文学应该包括这些作品(戏剧、小说、诗歌),即在感情上,在效忠的问题上,在描述上,在社会背景上和在所关心的问题上是有关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这些作品可以用星马四种所公认为主要语言的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或者英文发表。”70年代末,方北方发表《马来西亚文学概念》[6] 一文,批驳了“将文学等同于政治”的荒谬,同样将矛头指向“华文文学”和“淡米尔文学”是“移民文学”的悖论。80年代后,云里风、吴岸等先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希望“华文文学”能早日争取到合法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黄锦树、林建国等新生代作家群围绕马华文学的定义及定位问题展开了深入论述,引起较大反响。特别是禢素莱发表《开庭审讯》一文后,更是了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黄锦树在《“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7] 一文里,建议把“马华文学”的全称由“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修改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从华人学角度重新赋予“马华文学”新内涵,企图针对马来西亚社会仿佛无可逆转的多元分歧性格,在文学/文学史的领域里做一点必要的步伐调整。林建国在《为什么马华文学?》[8] 的长文中,对黄锦树的观点加以解释,他认为黄氏从人类学观察出发的“马华文学”新定义,不仅涵盖马华新文学,也涵盖1919年以前及以后的“旧文学”,还延伸至QQ文学和华人写作的马来文学、英文文学,使“马华文学”成为异质性空间,具有颠覆力量。换言之,使“马华文学”既在马来文学之内又在其外,整个拆解了“国家文学”的族群语言中心论。应该说,黄锦树、林建国二人从更深层次对“马华文学”的定义及定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反思,打破了华人以及马来当局围绕狭隘的“语言—种族”中心论出发看待华文文学的迷障。这是从另一角度为马华文学能早日纳入国家主流文学所作出的努力。1992年,留学日本的大马华人禢素莱发表《开庭审讯》[9] 一文,表达了对日本学者认为马华文学是中国的支流文学不是马来西亚文学的愤慨。引发一场争论,沙禽、陈应德、陈雪风、黄锦树等人先后撰文参战。随后,胡金伦发表专访《寻找马华文学的定位——马华文学实质为何》[10] 予以了总结。在这篇专访中,胡金伦分别以张锦忠的复系统视野中的“华马文学”、黄锦树的从文化人类学出发的“华人文学”、永乐多斯的“马来社会眼中的马华文学”、陈应德的“马华文学的‘古典’与‘白话’”和姚拓的“马华文学与华文教育”为分析对象,寻找马华文学的历史定位,强调马华文学摆脱中国支流文学地位迈向新里程碑的重要性。
三
关于中国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自新马华文文学诞生之日起就已存在。方修是最早对这种关系进行过梳理的人,除了《马华文学简史》里面对两者关系进行过对比分析之外,他的《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11] 及《马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的发展》[12] 也是概括性很强的研究文章。前者主要从影响的角度分析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815至1919年,新马华文文学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中国文学的哺育,作为中国文学的支流而存在。1919至1949年,新马华文文学排除种种制约因素建立自己的独特性,这时候许多作家包括南来作家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为的是更好地反映本地生活,与表现自己的问题。1950年以后,新马华文作家把中国文学看成是世界文学的一环,他们把它和世界各地文学同等看待,平等交流,摆脱了中国文学支流的地位。后者则把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发展与新马现实主义的写作路线对照比较,肯定了新马现实主义思潮受中国新文学影响但不失独特性的本质。
方修作为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第一人,他的辨析思路对本土后来者的研究影响深远。七八十年代后,本土一般研究者对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所持的看法仍与方修的观点类似,咸认为新马华文文学脱胎于中国文学,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国文学分道扬镳,自立门户,但中国文学对新马华文文学造成影响却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例如,1978年,林万菁出版《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3] 一书,细心地研究了1927至1948年间20余位南来的中国作家如洪灵菲、老舍、艾芜、吴天、郁达夫、胡愈之、高云览、沈兹九、杨骚、王任叔、杜运燮、夏衍、巴金、徐志摩、米军等在新加坡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社会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从中国南来的作家对新马华文文学所作的巨大贡献方面论析中国(新)文学对新马华文文学所造成的影响。1999年,杨松年的学生郭惠芬对林著的“中国作家”概念予以宽泛化,重新界定为“中国南来作者”,将林著中无法列入研究范围的一批南来作者如拓哥、丘士珍、许杰等也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畴,出版了《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9)》[14] 一书,对中国南来作者在新马期间的文学活动进行总体研究,探讨了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关系及其对本地文学的贡献。除了以上专著之外,还有一些单篇论述也谈到中国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如流军的《马华文学的渊源与发展》、林方的《斑兰叶包扎的粽子——序〈五月现代诗选〉》、王润华的《中国作家对新马抗战文学的贡献》、彭杜生的《新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等。这些论述的基本思路都肯定了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起到正面的扶植作用,是新马华文文学继续前行的巨大后盾。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马华新生代作家群的崛起,开始出现反省/反思中国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述。它们将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看成是制约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障碍,强烈要求摆脱“中国”这个大帝国的阴影。其中,黄锦树的“中国性”批判与林建国的“断奶论”是典型代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中国性”问题是黄锦树对马华文学文化属性考察的起点,“中国性”又可称为“中华属性”,“中国特性”、“中国特质”等,指涉的是一个文化想象上的问题,牵扯到马华文学中纠缠不清、暧昧而又复杂的内在中国影像。黄锦树的《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15] 最早涉及到这一命题,以温瑞安领导的神州诗社为主要的论述对象,通过文化乡愁的解析批判了现实的神州诗社里面四处游荡的“中国幽灵”。在《两窗之间》[16] 一文里,黄锦树进一步将马华新生代作家辛金顺、林幸谦也置入他的批判视野,指责他们的作品为“文化乡愁的过度泛滥”。林幸谦随后发表《窗外的他者》[17] 予以回应,希望黄能正视文化与身份属性的问题。他说:“关于身份认同、文化冲突/差异、中国属性、尤其是边陲课题等问题,对于海外中国人而言,足可以让几代的人加以书写阐发,是世纪性的一个问题。”之后,黄锦树迅速以《中国性,或存在的历史具体性?——回应〈窗外的他者〉》给予反击,认为辛金顺、林幸谦与天狼星——神州诗社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以哀怜、自伤、悲情作为书写形式反省自身的边缘处境很不应该,因为这会堕入民族主义与想象的大汉帝国的深渊。关于“中国性”问题,黄锦树在专著《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一书进行过全面整理与批判。全书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收录三篇文章:《华文/中文:“失语的南方”与语言再造》、《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的限度》和《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西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第二部分除了收录《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之外,还有三篇是关于李永平、张贵兴、陈大为的作家论。总的来说,不论是从语言的角度,文化表演性的角度以及马华现实主义困境的角度出发论证“中国性”的危害,还是从神州诗社和有着完整“中国性”展示的三位作家的剖析中批判挥之不去的“中国性”魔魇,黄锦树的偏颇与激烈都溢于言表。然而,正是这种姿态,给沉寂多年的马华文坛带来雷霆与闪电,震撼了所有写作人,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黄锦树现象”。
林建国对待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对马华文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黄锦树一样深恶痛绝,在黄锦树的观念基础上大胆提出“断奶”之说。他的《马华文学断奶的理由》(注:见报时题改为《大中华我族中心的心理作祟》。)[18] 认为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断奶,乃是基于“一石三鸟”之计,即反奴役、反收编和反大汉沙文主义,马上遭到陈雪风等人的批驳。陈雪风先后发表《华文书写和中国文学的渊源》(注:由胡金伦专访整理发表。)[19] 和《访谈的补充与解释》[20] 指责林建国的“断奶”论是将马华文坛当作了台湾文坛,不管主客观条件,成为台湾“断奶”论的翻版。他认为,在马华文坛,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关系,不存在奴役、收编与大汉沙文主义的威胁。因而,用计来反对不存在的东西,无异于制造假想的敌人。林建国随后又发表了《再见,中国——“断奶”的理由再议》[21] 再次陈述“断奶”的必要性,认为陈雪风等人的反应是由于心中的“中国情意结”变成了情绪问题,而这种情绪阻碍了思考的进步,仍然坚持马华文学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受到了民族主义的蛊惑。用他的辨证逻辑,必须这次和“中国”说“再见”,但不是不见,下次“再见”的时候就是批判与继承。林建国的激烈不亚于黄锦树,对马华文学如一棵小树在中国文学这棵大树的树荫下得不到健康成长表示了极端的关注。说到底,还是为马华文学的边缘地位而焦虑。
不管怎么说,黄锦树与林建国的“暴风骤雨”还是惊醒了大马华文文坛,沿着二人的反思路线,林春美、张光达、张锦忠、温任平等人分别发表《近十年来马华文学的中国情结》、《乡愁诗,中国性与现代主义》、《中国影响论与马华文学》、《与林水壕谈“断奶”与“影响焦虑”》等,不同程度地表示了他们对中国文学/文化与马华文学之间关系的关注,偏重于反省中国文学/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四
20世纪80年代后,除了方修不断修补完善自己的新马华文文学史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李锦宗、杨松年、周维介、方北方、黄孟文、吴天才、马仑、原甸、田农等也加入了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撰述中。至20世纪末为止,已经出版了原甸的《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22] 和田农的《砂华文学史初稿》[23] 两本专著,其他则多为简史梳理或单篇论述(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评述了)。
原甸的《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主要以1965年新马两国分家之前的华文新诗发展为论述对象,分期择取代表性诗人诗作分析评论,试图勾勒马华新诗(包括新华诗歌)史的轮廓。全书共分九章,一章代表一个时期,如第一章“马华诗坛第一批诗人的呐喊(1920—1926)”、第二章“马华新兴诗歌运动(1927—1931)”、第三章“沉郁的低唱(1932—1936)”、第四章“抗日战鼓(1937—1941)”……第九章“新时代的激情(1960—1965)”,可以看出,作者的分期基本上以马华社会的政治变化、社会变迁对新诗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为根据,力图展现马华新诗发展的全貌。由于作者注重诗歌的“为社会,为人生”的服务功能,因而他笔下的诗歌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力作,整部新诗史实际上是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思潮史。在这一点上,与方修的文学史观一脉相承,带有明显的文学意识形态色彩。
田农的《砂华文学史初稿》以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洲——婆罗洲的首府砂罗越的华文文学为论述对象,显得比较特别。作者说:“一般而言,砂华文学是属于马华文学的一部分。但在一九六三年砂罗越加入大马以前,不但砂华文学的定义和现在有所不同,即使当砂罗越成为大马一个洲属,砂罗越的华文文学仍有其独特的一面。”[24] 具体考察时,作者将砂华文学史分成四个时期:一、战前的侨民文学(1945年以前);二、砂华文学的萌芽期(1946—1955);三、砂华文学的成长期(1956—1962);四、砂华文学的低潮期(1963—1970)。70年代以后的砂华文学发展,暂时未放进研究视阈。很显然,作者对砂华文学史的梳理超出了一般的、笼统的马华文学史范畴,将砂华文学独立出来,彰显了它的主体性,并且丰富了马华文学史的论述,改变了已出版的马华文学史著偏重于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的局面。整个史的论述中,作者力求资料翔实,重点作家作品突出。
20世纪90年代后,禢素莱发表《开庭审讯》一文,不但引发了关于“马华文学定义及定位”问题的论战,而且还掀起了“经典缺席”之争,导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越来越高。1992年,为了回应禢素莱的《开庭审讯》,黄锦树发表了《马华文学“经典缺席”》[25],一方面指责日本学者对马华文学的无知,另一方面则将责任归结为马华文学“经典缺席”。在他看来,如果马华文学有经典文本的话,就不至于被日本学者轻视了,因此,必须尽快结束马华文学史的“酝酿期”(即马华文学还处于粗糙的拓荒阶段),引起了陈雪风的高度不满,他署名夏梅发表《禢素莱·黄锦树和马华文学》[26] 一文对黄锦树将马华文学全盘否定提出质疑,批评黄是“对文学的外行与对历史的无知”。黄锦树马上以《对文学的外行与对历史的无知?——就“马华文学”答夏梅》[27] 反驳,坚持认为似乎所有的马华作家都带着拓荒的形象,作品质量堪虞,没有“世界性的作品”,“马华文艺独特性”也只是一个空集。陈雪风又以《批驳黄锦树的谬论》[28] 应战,批判黄锦树刻意卖弄西方的术语与转换概念,否定马华文学,轻蔑马华文学,却无法自圆其说。这场“经典缺席”之争影响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端木虹、刘育龙、何乃健、张锦忠、张永修等都先后撰文参予论争。其中张锦忠的《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注:此为1997年“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9] 具有总结性意义。张锦忠借助于以色列理论家易文·左哈尔的复系统理论,认为典律(或称经典)是所有文学系统的运作条件之一,有潜在典律、流通典律、选辑典律之分。马华文学有没有经典之作,基于每个诠释者的美学标准不一,是见仁见智的事。任何独尊一种典律诠释权的认知都将无助于马华文学系统。
经典与文学史的生成有着辨证的关系,一般而言,只有经典的文本才能构成文学史,反之,文学史对经典形成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黄锦树宣称马华文学“经典缺席”,那么在他眼中,既成的马华文学史当然就不成为文学史了,这直接否定了方修的关于新马华文文学史的著述。黄锦树在《“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的限度》、《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和《反思“南洋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30] 等多篇论述中不同程度地指责方修的文学史存在着重大问题,可归纳如下:“①方修遗漏了非汉语书写的华人文学;②方修的文学史分期完全以政治事件为脉络,而缺失艺术与审美的维度;③以政治事件为脉络的文学史必然忽视经典问题,没有经典的位置;④方修视现实主义为马华文学史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是片面的文学史观,黄锦树至今似乎还在怀疑方修的文学史故意遗忘了现代主义,否则为何马华新文学没有它的踪影?”[31] 黄锦树完全以审美标准衡量意识形态唱主角的方修文学史,当然嗤之鄙之,其中不无偏激之处。然而,我们看到了黄锦树在努力尝试建构一种新的文学史构架,以期重写文学史。可惜他未能像方修一样钩沉史料,即使怀疑方修的文学史处理掉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但也好似捕风捉影。
同是考虑文学史的重写,张锦忠与黄锦树有很大不同,正如刘小新所说:“他(黄锦树)的问题在于他自己也深陷在以一种主义否定另一种主义、以一种文学意识形态否定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单向思维的泥淖里。方修们否定或排斥了现代主义,而黄锦树也否定或排斥了现实主义;方修走了极端,黄也同样走了极端;方修治史以客观史料为依据但仍未摆脱意识形态的主观性;黄虽讲求学院派的学理性却暴露了价值取向上的唯我主义。”[32] 张锦忠则从易文·左哈尔借来“复系统”理论借此重构马华文学史。他在《文学史方法论——一个复系统的考虑:兼论陈瑞献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系统的兴起》[33] 里说:“尽管‘文学史’一词词义甚明,书写文学史往往涉及‘文学’、‘历史’、‘书写’,甚至‘文学史’、‘历史性’或‘时间’的重新界定或诠释。重新界定或诠释的结果是,每一部文学史的书写都是重写文学史。文学史不断重写,分析到底,原因在于文学史(书写)本身乃复系统中的文学现象或系统之一,恒在游移不居,而在其不断的游移变动中,和其他文学、文化、政经、教育、法律系统互动,构成了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历史性、文学建制或文学生活的场域,故以复系统理论论述文学史的学者如莫瓦颂即视文学史书写为‘历史性的场域’。”张锦忠从复系统出发考察马华文学史,彻底跳出方修的现实主义单向度文学史架构,或许能真正还原马华文学真实的复杂的历史场景。其中,他以“陈瑞献与新马华文现代文学系统”为个案,寻觅已被遮蔽的60年代新马现代主义踪迹。因为他发现1964年陈瑞献在《南洋商报》的“文艺”版翻译过西方现代主义诗作《星在疾行》,后来又与李有成、梁明广一起在《蕉风》上翻译过《尤利西斯》等作品。复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是复系统的一分子,完全参与复系统的历史。因而,从复系统看,陈瑞献的翻译文学却可以进入马华文学史。这就改写了温任平的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即改写了温任平把天狼星视作马华现代主义的起源和主流的“定论”,影响了后人对新马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认知。张锦忠援引西方理论获得冷静、客观的研究契机,对重写新马华文文学史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惜有先入为主以理论套文学史实之嫌,缺乏从新马华文文学本身出发的坚实。
林建国的《方修论》[34]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黄锦树批判方修文学史的修正。在这篇长文里,他很敏锐地指出:“我们困在主奴辩证里太久了,才不理解所有我们看似文学的‘内在问题’(如经典缺席),皆卡在资源(文化资本)分配与抢夺的节骨眼上。方修看起来化约和跳跃的左倾思考,切中的是问题的要害。”由于他能回到历史境遇感同身受地体认方修文学史所产生的问题,并非单纯的文学美学标准所能解决,直接回应了黄锦树的批评和挑战。林建国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发现了方修的现代性,一种属于第三世界文学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拒绝以西方流行理论诠释马华文学,强调“拿着最简陋的考古工具,走进那片贫瘠的田野,自己当起自己的人类学家。”“方修的文学史就是这种田野作业的人类学,在殖民统治的废墟里发现或记录下自己的身世和命运,他的工作建构了一种质朴的、本土的、应许自己族群身世答案的‘地方知识’。”[35] 林建国批评了以西方理论注解第三世界文学/马华文学的做法,包括张锦忠的复系统理论,鼓励应该像方修一样做一个朴素的、原始的“田野工作者”,从另一个高度肯定了方修对新马华文文学史的贡献。吊诡的是,林建国在这篇长文中,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大量借鉴西方后殖民批评的思想与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论述的力度。
另外,1996年大马华文作协公开征稿出版马华文学大系,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温任平、黄锦树、张光达等人都为文正面肯定了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工作。其中林建国的《等待大系》[36] 从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说起,将大系的编选与典律(经典)建构联系了起来,给那些对典律概念模糊的马华作家上了宝贵的一课。实际上,编选《马华当代文学大系》含有建构马华文学史的企图,编者把自己的典律认知套用在检验作品上,重新编排然后重点推介出去,形成马华文学的新典范,这种工作里面当然蕴含了“重写”文学史的意图。
经过一系列论争与前期的理论储备,重写(新)马华文文学史似乎已经提到历史日程,好在21世纪已经来临,相信这个世纪一定能出现更好的(新)马华文文学史,虽然它仍然还处于不断的修正与重写中。
五
新马华文文学本土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恢复生气,至90年代后进入“众声喧哗”的时代,给我们展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观。马华新生代作家群以激进的姿态介入马华文学场所造成的一次次美学骚动,更为马华文坛带来范式转换、思潮嬗变的契机。新华文坛相对来说,平稳一些,但多少也受到马华文坛论争的影响。新马本土研究除了上述议题值得注意之外,还有一些论述也是无法忽视的。如马仑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注:马仑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是在《马华写作人剪影》(1979年版)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收罗的作家由原来的200位增至505位,资料更加翔实。),为60多年来活跃在新马华文文坛的505位写作人留下珍贵的千字生平资料和照片,其中早期作家张叔耐、拓哥、陈炼青、丘士珍、陈南、莹姿、冯蕉衣、殷枝阳、夏霖、陈全和铁戈等11位缺少照片。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新马华文文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再如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系列新华作家研究丛书,有《姚紫研究专集》、《苗秀研究专集》、《杏影研究专集》等,将新华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作家研究汇集起来,有利于多角度理解这位作家。
通过以上删繁就简的梳理,我们至少可以窥见新马华文文学本土研究的大致发展方向,而这些一定能为21世纪的本土研究进一步拓展空间和提升学术品格提供发展之根基和借鉴之意义。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马华论文; 新加坡华人论文; 艺术论文; 南洋商报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