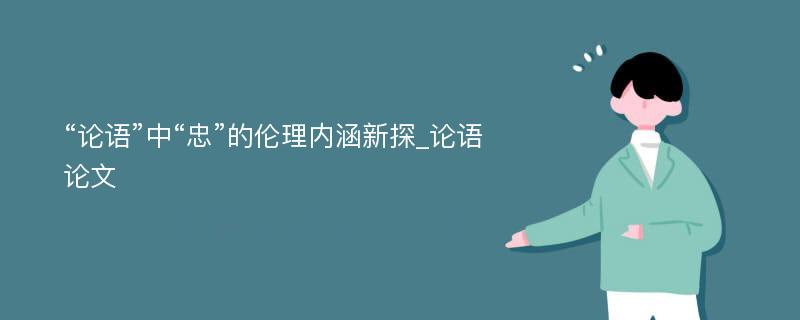
《论语》“忠”的伦理内涵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伦理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2)05-0068-07
罗哲海以“后习俗伦理”解释孔子的伦理思想,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他说:“中国在轴心时期的中后期(公元前600年—公元前200年间),曾经历过一个早期的‘启蒙新纪元’,因为此时的哲学家们不但对先前视为理所当然的规范进行反思,而且具有向‘后习俗’(postconventional)思维的突破性进展。”①
那么,什么是习俗性的伦理呢?美国的汤姆·L.彼彻姆在他的《哲学的伦理学》中谈到“什么是道德”的一种含义时指出:“道德是一种带有一套可习得的规则的社会惯例。”②如何辨别社会惯例是法律还是道德呢?“许多此类惯例,特别是法律和礼仪,只有根据他们的社会重要性程度,才能与道德相区别;而它们在性质上或者实质内容上并无区别。”③当然,习俗性的伦理也会包含一定的道德辩护方式,不过这种道德辩护往往是以习惯为根据的。“即使在谈到‘习惯性道德’的时候,它也决非仅指习惯本身——那种有规则地反复出现的行为次序,而是还指行为者起码是含蓄地持有的观点,即他们认为自己反复做的行为在某些方面是正当的;它决非仅仅指人们实际完成的行为,而是必定还指应该做的行为。”④
对于“后习俗伦理”,罗哲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他所说的后习俗指的就是将思维从自然和习俗中解放出来。本文拟从罗哲海的论述切入,力求说明《论语》“忠”的后习俗性内涵,并认为“忠”的习俗性伦理含义是通过“忠于”的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
一 “忠于”伦理视野下的“忠”
在把握《论语》思想的时候,要注意鉴别孔子直接承续社会文化一般观念的部分和孔子独特理解的部分,并且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在这里一开始就把语境设定为社会的背景,即“十室之邑”。孔子说有“忠信”像自己的人,说明从社会流行的“忠信”观念来看,孔子的“忠信”观及“忠信”品格和其他人差不多,但除此而外,孔子还有自己独特性的追求,这种独特性就表现为“好学”。“学”有练习、仿效、教育、学说、学问、觉悟等诸种含义,但其核心意义是觉悟。孔子强调“好学”,说明在社会流行观念背景下一个人认为自己达到了孔子的“忠信”,在孔子自己看来只具有表面的意义,“忠信”的核心是“学”。这一点是他人所不能了解的。在孔子心目中,最好的“忠”是建立在觉悟基础上的。关于这一点,后文会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这里可以看出《论语》的“忠”与习俗之间的距离。
在现代生活经验中去认知《论语》中的“忠”,一个很难突破的思维框架就是对象性思维(主客体思维)。也就是说,人们谈到“忠”,首先想到的是“某某A忠于某某B”。我们可以大致把这一语境分析为三对关系:A和B间的主客体关系;A和A间的对象性关系;B和B间的对象性关系。三种关系是互相制约的。A对A自我的关系往往是以B为参照看待自我而形成的,同样,B对B自我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忠”是A主体对B客体的“忠于”关系,其中必然包含着A对A自我和B对B自我的“忠于”关系。
笔者认为,最好不用这种“忠于”关系来理解《论语》的“忠”。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忠于”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与《论语》的“忠”有差异。现代语境中的“忠于”表述,着眼点是某个事实性的人A忠于某个事实性的人B。这样一来,“忠”就首先被置于一个事实性的世界,尤其是“自己”与“他人”构成的人类社会这一事实性世界。在这一意义上强调“忠于”的关系,A的个性问题就不会得到保证,B为什么值得A去“忠于”的问题也得不到反思性的回答,A和B之间的工具性的利用关系也不能得到有效的避免,形成“愚忠”。
为了克服把“忠”理解为“臣忠君”的时代局限,有的论者把“忠”的主客体外延进行扩大性处理,如裴传永在《孔子的忠德观探析》一文中专列“忠”的主体与客体部分,认为“忠”是一切人都应具备的道德品格,“‘忠’的美德不仅应当施于主体以外的所有人,而且应当施于主体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施于自己的祖国”⑤。该文引《论语·八佾》说明“忠”的主体是“臣”,引《论语·学而》、《论语·季氏》说明“忠”的主体是“君子”,引《论语·为政》说明“忠”的主体是“民”,引《论语·颜渊》说明“忠”的主体是“从政者”、“交友者”;引《论语·颜渊》说明“忠”的客体是“朋友”、“本职工作”,引《论语·子路》说明“忠”的客体是“他人”。但扩大了主客体范围的“忠”依然没有办法回答某个主体为什么要“忠于”另外一个客体的问题,没有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忠于”才更具有积极的伦理道德意义。
为避免把“忠”理解为一个人“忠于”另外一个人可能带来的弊病,人们能够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忠于”理解为自我对自我的忠,也就是A对A自我和B对B自我的“忠于”关系。但“忠于”自我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自我封闭、自以为是,堵塞了向他人开放,向有道德的人学习,并改善自我的道路。实际上,“忠于”自我本身就是主体“忠于”客体思维模式的延续。
朱熹在注释《论语·为政》中“孝慈,则忠”这段话时,引用了张敬夫的一段话:“此皆在我所当为,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⑥按此理解,季康子提出的问题就是:在使民的时候,我如何能做到“忠”、“敬”、“劝”这些“应当”呢?“忠”是自己对自己的“应当”关系,后面的回答自然也就是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种阐释是主客体思维模式的一个必然结果。“某某忠于某某”,自然涉及到可以把“忠”理解为“主体”或“客体”的“应当”价值。张敬夫就是把“忠”理解成“我”(自己)对于“自己”的一种“应当”关系。不过他强调的是“君”的“应当”。如果“君主”做到了这个“应当”,就会受到臣民相应的“应当”的回应,这种回应往往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
在“应当”关系中,“我”(自己)依然是一个对象,而且是一个被动的对象,即自己应该向某种价值目标趋进。按照这一思维进程,“应当”本身就包含着“使某某如何”。因为如果一个人“应当”向“忠”的价值理想趋近,他在事实上就被认为是没有达到这一价值目标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人自然可以使其向“忠”趋近。所以,在主客体思维进程中必然会形成另一种对“忠”的解释,这就是把“忠”理解成“使民做到‘忠’这个‘应当’”,“忠”是“民”的“应当”。“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与使民劝于为善也。”⑦
把“忠”理解为“自己”对“自己”的“应当”关系,或者是“忠于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在哲学上有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按照这种理解,“忠”和人的关系是外在的、非“现实”的关系,是一种“理想”、“幻想”的关系。“忠”作为一种“应当”与人发生关系,对于人而言就是一种限制性关系。对于“自己”而言,“忠于自己”中的“自己”被“忠”从外在固定了,“自己”成了封闭的自我。并且由于“己”的内容不同,“忠于自己”既有积极意义,也可以有消极意义。比如“忠于自己”很难和“自私自利”摆脱干系。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刘殿爵更愿意把“忠”理解为“尽力而为”。而“己”是一个人独有的特殊性。因而,“忠”就是把尽力而为作为真正的自我。⑧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关于这句话,后人的训诂五花八门,其中,将“忠”纳入到君臣对象性关系当中是一种很有影响的训诂倾向。“忠”的主体是“臣”,客体是“君”,主客体的关系是“忠于”的关系。在这一思维模式下,“忠”必然被理解为“臣子忠于君主”。季康子即鲁卿季孙肥,季康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作为领导干部如何才能做到让民众尊敬我,忠于我,听我的话呢?”这种理解的问题在于把“忠”简单化了,把民“忠于”季康子当作了目的,而君主的道德表现则是一种手段,即用孝慈的手段来达到让民“忠于”季康子这一目的。在这一解释逻辑中,无论如何在伦理上进行探索,都没有办法避免民“忠于”季康子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
如果把孔子的话换成是回答“民如何才能忠于季康子”这个问题,则需要把孔子的回答当中省略的或者不明确的主客体都加上去。如其中的一种加法就是加上“君”、“民”、“亲”。孔子的回答就变成了:“君临民以严,则民敬其上也。君能上孝于亲,下慈于民,则民忠矣。”⑨这里主客体更为明确了,并且变成了普遍的“君”和“民”,而不再是具体的季康子和其所要管理的民众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说加上主客体就会绝对影响孔子的意思,但至少会丢失掉孔子表述当中可能包含的更为丰富的意义,或者说把某些范畴限定在“君”“民”某个主体上面了。如本句的处理就把“忠”和“敬”限定在“民”上面。
朱熹在注释这段话的时候说:“临民以庄,则民敬于己。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己。”⑩朱熹把“忠”换成了“忠于”,对“忠于”的客体做了抽象化的处理,把孔子针对季康子的具体的回答换成了抽象的回答,把“季康子”换成了“己”。还有一种解释把“孝慈”和“民”联系起来,把“孝慈”作为实现君臣之间“忠于”关系的中介或者过渡性环节。“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民亦孝慈。孝于其亲,乃能忠于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也。”(11)这种解释的落脚点依然是“忠于君”、“忠臣”。如果仔细分析,这类解释其实还是建立在主客体思维模式基础上的,是主客体思维模式可以想到的补充性阐释。
笔者认为,以“忠于”的语言结构来理解传统道德范畴“忠”属于习俗性伦理的范围。因为这种解释指向既定的社会关系结构,虽然其中也有自我“忠于”自我的内容,但由此难以走向后习俗的伦理。某个人“忠于”某个人或者国家的用法在《国语》中有较为典型的例子。《国语》讨论了如何在具体的君臣关系中实现“忠”。“荀息曰:昔君问臣事君于我,我对以忠贞。”(《国语·晋语二·里克杀奚齐而秦立惠公》)荀息紧接着解释说,对国家有利的事凡是力所能及的都会去做,这就是忠。“杀身赎国,忠也。”(《国语·晋语四·郑叔詹据鼎耳而疾号》)愿意牺牲自己而挽救国家,这是忠诚。“贼国之镇不忠。”(《国语·晋语五·灵公使鉏麑杀赵宣子》)杀害国家的栋梁,则是不忠。这里面都是强调要对君主和国家保持“忠于”的关系,是典型的习俗性的关于“忠”的伦理道德观念。当然,《国语》中的“忠”不仅仅有这样的看法,还有一些能够导致对习俗伦理进行反思性思考的看法,不过相比较而言,《论语》的“忠”具有比《国语》更为丰富的伦理内涵。下面就对这些内涵进行一些分析。
二 后习俗意义上的“忠”
1.作为道德教化和学习的“忠”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教导的“忠”到底有怎样的内涵呢?这要联系孔子在《论语》中所表达的伦理思想的整体来理解。“《论语》的文本提出了一种首尾一贯和饶富哲学趣味的关于权威的典范作用的(authority-as-model)思想。”(12)一个人能够对他人产生道德影响,就意味着完成了道德教化的过程,而对方从道德典范这里得到了某种道德的启迪,就完成了道德学习的过程。孔子很注重在这样的教化和学习过程中实现人类社会整体道德的提升。《论语》的“忠”的伦理道德内涵可以借助道德起源问题中的“学”和“教”来得到说明。道德典范有其独特的道德教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对教化者来说是“忠告”,对道德典范的追随者来说是“忠”心的追随。
从《论语》中提到“忠”的相关句子来看,从“学”和“教”的角度入手理解“忠”有一定的合理性。“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忠”自然就能起到教诲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还优于“诲”。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爱”是超越“劳”的,这种“爱”显然是一种彼此心灵有深入交流、平等、相互性的爱。关于这句话的深层内涵,我们可以从当代人生经验中得到某种确证。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如果父母过多地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子女,彼此间渗入过多的功利因素,这种爱就会带来子女的“劳”,使子女感到一种压力,形成一定的负担,或者形成逆反心理,而父母自身也会陷入“劳”的境地。同样,劝导、忠告、教育也是如此。如果在劝导过程中,彼此缺少足够的内心交流和认可,被劝导者就会觉得被贬低,从而从内心深处反感劝导者,形成彼此不信任的局面,“忠告”自然不能切实地发生。在“忠焉,能勿诲乎?”中,“忠”和“诲”并用,说明“忠”是个涉及学习和教育的范畴。而且从形式上看,“忠”达到的劝导效果超越了“诲”,在逻辑地位上高于“诲”,显然在孔子心目中“诲”达到的育人效果还不够理想,而“忠”所完成的“教”在较高程度上实现了人际和谐。
《论语》的“忠”具有道德教化的内涵,回答道德典范如何恰当地对他人进行道德教化的问题。“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如果把这里的“善导”理解为“好的引导”,或者“用善来引导”的话,“忠告”则具有“善导”的功能。那么什么才是“善导”呢?“忠告”如果要发挥作用,一方面需要忠告者有智慧,同时需要启迪被忠告者的智慧,使其发挥主动性、能动性,使被忠告者自觉接受忠告者所提出的意见,这时候“忠告”才能在对方真正地发生,才不会发生彼此的对立和隔阂,从而起到道德典范的教化作用。赫伯特·芬格莱特对完美典范的说明有助于理解《论语》中“忠”的典范价值。“我坚持认为,对孔子来说,中心的问题是把君子看作一个典范——不是工具性的典范,而是圆满的典范,不仅仅是典范的父母或者大臣,更是典范的人本身。君子即意味着人性的圆满实现。从这种人性的角度来看,成为一个君子就是其本身的理由和本身的实现。”(13)典范性价值来源于生命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的力量是无形的、无限的,具有高度的感化力和直接的吸引力,使得人们自然仿效。“譬如北辰”(《论语·为政》),“草上之风”(《论语·颜渊》),“不令而行”(《论语·子路》),“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完美典范的吸引力来自于典范对人性完美的求索,其道德教化作用是关联性的。“就理想的情况来说,所有其他人对于君主的响应,是以一种关联性而非模仿性的方式,那就是:君主要像君主,臣子要像臣子。”(14)
体现后习俗特征的“忠告”强调无功利的爱,强调劝导者和被劝导者间的平等交流,强调宽容和彼此的理解、信任;强调劝导性的语言要建立在劝导者对善的不断求索的基础上,劝导性的语言不再是简单复述习俗规则,而是要有丰富的心灵内涵,被劝导者也不再是简单地服从,而是拥有反思、选择的自主性。因此,对于《论语·为政》“季康子问”那段充满歧义的话,笔者认为应该表述成“在君臣关系中体现‘忠’的伦理内涵”,忠是意义世界,君臣关系是事实性世界。在这里,“忠”是描绘道德典范的追随者的道德状态。这里讨论的不是具体的谁忠于谁的问题,如果一定说“忠于”这一词语的话,“忠于”的对象首先是“孝慈”的伦理道德价值,其次才是某个人。“某某A忠于某某B”只是说B因为具有人性的吸引力,使得A获得完善人性的动力,从而有相关的道德反应。其间没有道德的强迫或工具性的利用,或者外表性的、缺乏自觉的模仿。这样的“忠于”,在忠于他人体现出来的道德价值的时候,就像忠于自己一样,因为那个道德价值是人性完善的需要。忠于他人不妨碍忠于自己,忠于自己不妨碍忠于他人,因为彼此都“立”、“达”、“尽己”了。
2.作为“理智德性”的“忠”
《论语》关于“忠”的思想具有后习俗性的一个证据是“忠”具有“理智德性”的内涵,从而在其中包含了反思性的价值。如果说“忠”也是一种德性的话,那么这个德性的首要内涵在逻辑层面上应该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智德性”,而不是“伦理德性”。(15)“忠”更多的是智慧的启迪,而不仅仅是规范的教导。“忠心”也更多的是从自我的智慧判断出发,接受他人的道德智慧创造出来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评价体系。
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忠”字,延续到现代汉语,“忠告”是典型的用法。这在《国语》中存在一定的例证。“考中度衷,忠也。”(《国语·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忠”需要发自内心,并得到内心真实的认可。“言忠必及意。”(《国语·周语下·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谈到忠,一定出自心意。遵循自己心意,恕而行之就能做到忠诚。“中能应外,忠也。”(《国语·周语上·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不谋而谏,不忠。”(《国语·晋语三·惠公悔杀里克》)郭偃认为不替君主谋划就进行劝谏,这是不忠。“忠”需要“谋”,需要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16)可以依据这个说法,把“忠”的理智德性内涵说成是“中心性智慧”。孔子多次在“忠”前加一个“主”字。“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爱”是“是”,“恶”是“非”,“惑”则混淆了是非的界限并陷入矛盾,“辨惑”就是要区分道德上的是与非。“辨惑”依赖“崇德”,“主忠信”、“徙义”就能够避免是非导致的困惑了。这说明在孔子心目中,“主忠信”人就能够知善恶,并超越两者对立带来的困境。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有两项优点,一是能够很好处理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关系,社会地位的变化不会影响个人的情感;一是能够履行好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要求的职责。是否可以把孔子的“忠”因此就完全定位在这两个含义上呢?笔者以为这是不充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子认为令尹子文上述两个表现是“忠”的时候,是就子张的想法或者社会一般流行的关于“忠”的看法而谈的。孔子也承认这些流行的看法,但孔子对“忠”还有新的见解。后面紧接着子张问“仁矣乎?”孔子回答“未知,焉得仁?”或许子张意识到孔子的回答并没有揭示孔子思想的特殊性,所以进一步提问。这个提问表面上看是在问令尹子文的上述两个表现是否达到了“仁”的要求,实际上问题应该是:“令尹子文这样的‘忠’是否是‘仁’所要求的‘忠’呢?”孔子回答说,不是“仁”所要求的“忠”,因为“未知”。在《论语》反映出来的孔子思想中,“知”是和“不惑”联系在一起的,“知”保证了在对不同的人生方向进行选择的时候能够有充足的智慧。孔子希望的“忠”是在“知”基础上的,这个“忠”使得人不受世界的迷惑,并成为“仁”性的道德。
智慧内涵是保证“忠”具有后习俗特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使得“忠”具有了反思、批判的潜能。“忠”的智慧内涵或者认识论内涵,在后来的注解当中,在某种意义上被忽略或者被弱化了,从而发生了一定的阐释重点和阐释逻辑的变迁。在当代,在进行《论语》“忠”的“现代转化”的时候,需要重视这一内涵。
3.作为个体品德表现的“忠”
《论语》中的“忠”的另外一个内涵就是个体的品德,包括对个体追求完善的价值地位的认知。这一点也体现了《论语》“忠”的后习俗性特征。从《论语》中有限的几处直接论述“忠”的句子来看,作为个体品德的“忠”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在个体的言行,包括精神活动中保持对智慧性的“忠”的记忆、应用和条理化,使“忠”的智慧体现并贯穿于个体的言行之中。“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言思忠……”(《论语·季氏》)“言思忠”要求在“言”的时候,由“中心性智慧”规范、指引,从而使语言做到清晰而有逻辑。还有一段话,孔子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忠”的智慧就像明灯,在一个人站立的时候“参于前”,在车子上就像“衡”一样是人的依靠。对于人而言,最不能离开的是智慧的明断,没有了精神的指引,显然人的言行就没有依凭。
其二是对个体独立于社会的追求完善的价值认知和实践。孔子讨论个人的德性,显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关系来进行的,言行总是涉及到他人和社会,“忠”显然包含处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相关价值考量。
倪德卫在解释《论语·公冶长》提到的令尹子文表现的“忠”的品德的时候,引入私德—公德模式,把其解释为“公德”。倪德卫解释说:“忠是这样一种品质:对上级或相同层次的人确实地遵守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恕是准职责之外的品质,这就是说,它跟对人不严格要求的东西相关;它将意味着一如各自的角色要求的那样,对下属或相同层次的人待以礼貌和体谅。”(17)在倪德卫看来,“忠”是人在其角色中的公德之要求。“忠是要人遵守由公德意指的责任。忠和信以一种方式连接成对,又和恕以另一种方式连接成对:恕表明对地位相等或地位更低的人的恩惠,这种恩惠要跟自己处于相反的角色时所想要的一样,当它是超越规则或软化和仁慈化规则的运用之事之时,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忠是严格要求自己对上者或与自己同等的人尽责,正如在角色倒转时,自己对处于其位的人所要求的一样。”(18)
倪德卫的理解注意到了孔子这段话的一个方面,但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在孔子和子张的对话中提到“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说明令尹子文遵守了其社会角色,“忠”可以理解为一个人遵守其社会角色要求的“公德”,这个“公德”的内容就是设想你处在相反的角色的时候,你对目前所处的角色的道德期待。这样理解的“公德”保证了作为主体的自我的领悟性,自我可以通过智慧和必要的类推能力把握自己所要履行的公德。但在子张对问题的描绘中还包含了另一个方面的内容。“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在这个句子中揭示的哲学问题和哲学逻辑是“个体”对超越社会角色的“自我”的认知,在“个体—社会角色”的关系中,令尹子文表现出来的是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得失对其“喜”、“愠”没有影响,这说明“忠”还表现为“个体”对自我道德价值地位的肯定和认知,而不仅仅是对社会角色要求的道德品质的认知和践履。令尹子文的“忠”德表现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显示,“忠”这个德性要求社会地位的变化不影响个人完善自我的道德价值追求。
4.作为伦理关系的“忠”
《论语》之“忠”还有一个含义是智慧指导下的体现正面价值的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在智慧指引下体现了积极肯定的价值,因而可以叫做“伦理”关系。“忠”的这种含义保证了“忠”不是对既定社会关系及其习俗规则的简单因袭,还包含了积极的调整。《论语》中作为具有伦理内涵的“忠”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在人际关系中带入“智慧”反思的因素,智慧反思是人际关系具有“忠”这一伦理意义的基石。“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在这里,“忠”是与“谋”联系在一起的。曾子要求一个人在为他人出谋划策的时候要有智慧,这是作为个人品德和伦理关系的“忠”的必然要求。
其二是在智慧的指引下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要求的社会责任、公德或职业道德。就像上文所述令尹子文一样,履行官员角色的要求,把旧令尹的政策措施告知后来者。到底该如何履行公德的要求才算“忠”呢?孔子提出了“知”,说明“仁”所要求的“忠”是在“知”的基础上,处理好个人品德完善和履行社会公职的关系。
其三是在纵向的、有上下级的人际关系中保持积极肯定的价值导向,从而实现政治认同。“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礼”的含义过于复杂,难以用一两句话解释,在此权当其是一个价值体系。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把这个正面的价值指示为“孝慈”,提出“孝慈则忠”。“忠”与其说是“忠于君主”,不如说是“忠于某种价值”。但这种价值不应是外在的,与其说是“忠于某种价值”,不如说是“忠于自己智慧的价值决断”。
其四是在横向的人际关系中要在个体智慧的基础上保持敏锐的道德感,从而实现肯定的正面价值。这里所谓的“横向”是从《论语》中“友”这种关系引申出来的。《论语》谈“忠”,往往是与“问友”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论语》“忠”所具有的后习俗伦理特征之一。笔者在此处命之为“横向人际关系”。这里所说的“正面价值”是指个体对可能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的人和事的自觉抵制,及其对自身负面价值的自觉改过迁善。“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在这样一个句子中,仅就“主忠信”三个字很难明确定位“忠信”的意思,其意思可以通过后面的句子来确定。这里的“不如己”主要是道德价值上的“不如己”。从这个句子来看,“忠信”要求克服道德价值上“不如己者”对自己的消极影响,保持自己积极的人生追求。“忠信”还要求对自己过错的敏锐的智慧判断,对自我可能出现的否定性倾向有敏锐把握,并祛除过错。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如果人际关系中有“忠”,无疑可能是和谐的,不过,这种“忠”起源于道德典范人性价值展现而带来的道德影响力,“忠于”典范的人从典范身上学习了人性的积极的伦理道德价值,从而完善了自身。两者之间不存在“愚忠”带来的种种伦理道德局限。从这一意义上说,《论语》当中的“忠”依然有其不可磨灭的现代价值。
注释:
①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陈咏明、瞿德瑜译,大象出版社,2009,第7页。
②③汤姆·L.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雷克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1页;第12页。
④艾伦·格沃斯等:《伦理学要义》,戴杨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页。
⑤裴传永:《孔子的忠德观探析》,《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⑥⑩(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1992,第16页;第16页;第35页。
⑦⑨(11)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119页;第120页;第120页。
⑧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蒋弋为、李志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第219页。
(12)(13)(14)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144页;第151-152页;第153页。
(1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5页。
(17)(18)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周炽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80页;第80页。
标签:论语论文; 论语·公冶长论文; 论语·为政论文; 论语·颜渊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国语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