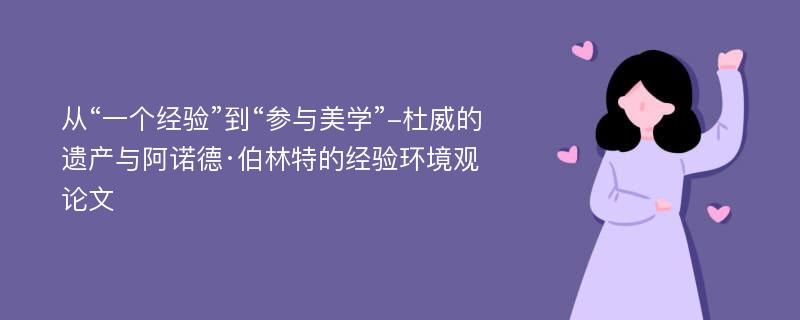
从“一个经验”到“参与美学”
——杜威的遗产与阿诺德·伯林特的经验环境观
史 建 成
(深圳大学 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 与卡尔松侧重于鉴赏方式探讨的环境美学不同,阿诺德·伯林特侧重于鉴赏经验的展开,即用一种“参与美学”来解释艺术与环境审美。伯林特的审美经验理论受到杜威美学的影响至深,他从三个方面借鉴了杜威的一元论经验观,即经验的连续性、经验的感知性、过程与对象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伯林特以杜威的经验理论为根本架构解释审美问题,他通过阐发包含艺术对象、感知者、艺术家、表演者的“审美场”理论为经验发生构建了一个合适境域,进一步细化了杜威的经验论美学并为经验划定边界。但审美场的构成要素既非解释任何问题的最终根源,同时需融合诸多要素于一体的经验发生作为理论言说的开端,所以,伯林特借鉴了杜威的“交互”观念,确立了“审美交互”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审美交互”路径下的经验论阐发开始摈弃主客二元的要素论、感性知性分裂的观念论,转而开拓出一种交融经验展开的“描述美学”方法,这可以被称之为用经验的方式来解释经验。事实证明,伯林特的“描述美学”成为他解读特定审美境域的根本方式,同时也为美学面向实践与日常生活提供了方法论。
关键词: 一个经验;参与美学;审美场;审美交互
在环境鉴赏模式的讨论中,卡尔松认为伯林特的“参与模式”同“科学认知”并不矛盾,两者在严肃、恰当的鉴赏视域中相互补充。的确,如果要以两种理论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定向来定义理论矛盾的话,我们无法给出两种理论存在矛盾的结论。但卡尔松的“鉴赏理论”以客观性为内核,强调主客分立的二元论,伯林特又恰好反对主客划分,两者为何不矛盾呢?
从教育活动三要素可知除了教师和学生,HPM与教科书(报告题目见表5)也是重要研究主题,如报告45对20世纪初4本尼泊尔数学教科书的分析比较,报告13对最近三版瑞典课程中代数内容的比较,报告12对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高中教材中数学文化的分析,报告18对教科书中阅读材料的研究及报告19对1~12年级21本土耳其教科书中数学和科技史的分析.
事实上,强调两者的矛盾性是缺乏对其理论根源深入考察的结果。卡尔松的客观性不是认识论上的客观性,而是“审美相关性” 视域中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指向审美经验的标准化,在根本意义上是审美的而非认识的,只是它在理论阐发中倾向于鉴赏方式[1]。伯林特则不以标准化的审美经验规范为目标,而是以经验自身的展开为研究对象。如果将两种理论置于同一审美鉴赏语境的话,那么卡尔松侧重于规范的鉴赏方式,伯林特倾向于敞开的鉴赏经验。正如伯林特所言:“对环境的理解是审美地经验它的一个前提,但理解自身还不能保证那种意识模式成立。”[2](P14)鉴赏方式的理论为审美经验提供契机和方法,但并不能代替经验自身的展开,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那么这种环境的审美经验如何展开呢?与卡尔松希望将“审美相关性”视野从艺术转移到环境不同,伯林特从艺术、自然、建筑、城市等领域的内在审美一致性出发,试图统筹起一个建立于感知经验之上的美学综合体,这个美学综合体也就是他的“参与美学”。所以从伯林特自身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其环境美学中的核心观念同其早期艺术美学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本文试图从伯林特美学思想整体视角出发,寻求其与杜威经验论美学之间的隐秘关联,进而梳理出一条跨越艺术论域与环境论域的“参与美学”发展史。
一、一元论经验观的传承
“经验”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本义具有尝试、试验的意思,后来演变为生活中互动交流的状态,以及在后天从事的活动中所获得的倾向、技能、判断等。阿诺德·伯林特的理论建构以“经验”为核心,试图澄清传统艺术同当代环境审美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环境美学并不是同艺术理论截然对立的,而且两者“在根本上相同”。这种包容两种审美领域的统一美学就是参与美学。参与性的美学使人“对于城市和区域规划的审美兴趣同建筑设计一样多,对于流行、民间文化多种方向上的审美兴趣同纯粹艺术一样多,在所有人类关系中而非单独为艺术目的而保存的特殊惯例中保有审美兴趣”[2](P12)。“一种综合的审美在经验领域包含了所有这些,但并没有模糊他们的个性”[2](P12)。“经验”成为内在地架构起传统艺术与当代环境的核心命题。
在职业中学政治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想实现有创新有发展,教师还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在教学过程中,由之前的“封闭式”教学转变为“开放式”教学,让学生在良好的教学氛围中主动、自主的学习政治知识。而要想实现这一点,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就需要对课堂内外以及教材内外的关系进行有效处理,在职业中学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唯本理念”以及“社会生活”都有效渗透到政治教学课堂中;也可以将社会热点以及焦点问题融入到政治课教学中,这样不仅能够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还能有效开阔学生的视野,让政治课教学得以更为良好的发展与进步。
正如前文所述,将自然与环境在“经验”中关联起来有着当代艺术扩大化的原因。绘画越来越突破材料、主题、图像的传统,雕塑的形式也允许人们在其中穿行,构成一个环境,戏剧也越来越讲求同观众的参与互动。艺术向自然环境、城市环境、文化环境领域扩展,这一现状构成了对传统二元对立的“静观”审美的挑战。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外物在一个统一经验中结合起来了。我们不是从一个外在视野鉴赏景观,而是生活在景观中。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严肃思考的是,为何伯林特要以“经验”理论来架构新美学?它同杜威的“经验”又有何关联?伯林特在《杜威的美学遗产》一文中坦言,自己的“审美介入”概念包含了杜威的基本洞见。他提到,这种过程中的“全神贯注”是审美鉴赏的特点。更为明晰和重要的是,他提出在审美感知中没有自我和对象的区分。主观和客观结合在一起,没有任何单独一方可以独立存在。这些观点在超越“一个经验”的审美扩大中仍然得到延续,并预示了“审美参与”的审美鉴赏观念。这个观念详细阐发了鉴赏艺术与自然,在这种鉴赏中,鉴赏者活动的经验交融是核心特色。正像杜威的理论,它使鉴赏围绕感知经验,但不对经验施加任何形式要求[3](P163)。
伯林特认为杜威经验主义中的主客融合是“参与美学”的重要先声,因为正是这种“连续性”的经验构成了艺术、自然、环境审美的共同基础。在杜威那里,经验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性过程。杜威经验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释自然,并试图解决现代社会科学、工业、政治同传统理智、道德的断裂。杜威认为:“经验乃是被理智地用来作为揭露自然的真实面目的手段。它发现:自然和经验并不是仇敌或外人。经验并不是把人和自然界隔绝开来的帐幕,它是继续不断地深入自然的心脏的一个途径。”[4](P3)经验在杜威那里是哲学研究的根本路径和方法。伯林特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杜威经验主义进行了继承与发展:
潘币:2011年10月,一种新的“计量单位”——“潘币”出炉。10月6日,当乔布斯去世的消息公布之后,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其官方微博上称,“苹果”董事会应该做一决定,大量生产1000元人民币以下一部的iPhone手机和iPad,让更多的人用上苹果,这才是对乔布斯最好的纪念。此微博一发,立即引发网上热议。有人回击道:要是潘石屹的房价是1000,中国13亿人民都纪念他。有人恶搞道:希望房价降到1潘!10月26日,潘石屹索性在其微博上晒出了面值一潘的“潘币”。
中药材生产并非以产量作为唯一目标,结合药材栽培方式、田间管理模式和有效成分含量的关系及有效成分的积累动态,目的是建立标准的生产技术体系使有效成分和药材产量二者达到综合最佳值,生产优质药材[31]。针对黄芩各个生长时期,田间管理方式包括中耕除草、间苗、定苗与补苗、排灌水、蹲苗与盖草、剪花枝。见表4。
为了阐述这种经验的“连续性”,杜威首先描述了现代社会造成经验断裂的原因。首先,这种断裂源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兴起的纪念馆。一部现代艺术史甚至可以根据博物馆和画廊制度的发展过程来书写。那些用来展示绘画、雕塑的博物馆收容了来自民族过去艺术的精粹以及对其他民族的掠夺物。其次,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艺术品同生活的分离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家们热衷于艺术品的收藏,他们以艺术的稀有来展现自己的高雅趣味。在国家范围,资本主义也极大推动了歌剧院、画廊等隔绝艺术品同生活关联的独立场所。杜威认为这些建筑物就像教堂一样,“它们与某种‘比你更神圣’的态度相对应”[5](P10)。再次,现代工商业的国际化削弱以至摧毁了地方特性。经济贸易的扩大以及人口流动使得本土艺术的地方特性越来越弱,艺术成了市场上用来售卖的美的艺术品。艺术品从其起源的社会生活中孤立出来。复次,艺术家为了逃避工业发展的机械性,试图通过“自我表现”来同经济力量分离,这种“个人主义”在杜威看来,甚至达到了夸张、怪异的程度。
在杜威看来,现代艺术同生活的经验断裂并不是艺术本性的问题,而是“由一些可列举的外在条件所决定的”。这些外在条件深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审美知觉。所以,杜威的理论工作就在于“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5](P12),恢复最为平常的经验的审美特质。这种连续性是一种澄清而非架接,它预示着审美扩大化的美学新理论。当然,杜威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艺术,他强调艺术是日常经验的完全表现。但这种连续性的恢复为伯林特的环境审美打开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理论视域。
紧随杜威的脚步,伯林特倡导一种“连续性”美学。在早期理论中,伯林特是从艺术审美讨论这一话题的。伯林特认为:“连续性观念反映了这样的理解:艺术不能与人类的其他追求相分离,而是融合进整体范围的个人、文化经验但不取消其经验的独特性。艺术品同其他通常在非审美语境的对象有着共同的人类活动和生产技术来源……审美经验是人类整体经验谱系的一部分。”[6](P46)伯林特不仅描述了艺术经验与生活经验的本然连续性,同时还以“审美参与”重新解读了这种“连续性”中共同的经验要素。这种“参与”来自于伯林特对现代艺术冲破主、客明确界线的反思。传统康德意义上的“无利害”审美愉悦强调一种对于艺术的远距离静观,审美感知与实用性、日常经验与审美经验是明确区分甚至对立的。20世纪的环境艺术模糊了艺术的传统边界,人们不能从特定距离进行鉴赏。装配艺术既不是绘画,也不是雕塑。偶发艺术打破了戏剧、雕塑、舞蹈、绘画的独立性而将它们混合为一个参与式的经验。艺术领域的多样性结合以及艺术的参与性共同引发了传统美学理论的困境。在鉴赏过程中,全身心的审美参与变得越来越重要。伯林特认为:“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已经促使我们认识到,进入到艺术世界需要一个整体的人的动态参与,而不仅仅是心灵的主观事件。这种参与强调关联与连续,并且最终导向到人类世界的审美化。”[6](P26)所以,杜威所强调的经验连续性在伯林特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人的全面经验的参与打破了审美经验与生活经验的过度区分,同时为这种连续性寻找到一种内在的统一性。
2.经验的感知基础。经验的感知属性并不新奇,因为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就积极倡导了人的生理感官甚至内在感官对于获取知识的重要性。杜威的经验“连续性”理论建立在“原初经验”基础之上。这种“原初经验”并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存在的主观认知,而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活动。这种同生命整体的沟通性和连续性是完全不同于主、客二元的传统经验论的。
正如伯林特所言:“经验在杜威那里并不能被理解为内在的、主观的过程而是在人类的普通事务中自然、有机的发生过程,这种经验的核心观点将杜威美学置于经验的生物、文化、现世的状况之中。”[3](P163)杜威通过动物的活动以及原始野蛮人的行为阐释了这种经验的当下性与过程性。动物的经验体现在它警惕的目光、锐利的嗅觉以及突然竖起的耳朵,它们的行动与感觉相互交融,过去与未来都作为当下而起作用。野蛮人的行为和知觉也具有连续性,“他的感官是直接的思想与行动的哨兵,而不像我们的感官那样,常常只是通道,经过它们,材料得以聚集和贮藏,以服务于久远的可能性”[5](P22)。这种经验在当下感觉与对象的交融中,从混乱转向平衡,周而复始。同时也正是在一种秩序丧失向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审美的“一个经验”才从中萌芽。“一个经验”显示出了经验本身从开端发展到完满的一体性过程。
这种感官感知是生命体意义的来源,它并不同行动、理智对立。杜威认为:“五官是活的生物藉以直接参与他周围变动着的世界的器官。在这种参与中,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精彩与辉煌以他经验到的性质对他实现。这一材料不能与行动对立起来,因为动力机制与‘意愿’本身是这一参与藉以进行与指向的手段。这一材料也不能与理智相对立,因为心灵既是参与藉以通过感觉产生成果的手段,也是意义与价值藉以抽取、保存并进一步服务于活的生物与其周围环境进行交流的手段。”[5](P25)可见,“原初经验”本身是与多重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孤立、静止的存在。全部感官同环境的一体互动形成了杜威意义上审美性的根源。伯林特评价杜威的经验时认为,“真实的审美经验,正如他所考虑的艺术品,是感知”[3](P163)。伯林特继承了杜威身体化感知的经验概念,在环境美学中他突出强调这种多感官的参与。
伯林特的经验美学从感官感觉入手,“环境感知的最简单形式是感觉意识,它是任何其他意识的前提”[2](P14)。伯林特批驳了传统艺术美学重视视、听感官而忽略触、嗅、味感官的传统。他认为以触觉、嗅觉、味觉为代表的接触感受器是人类感觉系统的一部分,理应成为环境审美经验的组成部分。他有如下著名论述:“嗅觉与我们的时空意识保持着亲和性。甚至味觉也能对意识作出贡献,正如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意味深长地证明的那样。此外,触觉经验也不如我们常常想象得那么简单。它属于触觉感受系统,既包含触感又包含对表面质地、轮廓、压力、温度、湿度、痛感和内脏感的皮下知觉。它也包括了其他的感觉渠道,这些途径经常被忽视,并与接触相混淆,它们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不同的。运动知觉包括肌肉感知和骨骼或关节感知,通过表面阻力的程度:硬、软、锋利、钝、坚固、易弯曲,我们感觉到位置和硬度。而且,我们通过前庭系统来直接把握身体运动:上升与下降、翻转与旋转、阻碍和通畅。”[7](P10)可见,伯林特的参与经验已经成为身体化的参与。这种身体同环境共成一体,不能分割,可以说环境构成了人的身体。此外,伯林特还强调身体多种感知经验的联觉。这种联觉将其内在的任何一种感知形态经验为诸种形态的融合。特定的感知形态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才能清晰辨认。
总而言之,伯林特认为从审美鉴赏的角度来看,经验的“统一性”可能是错误的,但经验的瞬间性、偶然性并不能证明“一个经验”在当代艺术和自然鉴赏中是不适用的。首先,“一个经验”虽然是过程性的,但并不以过程时间长短作为依据。“一个经验”的时间可长可短,只要能为经验过程划分出开端、发展、完满的逻辑站点即可,而不是具体规定时间的范围。其次,“一个经验”的完满实现以感觉经验的达成为归宿。感知的当下性、完成性并不因对象表现形式的断裂、片段而相应缺乏完整,经验本身就不是对于纯粹客体的形式描述。
1.经验的连续性特征。杜威经验方法的重要工作是为其赋予一个真正解决一切问题的意义。传统经验主义要么将经验视为偶然的、零散的,同自然本质有着巨大差异的主观意义,要么将其视为完全是机械和物质的。杜威为了解决这种人与世界的断裂,提出了经验的“连续性”问题。这种“连续性”内涵在美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强调艺术经验同生活经验的“连续性”。
3.经验是过程与对象的统一。杜威经验主义的重要特点就在于以经验的连续性试图统一起实践与理论、艺术与科学、自然与经验。这些看起来似乎对立的要素在杜威看来归根到底都统一于经验。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说,杜威的经验既不是客观对象,也不是主观意识,它就在生物体克服困难获得与环境均衡的过程中。
“原初经验”是“活的生物”均具有的最基础的经验形式,这种“活的生物”处于自身同环境相互作用、从矛盾走向协调的过程中。人作为“活的生物”同鸟兽一样,具有眼、耳、口、鼻、舌的官能。“生物的生命活动并不只是以它的皮肤为界;它皮下的器官是与处于它身体之外的东西联系的手段,并且,它为了生存,要通过调节、防卫以及征服来使自身适应这些外在的东西。”[5](P12)在杜威那里,这种经验事实上是全部身体官能同环境进行的交换和互动。生物既要深入到环境中,克服困难获取生存的补偿,又要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自身与环境的相对均衡。用杜威的话说,就是以“最内在的方式作交换”。
伯林特在经验中虽然突出强调身体化的参与,但在经验中身体是行动中的身体。他认为:“环境的主要维度——空间、质量、体积和深度——并不是首先与眼睛遭遇,而是先同我们运动和行为的身体相遇。”[7](P10)经验在伯林特这里也是一种当下性的过程,而非固定的实体,并且只有这种丰富性、直接性、当下性的经验过程才是审美的。在杜威那里,感知经验虽然具有包容性和统一性,但文化的因素似乎只有还原到原始经验时才同感官的知觉融合起来。而伯林特则强调在身体化的感知过程中价值判断、生活方式、宗教等文化要素作用于感知。他强调人的身体化经验本身就是不能脱离文化的,身体是文化中的身体。不同民族、国家、地域的人对于时空和环境的感知非常不同,这是文化背景带来的经验差异。所以,要讨论环境的经验审美,就必然不能摆脱文化有机体的讨论来单独探讨感官经验的当下性。伯林特对于经验感知过程中文化介入的强调无疑是对杜威经验主义的进一步深化。
工作中,我用真诚、坦率的处事风格和扎实、厚重的业务功底,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1986年,机会再次降临到我的头上,通过筛选,我被海淀区教委选派到北京教育学院脱产学习两年,专业是教育管理。
虽然伯林特非常推崇杜威的经验主义,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也提出了质疑。如他认为杜威有些过于固执于经验的“统一性”了,“一个经验”的完满、自足已经受到了当代新兴艺术发展的质疑。伯林特举例论证了这一点:“例如,聚焦于绘画表面的抽象表现主义和硬边油画并不能为他们自身提供一个经验的过程,并导向完满。事实上,他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鉴赏,并且我觉得这种方式能够推动他们如此,但他们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绘画表面的瞬间影响,例如它的纹理、它的色彩感知的张力以及它们的对比和对立。”[3](P163)
现代艺术已经越来越排斥完整性。不仅在绘画,而且在音乐、电影、戏剧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新兴艺术表现方式。它们拒斥完整的“一个经验”,关注于断裂、细节的刻画。同时在自然鉴赏领域,杜威的“一个经验”也并不具有典范意义。伯林特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审美很多时候聚集在瞬间和细节。我们不仅可以审美地凝视落日余晖的傍晚,而且在一朵花、一个孩子的脸上,我们也往往能够抓住瞬间之美。在自然的很多形式要素中,我们也保有审美的愉悦,例如水泊中的涟漪、挂着露珠的青草等,这些情形都是转瞬即逝的,对它们的审美很难用完满的“一个经验”来解释。
现如今国内的电力企业使用监测系统时结合自动化技术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合理使用自动化在线检测,可以及时找出设备运行期间的故障,并可对设备运行的安全性起到保障作用,进而实现供电系统中的数据采集工作。通常情况下,国内的自动化监测系统在监测技术研究领域一直使用到大量的人力、物力,且监测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更是为实现电力系统的自动化管理,并在减少成本的同时还可以有效提升我国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运行效率。
可以说,伯林特将杜威从生物学意义上的经验感知进行了更加细密、深入的当代化阐释。在这种阐释中,人与环境的紧密关联被阐明,并为其进一步提出环境美学理论奠定基础。
由此我们认为,伯林特的经验参与理论并不具有彻底反叛杜威理论的意义。在杜威的经验主义的基础上,伯林特确实根据当代艺术、环境的新问题做出了更加深入的阐发,但他的新理论很难说在经验的核心概念上区别于杜威。
伯林特将“审美场”视为参与式经验的阐释语境,以此区别于传统艺术理论将概念过分孤立化的弊病。正如学者Elmer H Duncan所评论的:“这一观点似乎认为,审美经验、审美对象、审美价值等核心观念除开包含它们所有要素的整个‘审美场’语境之外,并不能被定义。”[9]尽管在“审美场”的区分性描述中,伯林特一再强调多种要素间的互动性和一体性,但他依然认为这种条分缕析式的结构性解读有着过分分析化的倾向。他说:“然而‘审美场’的这种解释一定被视为发生于审美境域经验整体的一种分析式解释。当我们经验地而不是分析地来理解场域的时候,我们可以称它为‘审美交互’。因此‘审美场’构成了分析审美经验结构的一个尝试。它并非实际的事件,但却是认知这一事件努力的产物。然而,所有这种尝试一定对艺术经验保持敏感,因此它们一直是派生出来的。美学中没有东西是建立在原则之上的也许应当被视为一个信条。”[8](P89-90)伯林特对这种审美场理论存有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设想,即首先提出四要素构成的一个理论结构来否定片面的、静态的传统审美理论,然后又试图消解这一理论结构,目的在于破除对于专断理论模式的本质归因。审美场试图追溯审美经验本身的发生,因而它是派生的而不是本质来源的,进一步它是认知审美事件的尝试而不是事件本身。所以,审美场理论在伯林特这里就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发展性,而非传统理论的封闭性和绝对性。为了将这种审美场的经验属性呈现出来而非埋葬于理论架构中,伯林特进一步论述了“审美交互”。“审美交互”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范式,不如说是一种审美经验境域的解读方法,一种基于互动、交融、一体原生经验的整体视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林特将其视为“审美场的关键”。
二、“审美场”的境域与“交互”视角
另外,我们要清楚的是,“审美场”理论早在1970年就被伯林特提出,这要比“参与美学”概念的提出早20多年。但“审美场”的理论言说却处处同“参与”经验相协调,甚至在理论严谨性、整饬性上更胜一筹。这种严谨性、整饬性首先体现在伯林特对艺术参与四要素的全面梳理,涵盖了艺术创作、艺术鉴赏、艺术表现等领域,并将它们之间经验基础之上的互通性阐发出来。同时,四要素分析最终服务于动态、开放、一体的“交互”经验而非理论结构的自洽,这无疑是其更高明之处。四要素固然是传统艺术经验场域中的核心参与者,但经验本身的交互发展,不断的衍生新分支、新特征使得任何一种机械的本质归因失去立足点。承认一种审美经验基础的开放性无疑对其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后期的“参与”经验阐释以感知为核心,理论视角开始缩小,此时的“参与美学”也被其他学者诟病为过于主观而缺乏界定,但这显然并非伯林特本意。
为了获得更大的理论阐释力,伯林特建构了其经验美学的境域理论——“审美场”。伯林特这样界定他的“审美场”概念:“艺术只能被一种整体境域的指涉所界定,艺术的对象、活动以及经验在其中产生,它是一种包含所有这些所指对象乃至更多的环境。我要叫它审美场——艺术对象在其中动态地、创造性地被经验为有价值的东西。它就是这样一个包容性的环境,我们必须从它的整体来考察,之后才可以给出一个什么是艺术的精确解释并且让人苦恼地回答什么构成美学理论。”[8](P47)伯林特一再强调这样一个“审美场”中的诸多要素是不可分割和区分的,它们在审美经验的发生过程中具有一体性。事实上,杜威在讨论艺术时就多次提到境域。他在情感表现的论述中提到:“情感是由情境所暗示的,情境发展的不确定状态,以及其中自我为情感所感动是至关重要的。情境可以是压抑的、危险的、无法忍受的、胜利的。”[5](P77)经验的内在机制——表现性活动并非只是两个固定要素的互动,而是有着多重因素参与进来的境域活动。只是在杜威的论述中,这种境域表达是隐含的而非显在的。无论杜威还是伯林特,他们所提到的境域都是一种限定性环境,即经验发生的环境。
伯林特将境域阐述视作经验理论的进一步细化。在“审美场”的境域中,他认为有四大审美构成要素:艺术对象、感知者、艺术家、表演者。艺术对象是有关艺术学问的焦点。在传统的艺术史研究中,纯粹艺术运动、学派的发展演化以及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和影响均围绕艺术对象这一焦点展开。伯林特认为这种解读使艺术对象过分孤立化了。伯林特从“审美场”的经验发生意义上来解读艺术对象。他认为艺术对象的合法性来源于它在审美场中具有推动审美经验发生的功能而非其自身的属性。他举例说,古希腊的花瓶、史前时期的鸟类化石、非洲的仪式面具以及类似对象在内在属性上并不具有艺术地位,但它们却在变换了场景之后被审美地接受了,这其实就是依赖于对象在审美场中对于审美经验的推动。在感知者方面,从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提出一种主体的感知经验到现代的审美态度理论,关注于主体的经验理论就一直延续下来。但伯林特认为,如果不能从审美场中的经验发生来探讨主体感知,那么过度强调“关注心理”就是一种局限。在当代艺术领域扩大化的语境中,感知者不再与对象保持静观的距离。感知者是投入到艺术经验中的感知者,是在一个特定审美场的发生过程中的感知者。此外,伯林特也非常重视艺术家在“审美场”中的重要作用。艺术家不仅是能够把握声音、线条、颜色等材料的工匠,同时他也在创作中拓展人类的感知。艺术家是艺术品的创造者,同时他也创造了审美经验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首先必须作为“审美场”中的感知者而存在,艺术家与感知者在这种场域中具有了融合的可能。另外,表演者的因素往往被传统艺术所忽视。表演者处于艺术创作者与感知者之间,一方面,表演者的艺术展现往往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不能等同于音乐家、剧作家以及舞蹈编排者的原初目的;另一方面,表演者又拒绝了传统感知方式对于距离、静观的诉求。但在伯林特看来,这恰恰是审美经验发生场域的重要内涵。他认为表演者通过表演使得艺术展现为一个事件。在艺术表演过程中艺术自身得以展现,同时它也将自身置于感知者审美经验的语境中。表演艺术的功能就是推动这样一个整体“审美场”具有美学意义。伯林特所提到的这四个审美要素还受到生物、心理、历史、文化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在这种综合因素构成的境域关系中,审美经验得以发生。
秦明月知道老马作为一个经验老到的法医,一般没有把握的事绝不会乱说,沉吟了会又问:“这么说来,死者可能是被人偷割了肾脏后而造成肾衰竭而死?那么这个过程一般需要多少天?”
“交互”的本义是商品交易。其现代内涵可以追溯到19世纪著名物理学家克拉克·马克斯维尔(Clerk Maxwell)。如果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从伽利略到牛顿一直延续了对物体运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那么近代电磁物理学的发展则拓展出了系统之中能量运动的“交互”关系,这是完全不同于实体性物质粒子对立关系的思维方式,它更加强调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的布局、运动以及协调关系。杜威同亚瑟·F·本特雷(Arthur F Bentley)于1949年出版的认识论著作《知与所知》突破性地将这一自然科学思考方法拓展到哲学认识论 。在这本讨论认知与命名的书中,作者认为“所有的观察都处在系统之中,通过假设的方式人们才能接近它们,好像这些观察之间的关联是可以建立的。但这种关联并非显而易见。那些宣称‘知者’以某种方式在可知自然面前更具优越性以及被称作‘所知’之物更具优越性的人,我们坚决反对,他们将古老的阻碍加之于像我们这样的研究。我们认为,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是人类有机体,受限于我们观察所处的世界位置,并且我们接受这一点且将之视作获得重大发现的境遇而非阻碍”[10](P80)。这样一种统一立场试图说明传统认知与被知、物与物之间的绝对分裂是一种人类认识局限性的结果。人类在承认这一局限的基础上,仍然可以从这种视野中假设、探求一种与他者的关联,从而破除一种以“知者”与“所知”者为核心的片面视角。进一步来说,这种关系性存在的方式有着“相互”和“交互”之别 。“相互”着眼于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配合。其中一方是施力者,另一方是受力者,两者都是已经完成定义的实体。“交互”作用的两方则均具有施为的动力,并且不具有完成性,也即双方在动态交换过程中才可以相互定义。“交互”关系中的能量流动使得我们无法从静态角度对其中一方进行最终定义,因为这必然涉及它同其他要素的交融关系。所以,“相互”关系可以完全排除环境进行二元划分,“交互”关系却必须从多元要素相互交融的系统、境域出发来认识其中任意一个要素。“交互”着眼于系统内在动态关系,并不将具体的物质、元素、实体视为解释一切的最终根源,同时也不将要素、关系等从系统中孤立起来,一切具体事物的认知建立于动态的系统关联之上。这样,“交互”较“相互”的认知方式能够更加清晰地还原事件发生的原貌,摆脱僵化认知和固定时空条件的束缚。伯林特正是借鉴了杜威在认识论上的突破性成果,从人存在于世界、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入手探讨审美问题。“交互”的立场对于审美经验还原的努力促使伯林特采取了上文所指出的观念立场——否定对审美场构成四要素的单纯分析。
显然,四要素的划分只是理论演进的一个节点,是还原审美经验“交互”现场的前提,因为“包含艺术感知者和感知审美对象的交互经验才是真正的审美场的核心”[8](P90)。伯林特还说道:“为了表达我们称之为审美的整体复杂经验,‘审美场’概念就是最好的方式。这里以客体、感知者、创造者、表演者为代表的四个要素是产生作用的核心力量,它们受到社会惯例、历史传统、文化形式和实践、材料和工艺上的技术发展以及其他类似语境状况的影响。单独挑选出其中之一作为艺术的中心都是用部分误导审美场的整体。”[6](P49)因此,审美场理论是以“审美交互”的经验一体性作为现实基础与理论基石。如果我们否定“交互”的整体性视角而滑向对立要素间非此即彼的片面逻辑,那么“审美场”理论则同传统审美要素分析理论没有差别,从艺术审美导向包含艺术与环境的参与美学理论也不会有必然性。
美国最大的战略优势,不是美军,美军与中俄对战,必将损失惨重;不是美钞,金融战争必是两败俱伤;不是战略核武器,一旦发生核战争必然相互摧毁。美国最大的战略优势是农业和粮食,农业和粮食不仅是美国最大的战略资源,也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基石。
在伯林特看来,理论自身来源于经验,而不是专断的设定。对理论家而言,首先要做的不是去界定概念,建构系统,而是要参与到对现象的体认、关联以及解释。他认为:“理论要首先考察那些吸引并困扰我们的经验,之后根据首要问题现象的相关性确定讨论的界限,理论家再发展出概念并辨别关联。他根据要解决的问题,能获得的资料,以及能够考虑到并把控的经验,综合成适合的条件详细阐发范畴与结构。这样,我们必须首先面向经验,并且经验决定了合适的理论结构、内涵以及操作。”[8](P6)伯林特将“经验”视作理论架构、范畴的核心依据,可以说是一种“经验”决定论。为了进一步将杜威的“经验”理论具体化,伯林特创立了为理论界所熟知的“参与美学”。“参与”在伯林特这里首先是一种艺术审美感知,它强调多维感官在传统艺术审美经验中的应用,并极力否定传统艺术的无利害静观,这同杜威认为的经验官能同外在世界具有连续性一脉相承。同时,“参与”的审美经验不仅局限于艺术,而且扩展到更为开放的、具有交叉性质的环境艺术甚至环境本身。伯林特认为:“由于相同特征以相似的方式在这些境域中发挥作用,在绘画和摄影中的参与感知在物理环境的感知中同样真实存在。当我们处理物理环境的审美感知时,人类对景观图画空间感知的感官交融方式同明显是一种动态艺术审美方式差别不大。”[6](P96)感官与境域的交融不仅在艺术中如此,在更大的环境之维也如此,“参与”在艺术与环境的境域转变中成为不变的核心枢纽。
三、审美境域展开的描述美学方法
正如上文所述,伯林特建构了一个以交互性经验整体为理论前提的境域理论,这一理论语境涵盖了传统艺术与现代环境思考。在环境美学的参与经验中,伯林特强调:“环境美学并不单单关注建筑和场所,它有关于在一个综合境域中一个人加入进来并成为参与者。”[2](P12)对于审美经验场域的还原必须从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整体而非独立参与者出发,这样,对于一体性经验的反思而非要素的独立分析就变得尤为重要。伯林特认为审美经验有着诸多整体性特征,例如动态感知、品质的、感官的、当下的、直觉的、非认知的。这些基于审美交互性的特征涵盖了从艺术到环境的开放审美境域,也影响了伯林特美学阐释的独特路径。
显然,“审美场”交互经验的还原要求放弃一种要素分析、对象静观式的理论模型,传统的理论言说很难直达这种经验一体性。同时,要在理论言说中展开动态感知、品质的、感官的、当下的、非认知的这些特征,传统学术语言显然无能为力。为此,伯林特提出了“描述美学”的核心方法,即“对艺术和审美经验的描述,它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叙述的,也可能是现象的,唤起的,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是启示的”[2](P26)。 “描述美学”从感知经验的描述着手,运用叙述或诗意的语言,从人与环境交融的关系性中展开言说,能够将动态、当下的感知经验呈现出来。相对而言,实质美学有着更为长久的历史,它以艺术总体的特征、经验以及意义作为探讨内容,并且擅长以哲学框架寻求艺术定位。同时,元美学搁置实质美学的宏观问题视野,转而寻求艺术的定义、概念的分析、艺术的分类等问题,其主要代表就是美国著名分析美学家门罗·比尔兹利。与上述两种被伯林特称之为“代理理论”不同,伯林特所提倡的“描述美学”既不侧重于哲学宏观归纳,也不侧重于概念分析,而是从审美本身出发,从经验事实中展开。可以说,“描述美学“是伯林特切入环境美学乃至当代新美学的核心言说方法和路径,是审美经验展开的呈现方式。
伯林特以名为《泛舟班塔姆河》的游记来作为自然环境经验的描述例证:“我慢慢地泛舟荡漾,穿过一座小桥,这时看见一株光秃秃的灰树桩,这由大树风化之后所剩的残骸活像一位守候在灰胡桃溪与班塔姆河交汇处的哨兵。此时,我处于拥有另外一种体验的时刻:身体蜷缩,膝盖紧紧贴着船身,手代替了腿来推动船前进。我还注意到,原先遮蔽天空的树丛不见了,明亮的天空显露出来,沿着这条三维自然之路前进的是与河床平行的树林。……顺流而行,突然一块钩住了许多漂浮物的水下浮木挡住了去路。独木舟只有小心地避开水中的枝条,借助水流的冲刷才能艰难地从狭缝中通过,就像漂浮物一样……公路上隐隐传来的声音与其说提醒我注意它的存在,还不如说让我意识到自己实际上离它有多遥远。眼前,一棵树伸展着宽大的枝条,几乎占满狭窄的河道。我急忙俯下身去,因为粗糙的树皮和破碎树枝的残余正迎面撞向我的眼睛。这儿可没什么水,稍不注意,坚硬的尖刺就会凿到或撕开粗心人的脑袋。每个环境都一样,其中审美和实用的考虑混杂在一起……猫鹊的鸣声,划桨声,浆板与船舷轻轻的碰撞声,灌木丛中鸟儿的拍翅声。近处有聒噪的乌鸦群,黑压压的一片,它们或飞,或蹲,或叫,一时间占领了整片天地。杆子同桨的在手感始终存在,它不是由冷冰冰的金属或塑料制成的坚固的现代体育用品,而是一种油漆过木头的温暖颗粒质感。有时它们被打湿,水的凉意刺激了我被太阳晒烫的皮肤,让我对杆子和桨的感受更加真切。河流逐渐变宽,像个大水塘,旁边还有山谷陪伴。树木、草地勾勒出的纹路和色调如此层出不穷,让这一小方时空变得无限生动。这是一次感官的沉浸,我深深地沉迷于感知与意义的当下性,无法与场景以及各要素相分离。”[2](P30-31)
在此经验中,动作与感觉统一于一身。人的感官异常敏锐,不仅通过看、听、触、嗅、味的五官同河流的大环境保持密切关联,而且感官感觉即是行动,中间不存在间隔。主人公看到河流中的浮木、河边的枝条、水草,听到各种鸟鸣,接触到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木桨,以及感受到身体与船体在水流中不断寻求平衡,这些身体的感官感受同他泛舟的过程结合在一起。此外,过往的记忆、现实的想象、理性的判断都统一于当下的人自身。因为在泛舟过程中,人的过往经验、对于河道状况的知识都融汇到统一经验之中,利害性的认识同审美态度在经验中变得密不可分。伯林特还多次运用“描述美学”方法进行经验解读,例如城市四意象的解读(马戏团、教堂、帆船、日落)、康涅狄格州的四种审美境域(春雨自驾行、诺福克盛夏的午后、秋日利奇菲尔德丛林漫步、冰湖曼舞)。在人文内涵的环境描述中,人的记忆、沉思、意义理解成为与感官感知同样重要的要素。事实上,这种经验性活生生的参与感在伯林特《艺术与参与》中对绘画、雕塑、建筑的传统艺术改造中就已经突出强调出来。境域整体的经验性描述并非环境独有,而是一种综合艺术与环境的审美解读方式。它揭示的是一种美学基础方法论意义上的根本变革。
其次,著为令。有时又称为定著为令或议著为令。是皇帝敕令上升为法律的第二个阶段。 沈家本先生曰:“凡新定之令必先具而后著之,必明书而附于旧令之内”[7] 按照沈家本先生的理解,汉代皇帝的敕令要想上升为法律,“必先具而后著之”,必须先通过立法批准程序,然后正式立法,上升为永久生效的法律,仅仅上升为永久生效的法律还不行。还必须用书面形式加以表达,也即著令。可见,汉代和今天一样,要想使皇帝的敕令上升为法律,不但要有立法的程序,而且要通过书面的方式加以表达,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沈家本先生只是概括地阐述了皇帝敕令上升为法律的程序。
然而,伯林特的质疑者必然会问:描述美学的规范性在哪里?它有理论意义吗?正如学者卡尔松所批评的那样,“描述美学”的笔法很容易让人认定其为一种主观幻想或毫无重点的意识投射。归根到底,无论它的表达形式,还是内在核心观点,都过为开放和零散,和真正的理论话语差别很大。
事实上,从伯林特的整个学术研究生涯来看,他早就为这样一种有偏见的驳难准备了思想武器,他为美学理论的建构设定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非认知的审美经验,属于美学理论建构最普遍的素材;第二步是由境域事实、经验事实、对象事实、评价事实、跨学科事实构成的审美事实,主要以描述为主,是对非认知审美经验进一步规范,其中境域事实最接近于原初的审美经验;第三步是建立于审美材料和事实基础之上的审美理论,是对审美事实的组织和解释,它的特点就是概念化和导向认知评价[8](P16)。三个层面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伯林特不反对理论建构,他反对的是凭空建立起来的或以其他代理理论为依据的理论模型。他认为任何事实、理论的描述和阐发都要紧密结合最基础的非认知审美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才具有价值评判、要素分析以及诸多理论模型的规范。所以,三个层面又是贯通到一起的。
小学语文教师要提高识字写字教学的效果,除了要依托教材,还要积极探索有效的指导方法,引导学生有效地识字、写字。
如果没有最基本的非认知审美经验的基石,任何理论言说都是无根的,这体现在伯林特同卡尔松及中国学者程相占关于规范性美学的争论上。卡尔松曾批评伯林特的“审美经验不能提供一个审美标准”“审美参与引起过分主观的结果”“立场难以实现严肃美的直觉”[11]等。事实上,这些判定隐含了卡尔松提出问题的重要形而上学前提,即“一个审美标准”、主客观区分、严肃审美和肤浅审美区分本身的依据。卡尔松延续了西方传统理性对于最终根据和标准的固定眼光,认为环境审美也需要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而且,审美活动要以主、客特征论进行研究,主观的审美态度和模式以对客观属性的符合程度为评判标准,这是以经验论美学为根基的伯林特所不能接受的,他反复强调“我们的差异在形而上学层面比美学更多”[12]。伯林特继承自杜威的“交互”认识论,不将任何静止的要素、实体视为最终解释源头,而是将包含诸要素的系统关系视为关键。所以伯林特承认参与式的非认知经验并不是审美的唯一标准,而是一个综合特征中起基石作用的必要部分。审美经验永远是向认知、文化、个体性特征敞开,而非封闭的内在理论循环。所以,伯林特的描述美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开放性的规范文本,其对于卡尔松的主客原则有所包容,却不限于这种机械论的切割和符合。程相占对伯林特的挑战也集中在他过于沉迷于经验一体性的论述:“正如‘环境公平’和‘政治生态’这样的术语所显示的那样,环境的边界是由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所明确界定的。我们在现实中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环境,都是必须添加定冠词‘这个’的‘环境’。”[13]认为伯林特对康德的“无利害”有意误读以达到对传统主客关系论的彻底否定,并在相反的方向指出康德美学可以为生态美学奠基。程相占的生态美学虽然赞赏伯林特的经验论美学,但归根到底是一种先知识后审美、先秩序后经验的规范性美学。伯林特针对程相占的回应,认为“生态美学更多的是从认知上而不是审美上,来促成对于环境的欣赏,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我不赞成将生态美学意义上的环境欣赏,等同于在理解环境情境中各要素之间的工作机制与相互关系之中,所得到一种智力上的满足”[14]。虽然伯林特也承认审美经验与生态视野并不相悖,但孰先孰后、以谁为讨论中心却构成两者的主要差异。
由此可知,描述美学紧紧抓住了美学理论建构的第一层,即基础性的感知经验,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包容任何理论的美学大厦。它不从根本上反对环境美学的科学认知理论和生态美学等差异化论述,而是将它们置于自己理论大厦的事实部分、认知部分,言明最基础的经验感知要贯通于诸部分。所以,描述美学并没有一种符合论的、客观的、统一标准的规范性,但它又有着面向经验事实的最为开放的规范性,它将艺术对象、感知者、艺术家、表演者 、生物学要素、心理学要素、材料与技术要素、社会与文化要素集结于审美经验发生的境域,将实验心理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梅洛·庞蒂的肉身化等理论进行经验化改造,即破除其理论的纯粹性,连接起它们同经验性参与的原初关系。这种具有开放性的理论标准,建立于共识性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
四、结语
伯林特的环境美学理论引介入中国已有多年,其理论在中国不乏拥趸。从中国环境美学的发起人陈望衡到生态美学的倡导者曾繁仁乃至生态实在论的研究者程相占,都对伯林特的“参与美学”持一种较亲和的态度。这一方面源自于伯林特的经验论同中国传统天人关系的一体性有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同当今学界杜威美学的重新回归和受追捧不无关系。中国环境美学自上世纪末开始起步,受很多西方环境思想的影响,现在渐渐可以在很多问题上同西方展开建设性对话。但是这种对话要形成具有理论深度的碰撞,则不能缺少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深入了解。本文从伯林特美学理论建构的整体视角,回溯其隐含的杜威哲学、美学逻辑,并为其理论发展的不同站点觅得隐含的连续性,希望这一研究可以有助于环境美学中西对话的进一步展开。
参 考 文 献
[1]史建成.艾伦·卡尔松“肯定美学”之演变及其理论倾向[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2]Arnold Berleant. 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1992.
[3]Arnold Berleant.Aesthetics Beyond the Art-New and Recent Essays[M]. Farnham: Ashgate, 2012.
[4]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Arnold Berleant.Art and Engagement[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7]阿诺德·伯林特.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M].刘悦笛,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8]Arnold Berleant.The Aesthetic Field:A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M].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1970.
[9]Elmer H Duncan.Review Work: The Aesthetic Field: A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by Arnold Berleant[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6, No.3(Jul,1972).
[10]John Dewey,Arthur F. Bentley. Knowing and the Known[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0.
[11]Allen Carlson. Critical Notice: 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2006,(4).
[12]Arnold Berleant.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 Reconsidered: Reply to Carlson[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2007,(3).
[13]程相占.从生态美学角度反思伯林特对康德美学的批判[J].文艺争鸣,2019,(3).
[14]阿诺德·伯林特.就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之关系答程相占教授[J].宋艳霞,译.文艺争鸣,2019,(7).
中图分类号: B8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 2019) 06-0005-08
收稿日期: 2019-10-11
作者简介: 史建成(1990-),男,山东莒南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美学、中西比较美学。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艾伦·卡尔松的‘审美鉴赏’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17WQNCX133);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扶持项目“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QNFC41)。
(责任编辑 乔学杰)
标签:一个经验论文; 参与美学论文; 审美场论文; 审美交互论文;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