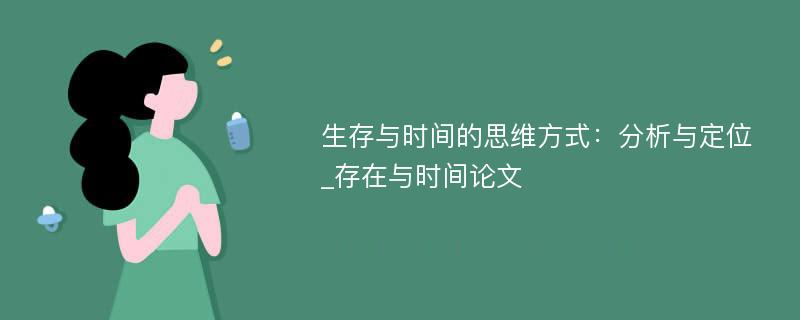
《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分析与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式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的重要作品,它奠定了海氏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对它的理解与分析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开展。本文以对《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的分析,作为读解《存在与时间》的一种途径:阐释其运思特色,并为其运思方式定位。
一、运思方式的发生——现象学存在论
哲学的创新常以思想方式的突破为契机。《存在与时间》的产生,便是如此。早在1907年,海德格尔就接触到布伦塔诺的《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触发了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说“存在”有多种含义,那么什么是存在(Sein)的根本含义呢?在接触现象学方法之前,海氏虽然对哲学史特别是中古哲学十分详熟,但缺乏明辨存在的有效方式。对此,海氏也承认最初的探索是笨拙的。(注:[德]海德格尔:《我进入现象学之路》,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80页。)后来,经过多年的蕴酿、思考,特别是接受了胡塞尔首创的现象学方法的思维训练,才使他看到了探索存在问题的希望。海氏在一篇回忆其思想发展的文章中表白:“通过现象学态度的昭示,我被带上了探索存在问题的道路。”(注:[德]海德格尔:《我进入现象学之路》,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86页。)正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和改造,促使海氏以现象学思考方式探索存在问题,才有《存在与时间》的问世。
《存在与时间》第七节专门对“探索工作的现象学方法”作了描述。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的词源分析,指出就本来含义而言,“现象学是说让人从自身显现自身者那里,以一种自身显现自身的方式来看它。”(注:[德]海德格尔著、J·麦克考利和E·罗宾逊英译:《存在与时间》,伦敦巴塞尔布莱克威尔1962年版,第58页。)这表明就现象学的形式含义,海德格尔接受了胡塞尔“描述现象学”所强调的无立场、无前置的直面事情本身来显示事情的观点。不过,胡塞尔的全部现象学到海氏那里,被归结为“面向事情本身”,并作为现象学方法的根本原则,抛弃了胡塞尔把现象学作为各学科奠基的绝对科学的企图。因为,在海氏看来,“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的概念。它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实事性的什么,而描述它的如何。”(注:[德]海德格尔著、J ·麦克考利和E·罗宾逊英译:《存在与时间》, 伦敦巴塞尔布莱克威尔1962年版,第50页。)另外,由于存在之存在超越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那种对象性认知方式,它无法如存在者一般摆出来供人认知。而传统认知方式说“存在”是自明的,是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表明了传统哲学对存在无法窥见真意,只是以遗忘存在的方式来说“存在”。存在的超越性,表明对存在的揭示,以现象学方式的“自身显现自身”才有可能。由此,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以“自身显现自身”为旨归的“事情”只能是存在。同时,存在又总是存在者的存在,通过此在(Dasein)来显示存在,这是海德格尔现象学方式的具体思路。这里,海德格尔现象学具有比胡塞尔更为彻底的性质。胡塞尔的现象学把现象学局限在纯意识范围内,把构建意向对象的意向活动的先验直观主体作为现象学最后根据,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先验主体”本身还是在传统认知方式“主体——意识”范围内寻求“科学性”,因此,还不够彻底。他试图以“在世”存在的不加抽象的“此在”本源处显现存在之意义。
“此在”并不表示这个存在者的什么,如“桌子”、“椅子”、“树”甚至“人”所表示的那样,以其范畴来概括存在者的本质。“此在”并不表示现存存在者的性质,它只是对在“此(Da)”在(Sein)着的存在者存在方式的描述。它不同于其他存在者之处,就在于它为它的存在本身而存在。即此在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着,它都以领会着存在的方式存在。这种无论以何种方式总与其存在相关联的存在称为“生存(Existenz)”。
对生存的初步界定可知,此在作为“去存在”的可能性,不可能先选择一种“存在本质”,再根据此种“本质”来造就自己,使此在完全“符合”其“本质”。此在并不是一无所是,然后获得某种本质性的存在特性,此在总已经在“此”,它具有从某种存在者方面来领会自己存在的倾向。同时,当此在被“抛入”世界时,承接了种种历史传统。结果,此在虽然在存在者状态领会着自身的存在,但现象学所要探索的存在,“它首先和通常并不显现,与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相对照,它隐藏不露。”(注:[德]海德格尔著、J·麦克考利和E·罗宾逊英译:《存在与时间》,伦敦巴塞尔布莱克威尔1962年版,第59页。)因而现象学的实际展示过程就是此在之生存去除遮蔽,显示存在的阐释过程,此在的现象学具体展示为阐释学。
现象学阐释的可能性同样导源于此在的生存特性。虽然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不具有本源地领会其存在的优先性,但无论以何种方式领会着,又总是对存在的领会。正是这种领会构成了阐释的可能性。存在通常“隐藏不露”,“但同时它在首先和通常显露着的东西中,它从实质上构成了显现者的意义和根据”,(注:[德]海德格尔著、J ·麦克考利和E·罗宾逊英译:《存在与时间》,伦敦巴塞尔布莱克威尔1962 年版,第59页。)即存在在存在论上隐藏不露不过表明了存在以遮蔽的方式“敞开”着自身。因而,如果没有此在已经处身于对存在的领会敞开性中,不可能有阐释。
任何阐释都已经包含着对有待阐释的东西的领会,阐释不过把领会所筹划的可能性揭示出来。这种揭示要使存在者状态上领会在存在论上清晰可见,要使领会中所包含着的此在存在的意义清晰可见。从方法上说,就是使阐释“面向事情本身”,使阐释通达此在生存的本源处。该如何通达生存之本源呢?海德格尔明确指出“现身情态”对“生存论分析工作具有根本的方法论含义”。(注:[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1页。 )具体说来,在所有一切认识、理解、活动中都融合着情绪,都是情绪性的存在方式。这当然不是指“涂”上一层情绪,而是指所有一切领会都是情绪性的领会,这种情绪性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称为“现身情态(Befindeichkeit)”。它最明白切身地、最为当下地开展着此在之“此”。“现身情态”表明其在认知方式的那种知之前已经以情绪“现身”着即对他的世界更为本源地“知”着。它从存在论上组建着此在世界的敞开状态。因而现象学阐释成为本源性现象状态的揭示。为此,“现象学的阐释必须把源始开展活动之可能性给予此在本身,可以说必须让此在自己解释自己。在这种开展活动中,现象学阐释只是随同行进,以便从生存论上把展开的东西的现象内容上升为概念。”(注:[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1页。)在此,现象学阐释为自己提供了一种阐释的深度标准。 这种标准不是外在的某种“根据”或“本质”,而是在阐释的过程中,让本源性的现身状态显现为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本源性在“此”存在,从而昭示了阐释是现象学的自身显现自身的过程。
这样,现象学方法成为存在论运思方式层面上的处理方式,展示为以“此在”为出发点,通过对“此在”生存的现象学阐释,开启存在之意义。(注:拙文:《海德格尔存在论建构方式及其特点》,《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9期,第113~115页。)
二、运思方式的旨趣——本源性之境
如果依照现象学所要求的“面向事情本身”的原则,就是开启此在在“此”存在的本源性之境,那么,《存在与时间》中的阐释自有其现象学意味的显示特性。
从现象学阐释的结果看,阅读《存在与时间》的读者不难发现在其他传统哲学著作中罕见的现象:该著作第二篇大多数章节都标有参阅第一篇第×章第×节或第×页的注释。据笔者统计,海氏仅仅要求读者前后篇参阅的原注多达80余处。这种不厌其烦的说明导出了现象学阐释过程所开启的是本源性境域展示:由于存在之存在的非对象性规定,决定了存在只能显现,而不能作为认识对象来认知和证明。这样,其开启的不是以概念所包容的某种本质,如黑格尔哲学以范畴的更替所包含的辩证的否定来完成思想的运作。因而出现了前后提示的特殊表达方式,让读者领会其相关境域。“现象学只能引导听众去接近事实,以便尔后在关键时刻最后指出:‘看,它就在这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别人什么也不能看到,由此就引起无法调解的争论,而任何想进一步给以说明的愿望也是毫无用处的,就如同为一个盲人‘解释’诸种颜色的努力一样。”(注:转引自[德]施太格缪勒著、王炳文等译:《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8页。 )舍勒对现象学的说明可作为海氏运思方式所展示境域性特征的恰当注释。阐释引导读者去接近事实,其阐释营造了某种相关境域,而术语只是相关境域的标记和提示,其目的是为了显示出某种境域。以“时间性(Zeitlichkeif)”为例。它在理解上的难度,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传统认识论的线性时间概念的消极影响。按传统认识论范畴去理解时间性,它只能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事物产生、发展、灭亡过程的概括。那么时间性表述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的现象”( 注:[德]海德格尔著、J·麦克考利和E·罗宾逊英译:《存在与时间》,伦敦巴塞尔布莱克威尔1962 年版,第374页。),就成为无法理解的逻辑混乱。相反, 只有把“时间性”理解为开启此在本源性存在境域的标记,在那里“向死亡存在”的存在论论证逼使读者领会死亡的边缘性境域昭示给我们,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意境,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畏”这一本真性现身情态所开启的境域,从而才能领悟“将来”、“当前”与“曾在”以绽出(Ekstase )的统一方式,开启着此在本源性生存之境。
再从现象学阐释的实际运作过程看,“在世”作为此在生存的机制,是在彼此牵引和通达的展开过程中,为我们开启了此在在“此”的原生态生存机制。“在世”的某一种环节的说明都牵出其他各环节。如,世界作为此在生存论上的特定领会方式,当世界之为世界开启着,就意味着世内存在者来照面,而照面意味着此在在烦忙,而烦忙总关涉着他人。因而,烦忙总是在烦神,这表明此在对他人与世内存在者已有所领会,从而表明此在是以现身领会的方式沉沦于世。由“在世”牵出此在之存在为“烦(Sorge)”。“烦”作为此在之生存论机制, (注:[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9页。)让此在生存的可能性从存在论上展开, 最后随着“先行决心”的开启,“时间性”这一此在生存意义得到揭示。同时这一过程就是“烦”之为“烦”,作为其生存论机制显示自身的过程。在时间性揭示之前,烦作为“领会着的筹划”、“现身的被抛”和“沉沦在世”的统一缺乏内在的融合性。从形式上看,领会奠基于将来,而现身基于曾在,沉沦则寓于当前,烦在形式上不统一,说明“烦”的分析还没有通达此在全过程。事实上,随着表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现象”的时间性开启,“烦”作为此在的存在随着时间性的揭示,从根本上为自身找到了“根据”。因为,作为方法论上有指导作用的现身情态中最为个性化的现身——“畏(Angst)”, 随着时间性的开启,使畏作为本源性生存现象得到了“验证”,从而在彼此观照、相互通达中显示本源性之境。
此在的现象学阐释总已经对某种领会的阐释,这种阐释是在一定情境中进行,发问则承担着显示这种情境的引导作用。海德格尔提出,“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寻求的东西而来的事先引导。”(注:[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即任何发问都包含了对所问东西的某种领会。毫无所知就无从问起,明白无疑也无所设问。以存在论眼光看,发问本身就是发问者的此在在“此”生存领会方式、程度的显示,从而开启其探索相关问题的情境,因此发问具有引导阐释的独特功能。具体说来发问所牵出的问题情境为应答造就了可能的方向。应答成为对发问的回应。这种回应,一方面是对问题情境挑明,另一方面以其解释过程,孕育着下一个新问题情境,甚至应答本身又是下一个问题情境的开始。我们不难发现《存在与时间》许多章节都含有表示发问的问句,这类问句成为对相关阐释学情境的说明和进一步探索的引导。如第二篇第一章是对“死亡”的存在论阐释。在这一章节中,首先以一系列发问对那种认为由于存在者状态上此在不能经历死亡,以通达此在的全过程,而否认完整把捉此在生存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以发问的方式为“死亡”的生存论探索导向,从而揭示“死不是一个事件”。又以死亡在何种意义上是结束的发问,得出死是“向死亡存在”。随后以此在的生存机制处描述出死亡的存在论结构。最后以一系列发问,导向对此在“向死亡存在”的本真存在论境域的开启。(注:[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0页。 )如果《存在与时间》中的章节标出了存在论阐释的实际内涵,那么其发问与应答成为担当其境域的开启、保持与转换的“阿里阿得涅之线”。
对《存在与时间》的运思分析,无法回避对该著作未完成状态作出解释。从《存在与时间》探索过程看,当海氏以“先行决心”揭示出时间性这一境域时,此在之生存论阐述达到高潮。它开启了本源性的生存之境。当“时间性”已表述为源始的本真的境域,海氏认为“时间性”需要在此在生存的各环节上验证,需要在时间性中为日常生活与历史定位。《存在与时间》最后三章做了这个工作,其中也不乏精彩之处。但当时间性被作为各生存状态的“标准”处境去说明各生存状态时,这种“验证”几乎演变为应用,从而渐渐失去了现象学阐释所显示出来的观照、牵引、通达本源的运思魅力。这恰恰偏离了现象学运思自身显现自身的原则。后来海氏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点出了《存在与时间》未刊出第三篇的原因:“成为问题的一篇扣下未发表,因为在此一倒转的充分的说中的思并不中用,而乞灵于形而上学的语言也无济于事”。(注:[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2页。 )由此看来,有充分的时间与能力来完成《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却让它以未完成的形式出现,这只能说明他领悟到后来的阐释慢慢丧失其本源性的意味。
可见,《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以发问与应答为引导,以相互牵引、彼此观照的运作过程,通达本源性之境,从而显现其运思方式为“面向事情本身”这一现象学方法的具体尝试。
三、运思过程的定位——开路之思
如果海德格尔探索存在问题的整个思想过程没有纳入运思方式的分析视野,那么我们就运思方式所作的说明还是不充分的,而确定海氏整个思想过程与《存在与时间》运思方式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海氏整个思想过程中为其运思方式定位。
为《存在与时间》运思方式定位,离不开对海氏思想过程的整体理解。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探索存在问题的思想过程就其具体的内涵来看,大致说来,经历了早期的以“此在”现象学方式求存在之意义;中期的追溯希腊思想之源,通达真理之无蔽,阐发荷尔德林诗之内涵和晚期的归于“大道(Ereignis)”之“言说(Sage)”。这种探索的前后期变化也被人描述为海氏思想的“转向”。(注:参见拙文:《国内海德格尔思想转向问题研究述介》,《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第23~ 24页。)对于探索过程的这种前后变化(或称转向),海氏作了明确的说明。针对《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思想》一书的作者把他的思想过程区分为“海德格尔Ⅰ”和“海德格尔Ⅱ”,海氏指出这种区分仅仅在以下条件下才能成立:“只有从在海德格尔Ⅰ那里思出的东西出发,才能最切近地通达在海德格尔Ⅱ那里有待思的东西。但海德格尔Ⅰ又只有包含在海德格尔Ⅱ中,才能成为可能。”(注:[德]海德格尔:《给理查森的信》,《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78页。)在此,海氏表明了他整个思想过程的内在相通性。在何种意义上相通呢?海氏作了解释:“对于转向的思考在我的思想中是一个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发生却不是基于立场的改变,更不是以《存在与时间》中问题的提法作代价。”(注:[德]海德格尔:《给理查森的信》,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 第1276页。)他还说:“转向出现在实事本身之中,这种转向既不是我编造出来的,也不是只牵涉到我的思想。”(注:[德]海德格尔:《给理查森的信》,《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76页。)在此,海氏认为转变并不是改变了《存在与时间》所提出的存在问题的主题。变化只是在实事本身发生的改变,是存在问题的探索本身所发生的内在变化。
具体而论,海德格尔整个探索过程,是在传统存在论及其表达方式的背景下开展的。他试图突破传统存在论的对象化思考方式,就面临着探索上的难题,“一方面,我们要从对象的表象方式中摆脱出来,而同时却必须使用那些被理解为对象而且只有在对象领域我们才能熟知的语言。”(注:[德]比梅尔著、刘鑫等译:《海德格尔》,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4页。)因而, 海氏不可能一开始用一种完全创新的语言来表述存在之本源,当然,也没有现存的某种存在之境摆在那里,等待去描述。他只能在与传统存在论及其表述方式的对话、澄清的过程中,不断开启存在本源性之境。海氏在一次与日本学人的谈话中,说到“存在”这个名称属于形而上学语言的遗产时,日本学人问海德格尔为什么不用不沾形而上学的新词来避免混乱,海氏说:“一个人如何能够命名他还在寻找的东西呢?寻找倒是以命名着的词语的召唤为基础的。”(注:[德]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024页。)这样,海氏的整个思想过程的每一具体探索就成为走向本源性思的一个路标,每一个路标都是尝试性开启存在之境的标记,同时又昭示了新的境域的发生。“存在之意义”、“存在之真理”乃至最后的“大道”成为探索存在的路标。每一个在前的名称大致上看作某一在后标记的暂先展示。每一种标记都是一种过渡。海氏晚年在其早期的著作边沿上几乎把他曾用过的一切概念都换上“大道”,这倒不是说前面的探索无效,而是说后者更为本源地通达存在之境,通过后者反过来又发现前者探索的意义所在。不难看出,存在问题的主题不是抽象的,而海氏也一直在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话中,尝试着更为本源地思考存在问题。如果我们不把“现象学”理解为固定的模式,不把形式化“回溯前进”看作现象学的模式,不把现象学看作技巧性的方法,而坚持把现象学理解为“面向事情本身”,即让事情自身显现自身,理解为“不时地自我改变并因此而持存着的思的可能性,即能够符合有待思的东西的召唤”,(注:[德]海德格尔:《我进入现象学之路》,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88页。)那么,整个探索过程“更为忠笃地坚持恪守着现象学的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梅尔在他写的思想传记《海德格尔》中明确指出:“后期海德格尔并不比前期海德格尔更少现象学意味;只是这一时期他的研究范围已超出我们通常理解的现象学。”(注:[德]比梅尔著、刘鑫等译:《海德格尔》,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2页。)
至于海德格尔在其思想探索的中、后期很少提现象学方法,事出有因。随着海氏思考的不断深入,正如他意识到早期“存在”、“意义”等词受到了传统形而上学语言的“污染”,“方法”一词也让人容易理解为外在技巧性的东西。海德格尔对之早有清醒的认识:“原始创造的现象学概念与命题,一旦作为传达出来的命题,无不可能蜕化,这种命题在空洞的领悟中,人云亦云,丧失其地基的稳固性,变为飘浮无据的论点。原始的‘掌握’而变得不可‘掌握’。”(注:[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5~46页。)但他中、后期很少再提现象学方法。这不是说他放弃了现象学含义上的思考,而是说海氏已有更恰当的语词如“大道之道说”、“思”等表达现象学方法的根本内容。如“大道的道说”,“意味着显现,让显现,让看和听”。(注:[德]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32页。)这与海氏对现象学的根本原则的描述是相通的。50年代日本学人问海德格尔为什么在后期著作中没有出现“现象学”和“解释学”这样一些用语时,海氏回答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否定现象学意义,而是为了让我的思想保持在无名之中”。(注:[德]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032页。)美国现象学研究专家斯皮格柏格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说:“这(指海氏上面的话——引者注)也是他(海德格尔——引者注)于1953年给予我的口头解释”,(注:[美]施皮格伯格著、王炳文等译《现象学运动》,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77页注[36]。)在海氏看来, 一切形式化的“有名”易遭致早已被传统“文法”、“逻辑”霸占了的语言解释的误导。由此看来,海氏避开了“现象学方法”的表述形式又坚持了现象学的根本原则。
正是由于海德格尔遵循了现象学基本原则,不断尝试着开启本源性的思,从而使海氏探索成为“路”。正如他所说:“我离开前期一个观点,但并不是为了以另一个观点取而代之,而是因为即使从前的立脚点,也只是一条道路上的一个逗留,思想中特有的都是道路。”(注:[德]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015~1016页。)海氏晚年在反思其思想时,在扉言上写道:“道路而非著作。”海氏的某些重要作品用与“路”相关的词来命名。如《林中路》(1950年),《走向语言之途》(1954年),《路标》(1967年)等。这显然不是偶然之举。“路性”可以说是其探索存在之路的内在特色。
当我们对《存在与时间》运思方式作了尝试性的分析,当我们对海德格尔思想之路作了尝试性的描述,那么《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在海氏思想中位置大致可以显示。
《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是以此在的现象学阐释学去开启存在论的本源性之境。《存在与时间》不仅由于在海氏思想过程时间上的暂先性,而且主要是以其现象学的探索方式,使它成为海氏思想之路上的第一个典型路标,它表明《存在与时间》的思考方式是开路之思。一方面,“在世”的分析、“烦”的建构、“时间性”的开启等,涌动着思想的激情,这些具有原创性的以现象学运思方式的展示,标志着海氏走上了探索存在之路。虽然以后的探索表明了《存在与时间》的“存在”、“意义”等表述带有传统形而上学的痕迹,但《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作为海氏走上探索存在之路的开创阶段,具有无可替代的思想意义。我们无法绕过《存在与时间》去理解海氏的思想过程,我们也无法不通过读解《存在与时间》去领会现象学方法。而中、后期的探索只有从《存在与时间》的本源性境域处出发才能理解。如,当我们接触海氏后期的大道所显示的“四重整体(大地、天空、诸神、终有一死者)”中的“终有一死者(die Sterblichen)”, 显然是以《存在与时间》中所开启的此在的“时间性”存在意义为观照背景。另一方面,海氏的《存在与时间》作为探索存在之路第一个典型路标,以现象学阐释学方式昭示出海氏思想过程的开放性和非绝对性。《存在与时间》标出了“面向事情本身”,展示了倾听存在召唤的“一条路的可能性”,以至于我宁愿认为海氏以《存在与时间》未完成作品结尾处一系列发问显示了思想之路的开放性。因此,只有把海氏整个探索过程看作《存在与时间》现象学运思方式所开启的“让事情自身显现自身”的本源性之路,我们才能理解海氏的论断:“从各方面说来,人们都认为《存在与时间》中的尝试已经陷入死胡同了,我们就让这些人去保持这种意见吧。在《存在与时间》这部书的探讨中力图跨出几步的那个思,直到今天还没有超出《存在与时间》的范围”。(注:[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