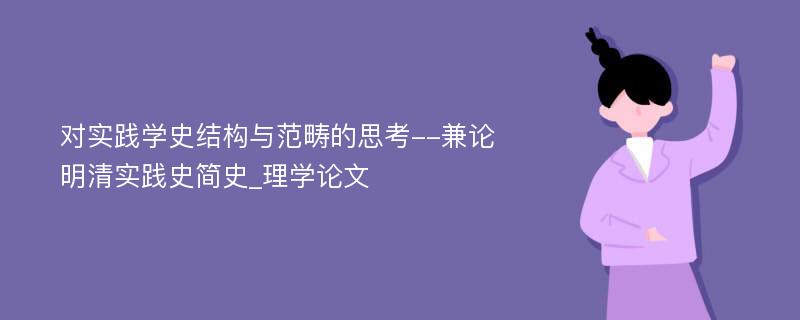
沉思实学史的结构与范畴——评《明清实学简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简史论文,明清论文,范畴论文,沉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明清实学简史》系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之简编本。《简史》较之原本更加言简意明,便于阅读。拜读之后,启发良多,受益匪浅,愿谈几点体会,以与同道切磋。
“实学”一词虽然远在明清时代的著名学者著述中经常出现,但是把它作为一种专门的思潮来研究还是近十年来之事。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的出版,即是我国明清实学思潮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最新成果。
“实学”作为明清时期的一大学术思潮,不大引人注意,所以也无明确地界定。其实,“实学”不过是对明清时期主要学术思潮的概括,也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主要学术思潮本质特征的描述。中国学术,在先秦时期有百家之学(或称子学),在汉代有经学(儒学经学化),在魏晋时期有玄学(哲学上的本末、有无之争),在南北朝至隋唐有佛学(研究佛性与人生之解脱),在宋明时期有理学(研究心性、道德,天理与人欲之辨),明中叶以后至清代实学思潮凸显,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将致思方向转为利用厚生、经世致用,使中国学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实学”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致思方向,我认为从致思方向来看实学,它更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里涉及对宋明理学的评价问题。宋明理学,涵容了佛、道,把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道德形上学发展到了高峰,把中国的道德理性进一步逻辑化,这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助长了思辨“天理”与“人欲”的空疏学风,如朱熹所云:“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三)又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同上)这不仅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而且把天理神秘化。另外一些思想家对待“天理”与“人欲”则改变了致思方向,把“天理”与“人欲”统一起来,加以实体化。如王夫之说:“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同上书,卷三),“私欲之中,天理所寓。”(同上书,卷二十六)过去,我们往往用“唯心主义”来批判理学,用“唯物主义”赞扬对理学的批判。今天看来,这种方法也未尽完善。这些年来把“实学”作为一种致思方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去批判空疏的宋明理学,甚得新义,这样更符合明清时期利用厚生、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大趋势,更富时代意义。这是明清实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从学术思潮史的划分来看,过去治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者,大凡都把宋明至清末这一时期看作理学时期。一般而言,这样划分当然也有道理。但是,从学术思想的兴衰及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主要思潮来看,明代中期理学走向衰颓,心学、禅学代起,把人们的致思方向进一步引向凌空驾虚之中。在这样文化氛围中,一批务实的思想家,如罗钦顺等相继起来用“气一元论”批判分割理与气的宋明理学,王廷相则明确提倡“惟实学可以经世”的主张。本来笃信王学的黄绾,到晚年由怀疑而转向批判王学,提倡实学。他自己回顾说:昔年初学王学,“始未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信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哉!”(《明道编》卷一)朱元璋的九世孙、郑王世子朱载堉也对当时流行的空疏学风、理学末流感到厌烦,明确提倡“惟求实理,不事文饰”(《进律书奏疏》)、“考究此理,勿事空言”(《律吕精义序》)的实学精神,对谈空说玄的学风提出了公开挑战。著名思想家吕坤更一针见血地揭露宋明理学家反复讨论无极、太极、理气、性命并非“今日急务”,他讽刺说:“假若了悟性命,洞达天人,也只于性理书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语,讲学衙门中多了一宗卷案。后世穷理之人信彼驳此,服此辟彼,百世后汗牛充栋,都是说这桩话,不知于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见在得济否?(《谈道》,《呻吟语》卷一)
由此可见,“实学”已经成为明清时代与“理学”、“心学”抗衡的重要学术思潮。而它的凸显又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的转向。实学在当时扭转社会风气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有:第一,发展了“经世致用”思想,认为一切言谈、学说,都应当有益于国计民生。明代后期的学者焦竑在廷试策对中提出“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治之实政,然后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齐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实心,然后其本立而有以妙转移天下之机。”(《澹园集·廷试策一道》)明清之际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孙奇逢,也极力主张“学在躬行,而不在口语”,把治学与经世结合起来。他在《四书近指》中指出:“四书”的精神是“治国平天下”,具体内容是“修己治人,亲师取友,理财折狱,用贤远奸,郊天事神,明理适用。”他批评那些“平居谈身心性命”者,一遇事便束手,“此腐儒曲士之流耳,实足为理学之诟厉也。”(《中州人物考·分类·理学》)
第二,发扬了批判精神、反对义袭古法。明末清初开一代风气的思想家傅山主张开拓创新,发扬批判精神。他批评那些以“明王道”而自居的腐儒们时说:“明王道,辟异端,是道学家门面,却自己只作得义袭工夫。”(《霜红龛集》卷三十六)他在批评空言心性的理学时说:“理不足以胜理,无理胜理;故理不足以平天下,而无理始足以平天下。……读者闻是言也,噪之曰:‘市井贱夫,无理者也,足以治天下耶?’曰:‘市井贱夫最有理者也,何得无理之!’”(《杂著录·圣人为恶篇》)这里是批评那些空言心性的理学家最不懂平治天下,而那些被认为是“无理”之人的“市井贱夫”,最懂如何治天下,因而是“最有理者也。”明末清初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一针见血的批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第三,明清实学的务实精神对于发扬科学求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明末东林学派创建者之一高攀龙,对于王学末流的儒学禅化倾向特别反感,批评他们的谈空说玄,提倡治学实用,做“有用之学”。他系统地批评了王阳明对“致知格物”不着边际、不务实物的理论,以比较科学求是的态度解释了“格物”问题。他指出“阳明格物”是诚意正心事矣,非格物也。格物应当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认为世界上的一草一木、鸟飞鱼跃,皆自有理,格其物理,便是格物而达到致知目的。高攀龙的这种实学思想,把“格物”引向了对客观万物的探讨,从而培养了“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是明清之际科学技术发达、科学家接踵而出(如朱载堉、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的思想文化氛围。例如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就是在“医者贵在格物”的实学思想指导下,一生奔波于山野考察药物,格草木虫鱼之理,写出一部世界性科学著作《本草纲目》,成为中国古代医药学的集大成之著。李时珍自己总结说: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本草纲目·凡例》)这便是对“格物”的实学性解释。很显然,这比那种把“格物致知”理解为“诚意、正心”、“致良知”的道德心性之学,更富于科学的求实精神。
总之,《明清实学思潮史》及《明清实学简史》,是一部有很高学术水平、有鲜明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开拓性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关于“实学”研究的空白,对于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对于中西古今文化的沟通,对于发扬“务实”的学风,都会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作为一部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总会给读者开拓出广阔的思考空间,同时也会留下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作为学术同行的读者从学术建设与发展的意义上来看,提出下面两个问题与作者及广大同仁商榷。第一,本书作为初创,呈现给读者的仅是以人(学者)为线索的“纪传体”的一篇一篇文章的著述,缺少一个内在的有系统的“实学”理论结构体系和理论框架。欲使“实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体系或文化形态,必须继续努力构架、创造“实学”的理论结构体系;第二,缺乏一个作为独立学术体系的特殊的范畴体系。例如,经学、理学、玄学等,都有自己特殊的范畴和范畴体系,否则就很难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实学”也应当有自己独特的范畴和范畴体系,然而本书没有呈现给读者。当然,形成范畴体系有一定难度,需要对“实学”进行本体论的形而上研究和对“实学”的认知的理论研究。这两者恰好是本书的薄弱环节,这也就限制了对于“实学”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性探讨,影响对“实学”的理论性构筑。上面所言“结构体系”、“范畴体系”实际就是“实学”的理论体系。它所包括的内容应该是:实学思潮的形成,实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实学的概念定位与文化内涵,实学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演进,实学思潮的理论化与范畴规定等等。提出这些问题是轻而易举的,做出并回答这些问题却是极其艰难的,需要深沉的思考、需要对历史文献的钩沉、更需要心智的反省与创造。我认为这是进一步开展“实学”研究首当沉思的问题。期望本书作者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贡献出关于实学的结构体系与范畴体系,那时的“实学思潮史”将不再是由单篇文章构成的合集,而是一部有自己特殊范畴和内在结构的学术史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