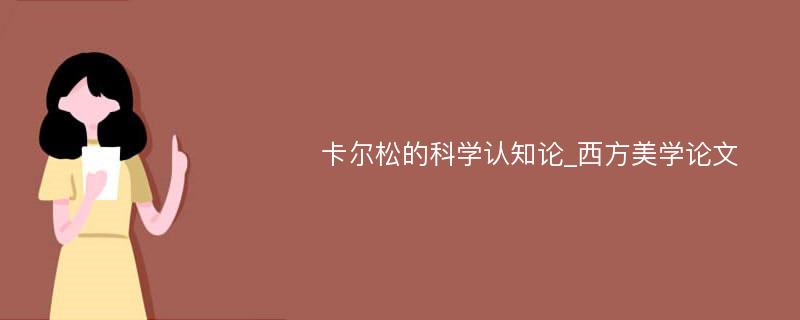
艾伦#183;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认知论文,艾伦论文,主义理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的自然美学理论在当代西方美学中独树一帜。这一理论因强调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重要作用而被同行称之为“科学认知主义”(scientific cognitivism)。认真分析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对当代自然、环境美学的基础理论建构很有参考价值。本文就此方面略作介绍与评述。
一、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功能
美学自创立以来,从鲍姆嘉通、康德、席勒、黑格尔一路下来,都着意强调人类审美活动的感性特征,强调感知、想象、情感等感性心理因素对人类审美活动的重要作用,并因而使审美成为一种与以科学、哲学为代表的人类理性认知活动显然有区别的特殊精神活动,感性成了我们对审美的最基本界定,成为审美的别名。以感性标志人类审美活动的精神个性,已然成为我们的共识,是我们审美阐释的立足点。
科学知识是什么?属于与包括自然审美在内的整个人类审美活动在精神个性上截然相反的科学活动。认知是什么?属于与审美所赖以生存的感性迥然不同的理性心理能力。在以感性为基本精神的人类审美活动中,奢谈科学知识与理性认知,有什么合法性?
正是这样的疑问,使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个性卓然,因为它似乎与美学自创立以来的历史,与我们对人类审美活动的基本认识公然相左。但是,卡尔松本人对此似乎并无明确意识。他提出这套理论,自有其特殊的当代西方美学背景。
20世纪以来,西方美学一直以艺术为中心,艺术成为美学家审美对象研究最重要的,甚至惟一的途径,以至于许多人将美学理解为“艺术哲学”。在此传统下,有的美学家持这样的见解:在艺术欣赏中,我们可以形成客观的审美判断,但是,对自然欣赏,我们的审美判断只能是主观的,至少也是相对主义的。卡尔松对此不能苟同,因为如果承认了这一点,自然审美的地位、价值,以及自然审美研究的可能性、必要性,都将受到致命影响。因此,他专门论证人类自然审美的客观性问题,认为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一样,同样可以达到客观性①。
客观性问题为自然欣赏和自然美学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那么,我们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怎么才能实现这种客观性呢?卡尔松找到了很明确的答案——科学知识。
乍看起来,卡尔松的观点似乎有点突兀:怎么会在审美这种以感性为特征的精神活动中大谈科学知识这种本属于人类理性科学研究的东西呢?但请注意,卡尔松的切入点其实非常实际,他设置了自然审美欣赏这一现实情境,并且有意识地与艺术欣赏进行对比:
这种知识,本质上说,是日常知识/科学,在自然欣赏中,对我来说,似乎是惟一可以起作用的可靠选项,就像在艺术欣赏中,有关艺术类型、艺术传统之类的知识所起的作用那样。②
现在的问题被转换过来:它不再从我们对审美的精神感性这一总体预设开始,而从自然审美欣赏,并且是与艺术欣赏相比较的形而下情境开始。卡尔松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在艺术欣赏中,有关特定欣赏对象——艺术品的艺术史、艺术传统、艺术风格类型之类的知识是重要的,它对恰当、正确的艺术欣赏是必要的;那么,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我们怎么可以设想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呢——我对自己正在欣赏的自然对象一无所知,可我还是很欣赏,觉得它很美?
如果我们居然认可这种状态,那么,卡尔松又为我们设置了另外的情境。设想有两种情况,情境一,某欣赏者对自己所欣赏的自然对象一无所知;情境二,某欣赏者对自己所欣赏的自然对象有较全面、深入的知识和理解。那么,我们对这两种自然欣赏状态应当做怎样的判断与评估?我们是否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这两种欣赏在质与量上都了无区别?如果有,它应当是怎样的区别?在情境二中,欣赏者所具有的科学知识对其自然审美欣赏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应当如何评价这种作用?
卡尔松从具体的自然审美欣赏情境出发所提出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思考这样的问题:要对自然审美欣赏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大概不能满足于人类审美的总体感性立场,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以科学知识为代表的人类理性精神因素在自然审美这一感性精神活动中的价值功能问题。我们必须思考,总体上作为感性精神活动的审美,是否可以全然脱离理性认知因素,对自然对象毫无相关知识的自然审美欣赏是否可能?它与有相关知识支撑的审美欣赏有何不同?这些问题一经卡尔松提出,便确实不容回避,且意趣盎然。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对人类自然审美活动有更深入的理解。
卡尔松认为,总体而言,在自然审美欣赏中,一定的相关科学知识,如同艺术史、艺术批评知识之于艺术欣赏一样,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确保自然审美欣赏中审美判断具有客观性的现实途径。他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科学知识对于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价值功能。
首先,科学知识为自然审美欣赏提供了必要的关注边界。
自然界是个茫然一片的整体,面对自然,我们有时不免感到很茫然,手足无措。显然,我们不可能看到什么都欣赏,把所遇到的自然对象都欣赏一遍。既然如此,面对自然,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自己审美欣赏的有效边界呢?卡尔松认为,是科学知识为我们的欣赏提供了必要线索。通过它,我们可以确知欣赏中,哪些是必要的信息,哪些则是可以忽略的。
我们关于特定环境的知识产生了我们欣赏的必要边界,审美意义的特定焦点,以及对于特定类型的环境而言,我们应当具有的反应。③
这也是卡尔松为何不接受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参与美学”(engagement aesthetics)的原因,虽然他们都承认自然欣赏作为环境欣赏应当是动态、多感官参与的。依卡尔松,绝对的参与性欣赏意味着所有东西都可以欣赏,没有了来自认知因素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指导,这样的参与性欣赏,其最后的审美经验便成为一种“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生理感官的混合”④。
其次,科学知识为我们提供关于自然审美特性和价值方面的信息。
就像艺术史、艺术批评方面的知识有利于我们对特定艺术作品做出较为准确、恰当的审美判断一样,有关自然对象的相关科学知识,也能够让我们正确、深入地了解特定自然对象到底是什么、为何如此,用美学的术语讲,关于特定自然对象的相关科学知识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把握既定对象之审美特性。
将自然环境欣赏与科学知识相联系的总体认知方法在环境美学中占有关键位置……关于自然,首先是科学提供了关于它为什么如此,以及它是什么之类的答案⑤。
如果有关自然事物的欣赏应当是对此类事物依其本来面目进行审美欣赏,如果科学知识确实能告诉我们自然事物实际上是什么,那么,对自然事物的审美欣赏就应当是依照诸如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科学所告诉我们的那些概念、范畴和描述而对自然事物所作的审美欣赏。⑥
既然是自然审美欣赏,所欣赏的是自然对象,那么,这里的知识便首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卡尔松称之为“自然史的知识”。这种知识典型地体现在三个具体领域,它们是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
就像严肃、恰当的艺术审美欣赏要求有关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方面的知识一样,对于自然的此类欣赏也要求关于自然史的知识——由自然科学,特别是诸如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之类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核心的观念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能够揭示自然对象和环境真实的审美特性。⑦
地质学告诉我们无机世界的秘密,比如特定山峰的地质构造、何以如此,即大山的历史;生物学告诉我们有关地球众多生命个体、种类、现象的秘密,使我们的自然审美不只欣赏各种生命物种之外在形态——其形状、色彩、声音等,还能更为具体、深入地了解其生活习性、内在的生命特性。生态学则告诉我们地球上各种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命个体、群体对于其所处特定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
总之,科学知识之重要,在于它解决了自然审美欣赏中最为基础的问题——面对自然对象与环境,我们到底应该欣赏什么、怎样欣赏?如果连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我们对自然美的欣赏,难道不是太莫名其妙、太离谱了吗?
如果说人类审美活动如同其他精神生活,也是一种有意识、自觉的活动,其自觉性到底表现在何处?恐怕首先表现在对自己所欣赏的对象有较为清楚的了解。既如此,自然审美欣赏中,我们关于自然对象、环境之必要的正确知识从何而来?应当,也只能是从科学知识中来。科学知识得之于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正是人类正确、深入地认识自然的最重要途径。正因如此,集中研究自然世界对象特性及其内部规律的自然科学所得出的具体成果——科学知识,恐怕就是人类自然审美所需关于自然对象、环境知识之最基础、可靠的资源。简言之,正是科学知识保证了自然审美欣赏客观性原则的实现,科学知识对任何有效的自然欣赏而言都是必需的。
对于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而言,科学知识是最基本的。没有了它,我们将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也将失去有关自然的审美特性与价值。⑧
在这里,卡尔松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appropriat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卡尔松认为,科学知识对这种“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或“恰当地”欣赏自然是十分重要,而且是必要的;没有这种科学知识支撑的自然审美欣赏,即便可能,也是“不恰当的”。
那么有没有“不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范例呢?有。最典型者,便是卡尔松所强烈反对的自然审美欣赏中的“形式主义”。他曾有系统论文,专门反对自然审美中的“形式主义”⑨。那么,“形式主义”究竟错在何处?卡尔松认为,那种只关注自然对象形式美特性,诸如色彩、形态、线条、声音等的欣赏,只能算是对自然美“肤浅的”(superficial)欣赏⑩,因此也是不恰当的,而有科学知识支撑的自然审美欣赏,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
再次,科学知识具有提升和深化自然审美欣赏层次的功能。
当然,有一种可称之为从常识性描述向科学性描述的观念运动。可是,此处最重要的是,如果说这种运动会带来景观欣赏上的任何不同,这并非审美欣赏与其他欣赏间的不同,而是这样的不同,它是从肤浅的欣赏向更深刻的欣赏的运动……科学知识深化和提高了对景观的恰当欣赏,这种欣赏发端于我们的日常知识。(11)
卡尔松想说的是,科学知识不只确保我们对自然有一种恰当的欣赏,它也是深化和丰富自然审美欣赏的有效途径。通过它,我们的自然审美欣赏便能超越原来的形式主义趣味,达到更高境界。因此,他将从形式主义趣味到科学知识之应用,理解为人类自然欣赏不断地自我深化、提升的运动。惟有在科学知识的帮助下,我们对自然对象、环境的审美欣赏才能超越表象之美的层面,我们对自然世界的感知与理解才更准确、更深刻、更丰富,我们的自然审美经验也才能更厚实、丰盈。因此,从形式主义到科学知识之应用,这种运动本身便标志着我们自然审美境界的提高。
最后,科学知识还是自然对象审美特性、价值之根源。
科学的信息和描述使我们发现了我们此前见不到的美、模式与和谐,取代了此前无意义的混乱状况。(12)
如果理解部分地是诸如秩序、规律、和谐和均衡等的功能,我们从中发现了审美价值,那么,科学的发展及其持续性自我完善便形成了一种指向此审美之善的运动。(13)
准此,科学知识又成为自然界审美价值之源。至少,没有科学,这个世界将是一个不可理解之物,这样,我们也就不能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即使它在本质上真的很美。当然,他没有意识到,当他如此这般地理解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价值的决定性意义时,在逻辑上似乎已然通向一条与他一开始所主张的客观主义正相反的主观主义道路。
上面是卡尔松对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作用所做的逻辑证明。此外,他还从西方自然欣赏史上发现了有力证据:
作为自然科学持续进步的一种功能,所有的景观都变成了欣赏的对象。(14)
现实的景观……在19世纪达到一种繁荣阶段……它的发展确实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快速进步有关,特别是地理学、生物学和地质学。(15)
这种美学史的证明与上面的逻辑论证相辅而行,增加了其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说服力,至少在西方美学背景下是如此,哈格鲁夫(Eugene C.Hargrove)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16)。
上面是卡尔松对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功能之总体性说明,此外,卡尔松还提供了在具体情境中科学知识如何充分体现其价值的实例——审美偏好与可持续性景观选择之间的关系。首先,他对一般性偏好、审美偏好和审美价值三者作了区别,指出人们的一般性偏好与其审美偏好可以不相协调。然后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会在审美上偏好于可持续性景观吗?
为了有力地回答此问题,卡尔松设计了以下四种情形:
情形一,有两处景观在外形上彼此均非常相似,人们不知道哪一处是可持续性景观。那么,虽然其中之一是可持续性的,另一处则非;可是由于它们在外形上看来起来非常相似,因此,人们对这两处景观并无偏好上的不同,因为他们没有关于可持续性方面的知识。
情形二,两处景观在外形上不同,人们同样不知道哪一处是可持续性景观。在此情况下,最可以想象的状态是,人们的偏好会有所不同,但是其偏好可能会倾向于外观上看起来更美观的那一处,而不会倾向于可持续性景观。
情形三,两处景观外形上看起来非常相似,人们知道哪一处景观是可持续性的,哪一处不是。这种情形又会如何呢?事实可能是,人们的偏好会有所不同,由于他们知道哪一处是可持续性的,因而人们很可能会倾向于可持续性景观。可是,由于传统的审美观念——形式美,所以,这种关于可持续性的偏好似乎又与审美无关。
情形四,两种景观很不相同,而且人们也知道哪一处为可持续性景观。情况可能是,人们将选择可持续性景观作为其审美偏好。
由于在没有相关知识的情形下,人们不能发现哪一处景观是可持续性的,卡尔松便对审美偏好给出新的解释:
真正的审美偏好不只是事物外观的产物,它同时也表达了人们所知道(或相信)的关于对象是什么的信息。(17)
因此,卡尔松强调自然欣赏中,“知道”或“知识”对于人们可持续性偏好的意义。
当我们审美地偏好于可持续性景观,我们审美地偏向于它们,是因为它们是可持续性的,因为它们表达了可持续性。简言之,在我们对于可持续性景观的审美偏好中,部分相关者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知道(或相信)它们是可持续性的,根据这一知识(或这些信念),它们表达了其可持续性。(18)
根据他对审美偏好的理解,情形三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释:虽然两处景观看起来很相似,但是,根据生态学方面可持续性知识,我们仍然能够有一种真正的对于可持续性景观的审美偏好。或者,“这种景观可以对我们表达不同的东西,即使它们看起来极其相似”。现在,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在审美上偏向于可持续性景观?卡尔松的回答是:
他们可能有理由说,如果他们知道(或相信)它们是可持续性的话,他们当然从审美上偏好于这样的景观。(19)
换言之,对人们在审美上偏好于可持续性景观而言,相关的知识是必要的。可是,我们仍未弄清的是,如果一旦知道了此类事物,我们是否就一定倾向于可持续性景观呢?这是卡尔松的核心立场:
我们不只是看景观,我们也知道它的真实特性……我们对于一处景观可持续性的知识,比之于它看上去恰好如此的面貌,对我们的审美偏好而言,通常更有意义。(20)
通过提出和回答对于可持续性景观,人们如何形成其审美偏好的问题,卡尔松揭示了理性认知及其相应成果——知识对于自然欣赏的功能。卡尔松从这一特殊情形(对于可持续性景观的审美偏好)所得出的结论,对于我们理解理性认知和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整体性功能,具有启发意义。
对卡尔松的这一理论,同行们还是有所质疑,首先是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的必要性问题:科学知识对所有的自然审美都是必不可少的吗?显然,欣赏自然美的人应当多于对自然拥有专门、精深知识的人。拥有丰富自然科学知识的科学家们当然可以欣赏经过剧烈造山运动之后峻峰的崇高之美;可是,一个儿童,或乡下不识字的老太婆,难道不同样可以被落日的余晖所打动吗?
科学知识对于以新奇、惊异、敬畏为特点的欣赏来说,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可是,它对于我们感知审美特性是必要的吗?发现反证并不难。我能欣赏一朵浪花伴随着波浪冲刷沙滩所卷起的白色泡沫而形成的完美曲线,而不需要知道浪花是如何形成的。我对浪花所作的壮观、令人愉快的判断,可以仅仅建立在对于其感知特性,以及赋予这些特性以意义的任何联想,或情感的欣赏之上。(21)
其次,同行们还提出另一个质疑,那就是自然审美中科学知识的相关性问题,或者说自然审美中科学知识的边界问题。即使在总体原则上承认了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中的合法性、重要性,但在具体细节上,在科学知识的应用层面,还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自然审美欣赏到底需要多少科学知识?我们总不能说,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与自然审美相关吧?这样一来,在实践上人们是做不到的,即使真正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也不敢承认自己已然获得了所有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这还会造成一种理论上的困难:自然审美与自然研究趋同,自然审美最后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
我们关于环境所拥有的知识之范围与种类可谓无限之大,除非我们能将那些与审美欣赏相关的知识和那些不相关的知识区别开来,诉诸知识并非相当有益。女士拖鞋分子壁的化学结构与我们对这些拖鞋的欣赏相关吗?对大多数人而言,我想是不相关的,那么,什么样的知识才相关?(22)
同行们的这些质疑都很有力,这便促使卡尔松进一步细化自己的思考。后来,对科学知识的具体应用问题,他作了补充性说明:
科学知识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对自然审美欣赏都是必要的,没有这种知识的自然审美欣赏也是可能的。但是,根据科学认知主义,这种欣赏并不是一种全面的欣赏,而只是一种不完善的,或是肤浅的,或是被误导的欣赏,有些情形下,还可能是一种有缺陷的欣赏。其次,随着相关科学知识的增加,审美欣赏会变得更为恰当,即是说,更多的对于特定自然景观或对象之正确科学知识,能够提升对于该景观、对象之审美欣赏,使它更深入,更丰富,更值得拥有。这就导出第三点,对于自然审美欣赏而言,当然,只有某些科学知识,而非任何,或所有此类知识是必要的。再者,任何此类知识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观念将是可笑的,而后者,即所有此类知识都是必要的,将会使适当的自然审美欣赏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上帝。(23)
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补充。为了更好地解决科学知识应用的层次性问题,卡尔松对常识(common sense)和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的区别与联系作了进一步说明,而在当初,他只是并用这一对概念而已(24)。
在重要意义上,科学知识只是常识的一种拓展,对于一处景观的科学观念比之于常识观念,也许在细节和理论上更丰富,但这二者本质上并无不同。(25)
当然,有一种可称之为从常识性描述到科学性描述的观念运动。但是,这里重要的是,如果此运动在景观欣赏中会造成任何不同,那么它并不涉及到从审美欣赏到其他欣赏的变化,而它只是审美欣赏从表面化欣赏到更深入欣赏的运动。(26)
常识是普通社会公众所拥有的关于自然对象之一般性知识,科学知识则是科学家所拥有的关于自然对象更为专精的知识。前者解释了自然审美欣赏对所有社会公众何以可能,因为我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关于自然的知识;后者则说明更高层次的“恰当”、“严肃”的自然审美何以可能,凸显仅以常识、形式美为支撑的自然审美欣赏的局限性。这些说明应当可以弥补他前面所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重要性的总体原则。
二、科学认知主义的理论价值
卡尔松的自然美学被称之为“科学认知主义”(27),这是很恰当的,卡尔松本人也乐于接受。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评价这份自然美学理论成果呢?
首先,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是当代西方自然美学的一份重要成果,它对整个当代自然美学具有普遍意义。
如果说罗纳德·海伯恩(Ronald Hepburn)的经典论文《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28) 标志着西方自然美研究的觉醒,那么,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则标志着当代西方自然美学的成熟。康德之后,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学术界缺乏对人类自然审美的严肃、系统研究,在这个领域要发现一种有意义的理论是很困难的。可以说,在20世纪西方美学史上,自然美研究比之于一直很发达的艺术哲学,明显地是个弱项。海恩伯唤醒了自然美研究的自觉性,但是,直到卡尔松的科学认知理论出现,当代西方美学才有了一套独特的自然美学理论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自然审美研究不足之情形。
卡尔松努力建立一套理论,用以客观地解释和评估人类的自然审美欣赏;努力发现一种有效的方式,以确保我们的自然欣赏是恰当、深刻的,最后他发现,这便是科学知识。他用二十多年的艰苦劳动,创建和打磨出这套被称之为“科学认知主义”的理论。它努力回答人类自然审美的关键性问题,诸如在自然中欣赏什么,如何欣赏自然;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等。应当承认,任何一位对自然审美感兴趣的美学家都不得不面对、严肃地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当代西方美学史上,追问和回答这些问题本身便意味着一种新意识:美学家不再满足于这样一种情境——自然审美阐释始终处于艺术哲学的庇护之下,它意味着自然美学努力从艺术中心论美学中独立出来的新时代已然到来,它代表了当代西方自然美学的自我觉醒。
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对自然审美欣赏贡献出一系列重要观念。他认为我们应当遵照自然本身特性欣赏自然,而不能以欣赏艺术的方式,像对待艺术品那样地欣赏自然(29);他提出就像艺术审美欣赏那样,我们对自然的审美判断也可以是客观的;他坚持没有关于自然对象、环境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支持,我们的自然欣赏很可能是不恰当的,至少很可能是肤浅的。
应当承认,这些观点不只富有启发性,而且也容易接受,它们理当成为我们对自然审美欣赏的共享性见解,成为当代自然美学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自然审美欣赏客观性原则,应当为任何严肃的自然审美欣赏、自然美学所遵从。
其次,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对人类自然审美欣赏的独特阐释,有助于拓展我们对人类自然审美的理解。
虽然西方有著名的科学传统,可是在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出现之前,并没有任何理论专门揭示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独特作用。
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是一套独特的自然美学理论。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专门地,甚至是排它性地只立足于理性认知及其成果——科学知识来审视和阐释人类自然审美活动。他将理性认知及其成果——科学知识的作用放在强光下进行考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以前我们总是只从感性一端来认识、理解包括自然欣赏在内的所有审美活动。但自从有了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情形便有所不同。
当然,卡尔松并非讨论审美感性中科学理性作用的第一人。在他之前,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很好地揭示了理性因素对于人类审美感性的重要作用,他甚至从视觉这一典型的感性现象中发现了理性认知的内涵。但是,阿恩海姆主要在艺术,特别是美术的领域讨论这一问题,卡尔松则专门在自然审美欣赏领域论证这一问题,因此,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仍然具有相对独立的创造意义。
当自从德国古典美学之后,我们已习惯于在感性与理性、科学与审美两立的框架下展开我们的审美思考,卡尔松则反其道而行之,正面论证科学与自然审美间内在的深刻逻辑联系。由于他的视野与主题已然偏离了主流立场,着意强调的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问题,因此,当他把人类认知理性、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面呈现出来时,自然也就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
从此,我们不再可以设想一种对于自然界、自然对象茫然无知状态下的自然审美欣赏,即使我们不怀疑这种自然审美的可能性,至少,我们会怀疑这种自然审美的内在质量、效果、层次,甚至合法性。
从此,虽然我们仍然承认审美在总体上是感性的,但大概没有人断然否认理性因素在审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我们不再纯感性地理解审美,不再认为审美感性与科学理性水火不容。
从此,对形式主义审美趣味的反思,我们多了一个新的维度,那便是自然审美欣赏的层次性问题。反过来说,我们也多了一条提升自然审美境界的新途径——欣赏者通过自觉地增加自然科学知识,深化、提升自然审美境界,丰富既有的自然审美经验。这条途径的新颖性在西方发达的科学传统背景下也许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它对我们这个主观的“借景抒情”艺术传统很发达的民族来说,应当别具深义。原来我们以为,形式审美之外,能丰富和提升自然审美境界者,惟“言志”而已,岂有它哉?现在,“科学认知主义”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这是一条足可与我们自身“言志”抒情传统相媲美的新路径。而且严格说来,这条路径比之于我们自身之原有传统,似乎更符合自然对象自身特性,更具客观性。
从这些角度讲,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确实打开一扇独特窗口,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深入反省中华自然审美传统的固有局限,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如何简要地理解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价值呢?从普遍性的角度看,科学知识是保证客观、独立地欣赏自然自身审美特性、价值的现实道路;从独特性的角度看,科学知识是我们丰富、深化和提升人类自然审美境界的一条通幽曲径。
三、对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质疑
作为一种自然美学理论,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无论在普遍性学术价值,还是独特性审美阐释两方面,均甚可观,故略述如上。但合卷思之,这种理论似又有诸多未畅、未洽处,引人生疑,令人遗憾。在结束本文讨论之前,本人特将诸端疑虑和盘托出,质之于同行。
首先,“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缺乏对自然对象的系统分析。
卡尔松一再强调自然审美欣赏的“客观性”(objectivity)原则(30),而且,他对自然审美阐释长期依赖艺术哲学表示不满(31)。他还提出,要依自然之本性来欣赏自然。但是,自始至终,卡尔松的自然审美阐释均立足于“自然审美欣赏”这一环节,而科学知识的作用也只在自然审美欣赏这一环节中提出来,只在这一环节内解释。对于自然对象特性本身究竟为何物,卡尔松始终没有正面论述。对自然,他只提出一般性规定——“自然是自然的”和“自然是环境的”(32)。但是,对于一个系统的自然美学理论来说,光有这两条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以“客观性”为第一性原则的自然美学理论来说便更是如此。
怎样才能为自然美学的客观性立场、独立自主的自然审美欣赏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其必要条件应当是,这样的理论应当首先建立在专门、扎实的自然对象理论基础上,建立在对自然审美对象特性、结构和范畴类型的系统研究之上。至少,专门、系统的自然对象研究应当是其自然美学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或缺、最为基础的部分。有了这样的自然对象论,然后才可进而讨论欣赏什么、如何欣赏,以及怎样的欣赏才是“恰当的”之类问题。但是,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不然,它上来便是“欣赏什么”、“如何欣赏”和“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之类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始终不出欣赏的范围。如此这般建立起来的自然审美理论模型,不免让人生疑:到底自然对象在先,还是对自然对象的欣赏在先?除了“自然是自然的”这一不免同义反复的抽象原则之外,如果我们对自然对象本身究竟为何物并没有明晰、细致的认识,那么,我们何以确切知道我们的自然审美欣赏到底是否“恰当”?而且,没有了对自然对象本身的正确、深入认识,这种“恰当”与否的标准又如何制定呢?因此我们以为,不是欣赏论,而是对象论,才是自然美学“恰当的”第一个逻辑环节;不是对对象的欣赏,而是对象自身之存在,才是人类自然审美的现实起点。
可是,卡尔松似乎以为,他已然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不是反复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吗?科学知识就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但我以为这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诚然,在形而下层面,在每一次具体的自然审美欣赏过程中,我们关于特定自然对象的特定知识确实可以帮我们不少,但是,欣赏环节,科学知识形而下的具体指导功能,并不足以取代形而上层面的自然对象论。科学知识在欣赏环节解决形而下“点”的“恰当”性问题;作为哲学美学、理论美学,系统的自然审美对象理论则为自然审美欣赏提供关于自然对象特性、要素、结构和类型的基本框架,宏观地解决“面”的“恰当”性问题。没有自然对象论支持的自然欣赏论是不扎实、不完善的;在没能较为明确、系统地回答自然对象为何物的问题之前,贸然提出欣赏什么、如何欣赏以及怎样的欣赏才是“恰当的”,甚至有点儿滑稽。某种意义上说,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的问题是一个自身并不能独立解决的认识论问题。相反,本质上,它当由自然对象特性论来规定。一旦欣赏成了自然美学的核心,甚至惟一内容,自然审美欣赏的客观性便失去其现实基础与规范依据,主观性便不可避免。在对肯定美学的论证中,卡尔松便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困难、不成功,最终是主观地论证自然审美价值的范例(33)。
其次,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缺乏对人类理性认知要素的深入分析。
卡尔松的自然美学理论被称为“科学认知主义”是恰当的,因为其主旨就是突出强调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重要作用,而科学知识是人类理性认知能力发挥作用的结果,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中的应用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理性认知功能在感性审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过程。
如上所述,卡尔松的自然美学其实只关心一个问题——自然审美欣赏——立足于审美欣赏环节研究自然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又可以将卡尔松的自然美学理解为一种认识论的自然美学。
那么,作为认识论的自然美学,我们对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的最初想象是:它将对人类各种理性官能要素,诸如感知、想象、推理、理解、直觉等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各自特性与功能,作系统、深入的哲学分析。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我们错了。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并不关心人类理性认知要素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而只对这些要素已然发挥了作用之后(而且是在审美之外——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发挥作用之后)的现实成果——科学知识感兴趣。换言之,卡尔松感兴趣的是,利用理性认知的成果——科学知识,以指导或校正人们的自然审美欣赏,规范人们对自然对象的理解,而对于科学知识之所以产生的内在因素——人类科学认知理性本身的工作机理不感兴趣。
这样说来,从哲学美学的角度看,用“科学认知主义”来描述卡尔松的自然美学理论,其实并不准确,改称为“科学知识论的自然美学”后似乎更为贴切,因为他只关心形而下层面的科学知识之应用,并没有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人类科学所以产生的理性认知因素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如何发挥作用做深入的理论分析,只是轻松地应用了这一因素的最后成果——科学知识。严格说来,没有对自然审美活动中人类理性认知诸官能,如感知、想象、推理、理解和直觉的特性、结构和工作机理,及其相互关系作专门、系统、深入分析的理论,就不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审美认识论。如果一定要用“科学认知主义”来指称和描述卡尔松的自然美学,那么,它也只能是一种相当初级的“科学认知主义”。
再次,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没有对认知理性因素之外的其他非认知因素,以及它们与认知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说明。
经过卡尔松的系统论证,我们确实深刻意识到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还有疑问:在一种有效的自然审美欣赏中,除了科学知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也是重要的?或者说,对于一种成功、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而言,是否只要有了正确的自然科学知识就足够了?在这方面,卡尔松并没有明确的论述。当然,这样的问题不应当是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主题,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重要作用才是其合法主题。可是,我们对卡尔松还是有所期许。解决这些疑问至少应当成为其自然美学理论有意义的补充性、拓展性问题,因为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科学知识确实难以独撑自然审美局面,会面临许多困惑、挑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套理论的审美解释力。
卡尔松一直强调自然审美欣赏的“恰当性”。诚然,没有了科学知识支持,对于自己所欣赏对象一无所知、胡思乱猜式的欣赏很可能是“不恰当的”,但是,有了科学知识帮助的自然审美就一定是“恰当的”吗?没有了科学知识支持的自然审美就一定是“不恰当的”吗?人类其他生理、心理因素对于“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是否也会有所贡献呢?“恰当性”的标准又如何制定?
卡尔松一直强调:只停留于形式主义层面的自然审美欣赏是“肤浅的”,应当走向“严肃的”自然审美欣赏,而科学知识对于提升自然审美境界,规范我们对自然对象特性之理解,深化我们的自然审美经验,导向对自然对象“严肃的”欣赏,显然是有帮助的,是重要的途径。但是,难道只有科学知识才能提高我们的自然审美境界吗?难道只有在科学知识指导下的自然审美欣赏才能是“严肃的”吗?
如果认知与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欣赏而言既不必要,也不充分;那么,卡尔松便有责任对认知、科学知识之外的人类其他感性、理性心理因素的价值功能,它们与科学认知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哪怕仅仅是补充性的简要说明。
确实,卡尔松并未声明:只有认知和科学知识对于自然审美欣赏才是有意义的。在具体讨论中,特别是与其他学者的论辩性文章中,卡尔松也会提及一些科学知识之外的其他事物,诸如情感和想象。对这些东西,卡尔松的策略总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至少,在具体的层面他是忽略的。在卡尔松的理论中,我们没有发现他对非认知因素、非科学因素的专门、直接阐释。比如情感在自然审美中的特性与功能。为追求理论的纯粹性,卡尔松几乎否认了其他精神心理因素对自然审美欣赏的价值,而让认知与科学知识独处其中。因此,当卡尔松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独特,逻辑上能充分自洽的美学理论时,由于其视野狭窄,阐释力也就大打折扣。这就决定了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只能是对人类自然审美活动的一种独特解释,而不能成为一种完善的自然美学理论。
最后,“科学认知主义”与环境美学间的紧张。
“科学认知主义”属于自然美学,但是,对卡尔松来说,自然美学只是其环境美学之前奏,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提出“自然是环境的”,并且将“环境模式”视为自然审美欣赏惟一恰当的模式(34)。20世纪90年代以后,卡尔松也主要以环境美学而知名。
作为“科学认知主义”创立者,卡尔松强调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中的作用;作为一个环境美学家,他又强调对自然环境应当作全方位、多感官、动态的欣赏(35)。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在他与伯林特的论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当他责备伯林特的“参与美学”时,卡尔松提出,对我们所欣赏的自然对象与环境,给出一个边界是必要的,而伯林特所倡导的对环境全面融入式的欣赏,将导致“什么都可以”的状态。可是,当卡尔松自己介绍环境美学的范围时,调子变了很多。依他的描述,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欣赏(36)。
再者,虽然卡尔松总体上肯定环境欣赏的动态和多感官特征,但是,当他讨论到自然审美的具体情形时,往往更强调科学知识的作用。当他突出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时,他是一个“科学认知主义”者,而当他强调环境欣赏的特征时,他又客观上成了“参与美学”的支持者。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当我们动态、多感官地体验环境之美时,是否还能有效地保持科学认知的效果与特征?而当我们力图对自然对象、环境作认知式观赏时,是否还能进行那种全方位、多感官、动态融入式的欣赏?众所周知,认知是一种反思性活动,它要求客体与主体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否则,明晰、正确的知识便不能获得。但是,环境欣赏如卡尔松和伯林特所描述,是对既定环境的直接感知和体验,它是一种多感官、整体性的把握方式,而不只是一种科学认知。
简言之,科学认知和对环境的全面体验这两种方式在内在特性上是冲突的,至少这两者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的具体情形如何,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两者间的紧张?对卡尔松来说,这些问题并不清楚。
注释:
①(30) Allen Carlson,“Nature,Aesthetic Judgment,and Objectivity”,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40(1981):15-27.
②③④(24)(29)(32)(34)(35) Allen Carlson,“Appreci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37(1979):267-276.
⑤ Allen Carlson,“Environmental Aesthetics”,in Berys Gaut and Dominic Mclver Lopes(ed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esthetics,London:Routledge,2001,pp.430-431.
⑥(23) Allen Carlson,“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s of Natural Landscapes and Appropriat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Rivista di Estetica(Review of Aesthetics),29(2005):41-51.
⑦ Allen Carlson,“Environmental Aesthetics”,in E.N.Zalta(ed.),Stanford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Stanford:SEP,2007(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environmental-aesthetics/).
⑧(12)(13)(14)(15)(33) Allen Carlson,“Nature and Positive Aesthetics”,Environmental Ethics,6(1984):5-34.
⑨ Cf.Allen Carlson,“Formal Qualitie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13(1979):107-114; Glenn Parsons and Allen Carlson,“New Formalism and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62(2004):363-376.
⑩ Glenn Parsons and Allen Carlson,“New Formalism and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62(2004):363-376.
(11)(25)(26) Allen Carlson,“Education for Appreciation:What is the Correct Curriculum for Landscap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35(2001):97-112.
(16) Eugene C.Hargrove,“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in Allen Carlson and Sheila Lintott(eds.),Nature,Aesthetics,and Environmentalism:From Beauty To Du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2008,pp.29-48.
(17)(18)(19)(20) Allen Carlson,“Aesthetic Preferences for Sustainable Landscapes:Seeing and Knowing”,in S.Sheppard and H.Harshaw(eds.),Forests and Landscapes:Linking Ecology,Sustainability and Aesthetics,New York:CAB International,2001,pp.31-41.
(21) Emily Brady,“Imagination and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56(1998):139-147.
(22) Robert Stecker,“The Correct and Appropriate in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37(1997):393-402.
(27) 帕森斯始用这个术语指称卡尔松的自然美学(Cf.Glenn Parsons,“Science,and Positive Aesthetics”,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42(2002):279-295)。
(28) Ronald Hepburn,“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in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eds.),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Broadview Press,2004,43-72.
(31) Allen Carlson,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Art and Architecture,London:Routledge,2000,p.114.
(36) Allen Carlson,“Environmental Aesthetics”,in E.Craig(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Online,London:Routledge,2002(www.rep.routledge.com/views/hom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