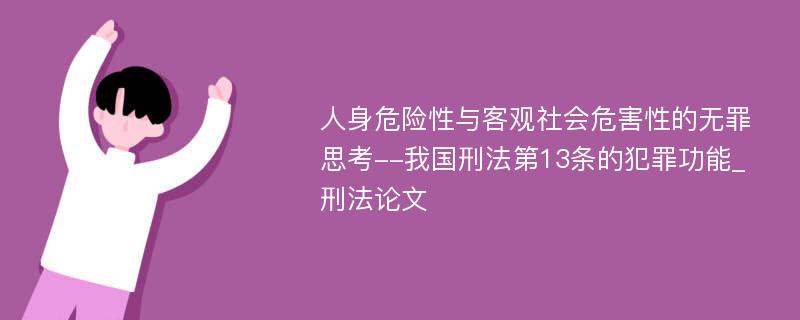
人身危险性与客观社会危害显著轻微的非罪思辨——我国《刑法》第13条之出罪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危险性论文,刑法论文,轻微论文,人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犯罪构成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的具体标准。犯罪构成,就是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具体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注: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2页。)这就是说:(1)定罪必须遵循主客观相统一(注:主客观相统一是指主体与客体、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统一;主观是指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客观是指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参见陈泽杰:“主客观要件相统一是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核心”,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48页。)的原则,即除符合主体、客体要件以外,主观方面必须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必备要件危害行为(选择要件危害结果(注:刑法理论对危害结果有着不同的表述,由此也决定了危害结果是否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本文认为,危害结果通常是指危害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包括有形的物质性的损害结果和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等)。(2)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即应定罪,定罪的唯一标准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对于正当防卫等正当行为,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正当行为在形式上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实质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因而不构成犯罪。(注: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有的学者明确提出,正当行为原本就不符合犯罪构成,事实上也不符合犯罪构成,不能认为正当防卫等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只是没有社会危害性而已。(注: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显然,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在外延上完全重合,尽管一般认为犯罪概念是从宏观上揭示一切犯罪行为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而犯罪构成是从微观上分析各个犯罪行为的内部结构及其成立要件。(注: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然而,在司法实际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某一具体罪的构成要件,但是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与行为的客观危害显著轻微。例如某村民携少女前往广州打工,随后两人恋爱并“结婚”,然而少女未满14周岁,该村民被判刑。这里,该村民的行为符合《刑法》* 分则第236条第2款奸淫幼女罪的构成要件,但是该村民既无前科也非累犯甚至无其它劣迹,很难说其有人身危险性(注:关于人身危险性的概念,下文详述。),从客观危害来讲,也很难说其这一违法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其实,既然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是两种界定而非一个概念,那么两者就可能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注:2000年2月13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中,从“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角度排除了上述案例情形的犯罪性——“不认为是犯罪”(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情节轻微”的法律术语不尽合理,与“不认为是犯罪”相对应的应当是“情节显著轻微”)。或许这一司法解释正可作为支持本文思辨的一个正面的实例。)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注:犯罪概念的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惩罚性均可在形式上与犯罪构成相吻合。)由此,刑法界有学者提出《刑法》第13条的社会危害性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指出社会危害性本身具有笼统、模糊、不确定性,因而不利于体现罪刑法定原则。(注:参见樊文:“罪刑法定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兼析新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概念”,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第27页。)也有学者对此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会危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具体的、明确的、确定的,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原则。(注:参见李立众、李晓龙:“罪刑法定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与樊文先生商榷”,载《政法论丛》1998年第6期,第5页。)这实际上是由于我们在理论上固守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相一致而带来的困惑。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刑法分则的犯罪构成要件与总则的犯罪概念是有距离的。他们认为,实质性的犯罪概念是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或危险性,然而这一界定过于抽象笼统,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将犯罪概念明确化,于是出现了将犯罪概念的社会危害性具体化的“犯罪成立要件(又称概念构成要件、总则要件)”和“犯罪构成要件(又称特别构成要件、分则要件)”。犯罪成立要件就是指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是指一种行为该当刑法分则各罪类型的具体的、特别的构成要件。这样,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某一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即该当犯罪构成要件),还不一定成立犯罪(即只有同时该当违法性、该当有责性,才可确定行为成立犯罪从而具有社会危害性)。(注:参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72页。)应当说,大陆法系国家的这一学说有其实际与理论的价值,它有利于解释现实中复杂的现象(注:笔者并非试图照搬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来解释我国的刑法实然与司法实际。此处仅借其启发思路。),同时又不失刑法的公正价值(注:储槐植教授指出:“当今世界大致有三类犯罪构成模式。一类是适应阶级专政需要,静态反映‘犯罪规格’的平面整合结构式,如原苏联自三十年代前后开始形成的犯罪构成体系。另一类是责任范围逐步收缩(排除合法、排除无责)反映‘定罪过程’的三元犯罪结构式,如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当今通行的模式。第三类是美国刑法犯罪要件呈双层次结构,即犯罪构成双层模式。这种模式体现控辩双方对等活动,蕴含刑法的维护秩序和保障人权两大功能,表明‘定罪过程’的公正性价值定向。可见,不同的结构发挥不同的功能。”储槐植著:《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作为刑法学研究,当理论不能解释实然的刑法或者实然的刑法不能反映社会事实的时候,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社会事实到底如何。“只有从实际现象出发才能阐述事物,而不能直接用观念想出事实的事物来。”“科学要成为客观的研究,必须从感觉出发,而不是从那些非科学方法形成的概念出发。”“用观念估量事物,就好比一种浮光掠影,外表似乎明白,内里却含糊不清。”(注:〔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5、16页。)倘若法律不能反映社会事实,那么法律有待于修订;倘若理论不能解释实然的法律,而法律又无明显地不合实际,那么说明理论需要更新(注:理论是现实的批判,同时现实又是理论的批判。)。因此,我们的问题应当是,我国现行刑法总则中犯罪概念的实然规定(第13条),能否囊括虽然行为符合分则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由于人身危险性与客观社会危害显著轻微因而不构成犯罪的情况,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说明将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一味统一的思想需要更新(注:倘若因为这一更新以致一发牵动全身,促使刑法理论作较大的变更,亦不足为怪。“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7页)系统要素决定了系统的功能。理论体系的某一方面的缺陷也必然影响到整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理论有缺陷就需要弥补。)。而这一问题的回答,又有待于下列问题的解决:(1)人身危险性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它能否被纳入《刑法》分则具体罪的构成要件的主观要件之中?即能否在犯罪构成中解决这一问题?(2)能否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入罪一个主观要件?(3)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有何确切的含义?
一、人身危险性与行为客观危害的基本观念
人身危险性与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相伴生,而行为客观危害是客观主义刑法理论的一个重心。刑法学是一门规范科学,因而刑法哲学是刑法理论的根基。刑法哲学探索刑法的本源,研究“应然之应然(即价值标准之应然)”,倘若从刑法的两大研究范畴“罪”与“刑”来说,就是公正的刑法应当如何界定犯罪?应当如何设计刑罚(或处置)?自刑法科学史以来,刑法理论总沿着两条主线发展着:其一,强调客观之罪、注重报应之刑,学界称之为客观主义的刑法理论、刑事古典学派、旧派;其二,强调主观之罪、注重教育之刑,学界称之为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刑事近代学派、新派。
文艺复兴赋予科学独立的意义,与封建的君权神授相对立,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是人人生而具有的权利,人人皆有保卫生存、追求幸福和财产、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此权利是永恒的,不得侵犯,不得让与。虽身为君王亦不得非法侵犯此权;如对此天赋的、人人享有的、普遍的、永恒的权利肆意侵犯,其统治将被推翻。(注:参见甘雨沛著:《比较刑法学大全》(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这时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它的主要任务是抨击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指出它们是违反自然、违反理性的,强调资本主义是合乎自然、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性王国。1764年意大利学者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贝卡利亚(1738-1794)发表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刑法科学的形成,贝卡利亚也获得了刑法学之父的美誉。旧派的其他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德国的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英国的边沁等。十九世纪初,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它们的任务已不再是摧毁封建专制,而是巩固、发展资产阶级统治。及至十九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逐步形成垄断。这时,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都市发达,人口涌入城市,并出现诸多社会问题,犯罪日益严重,累犯、惯犯、青少年犯罪、妇女犯罪突出,贫穷、失业、卖淫等普遍化,阶级斗争激化。对于这种新形势下的犯罪问题,刑事古典学派理论不能合理地作出解释与处理。同时,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已成为18、19世纪欧洲学术界流行的一种风尚。1876年意大利学者刑事近代学派的创始人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6-1909)发表了其代表著《犯罪人论》,标志着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龙勃罗梭由此被誉为犯罪学之父,刑法理论也产生了根本性地转变。新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意大利的加罗法洛(Rattaele Garofalo,1852-1934)、菲利(Enrico Ferri,1856-1929)、德国的李斯特(Franz von Liszt,1851-1919)等。在刑事古典学派、刑事近代学派之后的现代帝国主义时期,刑法学家们又提出了许多学说:德国宾丁(Karl Binding,1841-1920)的规范论,德国贝林格(E.Beling,1866-1932)、迈耶(Max Ernst Mayer,1875-1923)、麦兹格(Edmund Mezger,1844-1962)等的构成要件理论,日本团藤重光(1913-)的人格行为论;法国安塞尔(Marc Ancel,1902-1990)的新社会防卫论,德国威尔哲尔(Hans Welzel,1904-1977)的目的行* 为理论等等。(注: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以下。)这些学说是刑法理论的开拓,但从哲学根基上来说,仍未从根本上超越旧派或新派的藩篱。(注:参见陈兴良著:《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近代认识论有两大对立的哲学派别:经验派和理性派。前者强调观察、实验,倡导经验归纳法,后者则强调数学方法的普遍意义,倡导理性演绎法;前者强调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和实在性,强调认识的经验来源;后者则强调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和必要性,强调认识的理性来源。(注:参见陈修斋主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就法哲学而言,关于法律和国家的使命也有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个人主义观念与超个人主义国家观。个人主义观念是以一种愈来愈著名的契约为图画:只有这种契约才可使国家合理化,这个国家仅仅通过意愿自由的、完全可以理解的自私自利的成员而实现其共同聚合。超个人主义观念以有机体,即整体的人为图画:如同在我们的躯体之中一样,在一个好的国家中,并不是整体为了肢体的缘故存在,而是肢体为了整体的缘故存在。(注:参见〔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这种哲学观念反映在刑法领域:总的来说,旧派源于理性哲学,以个人为本位,崇尚客观主义刑法理论;新派源于经验哲学,以集体(国家)为本位,崇尚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客观主义认为,定罪量刑应以外部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论断,而不以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为转移。人是有着自由意志的抽象“理性人”,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在能够选择不犯罪的情况下实施了犯罪,因而应当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刑法应注重人权保障机能。主观主义认为,定罪量刑应注重的不是行为人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而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人身危险性。人是受先验决定的“经验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员,应当对自己的社会危险性格负担责任,强调行为人因其社会危险性而必须接受社会所采取的防卫措施的地位,刑法应注重社会保护机能。刑法理论上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然而从各国刑事立法的实际来看,定罪均需同时具备主客观要件,量刑也都要同时考虑主客观因素,尽管根据情况差异不同的刑法表现出对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的不同倾向。我国刑法始终贯穿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与客观相统一,首先表现为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作为一种行为,它离不开主观罪过的指导和支配;另一方面,缺乏客观上的犯罪行为,罪过就只能完全停留在主观活动的状态,而主体的犯罪意图也就无法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还表现为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害性的统一。社会危害性本身是主观恶性与客观的统一。但是,社会危害性又
是一种已然之罪的客观存在;相对而言,人身危害性却是一种未然之罪的主观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害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注:参见陈兴良著:《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238页。)
这里涉及到一组概念:作为客观主义强调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作为主观主义强调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罪过、犯罪人格。刑法上所称行为有广狭两义:(1)广义的行为是指行为者身体外部之一切动作(包括积极的以及消极的动作),其不以犯罪行为为限;(2)狭义的行为指行为者基于意思活动而在社会上作有意义之身体的外部动作。(注:参见〔台〕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37页。)我国刑法中的“危害行为又称为构成犯罪的事实或构成要件的行为,仅仅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一个要件,属于客观的事实特征,排除了行为主体和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注:熊选国著:《刑法中行为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熊选国博士认为,与危害行为不同,犯罪行为是指已经具备犯罪构成四个方面全部要件的行为,具有主、客观的统一性。关于刑法中行为概念的阐述,还可参见鲍遂献主编:《刑法学研究新视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165页。)刑法界对危害结果大致有三种解释:(1)危害结果是犯罪意思的客观化,它不仅包括行为对客观外界所造成的有形变化,还包括身体动作和其他非物质性损害。(2)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致使犯罪客体发生的事实上的损害或危险状态。(注:参见马克昌主编,前注[12]引,第191-192页。)(3)危害结果是主体的行为对客体已造成的损害,而不是指可能造成但尚未实际造成的损害。(注: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关于危害结果的阐述,还可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0-567页;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张明楷著:《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146页。)其实,我国刑法中的危害结果通常是指危害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的损害结果包括有形的物质性的损害结果和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损害结果。(注:我国刑法总则明确规定有(犯罪或危害或损害)结果的条文主要有:第6、14、16、17、24条;刑法分则有若干条文规定了后果。我们可以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这些结果、后果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看出此意,这一界定较合理地解释了实行终了的中止、未遂、危险犯、故意或过失的心理事实等,详见下文。)罪过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将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一种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是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罪过的形式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
(注:参见杨春洗、高铭暄、马克昌、余叔通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1页。)有的学者认为,罪过是刑法所否定的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对将造成的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注:参见姜伟著:《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其用意之一在于将犯罪动机、犯罪目的作为犯罪故意构成的因素,涵括于罪过之中。)对于犯罪的故意和过失,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有的统称为责任意思或责任条件,也有的统称为责任形式或责任种类等;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统称为犯意;俄罗斯联邦和东欧等国家的刑法统称为罪过。主观恶性是指由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行为表现出来的犯罪人的恶劣思想品质,它具体表现了犯罪人应受道义上和法律上责难的程度。主观恶性不仅包括罪过,而且还包括犯罪的目的、动机以及犯罪前犯罪后的表现所反映出的犯罪人的品质。(注:参见鲍遂献主编:《刑法学研究新视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有的学者则将主观恶性与罪过相类同,认为主观恶性的外在表现称为罪过形式。笔者认为,如果说罪过是一个法律形式意义上的概念,那么主观恶性则是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它所强调的是形式背后行为人主观上的罪恶程度;另一方面,就内容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仅由罪过(实施危害行为时的心理态度)表现,而且通过犯罪前、后的一系列行为展示。因此,主观恶性在横向上比罪过宽泛(不只取决于罪过,而是由与犯罪有关的包括犯罪前、中、后的一系列行为所表现),在纵向上是对行为人主观深层内容的揭示(深入地反映了行为人主观上的罪恶程度)。人身危险性是新派理论中的基石性概念,也是新派与旧派争论的焦点。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将来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人身危险性是指曾经实施过犯罪行为受过刑罚处罚的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广义的人身危险性则不以行为人曾经犯过罪、受过刑罚为前提,即不仅指再犯可能性,而且指初犯可能性。(注:参见王晨著:《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的重心在于说明刑事处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属于刑法范畴,在这一点上其与下文所述的犯罪人格有所不同。不过,作为刑法范畴的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亦有区别。人身危险性,通过行为人的具体行为以及行为人自身和外在环境的一系列因素,预测其未来犯罪的可能性,由此论断对其的处置;而主观恶性,根据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前
、中、后的具体表现,确定其现实主观上的恶劣程度,从而提供定罪量刑的依据。尽管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判断以及基于人身危险性对行为人的处置,也必须以危害行为的出现为条件,但是这种判断与处置却不仅仅是基于此危害行为,它强调的是行为人由于自身与外在因素的作用而表现出这种危害行为的必然性。犯罪人格也称犯罪个性。让·皮纳泰尔将犯罪个性理解为其核心中集极端自私、好斗、缺乏适应性和交际能力以及感情冷漠和麻木不仁等特征于一体的个性。由于犯罪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性和暴力犯罪、财产和经济犯罪等),不存在以这种方式一成不变地被刻划成具有那些特征的犯罪个性。(注:参见〔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著,吴鑫涛、马君玉译:《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22页。)有的学者认为,犯罪人格与“反社会人格”完全相同,而反社会人格又称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是精神病学中所说的人格障碍的一种类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反社会人格是精神病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有明确的含义,不能离开精神病学中的含义而在犯罪心理学中笼统地使用。(注:参见王顺安主编:《中国犯罪原因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也有的学者认为,犯罪人的人格也称犯罪人格,这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犯罪人格与一般人格不能截然分开;没有固有的犯罪人格;犯罪人格具有社会性本质;必须把犯罪人格放到社会化的过程中去考察。(注:参见邱国梁著:《犯罪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笔者认为,对犯罪人格的界定,应首先明确人格的概念。人格(personality)的含义很多,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注:参见〔美〕阿瑟·S·雷伯著,李伯黍等译:《心理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608页。)通常心理学家认为,人格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个人所具有的意识倾向性,以及经常出现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人的个性结构主要包括个性的倾向性和个性的心理特征(包括性格、气质和能力等)两个方面。(注:参见叶奕乾、祝蓓里主编:《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252页。)美国著名社会学戴维·波普诺(David Popinoe)认为,人格指的是特殊的思想、感觉和自我观照的模式,它们构成了特殊个体的一系列鲜明的品质特征。人格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部分:认知(思想、知识水平、知觉和记忆)、行为(技能、天赋和能力水平)及情感(咸* 觉与感情)。(注:〔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不过不论怎样,通常人格界定都强调:个性的倾向性、稳定性、独特性和心理特征。有鉴于此,犯罪人格是一种人格类型(personality type),是犯罪心理(注:犯罪心理,指影响和支配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的总称。这些心理因素包括认识、情感、意志、性格、兴趣、需要、动机、理想、信念、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心理状态等。见罗大华、刘邦惠主编:《犯罪心理学新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中具有相对稳定的犯罪(注:犯罪人格(criminal personality)通常与犯罪性(criminality)、犯罪人格特征(criminal personality traits)相关联。)倾向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不宜将犯罪人格称为犯罪人的人格,因为犯罪人的人格可能具有两面性(某些方面亲合社会规范,某些背离社会规范);犯罪人格是犯罪人的人格中具有稳定的犯罪性的部分。(注:犯罪人格的界定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鉴于其并非本文的主题,笔者拟另文论证。)人格是在生理、文化以及社会因素交互影响下形成的,是社会化的产物。(注:参见〔台〕蔡文辉著:《社会学》,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20页。)人格的研究,注重探索人格的形成过程——社会化。“科学地认识个性的关键只能是研究人的个性在其活动中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个性在这各脉络中既是活动的条件,又是活动的产物。”(注:〔苏〕安德列耶娃著,蒋春雨、唐慕文、李锡勤、于秀贞译:《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页。)因此,犯罪人格不仅仅是一种评价,犯罪人格更为注重的是揭示这种人格的形成——个体通过不良社会化而形成的人格定势,属于犯罪学的研究。(注:犯罪学注重犯罪前的研究——根据犯罪现象,探索犯罪原因,寻求犯罪对策,其中犯罪原因是核心问题;刑法学注重犯罪后的研究——针对犯罪行为,确定公正合理的法律处置,强调的是公正的定罪量刑。)与此不同,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主要强调这种恶性、危险性在刑事处置中的意义(注:新派提出人身危险性,其着眼点在于事后的处置,强调确定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轻重的标准,不应是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的大小,而应是行为人反社会性或社会危险性的大小。这正如比利时刑法学家普林斯所指出的:“这样一来,我们便把以前没有弄清楚的一个概念,即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状态的概念,提到了首要的地位,用危险状态代替了被禁止的一定行为
的专有概念。换句话说,孤立地来看,所犯的罪行可能比犯这种罪的主体的危险性小。如果不注意主体固有的特性,而对犯这种违法行为的人加以惩罚,就可能是完全虚妄的方法。”(博利斯:《刑罚科学》,1901年英文版,伦敦,第38页。转引自王晨著:《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而并不刻意求证这种恶性、危险性的具体的形成。当然,犯罪人格作为一种评价结果,其也可以用作刑事处置的基础概念。以犯罪人格(包括人格的评价与人格的形成)作为基底之一,刑法理论上也提出了人格责任论。(注:由此犯罪人格从其形成的追溯(犯罪学视角)、评价结论(刑法学视角的起点),又进入到刑法学的领域(犯罪人格在刑事责任中的地位、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人格责任论论是一种折衷主义理论,人格责任是将具有人格性的责任、行为责任与人格形成责任相结合的责任。关于人格责任论详见下文。)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以人身危险性为基底的责任论是社会责任论,其与人格责任亦有明显的区别。社会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行为责任论)针锋相对,认为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是由其本人的素质和环境所决定的。犯罪者一般是对社会实施有害行为的具有危险性格的人,社会必须摆脱具有这种危险性格的人的侵害来保护自己。社会基于保卫自己确定刑事责任的依据。构成责任的不是各个具体的行为,而是对社会造成危险的行为者的性格(性格责任论)。(注:参见〔日〕木村龟二主编,顾肖荣、郑树周等译校:《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2页。)人格责任论属于一种折衷主义理论,人格责任是行为责任、具有人格性的责任与人格形成责任(注:人格形成责任与性格责任是不同的。前者是向行为者对其人格形成施加非难,后者是对社会造成危险的行为者的性格施加非难。)的综合。人格责任论认为犯罪行为并不是自然且必然地暴露了行为者一定的性格,而是行为者根据人格特性,在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条件下,有选择地排除其他可能性而实施的行为,必须首先承认行为本身就是刑事责任的基础,于是就提出了行为者对具体犯罪行为的人格态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格责任论可以认为就是行为责任论;但是,这种行为责任本身也对行为中的人格态度进行理解并作责任判断的,因此它是具有人格性的责任;同时,人格责任论也要求在确立责任时不能只针对行为,也要考虑犯罪行为背后潜在存在着的人格体系,并且行为背后的人格也是在受素质和环境制约的同时独立形成的,
因而在行为者能独立自主地实施某行为的范围内,可向行为者对其人格形成施加非难(人格形成责任论)。(注:参见〔日〕木村龟二主编,前注[48]引,第222页。)
二、人身危险性、行为客观危害与定罪量刑
定罪与量刑、主观与客观是刑法研究中的两对重要的分析轴(注:作为刑法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轴还有:事实与规范、个人与社会、权利与权力等等。)。有鉴于此,我们形成对刑法剖析的四条基本线索:作为客观主义强调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与定罪、量刑;作为主观主义强调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罪过、犯罪人格与定罪、量刑。当代的刑法理论与实践很少有单纯的主观归罪(刑)或客观归罪(刑)。“犯罪构成理论阐述的犯罪构成要件(成分),不同法系各国大体相同,它们有:犯罪行为的结果,犯罪行为侵害的权益,行为的主体,行为时的有罪心态。”(注:储槐植著:《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即使新派所强调的保安处分(注:一般把保安处分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保安处分,是对显然具有犯罪危险性者采取防止其将要实施犯罪的社会措施,对犯罪者代替刑罚适用或作为刑罚的补充而适用,以及由国家执行的一切保护、教育和改善处分。狭义的保安处分,是代替刑罚而适用或者作为刑罚的补充而适用,以现实犯罪的危险性为要件,以剥夺自由的方式,由法院宣判的处分。对刑罚与保安处分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刑罚理论的旧派主倡刑罚与保安处分二元论,新派主倡保安处分一元论,即刑罚与保安处分不加区别。前者是报应刑论,后者是教育刑论。前者是客观主义的行为论,后者是主观主义的行为者论。前者是伦理、正义或道义观念,后者是人格及人格形成责任或社会责任的观念。前者是非决定论,后者是决定论(不排除选择的自由)。前者是绝对观念论和启蒙时期理性人的理念观,后者是观念的辩证法、工业资本时期的理性人的理念观和实证论。保安处分二元论的核心是既成的犯罪行为事实,着眼点是行为者的过去行为事实,客观的犯罪行为是适用刑罚的必然前提,而犯罪须有严密的犯罪构成,又必须与其他行政违法、违警罪等加以区别。但是除既犯者以外,还有将犯或再犯的危险者的存在,同样有破坏社会的安全秩序、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可能,对此不能不考虑采取预防或防止犯罪危险的相应措施,这就须承认保安处分制度的必要性。保安处分一元论的核心是保卫社会论的预防犯罪危险性,其重点是特别预防,但不排除一般预防,着眼于现在的危险性,不受罪刑法定的责任主义的制约。保安处分也好,刑罚也好,特别预防也好,一般预防也好,在保卫国家,保全社会,改善、教育犯罪者,预防和防止犯罪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刑罚与保安处分无须区分。* (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591、639-640页;〔日〕木村龟二主编,顾肖荣、郑树周等译校:《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64-469页),也并非单纯地根据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论处,而是必须要有客观的危害行为。(注:适用保安处分必须有保障个人人身自由的制约,否则难免产生扩大化和侵犯个人自由的恶果。作为这一保证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的一条保证是要有触犯刑罚法规的行为事实。(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等著:《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305页)
在我国刑法中,罪过与行为及其危害结果在定罪、量刑中均有着重要的作用。就罪过而言,罪过是定罪的必备要件,没有罪过就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其犯罪构成的罪过形式、内容都是特定的,不同的罪过形式、内容与犯罪构成的其它要件一起共同决定了罪与非罪(例如过失致人轻伤不构成犯罪,而故意轻伤则构成犯罪,尽管这是自诉案件)、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例如,同样造成被害人重伤的结果,如果行为人主观持杀人的故意,则构成故意杀人未遂;如果行为人主观持伤害的故意则构成故意伤害)。同时罪过也是决定刑罚的一个重要因素。刑法根据不同的罪过形式、内容规定了轻重有别的法定刑。例如,故意杀人的法定刑显然重于过失致人死亡;同样是故意,以伤害的故意而构成的故意伤害罪相对于以盗窃的故意而构成的盗窃罪来说,前者的法定刑重(当然立法中决定法定刑轻重的指标是综合的,不过故意的内容不失为一个方面)。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结果对定罪量刑的意义表现为:(1)在过失犯罪中,将实际造成一定程度的物质性危害结果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例如,构成《刑法》第235条规定的过失致人重伤罪,必须以重伤为前提;构成《刑法》第133条的交通肇事罪,必须以发生重大事故为前提,等等。是否具有一定的物质性危害结果,是区分这些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2)在故意犯罪中,有以下情形:①以发生严重物质性危害结果的可能性,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例如,《刑法》第116条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和第117条规定的破坏交通设施罪,就是以“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破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为构成条件的。这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称之为危险犯。(注: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危险状态,严重的危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与危险犯相对的是实害犯。实害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实际的损害,始构成既遂的犯罪。)②以发生某种特定的物质性危害结果,作为构成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或者适用特定法定刑的条件。前者例如,《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如果没有杀死被害人,就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这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称之为结果犯。(注:结果犯,是指不仅实施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后者例如,《刑法》第260条规定的虐待罪,将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作为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的条件。③对危害结果未作任何规定,只要实施了法律规定的行为就可以构成犯罪。例如,《刑法》第243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这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称之为“行为犯”或“举动犯”。(注:行为犯、举动犯与结果犯相对。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这类犯罪的既遂并不要求造成物质性的和有形的危害结果。举动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犯罪完成和完全符合构成要件,从而构成既遂的犯罪。行为犯与举动犯的不同点在于:举动犯的既遂以着手实行犯罪为标志(因而不存在实行阶段的未遂),而行为犯只有当实行行为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过渡到既遂状态(因而存在实行阶段的未遂)。)④有的犯罪以特定的危害结果作为划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例如,《刑法》第247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罪,如果以肉刑致人伤残的,就要以故意伤害罪从重论处;致人死亡的则以故意杀人罪从重论处。⑤有的犯罪把造成危害结果或者有造成危害结果的严重危险同时写入条文,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例如,《刑法》第332条规定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以“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作为构成此罪的要件。这种犯罪“危险犯”和“实害犯”熔为一体,具有同一的法定刑(司法中在法定刑幅度内实行一定的区别对待)。
罪过与行为及其危害结果对定罪、量刑均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不成问题的,重要的是我们来分析一下,人身危险性在定罪、量刑中有何地位。在这一问题上新派、旧派观点不一,构成了新派、旧派在刑法理论上的分歧焦点之一,并由此辐射到刑法理论的其他方面、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旧派着眼于已然之罪的报应,严格地以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注:这里的犯罪构成指犯罪成立条件(又称概念构成要件、总则要件),即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就刑罚与保安处分二元论来说,刑罚以犯罪为对象,犯罪是具备构成要件该当、违法与有责之行为,仅系构成要件该当与违法之行为,尚不得成为可罚之对象。构成要件该当违法之行为,属于所谓广义之犯罪,乃赋科保安处分之对象,不得成为赋科刑罚之对象。参见蔡墩铭著:《刑法总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77、283页。)作为适用刑罚的依据,而对于危害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有显著人身危险性者适用保安处分(刑罚与保安处分二元论);新派着眼于未然之罪的预防,侧重于危害行为所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适用刑罚、保安处分(刑罚与保安处分一元论)。(注:一般把保安处分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对刑罚与保安处分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详见前注[53]。)前苏联学者В·Н·库德里亚夫采夫强调,犯罪构成(注:В·Н·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犯罪构成包括表述犯罪四个相应要素(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四组要件(“要素”表示犯罪的四个组成部分,“要件”表述犯罪构成的内容)。这是犯罪构成的结构基础。然而,仅限于这一点是不够的。犯罪构成的结构还由它的几组更小的要件组成。这几组要件综合表示犯罪构成的个别要件,而这些要件是各罪或很多罪所特有的。这不是内容丰富的要件本身,而是它们的类别或级别。参见В·Н·库德里亚夫采夫著,李益前译:《定罪通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88-90页。)是定罪的必要和充分的要件系统。所谓必要,即在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中,缺少任何一个要件,行为人就不能被指控为犯罪,亦不负刑事责任;所谓充分,即在对有关行为人指控其犯罪时,没有必要查明任何补充材料。(注:参见库德里亚夫采夫,前引第71页。)我国有的学者认为,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是定罪的标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首先表现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辩证统一;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还表现为犯罪构成要件上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注:参见苗生
明著:《定罪机制导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3页。)也有学者认为,主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因素对定罪不发生作用的观点是不妥当的。不但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因素,如犯罪的故意等,体现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而且一般情况下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体现了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因素,如一贯表现、事后态度等,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影响犯罪构成要件,从而对定罪发生作用。(注:参见王勇著:《定罪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就我国刑法的实然规定来讲,人身危险性是影响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是酌定情节,也可以是法定情节,前者例如前科,后者例如立功(我国《刑法》第68条第1款规定:“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以是应当情节,也可以是可以情节,前者例如累犯(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后者例如自首(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人身危险性对定罪以及某些特殊情况下的刑事处置的影响。单凭人身危险性,而没有危害行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行为人治罪的。即使是倾向于主观主义的刑法,对具有人身危险性者适用保安处分,也必须首先有危害行为的表现。(注:参见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等著:《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305页)而我国平面整合的静态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不仅是对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描述,而且也囊括了在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成立要件中作为责任要素的故意过失、责任能力(注: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因此,在我国刑法中,行为必须首先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才可入罪受罚。另一方面,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人身危险性并非犯罪构成因素,犯罪构成因素不能充分反映人身危险性,而人身危险性也不只通过犯罪构成的因素体现。(注:详见本文第一部分“人身危险性与行为客观危害的基本观念”的论述。)所以,人身危险性对定罪以及某些特殊情况下的刑事处置的影响,主要在于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1)倘若行为具有一定的客观危害,并且行为人具有相当的人身危险性,但是行为并未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或者客观危害并未达到法定的定量标准,或者行为主体有一定的精神障碍,或者因为主体的年龄等其它情由),对于这些人应当如何处置?(2)倘若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但是其具有的人身危险性显著
轻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根据行为人显著轻微的人身危险性而作非罪处理?通常,这两个问题在西方刑法中可以得到较好的处理。因为“总的说来,具体犯罪定义在外国刑事立法中至今基本上仍停留在定性认识阶段,数量大小和情节轻重一般都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注: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而犯罪的定量则留待司法掌握,所以司法人员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注:当然自由裁量权也会发生异化,即违背法的精神或者放纵罪犯或者追究无辜。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就涉及到法律的文化背景了。黑格尔认为,法律决定于一国人民的特殊民族性,它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属于自然必然性的一切情况的联系。在有着法治传统的西方,在民主与法治成为其主流文化的时候,对犯罪与否由立法定性司法定量,赋予司法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或许是顺理成章的做法。而我国正处于法治建设之中,封建专制思想有着浓重的影响,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来推进我国民主法治主流文化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刑法的客观主义,增强立法的明确性、确定性,适当地控制司法自由裁量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否认需要将危害行为所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处断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这正如旧派也不否认对具有人身危险性者处以保安处分一样。),同时,反映定罪过程的犯罪成立要件的三元模式以及将保安处分作为与刑罚并列的一种刑事处置,就使得在刑法的实际运作中,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实际情况,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酌情作出处理。与此不同,我国刑法立法既定性又定量,并且这次97年《刑法》又向客观主义倾斜(注:参见张明楷:《新刑法与客观主义》,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第98页。),立法与司法的僵硬,以及单一的刑罚体系,就使得在出现上述两方面情况时,实际处理的结果与刑法的功能(注:主要表现为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刑罚的目的(注:通常认为,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特殊预防。)不利。对于第1种情况,由于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司法上不予治罪,但是这种人人身危险性大且已有危害社会的行为表现,放之社会不利于保护社会。对于第2种情况,由于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并且加上对《刑法》理解的偏差(注:倘若正确地理解我国《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这第2个问题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应当是可以解决的。下文详述。),司法上一般均予治罪,但是这种人人身危险性* 显著轻微,被贴上了犯罪人的标签不利于其继续社会化,“获释犯人的处境必然使他们成为累犯。”(注:〔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1页。)同时对其收监也极易使其进一步感染,这显然有损于特殊预防。“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注:福柯这里所言的过失犯是指因恶劣环境或性格缺陷而有犯罪倾向的人,也指屡教不改的习惯性犯罪者。)。这是它强加给囚犯的生存状态所决定的。”“福歇把监狱称作‘犯罪兵营’。”(注:〔法〕米歇尔·福柯著,前注[73]引,第300、301页。)并且对人身危险性显著轻微的人实施刑罚也无助于一般预防。可见,僵硬的法律同样会带来弊端。
笔者认为,对于问题1中的行为人,尽管不处以刑罚,但是应当施以一定的保安处分。这就涉及到我国刑法理论研究方向转变,刑事政策内涵的深化和刑事立法的完善。(1)就刑法理论研究方向的转变而言,我们应当加强刑事责任(尤其是作为折衷主义责任论的人格责任论、规范责任论)、再犯预测、犯罪学等的研究。刑事责任问题是刑法理论的聚焦。刑法究其根本是要公正、合理地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前提是罪,而罪有主观之罪和客观之罪。针对主观之罪与客观之罪对刑事责任决定程度的不同,形成了诸多刑事责任的理论。在刑法史中,近代以前盛行的是结果责任和团体责任(注:结果责任,即制定和适用刑法的人,更多地注重犯罪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并根据这种结果的危害程度来决定刑罚,而很少考虑犯罪时的具体情况和犯罪人是否有罪过,主张带有团体主义色彩以绝对的报应刑体现惩罚的正义。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严格地以结果论责任;机械地实行对等报应;长期实行株连责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参见张智辉著:《刑事责任通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6页。);旧派在抨击封建罪刑擅断的过程中,开创了近代刑法科学,提出了道义责任论(注:道义责任论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存在于道义上的非难可能性中。该理论以意思论作为前提,认为具有自由意思的人虽然可按其自由意思实施合法行为,但结果导致违法行为时,就有道义上非难的可能性。参见〔日〕木村龟二主编,顾肖荣、郑树周等译:《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1页。);新派与旧派针锋相对,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以犯罪人为本位,提出了社会责任论(注:社会责任论的思想基础是哲学上的决定论,即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外界环境和本人素质等因素制约的,因而人的意志并不自由。社会责任论的基本点是,刑法上的责任不应着眼于个人的道义观念,而应以社会价值为根据;国家基于保卫社会的责任,对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和对社会有危险性的人适用刑罚(社会保卫方法),目的是使犯人适合社会生活,不再侵害社会。参见杨春洗、高铭暄、马克昌、余叔通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页;张文、苗生明、刘生荣、李卫红著:《刑事责任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各持一端,难免偏颇,于是在扬弃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的基础上结合这两种理论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规范责任论(注:规范责任论首先由德国学者麦耶(
M.E.Mayer)在1901年提及,后由德国学者弗兰克(R.Frank)倡导,并由高登修密特(Goldschmidt)、弗洛依登海尔(Freudenhal)、多纳(Dohna)、施密特(E.Schmidt)以及麦兹格(Mezger)等人加以发展,是当今西方刑法学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责任理论。规范责任论认为,责任的本质属性是从规范的角度对事实加以非难的可能性,即行为人违反了关于不该作出违法行为决意的法律上意思决定的规范要求,亦即违反应为规范和义务规范,而决定实施违法行为。规范责任论是站在道义责任论的立场上对道义责任论进行的修正。道义责任论也是把责任理解为非难的,但是道义责任论认为只要存在责任能力这种生物学因素和故意或过失这种心理学因素,就可以予以非难。而规范责任论则认为即使存在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如果不存在实施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这种规范因素,也不能非难行为人。参见王晨著:《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人格责任论(注:人格责任论是在麦兹格提出构成责任的是可以用以非难行为者品行的品行责任的理论以后,由日本的安平博士、团藤教授、井上教授等接受了麦兹格的行为责任论和卜凯尔的刑事责任的本质存在于对犯罪倾向有决定性作用的“生活决定”之中的理论启示而提出的新的责任理论。该理论认为,责任的基础不仅仅是具体的行动,而且是行为者内在的人格;犯罪行为是行为者人格的具体化,并且也是主体的具体化。行为责任与形成人格责任虽有显著的区别,然而在活生生的现实上,两者可谓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格责任论最大的特点是综合了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吸取了两者合理的因素,同时试图克服两者的不足。参见〔日〕木村龟二主编,顾肖荣、郑树周等译:《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2页;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等折衷主义责任论。在对行为人的刑法处置中应当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而这一理论命题得以转化为现实的当然前提是存在着一定的方法可以具体地测定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这就涉及到再犯预测研究。再犯预测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科学的方法,探求得用以预测犯罪人将来陷于再犯危险性之有无及其程度之客观而有效的工具(再犯预测表),可供司法当局量刑上(判决时预测)及执行当局决定处遇方针及选择假释者上(释放时预测)之重要参考。同时,在抗制犯罪上事先的预防恒胜于事* 后之处理,探讨犯罪人出狱后又再犯者,在其个人及社会经历上与出狱后未再犯者间之差异、其陷于再犯或未再犯之重要原因及再犯危险性之有无及程度等问题,俾事先采取社会保安上、教育上、矫治上之必要措施以防患于未然。(注:参见〔台〕张甘妹等:《再犯预测之研究》,法务通讯杂志社1987年版,第2页。)再犯预测是我国刑法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犯罪学是揭示犯罪本质,依据犯罪现象,探索犯罪原因,寻求犯罪对策的科学。刑事新派的掘起与犯罪学的诞生相伴,犯罪学将研究的中心由犯罪行为转向犯罪人,从探寻事(犯罪)后的合理惩罚到致力于事前的有效预防,因此犯罪学也可以表述为研究犯罪人的形成机理(微观上回答一个人为什么犯罪)、社会犯罪现象的形成机理(宏观上回答社会为什么存在犯罪),以求犯罪对策的科学。犯罪学标志着刑事法学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是一种变被动为主动的思维模式。犯罪学是刑法学的基础学科。我国的犯罪学研究还未深入到一定的理论层次。(2)就刑事政策内涵的深化而言,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略。刑事政策探求犯罪控制(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理想模式(理想的结构和理想的运行机制以及理想的效果),由此出现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潮流。刑事政策不仅研究刑罚而且研究非刑罚处遇方法,这是刑法学所不及的。(注:参见杨春洗主编:《刑事政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12-14页。)在我国早就形成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等刑事政策,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也发生着嬗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倘若考虑到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定罪中的作用,那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等刑事政策又应表现为哪些内容?如何发展、创新我国的刑事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司法的生命、灵魂。(3)就刑事立法的完善而言,涉及到我国是否需要保安处分,我国目前是否存在保安处分,我国应当构建何种保安处分等问题。现实中,行为人具有相当的人身危险性但又不宜对之刑罚处罚的情况是存在的,对于这些人不能放任不管,否则既有失于公正也不利于功利。在我国刑法中设置保安处分有其必然性。尽管我国刑法界对这一问题仍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注: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保安处分之名(《刑法》上更无保安处分之说),但是我国《刑法》和行政法上业
已存在一定的具有保安处分部分功能的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①劳动教养,适用对象包括:其一,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其二,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其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其四,不服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注: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②收容教养,针对不满16周岁不处罚的未成年人。(注:《刑法》第17条第4款的规定。)③强制医疗,适用对象包括:精神病人(注:《刑法》第18条第1款的规定。)和患有性病的卖淫、嫖娼者(注: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第4款的规定。根据《刑法》附件2的规定,虽然该决定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纳入《刑法》,但是其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④强制戒除,适用于吸食、注射毒品成瘾者。(注: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第8条的规定。根据《刑法》附件2的规定,虽然该决定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纳入《刑法》,但是其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⑤没收财物,针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注:《刑法》第64条的规定。)对于这些措施,有的学者认为其类似于西方保安处分,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注:参见苗有水:“保安处分理论及我国保安措施刑事立法化”,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应当说,我国预防犯罪的一些措施与国外的保安处分之间有着较大的距离。例如,国外保安处分一般只能由法官、检察官或特定的裁判官宣告,而我国预防犯罪的这些措施多数由一般行政执法人员掌握其适用权(即使是《刑法》上的有关条款,也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其处理规范均转至行政措施之中,最终须在行政法规上找到操作依据)。(注:同上书,第320页。)由行政机关在缺乏明确、统一、严谨的程序的前提下,对公民施以剥夺或限制自由,显失公正与法治。现实中对处置问题1中行为人的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和不完善,决定了我们应当将保安处分统一规范至《刑法》中。(注:我国《刑法
》第37条规定的非刑处分与保安处分有着明确的区别,前者适用的前提是行为构成犯罪,而后者适用的前提(保安处分二元论)是行为不完全充足犯罪成立要件,但行为人的行为表现出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当然,根据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状况,我国不宜实行保安处分一元论,而应采纳保安处分二元论的观点。
对于问题2中的行为人的处置,笔者认为,从我国《刑法》第13条的但书中可以找到答案。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1)社会危害性的内涵;(2)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的关系。(1)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含义,刑法界主要存在如下几种观点:事实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在客观上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法益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对刑法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的侵犯或破坏;属性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因为行为人侵犯了刑事法律规范而给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带来危害的行为属性。(注:参见青锋著:《犯罪本质研究——罪与非罪界说新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5页。)笔者认为,就《刑法》第13条的表述来看,对社会危害性的理解,关键在“(社会)危害”,因为本条强调的是危害,但书的表述也是危害(注:“危害”与“危害结果”是两个概念。)。这个危害应当是包括主观与客观的综合指标。其中主观包括:恶过、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客观包括: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等。社会危害是主观危害与客观危害的有机统一。(2)关于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的关系,我国刑法界有不同的观点。(注:樊文,前注[11]引;李立众、李晓龙,前注[12]引。)笔者认为,《刑法》第13条社会危害性的规定就局部来说其具有笼统、原则的成分,但是就第13条以及《刑法》整体来讲它是确定的,《刑法》第13条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矛盾。具体说明如下:之所以说《刑法》第13条社会危害性的规定似乎有笼统、原则的成分,这是因为《刑法》第13条但书之前的犯罪界定是一种宣言式的命题。但是,这种笼统、原则的宣言并不影响《刑法》第13条整体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结合,构成了社会危害的明确内涵,也就是说《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使第13条社会危害含义明确化。说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既然罪刑法定已将社会危害性明确化,那么为什么又要作第13条这么一个规定,这岂非多此一举,而且说不定还会引起理解上的歧义。笔者认为,答案就在为《刑法》第13条的功能,这一功能也正体现了《刑法》规定第13条的立法妙处(注:或许立法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一意义是客观存在的,这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立法的动机有时连立法者本身也未必能说清楚。)。从《刑法》第13条的功能来说,假如说1979年《刑法》规定第10条为当时《刑法》所保留的类推提供了入罪的依据的话,那么在1997年《刑法》取消类推而实行彻底的罪刑法定的今天,《刑法》(注:倘若没有特别说明的话,本文中的《刑法》均指
1997年《刑法》。)的第13条决不是再为类推的适用而存在,而是有着其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特定功能,这个特定的功能就是起排除犯罪的作用(限制功能),具体表现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是犯罪。”但书应当有其前提,因此《刑法》第13条作为整体的存在有其必要性。由于功能的不同,因此同样是但书,其所表示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刑法界通常认为,1979年《刑法》第10条的但书是对前段的补充,“是从什么情况下不认为犯罪的角度,来补充说明什么是犯罪。”(注: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其着眼于入罪,为类推服务。与此不同,1997年《刑法》第13条的但书是前段例外,强调对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犯罪处理。其着眼于出罪,为罪刑法定服务。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意义是保障人权,《刑法》第13条之规定的出罪功能(限制功能)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矛盾,在理论上对《刑法》第13条作这一解释完全恰当;就司法实际来讲,它也解决了本文上述问题2的情况:倘若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但是其人身危险性显著轻微,而人身危险性也是社会危害内容的一个方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对其作非罪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