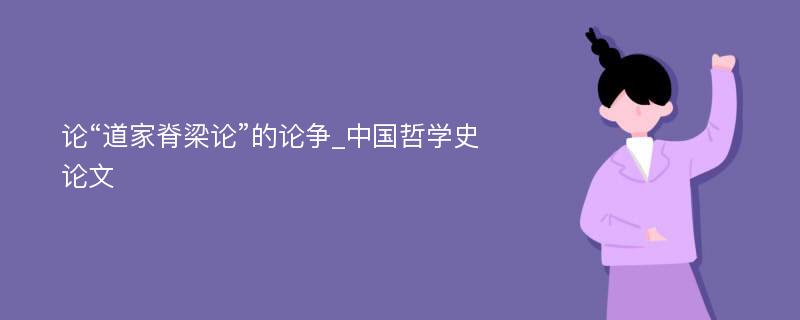
围绕“道家主干说”争论的述与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家论文,主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1001—5124 (2000)01—0060—07
显然,既曰“主”,就有“次”,主干的确立应在多元的格局中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史向来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这造成了多元格局,使确立主干成为可能。我国最早概括的多元格局是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这一学术局面的,如《庄子·天下篇》的“百家之学”,《荀子·非十二子》的“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篇》的“十人”,《韩非子·显学篇》的儒墨显学,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中的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其中司马谈概括的六家全面而精辟,因此得到后代学者的认同。他们不仅用它来概括先秦学术史,而且用它来分析秦汉以来文化辐射、流徙、涵化、融合的情况。主干研究正是这种表现之一。
以司马谈确立的六家格局为前提,目前大陆学界在主干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道家主干、儒家主干、儒道主干三种最根本的看法。其中道家主干说最早揭橥而出,儒家主干说随后标帜对峙,儒道主干说再后另立一方。以下就对这一情况作一简单回顾。
道家本是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很久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研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基本被忽略。50~60年代虽然出现过两度关于道家的讨论热,但由于当时过分纠缠于“唯物”与“唯心”的争论,基本上没有探讨道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等大量道家文献后,在海内外掀起了道家研究的高潮。特别是1985年11月举行的全国首次老子思想学术讨论会,更将道家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逐渐感到学界对道家的不公,于是提出了“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的观点,这就是道家主干说的揭竿。此说提出后,将学界普遍以儒家为传统文化代表的观点指斥为“儒家主干说”,一些学者站在儒家的立场自觉承袭了这一说法,这样便产生了儒家主干说。由此可见,是道家主干说的先出促成了儒家主干说的标帜,虽然儒家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早已不言而喻。当然,诚如陈静先生所言,儒道主干说是“调和主义”,[1]但可以肯定的是, 儒道主干说确实后出。
正由于道家主干说先发制人,有关主干问题的争论,儒家主干说、儒道主干说颇显被动,表现在:都是在驳斥道家主干说的基础上立论,对自己的立论正面阐述不够,而且总是跟着陈鼓应先生的学术方向转(他虽不是道家主干说的最早提出者,却是此说的主将),不能离开陈先生拓开的学术视野。一言以蔽之,是围绕道家主干说的争论。这一争论从1986年开始,至今已持续十余年。虽然各说还有尚待商榷的地方,但是它们的争论却直接激发了传统文化、哲学史的研究,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反思。下面拟就这一争论的来龙去脉作一述评。
一、道家主干说的提出
道家主干说的提出与两篇文章有关,一是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周玉燕等人的《试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2] 一是北京大学陈鼓应教授的《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3] 这两篇文章虽然前提不一样,但主旨相同,思维路向也大体一致,都是根据“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是形上学与知识论”这两方面来论证道家为主干的。
在从形上学角度论证时,周文指出,“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首先表现为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框架”,并称之为“道家模式”。其特征是:道家抽象出了一个新的、高于一切范畴的“道”,不仅把自然作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对象来理解,而且把人类作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置于这一整体之中,从而形成了从道出发建立封建政治理论体系的“中国哲学致思的传统趋向”。“董仲舒的‘天人比附’,魏晋的‘名教出于自然’,宋明的‘天理’、‘人欲’之辨,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道’的范畴来论证”。因此周文得出结论道:“中国传统文化从表层结构看,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伦理学说,从深层结构看,则是道家的哲学框架。”在论证中,周文已间接涉及道家的创生作用及“道家模式”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这两点。而陈文对此论证得更为明确。首先,指出“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形上学体系”。其次,在阐述道家对中国哲学史每一重要阶段的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指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道家。即使某些体系因其伦理道德方面明显的儒家倾向而被学者们视为属于儒家的,如《易传》学派及宋明理学,但构成其伦理道德学说基础的理论构架、思维方式等仍然是由道家所确立的。”可见,陈文同周文一样,认为道家之所以是主干,就在于道家提出了一个“理论构架、思维方式”。
从文献上看,周文虽首先提出了道家主干说的观点,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回应,而在陈文发表后,随即掀起了一场关于主干的大讨论。
二、围绕道家主干说争论的两个问题
有关道家主干说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这一命题本身的争论,其次是涉及有关经典归属问题的争论。
1、道家是不是“主干”。自陈文发表后,1990~1994年间,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李存山和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吉惠分别发表《道家“主干地位”说献疑》、[4]《重新确认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5]《论儒道互补的中国文化主体结构与格局》,[6] 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第一阶段的讨论。
李文、赵文都既不赞成儒家主干说,也不赞成道家主干说,并主要从三方面驳斥道家主干说。一是驳斥周文的哲学是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观点。李文认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应是指这个民族被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某种价值取向、‘思维的心理定势’等等;哲学并不能简单地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深层结构,而应该说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势的强化或规范化。”因此周文缺少文化学的理论依据。二是驳斥陈文的哲学主流是形上学与认识论的观点。李文就陈文也并不否认孔子的政治道德说教具有哲学意义这点指出,如果说这种思想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话,那么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就在于他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人学主题。两文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不应以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是形上学与知识论为标准来判断儒道两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三是驳斥两篇文章将所谓“框架”派归道家的观点。李文认为“探讨是儒家还是道家在中国传统哲学或文化中占有‘主干地位’,不是探讨哪家首先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哲学框架,而是探讨哪家主要影响或决定了这一框架的发展和特殊性质。”显然,李文认为使儒家之成为儒家、道家之成为道家的东西不是框架,而是充实框架的内容。认为区分儒家和道家应看它“如何解释‘天道’、‘人道’及其关系”。同样,区分哪家为主干也应从此考察。否则,以框架来辨别儒道,“不仅程朱而且孔子以下千古无真儒了”。赵文从同样的意见出发,得出了中国文化是以儒道为主体的结论。
2、《易传》是否属于道家著作。 当陈文把周文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改为“中国哲学史”时,关于谁是主干的争论实际上就成了《易传》问题的争论。《易传》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哲学著作,它的归属对决定谁是主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一直被认为是儒家著作。因此,自1989年起,陈先生发表《〈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乃道家系统之作》、[7] 《〈易传·系辞〉所受庄子思想的影响》,[8]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吕绍纲和李存山随即反应, 发表《〈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兼与陈鼓应先生商榷》、[9]《道家“主干地位”说献疑》, 陈先生又作《对两篇商榷文章的答复》,[10]对《易传》的归属展开了第一次争锋。
首先,陈文指出:“就严格哲学观点而言”,即从天道观和辩证法思想两方面看,“《易传·系辞》是较近于道家系统的著作”,而这两方面在孔子那里是一个空白。对此,吕文首先不赞成撇开《易传》中的政治伦理学说而仅从自然观和辩证法两方面来断定《易传》归属的做法。其次,指出孔子和《易大传》的讲变讲动都是讲的时变,而老子虽然也讲变讲动,但由于“弱者道之用”这个命题,从总体上看有僵化之势。因此,《易传》和孔子在“严格哲学观点”上也有一致之处,而“在辩证法这两个体系最容易接近的领域里,《易大传》与《老子》却相去甚远。”
其次,陈文采用概念、文句的比较方法从十三个方面论述了《系辞》在自然观方面与道家的一脉相承。对此,吕文反驳说:陈先生“只是在哲学范畴、概念和命题上将《易大传》与老子思想做了一般性的直接对比,指出他们的某些表面的相似之处,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吕、李文主张从概念与命题的关系入手,认为“谁采用谁一个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它们用这个词构成了怎样的命题。”“虽然用词有时候很相似,可是体系却是极不同的。”他们在对陈文列举的第一、七、八、十二方面(即天动地静说、阴阳说、太极说、道德概念)进行质疑后,得出结论:“《易大传》在天道观上与《老子》根本对立。”
以上是有关《易传》归属的直接争锋,在这同时还有两文间接参与进来,提出了第三种看法。这就是王德有的《易入儒道简论》,[11]余敦康的《〈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一个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12]两人的观点建立在《经》、《传》区分的基础之上。认为《经》到春秋已最后完成,而《传》直到战国中后期才完成,它是战国末年学术大融合的产物,是道家与儒家的有机结合。
1992年5月湖南出版社出版了《马王堆汉墓文化》一书, 书中收有先前未公布的帛书《系辞》的照片,与今本不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今本《系辞上》“大衍之数”章,既不见于帛本《系辞》亦不见于《易之义》、《要》;二是今本《系辞下》第五章自“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至第十一章,它们基本不见于帛本《系辞》,而散见于《易之义》和《要》。于是这又引起《易传》归属的第二次争锋。
陈先生先后发表《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13]《也谈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14]《帛书〈系传〉与今本〈系辞〉——再论帛书〈系传〉为道家之传本》,[15]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发表《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1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葆玹发表《〈系辞〉帛书本与通行本的关系及其学派问题——兼答廖名春先生》,[17]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今本《系辞》不见于帛本《系辞》的内容是原有的还是后加的?在帛本《系辞》之前有没有一个更古的祖本?今本《系辞》不见于帛本而见于佚书《易之义》、《要》的文字与祖本、今本《系辞》是什么关系?帛本《系辞》是什么性质?
其中,对于至为关键的第四个问题,廖文指出帛本《系辞》由非“子曰”部分与“子曰”部分组成,“前者是后者的推阐和发挥,后者是前者立论之所从出”,从而认定“帛书《系辞》不可能是道家的传本,只能是儒家之说。”陈文和王文则认为“子曰”指经师之言。退一步讲,即便就是指孔子语,也只是依托,坚持帛本《系辞》属道。陈、王文还提出了三方面的论据:一、帛本《系辞》的周易创兴说是上古伏羲作八卦,神农重卦,黄帝尧舜完成,正属道家古史系统。而今本的周易创兴说,显系儒家古史系统。二、从春秋时起,就形成了儒道解易的不同倾向和派别,而且《史记》所载传易诸子大多是齐楚人,而当时道家正盛行于齐楚,因此出现道家传本的帛本《系辞》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三、帛本《系传》重“始”、重“初”,而今本很多重“中”的文句,“始”与“中”正是道儒的分际,帛本属道无疑。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面几个问题的争论中,道家主干说作了大量详实的概念、文句比较工作,这主要是帛本《系传》和老庄的比较,但其中亦涉及到和稷下黄老的比较。对于稷下和黄老是否归属道家学界尚存疑问,但道家主干说派却非常肯定,并在这个基础上间接论证《易传》、帛本《系辞》与稷下黄老的关系,进一步论证它们的属道性质。如《〈易传·系辞〉思想与道家黄老之学相通》、[18]《〈易传〉与楚学齐学》、[19]《论〈系辞〉是稷下道家之作》、[20]《帛书〈系辞〉和帛书〈黄帝四经〉》。[21]
在以上两次交锋的同时,陈先生还陆续发表了《〈彖传〉与老庄》、[22]《〈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23]《〈象传〉中的道家思维方式》、[24]《〈文言〉解〈易〉的道家倾向》,[25]对《系辞》外其它篇的属道性质进行补充性的更深入的论证,仍是采用概念、文句的比较方法。
三、道家主干说讨论的深入
1994年11月在四川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的“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上,陈先生再次申明了他的观点:儒家思想是文化的主流,而在专业哲学的领域,则道家充当着主干。与最初提出道家主干说相比,陈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26]一文中。此文与陈先生揭橥而出的那篇文章比较,有三处突出的方面:
一、以前采用的是韦伯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对自然界的全部的研究,是期望对事物作一个普遍性的解释。”现采用文德尔班的哲学观,认为“哲学乃是对宇宙观、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这样明确将儒学作为人生哲学囊括进哲学的范围,但陈文得出的结论仍然未变:“就宇宙论和辩证思维方法而论,道家主干说当无疑义,至于人生哲学则孔孟思想之远逊于老庄,自不待言。”
二、从创生决定归属的逻辑出发,说明道家“开启了中国特殊形态的人生哲学”,这是基于文德尔班哲学观,对道家开创中国形上学传统的补充。中国人生哲学的主要方面是内圣外王,作者循着老子——黄老——庄子这一线索,理出了它们各自的内圣外王之道,认为是它们建构了中国人生哲学的内圣外王模式,并影响了之后中国思想发展的三个高峰:魏晋玄学,隋唐之华严与禅宗,宋明之理学,无疑这比以前更全面了。
三、早期儒家也有对哲学问题的关注(从西方哲学主体——形上学与知识论而言),这是道家主干说的反方提出的,亦是陈先生承认的。但陈先生通过概念、文句比较认为这些都是道家稷下黄老的影响,他认为这始于战国中期之后,包括《孟》、《荀》、《学》、《庸》。这样儒家创生哲学的一点可能也没有了。无疑,这观点又比以前更彻底深入了。
显然,陈先生观点的变化和论题的深入,是吸取了对方意见的结果。
总观以上争论,当我们分阶段阅历争论焦点的转移和观点的深入时,我们发现有些问题已在争论中得到解决,而有些问题却越来越分明地横在我们面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文化与哲学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文化的界定仍然没有统一,但随着文化的广泛和深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要素归类和层次划分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独辟蹊径,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区分文化的范围和层次,更全面深入地揭示了文化的现象和本质。[27]他们针对一般人将文化误为文化物的不自觉理解,明确指出文化不是文化物。一般人谈到文化时,总会想到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然而严格地说,那是文化物,不是文化。文化物对于人本质上是外在的,可以把握;而文化之与人,如如来佛的手掌与孙悟空,无法摆脱也不可捉摸,它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人在文化中衣食住行,人在文化中言行举止,甚至在文化中继承以及反叛某种文化。这使人面对一种无法逃避的尴尬境界:人实际上无法将文化作为对象性的东西,即作为文化物来占有及失去,不能象对待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那样,这就是文化的本体论维度。一切将文化作为对象来捕捉的理解和解释,是文化的认识论维度。显然作为将文化对象化后的产物,儒家和道家学说同处认识论维度,不能将它们分割异置。周文将它们一个视为表层结构,一个作为深层结构,缺少文化学理论依据。
其次,哲学史观的问题。由于是在中国哲学史中确立主干,因此何为哲学对于谁为主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由于对哲学的不同界定,整个争论中就出现了儒家主干、道家主干、儒道主干三种说法。但是不管如何界定哲学,一个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经过界定的中国哲学史起码是应包括儒道在内的发展史,否则主干的确立将变得毫无意义。这就要求争论双方在对哲学进行界定时,不应立足于西方哲学,从中国哲学寻求共通点,而应立足于中国哲学,以反映中国哲学的多元格局。对于这点,道家主干说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起初,陈先生认同韦伯的哲学观,自西方哲学观点视之,非常看重道家宇宙论、辩证法等思辨内容,而简单把儒学等同于政治伦理思想。这固然纠正了以儒家一统中国哲学天下的弊端,但也在无意中将儒家排斥在哲学大门之外,从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使中哲史成为道家一家的发展史。在《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中,陈先生转而认同文德尔班的哲学观,并强调“中国哲学则更多地把宇宙看成人生的背景,主要通过对现实人生的系统反思,建立一种系统的人生哲学。”“一种流行的观点以为,道家偏重天道观,实际情况正相反。道家虽在宇宙中思考,却仍然落实到人生中来。”显然,陈先生企图用文德尔班包容了中西哲学特质的哲学观,以人生哲学的形式将从后门赶跑的儒家再从前门重新请进哲学殿堂,使之得以和道家一起并立于中国哲学史。虽然陈先生最后还是得出了道家主干的结论,但我们可以肯定,哲学史观的转变使他的结论更合理更有据。
第三,创生与归属的问题。道家主干说首先把道家首次使用的概念、范畴、理论构架、思维方式等都归为道家,然后再以此称衡其它学派和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从他们的论证中可以看出,创生包括模式和概念的创生,创生即意味着产权。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一点是文化的传统性。动物由于没有经验的积累,每一代的起点都是零。而人类就不同,由于文化的代代相传和整合,后代总是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这个起点就是每一代所处的文化背景。哲学解释学对文化传统的过程揭示得非常深刻,[28]认为能够使文化传统实现的是语言(包括身体语言、概念语言等各种形式的语言)。人必降生并生活于某种文化背景中,他必须接受某种文化的语言,由语言来理解和解释他所处的文化背景,在他接受并理解语言的同时,文化背景通过语言进入他的生活与存在,在文化背景被通过语言理解并接受时,文化背景又获得了新生和发展。因此,从文化传统性看,一种模式和概念被创生后,就被传统为人类文化背景,它面临着被人挑选并走上前来的可能,人生活在文化传统中,他并不总是创建新的模式和概念,他很容易接受某种模式和概念,而当某种模式和概念被接受后,它并不是一成不变,因为人赋予了它新的理解。因此,正如李存山指出的,使道家、儒家成为它们本身的不是模式,而是模式的内容。也正如吕绍纲指出的,概念的相同并不能绝对说明什么,关键要看作者在思想体系中赋予了它什么样的理解。一言以蔽之,模式、概念的创生并不意味着产权,决定产权的是模式的内容,概念的理解。
道家主干说认为道家模式首先是天道推衍人道,它影响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因而道家是哲学史的主干。可是如果我们把天道推衍人道放到天人合一中考察,我们会发现,天道推衍人道只是天人合一中的一个环节,为儒、道所共有。只是由于对人生安顿的途径不同,前者更喜好人道,后者更喜好天道。长期以来学界以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哲学最大、最基本的思维模式来分析中国哲学,并以“蔽于人而不知天”和“蔽于天而不知人”将儒、道对立起来,无疑这对把握中国哲学特质及儒、道性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常常以定论的形式把我们带进了凝固静止的误区,好象天人合一就只有以人合天或以天合人的一个环节,天就是纯自然之天,人就是纯孤立之人。其实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考察,儒、道的天人合一都是两方面的不断循环往复。一方面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一方面又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在这个过程中天不再是纯自然之天,而变成了人化之天,人不再是纯孤立之人,而变成了天赋之人。因为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就必须从人道中寻找出合乎理想的人文精神,而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也必须从天道中寻找出合乎需要的自然根据。结果在两方面作用的影响下,天道被赋予了人文的精神,而人道被赋予了自然的根据。从中国哲学的特质看,儒、道的天人合一至少包括以人塑天和以天推人两个环节。中国哲学的特质表现在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上,安顿人生是儒、道的最终目的也是出发点。从此出发,必须以人塑天,以此为的,又必须以天推人。因此以人塑天、以天推人并不为儒、道分别独有。道家的以天推人是以人塑天的继续,而儒家的以人塑天是为了以天推人,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的价值取向获得根据和信念。老子说天道即是柔弱、虚静、处下、不争、无为等等,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同样孔子重人事的务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兢兢业业,都可从天那里觅得启示和支持。“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天道推衍人道不是孔子、老子分立的根据,儒、道的分立首先是人生安顿的分立。
另外,道家主干说大量采用概念、文句的比较手法来说明各学说间的承袭和影响,并判断它们的归属,这使我在钦佩的同时又不禁疑惑。中国传统哲学一直以解经、注经的形式进行和发展。我想,如果在宋明理学中寻找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创生的概念、命题,其数量一定比道家多得多,因此无论如何得不出宋明理学以道家为主干的结论。有人说哲学是门“关于不可解决的问题的艺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概念、文句比较方法的局限。许多问题自从被提出的时刻起便与人类共存。不同时代哲学家面临同一问题,虽然答案不一致,但是所用概念、范畴、框架却可能一致。因为用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框架并不完全由哲学家主观决定,它还由问题本身客观决定。
第四,主干确立范围的问题。在有关主干问题的争论中,曾经出现“主流”一词,主流与主干似属同一层次,但仔细分辨,实有优劣之分。“主干”是借枝干在一棵树上的位置来比拟六家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从静态的角度讲,这是适当的。然而,一棵树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先有主干,然后有枝干,然后才有枝叶的茂盛,它的生长是一个由一到多的增长过程;与此相反,中国哲学史的发生发展却是一个由多到一的消融过程。因此,从动态的角度讲,“主干”的比拟是不恰当的。而“主流”不仅能突出各家在传统文化、哲学史中所处地位的层次,而且还能反映各家在哲学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的历程,比“主干”更确切适当。
既然如此,我们暂且用主流代替主干,但是有关主干研究的思维路向在主流这里是否仍然适当呢?主干研究是从司马谈确立的六家格局中选取一两家作为整个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这是极不合理的。因为中国哲学史发展到后来,随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内容越来越丰富,范围越来越庞杂,成分越来越不能为六家所包含。而且先前的诸子百家在显与隐中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嬗变,在不停地被理解和运用中模糊了自己的分际和面目。因此,如果仍从儒道等六家挑选主干而不纳入新融汇的内容成分,不仅是一种极端狭隘,而且是一种严重错位。
吸取主干研究的教训,我认为确定哲学史的主流应该象确定江河的主流那样。首先,在江河上选取一段作为基准;其次,看在此段之间有哪些支流,在未确定主流之前,不妨把已视作主流的也当成支流。最后,计算确定主流。这就是说,确立中国哲学史主流应该采取三个步骤:一、选取时段;二、研究时段之间有何独立哲学形态;三、根据统一标准确立主流。分析以上三点,可以得出以下原则:
一、主流是动态发展中某一时段的静态分析。可以想见,每一时段有一主流,前一主流可能存在于后一主流,第一主流可能贯穿在所有主流中,可是还是不能因此就说第一主流是整个哲学史的主流,就象金沙江曾作主流,但不能说它就是整个长江流域的主流一样。况且第一主流贯穿所有主流只是一种可能,历史是否如此还待考证。事实上,就中哲史研究的成果看,第一主流贯穿所有主流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哲史的结构和功能是变化多端的,并不仅仅是六家并存的格局,而在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中把握到的主流是不同的。如春秋是儒、墨为显学,战国末期则是法家盛行。随着秦汉的统一,先秦诸子汇集为黄老之学,即使黄老之学名为道家,其实也与先秦道家大不相同。同样,继黄老之学而起的两汉经学,虽名为儒家,其实也是百家之汇集,与先秦儒家已不同。道家主干说视哲学史的结构和功能为不变,并认为道家最初在这个格局中奠定的地位也不变,这其实是一种刻舟求剑的做法,忽略了主流动态分析的精神。我们还可以想见,时段越多,哲学史研究就越接近哲学史发生发展的真面目。哲学史研究现存的问题是时段太少,只能将中哲史分为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几个时段。因此今后的主流研究应建立在增加时段以了解哲学史真面目的目的上,而不是归属问题上。
二、主流研究的实质是比较研究,确立主流的先决条件是各独立方的存在,而且应该看到各独立方已不是或不同于上次参比的各独立方。由于参比方水平、成分的变化,因此在主流判定中,主流并不是永远的主流。这点是主流判定和道家主干说的最大区别。很显然当我们用司马谈确立的六家格局去分析哲学史的发展变化时,我们已经默认了一个原则:六家是原始的独立的六家,而不完全是司马谈概括的六家。我们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西汉前期的司马谈在格局化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所处时代的烙印。他概括的道家实际上是西汉显学黄老道家。因此为了还历史真面目,也为了符合比较之逻辑,当我们从儒道等几家中确立主流时,相对于孔孟原始儒家,道家应是老庄原始道家,而不同时是稷下黄老道家。正象道家主干说所言,如果把整个稷下学宫看作一个学派,则稷下学宫是一个汇集了道、法、儒等各家之学的学派;而黄老之学最大的理论特点是:“兼采了诸家之长,并冶之为一炉,成为汉初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可见稷下黄老学是战国后期诸子百家互相渗透互相吸取的产物。道家主干说认为稷下黄老学是以道家为主干,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无可厚非。但是接下来道家主干说论证早期儒家由于受到稷下黄老学的影响而出现道家化,《易传》、《系辞》由于和稷下黄老相通而归属道家,就特别值得商榷了。很显然这是两次主流判定的混淆,也是创生决定归属的循环利用。第一次是原始儒、道等作为参比方,稷下黄老作为判定对象,而在第二次稷下黄老却悄悄代替原始道家成为参比方,与仍然是原始的儒家对手,难怪明眼人鸣不平了。显然依此下去,只能如李存山所说,天下一道家,主干是永远的主干。
三、造成主流变化的不只参比方一个因素,标准的不同也会造成主流的不同。陈文从韦伯的哲学观出发,和赵文参照黑格尔的哲学观,就曾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因此为避免无谓的纷争,判定主流时应该统一标准,同时应仔细辨别对方所用标准,否则会把对方的哲学主干说误为文化主干说进行驳斥,陈文一开始就遭遇过这种情况。
综上所述,我并不反对以六家给某一个哲学形态定性,但反对从它们推出整个哲学史主干的方法,主张以主流消解主干。参照主流判定,我认为,道家可能成为主流的时间,最多只能是先秦哲学史这一段。
收稿日期:1999—09—28
标签:中国哲学史论文; 道家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陈文论文; 哲学史论文; 国学论文; 儒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