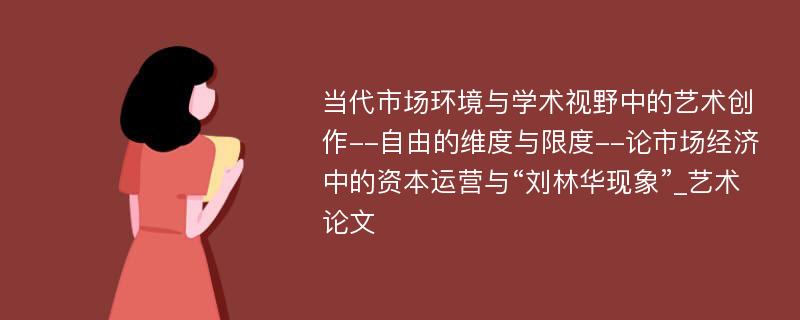
学术视野中的当代市场环境与艺术创造——自由的维度与限度——论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运作与“刘令华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资本运作论文,市场环境论文,市场经济论文,限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走出潼关
我认识刘令华,并不是在西部,而在上海。我看到的刘令华,并不是背着行囊、画夹,气质飘逸的画家,而是在豪华的别墅,从一间充满油色味的画室——堆满画框和一些完成与未完成的作品,走出的一位墩实憨厚、见了理论家总有点不知所措的画家。他送我一本画册,也谈起他的近况以及有关绘画的一些想法。我,一页页地翻看,一幅幅地观看。我看到走出潼关的刘令华,被签约的刘令华,在现代商业都市的文明中寻找表达自我情感的方式,在各种纠缠与限制中寻找自由与宣泄。慢慢地,我感受到一位画家在各种文化约定中的存在。
这是一种很尴尬的存在。譬如,初到巴黎的毕加索,是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寻找最能充分培育他的社会,但很长一段时间,“画家连买个绷画布框子的价钱也拿不到”,因为他未曾受到公众的欢迎(注:[英]罗兰特·潘罗斯:《毕加索》,周国珍等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不是毕加索没有才能,而是公众的眼光和属于公众的媒体舆论还没有关注到毕加索。这就是文化的制约吗?代表某种流行趣味的公众眼光和媒体舆论,一旦施加在独具个性的画家身上,会遭遇到什么?会将画家推入到怎样的一种境况?很多人会去适应,去迎合,然后调整自己,使自己成为公众视野中的一道风景。适应是生存的必备条件,但艺术家不是为适应而生存的。毕加索在第三次离开巴黎之前,才卖掉一幅画(即《母子在海滩》),值200法郎。临走的前夜,他靠烧画(素描稿)取暖。他经历了欲为自己打开出路的人所共有的孤寂,“蓝色时期”的忧郁,并不仅仅因为贫困,而更多是受到当时象征主义思潮的影响,倾向于内在的心理感受方式(亦称“内视觉”),无视外在的光色变化,所以,他开始清洗自己画中的颜色。1904年,毕加索再次来到巴黎并定居于此,也不是企图以他的艺术个性征服巴黎或引诱巴黎,以莫里斯·雷纳尔的说法,“他到那里是要寻找救生良药”。巴黎是艺术之都,巴黎社会对一个艺术家的评价很重要,巴黎社会对艺术的宽容与理解更为重要。他的确在巴黎逐渐赢得了声望,开始了作为画家真正的艺术生涯。后来,他对雷纳尔说,如果塞尚在西班牙工作的话,他会被活活烧死。——他谈的是社会文明的开放程度对艺术家的影响。毕加索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西方文化背景下现代画家成功的案例,一个充满个人创造力的艺术神话。但在中国,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从黄土高原走来的同样具有创造性活力的画家在中国的上海如何生存?
难道生存的问题压倒了艺术的问题?人们关注到上海的刘令华,是注意住在别墅里的画家,是注意被包装被炒作的画家,还是注意投资方与签约画家之间各种显在与潜在的关系?许多非艺术的问题冲淡了艺术本身,而艺术自身的问题又遭到非艺术人的质疑。艺术的现象就像是一个万花筒,转瞬即变。对于刘令华而言,他离开了西安美术学院,成为一名被签约的职业画家,或者说是依靠艺术谋生的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当艺术成为谋生手段时,就意味着一种“低品位”、“低格调”,所谓“匠作”而已。这也难怪,职业的艺术家向来处于一种雇佣状态,无论是敦煌石窟中的壁画或雕刻,还是五代两宋皇家画院中的丹青高手,其创作的题材、手法,不是由于某种范式的规定,就是由于某种趣味的限定,迫使艺术家在有限的表现空间中寻找自我实现的各种可能性,职业性的绘画,也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一种具有普遍审美倾向的大众文化现象。在中国,文人视野中的职业绘画缺乏个性,缺乏创造性,而业余的文人绘画,因排遣闲情逸致,日见推崇。在欧洲,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画家、雕刻家,还是文艺复兴“三杰”乃至毕加索,都是职业艺术家。职业化的现象根基于欧洲注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文化观念。譬如master,意为技术高明的专家,即大师。真正业余性质的“艺术家”,在20世纪以前的欧洲,几乎是不入流的。只是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泛起,才有“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说法。
刘令华从西安到上海,面临着一种身份的转变——从美术院校的教师变为签约画家,自由职业者。在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中,美术学院的教师是专业人士,而签约画家似乎属于“盲流”(与无业游民近似)一类。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人对专业画家的概念,基本被限定在画院、高等美术院校等国家体制中的专业人士,而不是游离在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艺术,是一种自由职业吗?其实,这种职业并不自由,无论所谓体制内或体制外,都会受到种种限制。艺术家要参与各种体制化的运作活动,如美术展览会、艺术博览会、画廊展销等,同时要遭遇批评,接触媒体,这些都会对画家造成影响,带来不少困惑。但艺术的确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艺术家又要不断摆脱批评,不断摆脱理论,不断摆脱自身的束缚,不断摆脱社会及“雇佣”的阴影。所以,艺术家的内心很孤独,也很痛苦——孤独和痛苦与艺术家的天才与个性是成比例地上升,而这种内心的孤独也正是自由的表征,因为不孤独也就不自由了。——呵,如此悖谬的问题。艺术不可能孤立地存在,那是艺术的外部问题;艺术也不可能不孤立地存在,那是艺术的内部问题。艺术是以其自身内部特殊的价值,才能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换言之,只有艺术家具有特殊的艺术品格与表达的方式,才能得到多方面的认可,才有与外部世界对话的资本。艺术是艺术家所拥有的话语权。艺术与政治集团的对话,艺术与商业资本的对话,艺术与大众传媒的对话,并不存在着什么对等的价值观念,而总是受限。艺术,作为一种职业,可以游离于他者之间,不附属任何领域但又不得不联系其他领域,在某种价值关联中确认自身的地位。到了上海的刘令华,遇到责难最多的不是他的艺术才能,而是他的生存方式;遭到批评最多的不是他的创作手法,而是艺术的“自律”与创作的自由问题,这些都发生在日渐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现实中。
什么是艺术的自律与创作的自由?是摆脱所有既定观念的支配,避免意识形态的同化,还是摆脱文化产业的庇护,避免消费市场的侵袭,拒绝庸俗趣味,追求纯粹的精神性,改换那种将艺术创作的目的倒卖成生产手段的做法?阿多诺说:“自律性,即艺术日益独立于社会的特性,乃是资产阶级自由意识的一种功能,它继而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在此之前,艺术也许一直与支配社会的种种力量和习俗发生冲突,但它决不是‘自为的’。”(注:[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阿多诺特别提到,从艺术发展之初到现代的集权国家,始终并大量存在着对艺术的直接控制。艺术并不独立,总是在一定的限度中发展,艺术家不自由,艺术的自律问题没有解决,但“资产阶级时期”是一例外。为什么?难道依靠资本运作的市场经济反倒解放了艺术与艺术家,解决了艺术自律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社会比先前的任一社会都更加彻底而完全地使艺术获得整一性。所谓的整一性,即强调了艺术的现实特性,艺术与经验性社会之间的关系。随即,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批判了黑格尔和卢卡契等人的“总体”、“整体”、“同一性”等概念,认为这是虚假的、抽象的社会存在幻影。他认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向个体性的差异,只能是“一贯意义上的非同一性”(注:[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纽约1973年版,第5页。)。伊格尔顿同阿多诺一样,也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重新阐释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理论,认为艺术首先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其次,又以它特有的方式与其维护和再生的社会权力发生某种联系。因此,艺术就成为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在现代商品社会中,艺术也就成为商品,而艺术家同时也就是生产劳动者——适应社会需求,带有雇佣性质的人员。本雅明同样将艺术创作看作生产活动,并以艺术创作的技巧直接衡量艺术发展的水平,认为艺术生产的关系决定着艺术生产力(即技巧与手段)。在“技巧”这一概念上,本雅明将其作为“内质”的存在,巧妙地消除了形式与内容的对立(注:[德]本雅明:《试论布莱希特》,法兰克福1966年版,第98页。)。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都从理论上支持了从达达派到超现实主义的先锋运动,说明新艺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说明“反艺术”的观念与行为是对现存制度“非人化”的批判,摈弃了对完美的感性外观的追求。面对这种情状,艺术的自由实现与艺术的自律性与个体的独立批判的意志相结合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依然是被资本运作着,在自由与批判的口号掩饰下,艺术的实验与探索,艺术家的个性与创意,在商业社会中被悄然利用,常常会不自觉地转换为带有“广告”性质的招贴。
社会就像是一张网,因为牵扯与限制,才有自由的奋争。艺术是人们争取思想自由最容易使用的手段,因为它只是表达一种声音,而这种声音依靠视觉媒介触动知觉达到意识层面,融为隐晦的“浑然”状态。对艺术的研究,是分析图像的视觉结构从而为社会提供某种价值的证明,而不是依据某些图像的社会背景来解释图像。那么,当我们关注到“刘令华现象”,是否就在注意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种被资本推动了的艺术创作,一种在市场经济的正常作用下,人们如何看待体制外的艺术现象,或者说是“艺术生产”的现象?但刘令华经历的却又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所谈论的那种生产方式,他没有一味地复制,没有将自己抛入生产的流水线,尽管也存在表现手法上的“风格化”问题。
二、秦腔京韵
刘令华从陕西到上海,从版画转到油画,都有一个“味”的问题。什么“味”?即从绘画中传递出来的有关审美、有关技法风格的某种品性。
刘令华的“味”变了。我不愿意在此说他绘画的“题材”转变了,风格手法转换了,或者说他绘画的门类变了,而说变“味”,或者说变“腔”、变“脸”。刘令华自己说过,他喜欢秦腔的高门大嗓,那种粗犷的不甚修饰的在黄土高原飘荡洋溢的唱腔。到上海前,他在艺术上也初露才华,无论版画或油画,都有一些“获奖”作品,尤其是描绘藏族的《母亲》系列油画,得到批评界的赞誉,也因此结缘上海,成为“宽视”的签约画家。但签约后所画的一系列“京剧”油画,画风骤变,引来议论纷纷,毁誉皆至。为什么?难道他到上海后,趣味转变,喜欢上了京剧这门高雅的“戏楼”艺术而远离了黄土高原那随处而歌的秦腔?还是签约方为了打开艺术市场,为艺术家限定了表现题材,培养他的都市趣味,包装他的艺术,让他进入一个预设的表现领域?从材料上看,应是后者。但看看他的作品,却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画中有艺术家自身的情感成分和表达欲望,而且还很强烈,有的画面(如《钟馗捉鬼》、《打焦赞》、《法海》等)达到浑然天成的状态,色彩随着人物的戏剧性动作——甚至可以感受到随着京剧唱腔而“阵发”,其节奏、韵律都很贴切。色彩纯度极高,色层关系也处理得很好,画面的意象性表现手法,使油画亲近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这一切难道也是一种现代大众文化的流行策略?
一般人谈论大众艺术的流行,总喜欢说人文精神的失落,总喜欢到古代的经典中一吟三叹,欣赏那般精致;或返回山野,在民间纯朴的形式中谈论艺术的天真。一般人说到签约的画家,看到画家被某种趣味或题材所限,总喜欢为艺术抱屈为天才扼腕为社会感叹。不错,严肃的题材容易引起人的情感共鸣,产生崇高感或悲剧意识。譬如《母亲》(布面油画,160×170厘米,1998年),历经沧桑的脸,岁月留痕,几缕散乱的长发飘过额前,一个用语言描述就十分感人的形象。艺术家将他的感受用特殊的材料特殊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或者说还原出来。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或故事,其感动的基础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怜悯之心,通常在不同处境中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情感交流。譬如都市人厌倦“现代”社会的繁杂喧嚣、机械的秩序、理性的规则,开始留恋乡土社会,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为他们演绎出单纯和善良。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是都市人的“母亲”,“母亲”的悲伤和伟大,不断被都市人所感动,或许还有那些来到都市生活时日不多并开始接受文化“启蒙”的农民,会有重新发现或唤醒的惊奇。真正的乡里人看到刘令华的《母亲》,抑或当年罗中立的《父亲》,又会有怎样的说辞?
乡土题材的流行,只是都市文化中一闪而过的景观。所谓高雅艺术,只是都市人的艺术,或者说是为都市人的艺术。都市中的艺术存在,实质上就是“商品化了的存在”,被资本支配着的存在。一旦进入艺术市场,任何人都无法躲避资本支配的力量。刘令华从乡土题材转到京剧题材,确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因为签约,因为“策划人”的介入,刘令华开始接触京剧,开始画京剧人物。对于画家而言,他关心不是画什么,而是怎么画,那是很具体的事。画什么和怎么画,也不是可以随意分开的。有些题材对表现的手法与风格就有限定,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当题材被确定之后,风格与技法的相应转换,往往就交给画家本人来处理了。从刘令华签约后的画风转变,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路线,或者说有两种画风推演变化着。从我与刘令华的交谈看来,刘令华的困惑主要在如何表现的问题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刘令华基本定型了。他发现将中国画的大写意手法运用到油画上,以色代墨,以布代纸,不仅以意象化的形式恰当地表达中国京剧的“唱、念、做、打”,在视觉方式上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要求,而且在油色肌理的变化中体现出现代西方抽象绘画的审美意趣。独特的刀法(使用一种特制的调色刀)将颜色的纯度提到极致,很耀眼,色层变化丰富,厚薄参见。应该说,刘令华早期那种沉稳而凝重的风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狂欢般热烈而明媚的色调。言其“媚”,有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评判,是都市中眩目的含有某种商业气息的色彩倾向,与中国文人传统的审美趣味——如淡雅、舒缓、平和等,格格不入。善于玩味的内向的中国“文人”们难以接受了,对现代艺术中倾向视觉感受的审美方式提出批判。他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即“媚俗”,似乎“媚俗”是商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像我们习惯以此评价明清时期与近代商埠文明一起出现的绘画与雕刻的审美品性一样,就像当初人们评价明末的陈洪绶、清初的扬州画派以及清末的海上画派一样。
文化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审美上的差异。如何评判现代商品社会中的艺术现象,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艺术创作,其审视的角度和评判的标准就是一个问题。现代艺术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从被古典艺术所忽略的那些或“低级”或“通俗”或“野蛮”或“原始”或“杂耍”的艺术中吸取灵感。譬如,毕加索对马戏表演、黑人雕刻面具所给予的关注与兴趣。京剧是清代才发展起来的,虽说号称国粹,毕竟还是十分通俗的大众化的娱乐方式。用油画的方式表现京剧,我感兴趣的地方倒不在于什么中西融合,而是考虑到现代艺术的通俗化与启蒙问题,考虑到都市文化景观中的视觉与幻觉要素。从视觉艺术的角度看京剧,那是五彩缤纷的世界,脸谱、扮相、服饰、灯光,绝不是水墨浅绛白描人物那种悠然出世的审美情状,而是喜怒哀乐,锣鼓喧嚣,在西皮二黄的声腔中,将情感倾泻而出。而油画,正是强调视觉冲击力的,既长于描述,也擅于表现。有人问我,如果用中国画的线描方式表现京剧,效果怎样?我对其言道,线描的方式长于叙述,表现故事,刻画情节,而泼墨写意的方式则长于表现瞬间的情状,将情绪或动作的力度发散于特定的心理空间。刘令华描绘京剧题材的油画所具有的视觉震撼力,一方面与极具表现性的油画语言有关,另一方面也借用京剧夸张的造型与夸张的色彩,增强了画面的表现力度,也满足了戏剧观众对某种幻象的期待。今日艺术最大的难题,就是对幻象的频频出现羞愧难当,却无法将其抛开。幻象的构成本质是“非实体性”的,像印第安人神话中的半人半兽,像保罗·克利的画,像萨尔瓦多·达利那挂在树上的钟。视觉的强度与力度的最终实现,往往在于主体综合性的外延思维。现代艺术只知主体而不知其他,甚至将客体主观化为自己心灵的图像。从这一层意义上,现代艺术并不取媚于观众,并不为“我们”而存在。
为“自己”而存在还是为“我们”而存在,在黑格尔那儿是统一的,并不矛盾,黑格尔认为这是由于艺术作品的自足性(即整体的谐和)所造成的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注:[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5页。)。在现代艺术中,这种整体的谐调关系是否被拆解?是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个性的艺术家十分强调自我,无视社会,孤独地探索,保持艺术的独立与自我的尊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不少艺术家走出象牙塔,以十分轻松的心态做着与大众与社会相互沟通的工作。真正向两极分化的,均有着“先锋”倾向。所以,理论家们讨论艺术的个性(保持艺术精神的纯粹性)或讨论艺术的“波普”(包括反艺术的行为倾向),讨论艺术文本在社会阅读群体中的意义。
中国社会公众对艺术的经典性阅读情结普遍存在。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表现出的还是一种民族情结,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心理定势。譬如,图像中的写意,中国人就特别容易接受;戏曲中的唱腔和扮相,中国人就特别爱玩味。虚幻的,模拟的,象征的,在艺术中都被融化被综合。刘令华以经典题材和类经典化的表现手法,迎合了公众的阅读。这种阅读处理也许不是出自刘令华本意,也许是“宽视”或策划人的主意,也许就是上海这个大众文化最为流行的都市对文化产品的期待:现代的视觉效果,传统的文化底本和习惯的欣赏方式。熟悉的故事和陌生的图式,刺激着现代人的神经,企望广泛的影响——这才是投资者的目的也是创作者的目的。大众文化并非绝对地排除经典文化,它可能利用经典,改装经典,从而消解了学术的等级制和标准化,触怒了专业领域内的知识分子。绘画,也是一门形式化的技术,有专门的技巧和知识体系,但它的受众却以最直观的方式接受产品形象而忽略技术规范。谁都可以阅读绘画,谁都可以批评画家,似乎谁都“懂”绘画——无形中构成了一个艺术的公众领域。这个领域是有很宽泛的社会经济基础支撑着的,譬如,乡村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或国际化标准化了的现代工业社会。不同的经济基础形成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相应的审美评判,其中,都蕴含着各自的精神与文化目的。旧价值的失落伴随着往昔精神,在社会转型期最招人非议,但谁又能提供一个平台,自由地吸收不同的价值观,用于各种边缘性的艺术探索和临时性的知识储备?
在上海,这个在中国近代曾经殖民色彩浓厚的“十里洋场”,对外文化的交流,自身文化的沉积,迅速地在这里汇聚。因此,文化的协变性(Cultural covariance)在上海就显得格外突出。刘令华到上海的转变,实际上也是某种文化协商的结果。刘令华自身的历史已内在于他的艺术中,不是某种外来的命运或评价方面的变化所能改变。他画京剧人物,控制画面的还是那西北人的气度和秦腔大嗓。如《通天犀》(布面油画,140×160厘米,2000年),对角构图,几个矩形穿插,画面满是沸沸扬扬的色块与线条。看来关于艺术,最终还得回到形式语言的层面,才能讨论艺术家的个性、风格及创作中的种种,才能对一位艺术家进行较为客观的审视。
三、世纪玫瑰
《世纪玫瑰》(布面油画,290×200厘米)是刘令华的荣耀。该画于2001年在上海APEC会议主会场展出,同时在国际会议中心展出他的26件京剧人物油画,成为惟一在这重大的国际会议展露才华的画家,也在上海油画界引人注目。
参加展览,对于一位画家是很平常的事,但能够参加重大的或高规格的展览,却不是一件易事。有的展览,对画家是至关重要的。譬如,1874年,法国巴黎举办一个画家的联合展览,莫奈的一幅《印象·日出》就为同时参展的画家赢得了一个称号——“印象派”。当时的批评家是带着嘲弄的口吻调侃画家,而历史却调侃了那些批评家。印象派画家不仅在形式风格上另辟蹊径,而且在展览方式上也属另类,采取民间的自由组合的展览,没有评议审查,也没有挑选淘汰。新时期以来,我国在国家权威的大型展览之外,也开始鼓励多种形式的展览,特别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国艺术博览会”,就属于相对自主的展销形式。刘令华与这还不一样——自从签约之后,刘令华的一切展事活动均由宽视公司安排。因此,他的展览也就纳入到公司的整体策划方案中。迄今为止,刘令华已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举办了个人画展,也多次参加国内艺术节和艺术博览会,但就是没有参加过一次需由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审入选的展览会,一切都是自发自主的,完全按照商业化的操作程序办理。
刘令华离开了美术学院,实际上也就离开了一个既定的学术体制。对于像刘令华这样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艺术家,如何评价他们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成就?是否也需要建立一个权威的学术评价体系,才能规范艺术市场和体制外的一切艺术行为?
评价,就是要建立一个等级制度,必然要涉及诸种有关艺术和艺术创作的观念。譬如,关于“完整”、“深度”、“纯粹”,琢磨风格手法,接近“可控经验”(controllable experiences),进行“内在分析”,都应该属于同一观念系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如何论定“断片”(fragment)的价值?论定“无深度表现”的艺术存在的合理性(或者说我们如何理解“深度”)?我们不能接近作者的实际经验,对其审美意向茫然莫测,我们是向往还是摈弃?一边是“文化遗产”,一边是“西方传统”,你如何评价?所有的艺术与艺术作品并不处于同一边界内,不仅文化内涵不同,技术维度也不同,而且有的作品还下取决于形式律的制约。现代艺术的发展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多样化,即使在现有的国家艺术评价体制内,也不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评判标准,评委会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成员及其知识结构,不断调整和修订评判条例。譬如,不断呼吁增加评委中理论家的比例;在第九届全国美展时,增设了“艺术设计”展项;上海的APEC会议,也安排蔡国强(装置艺术家)设计焰火。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所设定的金、银、铜奖,毕竟还是在一个学院化了的学术体制内评判,尽管社会上的意见不少,还能维持。若面对体制外的艺术市场,恐其学术委员会也难以评价。
人们对艺术最常用的评判通则是内涵与精神。能够被理解的被感受的从内心深处打动你的作品,往往被视为有内涵有深度的作品。可是,现代的艺术多停留于视觉表层,注重视觉效果,注重形式的设计,强调某种个体的创新理念的体现,不可能出现卢卡奇所谓“规范的艺术品”。艺术无法容纳规范其思想的作品,也不容纳规范其形式的作品。就某一艺术体系,规范不可避免,尤其是在美术学院传统的教学体系中,规范性十分普遍。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就一个契斯恰柯夫体系,学生丢掉了碳条换铅笔。在艺术的任何领域,规范仅对学习有效,不对创作生效。艺术作品拒绝以某种等级排列名次,但并不是说批评不能够进行。艺术批评所通用的量性维度(quantitative dimension)是根据作品的“自我同一性”原则来界定的。回到本文(text),不论是结构主义者的眼光,还是解构主义者的分析,对形而上的批判是共同的声音。理论的广泛含义,也许在新的启示录腔调中为人所着迷而有所兴奋。这里,我排斥了有关一般批评的清晰度,转向具体而谨慎的表达。模棱两可的批评不是人们所期待的,批评也不可能超越形而上学的历史。批评的现状,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已陷入“双重的抛弃”——已逃逸的诸神的不在场和即将降临的诸神的迟迟未见(注:[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6-287页。)。
不过,对艺术市场规范化的吁求不是没有道理。完全商业化的资本运作,必然掺杂着许多非学术性的意图,必然会出现非规律性的艺术现象。无论如何,艺术还是人类一项精神性的活动,其自由的意旨需要艺术家自身给予揭示,也需要一种独立的批评意志对待自由的艺术。自由总是相对的,但没有自由的艺术活动,缺乏独立的艺术批评,就会沦为某种权力的附庸。资本的权力,不是单纯的个人意志体现而是源自消费群体或市场环境所构成的利益分配机制。文化艺术的精神消费与其他物质品的消费还不同,公众的趣味与流行的时尚也在起作用。几乎与艺术产业化的趋势同步的大众娱乐性艺术,如潮水般泛滥。视觉的绘画艺术,在主题及图像资源方面也受到不少侵染。与大众接近的意图,使得想进入市场的艺术家和控制市场的文化产业者都在不同程度地蒙蔽艺术,体现出原初的拜物与消费意识,单纯的审美观照越来越少。从策划与运作的角度,宽视公司似乎不想充当艺术经纪人的角色,不直接与著名的画家签约,不进行单纯的买卖,而是在某种企业策略下,用“关注—协商—调配”的方式消除了文化产业中常见的专制主义色彩。签约后的刘令华创作,观念的自主性与艺术手法的自由表现程度并没有受到损害,反倒得以在一个不受经济困扰的环境中潜心思考。刘令华不再过多地考虑题材问题,不再忧虑作品的出路问题,他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如何为京剧人物寻找到恰当的表现手法,并在具体的画面上加以完善。这种“沉潜”状态,为艺术家的“自我”提供了表现的空间,为某种风格的探索给予了自我实验与自我评判的机会。这时,亢奋中的五彩斑斓的刘令华不同于以往沉默的参杂在红与黑中的刘令华,特制的调色刀逐渐代替了鬃毛笔,开始得心应手。我看到,使用同样技法表现出的静物、风景,如《葫芦》、《玫瑰》、《窑洞》等画,画面都很完整,作画的感觉是统一的,没有外在的干扰。在创作京剧人物油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新的意象性的语言,还是刘令华的——这是刘令华对自我的新发现,是在某种限制中自由发挥所得到的新收获。可见,艺术的自律性并不是先验的,自由是思想过程的产物,支配着普遍的内在形式律。“艺术作品越是想方设法摆脱外在目的,越是受到组成创作过程的自设原则的制约。艺术作品也正是如此反映和内化了社会的支配作用。”(注:[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阿多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产业的批判,同时也批判了艺术,因为艺术有着迎合现存社会需求的倾向。毋庸置疑,刘令华某些作品所出现的“媚俗”倾向,正是流行的大众趣味侵入或在协商和调配过程中艺术家无法自律的结果。
艺术创作规律和市场运营规律的矛盾需要调节,个体性的独创和规模化的生产需要区别。从图像上,刘令华并没有重复制作;在手法上,刘令华似乎出现了风格化的倾向。签约方没有制止,反而鼓励其完善。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需要过程,更需要不断地肯定和批评。没有个人风格的画家,无法称其为有创造性的画家,也没有个人的艺术形象。但过于风格化的画家,又是创造力开始萎缩的画家。刘令华现在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定型的画家(这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他必须毁掉一批画,但他的确是一个画家,他有过人的精力和痴迷的情态,创作欲十分旺盛。我不知道签约方与他对今后的发展有何设想。从一般职能性分工的角度分析,作为艺术家的刘令华需要不断地画画,创作新的形象性作品;作为文化产业的宽视公司,需要为这些艺术品制造更大的增值空间,设置各种环节推入市场运作的轨道。从商业的角度,我们无法非议“宽视”;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似乎也无法责难刘令华,因为刘令华只是一个画家,他没有直接经销他的作品,没有直接投入商业运作(即便如此,也不构成“责难”的理由,那是艺术家自身的定位与存在方式)。问题在于他们之间的“协定”,这种协定可能成就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也可能毁掉一个有天分的艺术家。理解是重要的,协商更为重要。
“创作”和“生产”绝对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在资本运作下的艺术创作,就有了“生产”的意味,或者说,就是生产。生产是为了经销,为了盈利。绘画一旦成为“生产”的手段,“图像”的概念就浮现出来。对艺术文化“产业”而言,批量化的图像再生能覆盖很大的消费市场,产生很大的利润,是绘画再生产的中间环节。这属于图像的“复制”过程,属于图像的应用性质(这里不针对“波普艺术”中的图像解释),它必然首先需要某种实验性质的创意原本,而原本的创作就成为受保护的“专利”。有意思的是,我偶然在上海一家星级宾馆的礼品部,看到一件苏绣,所采用的图像就是刘令华的京剧人物油画,据说销售状况不错。我问销售员,这是否为宽视公司的产品或其授权单位的产品,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这里牵扯到许多问题,但我关心的是一家文化艺术产业机构在包装一位艺术家的同时,是否也在开发图像资源,从创作转入制作,建立相配套的规模化的市场机制。似乎,“宽视”并不在意图像的“复制”而在于艺术家的创意,没有直接动用这一生产要素,显然是在保护刘令华和他的艺术“专利”,防止艺术的“堕落”与流俗。
“刘令华现象”的确是当前被资本运作的一个案例。我们研究这个案例的现实背景,正是我国逐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我们研究这个案例的意义,也在于这个现实下,中国的艺术家从国家计划体制中正逐步分离出来,从各级画院、高校等专业团体走向社会走向市场,各种策展人、经纪人应运而生,文化艺术产业相继出现,艺术与整个社会存在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艺术和艺术家又是如何处理和应对这种变化了的状态。刘令华的艺术道路成功与否,我们还不能断然结论,因为他和他的签约人也在不断协商,不断调适,以寻找发展的途径。但是,我们能够研究的或已经看到的,是这一阶段刘令华的艺术实践所提示的问题。
当尼采说“上帝死了”的时候,艺术中的神性是否也黯然消失?在物质的世界中,精神的纯粹性依然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变得多样了。许多时候,带有种种蒙蔽性,外在的与内在的并不统一,有幻影伴随,有幻象产生。精神,尤其是艺术精神始终没有离开过人的存在层面,尽管存在是现实的,就像一朵玫瑰。
标签:艺术论文; 当代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油画人物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美术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母亲论文; 油画论文; 京剧论文; 画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