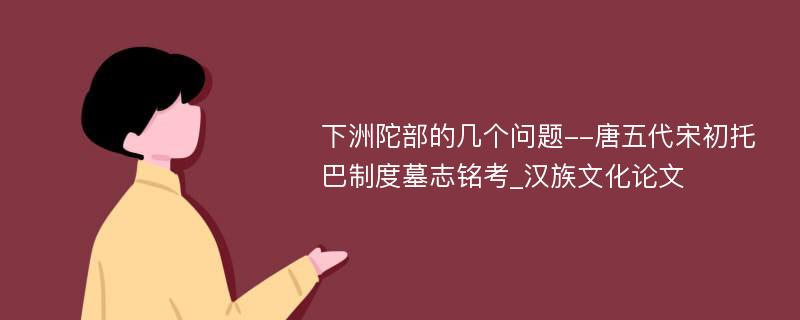
夏州拓跋部的几个问题——新出土唐五代宋初夏州拓跋政权墓志铭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拓跋论文,墓志铭论文,初夏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政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部的无定河镇与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拱盖梁村等地相继出土或从盗墓者手中截获了一批夏州拓跋政权墓志。按其制作时间顺序排列,分别为《大唐静边州都督西平郡开国公拓跋守寂墓志铭》、《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铭》、《大晋故定难军摄节度判官毛汶墓志铭》、《大晋故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大晋故定难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大晋绥州故刺史李仁宝墓志铭》、《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大汉故沛国夫人里氏墓志铭》、《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故大宋国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成墓志铭》、《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大宋故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和《大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①。这批墓志的志主既有拓跋政权的府主大王和郡国夫人,又有刺史、判官之类的属下官员;不仅有党项族,还有汉族。墓志在记述他们“事迹”的过程中,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本文仅从拓跋政权中的汉人士大夫与汉化问题、拓跋家族的婚姻关系、拓跋部的族属问题三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拓跋政权中的汉人士大夫与汉化问题
有关夏州拓跋政权中的汉人士大夫与汉化问题,有两条重要的史料。一是宋初边帅张齐贤上言:李继迁起兵后,“潛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1]1099。另一条是宋仁宗时枢密副使富弼的奏言:“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1]3641
这两条史料使人们误以为李继迁起兵前,拓跋夏州政权全是“羌夷之体”,或者是西夏自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占据灵夏以西的河套平原后,方“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但事实究竟如何呢?目前发现的这一批夏州拓跋政权的墓志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在这些墓志中,将近一半的志主是汉族,他们或为幕僚,或是军将,为拓跋夏州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志主白敬立,系秦将白起之后,白起被赐死于杜邮(今陕西咸阳境)后,子孙沦落,一部分随太子扶苏筑长城,从此定居塞上。“自有唐洎九世,世世皆为夏州之武官”,传至白敬立,“为故夏州节度使、朔方王(即拓跋思恭)信用门下。王始为教练使,公常居左右前后”。教练使为唐代方镇军将,至德元载(756)始置,掌教练兵马及武艺。拓跋思恭在夏州节度使(汉族节度府)帐下做教练使时,志主就“居左右前后”,反映出拓跋部建立夏州政权前已打破了地缘与血缘(民族)界限,吸收了大量汉族人才。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后,拓跋思恭应诏纠合夷夏兵“赴难”,志主(白敬立)侍从顾问,传呼号令。“王(拓跋思恭)乃推腹心,委之如父子;公亦尽忠瘁,报之如君臣。”形成了不同一般主仆的君臣关系,被喻为“蜀先主得孔明”。
志主毛汶,夏州拓跋政权节度判官兼掌书记,家居巩洛。祖父“守京兆府万年县令”,父“皇任定难军节度观察判官”。乾化元年(911年),夏州节度使故虢王李仁福以为志主率直尚气,“委赞巡属”。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署摄当府节度推官”,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又迁花幕”,“官崇上佐,贵列夏台”,拓跋夏州政权数十年章檄文字多出其手。
志主何德璘,夏州拓跋政权观察支使,南阳郡人。历任衙前虞候、州衙推、观察衙推、右监门卫长史、节度衙推兼银州长史、观察支使、将仕郎、试大理评事。
志主刘敬瑭,夏州定难军节度副使,彭城人。其先为“唐代宗皇帝之宝臣晏相六世之玄孙也”,历任虞候、四州马步都虞候、左都衙官、管内马步军都知兵马使、检校司徒、银州长史、宥州知州、光禄大夫、右监门卫大将军、定难军节度副使等职。长兴四年(933年),唐明宗为兼并夏州,命定难军留后李彝超与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对调,并派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兵五万护送安从进赴任。大敌当前,李彝超坚守夏州城,志主刘敬瑭“请权兵把截四面,师徒抽退,士庶获安”。
志主康成,夏州定难军管内都军指挥使,历任安塞副都兵马、安远将军使、东城都虞候、左都押衙、都知兵马使、五州管内都军指挥使。在长兴四年(933年)夏州保卫战中,康成“披坚执锐”,“屡奋先登之勇”,成为夏州拓跋政权凭借的“奇人”。
志主何公,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出身医学世家,曾祖摄夏州医学博士。志主“幼习家风,颇积医论”,因治愈府主大王疾病,名声大震。历任文林郎、左武卫兵曹参军、将仕郎、太常寺协律郎、府衙推、宣德郎、绥州长史、监察御史、节度衙推、银州长史、朝请郎、大理司直、殿中侍御史、柱国、夏州长史、夏州观察支使,所谓“匡持侯府,正当重任”,“内则以妙散神丸,供应上命;外则以文才武略,开拓边封”②。
由此可见,积极吸收汉族地主阶级人才,使其为夏州拓跋政权效力,是拓跋部首领的一贯策略。唯其如此,夏州拓跋部势力才日渐壮大,从而最终完成建立西夏国的任务。
二、关于拓跋家族的婚姻问题
婚姻关系是夏州拓跋家族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大汉故沛国夫人里氏墓志》以及其他墓志有关婚姻方面的记载,弥补了史书缺佚,为研究唐五代拓跋家族婚姻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材料。
早期党项“不婚同姓”[2]5291,因此和拓跋部一起内迁的野利、把利、破丑等大族”③,是其重要的通婚对象。除李仁宝妻永定破丑夫人外,墓志中还有多处与破丑氏通婚的记录。李彝谨曾祖李重建,“(曾)祖妣破丑氏,累赠梁国太夫人”[3];李彝谨长子李光琇“娶破丑氏之女”[4];李光睿“次婚破丑氏”[5]。破丑氏即史书上的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2]5292,“居雪山者曰破丑氏”[6]6215。雪山为青海河曲的大积石山。贞观末年,吐蕃势力对外扩张,破丑氏和拓跋等部迁居陇右地区。
野利氏,又作野辞氏、野由氏,为党项八部之一,和拓跋部一起迁入陇东庆州。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年),以党项拓跋氏十八个部落为主的静边州都督府,在拓跋守寂高祖拓跋立伽的带领下,又从庆州迁到今陕西省横山县无定河之南[7]。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隔断吐蕃与党项的联系,把静边州、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迁往银州之北和夏州之东,“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6]。由此可见,拓跋部与野利部的居地一直比较接近。唐五代拓跋家族墓志虽然没有娶野利氏女子为妻的记录,但拓跋部有女嫁到野利家族。李彝谨和里氏“有女三人,长适野由氏,次适苏氏,皆以婚成伉俪”[8]。
唐五代以来,银、夏诸州户口最基本的特点是“蕃汉相杂”。永定破丑夫人亡故后,“蕃汉数千,衔哀相送”[9]。宋初夏州汉户2 096,蕃户19 290[10],汉户仅占蕃户的十分之一过一点。但汉族的文化水平较高,加之夏州拓跋政权是在联合蕃汉地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和汉族通婚也在情理之中。《故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称其“望重华族,德光清节”,她的从表姪孙又是摄节度判官荥阳毛汶,似乎渎氏出身于汉族。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渎氏五男李彝殷、李彝谨、李彝氲、李彝超、李彝温都有汉族血缘,其中李彝超、李彝殷相继做过夏州节度使。李光睿“婚濮阳郡吴氏”[5],吴氏的郡望为濮阳,当为汉族。
李彝谨长子李光琇娶破丑氏,次子李光琏娶苏氏,三子李光义娶杨氏。长女适野由氏,次女适苏氏。这里的苏、杨两姓很可能是汉族,或是接受汉文化的党项人。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拓跋家族亦是一夫多妻制,这在墓志中也有反映。李仁宝亡故后,“诸夫人目断幽津,遽失和鸣之响”[11]就说明了这一点。
西夏盛行姑表婚,据研究西夏语“为婚”一词,第一字同“舅”音,第二字“甥”音。从构字上看,第一字是“子”加“娶”,第二字是“女”加“嫁”。西夏语“舅甥”和“为婚”两词语音完全相同,表现在党项人社会中,舅甥关系是一种必然的姻亲关系,外甥娶舅舅的女儿为妻是社会的约定俗成。同时西夏文“婆母”二字,第一字与“姑”同音,且在字形上取“姑”字一半构成,说明党项人“婆”和“姑”相通。这是因为外甥娶舅之女为妻,舅之女称其丈夫的母亲既是姑母,又是婆母。此外,西夏语“岳父”和“公公”是一个词,“婆母”和“岳母”也相通,表明不仅盛行姑舅表婚,而且这种姑舅表婚是双向的,即姑姑的儿子娶舅舅的女儿为妻,舅舅的儿子也可娶姑姑的女儿为妻。单向姑舅表婚,后者是被禁止的[12]。史书记载西夏的姑舅表婚都是单向的,如开国皇帝李元昊娶舅女卫慕氏为妻,第二代皇帝李谅祚娶舅女没藏氏为妻,第三代皇帝李秉常娶舅女梁氏为妻。而拓跋家族墓志所记的姑舅表婚则是双向的,李彝谨妻子的母亲为拓跋氏,即舅舅的儿子李(拓跋)彝谨娶姑姑的女儿为妻[4]。
三、关于党项拓跋氏的族属问题
西夏由号称强族的拓跋部建立,由于鲜卑也有一个拓跋部,并且一度统治过党项羌,由此引起党项拓跋部究竟是源自东北的鲜卑族、还是源自羌族的争议,这是自唐代以来就形成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元和姓纂》、《辽史》和《金史》都认为拓跋部出自鲜卑,而《隋书》、《旧唐书》、《宋史》则认为出自羌族[12]。
持拓跋部出自鲜卑说的重要依据是早在元昊二百年前唐人林宝撰写的《元和姓纂》书中说拓跋守寂是东北蕃,亦即鲜卑族,而拓跋守寂就是西夏王室的先祖[13]。持拓跋部出自羌族说则认为:《元和姓纂》提供的材料是西夏皇族出自鲜卑族的最早的材料,但“据《元和姓纂校勘记》的考证,此书早已亡佚,是孙季逑从《永乐大典》和其他文献中钩沉补辑的。而且林宝成书过于匆忙,孙季逑的校录时间更为紧迫,所以书中错误很多”。因此,“《元和姓纂》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其原因可能由于鲜卑拓跋部在历史上较为著名,因而将党项拓跋氏误认为是鲜卑拓跋部之后”[14]154-156。但这仅仅是“怀疑”或“推测”。鲜卑拓跋部在历史上较为著名,而将党项拓跋氏误认为是鲜卑拓跋部之后,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早期拓跋家族墓志的发现,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推断是正确的。立石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的《拓跋守寂墓志》,明确记载拓跋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显然元和年间(806-820年)成书的《元和姓纂》把拓跋守寂定为鲜卑拓跋之后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和三年(883),崔致远在《贺杀黄巢贼徒状》中说:“拓跋相公(拓跋思恭)、东方尚书(东方逵),或力微(北魏神元帝拓跋力微)裔孙,或曼倩(西汉东方朔)余庆”[15]26。此后立石于后晋开运二年(945)的《李仁宝墓志铭》,亦称其“乃大魏道武皇帝之遐胤也,自仪凤之初迁居于此”。立石于后周广顺二年(952)的《李彝谨墓志铭》,说李彝谨是“后魏之莘系焉”。立石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李继筠墓志铭》,亦认为“公本后魏之苗裔也”。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时,再次提出:“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16]可见拓跋李氏称鲜卑之后,主要由林宝《元和姓纂》错误所致,并不是人们通常说的“攀附”。这种以讹传讹,错误地把李仁宝夫人破丑氏也当作“元魏灵苗,孝文盛族了[9]”。
注释:
①碑文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年;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校以内蒙古乌审旗文管所、陕西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靖边县文管会办公室惠赠的数码照片,其中《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与《大宋故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属于首次公布。
②以上所引皆见本志。
③《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戎党项羌》载,“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第6217页。
④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再论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认为拓跋氏出自鲜卑族。李范文《试论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民族史论丛》,1980年;《再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154—15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史金波《西夏境内民族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增订本,均认为拓跋部属于羌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