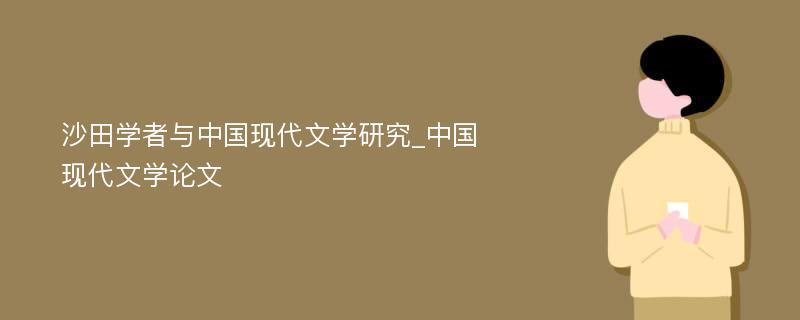
沙田学者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田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104-0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海外也叫作中国新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有着半个世纪的历史 了 。50年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学者都为这一学科的建设倾注了心血。虽然 ,思维方式、观察视角和治学方法不尽相同,但各方都有真诚的学者和通才,在这一学科的 各个领域中默默开拓,正是这四方成果的汇流激荡,才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蔚为大观,健康 成长。
香港地处交通要冲,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言论尺度较两岸更显自由宽松,各种文 化思潮得以在此争奇斗妍。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提倡政治挂帅,唯“左”是瞻;而在台湾 许多30年代的文学作品仍然是禁书;此时香港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却极为活跃:自60年代起, 便有曹聚仁、司马长风、李辉英等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整理成文,公诸于世。此后,在这一学 科耕耘的在港学者,有刘以鬯、陈炳良、梁秉钧、璧华、彦火、王宏志等。而成绩最为卓著 当属沙田学者,包括了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任职于中文大学的林以亮(宋淇)、余光中、梁锡 华、黄维樑、黄继持和小思(卢玮銮)。鉴于各家的研究领域、切入点及方法不 尽相同,本文先撮要介绍沙田学者的研究概貌和基本观点,然后理出大致脉络并作整体评价 。
一
林以亮1948年到香港,潜心翻译与编剧。1968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兼翻译中心主任 ,主持《译丛》。1955年,他回顾自我创作路程时说,“对十九世纪文学,我是从死心塌地 的拥护变成怀疑,再变成批判和排斥。”[1](P56)他这里说的19世纪文学,指的是拜伦、雪 莱、歌德、海涅等浪漫主义诗作。
70年代,林以亮先后出版了《昨日今日》、《前言与后语》和《林以亮诗话》等著作,深 入地讨论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创作的历史与现状,并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话剧、小说、文 学批评等文类。他评论的作家有林语堂、闻一多、茅盾、徐志摩、梁宗岱、冯至、朱光潜、 李健吾、曹禺、张爱玲、穆旦、施蛰存、李金发、卞之琳、杜运燮……还有几乎被埋没了的 吴兴华。
在《前言与后语》里,作者大胆地指出,新诗取代旧诗,自有功绩,但它也是中国现代文 学中成绩最弱的一环。我们的新诗作者对西方现代文学没有足够的认识,又不重视中国古诗 的传统与中国文字的特点,却深陷于浪漫的伤感纵情中,创作轻率随意。“拿情感看成诗中 最重要的因素,源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一向为五四以来的文学所信奉。这种看法,与现 代文学批评有很大距离。”[2](P1)文章细致分析了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功用,强调了诗歌 的多样宽广,强调诗人凭借精深的文化素养及知性,改造提炼原始情感的重要性。“认为没 有感情就不是诗,是19世纪浪漫主义盛行以后的事,18世纪处处以理智和通达事理为先…… 现代人的诗更是对19世纪的反动。”[2](P78)“诗可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如某些民歌,但 还可以是华滋华斯说的‘在沉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2](P80)作者说,“感情而要在沉 静中回忆,可见不纯然是自然地流露。痛定思痛才是真正的沉痛,和当场大叫一声‘痛死我 了’是不同的”。[2](P90)
《林以亮诗话》延续了《前言后语》的观点,并延伸到对中国新诗的评估中。他批评了新 诗的浅薄、狭隘与偏激,指出病根在于全盘接受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与背弃中国古典文化。 诗人“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根本忽略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性质、构造和音乐性”,[1]( P18) “整个读书界和群众都免不了浪漫主义的坏影响:无病呻吟,感伤,暴露,以破坏逞一 时之快,喜欢喊口号和用大字眼,感情冲动而缺乏自制,个人主义等等”,[1](P56)“他们 的作品都犯了浅而露的毛病”。[1](P60)被他具体指证的有:意象派(施蛰存)和象征派(李 金发),他们仅仅学得西洋诗的皮毛;冯至与梁宗岱,没有掌握梵乐希和里尔克的深邃、严 谨和纯真;新月派有贡献,“可惜他们只提出了一些问题,却不能深究并加以解答……他们 对西洋诗虽然熟悉,可只是极少数浪漫主义诗人”。[1](P56-60)
林以亮还思考了新诗的出路,从诗的形式、题材和语言风格几方面细加研究。首先,他研 究了新诗创作中节奏与字数的关系。他从方块文字的特点——建筑性(文字排列起来和印刷 后,每个字所占空间相等)入手,指出新月诗人已经了解这一点,但是“整齐的字数不一定 产生调和的音节,新月派诗人有时硬性规定每一个中国字等于英文的一个音节”。譬如,把 英文的五拍诗改换成中文的十个字一行。他认为,所谓的一拍只是随着语言自然节奏而来的 一个停顿,这种停顿通常是两三个一组,有时也可以多到四个字。许多新诗人对此认识不清 ,所以出现了要求每行字数一样的“豆腐干”体。[1](P1-2)此外,他还结合吴兴华、闻一 多的诗作,分析了新诗创作中借鉴英诗体式(如抑扬格无韵五拍诗、十四行诗等)的得失。[1 ](P18-19)
其次,他指出,新诗的理想模式应是现代诗的精神与中国古诗优秀传统的有机结合。他所 认定的现代诗精神是感性理性相融,包容人生百味的多元美感;它应富于启示,深邃而又纯 真,冷静而不滥情。他引用现代诗人奥登的话加以说明,“诗并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 ;诗是深刻的,同时却又浅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随 时变换不定”。[1](P57-59)而他所说的中国古诗优秀传统也着重于包容性与启示性。他指 出,中国古诗形式谨严,而题材宽广,赠答、应制、唱和、咏物、送别,甚至议论和讽刺都 可以入诗。可惜许多新诗作者戴着19世纪浪漫主义的眼镜看中国古诗,结果未能发现那些能 “给读者一种新的启示,使读者对人生和历史有更深了解”的好诗。他还指出,40年代初期 ,出现了王佐良、杜运燮、穆旦这样一批诗人,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出发点和技巧与西方现 代诗人非常接近,可惜未能与古代汉诗接上,反而把新诗与古诗传统和汉字特色的距离越拉 越大。[1]
再次,他针对新诗语言与题材上的弊端中肯地指出,“新诗语言一定要超出大众化和口语 之上……不妨采用一部分可以接受的文言句法”。[1](P62)新诗的题材要超越太过抒情(感 伤化)和太过严肃(政治化)的藩篱。[1]
林以亮以上论述写于50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处于混沌不明的时期,他没有轻率地为新 诗开出万灵的药方。他认为,问题的彻底解决有待于多方的试验和长期潜心研究,更有待于 天才诗人的出现。
二
余光中是五四新诗的继承者,他说:“五四以后三十年间的新文学,我在大陆的少年时代 已濡染有年。”“我写新诗,开始是走新月派格律诗的路子。”[3](P311)但是余光中并不 愿在新月派的月影下徘徊过久,长期涉猎、钻研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英诗)和中国古典文学 (特别是唐诗宋文),不间断地文学创作探索,使他具有敏锐不俗的艺术感觉和精深宏大的文 学史眼光,能够综观全局,有轻重有比例。因此,他在新文学的研究中,能发掘杰作,也能 批评劣作,不至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早在60年代,余光中已觉察到新文学的局限,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化不够,对中国古典 文 学的再估价也不准确……盲目地否定传统中的某些精华,在改造社会的热忱中,他们偏重了 作品的社会意义,忽略了美感的价值”。[4](P15)他大胆号召“中国新文学史第一章已经写 完……第二章已经写下了绪论,但仍留下大片的空白,等我们去飞跃”。[5](P10)
70年代他到港任教,先后开了“中国新诗”、“中国现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等课程 。[3]为此,他重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写了大量的笔记和讲义,已整理发表的有《评戴望 舒的诗》、《闻一多的三首诗》、《新诗的评价——抽样评郭沫若的诗》、《论朱自清的散 文》、《徐志摩诗小论》。此时,他还写了一些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文章:《骆驼与虎》 、《闻道长安似弈棋》、《论中文之西化》、《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谈新诗的三 个问题》。涉及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朱自清、徐志摩、戴望舒等十多位重要作家,评论 涵盖了诗歌、小说、散文多种体裁。
7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处于僵局中,流行或通行的撰述不是偏于政治挂帅就是 流于泛述草评,少见深入的分析和犀利的批评,余光中的研究颇见新意。
余光中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以精细的鉴赏为基础。如对徐志摩《偶然》一诗的品评,他仔 细 分析了此诗的格律、句法与取材。对戴望舒诗歌《我的记忆》、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 河》和《荷塘月色》,余光中都用了千字甚至两千字的篇幅详加分析。《早期作家笔下的西 化中文》一文,把鲁迅、周作人、徐志摩、何其芳、艾青等新文学名家笔下的西化拗句摘出 ,一一加以纠正。[5](P123-134)这些评析,不仅显示出一个中国作家文字素养和艺术视野 ,而且表现了批评家不惧流俗的责任感。
余光中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纵观全局。他认为新文学上承古典,旁采西洋,必焉穷究西东 ,对其来龙去脉与成败得失,才能有个通盘的认识。因此,他总是将新文学作品放置于中西 文学杰作构筑的艺术世界中,把特定作品与古往今来题材相近风格相似的作品相比较,把新 文学与整个文学史相沟通,从中估定美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戴望 舒的诗与李贺、济慈、何其芳、方旗比较;朱自清的散文与苏轼散文;徐志摩的诗与雪莱、 哈代之诗,郭沫若诗和与其题材接近的杜甫诗、美国现代诗的参照阐发。余光中说,“颇有 一些文学史家或评论家,喜欢抽刀断水,用中国新文学本身的标准,(假定真有这么一个标 准)来评估新文学作家的地位。这种绝缘的评价,恐怕是站不住脚的”。[3](P331)
在通观全局与细微辨析的研究中,余光中着重剖析的是新文学的两个通病:一是伤感滥情 ;二是恶性西化的文字。余光中认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前者是西而不化在创作风格与 情感格调上的症侯,后者是西而不化在语汇句法上的病灶。(注:余光中对恶性西化中文的批评,可参见徐学《西而不化与西而化之》,载《台湾研究集 刊》2000年第2期。)
三
梁锡华的新文学研究的范围较广,著述颇丰。他在收集史料,爬梳源流上用力甚勤。这方 面的著作有《徐志摩英文书信集》、《徐志摩新传》、《徐志摩诗文补遗》、《闻一多诸作 家遗佚诗文集》、《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爱眉小札》等多种。这些著述,为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者保存和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徐志摩英文书信集》,如果不是他当年 在海外四处奔波,这些原始材料恐将永远流失。
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梁锡华着手历史考证,以坚实的史料纠正沿袭的谬误及僵固的 偏见,发掘一些为人们忽略的历史原生态。如《说人·话文·道情》和《一段哀情》把徐志 摩对凌叔华、林徽音发乎情而止于礼的微妙关系和盘托出。[6]《新月的内部圆缺》从徐志 摩的书信入手,看出了《新月月刊》编辑宗旨上的变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徐志摩与新月同仁 的貌合神离。[7]《徐志摩第一册诗集的初版及其他》细细说明了徐志摩对处女诗集大加删 改的缘由……[7]
梁锡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贡献是突破意识形态的困囿,恢复那些被忽略或被扭曲 的作家的原貌。他研究的被人忽视甚至几乎要遗忘了的作家有林徽音、康白情等,作品有闻 一多、沈从文的小诗,朱自清的长诗,钱钟书和梁实秋的少作,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土白 诗和口语诗……他用了很多的力气去阐述那些被误解的作家,比如,闻一多与梁实秋。
在梁锡华开始研究闻一多之时,论者对闻大多着重其人其行而对他的诗文轻描淡写一笔带 过;对其人其行也偏重闻一多后期的政治参与。梁锡华重塑了闻一多文学史的真实形象,他 对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做了细致入微的评析。他分析了闻诗的色调和意象——红色为主的色调 ;烟、灰、火意象群;金石珠宝意象群以及蛇、蜘蛛、蝙蝠意象群;分析了闻一多的诗式包 括“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的格律诗和“多类纷陈即美”的土白诗。对闻一多所受的中 外唯美诗人的影响,闻一多刚烈而虔敬的爱情姿态……也一一论列,由此,完整展现了闻一 多诗歌丰富多彩的美学内涵。当然,他也没有否定闻一多诗歌中的爱国之情。他在研究中把 闻一多的爱国情怀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考查,分为几个层次,感性的爱,理性的爱,对故乡 故国的爱与对东方文化的爱,诗人的爱国之情与艺术生命的关联由此得到更清晰的展现。
梁实秋是一个长期遭人误解的作家,梁锡华对他的研究也许不及对徐志摩那么广泛而深入 ,但应该说梁锡华是最早挺身而出于国际论坛上为梁实秋正名的学者。1980年,梁锡华出席 了在巴黎举办的《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海外的 学者,隔绝多年后,第一次同聚一堂,是一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碰撞。梁锡华在会上宣 读了题为《风暴之眼——抗战期间文学史的一页》,全面中肯地阐释了梁实秋《雅舍小品》 的美学价值,并对梁实秋发表“与抗战无关论”的背景和本意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虽然引 来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却打破了文学史意识形态垄断的一统天下,一时小梁挑大梁被传为 佳话。
出于文学本位,也出于对美文的醉心,梁锡华在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常常从文字的分析 入手评定作品,并以此作为评估作家文学史地位的重要依据。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文章有《鲁 迅与现代中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有关中文的联想》、《谈朱自清“理想 的白话文”》、《学者的散文》等。
四
黄维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攻诗歌,其中又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部分。黄 维樑有相当细微的艺术感觉。比如,郭沫若《凤凰涅槃》中有“五百年来的眼 泪淋漓如烛”一句。他说“烛泪滴下来,是相当慢的,杜牧‘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 天明’中用‘垂’字就对了。……郭诗用词不确,为韵所误”。[8](P5)又如对卞之琳《无 题四》“隔江泥衔到你梁上/隔院泉挑到你杯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 史/昨夜付一片轻喟/今朝收两朵微笑/付一枝镜花/收一轮水月/我为你记下流水帐。”黄维 樑节节分析后说,“这首诗所用的意象非常统一:江、泥、泉、海外、舶来、 水月、流水帐,全部与水有关。第一行的梁上,第二行的杯里,第三行的胸前,三者与女子 的距离,越来越近,可谓层次井然。语言则整齐中有变化,古典诗的对仗,用于现代口语中 ,节奏跌宕多姿”。[8](P157-159)这样的评析,足见黄维樑的细读功力。当然 ,黄维樑也不为新批评所囿,他每每从更开阔的视野中俯瞰现代新诗。如对臧 克家《运河》一诗的分析,以“历史感”为标准;评介卞之琳《酸梅汤》则拈出“戏剧独白 ”的技巧。
黄维樑中国现代文学宏观研究的另一贡献在影响研究,这方面的力作是《五四 新诗所受的英美影响》和《论诗的新与旧》。前者探讨新诗的西方源流,后者梳理现代新诗 在修辞技巧和主题思想方面对中国古诗的承继关系,显示出他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力求整体把 握五四新诗的学术取向。
卢玮銮于香港新文学史料整理上用力最勤。自1977年起,她开始对1925-1950年间的香港新 文学活动资料作广泛而细致的搜集,范围包括以下四方面:1.报纸期刊。2.来港文化人的作 品、传记、回忆录、追悼文字。3.访问当年文化人,或对当年文学活动有所了解的前辈,取 得口头或书面的材料。4.近人对该时期的评论与研究成果。她出版的相关著作有《香港的忧 郁》、《香港文纵》。前者收集了1925-1941年间来港作家对香港的描绘和印象,共有45 位作者的48篇作品;后者是她对来港作家文化活动材料的整理和描述。虽然,卢玮銮认为自 己的目的只是“在订正史料后,尽快罗列出来,好让有心修史或研究者取材”,“没有把修 史当作工作目标,一方面因为史料还未齐备,另一方面因为修史必须有见识与胸襟,我十分 清楚自己没有这些条件”。[9](P6)可浏览了她的文集后,发现不仅仅是史料,如她对萧红 、戴望舒在香港活动的追述,不仅仅是作家活动的实录,其中还有新文学作家的特殊际遇和 复杂心态,有从一个个真实细节中突显出的那个过去了的时代风貌。
黄继持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亦有独到之处。在史料的整理编纂上,除与卢玮銮合作研究30 年代居港作家外,更为人称道的是对中国新诗的编选,即《现代中国诗选》。
《现代中国诗选》是一部兼收并蓄视野开阔的诗选。它收录了1917年至1949年间110家诗人 的 479首诗。诗选前有中、英文导论各一篇,并有每个诗人的小传,介绍诗人生平,并且评论 作品风格。此书从香港和美国的各大图书馆搜集了许多的期刊和诗集,从中发掘了很多当时 不为人所知的作者和佳作。此书出版后在海内外赢得好评。远在美国的夏志清教授说“ 说起1949年前的新诗,一般人的注意力还停留在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版的诗集台港书铺 绝 少见到,只有前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选进了不少四十 年代新兴诗人,可供我们研究参考。”[1](P1)经过编选者集体讨论后由黄继持执笔的《现 代中国诗选·导论》可说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诗歌发展小史,全文一万两千多字,理清了 新诗30年的发展脉络,兼顾思想和艺术,并不以政治意识或党派眼光作标准,今天读来仍时 见中肯精当之处。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黄继持也多有阐发,《关于 巴金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思考》和《香港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关系漫谈》,都能别开生面 ,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一条新路。
五
以上分别简述了六位沙田学者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60年代,林 以亮和余光中在台港两地不约而同地觉察到新文学的两大弊病:滥情与西而不化的文字,并 指出其主要病因,是对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认识不足。不少作家仅仅拾取了19世纪 浪漫主义的皮毛,轻率随意地否定中国文字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此时,在夏志清和许芥昱的 帮助下,中文大学的黄继持等一批青年教师也开始持之以恒地搜集和梳理五四以来的新诗, 以此突破狭隘的泛政治化的新文学史。余光中、梁锡华和黄维樑以细读精 析品评了许多范文和名家,并从更为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中为它们重新定位。与此同时,卢 玮銮开始了她扎实而不懈的香港新文学史料挖掘工作。
20年后的今天,重新浏览沙田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稿,可以说它有两大贡献:一是 以史料整理、作家作品论及诗论、散文论等方面的踏实工作,突破了一度盘踞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中的“政治挂帅”和“泛述草评”两座堡垒,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通道。二 是树立了新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风气,其特点如下:
1.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或者以收集和整理史料为基础,或者从作品细读与文字辨析入手 ,在学术空气浑浊学术规范错乱的非常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即将到来的拨乱反正提供 了坚实的立足点。
2.融合中外文化的学术视野。沙田学者大都曾负笈海外,他们对国外的当代文学潮流有相 当的了解,同时又都酷爱中国古典文化,品文论作,每每兼顾中外,出入古今。时隔20年, 重读他们的撰述,许多论点并未过时,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具有道德勇气的破冰之作,也是 富于真知灼见的学术文章。
3.将严谨的学术内容与优美的文字形式相结合。沙田学者都认为文学是文字的艺术,同时 他们都有一支健笔,作论文丝毫不苟,甚至着意文采,努力化生硬为活泼,让人感到面对的 不是几条干枯的理论一堆陈旧的史料,而是一个清晰的头脑和一颗充满情趣和智慧的心灵。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余光中的论文,警语成串,灵感闪烁,学问上有见识,见识上有文彩,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必将存有他的笔迹。
收稿日期:2001-03-12
标签: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徐志摩论文; 闻一多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余光中论文; 诗歌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作品分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