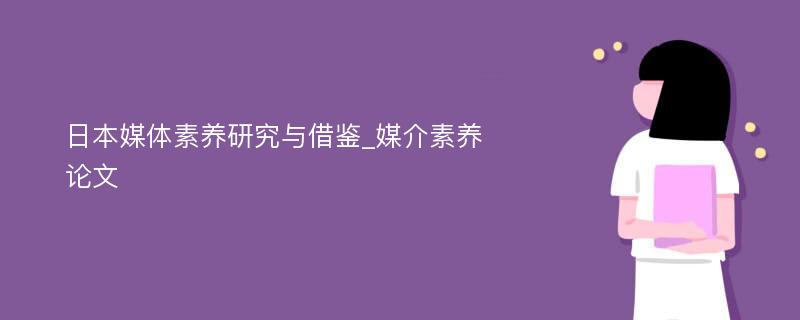
日本媒介素养探究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素养论文,媒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内兴起了讨论和研究媒介素养的热潮,目前的研究主要处于引入国外媒介素养理论和介绍他国的素养实践的层面。纵观讨论热潮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媒介素养的讨论存在着对媒介定位的不清晰和对媒介素养的情境性的忽视等问题。本文探究的是邻国日本的媒介素养的现状,但首先对本文论及的媒介作一个简单界定。媒介素养问题讨论的起点应该明确“素养”到底指向何种媒介。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素养”所指的“媒介”是不同的。有学者认为素养主要与纸质的打印的媒介相关,也有人认为应该扩展到视觉素养比如电视和电影。甚至有的学者提出应将媒介素养修改为电脑的素养。本文所讨论的日本的“媒介素养”是指向广义上的所有媒介,而且从对日本媒介素养现状的讨论中,归纳出日本的社会情境中“媒介素养”的含义是指“市民将媒介放置于社会的情境中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评价的能力,以及获取媒介信息和创造或制作多种媒介形态的能力”。(铃木,2001)这与为西方普遍接受的“我们对处于媒体环境中所碰到的信息背后的意义作解释时所主动运用的一系列透视法”(W.James,2005)的媒介素养的含义有所不同。
一、日本媒介素养的现状
日本媒介素养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学校教育、社会实践方面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本文立足于日本的社会、文化、技术的情境,以日本媒介素养体系的总体特征、教育的出发点和实践的着力点三个方面着眼,展现日本媒介素养的总体现状,力图勾勒出日本媒介素养的特征图景。
1.日本媒介素养体系的特征:侧重“传播能力”
从发生学上看,媒介素养的基本含义是“批判性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 skill)和“传播能力”(communication skill)。欧美传统的媒介素养的概念主要是聚焦大众媒介,重视培育“批判性思考能力”。西尔弗布拉特(silverblatt)明确地将媒介素养内涵的重心置于批判性思考能力,并且强调培育能正确地批判性解读媒介信息的公民的重要性。白金汉(Buckingham)认为媒介素养是“利用和解释媒介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同时指出媒介素养不仅仅是功能主义式的技能,而且包括分析、评价、批评性解读等更大的范围。另外,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提出的媒介教育18项原则以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教育基本理念对媒介素养的论述都侧重于媒介批评能力的培育。(铃木,2001)
然而,日本媒介素养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侧重于对媒介信息的接受和利用能力的“传播能力”。铃木(2001)对媒介素养的界定是“市民将媒介放置于社会的情境中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评价的能力,以及获取媒介信息和创造或制作多种媒介形态的能力”;生田(2000)认为媒介素养是“充分灵活使用媒介传播的发送和接收能力。从更广的范围而言是指通过媒介表现自我以及解读媒介信息意义的综合能力”。这些都将利用、掌握媒介的获取和创造、发送和接收等技术性的能力置于素养能力中的重要地位。另外,从下文论述的日本“媒介素养”活动的“社会行动者网络”中也可以看出日本侧重于媒介信息的接受和利用能力的特征。就此井上(2002)曾尖锐地批判“(日本)学校教育的范围内,对于媒介批评能力的培养不够,国内至今不存在这样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
2.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出发点:强调视听能力和制作能力
今津(2000)指出,欧美的媒介素养研究“一方面是探究影像如何对于人们的情感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是研究如何正确地理解影像”,他认为欧美媒介素养是在深厚的大众文化批评中生发出来的,是以大众传播社会学研究作为媒介素养的根基而展开,而日本“更倾向于依据视听教育课程论、教育技术学或者说是计算机信息论”。也就是说日本媒介素养教育是从重视培养学生对媒介视听能力和制作能力出发的。
日本学校课程教育体系设计中确实将影像视听能力的教育作为最重要一部分。宇川(1980)指出,(在日本)比起“关于影像的教育”(把握影像自身应该传达的内容)而言,“通过影像的教育”(视听教育、传播教育、甚至是教育技术的教育)得到更大的发展。日本最初的媒介素养教程的三大内核就是“理解”(对媒介特性的理解和批判性接受)、“使用”(媒介的利用和选择)和“制作”(媒介的构成和制作)。(冈部,2006)日本国语教科书上媒介素养的内容也集中体现于“节目制作”、“报纸的写作”、“采访方法”等方面。
3.日本媒介素养实践的着力点:“社会行动者网络”的构建
媒介素养的社会教育与正式纳入教学体系的学校教育不同,社会学习没有学习时间的限制,以终身学习为目标,而且学习时间更有弹性,活动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目前,日本媒介素养的着力点已经从以前的学校教育,转为社会学习,力图构建一张各社会主体相互协作的媒介素养社会协力网络。这个网络是由日本各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学界、企业界等各个主体共同构筑的媒介素养教育与实践的“社会行动者网络”。
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日本是一个注重地方性纽带的社会,非政府组织相当发达,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媒介素养的社会活动中,社会组织充当了主体作用。其中最活跃、影响最大的组织要属“FCT媒介素养研究所”了。该组织围绕“儿童·青年与媒介”、“性别与媒介”、“老年人与媒介”、“媒介社会与市民”、“媒介伦理”等研究领域积极而广泛地开展各类研究和各类社会活动,曾多次策划国际研讨会,召开公开的论坛和市民讲座。该研究所原所长铃木教授设立的“铃木媒介素养基金”,每年支出100多万日元资助在媒介素养领域作出贡献的年轻学者。其他的社会组织虽不像“FCT媒介素养研究所”专注于媒介素养活动,但也会时常涉及媒介素养方面的内容。比如笔者曾于2007年6月应邀参加了NPO法人市民科学研究室举行的第18回市民科学讲座,此次讲座讨论的主题就是关于手机和RFID“新媒体技术与市民生活”。
政府组织的大力推动。从日本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媒介素养的践行相当重视,大力推动媒介素养相关活动,为媒介素养活动的推进营造良好的环境。如原邮政省从1999年11月至2000年6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就召开了7次关于青少年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会议。文部科学省2006年开展电视节目制作进教室、“No Television Day”、 “No Game Day”活动,并与学校合作开展“青少年和媒介接触之于其心身健康的影响”的相关调查研究。地方政府如埼玉县政府出资建造了SKIPCITY基地(日常管理委托给相关的社会组织),其中设有NHK电视台和埼玉县电视台的影视资料档案馆、高清电视制作基地、影像制作编辑室和影像制作学习室等;SKIPCITY基地承担着对埼玉县内中小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职责。
学界教育界的鼎力支持。日本许多知名大学都成立相关的媒介素养研究机构,积极开展与媒介素养相关的研究活动。比如日本著名学府东京大学,其情报学府设立了社会和媒介研究机构,并与日本放送局一同发起了MELL(Media Expression,Literacyr and Learning)项目(该项目致力于支持信息素养论、媒介表现论等课程的建设,促进各地方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同时积极地与地方合作开展具体的媒介素养研究项目(如东京都媒介素养项目、长野县媒介素养研究会项目、亚洲image网络项目、媒介教师村项目等)。另外东京大学几乎每个月两次举行面向社会的“公开讲座”,其中的主题也时常会与媒介或媒介素养有关。
企业界的协作配合。日本媒介素养的特征之一是注重对学生和市民的媒介制作能力的培养,这离不开社会企业界的积极协作与配合。日本各地时常举行学生和当地居民参与制作电视节目的活动。如福井县大野市阪谷小学制作的校外活动以及介绍阪谷地区的节目在NHK福井放送局的地方节目中播放。其后的调查显示,共有64%的家长观看了这个节目,其中有88.5%的家长表示观看这个节目后更好地了解了学校课外学习情况。(村野,2006)另外,当地居民参与的节目制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市民制作的节目与电视台制作的节目虽然在质量上有差距,但市民的广泛参与不仅给新闻带来了新鲜材料,而且促进了地区内的互动与了解。另外,NHK从2000年开始对小学高年级学生开展“放送体验俱乐部”活动,让学生们体验媒介的真实生态。“童眼看世界”(Kid Witness News)是松下电器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展的学生课外DIY型教育活动。松下电器向学生们提供相关摄影器材及相关用品,让孩子们通过孩童的独特视角去触摸世界,培养媒介信息的创造力、交流技巧及团队意识。
二、借鉴日本媒介素养的可能性
1.相似的认知基础:中日两国共有的文化认知背景
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史的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明圈,在社会文化方面有着极为相似的认知基础。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实行了西方化,但不是进行个人解放的西方化,而是强化国家的西方化;杜维明先生指出的儒家实际上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张立文教授指出孔子思想的广泛传播深刻地铸就了东亚地区的文化性格;沃勒斯坦教授也提出了“东亚意识”的理论,他认为东亚曾经存在过一种有机关联、自足一体的国际体系,历史上东亚区域的经济、政治秩序曾长期由中国或日本提供,这一政治生态系建构了东亚国家的独特空间意识与国际观念。这些学者虽观点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地看到了包括中日等国在内的东亚文明圈有着许多共享的价值观和相似的认知基础。
同处东亚文明圈中,受儒家文化的浸濡,拥有“东亚意识”的中日两国,在文化背景、社会逻辑和个体认知方式等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比如,欧美人倾向于表达自我,凸显出个人独立的自我。而中日的本土文化则把集体主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种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kitayama & Markus,1995)。日本人在上下文能清楚地表明主语时,较少说“我”,中国人也更倾向于使用“我们”,而非“我”,这也说明了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具有集体主义表征。
2.潜在的合作空间:两国合作网络建构的积极意义
中日有着相似的文化认知背景,在媒介素养的教育与实践中展开多方面交流和多层次合作有着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日本从热衷于学习欧美媒介素养理念和实践经验,转而对亚洲诸国的媒介素养实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本已经与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努力建立交流协作关系,有着相似文化认知基础的中日两国在媒介素养方面的交流协作前景广阔。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运动与青少年局”专门设立了“应对青少年有害环境的对策”的研究项目。项目组成员在2004—2005年期间以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研究对象,围绕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NPO的活动,先后进行了4次海外调查研究。2000年到2005年,东京大学情报学府共展开了六届“Mell Project衍生—亚洲媒体素养教育学术研讨会”,不少台湾学者参加了该研讨会,并与日本学者一起开展相关项目的合作研究。台湾政大传播学院媒介素养研究室至今也已举行了四届台日媒体素养教育论坛,并且与东京大学情报学府合作“真实与再现——台日儿童媒体素养创作与近用计划”,通过日本福冈县Media kids组织与台北政大实小的儿童进行教学研究与交流。
相对而言,中日两国目前在媒介素养方面的对话与交流协作相对不足。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曾于2003年出版了《媒介素养的综合研究:终身教育的视角》一书,其中包括对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和实践活动的介绍。但是国内对于日本媒介素养研究和实践方面的介绍更是处于空白状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需要中日两国政府、民间以期行动,积极开展学术对话与实践交流。
三、我国媒介素养建设的可行路径
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刚刚发轫,媒介素养的实践也刚刚蹒跚起步,时间短,经验少,正是博众家之长补己之短之时。学界在介绍欧美媒介素养理论的同时,也不应忘记了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日本的媒介素养的研究和践行的现状能给予我们不少的启示。
1.构建符合国情的媒介素养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
建立媒介素养课程体系和相应的评价体系是开展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日本从2003年开始,高中教学将“信息素养教育”列为必修课程;各个中小学校基本上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正式的教学课程,许多大学都开展了媒介素养的教学与实践。日本从中小学到大学基本上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媒介素养的教育体系和评价体系。相比之下,我国学校课程中媒介素养的内容很少,且没有系统地统筹安排,媒介素养的知识散落于各门课程和各块内容之中,如艺术教育课程有媒介的欣赏内容,教育技术课涉及媒介制作的内容,思想品德课则包括了利用媒介的伦理道德问题。因此,研究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媒介素养的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构建符合国情的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刻不容缓。
2.强化“批评能力”和“传播能力”教育
日本在媒介素养的教育与实践上体现出的特征是注重“传播能力”的培养,而“批评思考能力”培育相对不足。这是由于日本和欧美的文化与社会认知结构的差异造成的。欧美的文化是批判思辨性的,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与培育倾向注重社会个体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文化是集体认同性的,学校和社会倾向于培养社会个体的集体主义精神。日本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批判他人做的事是让人难堪的”、“否定别人的意见就是否定对方为人”,从而对媒介的态度就往往是“不要怀疑媒介承载的信息”。因而,相对于欧美人,日本人对媒介有着更高的信赖感。但现实是大众媒介往往与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各种政治、经济体的利益常常“转译”(translate)到媒介信息之中。因此,正确地分析媒介,批判性认知媒介对于每一个公民而言相当重要。所以,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不仅要学习日本在“传播能力”教育方面的先进经验,同时要学习欧美的“批评性思考能力”的培育经验。
3.积极开展媒介素养的社会活动,构建“社会行动者网络”
媒介素养教育与实践的深入开展,离不开整个“社会行动者网络”中每个行动者的积极努力,因此构建“社会行动者网络”是媒介素养活动成功推进的路径。我国目前推动媒介素养研究和实践的中坚力量是相关的学者,他们为媒介素养活动正在或已经做了不少的理论准备,但整个行动者网络远未形成,其他的行动者力量相当脆弱,各级政府部门虽已意识到媒体素养的重要性,但尚无积极的应对措施。我国的社会组织先天发育不足,社会动力不足,新闻媒体尚存理论误区,将媒介素养等同于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素质,缺少与社会其他行动者的互动。日本的“社会行动者网络”的成功实践应该能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