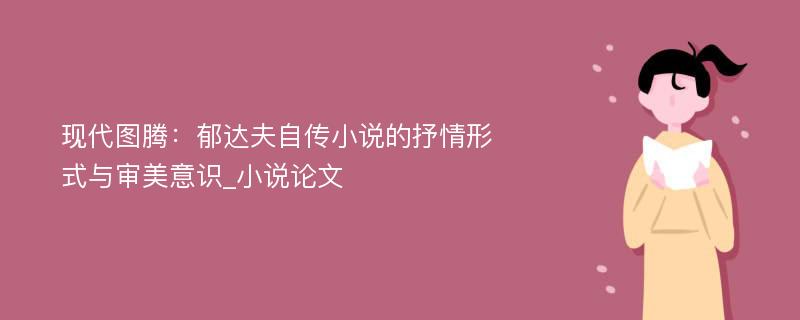
现代之“图腾”——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抒情形式与美学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叙论文,图腾论文,美学论文,抒情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1)03-0081-08
一
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以其直露大胆的内心独白,不仅在痛彻心扉的呐喊中表露出精神上的苦闷和困惑,而且将这种精神上的创伤体验和痛苦经历与中国当时羸弱和病态的历史相结合,创造出涵纳现代意味的个人情绪和社会历史的自叙传文体。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白话短篇小说最初的创作实验之一,而《银灰色的夜》《沉沦》《茫茫夜》《空虚》《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则代表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无论从创作姿态还是小说内蕴而言,郁达夫前期的小说创作都体现出了独特的复杂性。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1]可以说,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以其大胆直露的内心呈现和欲望书写,形成了强大的冲撞力,捣乱了困囿在封建文化思维中的旧梦,从而对中国的国民和社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精神冲击,同时对其进行一次“精神”分析和诊疗,使沉湎于陈腐“梦”幻的人们不得不卸下虚伪而沉重的背甲,睁开蒙昧的眼睛,解放受缚的心灵,去面对自身的灵魂、身体、欲望,真正地去做属于一个“新”人的梦。然而,郁达夫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在他1922年发表的《艺文私见》中,他提出当时是一个“混沌的苦闷时代”,“目下中国,青黄未接。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2]而在《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中,郁达夫同样说道:“记得《沉沦》那一篇东西写好之后,曾给几位当时在东京的朋友看过,他们读了,非但没有什么感想,并且背后头还在笑我说:‘这一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国那里有这一种体裁?’因为当时的中国,思想实在还混乱得很,适之他们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过博得一小部分的学生的同情而已,大家决不想到变迁会这样的快的。”[3]可见,在那个摇摆不定、混沌不清的历史时代,在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符码生成过程中,采取何种思想方式、理论向度和创作姿态,成为现代文学写作者亟需面对的问题。此时的郁达夫选择了以“我”嵌入文本的思想指向和创作姿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浪漫派文学与日本私小说的影响,而郁达夫的尝试则是将这种表达方式进行了一种在地化处理),将本人的精神心态、思想情绪,甚至潜意识中的欲望以及在抑郁中的烦闷,都通过“夫子自道”的方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内心解剖和精神拷问。在郁达夫前期的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形象——零余者,“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4]。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也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和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5]149由此可见,郁达夫在这里强调的并不只是忧郁病的问题,更重要的着眼点还在于“解剖”二字,即在特定历史时间中对以“自叙传”形式在真实与虚构中游移的“他”(包含着自“我”的因素)进行一次直露而深刻的精神层面“解剖/分析”,而“梦”以及通过梦所生产出来的隐喻则是在这一文学生产进程中所倚赖的主要媒介,这也使得郁达夫的“自叙传”形式的小说文本实验,具备了丰厚的思想意蕴和充分美学自觉。
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创作的意义也在于此——将社会和国民精神解剖与个体自“我”的精神拷问合而为一,这不仅体现出一种对转型时代、混沌社会和国民精神迷乱的关注,而且更深入开掘了个体内部的灵魂躁动、情绪郁结和欲望纠斗;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考量通过“梦”的隐喻来结构文本,这样的话语生产不仅产生于现代历史和主体生成过程中,而且代表了时代征候(症候)和现代文学写作者的话语策略、无意识欲望和精神审视中的得与失。
但是作为自叙传小说,作品中的“我”与代表作者立场的“我”是不同的,因为文学作品存在着其特有的独立性空间,但也并不代表可以完全割断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当时特有的时代氛围和思想空间中,自叙传小说中的抒情主人公(即自叙主体“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文学生产过程中特定的话语机制和言说姿态——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情感/精神/心理表达介质中的形式体现和具体生发。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抒情主人公“我”在经历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时,进行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自由联想”:
“就去作筋肉的劳动吧!啊啊,但是我这一双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黄包车的重力。
“自杀!我有勇气,早就干了。现在还能想到这两个字,足证我的志气还没有完全消磨尽哩!
“哈哈哈哈!今天那无轨电车的机器手!他骂我什么来?黄狗,黄狗倒是个好名词……”[6]
这些“零乱断续的思想”,并没有能挽救抒情主人公自身艰难的境地,然而却将其在面临生存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一筹莫展甚至一无是处的思想困境充分展示了出来,而“神经衰弱症”的折磨、自身的柔弱与忧郁,以及在生存面前倍感无奈和哀痛,都使其更深层次的精神困境也得以通过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作者本身来说,“悲剧的出生”造成了他的创伤性体验的同时,也对他整个人生的精神特质和性格特征起到了重要影响,“儿时的记忆……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7]。那种从物质供给到精神生活层面上的匮乏,使得“很悲凉很寂寞”的心情笼罩在郁达夫“孤独的童年”里,少年时代的郁达夫在富春江旁过着傍水人家的诗意生活,“我梦见有一只揩擦得很洁净的船,船上面张着了一面很大很饱满的白帆,我和祖母母亲翠花阿千等都在船上,吃着东西,唱着戏,顺流下去,到了一处不相识的地方”[8]366。郁达夫年少时期待着与亲人朋友同聚并寻找新生活的“梦”也成为他“青春”期的深刻印记,但是,“悲剧的诞生”使那种美好的梦想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小英雄”阿千在大水中被淹死的事实,也连同郁达夫少年时的梦和对青春的向往一起幻灭了。[8]367处于青春期的郁达夫在“书塾和学堂”的初期求学,也经历了性格的叛逆与时代的动荡,尤其是后者,也开始在郁达夫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到了我十三岁的那一年冬天……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9]。此外,“初恋”爱情的受挫更加深化了郁达夫年少的孤独和悲哀,家道的中落造就了郁达夫忧愁抑郁的心性,更重要的是,发生在郁达夫身上的“创伤体验”却又同时被抛置于一个新旧更迭的时代,使得他对时代的动荡、国家的衰落和民生的疾苦体验保有高度的敏感的同时,尤其对人心和人性的隐幽体悟得特别深刻。尽管这些与作品并不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但却是相呼应的。郁达夫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作品中对其笔下人物“神经质”精神状态的剖析,揭示人物病态内心的孤独苦闷,并且通过一种宏大的叙事进行呼唤,使人们从“旧梦”觉醒,从而将个体微观层面的“精神拷问”实践引向宏观的国族和社会层面,就在这样的结合和努力中,一种波涛汹涌的社会思潮慢慢形成,而社会的转向和位移逐渐实现。
而在另一部小说《空虚》中,主人公于质夫面对前来投宿的日本少女,难以抑制内心的苦闷,而当少女的表兄N来接她走时,于质夫则显得更加抑郁和空虚,在他借酒浇愁之后,作者描述了他所做的一个“噩梦”:
他听见那少女又把纸壁门一开,进他的房来。质夫因为恨不过,所以不朝转身来向她说话。她一步一步的走进了他的身边,在席上坐下,用了一只柔软的手搭上他的腰,含了媚意,问他说:
“你在这里恨我么?”
质夫听了她这话,才把身子朝过来,对她一看,只见她的表哥同她并坐在那里。质夫气愤极了,就拿了席上放着的一把刀砍过去。一刀砍去,正碰着她的手臂,剎的一声,她的一只纤手竟被他砍落,鲜血淋漓地躺在席上。[10]
在这里,身处异乡的于质夫由于平时寂寥的生活所产生的空虚情绪,以及少女离去所带来的抑郁和痛苦,压抑于胸中强烈的痛苦和愤恨通过梦境呈现了出来,于质夫的欲望和无意识也于此暴露了出来。从于质夫这个血腥的噩梦中,还存在着做梦者与释梦者的统一与分化,以及欲望的被压抑与被释放问题。吴颂皋在1923年发表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中着重讨论了“性欲”的范围,其在承认弗洛伊德所言之“性欲”存在着狭义的理解——“两性间的恋爱”,而且将其扩展至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温顺”的表示,并指出“性欲”所代表的是广义的“人类本有的倾向”。[11]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人物的欲望主要是通过“性欲”加以表现,而从广义而言,“性欲”代表着一种更为宽泛的“人类本有的倾向”。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郁达夫通过小说的形式,在其笔下的抒情主人公身上创造出了“性欲”的表征,不仅将其欲望通过一个血腥的噩梦表现了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将其思想困境与精神龃龉加以结构;这当中也表现出了郁达夫对自身“性欲”的释放,将历史和主体的压抑通过虚构性的文本(当中又体现为设置式的梦境结构,具体则通过《空虚》中一种极端的宣泄方式)加以表现、疏导和释放,也即体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通过文学的方式实现“欲望的升华”。
二
郁达夫在《文学概论》中坦言:“所以艺术家是对于选择表现象征最精细的人,就是最能纯粹表现自己的人。他的任务,一方面是满足自己的欲求,一方面于不自觉的中间也是满足一般人的艺术的冲动的。”[12]68这种冲动的发生代表着一种现代主体的发现,而在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这种发现是通过一种缺失和贫乏实现的,正是现实与心理的巨大落差,导致了精神层面的痛苦拉锯,梦境的诞生既是对小说人物的精神“结构—分析”,也是艺术的表现者——现代文学写作者的欲望和冲动,更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和时代“无意识”的满足以及在文本实践中的话语行为与精神指向。“艺术既是人生内部深藏着的艺术冲动,即创造欲的产物,那么,当然把这内部的要求表现得最完全最真切的时候价值为最高。”[12]69具体到郁达夫作品对梦的表现和认识中,以虚构性的方式进行结构,是一种艺术“冲动”的表现,可以说,启蒙并不是将人从传统的噩梦中拉回光明的现实,而应该理解为通过种种召唤,从一种梦境渡入另一种梦境,而对于现代文学而言,即是从传统之“梦”过渡到现代之“梦”。
郁达夫的出现并非偶然,“与其说抒情主人公报国无门方才于情欲中寻找麻醉,不如说‘他’是在情欲苦闷中才深切感受到弱国子民的屈辱,因此,《沉沦》的伦理意义(‘反道德’效果)比政治倾向(爱国热忱)更为重要……”[13]现实历史造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伦理和政治的融合与冲突。在《沉沦》中,伦理意义与政治倾向并存于具有自叙传意味的小说主人公的身上,并且以“身体”为表征呈现出来,身在异乡的“他”,其身体依赖于异域的环境,感受着日本的生活风情和艺术氛围,如郁达夫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中就提到的:
若再在这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乱杂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14]
而日本却又恰恰是给自己祖国带来灾难和困境的外族,作者的特殊境遇代表着一个现代身体在异域的特殊政治性际遇,而“我”则被沉重的政治性所包裹,是一个裹挟着传统—现代、个体—国族、精神—肉体这些二重对立以及在对立中发生严重裂变的政治身体,因此带来了所谓的性的苦闷与精神病疾。这种身体上的冲突与裂痕,又与其他身在国内的人们受到西方思想浪潮冲击而遭受蜕变的民族心灵是同质相生的。
在小说《沉沦》的开头部分出现了华兹华斯的诗歌,作者将此一文学的因素直接移置于文本的主要位置,嵌入到主人公“他”的忧郁“病”与“性”苦闷中,意欲以弗洛伊德所说的“升华”来抵抗个体精神的“沉沦”。这里便存在着双重意旨,一方面,抒情主人公“他”想通过华兹华斯的诗歌来消解自身的寂寞和苦闷,将“他”的无法减灭的欲望进行转移和另置;另一方面,小说作者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倾吐自身的痛苦和无助,以文学的象征性和隐喻性,释解内心的矛盾和压抑。但是在文本中,“文学”(华兹华斯的诗歌等)的疗法未能舒缓主人公内心的苦闷和压抑,在“沉沦”中挣扎的“他”也无法通过内心独白、日记写作等等方式来冲破精神的障碍和困境,于痛苦不堪的“神经病”中难以自拔,难以“升华”。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作为小说作者的郁达夫,在一个患有“神经病”的时代和社会中,又是否可以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升华”进而民族的“沉沦”呢?在其自叙传小说中,这样寓“沉沦”与“升华”于一体的文体实验意义和价值何在?国家和民族意识面临苏醒的“国民”及其“性”意识中无法消解的苦闷如何得以体现和摆脱?在具体的自叙传小说写作中,作者如何穿梭于现实与虚构之间,在文本中合理调节“叙”与“传”的素材,使源于内心紧张的创作本身,能缓解精神的焦虑?作者在国族和自“我”精神拷问实践历程中通过“梦”的隐喻对小说抒情主人公的精神“解剖”和“分析”又是通过怎样的文本形式加以呈现的?
许地山的散文《花香雾气中的梦》以妻子的梦及醒后夫妻俩的谈话为中心,其中妻子在复述梦的情节时引用女郎的话说到“你所认的不在东西,乃在使用东西的人和时间;你所爱的不在体质,乃在体质所表的情。你怎样爱月呢?是爱那悬在空中已经老死的暗球么?你怎样爱雪呢?是爱它那种砭人肌骨的凛冽么?”[15]人们所体认和爱护的,并不一定是内在的实体,而常常表现为对实体外部形式与延伸性想象的追逐。而丈夫最后说到“到底没有找着我”,则一语中的:“梦”并没有特定的核心和本质,而其本身则是一个具有特定征兆的作品(Work),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相类似,代表的是一种想象性的结构,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其内在虚无的空心,关键在于其组合形态的形式和结构,以及这种构造形式所彰显出来的价值内涵,因此,需要通过种种方式对其进行解析和阐释,从中形成丰富的悬而未决的创造性言说。鲁迅《狂人日记》以“救救孩子”结尾不仅让小说戛然而止,而且作者也没有对此举出相应的对策和方案,这与《新青年》中的许多文章动不动就列出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的突进式举动形成鲜明的对比。① 对于新文化思维的崛起与新民族意识的催生而言,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无疑能够为其创造出特有的形式,尽管文学并不直接指示最实际的用途,但却为各种社会、人生、精神和文化愿景提供多元的可能性,并为其设计出种种想象的空间。
在郁达夫心中,对“祖国”和“国民”的体认,存在着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二律背反,和当时许多现代文学作者的思想不谋而合,郁达夫必然早就有着一个对羸弱的民族国家的体认,并且认为生活于其中的国民也存在着严重精神缺憾的“神经质”倾向,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鲁迅的阿Q与郁达夫的“祖国”是相类似的。这里有必要先援引阿Q的梦: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16]
鲁迅如此详尽描述参与“革命”后“飘飘然”的阿Q在土谷祠做的“美梦”,可以说,这个梦境无论是对阿Q还是鲁迅而言,都是“酣畅淋漓”的。对于阿Q的梦而言,阿Q既是做梦者,以其独到的精神胜利法达成“欲望的满足”,但由于鲁迅是虚构小说的作者,因而阿Q的梦也可以说是鲁迅“做”的,即通过阿Q的梦,不仅结构出中国传统社会中陈旧腐朽的部分,而且也通过阿Q的假革命反思了晚清和民国革命空幻的虚梦,而这些现实以及围绕相关的社会历史的思考,显然成为了智识者编织现代之“梦”的素材;另一方面,作为阿Q之梦的文本载体的《阿Q正传》,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批判、拯救和启蒙,则无疑成为鲁迅为“五四”这场现代之梦所创造出来的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既是做梦人,也是释梦人,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由此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和思想启蒙之“梦”的创造者。这个包含着阿Q的梦的文本,不仅蕴含着鲁迅作为作者和读者对阿Q的梦进行解析的过程,背后不乏无情的揭露和痛斥,同时也表明鲁迅是沉溺于新文化的现代之“梦”中,并且通过小说创作的方式,赋予这种时代无意识以形式表征而成为“旧梦”拆解者和“新梦”织造者,代表的是鲁迅们及其所处时代的一种历史无意识的欲望满足。
三
在众多现代文学写作者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巨大的悲愤和宏大的志愿,从而形成了对羸弱病态的社会、国家和国民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精神拷问的“冲动”,这种欲求通过他们的小说反映了出来。对于郁达夫而言,例如在其代表作《沉沦》中,尽管具有“自叙传”性质的主人公“他”对祖国的控诉和哀怨不时地出现,这种情绪显然在其身上孕育已久,但这种社会精神拷问的目的在诉诸文学表现时,则往往将其加以形式化而归入到“个体”——“我”的精神拷问过程中。在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个体精神拷问”实践中,所蕴含的“我”及其所包孕的现代主体问题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我”既不是作者本身,所代表的也不是作品中的虚设人物,而是指示着虚构者自身的主体色彩和现代意识,是一种历史和时代的现实表征。从文学创作层面而言,“我”不仅是作者赖以形式化为小说文本的轴心要素,通过“自白”和“抒情”的方式透视精神状况以及无意识欲望的介质,重点讨论“自白”和“抒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是被解剖和分析的对象,郁达夫怀抱着“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这个“自我扩张的信念”,[17]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是千真万确的”,并进一步指出“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紧抱在一起”。[18]一方面,“我”成为一个自足的系统,体现出如同人体内部经脉、血液及身体机能的稳定运转状态;另一方面,“我”也成为作者及其“自我”信念的延伸,而当以“我”为核心所进行的规模化延展、剖析和审视,所表示的即是作为一个时代表征的无意识欲望。
从广义而言,郁达夫在其自叙传小说创作中所强调的“我”,不仅代表着作为创作者和生产者的“我”本身,而且还包括作品中其他具有“自白”倾向的抒情主人公——甚至包括以第三人称为主的写作,正如郁达夫在《日记文学》中所谈到的:“我们都知道,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传的色彩的,而这一种自叙传,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不自觉的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如贝朗的长诗Childe Harold里的破绽之类。并且缕缕直叙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的时候,读者若仔细一想,何以这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会被作者晓得这样精细?”[19]261这里所隐含的意思是,即便是运用第三人称来表现,但是由于在刻画人物“心理状态”时,则同样能体现出“文学家的作品”是由作者的授意形成的,反映出来的是作者对人物的虚构和设计,因此也可以视为带有作者的“自传”意味。然而,也正因为此,渗透了过多作者自我的因素的小说作品往往让人对其真实性产生质疑,这“却是文学上的绝大危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郁达夫看来,答案便是“日记的体裁”,因为“日记的目的,本来是在给你自己一个人看,为减轻你自己一个人的苦闷,或预防你一个人的私事遗忘而写的”。[19]261-262在日记中,作者通过自由地抒发,利用自白和抒情的方式将自“我”的抑郁倾吐出来,从而达到排遣和消解的目的,这当中也并不排除种种虚构和想象,而由于日记的私密色彩,作者也不消对其真实性负责。与此相对应的即是“日记体的文学”,作者通过日记的写作,提高了题材选择的自由度,可以随意出入于文本。而从郁达夫对中西方日记文学的介绍和讨论中可以看出,他更倾向于通过日记文学“解剖自己”、“批评自己”,对自己的苦闷进行“鞭挞”以至达到缓解甚而消除痛苦的目的。由此观之,郁达夫的小说所具有的“自叙传”色彩,大致与其所倡导的日记文学内涵和特性相当;而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而言,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创作,实际上也可以视为是中国社会和国族创作的“日记”,揭示的是“国”的意识萌生和发展之际的社会整体心理,解剖和分析的也是广大“国民”的精神状况,透视国族长久以来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中隐含的心理病痛和精神性创伤。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的抒情主人公显然成为作者进行宏大精神诊疗意图的具体对象,但是,问题在于,郁达夫创作的初衷并不是要启蒙世人和改造社会,他在创作小说集《沉沦》的过程中,甚至提出“这两篇东西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5]149。可见,郁达夫在写作中还故意避开了敏感的现实话题,也不屑于“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20]。因为他遵循的是“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写作理念,注重对自我体验的表现,意在揭示和解剖人物的性格心理和精神苦闷,然而,即便如此,郁达夫也仍然被归入了启蒙者的行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郁达夫连同其小说作品却又是被时代和历史所规定所结构的。
《青烟》是郁达夫1923年创作的一部在形式上颇为独特的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描述了一个青年忧郁病患者的精神状态,尤其以大篇幅详述了“我”所做的一个幻梦。然而,在“我”的梦中出现的于质夫,是在郁达夫其他小说中(如《怀乡病者》《空虚》《秋柳》等)出现过的抒情主人公。而在《青烟》中,于质夫在“我”的梦中再现,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转换成了对“他”的心理和行为的聚焦,悲凉抑郁的空气依然充斥在于质夫的梦中,贫困落魄的于质夫回到家乡,面对家道中落的哀戚,无法接受沉痛现实的他最后投河自尽。事实上,梦中所呈现的于质夫的悲剧故事是小说主体,问题在于,根据郁达夫其他小说中将于质夫作为独立抒情主人公的习惯,郁达夫大可以直接述写于质夫的故事部分,但此处却是通过“我”的梦境来完成,这种具有包孕意味的小说结构,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怎样的效果?小说又是如何通过具有同质性的人物——“我”和于质夫的心绪叠合,来展现在那个“秽浊”时代中青年的精神病疾?具体而言,小说的中心意象是“青烟”,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物体,在虚与实中缥缈不定,成为小说中抒情主人公的情绪心理的表征,“自家以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21]。与其说这是一种对现实“物事”难以把捉的状态,不如说代表着“我”的心理迷惘和精神困境,生存困顿的“我”,忍受着小说作品“受人攻击”的抑郁,生活的“寂寥”和“郁闷”使其深切地感受到命运的幻灭与虚无。在这种现实和心理的双重困境中,于质夫走进了“我”的夜梦,“我”的精神状态正是通过于质夫得以延伸的,而正是通过这样的形式,再加上“青烟”这一意象,从而结构成了小说本身。事实上,郁达夫前期创作的小说中精心设置的抒情主人公“我”一出场,就同时承载了多种文化内涵。“我”不仅是作者作品中虚构的人物类型,也是“自叙传”的表现形式,代表着作者的意念膨胀和精神延展;而且郁达夫笔下“我”的传统中国式的身体往往在浸润异域(日本)文化时表现出种种撕裂,作为一种现代主体在沉浮不定的时代出现。更重要的还在于,“我”的存在依托于各种形式语言的凸现,这些语言的生成不仅仅体现的是话语行为,实际上,“我”的身体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包括时代、历史、人际关系等)及其在自我发现过程中所遭受的欲望纠斗、虚空缠绕和无名焦虑,同样表现为某种内在语言的表达。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我”的意识和心灵深处所形成并得以运行的梦幻、呓语、想象、冥思以及以此为症兆(征兆)的精神病特质等,都是可以用来指认“我”(一种现代意义中的主体性征)的整体语言。这些具有特殊指涉功能的广义性语言,则成为某种隐喻②,而隐喻的具体化陈述和具象化表达则形成了一条无限延伸的能指链,犹如一道强大的生产线,参与到现代文学的书写和创造中。
可见,郁达夫以一种浪漫式的“我”来显现国民的主体发现,并通过此来揭示和剖析民众精神病症。与西方浪漫派意义上的“我”的主体生成历程不同之处在于,郁达夫笔下苦闷而忧郁的“我”是经过“旅行”而实现了在地化的现代主体,通过“性”的压抑和苦闷加以表现,与此同时,抒情主人公精神状态的“梦”与“醒”又往往与国族在时代沉浮激荡中的精神病症密切相连,主体的性格忧郁、心灵焦虑和精神病痛又是在遭受外族侵凌和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境况中生成的。因此,郁达夫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无疑同时经历了国民(国家、国族)与主体(自我、性)的双重蜕变,而这显然造成了“现代主体”的创伤性体验,现代文学写作者的“精神拷问”实践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郁达夫而言,自叙传的形式使他能够更多地倾泻“我”的情绪和感受,将抒情主人公的内心躁动和精神病疾充分展示出来;然而回过头来说,对某种形式的选择(自叙传小说的形式厘定)则迫使作者不得不有意识地在现实中的我与虚构作品中的“我”保持距离,从而才能形成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并以此达到情感和灵魂的“净化”,这不仅是缓解写作者自身焦虑的良方,而且也是现代文学写作可以成为置身于外的“旁观者”——“梦”的解析者(占梦者)——精神病医生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还在于郁达夫对自叙传文体这一形式的选择,“形式是在艺术运动中确定的,而任何艺术都需要把自己寄托到一个确定了的世界之中,它能够把任何不确定的、朦胧模糊的、处于自在状态中的生活原素和意识原素,按照特定的美学理想统一和组合起来”[22]。在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中,不仅人物的“梦”及其中蕴含的国民集体无意识和现实历史的无意识被“组合”了起来,而且从中透露出来的社会、时代、国族的精神病症也得以结构,而这些“原素”的聚合都不可避免地归入到写作者的“美学理想”中,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体现为一种现代修辞的运用。这种在现代文学作者笔下生成的新的形式和修辞又往往与其创造的“梦”的隐喻相勾连,并且以特定的文学形式(如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为美学旨归的文本实践,将那些社会的、国民的以及知识者本身的“梦”和其中的精神病疾结构了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之相关的精神解析实践则又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权力话语和文学符码,而依托于此的精神法则也得以制定和运行。这种建立在精神之法上的评判、解剖和分析准则,以及让当时的现代文学写作者坚信不疑并汲汲以求之的时代性整体精神质询,成为移植于现代时间中的“图腾”行为——一种基于特定的美学自觉的艺术形式追求。
收稿日期:2011-03-12
注释:
① 参见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见《刺丛里的求索》,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67-293页。
② 本文主要讨论的即是关于“梦”的隐喻。
标签:小说论文; 郁达夫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阿q精神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鲁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