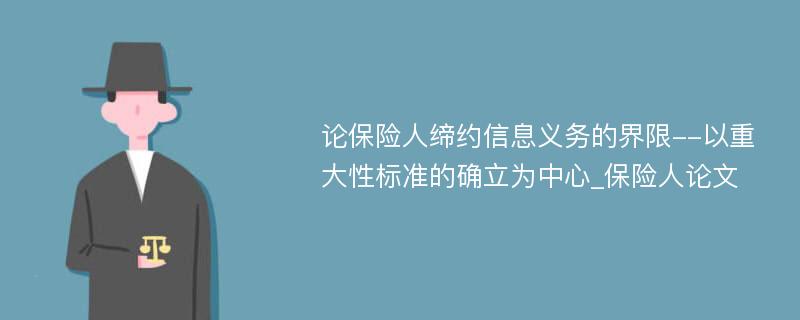
保险人缔约信息义务的边界——以重要性标准之建立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险人论文,边界论文,重要性论文,义务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序言
保险合同是高度附合性与技术性合同。附合性理念下的保险合同,依循“接受抑或走人”(take it or leave it)的规则,一般投保人无对合同内容增、删、变、减之余地;技术性理念下的保险合同,体现为保险条款术语的晦涩难懂与冗长繁杂,非经专家明释普通人几难以明了何所云。如美国保险法专家约翰·F·道宾(John F.Dobbyn)所言:“从理论上讲,保险法仅仅是合同法的一块领地,但如果有人以为合同中的字词适用于它们的常用释义,那么这块领地就会像雷区一样布满陷阱。”①这种保险合同知识性信息上的不对称使保险人对保险消费者(投保人)具有“不合理优势(Unconscionable Advantage)”,使“保险人从与被保险人的不公平交易中占了便宜”。②由此,规制保险人缔约信息提供以衡平保险合同两造之不公平性为各国保险立法与判例所重视。③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17条修订了原《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强制说明义务制度,不仅增订了保险人格式条款(保险条款)的订约时提供义务和内容一般说明义务,且增订了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提示并明确说明义务。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客体由原《保险法》中的“责任免除条款”修改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这框定了保险人订约时提示并明确说明的边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显然,《保险法》课以保险人免除其责任的条款“明确说明”义务意在彰显免责条款对投保人缔约决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116条、第131条和162条从监管的角度,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和保险代理人在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的行为,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重要情况”概念的出现亦表明保险合同的内容是存在重要与否的程度差异的。保险人应为缔约提示并明确说明的重要事项是否限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即已足?是否应确立“重要性”标准以规范保险人缔约提示并明确说明的边界?何种条款或事项可以列入“重要性”范畴?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确立“重要性标准”之实益
在普通法传统中,缔约之际的信息披露义务被区分为两个部分:如实披露所知的全部重要信息的义务和不得误述重要信息的义务,一般被称为披露规则与误述规则。在披露规则与误述规则中,信息的重要性均是关键的一个环节。在误述中,被错误陈述的信息应该是重要的信息;在如实披露义务中,应被揭露的信息也应为重要的信息。同时,重要性问题有时与诱因因素(inducement)又相互作用,相互印证。在保险实务中,被错误说明或未予披露的信息越重要,投保人越容易被诱导而订立合同;同时,投保人被误述或隐瞒的信息所诱导而与保险人订立了合同,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该事实的重要性。保险合同中的信息规制着眼于纠正保险合同双方在缔约之际信息的不对称地位,力求在保险合同中实现公平交易。
一般来说,保险合同条款或信息的重要性主要从性质上判断。就保险合同的性质而言,如果某一合同条款或信息的揭示、说明或建议是否适当会直接对投保人缔约决策构成实质性影响,则该条款或信息即具有重要性。在日本保险法上,“重要事项”的概念在有关保险人资讯提供或说明义务规则中居于核心地位,亦为构成判断说明事项的惟一标准。日本《保险业法》第100条之2所规定的保险人所欲说明的“重要事项”是“与业务有关的重要事项”,而该法第300条第1项1号所规定的保险人所欲说明的“重要事项”则是“保险合同条款的重要事项”。日本保险法学者山下有信认为,所谓的“合同条款的重要事项”,系指对投保人作出是否缔结保险合同的判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④前者之“重要事项”所应涵盖的范围显然要宽于后者之“重要事项”范围,而且违反后果也不尽相同;违反后者之“重要事项”说明义务将课以刑事罚,⑤而违反前者之“重要事项”说明义务则不课以刑事罚。但法律并未具体规定什么样的事项是“重要事项”,⑥以及保险人用何种方法尽到何种程度的说明义务。
“重要事项”(或“重要信息”)这个词的意思在各种规定中的意义都是一样的,还是有所差异?其判断标准是否就是指左右投保人缔约意思决定的信息或对投保人缔约判断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抑或是指构成投保人合理缔约判断的必要信息?日本《保险业法》第300条第1项1号所指称的有关重要事项的说明义务,究竟是以一般保险业的保险投保人为基准来进行客观的判断,还是适应个别投保人的特质和情况,进行主观的判断?作为《保险业法》的规定,若采用主观判断为基准,恐怕是难以想像的。但在不过多地依托于《保险业法》第300条第1项1号,而是从民事法律上的说明义务角度考虑,似可主张采用主观判断为基准。上述日本保险法规范上对“重要”一词的使用本身可以构成法律解释学上的问题。当歧义出现时,对于事项是否重要,在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间常会发生争议,对于应作说明的事项若不在客观上予以明文化、确定化,就会演变成保险人对全部事项进行说明,其不但会大大增加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的成本,其结果亦会不利于投保人。由上显然,对“重要事项”边界的界定就显得极其必要。
三、“重要性”标准的判断
在“斯堪的亚案”中,初审法官斯泰因(Steyn J.)认为:“在考虑告知义务范围的时候,出发点应该是这样的:在恰当的案件中,它将覆盖主要在保险人知识范围内的情况,这些情况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是不知道并且不能知道的,但是确是重要的情况,因为它们对于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的决定有一定影响。”更进一步的观点是,应告知的重要情况不仅包括影响被保险人签订合同决定的情况,甚至包括对签订合同中的任何条款(如保证条款、除外条款)有一定影响的情况。⑦而上诉法院在确定保险人告知义务范围时,采取了比斯泰因法官更严格的标准:“保险人要告知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只要这些情况对于投保的风险是重要的或对于根据保单求偿是重要的,并且是一个谨慎的被保险人在决定是否将风险交付给保险人时要考虑的情况。”⑧根据上诉法院的观点,保险人有义务向被保险人说明承保范围和保单条款,只要被保险人不能被期待明了。上诉法院在其观点中提出了“谨慎的被保险人”的概念,并将其在决定是否将风险交付给保险人时要考虑的情况,均认为是“重要的”。
将“谨慎的被保险人”所虑及的情况认定为重要性测试(materialtest)标准的合理性自不待言,惟“谨慎的被保险人”以其知识结构及智能是否能虑及到影响其投保决策的真正重要的事项,则不无疑问。将保险人关于保险合同及与之相关的“重要信息”提供、提示与说明义务的范围仰赖于“谨慎的被保险人”所考虑的情况往往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利。因为一般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一定具备相当的保险专业知识而知悉何者为决定其缔约与否之“重要信息”,其所认为或预见的“重要信息”与保险人所认为或预见的“重要信息”会有相当的差距。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未认识或预见而保险人明知的“重要信息”,保险人不为告知或说明,则不啻于在订约中挖掘一“陷阱”,由此,被保险人的保险保障难免有落空之虞。总之,“谨慎的被保险人”或“合理的被保险人”等标准会限缩保险人提供、提示并说明的重要信息的范围,减轻其信息提供工具不足或瑕疵之责,不利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权益之维护。
“重要”一词的涵义以普通的相对方为标准进行客观的判断,与分场合、以个别的相对方为标准进行主观的判断会有差异。本文从客观标准的角度,提出三个判断的维度:a.左右是否缔结合同之判断的程度;b.影响是否缔结合同之判断的程度;c.即使不影响对缔约的判断,充分提供信息并说明的必要性有多大。关于a和b,是否应加以区分,十分微妙。“左右”一定是实质性影响,但“影响”未必是实质性或“决定性”的。某一信息或事项可以“左右”合同当事人是否缔约,则该信息或事项一定是重要信息或事项;某一信息对是否缔约不起实质性作用,则该信息就不能构成重要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重要性的判断,应是a标准,亦即是实质性影响标准。在Banque Financiere De La Cifé S.A.V.Westgat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⑨一案中,将“影响一谨慎的被保险人决定是否将拟投保之保险向该保险人投保之所有事项”作为保险人应告知的义务,这是采决定性影响标准的著名判例。
日本《消费者合同法》将违反对“重要事项”说明义务作为消费者行使合同撤销权或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要件,其“重要事项”被法律条文定义为“与消费者合同有关,会影响到一般的消费者是否缔结该消费者合同的决定的”事项(日本《消费者合同法》第4条4项)。日本法案制作事务局的解释为:按照合同缔结时的一般社会大众的观念,想要缔结该消费者合同的一般消费者,对于是否缔结该合同,左右其判断的、可以从客观上来考虑的有关该消费者合同的基本事项(按照通常能够预见到的合同的目的,一般消费者关于该消费者合同的缔结在形成合理的意思表示时,通常有必要认知的重要的事项)。⑩由该解释言之,基本上采用的是实质性影响标准。在日本《消费者合同法》中,对重要事项的不实说明引起的消费者的误解和消费者缔结合同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撤销权产生的要件(《消费者合同法》第4条1项1号、2项),(11)重要性的要件和因果关系的要件是相区别的,上述关于重要性的讨论,只要采实质性影响标准,则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实际上基本不需要了。相反,如果宽松到b标准,则对因误解而缔结了合同这种因果关系的证明就重新被要求了。从这一点看,a与b之区分,尚存实益。
日本《金融商品贩卖法》(12)采列举主义方式列出了金融商品贩卖业者于营业贩卖之际,对顾客应为说明义务的“重要事项”(该法第3条第1款1-3项)。(13)除具体列举出“重要事项”者外,还于承认政令之规定中进行了定义:“关于该金融商品的贩卖,影响到顾客之判断的重要事项。”将“发生本金亏损的可能性”作为重要说明事项,其理由之一在于,金融商品的权利具有抽象性和期待性,其获利与否具有不确定性风险;对顾客而言其所支付的价款能否确保(本金),为其购买时决定性的判断标准。在此可以理解为是a标准。应提及的是,该法具体列出的“重要事项”,未必是传统民法上承认的信息提供义务或说明义务的事项。这并不是说其他的事项不是重要事项,只是考虑到没有必要将一些对顾客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容易理解的事项再课以法律上信息提供与说明义务。因此,作为重要性的标准,只要认为是实质性影响即足。在日本《金融商品贩卖法》中,作为把金融商品相关的风险转移给顾客的要件,对该法规定的重要事项予以类型化的说明义务,以确保缔约双方高度预见的可能性,很有借鉴意义。
不论如何,以a为标准和以b为标准,均是以对接受说明(投保人)的一方作出是否缔结合同的判断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为重要考虑的。此外,与合同有关的信息提供或说明,从a、b以外的观点言之,亦有其重要性。基于这种观点的标准即为c。例如,保险合同的全部或其中的重要条款信息的事先公开,是否是合同发生约束力的要件,以及保险合同制定者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效果要件等问题中,c标准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14)
四、重要信息的边界
保险合同订立之际,保险人应尽其可能满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获取缔约决策所需的充分、必要信息(重要信息),该充分、必要的信息量应当是可确定的和有限的,而不是漫无边际的。本文认为,以下应是确认是否为对投保人缔约决策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重要信息的重要考虑。兹分析如下。
(一)除外与不包括条款(exceptions and exclusions)
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即一般所谓之“除外条款”(exceptions)或“不包括条款”(exclusions)。(15)“除外条款”或“不包括条款”是合同中一类排除或限制,或试图排除或限制合同责任的条款。该条款试图排除或限制的责任可以是合同责任、独立于合同之外的普通法责任或成文法责任。除非成文法中的禁止性规定者外,免责条款可以排除任何合同责任。不论免责条款的存在形式是以免除或限制违约责任的形式出现,以预定损害赔偿额的形式出现,或以限制损害赔偿发生原因或限制危险事故范围的形式出现,只要实质上能达到免除或限制义务或因违反义务所发生的责任者均属于免责条款。(16)在美国,商业普通责任保单(CGL)在对第三方提供广泛保障的同时,包括了数个一致的除外责任(exclusions)。例如,商业普通责任保单并不承保从被保险人立场看属于预期的或将来的损失。除此以外,商业普通责任保险不保障雇员在工作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真实的、假想的或可能来临的解雇、污染的扩散、释放或溢出,源于使用汽车所造成的损失以及被保险人自己财产或产品的损害,也都属于除外责任范畴。(17)
除外责任以外常为忽略的是限制保险人责任条款,其涉及到保险范围的缩小,应认定其为“重要事项”。如日本高等法院在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法院认为,关于驾驶人的年龄限制是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事项,对投保人,一方面要给予保险费按比例减额的优惠,另一方面作为保险合同的内容因为明显缩小了保险的范围,所以以上的特别约定事项解释为符合《保险募集取缔法》第16条第1款I项(即1998年修法后的《保险业法》第300条1款I项)规定的保险合同条款之中“重要的事项”。(18)
在我国台湾地区保险实务中,各保险公司制定的保险单条款均有除外与不包括条款之规定,如《台湾人寿团体一年期伤害保险保险单条款》(A20)(修订文号:2006年09月13日台湾“金管保”二字第49542524481号)第10条为“保险给付的限制”、第11条为“除外责任(原因)”、第12条为“不保事项”、第13条为“合同的无效”。在我国大陆保险实务中,各保险公司制定的保险条款一般均以一部分专门规定“免责条款”。
(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及其违反效果条款
所谓的保险人法律效果告知义务,系指缔约之际保险人应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尽的义务及其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予以提示注意并说明。在保险合同中充斥着大量投保人义务条款,对该类义务条款及其违反效果是否应构成重要信息或事项而成为保险人应当揭示、说明与建议的内容,极具探讨性和实践价值。在某运输公司与太平洋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19)中,终审法院认为,《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条款,并非“责任免除”条款,保险公司无须对其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故运输公司违反此义务,太平洋保险公司理应免除其保险责任,遂判决保险公司拒赔有理。不难发现,虽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条款未约定在“免责条款”栏内,但一旦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这一条款,则会达到和违反“免责条款”一样的法律效果,即保险人免除其保险责任。亦即是说,无论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的是“免责条款”还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条款”,保险人均可免除保险责任,“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条款”在本质上与“免责条款”没有区别。同样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将其置入“免责条款”栏目则保险人必须对该条款予以明确说明,否则不得以该条款主张免责;将其置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栏则保险人无需对其进行明确说明,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此义务,保险人却可以此主张免责。这种在保险条款之间区分“高低贵贱”、“双重标准”的做法客观上扩大了保险人责任免除的范围,限缩甚或剥夺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权利。而且,由于将这些本质上属于保险人免责范围的条款置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栏内或其他条款中,使其“隐蔽化”,不易引起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注意,当缔约之际保险人不为此“隐蔽条款”提示注意并明确说明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就会认为“免责条款”仅限于“免责条款”栏目内的条款而可能遭受信赖损害。这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也是与当今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趋势不一致的。因此,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条款亦列入保险合同之重要信息,并课以保险人对该重要信息之提供、明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是必要的。我国2009年《保险法》将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修改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仅包括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部分,而且应包括投保人违反义务可致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效果等条款,以及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20)保险人强制说明的范围显然与原《保险法》相比有所扩张。
在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上,保险人的告知或说明义务有极其重要地位。在许多涉及保险法之案例中,此义务的遵守常为特定法律效果的先决条件。尤其经由立法或判例学说形成之“全部或没有之原则”(Alles-odr Nichts-Prinzip),(21)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尽的义务,赋予保险人主动提示违反此义务的法律效果的告知或说明义务。针对充斥于在保险合同中的大量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及其违反效果条款,直接威胁到被保险人对保险给付请求权的合理期待,对该类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条款及其违反效果应构成重要信息或事项而成为保险人缔约揭示、说明与建议的内容。本文认为,保险人应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如下义务条款及其违反效果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
1.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及其法律效果的提示注意及说明义务
保险危险的合理估测有赖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投保客体资料诚实告知以确定保险费率,因此各国保险立法或判例一般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本于最大诚信原则善尽告知义务,无论其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型态脱逃此义务,均应致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根据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显然,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后果是相当严厉的。为免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遭受因无知之损害,保险人有义务提示注意并说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告知重要信息或不实告知或故意不告知或因重大过失不告知重要信息等不同法律效果。
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的修改最重要突破在于:从消费者保护角度结合了欧盟严格要求保险人的指令,详细规制了保险合同信息提供义务及其违反效果。例如,该法第6条增订了保险人对投保人缔约询问义务、(22)提供建议并逐条说明理由义务、(23)对建议记录义务、(24)交付建议和说明文本义务,(25)同时,该法第6条还规定了投保人通过特别的书面声明放弃保险人提供建议及记录建议权利的,保险人应声明明示投保人放弃建议和记录会损害其依本法对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的可能性;(26)第19条增订了投保人对缔约决定有重大意义的以及保险人以文本方式询问的危险情况告知保险人的义务、(27)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28)但保险人在此情况下的合同解除权仅在其以文本方式特别通知提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时才享有;(29)第28条规定了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合同上的对己义务”会导致保险人全部或部分的给付义务免除的法律效果,(30)但投保人违反保险事故发生后产生的说明义务(Auskunftspflicht)或解释义务(Aufklamngspfiicht)的,保险人全部或部分的给付义务免除须以其通过特别的文本方式的通知提示投保人这一法律后果为前提。(31)
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上的建议义务和告知义务均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保险人信息提供义务,保险人违反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构成信息提供义务的违反。如果因保险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致使投保人产生错误而订立合同的,投保人可以撤销保险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当然,如果义务违反不能归责于保险人的,保险人得免除损害赔偿责任。(32)
英国亦注意到保险人应于“建议书及保险单”中提醒被保险人未揭露所有重要信息的后果。《英国1994年人寿保险和单位信托监管组织(Lautro)规则》第L:Ⅲ关于保险合同“建议书及保险单”之L3.6.(3)规定:“若建议书中规定有重要事实之揭露,即应于揭露部分包括一项声明,或于建议书之其他部分以明显之方式为之:(1)提醒注意未揭露所有重要事实之后果,并说明重要事实系指可能影响保险人对建议书之评估及接受与否之事实;(2)提醒注意凡签署人对于某些事实是否属重要事项而有疑虑时,即应将这些事实揭露。”(33)马来西亚《1963年保险法令》第16条(4)规定:“投保申请表格内,若没有显著地印上一项警告,说明‘投保申请人若未竭诚地提供其所知或应知的事实,他可能得不到任何赔偿’,任何马来西亚保险商不得在本邦使用之。”(34)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监管机构亦颁布命令要求保险人的业务人员于招揽保险时,必须善尽说明义务,务使要保人(投保人)充分了解其内容,及对于书面询问不据实说明可能发生的后果,(35)并应先行将保险单送请保户阅览了解,并当面解释容易发生误会之点,以减少核保纠纷。(36)
2.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缴纳保费义务及其法律效果的提示注意及说明义务
保险费乃保险人承担危险的对价,亦即被保险人移转危险所应支付的对价。(37)交付保险费是投保人最主要的合同义务。各国保险法对保费缴纳义务及其违反效果几乎均有规定。例如,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未给付一次性保险费或首期保险费的,保险人免除给付义务(不能归责于投保人的除外),但仅在保险人通过文本方式的特别的通知或在保险单中的突出提示使保险人注意不缴纳保险费的后果时,保险人才能免除给付义务;(38)投保人续期保险费给付迟延的,保险人得以投保人的费用以文本方式为投保人设立给付期间(最短为两周),但仅在保险人将未支付的保险费、利息和费用的款项单独编号并注明期间经过的后果时,期间设立才有效。(39)
在英美法上,保险人通常对被保险人为付费之通知。(40)如分红保单(Participation policy)规定保单之红利(dividends)得用以抵充保费者,如红利不足以抵付保费之全部,保险人应通知被保险人。(41)《纽约州保险法》第151条规定:“除非保险人在保费到期前45日间,以书面通知被保险人,人寿保险合同或长期残废保险合同自迟延之日起1年内不因付费延迟而终止。”(42)
实务中仅仅有付费之通知是不够的,因为一般保险条款中都规定有迟延付费或未付费之法律效果。(43)保险费缴纳的时间一般得于保险合同生效前、生效时或生效后为之,而实务上,常常将保费的给付列为保险合同生效或解除的条件。即是说,即使保险合同已经签订,但由于附有保费交付后保险合同生效的条件,如此一阶段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在我国台湾地区亦有于寿险送金单上载明“要保人以支票交付保险费之全部或一部时,在支票兑现前,本公司不负保险责任”的约定,以“支票兑现”为保险公司负担保险责任之条件。(44)
由上显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按约交付保险费会产生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解除保险合同、承担保险责任始期未至、按实际缴费比例承担责任、投保人解约之费用扣除等后果。
保费可分一次交付或分期交付,在应一次交付而未交付的情形下,可致保险合同的效力不发生;在分期交付而未付之情形下,可致保险合同的效力中止或终止。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36条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30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60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45)考虑到寿险合同一般为长期合同的性质,投保人可能因一时的经济问题或忘记应缴纳时间,若因此丧失保险保障实为可惜,故保险条款都有宽限期之规定,在宽限期内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仍需理赔,当然应在保险金内扣除欠缴保费。
投保人未为保费交付或未按约定交付,一般可视为对保险合同的不履行,保险人据此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承担保险责任并无不当。然出于保险合同特殊性之考虑,如投保人未付或迟延支付保费可直接导致保险人免除其应承担的责任,此种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严重的不利益后果,保险人有必要于合同缔结之际进行明确说明,并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充分认知该法律效果之利害关系,以为预先防范。这亦是基于保护保险消费者知情权之考虑,使其在充分享有相关资讯的情形下,作出最有利的判断及选择。因此,保险人于缔约之先或缔约之际,有必要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主动提示并说明保险单中的保费交付方式及迟延交付法律后果的条款,以敦促、警示其按期付费,或避免脱期付费。
3.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及其法律效果的提示注意及说明义务
所谓危险增加,系指作为保险合同基础的原危险状况发生严重不利于保险人的变动。危险增加应当是重要危险的增加,所谓重要危险的增加,系指危险增加的事实,将会提高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46)如增加的危险对保险人并无严重不利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即无发出通知的必要。因此,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应理解为是重要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日本2008年6月6日公布的新《保险法》第29条将危险增加定义为:“告知事项相关的危险增加,而损害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费低于以该危险为计算基础计算出的保险费的状态。”显然,日本新《保险法》上的危险增加应理解为是危险显著的变更或增加。根据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的规定,“非显著的危险增加”不予考虑“仅出现非显著的危险增加或根据情况应当认为双方约定危险增加也得到保险的”,不适用于因危险增加所致的投保人通知义务、保险人终止合同或增加保费或免除给付义务的情形。(47)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既规定了危险增加的后果,又规定了投保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及不为该通知的法律效果,但未规定保险人须对该法律效果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进行提示或说明。
保险危险增加的意义在于正确估计变动之危险以计算保费,甚或拒保,实以危险共同体的公平为考虑。订约之时保险人所确定承担的危险,如有发生危险变动的情况发生,必打破订约时保险合同当事人间的对价平衡,扩张保险人所负担危险的范围。本于最大诚信原则,投保人应就增加的危险及时通知保险人,以便使保险人因应此情事变更,及时调整合同内容。如投保人不通知或怠于通知此危险增加事实,保险人得主张不承担保险责任或解除合同或终止合同,对此给保险人造成损害甚至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49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文认为,对于如此严重之法律后果,绝非单是希望投保人于合同订立时即可完全明白并为承诺,因此,责以保险人将此严重法律效果缔约时即预为提示或说明,嗣后于危险增加之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怠于或不为通知,再课其以应尽之责,一方面可敦促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注意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以免违反此义务而致保险保障落空或受到损害,另一方面维护了保险交易的安全,因此,对保险人亦不是苛刻要求。
4.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及其法律效果的提示注意及说明义务
保险事故发生后的通知义务,保险人是否在需缔约时预先提示或说明,而后才课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该项义务之责?因保险事故的发生惟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知之最详,其负责通知保险人属事理之当然。实务中,各保险公司设计保险条款时均有保险事故发生通知义务及其义务违反效果的条款。发生保险事故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如果未按约定时间通知保险人的,可能会承担因此而增加费用,甚至导致保险人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因此,发生保险危险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一旦疏忽大意错过通知时间,可能面临保障落空之危险。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8条规定:“要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遇有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之事故发生,除本法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订定外,应于知悉后5日内通知保险人。”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以及早确定责任范围,避免法律事项悬而不决。如时间拖长不利于保险人为调查及取证,可能致保险人无法行使代位权。故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3条规定:“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不于第58条,第59条第3项所规定之限期内为通知者,对于保险人因此所受之损失,应负赔偿责任。”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21条亦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一般而言,法律不应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基于订立合同目的之考虑,及被保险人于保险事故发生后必得补偿之必然,保险事故发生后之通知义务似可不必再由保险人为说明。惟另一方面,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非保险实务之专家,且订立合同之时其未必仔细阅读保单条款或不能读懂保单条款,对违反此项通知义务之效果并不清晰,一俟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陷于非常之境,常常会因疏忽注意而延误通知期限,并须因此疏忽而给保险人造成损害负责。因此,如保险人能于缔约之际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主动说明其违反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的后果,将敦促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于危险事故发生后立即履行本项通知义务,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分析,保险人之有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违反之法律效果的提示或说明义务应存在于整个保险期间,而非仅限于缔约之际。学说上对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亦有批评其太注重形式化,因期限经过等法律效果有多种可能结果,如果要求保险人对于所有可能涉及保险费给付迟延而生的各种行为的法律效果一一加以通知及告知,则不啻要求保险人作一保险法之评论,尤其大而无当的保险人告知义务范围,惟有产生对投保人之吓阻作用而已。(48)
本文以为,基于对信息劣势方的保护,课以保险人关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违反法律效果的信息揭示义务,可以大大减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对保险及法律技术的无知可能陷入的损害危险,有利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缔约能力的平衡。惟保险人信息揭示的范围为何尚须谨慎考虑,但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言,危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保障的丧失不啻是最重要的法律效果,因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保险合同义务之违反可致保险保障丧失法律效果,保险人应予以主动信息揭示。
(三)“特约条款”
特约条款是指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于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外,另加约定,承认履行特种义务的条款,又称“个别议商条款”。“特约条款”源自于英美法上的担保(Warranties),或译为保证。英美法上之担保,有肯定担保(Affirmative warranty)与允诺担保(Promissory warranty)之分。(49)肯定担保在于有关订约时(现在)或订约前(过去)某一事实之存在或事务状态之陈述的真实性,若非属真实,不论是否影响危险评估,保险合同自始不生效力或得解除使溯及失效。允诺担保在于担保有关合同订立后(未来)某一作为或不作为之履行或某一事实之存在,若有违反,将使保险合同自违反时起失效或得终止使自违反时起向后失效。(50)
普通法中的保证原则为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欺骗和设置限制创造了条件。另外,承保危险条款——即使是用黑体字标注,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进行表述,也可能是恶意的——这种不合理表现得更加明显的时候是该条款是用小号字体印刷的,很可能隐藏在合同冗长晦涩的条文中不易发现——保险人在很多保险合同中的措辞是没有保险专业知识的普通人所难以理解的。因此,在适用于非海上保险后,由于保险人发现保证之好处,乃开始在保单中无限制地使用保证条款,以特约条款的方式扩大担保范围,致担保条款之滥用,其结果纵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已尽最大善意,但只要轻微违反所担保的陈述就会导致保单无效,这些担保演变成了隐藏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身边且时时威胁其权益保障的不公平的陷阱。保险人甚至因此赢得“伟大的拒赔者”(the great repudiators)之封号。(51)上述种种问题导致了立法和司法对保险人运用保证条款进行限制。另外,法院也对保险人依据保证条款进行抗辩设置了一些重要的限制,许多的判决结果都是运用禁止不公平优势原则的结果。(52)
鉴于上述,美国各州法院于解释合同条款之际,常倾向于保护被保险人。保险人努力搜寻被保险人对保证的违反,以便解除被保险人对保单的权利;法庭则通过严格的法律规则进行解释,对被保险人予以救济。各州法院皆认为:除保险单明文为担保之规定外,被保险人的说明或陈述并不因见诸于保险单文本即解释为担保。(53)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用一节共6个条文规定了“特约条款”,将“特约条款”定义为“为当事人于保险合同基本条款外,承认履行特种义务之条款”(第66条),而且“与保险合同有关之一切事项,不问过去、现在或将来,均得以特约条款定之”(第67条),“保险合同当事人之一方违背特约条款时,他方得解除合同;其危险发生后亦同”(第68条)。当这些“特约条款”均属于投保人方面应履行之义务时,其性质就类似于英美法上的担保条款(Warranties)了。当此情形下投保人违背特约条款,无论保险危险是否发生,保险人均有权解除合同。
我国2009年《保险法》关于“特约条款”的规定见诸于第18条第2款:“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约定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学界一般认为这即是“特约条款”的规定。(54)也有学者认为是“任意条款”(Voluntary clauses)或任选条款,(55)意指由保险合同当事人任意选定的条款。第18条第2款规定的“特约条款”是与本条第1款规定之保险合同基本条款(法定条款)相对应的概念,其范围应当在第1款所列基本条款之外,当事人特约并同意的其他条款。至于何谓“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我国2009年《保险法》未进一步规定其边界范围、规范条件等。目前,我国保险业推行的保险条款均为经保险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条款。这些条款皆经审的保险条款之一般性情形,兼顾保险法的规定与一般合同应具备的条款而成保险合同所称之基本条款。因此,在实务中常显这些基本条款之不足,须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另行约定特别条款,以补其缺失。那么,保险人对“特约条款”是否具有信息说明义务,值得讨论。在司法实务中,只要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因有“特约条款”的保单上签字,法院一般就视为对“特约条款”的同意。例如,在迟某与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保险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针对双方于争议保单《华泰机动车辆综合保险单(正本)》的正页之“特别约定”条款第4条关于承保车辆在保险期限内,从发生第三次保险事故起,每次赔款递增5%的免赔率的约定,法院认为,上述特别约定条款,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迟某在印有特别约定的保险单上签字确认,应视为其已对该合同所有条款知悉,故其以华泰保险分公司未能明示特别约定中的第4条内容为由,要求确认该条款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56)
“特别约定”一般均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设定的义务,保险人往往利用“特别约定”变相达到扩大免责范围的目的,这使“特别约定”成为保险人在基本条款外设定用于限制和排除被保险人实体权利,同时免除保险人实体义务的手段,因此,此类“特别约定”之性质实与责任免除条款无异。本文认为,判断保险人是否应对“特别约定”或“议商条款”进行信息揭示的准据在于对“特约条款”义务性质的认定。在保险合同条款中,何者为保险人单方拟就的格式化保险条款,何者为个别议商条款,从合同条款的外观是否可以作为判断的基础?以合同条款之外观为判断基础本无问题,因只要该条款于合同中被“明示”为“特约条款”或“个别议商条款”,就应认定为其是“特约条款”或“个别议商条款”。但以外观为判断的基础往往只具有推定的效力。换言之,徒有“特约条款”或“个别议商条款”之外观,但该条款事实上却根本未经过双方的议商,而只是保险人单方打印上去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未予认可,那么,仅从外观推定其为“特约条款”的基础就动摇了;反之亦然,虽有格式化保险条款之外观,但并非就已经确定为格式化保险条款,只要有证据表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约过程中,就其中的某些条款确实经过自由意思磋商,且条款之拟定人或使用人(保险人)一方确有让步或修改之真意,则该条款即使在格式条款中也可以转换为“特约条款”或“个别议商条款”。对达成合意的“特约条款”已和普通合同条款无异,是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的结果,双方均应受其拘束,自无须再互为说明。
五、尾论:对保险人缔约信息义务边界规制之建构
保险合同上“重要信息”的判断标准,应以对投保人作出缔结合同的决定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为重要考虑。依据消费者“知情权”之法理,这些对投保人缔约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事项,是其“有权知悉”的事项。这亦可构成另一“有权知悉”标准,即是指在一般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决定是否签订保险合同的思考过程中只要有一个斟酌的合同条款或事项信息对其是否缔约及如何缔约之判断产生影响,即为标准。在此一“实质性影响”标准和“有权知悉”标准下,投保人在明了条款或事项的真实意义后,或拒绝签订该保险合同,或提出相关变更条件或其他要求。此一条款或事项即构成“重要信息”或“要素”。对此“重要信息”或“要素”,保险人及其代理人应主动履行提示注意、建议及说明义务。“特约”亦为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亦会对承保范围构成影响,自然也会影响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判断,故应将其列入“重要信息”。客观上,“重要信息”并不以保险合同条款所列的事项为限,因此,应将“重要信息”扩张解释为,对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作缔约判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信息或事项。
以上为“重要信息”的抽象判断准据,具体到保险合同实务中尚须具体斟酌,具体到不同保险种类,会有所变化。对何谓对投保人缔约决定有实质性影响的事项的认知,既要考虑保险人对重要信息的认知,又要考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重要信息的认知。保险人对重要信息的认知是基于保险专业知识与技术的认知,保险人本于最大诚信原则应充分地对其认知的重要信息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示注意,并提供适合性建议及说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重要信息的认知,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普通外行人的认知,其认知程度和水平定与保险人有具体差异,亦可能将在保险人看来极简单明了的一般性条款或事项认定为重要信息。此情形下,保险人不能因此拒绝对“简单明了”的信息或事项进行释明。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认为,应考虑建立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事项推定为重要事项原则,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之事项,保险人均应履行明示及说明义务。但必须注意的是,“询问说明规则”只能是辅助性规则,不能对所有保险合同条款信息都采取询问说明规则。因为缺乏保险知识、专业技术与经验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往往并不清楚或不知道他们需要询问什么,何为缔约之“重要信息”或“要素”,如以“询问说明规则”为主导性规则,则就失去了立法设立保险人强制说明义务制度的宗旨和意义。因此,保险人缔约信息义务规则的协调,只能以保险人主动提供信息规则为主导,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说明为补充,并以此设计针对不同合同信息的主动揭示规则和询问揭示规则。对于列入保险合同中的重要信息,保险人应当主动履行信息揭示并释明的义务;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之信息应推定为重要信息而为揭示并说明;对于未列入重要信息,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亦未询问的信息,并有合理理由确信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谨慎投保人的理解力且有理解的机会者,保险人可不为主动说明。比如合同中之姓名、地址、年龄、性别等显明易知条款、双方议商条款等无需使用保险人信息义务规则特别加以规范。韩国大法院就有判例认为,保险人对一般的、共同的、投保人能充分预测的和不必说明的重要事项未进行说明,视为未违反说明义务。(57)
综合上述,本文认为,保险人缔约信息义务边界的规制,应以“重要性标准”之建构为中心考虑,而“重要性标准”的判断应以对接受信息的一方作出是否缔结保险合同的判断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为重要考虑。我国2009年《保险法》把明确说明的对象限定在“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难以涵盖对投保人缔约决定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全部“要素”,如理赔条款、投连险之收益条款、现金价值条款、宽限期条款等,虽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但会直接影响投保人的缔约判断。易言之,“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为“重要信息”范畴之构成部分,将保险合同中“重要信息”作为保险人缔约信息义务的边界可更周延地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将“非重要信息”排除于保险人信息义务之外亦可有效限缩保险人的缔约成本。换言之,“严重要性标准”不是“包罗万象”的,而是有限的。过窄或过宽的信息量或使保险消费方信息过度失灵或使保险经营方信息义务过度。强制保险人揭示其所掌握的全部主、客观信息是保险人无法负荷的,也是无效率的。因此,必须对保险人缔约信息提供的量予以合理界定。列入“重要信息”范畴的信息应是投保人缔约决策所必要的信息,该必要非保险人的必要,亦不是保险消费者个体的必要,而是指能够最大限度保障保险交易实质公平的信息量,使处于合同信息劣势方通过信息优势方的主动充分披露必要信息克服其信息赤字或瑕疵或错误所致之不利益。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采取具体列举和抽象概括相结合的方法,明确列出保险人缔约前应主动披露的保险合同中包括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及其违反效果条款等可能对投保人缔约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要信息,并予以充分、准确、及时、有效的揭示与释明。基于重要性标准,本文认为,保险人缔约之际信息义务的度量范围应包括:(1)投保人所负担的费用、保费及其费率的变化及其结构信息;(2)保障风险的范围;(3)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条款;(4)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义务及其违反效果条款;(5)权利行使期间及撤销、解除、消灭期间条款;(6)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的事项;(7)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权利放弃效果条款;(8)具有保证性质的特约条款;(9)投资收益及其风险条款;(10)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确定披露的信息;(11)可期待的给付及其计算和销售成本信息。其他对投保人缔约判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其他对投保人缔约判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即是一概括条款,人类的行为受制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即是说,人在接收、储存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58)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无法列举出所有保险人应提供的重要信息。
注释:
①[美]约翰·F·道宾(John.F.Dobbyn):《保险法》(第3版)(英文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②[美]基顿·R·E、威迪斯·A·I:《保险法:基本原理、法律原则与商业惯例指南》(学生版),西部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24页(Keeton R.E.and Widiss A.I.,Insurance Law:A Guid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Legal Doctrines,and Commercial Practices,Student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88,p.624.)。
③典型法例为日本《保险业法》第100条之2关于保险人积极说明义务的规定及第300条第1款1-9项(排除第5项)关于保险人消极说明义务的规定;2008年1月1日实施的新《德国保险合同法》(Versiehemngsvertragsgesetx-VVG)第3、5、6、7、15、19、28、37、38、40、60、61、61、120条等关于保险人缔约信息提供、说明、建议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应尽义务的法律效果的规定;《法国保险法典》L.132-5-1条第2项关于保险人应对合同的基本条款、撤销权的行使条件、撤销权行使后死亡保险金的归属等问题作以明确的说明,并应交付含有该说明的信息提供书等缔约信息提供义务的规定等。
④[日]山下友信:《保险法》,有斐阁股份公司2005年版,第169页。
⑤日本《保险业法施行规则》第317条之2规定:“属于下列各号某一情况者,处以1年以下监禁或100万日元以下罚款,或者,并罚:……(4)违反第300条第1项规定,有同条第1号到第3号记载的行为者。”
⑥1981年,日本神户市修改的《保护市民生活条例》中,规定了保险募集时的“重要事项”,要求生命保险界充实生命保险合同所提供的信息。接受《条例》的各家保险公司,在本公司准备的《保险合同指南》中,明确说明了营业职员在募集时,必须给予说明的“重要事项”包括:“该保险的特征和其构成条款”、“申请解除合同(无条件解约)”、“不予支付保险金、赔偿金的情况”、“告知健康状态、职业等的义务”、“保险公司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可延期支付保险费的期间和保险合同的失效”、“保险合同恢复效力”以及“解除合同与解除合同返还有关金额”,以上事项要让投保人彻底知晓。
⑦Law Commission Report No.104(1980)Cmnd.8064,at para.4.48.转引自张劲松:“论海上保险中保险人的告知义务”,载《中国海事审判年刊》(2001年),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⑧同注⑦引文,第97页。张劲松在该文中将保险人告知义务定义为:“保险人按照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向被保险人披露和承保风险及保险求偿有关的重要情况的义务。”我国保险法上关于保险人一般性说明义务的范围限于保险合同内容,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限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因此,张劲松定义的保险人告知义务是个包含保险人合同条款说明义务的较宽的定义。
⑨J.P.P.Shaw:《公共责任保险单概述》(Introduction to Public Liability Policies),黄正宗译述,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1998年版,第17-18页。
⑩[日]山下友信:“保险募集与信息提供规制”,载《财产保险研究》第63卷第1号(2001年5月)。
(11)日本《消费者合同法》第4条1项1号条文:“经营者在作缔结消费者合同的劝诱时的下列各项行为,导致消费者发生下列各项误认并从而作出消费者合同的要约或承诺的意思表示之时,消费者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1)经营者对重要事项的说明与事实不符,而该说明的内容被消费者误认为事实。”《消费者合同法》4条2项条文:“经营者在作缔结消费者合同的劝诱时,就某一重要事项或者与该重要事项相关的事项仅作对该消费者有利的方面的说明,而对该重要事项对该消费者不利的方面的事实(以消费者通常会因该告知而认为该事实不存在为限)故意不作说明,导致消费者误认为该事实不存在并从而作出该消费者合同的要约或承诺的意思表示之时,消费者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但是,虽然该经营者要就该项事实对其作说明,但该消费者作了拒绝的,不在此限。”
(12)日本《金融商品贩卖法》适用于保险合同,该法第2条第4款规定金融商品贩售的行为包括:“缔结以从事保险业法第2条第1项规定的保险业者为保险人之的保险合同或与政令所定在保险或共济相关合同中类似保险合同之要保人或类似者的缔约行为。”
(13)日本《金融商品贩卖法》第3条第1款1-3项条文:“(1)该金融商品的贩卖关于其利息、通货的价格或因其他有价证券市场上行情变动会导致产生本金亏损的可能时,其内容及指标;(2)该金融商品之贩卖关于其从事贩卖者或其他之人之业务或财务状况之变化为原因所导致可能发生本金亏损时,其内容及当事人;(3)除前二项之外,就该金融商品之贩卖影响顾客判断的重要事项,为政令所规定的事由为直接原因,所导致可能发生本金亏损时,其内容及该事由。”
(14)于海纯、吴民许:“日本法上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及其启示”,载《保险研究》2009年第8期,第23页。
(15)施文森认为,除外条款(exceptions)系自原因着眼,指讲某种可能致使保险事故发生之危险予以除外之条款,如车险保单中规定之“本公司对碰撞或翻车所致之损害不负赔偿之责”即属之;不包括条款(exclusions)系自保险事故着眼,指将某种危险事故不予承保之条款。如一般海上保险单所载之“本公司对捕获所受之损失不负赔偿责任”之条款即属之。参见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1集),1988年增订7版,第119-120页。
(16)刘宗荣:“免责约款之研究”,台湾大学法律学系博士论文,1985年6月,第1页。
(17)同注①引书,第44页。
(18)同注⑥引书,第490页。
(19)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渝一中民终字第2060号民事判决书。
(20)同注(14)引文,第24页。
(21)所谓“全部或没有之原则”,系指任何对保险人的请求权完全视保险人是否已履行其应尽义务而定,换言之,如果保险人未尽其应尽义务,则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提出的保险赔偿请求权,保险人不得抗辩,以减少其赔偿金额。参见江朝国:“论保险法上保险人之通知及告知义务”,载《中兴法学》第25期,第129页。
(22)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德国保险合同法》(Versicherung svertrags gesetz-VVG,以下简称VVG)§6(1)。
(23)同注(22)。
(24)同注(22)。
(25)VVG§6(2).
(26)VVG§6(3)、(5).
(27)VVG§19(1).
(28)VVG§19(2)、(3)、(4).
(29)VVG§19(5).
(30)VVG§28(2).
(31)VVG§28(4).
(32)VYG§6(5).
(33)《人寿保险公司咨询揭露相关法令》,梁正德、周玉玫等译,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1999年版,第200-201页。
(34)丘惠中:《马来西亚保险法令》,代理员文摘(马)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40-41页。
(35)中国台湾地区“台财钱字”第17183号行政释令(1979.8.24)。
(36)中国台湾地区“台财钱字”第18890号行政释令(1974.9.18)。
(37)林勋发、梁宇贤、刘与善等:《商事法精论》,今日书局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版,第569页。
(38)VVG§37(2).
(39)VVG§38(1).
(40)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1集),1989年版,第55页。
(41)Vance,Ins.,333(3rd ed.1951)转引自同注(40)引书,第55页。
(42)同注40引书,第55页。
(43)例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17条明确规定:投保人应当在本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保险费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44)林勋发:《保险合同效力论》,1996年版,第179页。
(45)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36条设置催告程序(不是必经程序)作为确定宽限期的方式之一,即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30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此处之催告的时间,应理解为履行到期后的催告,而非履行到期前的催告。但此催告如果发生在超过约定的履行期限的第30日以后,例如,第59日(超过约定的期限60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依法中止),此催告是否发生自第59日起宽限期延长30日的效果?本文认为,当保险人选择以催告方式确定宽限期的条件下,应当发生自第59日起宽限期延长30日的效果。此情形下,保险人不应再以投保人超过约定的期限60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为由主张此时合同效力中止。
(46)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自办发行,2007年出版,第175页。
(47)VVG§27.
(48)同注(21)引文,第132页。
(49)约翰·F·道宾认为,保证分为肯定担保(Affirmative warranty)与允诺担保(Promissory warranty)是万斯(Vance)教授的分类。Amnnative warranty是合同成立前关于某事实的说明,而不涉及合同成立后的问题,如果该说明在合同成立前不真实,则保单自始无效。Promissory wananty则是对某事物将来真实或持续真实所作的表述或允诺。法庭的立场一般是,除非保证明确表明是允诺担保,否则就将其作为肯定担保处理。参见同注①引书,第203页。
(50)同注(37)引文,第680页。
(51)同注(37)引文,第680-681页;另参见蔡丽照:《保险法上确定与控制危险之方法》,1976年1月发行,第118-119页。
(52)同注②引书,第627页。
(53)Moulor v.Insurance C.,111 U.S.335.转引自蔡丽照:《保险法上确定与控制危险之方法》,1976年1月发行,第119页。
(54)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55)李玉泉:《保险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56)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民终字第10216号民事判决书。
(57)韩国大法院1992年5月22日宣布的91号第36642判决。转引自廖建球:“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10日,第23页。
(58)[英]安东尼·奥格斯(Anthony I.Ogus):《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标签:保险人论文; 保险合同论文; 投保人论文; 合同条款论文; 标准保费论文; 保险费率论文; 法律论文; 投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