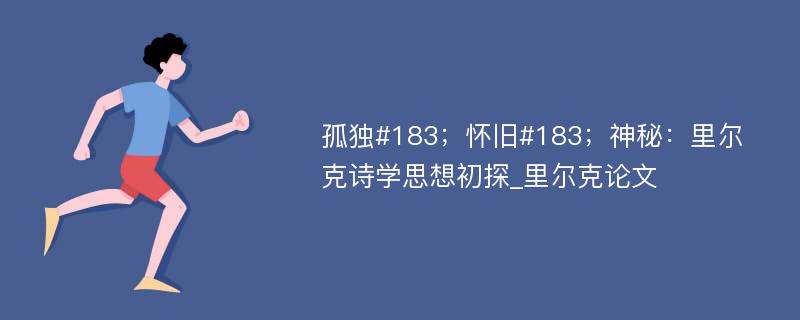
寂寞#183;怀念#183;神秘——里尔克诗学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神秘论文,寂寞论文,思想论文,里尔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5X(2006)02-0073-04
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是现代德语文学中一位影响十分深远的诗人。他在《罗丹论》一书开篇即说,“罗丹未成名前是孤零的。荣誉来了,他也许更孤零了吧。因为荣誉不过是一个新名字四周发生的误会的总和而已。”[1] (P1)里尔克生前虽然有好多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曾走近里尔克精神和情感的腹地,但他终身爱好孤独寂寞,在孤独寂寞里孕育出精神的诗意花朵。他对罗丹的“孤零”体验何尝不是感同身受,对荣誉本质的一语道破也未尝不是夫子自谓也。诗人对寂寞的情有独钟和深刻体验,是本文论述里尔克诗学思想的起点。
一、“忍耐”是一切
里尔克在新城陆军学校的老师荷拉捷克,说“他是一个平静、严肃、天资很高的少年,喜欢寂寞,忍受着宿舍生活的压抑。”[2] (P2)“他再次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些精彩的本能的东西。/和那些早先岁月里的黑暗而丰富的/传奇是无穷无尽的圆圈。”[3] (P130)里尔克的寂寞从童年就开始蛰居在他敏感的心灵了,那是在黑暗中的精神舞者,用孤独划着无穷无尽的圆圈,用想象制造自己的传奇。他在寂寞中忍耐,在寂寞中长大,在寂寞走向无奈的成熟。所谓“无奈的成熟”是意指成熟要付出代价,比如青春的不再,知音友情的中道离弃,家族荣耀的回光返照,等等。虽然他后来反复强调,我们最需要的却只是寂寞,广大的内心的寂寞。但亲情的淡薄和红颜知己的英年早逝却是里尔克终生挥之不去的感伤和遗憾。于是只要他回忆童年,就怀念儿童间寂寞的快乐;成人的尊严在此没有任何价值;所有人世间的存在都罩上了童年寂寞的快乐。里尔克最本原、最重要的体验是在喧嚣尘世间的孤独感,视孤独感为神明,甚至是他创作的必要条件和保证。孤独是走向内心世界的绝妙时刻。人的存在只有在内心热烈地、无限地进行体验时方有可能,恐惧感乃是内心自信的毁灭,只有一种自信硕果独存,那就是不断超越。里尔克诗歌表现的主题主要是生、死、存在,竭力开掘内心世界,意象奇特新颖。生与死的界限不复存在。孤独感在里尔克看来不可受到威胁。里尔克1908年写给保拉·贝克尔的安魂曲:“因为生活和伟大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4] (P75)这种孤独哪怕是夫妻生活都不能打破,当然里尔克主要是针对艺术家而言的。“我感到结婚并不意味着拆除、推倒所有的界墙建立起一种匆忙的共同生活。应该这样说:在理想的婚姻中,夫妻都委托对方担任自己孤独感的卫士,都向对方表达自己必须交于对方的最大信赖。两个人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倘若两个人好像在一起了,那么这就是一种约束,一种使一方或双方失去充分自由和发展可能的同心同德。”[4] (P79)作家是需要寂寞滋润的。寂寞之于诗人里尔克是如此重要,以致他在给一位素未谋面的诗歌爱好者的信中情不自禁地写道,“顺便我劝你尽可能少读审美批评的文字,——它们多半是一偏之见,已经枯僵在没有生命的硬化中,毫无意义;不然就是乖巧的卖弄笔墨,今天这派得势,明天又是相反的那派。艺术品都是源于无穷的寂寞,没有比批评更难望其边际的了。只有爱能够理解它们,把住它们,认识它们的价值。……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完成。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这才是艺术的生活,无论是理解或是创造,都一样。”[2] (P14-15)无穷的寂寞意味着无穷的忍耐和等待,在忍耐等待过程中,体验和回忆得到情感和智慧的发酵,以至创造出包括诗歌在内的伟大艺术作品。里尔克在《孤独者》中这样写道:“不,我的心将变成一座高塔,/我自己将在它边缘上:/那里别无它物,只有痛苦/与无言,只有大千世界。/只有一件在巨大中显得孤单的东西,/它时而变暗,时而又亮起来,/只有一张最后的渴望的脸,/被摈弃为永远无可安慰者。/只有一张最远的石头脸,/甘于承受其内部的重量,/而悄然使之毁灭的广漠空间/却强迫它日益趋于神圣。”[5] (P233)在孤独中走向神圣,同时承载着来自心灵世界的压力。
所以,我们“不能计算时间,岁月都无效,就是十年有时也等于虚无。艺术家是:不算,不数;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它的汁液,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来到。夏天终归是会来的。但它只向着忍耐的人们走来;他们在这里,好像永恒总在他们面前,无忧无虑地寂静而广大。我天天学习,在我所感谢的痛苦中学习:‘忍耐’是一切!”[2] (P15)我们生活在日益物化、也日益浮躁的社会,也许里尔克给予我们的启发不止是诗学意义上的,也有生活意义上的。归根结底我们要使自己不是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尊严并富有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即使我们要忍耐寂寞,承受世俗社会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可这似乎是诗人的宿命,也是一种丰富的怀念,——而怀念出诗人!
怀念是无穷寂寞链条上的蝴蝶结,给诗人灵感降临提供充满温馨的驿站。里尔克的怀念已因拉开距离而更显客观、冷静,但冷静背后却蕴藏着更深沉的情感,只不过这种情感被具体的客观事物所替代。他对法国的艺术和象征主义诗歌很感兴趣,罗丹和象征主义诗人深深地影响着寂寞的诗人。里尔克曾旗帜鲜明地说,“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很够了),——诗是经验。”所以他在诗歌创作中着重表现的不是他的情感,而是对客观事物的冷静观察,经过认真的体验之后再做出精确的描绘,他力图使诗歌达到雕塑的效果。里尔克在其散文杰作《布列格底随笔》中写道,“一个人早年作的诗是这般乏意义,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能,还要悠长的一生;然后,到晚年,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因为诗并不像大众所想的,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单要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姿势。要得能够回忆许多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光光望着它接近的分离,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和容易生气的父母,当他给你一件礼物而你不明白的时候(因为那原是为别一人设的欢喜),和离奇变幻的小孩子底病,和在一间静穆而紧闭的房里度过的日子,海滨的清晨和海的自身,和那与星斗齐飞的高声呼号的夜间的旅行……可是单有记忆犹未足,还要能够忘记它们,当它们太拥挤的时候;还要有很大的忍耐去期待它们回来。因为回忆本身还不是这个,必要等到它们变成我们底血液,眼色和姿势了,等到它们没有了名字而且不能别于我们自己了,那么,然后可以希望在极难得的顷刻,在它们当中伸出一句诗底头一个字来。”[6] (P19-20)忍耐是体验,寂寞地体验;是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一切都本其自然,静静地严肃地从自己的发展中成长起来。大多数诗人的问题也许只是他们最深的情感在自己最微妙的时刻所能回答的。“里尔克是‘心灵’的诗人、内心世界的诗人,而瓦雷里却是‘思想’的诗人、伟大的笛卡儿主义者,吟咏反差强烈、明朗透亮的地中海之光的歌手。”[4] (P228)若欲走向自己的心灵,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么孤独寂寞就成了诗人里尔克的宿命。在这一世界里别人无法分享或承担他的孤独,只有在书信里别人才能有幸分享。里尔克一生不知疲倦地写了大量思想精彩文笔优美的信笺就是证明。“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必须这样孤独下去,必须忍受孤独,不能退缩让步,必须不求助于其他人,而求助于我们在自身感到、并不是认识或理解到的那种神秘莫测的制约力量……”[4] (P165-166)只有孤独才能保持相对的平静,因为“在诗中,人专注或避开人的实在的最深处。他通过平静审视那儿:的确不是通过空闲虚幻的平静如思想的空虚,而是通过一切活力和关系都在其中起作用的无穷的平静。”[7] (P188)
二、记忆与怀念
“凡是能被称之为体验的东西,都是在回忆中建立起来的。”[8] (P85)里尔克对童年的体验尤其如此。虽然这种回忆伴随着欢乐或痛苦,比如因父母婚姻的不幸,再加上母亲的虚荣和无聊,给童年的里尔克心灵带来了无穷的阴影,使之在给友人的私人信笺或诗歌创作染上了忧郁和痛苦的调子。这也许是对母爱渴求的一种间接表达吧;他同众多女性的交往或多或少是出于这方面的心理诉求。“梦想童年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梦想之源,回到了为我们打开世界的梦想。”[9] (P128)虽然这种梦想对里尔克来说可能是模糊的,但他依然顺从地做了,重新创造童年成为他——几乎囊括所有诗人——的秘密追求。童年是对一个人生活最伟大的馈赠。最早的童年依然保持着原初的、自我养育的安全感。而这些深刻的体验“都是在回忆中建立起来的”。
里尔克记忆的阴影里有着父母亲对自己的不理解和严厉,我们从他的《杜伊诺哀歌》长诗里就能读到,“难道我不对?你,在我周围尝到/生活如此苦涩,呷着我的,父亲,/用我的‘必须’沏的第一遍浓茶,/在我的成长中,一再地品尝,/并忙于如此陌生的未来的/回味,你检验我擅长的尊敬,——/你,我的父亲,自你去世,常在/我的希望中,在我内心,怀着恐惧,/你为我微不足道的命运,放弃镇静,/放弃了死者具有的大量镇静,/难道我不对?……”诗人后来又感叹:“哦,童年的时刻,/在那形象背后不仅是过去,/我们面前却没有未来。/但是我们成长,有时候急于/快快长大,为了那些一无所有/只不过已经长大的人们。”回忆过去,是站在此岸的现在打量在水一方的“伊人”;我们羞涩地转身,默默地长大。正如法国符号学家高概所言,我们“只有现在时是被经历的。过去与将来是视界,是从现在出发的视界。人们是根据现在来建立过去和投射将来的。一切都归于现在。”[10] 显然这个“现在”已不单纯,因为“那些久已逝去的人们,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作为我们的禀赋,作为我们命运的负担,作为循环着的血液,作为从时间的深处升发出来的姿态。”[2] (P37-38)而这就是从现实视界出发的过去之于现在的意义,哪怕是怀念的、沉重的。" One travelled to discover the past" [11] (P50):只不过里尔克是在词语里赤脚漫步旅行,踱回到过去的似水流年,回到生活表象的背后和彼岸的精神世界。
三、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
上帝本身一直是里尔克诗歌的对象,并且影响他对自己内心最隐秘的存在的态度,上帝是终极的也是匿名的,超越了所有自我意识的界限。上帝在里尔克那里必须被客观化,从而铸就里尔克的神秘和晦涩。里尔克在孤独感与幻象之间徘徊复徘徊。对“物”的不断质询,折射出里尔克孤独的魂灵。里尔克特别喜欢同代作家鲁道尔夫·卡士纳的一句话,“从内心通向伟大的路是途经牺牲的。”也许对里尔克而言牺牲的只是世俗的喧哗和快乐,但获得的却是对生活表象的超越和升华,——具体表现在由外到内的感情变化上。“感情的内化,特别是爱的感情的内化,是中期以后的里尔克所格外强调的。”[12] (P212)比如国内各种选本上都要选的名诗《豹——在巴黎动物园》,还有似有神助而写就的《杜伊诺哀歌》。
“再没有比批评的文字那样同一件艺术品隔膜的了;同时总是演出来较多或较少的凑巧的误解。一切事物都不是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可理解而又说得出的;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它们是神秘的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赓续着。”[2] (P1)里尔克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语言不是万能的,无法穿透神秘的存在。万物的世界必须吸收融化为自己的意识,可见的世界必须化为不可见的东西,他后期的诗歌正是如此形成的。人类精神的升华必定是从物质世界向着象征世界推进的。《杜伊诺哀歌》中出现“天使”的象征,代表着已完成这种超越过程的生命;而俄耳浦斯则不在话下,是卓越的艺术大师,能随意改造物质环境。里尔克强调指出,他的观念不是基督教的观念;但就其多数含义而言,却显然是宗教性的,几乎像新柏拉图主义或诺斯蒂教派那样,力图通过词语及词语间的象征关系发现一种更强烈的生活方式和经验。实际上里尔克所谓的不可见的世界,其实是指以某种方式塑造的文字世界。里尔克说过,所有的诗人都是俄耳浦斯的再现。象征世界不是一个主观世界,象征之间是相互沟通的:它们并不是密码,不必像对梦中象征那样必须用做梦人内心不为人知或受到压抑的欲望去解释。里尔克明确反对将象征与基督教教义联系起来。“里尔克的一生是在紧张地聆听在其自身之内的神谕的声音中度过的。”[13] (P48)他欲通过诗歌意象以走近现实表象背后或彼岸世界的东西。
四、情欲地生活,情欲地创作
“他的作品中有新颖的技巧,他一方面跟词语搏斗,另一方面也被过度的情绪所俘虏。”[3] (P121)上文我们已经论述了里尔克的语言旅行既是重建童年又是与词语搏斗的过程,情绪化的体验也贯穿其中。古今中外的艺术家的体验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接近于性的体验,接近于它的痛苦与它的快乐,这两种现象本来只是同一渴望与幸福的不同的形式,就像生命与死亡都是人生的组成部分一样。里尔克的“性”是博大的、纯洁的、没有被教会的谬误所诋毁的意义中的“性”,只有这样情欲地创作出来的艺术或者会博大而永久地重要。里尔克心目中的诗人的力是博大的,“坚强似一种原始的冲动,在他自身内有勇往直前的韵律爆发出来像是从雄浑的山中。”[2] (P16)这个“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直率的,毫不装腔作态。“若是你依托自然,依托自然中的单纯,依托于那几乎没人注意到的渺小,这渺小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庞大而不能测度;若是你对于微小都怀有这样的爱,作为一个侍奉者质朴地去赢得一些好像贫穷的事物的信赖:那么,一切对于你就较为轻易、较为一致、较为容易和解了,也许不是在那惊讶着退却的理智中,而是在你最深的意识、觉醒与悟解中得到和解。”[2] (P20)
“精神的创造也是源于生理的创造,同属于一个本质,并且只像是一种身体快感的更轻妙、更兴奋、更有永久性的再现。”[2] (P23)身体与情欲与快感三位一体,紧密相连,但身体无疑是情欲和快感的基础,从身体出发的才是真实的体验,使通向精神维度成为可能。“身体的快感是一种官感的体验,与净洁的观赏或是一个甜美的果实放在我们舌上的净洁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它是我们所应得的丰富而无穷的经验,是一种对于世界的领悟的丰富与光华。”[2] (P22)感受身体的快感不是坏事,但不应把它当作刺激,而应当作向着顶点的聚精会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凡·高对那么多人整天挂着笑容而感到悲哀是可以理解并值得我们深思的。没有精神的肉体快感是苍白的,同样没有肉体的精神是抽象的虚幻的骗人的;一切都要亲身生活的价值绝对离不开我们日益沉重的“肉身”。画家凡·高和诗人里尔克在此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说,诗歌创作离不开肉身的体验,也就离不开女性。里尔克曾由衷地赞美道,“母亲的美是正在尽职的母性;一个丰富的回忆则存在于老妇的身内。”[2] (P24-25)他还认为,男人身内也有母性,无论是身体的或是精神的;他的创造也是一种生产,只要是从最内在的丰满中创造出来的便是生产。[2] (P25)男女两性间的关系在里尔克看来比人们平素所想的更亲密,而不是两性间永无休止的战争,世界伟大的革新也许就在于这一点。由此我们可以反思曾经红火一时的女权主义。“男人同女人从一切错误的感觉与嫌忌里解放出来,不作为对立面互相寻找,而彼此是兄妹或邻居一般,共同以‘人’的立场去工作,以便简捷地、严肃而忍耐地负担那放在他们肩上的艰难的‘性’。”[2] (P25)在少数的事物里绵延着我们所爱的永恒和我们轻轻地分担着的寂寞。里尔克还在诗里情不自禁地呐喊道:“少女们,诗人向你们学习,/学习如何表达你们的孤独”[4] (P87)。
笔者喜欢里尔克,是从阅读他的一本小书《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开始的。读罢被他的思想和精神所激动所鼓舞。再读其诗作,愈来愈认同里尔克给青年诗人冯至的最初印象,——他的诗具有先知般的预言和哲学家的深刻,恰似从自己心里流出的一样。最近重读这本薄薄的然而又非常厚重的大书,其中有关如何写作诗歌的思想依旧那么新鲜深刻,使人对过去的记忆复活,重新用原始人般笨拙而新奇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生活世界,蓦然发现同过去截然不同的景象和体验:孤独和寂寞竟然那么和蔼可亲,哺育着智者的思想和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的诗人虽然活得像流星那么短暂,但他们精神的生命却会长久地生活在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心中。因此,海德格尔从存在、生活和生命去阐释自己的哲学是颇具眼光的,只要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思考自己的存在,使生活和生命拥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让生命诗意地栖居在尘世上,也让生活之流深沉而又缓缓地流向生命的终点。
一位与里尔克从未谋面的收信人由衷地写道,“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2] (P3)我们面对里尔克应该抱着倾听的姿态,默默领悟语言之外的存在;那将是严重的时刻,也是我们心灵最为充盈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