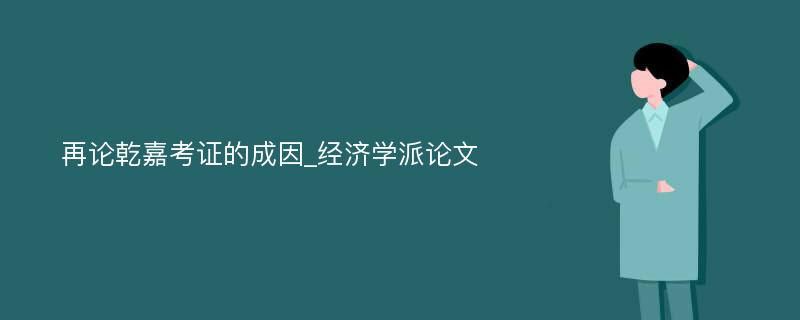
乾嘉考据学成因诸问题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据学论文,成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有清一代学术而言,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或称“经世致用”思潮);二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思潮;三是晚清的春秋公羊学思潮。三个阶段学术各有擅场,但并非截然划界。而就清代学术发展的主线而言,能贯通清代学术全程、并称得上清代学术特色的,那便是“考据之学”,故我们可以称之为“清代考据学”;若往前再加上明中叶以后的考据学,也可以称之为“明清考据学”。
考据之学或考证之学,其所谓“证”、所谓“据”,一般是指文献证据。“考”的意思是考核、考察。因此考据学从字面意义上说,是考核文献证据。考据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形态,它的确立首先需要有一定的文献条件。《论语·八佾》载孔子之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的意思是说,即使在夏、商的后代杞国和宋国那里,已无关于夏、商之礼的文献证据。而无征不信,缺少文献证据便不足以言考证之学。西汉经学注重师法、家法,不同师法、家法之间不能相通,经师信守一家之言,不采他说,故无须考证之学。考据之学的前提是广泛收集证据,但并不以罗列证据为满足,而是要求知识的真确性。东汉郑玄解经,打破今、古文经学的壁垒,综汇各家经说,加以比较,并收集古代社会的礼制证据作为客观参证,以定取舍,故郑玄可以说是儒家经典考据学的鼻祖。宋代虽说是讲理学的时代,但也出现了优秀的考据学著作,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但偶然、个别出现的考据学著作,不足以影响一代学术风气,更谈不上形成考据学的思潮。
作为影响时代风气的考据之学,兴起于明中叶,以后持续发展,至清乾隆时期遂形成一种波澜壮阔的考据学思潮。
一、关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问题
上世纪学术界关于清代学术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乾嘉考据学”的成因问题。之所以用“乾嘉考据学”的提法,是因为当时大部分学者对清初、特别是明代考据学的了解很少,还不能将明中叶以来的考据学看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脉络。所以,我们似乎不应该问“乾嘉考据学”或“清代考据学”的成因问题,因为乾嘉考据学不过是清初考据学的延续和发展,清代考据学不过是明代考据学的延续和发展;而应该问:明中期以杨慎、梅鷟等人为代表的考据学是如何兴起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乾嘉考据学”理解为一个时代主流学术的代名词,而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相并列的话,那么“乾嘉考据学”就可以从广义上来理解,将它上溯于清初乃至明中叶,此正如宋明理学之渊源可以上溯至唐代的韩愈、李翱一样。所以,对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问题我们仍然可继续讨论下去,不一定非要将它修改为“明清考据学”的成因问题来讨论。
探讨乾嘉考据学的成因,首先要确定研究的起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实际上暗含着以下两层意思:(1)考据学思潮发端的时间及其形成原因;(2)考据学思潮何以在清中期(乾嘉时期)成为主流学术。以前的学者或在第一层意义上回答问题,或在第二层意义上回答问题,因而在对问题的理解上,学者之间有错位的现象。
1.考据学思潮发端的时间及其形成原因
以前学术界由于对明代考据学缺乏研究和了解,因此在寻找乾嘉考据学的发端时,一般是把清初的顾炎武作为清代考据学的先导。主此说者又认为,清初学术思想(包括顾炎武的学术思想)的主旋律是经世致用思想,当时的考据学与经世致用思想是有矛盾的,不合拍的;乾嘉时期的学者买椟还珠,继承了清初学者顾炎武等人的考据学,却丢掉了他的经世致用精神。
胡适曾说:“人皆知汉学盛于清代,而很少人知道这个尊崇汉儒的运动在明朝中叶已很兴盛。”(《胡适文存》,第70页)嵇文甫说:“杨升庵慎生当嘉靖间,最号博洽。所著《丹铅录》、《谭苑醍醐》等数十种,虽疎舛伪妄,在所不免,然读书博古,崇尚考据之风,实从此启。”(嵇文甫,第145页)台湾学者林庆彰也说:“在中明心学和复古风潮笼罩中,用修之出现,无异一颗彗星。其挣脱宋学羁绊。倡复汉学运动,并开创数百年考据学风……”(林庆彰,第47页)又说:“考据学大兴的原因,一定要追溯到明代中叶去,绝不是清代自身发展出来的。”(参见周美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林庆彰著《明代考据学研究》,主要论述了明代考据学家杨慎、梅鷟、陈耀文、胡应麟、焦竑、陈第、周婴、方以智等人的学术思想。这部书有力地说明作为影响时代风气的考据之学,实际上发端于明中叶杨慎、梅鷟之时。此一时期的考据学代表人物由于个人的种种原因,成为社会边缘性人物。这些人除梅鷟作专经的考证之外,大多自得其乐地进行杂考性的学术研究。当时阳明心学如日中天,学者看重心性哲学,牛毛茧丝无不辨晰。从事杂考的学者因为缺乏“思想性”,往往不为人们所关注,但其笔记、札记式的解经形式,也许可以看作一种新的经学研究范式:虽然它不追求在整体意义上理解经典,但在对经典中某些重要的疑难问题的解释上,却体现出一种步步深入和寓精于博的特点,其中的许多札记和解释像是一篇篇短小精悍的专题论文。
当学者开始把明中叶的杨慎、梅鷟作为明清考据学思潮的发端之后,不仅其时代比顾炎武之时大为提前了,同时也使得所谓“考据学的成因”问题变得相对单纯了,即不再更多地考虑政治影响的因素,而着重去探讨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和外在条件。
探讨明清考据学的成因,当首先认识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汉代以后学术的发展是由儒家经学主导的,而经典诠释不外训诂和义理两条路,因而训诂之学(汉学)与义理之学(宋学)的交替发展便成为此后学术演进的内在规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经学总论》所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这种看似循环往复的学术发展形式展现了这样一个道理:当一种学术思潮走到尽头的时候,又可能回到起点,重走老路。就此点而言,颇合民间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当初,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为了回应佛教、道教心性理论的挑战,摆脱汉唐经传训诂之学,试图通过以义理解经的方式,重建儒家人文精神的信仰。其时,作为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发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声音,相信只要重新发现古代圣人“性命之学”的绝对真理,便会为人类开出万世太平。在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学者对于汉唐儒者的训诂之学,“弃之如土梗”,几乎不屑一顾。以《古文尚书》为例,朱熹虽然怀疑其为东晋人的伪作,但并不鼓励学者对它认真加以考证。究其原因,一是担忧“《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朱子语类》卷七十九),二是他在“义理之学”与“考证之学”的比较中,认为考证之学是末流学问,甚至可能与义理之学相抵触。① 实际上,对专经的考证相对于杂考而言,并不需要看许多僻书或秘本。就后世梅鷟的《尚书考异》和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而言,其引书之范围主要在魏晋以前,多是常见书,这些书在宋元时代一般学者都是可以看到的。然而这样的考据学成果不出于宋元,而必待明清而后出现,自是学术时尚使然。从宋代至明中叶学者群趋于心性义理之学,人人试图去发现古代圣人“性命之学”的绝对真理,其结果最终导致了“空谈误国”的弊害。明中叶以后,理学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一些学者厌弃理学,遂自觉不自觉地回到汉唐训诂考证之学的老路上来;虽然走的是老路,却又表现出与汉唐训诂考证之学十分不同的特点,即此时考证学者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儒家经典,而是天地万象无所不包,因而其考证文章往往表现出五彩斑斓、引人入胜的特点。
当考察明代考据学家的治学经历时,我们会发现文献考证对于他们似乎只是个人的雅好。但如果把明中叶考据学的兴起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的雅好,这个看法又太表面化了。他们考证的对象是儒学文献,而儒学文献所体现的文化积累有一种知识的条理性和真确性的需求,这是考据学的意义所在,也是考据学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和动力。
以上所说的“文化积累的条理性和真确性的需求”是长期以来一直都存在的,并不是到了明中叶以后才有的。大家知道,汉代以后的文献,除开佛、道两家文献外,基本上皆属于儒家文献,其总量每代激增,发展到明中期已经达到了异常庞大的数量。而且中国传统学术颇不重知识的科学分类,西汉时司马谈《六家要旨》批评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后此弊端并没有很大的改观。而考据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从庞杂的资料中梳理出他们认为有用或有趣的知识来。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考据学之所以特别发达,可以说主要是由传统文献的异常庞杂决定的。
考据学之成立,需要这样几个条件:
一是文献积累数量庞大,非常人所能遍阅索解,以此方见考证意义之重要。若文献存量甚少,稍加翻阅便可知道,又哪里用得着考据学?我们知道,自汉至明,中国文化经过一千五六百年的发展,文献的积累量已经非常巨大。
二是从事考证的学者能较方便见到相关的文献资料。明代杨慎因为曾做过经筵展书官,有机会阅读皇史宬藏书,这属于一个特例。对大多数考证学者而言,主要还是依靠当时民间的刻书和藏书事业。而明中叶以后考据学的兴起,正是与当时民间蓬勃兴起的刻书业和藏书业相一致的。② 而这又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刺激起来的。除此之外,可以说并没有特别的政治方面的原因。
三是要成为考据学家,需要有博闻强记的天分;若读后忘前,则读书再多也难以发现其中的关联性。此外,考据学家还要有勤于搜考、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和较强的资料归纳和分析的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够实现某些知识条理化和真确性追求的目标。
由上分析,考据学之所以在明中叶兴起,文化积累的知识真确性追求和需要是其内在原因,而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刻书业和藏书业的发达是其外在条件。而清初考据学与乾嘉考据学不过是明代考据学的延续和发展。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新学派的创始和新学风的开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一种新学术思想体系的创立并不是其开创者胡乱摸索、盲目撞出的。这里,我们不妨将学者与商人作一类比:商人凭其职业的敏感,懂得向那商机无限的地方投资,以求得丰厚的回报;学者也自有其职业的敏感,当他立意要去发掘文化遗产的时候,也自然懂得哪里是知识的“富矿”,可以做出其产品——学问来。明清时期有那么多考据学家都在各自所选定的治学范围中做出骄人的成绩,也反过来证明这一座考证学的“富矿”有多么巨大;有了这样大的知识“富矿”,当然就会有人发掘。所以考据学的兴起是中国传统文化后期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
言及此,现就清代考据学形成原因的问题,检讨一下梁启超的“理学的反动”说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
先来谈梁启超提出的“理学的反动”说。一种学术思潮为另一种学术思潮所取代,它表示一种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它表示的是后起学术思潮较先前的学术思潮具有异质的性质。如果不具有异质的性质,如明代之心学与宋元之理学虽然有所不同,但同属理学思潮的大范围,便只笼统标识为“宋明理学”,而不别立名目。但一旦标识了新的思潮的名目,那就意味先前的学术思潮已无发展的余地,已经开始走向它的反面。梁启超说清代考据学的形成是对“理学的反动”,说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然而套用梁启超的概括方法,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两汉经学是先秦子学的反动,魏晋玄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宋明理学是隋唐佛学的反动,晚清公羊学是乾嘉汉学的反动,但这些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并没有解释一种思潮是如何转变到它的反面的。因而,我以为此种概括缺乏较强的解释效力。
再来看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余英时较早摆脱就清代论清代和从“外缘”求成因的思想方法,他提出的“内在理路”说可谓别开生面。余英时认为,明代“阳明以来儒学内部‘性即理’(程、朱理学)与‘心即理’(陆、王心学)的争论日趋激烈,尽管争论的两造都理直气壮,充满自信,但毕竟谁也不能说服谁。所以这场官司是不可能在哲学层次上得到结果的……心性官司的两造最后只剩下唯一的最高法院可以上诉,那便是儒学的原始经典”(余英时,1987年,第412页)。因此,“清学便不能是宋明儒学的反命题,而是近世儒学复兴中的第三个阶段……清学正是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两派争执不决的情形下,儒学发展的必然归趋,即义理的是非取决于经典”(同上,1976年,第105-106页)。这一观点影响甚大,学者一时纷纷引述;但今日重新检讨,发现其有许多可以商榷之处。
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脉络,这可以说是“内在理路”。假如把“内在理路”作为研究学术史的一种方法和向度,那就要看是一种怎样的“内在理路”。而实际上,研究者在用“内在理路”说来解释学术史的时候,最容易犯主观构造“内在理路”的错误。上面所引余英时的话中有相当大的主观构造成分。阳明以来儒学内部有争论是事实,但朱学与王学争论焦点是否“性即理”与“心即理”的问题?以及对此问题的争论真的那么“激烈”吗?即使如此,据我的认知,理学中“性即理”与“心即理”一类观念,乃是宋明理学家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才提出的,“儒学的原始经典”中并没有这种问题意识,也没有可以援引的类似的案例。因此,理学中“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争论也不可能用“儒学的原始经典”来判决。如果能用“儒学的原始经典”解决问题,那么可以断言,无论朱熹和王阳明,以他们对儒学经典文献的熟悉程度,问题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应该解决了,无需等待清儒来判决。事实上清儒也没有做这样的判决,他们大多数人并不屑于理学的议题。更主要的是,宋明理学与清学之间并非表现为一种“连续性”,或者说考据学并不是由理学内部的争论衍生出来的。只要研究一下明中叶以后的考据学家的学术经历就会知道,他们基本上不是理学中人,他们的考据学内容也不是要解决朱、王之争的问题。我宁可说他们是当时主流学术——理学之外的边缘学术人物,清初大多数考据学家也是如此。
所以,我以为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是有意义的,但其关于“内在理路”的具体说法则属于主观的构造。若讲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就不能限于宋明理学的时段,而要从儒学发展的更长时段来考虑。在我看来,儒家文化长期积累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条理性和真确性的需要,才是考据学得以形成的“内在理路”。
2.考据学思潮何以在清中期(乾嘉时期)成为主流学术?
如上所述,考据学思潮在明中叶已经兴起了,经清初,迤逦而至清中期,其势转盛,亦属自然。但这里还要强调,虽然考据学有其内在发展的原因和动力,但能在乾嘉时期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也要靠强大的外力帮助。这个强大的外力是什么?就是清廷(主要是康雍乾三朝)统治方略的铁腕主导。学术界关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提出过许多种观点,如“文字狱高压政策”说、“康乾盛世为主”说、“清廷笼络”说等。我认为,以这些观点解释考据学的形成原因有时代错位之嫌,因为如前所说,考据学思潮在明中叶就已经开始了。但如果以这些观点来解释考据学何以在乾嘉时期成为主流学术,则不失为有价值的见解。而在我看来,所有类似的见解都可以归结为“清廷统治方略的铁腕主导”。
清朝前中期的皇帝自幼受过严格而全面的经筵教育,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深厚的学养,特别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学术见地,并不在当时的一流学者之下。但他们毕竟是清朝政权的代表者,他们以维护清政权的长期统治为第一要义。清王朝建国初期,由于忙于军事平定和政权稳定,尚无暇顾及学术文化战线的思想统一工作;到康熙朝后期,国家大体安定,经济生产恢复,清廷统治者从此便开始有意识地直接主导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
清初大约有三类学者,第一类是具有明遗民意识的学者,明清鼎革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给予了他们强烈的刺激,他们痛定思痛,深感宋明理学空疏无用,由此在学术界掀起一股批判理学的思潮,其矛头所向不仅仅是陆王心学,而是直指当时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这一思潮的最大特点是反形上学,主张经世致用。这些学者对于新的清王朝大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此他们具有明遗民特征的思想也只能在民间传播。第二类学者对程朱理学的态度看上去较为温和,但其学术形式却是新的考据学式的;他们对于宋明理学的理气心性一类议题较少兴趣。这一类学者对以后乾嘉时期的学术起了一种典范的效应。第三类学者则依然坚守理学矩矱,他们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延续。清初统治者对第三类学者基本上采取扶持的态度,因而在康熙朝有许多理学名臣;对第二类学者即考据学者,亦时有奖励之词,如康熙御书“耆年笃学”赠胡渭即是其例;而对待第一类学者,鉴于天下初定,只要他们不持明确的反清态度,清廷也报以怀柔、容忍的态度。
康熙后期天下大定,清廷有意识地加强了思想的控制。此时那些早期的明遗民思想家已逐渐凋零,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也随之在思想界消歇,已不须清廷刻意压制。由于清廷此时实行限制讲学、打击“假道学”等政策,清代理学家也只能奉行前贤理念,不敢标新立异、自创新说。因此清廷虽然推崇理学,理学却日渐萎缩,不能自立。
更重要的是清廷此时采取两手政策,一手是通过“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严厉打击那些有反清意识的学者或触犯思想禁忌的人,这其中有许多“冤假错案”。但清廷此举的目的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形成一种思想震慑的氛围。晚清龚自珍有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当时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严重扼杀人民的创造性、形成了百十年来“万马齐喑”局面的真实写照。其后经学家皮锡瑞说:“今日有益之事万不可为,耗有用之精神于此(按:指考据学),良可惜也。以此知乾嘉诸公专搬古董,亦实有不得已之苦衷,犹信陵君醇酒美人意。”(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戊戌年十月廿九日)章太炎在其《学隐》一文中也指出清世文网周密,学者只好逃于训诂考证之中,“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③ 矣”(章太炎,《检论》卷四:《清儒》,见《章太炎全集》第3册)。但若把考据学的形成原因归结为清廷“文字狱”的高压政策,则是有问题的,因为考据学在清廷实行“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之前已经形成了。不过我们又必须承认,清廷实行“文字狱”的高压政策确实对后来考据学独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近年有学者认为,文字狱与考据学的兴盛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种看法恐怕是矫枉过正了。④ “文字狱”对于学术发展走向到底有无影响,凡上个世纪在中国内地经历过“文革”的学者,都会有感同身受的体会。在我看来,“文字狱”对学术文化的影响不能低估,更不能一笔抹煞。但我们也不必因此责难清代的考据学家,把他们看成避祸苟活的人物,把他们的学术看成是“畸形”的学术。
清廷的另一手政策就是积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满族贵族通过军事力量推翻了汉族政权明王朝,建立了清王朝。他们又是汉文化的倾慕者和积极学习者,在一两代人之后,其优秀者的汉文化修养甚至驾汉人而上之。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尽量笼络和吸纳汉族优秀人才,清廷通过设博学宏词科、修明史延揽汉族文化人才,当时一些遗民思想家不愿意合作,其中如黄宗羲等人还有过清王朝很快会垮台的设想(他作《明夷待访录》即以此为前提)。但清王朝逐步稳定大局后,又通过开三礼馆、四库馆等形式进一步延揽汉族文化人才,这一时期明遗民思想家多已去世,新一代的汉族知识分子在名义上已经是清王朝的子民,能参与中央王朝的大型文化工程之中,贡献他们的才智,已经成为他们人生的荣耀了。
应该说,清廷采取这两手政策来主导文化的发展是非常奏效的。台湾学者鲍国顺先生说:“清人入关伊始,恩威并施,怀柔与高压政策,交相利用。前者如年年开科取士……后者如严禁士子集社讲学,批评时政,并屡兴文字狱,迫使读书人不敢轻论义理,于是群将其精神与力量,专趋典籍考证一途,一方面满足做学问的心愿,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政治上的无端迫害。”(鲍国顺,第24页)鲍国顺先生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
近年王俊义、黄爱平关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提出“康乾盛世为主”说,认为“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与考据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统治者对学术文化的大力倡导才是乾嘉学术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这里有必要对这一观点谈谈我的意见。首先,我认为,清廷“文字狱”的高压政策虽然与考据学的产生并无必然联系,但与乾嘉时期考据学的兴盛是有一定关系的。这点已如上述。其次,我承认,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是考据学兴盛的必要条件,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如无康乾盛世时期雄厚的物质基础,怎能编纂刻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那样浩瀚的类书和丛书及各种通志、通典和通考?如无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乾嘉学者又怎能经年累月、怡然自得地‘皓首穷经’?”(王俊义、黄爱平,第273页)王、黄的观点滥觞于梁启超,梁氏曾说:“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梁启超,1990年,第24页)又说:“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同上,1998年,第27页)鲍国顺也说:“清自康熙、雍正、以至乾隆,维持了一段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的安定社会,也直接促成了考证学的发达。因为考证学重分析归纳,此一学问的形式,是需要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方得以顺利进行。而且清代的考证学,主要是典籍的考证,考证典籍,必须仰赖良好的图书环境,而一个秩序安定、物力丰裕的社会,大有助于图书的刊刻、整理与传布。清代考证之学,至乾嘉之际,达于全盛,当非偶然。”(鲍国顺,第25页)考据学的兴盛的确需要政治上稳定统一的大环境,也需要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物质基础,这是一个方面。此外,我还可以补充的是,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而言,乱世往往出思想家,而盛世往往出学问家,因为孔子早就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盛世即是所谓“天下有道”之世,学者对于现实政治多的是歌功颂德,而很少批评议论,他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无关现实社会实际的古董学问而已。从以上种种看,我认为“康乾盛世”说有其合理性的因素,但并不认为这是考据学形成和兴盛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把它看作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点也可纳入“清廷统治方略的铁腕主导”的大框架之内。
现在可以将以上论述总结为三条:第一,在汉以后汉学(训诂之学)、宋学(义理之学)交替发展的内在规律制约下,明中叶以后的学术发展开始转回到汉学的老路上,逐步形成一种考据学思潮;第二,“文化积累的知识条理性和真确性的需求”,构成考据学思潮的深层动因;第三,“清廷统治方略的铁腕主导”排除了学术文化多元发展的可能性,由此而有乾嘉时期考据学“一花独放”的局面。
读者也许要问,既然“文化积累的知识条理性和真确性的需求”是考据学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那么清廷将学者引导到考据学中来,岂不是顺应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吗?是的,清廷的确做了因势利导的工作。但清廷的做法又有大大过头的地方:第一,正常的学术发展总是多元的,如清初学术尚是一种多元的发展,而清廷用其铁腕的两手政策逐步将学者引向考据学之一途。章太炎称其统治术高明隐秘(“工眇踔善”),意亦在此。第二,经世致用本是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乾嘉考据学为考据而考据,完全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由于这样两个特点,遂造成清中期“万马齐喑”的思想禁锢局面。
二、关于乾嘉时期的“学派”问题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被称为“康乾盛世”,其中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彪炳史册,他们本人也颇以“内圣外王”自居。张岱年先生曾在一次谈话中说,一个人既是内圣,又是外王,人人都要以其思想为思想,那别人就没法活了。张先生所言甚是。“康乾盛世”之时,正是清廷对人们的思想钳制最严的时期。在学术史上,关于学派的认定本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说到乾嘉时期有什么“学派”,则显得相当勉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清廷防范学者借“讲学”以树“朋党”,因此在当时标新立异、创立“学派”是一件遭忌讳的事情。
按照我的理解,学术史上的所谓“学派”,其意义并不简单是“一群学者”的意思,它一般须具备三个要件:(1)有共同的学术宗旨;(2)有共同的学术宗师;(3)有学术传承(弟子、门人及私淑等)。具备了这三个要件,可以说具备了“学派”的充分条件。在这三个要件中,第一条——“学术宗旨”的要件是必不可少的,无明确的学术宗旨不足以成为学派。有的时候,几个人或若干人,虽然他们之间并无宗师与弟子的关系,但只要他们有共同的学术宗旨,也可以“学派”称之。但这个“共同的学术宗旨”应该是他们自己有意识标举出来,并为当时的学术界所认可或认知。我们可以以这样的认识来看乾嘉时期的学派。
乾嘉时期宗师级的学者有三位,第一位是惠栋,因他是江苏吴县人,他所代表的学派被后世称为“吴派”;第二位是戴震,因他是皖南人,他所代表的学派被后世称为“皖派”。这里之所以强调“后世”的推许,是因为无论惠栋和戴震,他们在世时都不敢把自己看作某某学派的宗师或领袖。第三位是庄存与,他曾做过皇子的老师,严格说来他的学问并不是考证之学,但他可以说是晚清流行的春秋公羊学的先行者。虽然乾嘉时期宗师级的学者有三位,但勉强而言,学派只有两个:“吴派”和“皖派”。此在当时已为学者所普遍认同,如作为吴派学者的王鸣盛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转引自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全书》第7册,第8页)在这里,我们看到,吴派的宗师是惠栋,其治学宗旨在“求古”;皖派的宗师是戴震,其治学宗旨在“求是”。
至于“常州学派”,虽其宗师庄存与和惠栋、戴震为同时代人,但常州学派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形成过程,其兴起之时已在乾嘉之后。其学派以阐扬春秋公羊学为主,是代乾嘉考据学而起的新的学术思潮,故不应以考据学视之。
学术界还有“扬州学派”的说法,被列入其中的有任大椿、汪中、王念孙、凌廷堪、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人。这些人大多属于戴震门人或后学,当然弟子门人中在学术思想上有大的创新而能卓然自立,也可再创学派,如阳明学派中的泰州学派等即是其例。但在上述数人中,任大椿、汪中、王念孙属前辈学者;后四人过从较密,其中阮元官位名望最高,虽有领袖群伦的材具,但也并未别标宗风。他们的学术风格与戴震的皖派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只是这些学者同居扬州,使当时的扬州有一种较强的学术氛围而已。学术思想贵在独立创新,无大的独立创新便不足以标宗立派。
对于乾嘉时期的学术,学术界有人笼统称之为“乾嘉学派”,以前梁启超也曾顺口如此讲,现在似乎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概念。但严格说来,这是一个习非成是、未加理性反省的概念。“学派”常以学术宗师的姓氏、名号、郡望命名,如以姓氏命名的朱子学派,其宗师为朱熹;以名号命名的蕺山学派,其宗师为刘宗周;以郡望命名的常州学派,其宗师为庄存与等。如果我们笼统地称“乾嘉学派”,那么乾嘉学派的学术宗师具体是谁呢?此外,讲“学派”和讲“学风”不同,讲“学风”可以虚一些,讲“学派”就要落实到具体人。历史上曾有以时代标学术风尚者,如说“正始之音”,可以解释为“正始学风”,而不可解释为“正始学派”。即使对一时代的主流学术,学术史上一般也不以时代称之,如对魏晋玄学不称“魏晋学派”,对宋明理学不称“宋明学派”。盖任何一时代,虽然可能有其占主流地位的学术,但也总有其对立面的学术。譬如乾嘉时期,虽然许多学者从事考证之学,但也有一些学者如彭绍升、姚鼐、方东树、章学诚等人,并不认同当时的考据风习,甚至对考证之学加以批判,他们虽也生活在乾嘉时期,是否也应以“乾嘉学派”称之呢?如前所说,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也生活在乾隆时期,年龄还稍长于戴震,是否也应以“乾嘉学派”称之呢?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说“乾嘉学术”、“乾嘉汉学”、“乾嘉学风”,或加以限定而称“乾嘉考据学派”等,但如笼统地说“乾嘉学派”便欠科学的严谨性,与称“魏晋学派”、“宋明学派”一样讲不通。
三、明清考据学的四个发展阶段
1.明清考据学的发生期
如上所述,考据学思潮的发端可以由清中期上溯于清初,甚至可以上溯于明中期。明代考据学成就之大者,有杨慎、梅鷟、陈耀文、胡应麟、焦竑、陈第、周婴、方以智等人。这一时期的考据学以杂考与专经考证为主,前者以杨慎的《丹铅余录》等著作为代表,后者以梅鷟的《尚书考异》为代表。明代考据学与清代考据学之关系,从逻辑上说有两种可能性:(1)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思潮;(2)它只是各时段偶然出现的一个孤立事件,而不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思潮,乾嘉考据学与其前的考据学毫无瓜葛。我认为,清代考据学与明代考据学是一脉相承的。以明中叶的杨慎、陈第等为例,在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杨慎认为《说文解字》、《尔雅》二书可通行百世,这一见解为清代考据学家所认同;在音韵学方面,杨慎作《古音丛目》、《古音略例》、《转注古音略》等,陈第作《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虽昧于古韵分部之说,然考订多精,开启了清代顾、江、戴、孔、段、王考订古韵之先河,顾炎武就曾言其所著《唐韵正》以杨慎《转注古音略》为蓝本。杨慎的《丹铅余录》的杂考类著作形式也深刻影响了清代的考据学家。
为此,我将明代考据学看作明清考据学的第一期,即发生期。
2.明清考据学的发展期
清初考据学绍承明代而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如顾炎武、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顾祖禹、朱彝尊、胡渭、阎若璩、姚际恒、江永等考据学的大家,其中很多人的学问绝不下于其后乾嘉时期的学者。这一时期的考据学仍以杂考与专经考证为主,前者以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著作为代表,后者以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为代表。清初考据学基本上是延续明代考据学的路数发展的,只是清初学术主流是批判理学(或“经世致用”思潮),他们的学术也服从于这个学术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鼎革所引发的批判理学思潮(或“经世致用”思潮)反而是一种特例和“偶然事件”,掩盖了明中叶以来循序渐进发展的考据之学。而以前关于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研究,更多地关注的是此一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反理学”思想、“早期启蒙”思想等,而对此一时期的考据学成就和特点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但从考据学的发展角度而言,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并不意味学术焦点的转移,它对长期占据学术主流地位的宋明理学所进行的批判和清算,在客观上也为考据学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
为此,我将清初考据学看作明清考据学的第二期,即发展期。
3.明清考据学的鼎盛期
至清中期或称乾嘉时期,清初的那些带有明遗民特征的学者和思想家陆续去世,由他们所掀起的批判理学思潮(或“经世致用”思潮)自然退潮,而原来已经在潜滋暗长的考据之学迅速壮大。此一时期考据学大家辈出,而惠栋、戴震为领军人物。戴震曾说:“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戴震集》,第183页)意思是说,要真正读懂经书,先须有天文、地理、算学、音韵、礼制、博物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否则便没有解经的资格。可能是受戴震此一观念的影响,乾嘉时期考证之学最突出的成就首先是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天算学等方面,其次则在史学、子学方面,而关于经学的考证,虽然在《周易》、三《礼》、《孟子》、《尚书》等方面已有很好的成绩,但对儒家经书进行全面、系统的注疏任务并未在乾嘉时期展开和完成,而有待清后期的考据学者来进行。乾嘉时期的著名考据学家,除惠栋、戴震外,尚有秦蕙田、卢文弨、江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毕沅、翁方纲、金榜、段玉裁、桂馥、孙希旦、任大椿、崔述、邵晋涵、汪中、王念孙、洪亮吉、孔广森、孙星衍、朱彬、凌廷堪、郝懿行、张惠言、江藩、严可均、焦循、阮元、王引之、陈寿祺等人。
为此,我将乾嘉考据学看作明清考据学的第三期,即鼎盛期。
4.明清考据学的延烧期
清后期,春秋公羊学思潮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其代表人物有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朱次琦、陈立、皮锡瑞、廖平、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这些人的能量和社会影响都很大,但在人数上未必比当时的考据学者多。此一时期承乾嘉学术之余绪,又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考据学家,而考据学的成就首先集中在对儒家经书的全面、系统的注疏方面。其次在文字学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晚清甲骨文的发现,使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成为甲骨学的奠基人。此外,这一时期在古书辑佚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绩。除上面提到的几人外,这一时期著名的考据学家还有胡培翚、马瑞辰、王筠、陈奂、朱骏声、刘文淇、黄式三、黄以周、刘宝楠、丁晏、马国翰、陈乔枞、邵懿辰、陈澧、钟文烝、俞樾、王闓运、吴大澂、王先谦、江有诰、缪荃孙、皮锡瑞、崔适、章太炎、刘师培等人。
为此,我将清后期的考据学看作明清考据学的第四期,即延烧期。
注释:
① 如朱熹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晦庵集》卷五十四:《答孙季如》);“若论为学,则考证已是末流”(同上,卷五十九:《答吴斗南》);“恃为考证,而昧于至理”(同上,卷七十四:《策问》)。
② 漆永祥所著《乾嘉考据学研究》是近年关于乾嘉学术研究的一部力作,其书探讨乾嘉考据学成因的篇幅有74页之多,所论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颇为全面。但浅见以为,所列原因过多,也许会掩盖或冲淡主要因素的作用。如其书第一章第二节“古籍错讹炽盛与学术文化日趋繁荣之间的矛盾”开头说:“考据学是对传世古文献的考据,其学赖以兴盛的条件在于必须有大量的古籍传世”,此论可谓先得我心。但接下去又写道:“且在这些古籍错讹日盛的情况下才成为一种客观要求,乾嘉时期的客观情势正复如此。”(漆永祥,第19页)对于这段论述我便不敢苟同了。古籍校勘只是考据学的一个方面,而考据学的功用并不局限于此,并且它也不构成考据学形成的动因。就考据学的主要功用而言,还是在于求得史实与知识的真确。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明清考据学著作基本属于此类。
③ “工眇踔善”出裴骃《史记集解》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此处谓清廷文化统治策略“高明而隐秘”。
④ 漆永祥所著《乾嘉考据学研究》第二章第三节“禁书与文字狱”,一面对清代禁书与文字狱的严重情况作了较详细的分析,一面又提出禁书与文字狱盛行并未能阻止清人著述传世之风气,亦未涉及高层知识分子和学界名流;认为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与禁书和文字狱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此一观点的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在清廷长期实行的专制主义文化政策下,那些高层知识分子和学界名流已经懂得了生存之道和游戏规则,什么能说能写、什么不能说不能写,他们已了然于胸。考据学一类著述当然可以传世,这并不意味当时学者有学术的自由。学者们心知肚明,只要那种有“干碍违禁”思想内容的著述问世,便可能带来满门抄斩的惨祸。晚清国事日蹙、文网渐疏,龚自珍方敢有“避席畏闻文字狱”的诗句,而在乾隆文网严密的时期,恐怕没有人敢作这样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