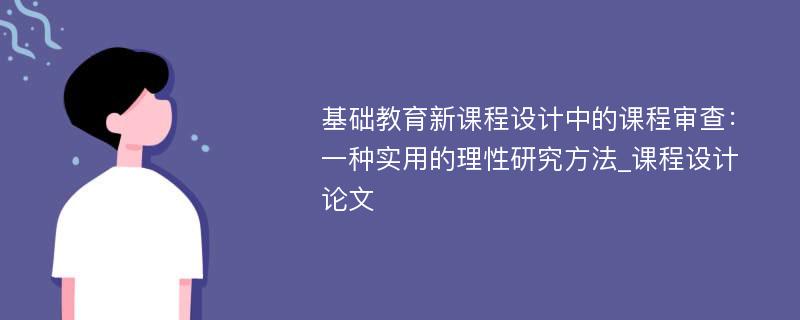
基础教育新课程设计中的课程审议———种实践理性的研究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新课程论文,理性论文,课程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课程审议的概念是1969年由施瓦布提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一直是课 程设计实践中普遍使用的研究与决策方式。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新课程设计是我 国国家课程设计史上参与人员最多的一次,也是充分尝试课程审议的一次课程研究过程 。对此,笔者对20多位亲身经历课标设计的人员进行了访谈,他们中有教育部有关的课 程管理者、资深的课程理论研究者、学科专家等。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本研究还收集 了课标研制中的一些会议笔录。在这些资料中,提炼出对这一实践过程的反省认识,以 期有助于我国当前及未来的课程研究。
一、新课程设计中的课程审议方式
(一)异质的寻求:审议人员的结构
参与新课程设计的人员有的来自高校,有的来自基教系统的教研部门,还有一线的中 小学教师、出版社的人员。来自高校的课程设计人员分为学科专家与课程专家。其中课 程专家一般来自高师院校、教育科研院所,有教育学、心理学或课程论等的知识背景; 学科专家一般是高师院校、普通高校的学科专业研究人员。教研员、中小学教师也都是 各自岗位上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是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出版社的人员比较了解我国以 往及现实课程、教材情况,因此,在组合中很多课标组都有出版社的人员。事实上,许 多课程设计者都有复杂的专业背景和职业背景,很难清楚地界定究竟属于哪一类专家。 以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标研制组为例,成员共31人,来自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9 人填报的专业特长为“数学教育”,另外一位为基础数学,一位为教育学。然而,填报 “数学教育”的研究者,有的在本科阶段学习的专业是数学,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教育 学或教学论;有的现在高校做研究工作,但曾经有相当长的中小学教学、管理的经历; 还有的设计者曾经在高师院校从事科研工作,现在的身份是课程改革的管理人员等。这 些不同背景的设计人员和设计人员的多重背景使得课程设计的思考从不同角度介入。
除了核心的研究人员,参与新课程审议的还包括一批参与人员,包括科学家、社会学 家、人大和政协的部分人员以及传媒机构、社会考试中介、各省及教育部的有关管理部 门。
不同的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地位,决定着他们在课程设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于这些角色,一位台湾课程专家认为,一般而言,“课程专家、学科专家、教师,是 课程设计团体的核心成员,而学校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传媒专家、学生、家长、 有关机构或行业的代表都是课程设计团体运作时可以征询的对象”(注:黄政杰.课程设 计[M].台北:台湾东华书局,1991.97.)。从新课程设计团队的构成来看,与这些专家 的总结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二)异中求同:课程审议者间的协商
审议小组是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地位、不同角色、不同地域人员的组合,其合理性就 在于这些不同角度、层面的视域交融能够实现互补,这是审议的意义和理想的结果。然 而,互补观点的形成过程却不断地伴随着审议者的冲突与沟通,问题的澄清是一个艰难 的过程,因此,纷争、协商、妥协、坚持、甚至“讨价还价”,使生产文化的过程本身 形成了独特的审议文化。
1.设计者的冲突与沟通
如果说新课程的理念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着力于学生 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与人文的素养”等,在这样的宏观的理想背后,每个人 对课程最潜在、最深刻的理解,自己对学科的认识、习惯的思维方式、学术派别,甚至 对自己付出巨大劳动的学科的情感都会在争论与协商中表现出来。此外,不同地域、不 同职业的设计人员之间的价值与利益的冲突,贯穿于课程设计的全过程。这些对峙来自 很多方面,比如:教研员与高校教师;学科内的不同专业倾向;学科专家、课程专家与 政府官员;学科专家与课程专家之间。
以学科专家与课程专家之间的交流为例,这两类人员都有较强的理论功底,也就是说 ,都掌握在交流中使用的工具性话语,都有一定程度的专业自信,但理论的结构却差别 很大,这些决定了他们视角的融合更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在访谈中,他们表达了对对方 在课程设计中角色的看法。
一位学科课程专家说:
我觉得课程理论中的很多问题是非常理想化的,课程理论中的好多东西用到实践中并 不可行。课程专家提出的一些事情和我们做学科的人的想法都要考虑,不能完全按照课 程专家的做,学科毕竟有学科本身的逻辑和规律性。
一位课程专家说:
中文专家说,中国人不学好语文,你还能干什么?我觉得他的想法太极端。我们是义务 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学好语文是应该的,但将来从事语文专业工作的小孩能有几个? 他们需要什么,不要老想着我是语文专家,好像语文就是第一位的;地理专家说,人生 下来就接触地球,死了要回归地球,人这辈子就跟地球打交道,你说地理重要不重要? 外语专家说了,外语多么重要我不说了,反正国家领导人说了,外语要从娃娃抓起。我 说你这个理解太极端了,对有些人来说,外语不需要学那么多。
前一位被访者是课标组的学科专家,他认为课程专家的认识是“理想化”的,而学科 专家遵循的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和规律性”;而课程专家恰恰认为是学科的逻辑给他们 的认识带来了偏执。在课程内容的编排、选择、表现形式上,这两类人员依据的标准是 不同的。课程专家组设计课程方案时会在逻辑上甚至时间上领先于课程标准的设计,以 至于“对峙”中的学科专家有被制约的感觉。
其实,课程专家与学科专家之间产生争论的核心是究竟怎样看待课程专家的作用,而 这种争论的本质是他们在课程理想上的分歧。学科专家与课程专家的理论背景不同,课 程理想也就不一样。从20世纪初课程专业领域诞生后,课程专家一直在课程设计领域, 尤其是进步主义教育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但60年代后,学科专家取代了课程专家的地 位。“来自各种学科的专家取代了课程领域的传统论者,成为决策者和改革者,无论私 人的基金会或官方机构都不认为课程学者可以领导课程改革”(注:周珮仪.从社会批 判到后现代——季胡课程理论之研究[M].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2000.56.),课程 专业领域濒临衰落。然而,美国60年代的课程改革并不令人满意,学科专家试图把课程 设计过程及课程内容科学化,却导致学生学业成绩的下降。70年代,原本是学科专家领 域的施瓦布“痛定思痛”,提出了以审议为核心的实践的课程研究范式,重振了课程专 家在课程设计领域的地位。70年代后,课程研究领域中出现的现象学、批判理论等的研 究,使美国课程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阶段。
我国的课程体制不同于美国,课程研究发展史也不一样,在我国的国家课程设计史上 ,大批的课程专家参与是第一次。或者说采用审议的方式,学科专家与课程专家共同合 作还是第一次。那么,课程专家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在课程设计中的作用呢?
一位课程专家认为:
做标准的时候,课程专家的作用一个是观念层面的,一个是技术层面的。首先,课程 标准要讲究课程体系自身的逻辑。学科专家习惯首先从学科内容出发考虑问题,而课程 专家更愿意从儿童的角度考虑问题,这里面就需要对话,同意哪一方都不行,双方要站 在中间考虑问题。学科专家强调得把我这个问题教完,强调双基,这种对话中课程专家 必须有他的地位,发挥他的功能。另外,课程开发需要技术支持。课程开发、设计、课 程规划都是一系列技术层面的问题,课程专家可以为学科专家提供支持,包括课程标准 里用什么行为动词,我们把这些动词提供给学科专家,他们按照这样的形式进行整理。
这位课程专家显然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他把课程专家在课程设计中的作用分 成了观念与技术的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恰恰是课程设计概念本身所包含的。他认为 ,课程专家在课程设计的全过程都应该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观念与思维的框架,在逻 辑上是上位的,是课程性质本然需要的。因为专业视角的不同形成的两种课程设计观已 经很明显了,因此需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于课程设计过程。对话中专业的疆界是明显的观 点派别标准,每一位讨论者原有的认知结构决定着他采择的信息,决定着在学生、学科 之间做出选择的尺度。认知结构为所有的设计者认识和把握课程元素提供了解释学所谓 的“合法的偏见”,之所以合法是因为离开了偏见,认识是不可能的。偏见是人们认识 世界的前提,知识分子被选择扮演创造文化的角色就是因为他们具备了这种独特的合法 的“偏见”的合理,这种“偏见”不应该妨碍共同文化的培育与发展,关键是讨论者在 呈现“偏见”的同时,要肯于倾听、移情理解另一种“偏见”的合理性。
一位学科专家认为:
做义务教育课标的时候,对于学教育学、心理学的那些人,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别 扭的,他们提出的东西有时候不着边际。后来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两方面结合,互相 促进还是挺好的。他们那些观念,像三维的教育目标,这些事情过去我们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给提出来了,系统化了,这是很好的促进。
这位学科专家对课程专家认识的转变从“不着边际”到“挺有道理的”、“很好的促 进”,转变的原因是他了解了课程专家所倡导的观念、所做的事情,他开始接受甚至使 用“学教育学、心理学的那些人”的思维逻辑看待课程问题,因此,他的结论是“两方 面结合,互相促进还是挺好的”。
2.决策的产生
在每一个课标设计组内,研讨的方式贯穿始终,冲突与沟通之后,决策环节怎样产生 ,不同的研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课标组的一位专家说:
大家都会使劲发表意见,但到最后,逐渐地组内还是会形成一个核心,核心人物后来 还是出现了,总得有拍板的呀。这个角色还是大学里的人物。比如在争论课程结构的时 候,设不设基础部分,有位老师坚持得最厉害:因为前期研究是我们做的,我们最了解 中国的现状,我们提出来要有必修、基础部分这一块。这个观点在第三次、第四次会议 上都是处于被否定状态。后来他就不出声,他只要一出声就是陈述这种理由,到第四次 、第五次会议的时候,大家还是走到一起来了。还是谁对这个问题研究得最深,他的意 见被采纳的可能性就越大。
课标组另一位专家说:
谁是决策者?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大家在一起争论,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标准,不是课题 负责人说了算的,是科学的决策过程。比如我们某个内容的选择,不是谁能说的,是大 家反复来论证的。你提你的观点,我提我的,在争论中慢慢地思路就清晰起来了,最后 大家达成共识。觉得这样很合理,不是最后谁拍板。反正我们课标组是这样,是科学、 民主的决策。
第一种说法中有明显的决策中心,是讨论中出现的权威,但权威不是召集人。作为形 成的权威及最后的决策人,他有两点特质:(1)他的前期研究“最”深入,其观点有可 能最接近合理性;(2)坚持并耐心地“陈述理由”,等待并使大家的认识走到统一的高 度。共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共同的信念、理论、目的、程序等共同的立场,如果 凭立场也无法做出选择的时候,对于基础的研究,实证的资料是最有说服力的。这里提 到的这位申述者,做了大量的“前期研究”,所以非常了解“中国的现状”。如果像杜 威所说“儿童与课程是教育历程的两极”,“儿童目前的程度或立足点及学科中的事实 及真理”(注:杜威.儿童与课程[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107.)便可决定“ 教学法”了,或者说申述者前期研究中对儿童(学生)程度的判断便可以决定这门学科课 程中应该设立“基础必修部分”。由于这个生成的决策中心与召集人(行政负责人)不是 一体,反对者可以没有太多的顾及而不断地“反对”,最后在逐渐理解已有研究的前提 下又自然地趋向一致。
第二种说法中看不到有明显的决策中心,被访者不断提到“大家”、“共识”,不同 的问题采纳的是不同人的意见,在消除行政负责人的权威性之后,大家在论争过程中自 然生成问题的结论。课标组之所以有召集人,不称其为组长,就是希望弱化指定的决策 者意识,以“遵循民主参与科学决策的原则”。那么,在一个行政组织相对宽松、自由 的团队里,决策权把握在敢于表现已见,甚至是偏执地表现己见的人手中,就像社会学 家所说的,“自主是领导权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只有一个人相信和珍视他自己的 特殊倾向时,他才能孕育出有价值的东西”(注: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 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00.)。当然,这种偏执与自信不是盲目的。
课标组一位专家说:
在没有做课标的时候,我们写了几套高中教材,实证研究的课题做了三年,因此我们 在发言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发言权,潜意识中觉得我们是走过来的,我们有实证的研 究,加上写过教材,我觉得这些都有作用。
另一位课标组专家说:
一次,请某先生给大家讲课程设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课程改革听谁的?谁的声音 大,听谁的。我想这个声音大是指在这个圈子里,小组里,认同你的业务水平棒,他讲 的是有道理的,在课标组里经常有这个事情,争执不下的问题好多,在这种情况下,大 家认同的这个人的意见就是主导意见。
有的课程设计者经历了课程设计的审议过程,回过头来,他们都在反思怎样做决策才 是合理的。不管是研究的积累,还是“业务水平棒”,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看来如 果抛开人际关系等“人为”因素,在一个设计团队里会出现一个或多个非正式组织的决 策中心。这个中心不是维护科层制的行政组织结构,而是产生于他们观点的说服力。对 于团队中的所有人员如果有这样的共识——申明自己的主张不仅是权力也是责任与义务 ,同样,团队中所有的人员也可以做到对知识、对科学、对道理的尊重,那么,这样的 决策中心被设计者认为是合法的。
二、关于课程审议的认识
本次新课程的研制,可以说是审议方式在中国的一次本土化的过程。课程审议是新课 程设计中很有特色的研究方式,通过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审议的考察,我们看到新课程设 计中课程审议表现出的特性。
1.以审议为基础的课程设计是对实践理性的追求
审议要解决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对实践中可行性的考虑。认知理性可以追求思维中 的无矛盾,可以追求绝对,因此,理论问题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而且是惟一正确的解 决办法。实践的难题却不同,对于一种课程方案,也许在城市是很好的办法,在农村就 不一定;对于大型学校可行,小型学校则不同;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对于一般的孩子则 不行。“审议中没有正确的,但有最好的方法”。(注:Joseph J.Schwab.The
Practical:A Language For Curriculum.School Review,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1—23.)方案的拟订是对现实情况的酌情而定,这 种判断与决定是在深刻了解实际问题的基础上的理性的直观。因此,对现实情况了解得 越具体、越真实,直观的判断越趋向合理。实践的难题的解决与理论问题的解决也是不 同的,理论难题可以在思维中用前置理论、逻辑判断检验问题解决的程度,而实践的难 题只有在事后,在已经采取行动之后,才能真正排除问题。事实上,施瓦布在提到课程 审议时主要指在学校层面的课程设计,因为能更接近具体的情境,更具有实践的意义。 而我国的新课程设计是在国家课程的层面上使用了这种研究方式,与学校课程设计的审 议相比,使用的信息特征不同,但审议的理论基础及属性是一致的。
2.“基础研究”是课程审议的基础
新课程设计中每一个课标组都曾围绕着自己的学科进行了现况考察、比较研究、社会 需求调查、学科发展研究、学生心理发展研究等,这些研究是对现有理论研究的梳理, 是对相关课程现实情况的把握。这一环节是课程审议的基础,因为这些知识与信息是判 断的依据。审议中研究者需要有这样基本的共识性的平台。美国课程学者沃克曾经把这 种平台或基础称为“立场”,他认为每一个课程设计人员“都用某种信念和价值处理课 程开发中的活动。他们会对工作有某种理解,会有什么是主要问题的理念,决定了将要 开出一个什么样的处方,以及他们准备追求与争执的承诺”(注:Colin J.Marsh.Key
Cconcepts for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The Falmer Press,1992.123.)。当然,立 场往往在审议的讨论中才会变得更加明确,基础研究也不会使课程审议中大家的意见完 全一致,但确实能够提高相对的共识。而审议中研究者发现了理论的困境以及对课程现 实问题了解的有限,又激发了研究者更深刻、持久的课程探究的欲望。可以说,课程研 究与课程设计中的审议有一种互构的关系。
3.审议的过程应该是去中心的,排斥权威又依赖权威
这里的中心指的是传统的科层体制中的行政权力中心。托夫勒曾谈到,由于科层体制 的持久性、等级制和劳动分工,个人便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组织的前途,长期养成了对 组织的忠诚性,个人也成了无所作为的驯服的人。那么,在科层体制之后,人类社会将 形成一种“暂时体制”(又译“特别组织”),指的是为解决某一专门问题而成立的、问 题解决后迅速解散的组织。在这种体制中,行政人员、管理者“在专业队伍之间起协调 作用。他们将熟悉不同专家组的术语,他们将在组与组之间传达信息,用笔头或口头把 一种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语言”(注: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6.123.)。在这种体制中“老式的效忠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职业的忠诚感 ”,将有更多的越轨、创新和冒险,专业人员将从他们的专业圈子和工作称心与否中得 到报偿。托夫勒认为,在我们今天的一些组织机构的雏形中已经有了这种人。未来学家 所描绘的“暂时体制”与课程设计中的专家小组的确有很大的同质性,在“暂时体制” 中,设计专家的思维观点和话语立场没有行政服从的责任,审议的方式恰恰是依赖每位 专家的自主性与歧义性产生意义,获得发展。审议排斥权威是因为审议得以产生的前提 条件是宽松的舆论空间,民主的、平等的人际氛围,每一个设计者都有自我表达的权力 与能力,因此在审议的团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中心。但审议的过程又常常是多种意见 相持不下,方案未经实施的检验,理论也无法判断方案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这样在审议 过程中“公认”的那个理论素养高,又真正全面了解课程实践信息的审议者的意见便会 对大家起到暗示与影响的作用。
4.视域的融合是艰难的历程,它需要包容、耐心甚至是“讨价还价”的策略
审议中各种观点不会轻易地融合,每个设计者在看似相同的课程价值观背后,蕴藏着 深刻的经验背景、思维路径、判断原则的差异,只有透过具体问题的探讨、判断、决策 表现出来。在交流中,设计主体的价值在于体现自我的特征,争执本身是一种交流,事 实上也是一种相互培训,最后削钝主体的特殊性,以达成统一。争端的解决会有两种路 径:一是争论中突然闪现出的前提性反省——一种超越性的认识,于是提升了在同一水 平上对立、矛盾的多个主体,放弃了固有的偏执,带大家的思维进入新的层面。二是“ 审议过程的成功,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在过程中带着某种标准或期待。这些标准或期 待包括,专注地听取他人的观点和争论,谨慎地接受或拒绝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同意或驳 回,在说服自己立场的断裂和他人立场的价值中妥协,承诺审议最后接受的标准等。这 不是教条者、不合作者所能做到的”(注:E.C.Short.Shift Paradigms:Implications for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practice/Paradigm debates in curriculum and
supervision: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edited by Jeffrey Glanz.Linda S.Behar-Horenstein.2000.)。
5.审议需要设计者多元文化的素养及积极的文化心理重建
课程设计用什么方式、多大程度上连接现实与理想,决定着课程产品的质量与水平。 课程设计者要有丰厚的课程文化的储备,并以此作为思维的背景之一,同时,请熟现实 的课程生存环境,并预测变革可能的情势。这一特征意味着课程研究的长期性、常规性 、潜伏性,也意味着对课程研究者文化储备要求的多元性。因为“实际的课程活动,是 在完整的情境之中的,而任何理论的来源都是有限的,课程判断与行动将要运用复杂的 研究方式,知识、理论、原理都是信息的来源”(注:Ilene Harris.Deliberative
Inquiry:The Arts of Planning,from.Short,E.C,Forms of Curriculum Inqui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285—303.)。审议过程中我们看到,由于 课程设计者间文化差异而带来的相互认同的困境,究其原因,包含着社会情境的相对性 和真理的超验性之间的悖论,有不同知识结构间“通约”的艰难。其实,这种文化认同 中的分裂,有时甚至表现为个体的自我认同的矛盾。它来自于知识分子“所受教育本身 的双重性,或者所受教育与本土经验本身的背离有很大关系”,(注:陶东风.社会转型 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39.)需要审议者在长期的、常规的、 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课程研究中实现心理重建。
6.审议注定课程设计是预成性与生成性的有机统一
预成性表现为既成的课程文化对人的设计活动的塑造和制约。除此之外,课程审议团 体对课程理论知识、实践知识的了解有限,审议资源(主要是时间与资金)的匮乏,“再 一种挑战是审议本身的能力的挑战,这种能力指的是执行审议结果的权力,当审议团体 缺乏决策与执行权力的时候,审议获得的观点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课程执行者。当 然,另一方面,如果审议无视课程决策者的愿望,也会使审议浪费时间”(注:Decker F.Walker.Fundamentals of Curriculum Passion AND Professionalish,Mahwah,New
Jersey,2003.217—239.),这些都会成为审议过程难以剥离的影响因素。生成性则表现 为人的创造性对新课程的重构。审议中决策的产生不是单向度的线性决定关系,而是双 向的、多元互动的线索,没有人能够也没有权力预设既定的结果,在多种可能的选择方 案中权衡创造,这是审议的本质,也是审议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