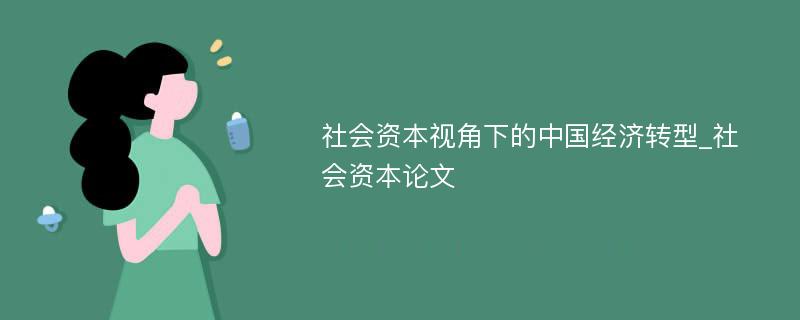
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资本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资本论文,经济转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经济转型,已有大量文献作了讨论(如Roland,2000)。无论是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的研究,还是对中国渐进改革的研究,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注意到了适应市场的制度变革的重要性(Roland,2000)。转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特定制度变迁的理论。经济转型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的变化,政府开支的紧缩,更意味着一整套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变动。依照诺斯的理论(1994),制度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包括各种行为规范、规则和习俗,在制度中占大部分。 但以往对制度转型的研究大多是在正式制度层面上进行的(如Roland,2000),而注意到转型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则是近几年的事。鉴于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有着重要影响和制约作用,研究转型中的非正式制度变革可以加深对制度建设的认识,并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上对过去各种改革实践的成败做出新的解释。
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社会资本(Raiser,1997),本文将考察中国转型所受到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和制约,并与俄罗斯进行比较。
一、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作用
社会资本是来自于社会学的术语,用来指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而在某个特定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关系,如常见的家庭、家族、街区、社团,以及朋友熟人关系等人际交往网络(布朗,2000)。某个特定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对于该网络以外的社会成员往往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可以是正的,比如,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维持街道的治安秩序,对路过者就有正的外部性;也可以是负的,在腐败网络中,处于网络中的成员存在着互惠的分赃机制,但对网络之外的成员却造成了损害(Warren,2001)。社会资本与市场机制可能是互补的,但也可能是互相替代的(Dasgupta,2002)。社会资本在网络成员中所起到的合作作用可以帮助网络成员抵御市场风险,或获得无法通过正常市场渠道而获得的资源。但是,如果网络内部存在高强度的社会资本,它也会产生消极作用,阻碍内部成员退出网络寻找外部市场机会,甚至会形成反社会团体。存在消极社会资本的网络实际上会产生负外部性。
在普特南(2001)和福山(1998)之后,社会资本跨越了社会学的边界而越来越成为政治学以及经济学中的热门词汇。在政治学中,社会资本着眼于整个社会,而不再是小的社团。与前面提到的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相比,政治学中的社会资本更多地具有宏观体制上的含义,用以概括社团间的合作行为和全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关系,以及遵守合作规范的行为倾向。这里,社会资本就不再具有负外部性,而成为完美的公共品,是市民社会、公民美德的类似词。普遍存在的信任关系无疑会促进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关系的形成和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从而构成支持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基础。它节约交易成本,缓解市场交易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相对于小社团内部的信任,这是一种扩展的信任(extensive/generalized trust),是对普通公民的信任。
二、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的社会资本
俄罗斯经济转型采用了“休克疗法”,但在随后几年中并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经济增长,反而出现了经济衰退,即所谓的“转型衰退”。在研究“休克疗法”所带来的这一后果时,学者们往往注意的是正式制度变迁造成的影响,例如“休克疗法”造成的信贷紧缩,以及原有计划体制下生产链条突然中断(Roalnd,2000)。“休克疗法”的实质是一下打碎旧的正式制度,但新的正式制度却不可能立即建立起来,人们适应新的正式制度则需要更长时间。在人们适应新制度的过渡期中,旧的非正式网络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这些旧网络甚至反作用于新的正式制度的形成。与此同时,新的正式制度的缺位和失效也刺激着旧的非正式制度以新瓶装旧酒的形式延续下来。社会资本在俄罗斯的“转型衰退”中就起到了这样的消极作用。
俄罗斯转型初期的社会资本存量要追溯到前苏联时期。前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基本特征是一切生产活动通过行政命令安排(注:原来还有意识形态控制。在前苏联前期,意识形态发挥了很大的正面作用,但在末期就没什么作用了。),一切自愿组成的社团和合作组织原则上都不允许在未经政府控制下存在,这就限制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合作活动形成扩展信任和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人际关系被原子化了(Paldam and Svendsen,2000)。
相对于普特南(1993)所强调的自发性市民交往形成社会资本而言,这种情况无助于市场秩序的形成,但它与计划经济的垄断性质是一致的。协调社会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信任关系主要是通过计划与组织,即计划制度得以维持的,也只能由这种信任来维持。计划制度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出于人们对计划制度的信心,而这种信心的形成要么由于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要么由于意识形态(注:Raiser(1997)认为,波兰经济转型时要比俄罗斯平稳,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教会等组织在转型前的波兰就独立存在。)。而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在现实中从没有强大到无所不包的程度。计划制度的理想形态是韦伯式的官僚制度,或兰格式的社会主义,它要求计划能够准确无误地调配各种经济活动,但经济计划在实际运行当中往往是很僵硬和笨拙的,这时便形成了企业间的一些局部交换网络,以及企业主管和计划部门中管理计划制定和物资分配官员之间的人际网络,并且产业链越密集,网络关系也越密集。这种网络使得计划的制定和完成有一定的调整余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计划的缓冲垫,润滑了计划的运行。同时,计划经济的软预算约束和重工业畸形发展使消费品严重短缺,再加上官僚主义,使得人们不得不依靠黑市或灰市交换网络来购买或倒卖物品及相关票券,以及与官员拉关系或行贿来获得有利结果。只要这些网络不是过分发展,当局也只能默许其存在,而在官员之间甚至形成庇护-依赖关系(Ledeneva,1998)。具体来说,这些非正式网络大致有两种类型(注:当然这两种类型的网络在实际中经常交织在一起的,区分也不严格。),一种是普通居民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比如自发形成的灰市等,这类广泛存在的网络出于补贴生活的目的,很多局限在家族或熟人圈子内,有些在一定程度上也接近于正常市场交换的雏形(灰市上的交换使用货币),或者是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水平型非正式网络。而另一种是利用计划制度空子倒卖物资或以权谋私而形成的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中往往是垂直型的,有很强的依附与控制关系,在短缺的生产物资或消费品分配中,利用自身或从上级得到的权力垄断了这些紧缺物品的分配与销售,而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这些依附型或排他性网络可以称为消极的社会资本,或负面的社会资本,它与市场经济下的正常贸易规则相违背。这些非正式网络很多情况下尽管是非法的,但作为计划经济润滑剂又是社会经济活动所必需的,这些网络的长期存在使得法律和正式规章制度的权威和有效性受到损害,从而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产生了负面影响。(注:同样地,这些看上去不怎么合理的网络的实际存在和扩张也不断加剧了民众对计划制度优越性宣传的怀疑。)
但计划经济形成了另外一套网络。在前苏联时期,社会生产活动的协调所需要的信任关系主要是通过计划与组织,亦即计划制度得以维持的,它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出于人们对计划制度的信心。不过,这种信心到前苏联解体时已经基本不存在了。计划制度的理想形态是韦伯的官僚制度,但它在现实中往往是很僵硬和笨拙的。在计划体制中,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些局部交换网络,但更重要的是在企业与计划制定和物资分配官员之间形成的人际网络,并且产业链越密集,这种网络关系也越密集,这也使得计划的制定和完成有一定的调整余地。另外,计划经济下的“软预算约束”使消费品严重短缺,再加上官僚主义,人们便依靠黑市网络来购买或倒卖物品,或通过向官员行贿来获得好处。只要这些网络不是过分发展,当局就会持默许立场,甚至会形成庇护关系(Ledeneva,1998)。这些依附型或排他性网络可以称为消极的社会资本,它与市场经济下的交易规则相违背。
到了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经济转型初期,原有正式制度迅速消失,出现了制度真空和正式组织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黑市组织和关系网络便被保留下来以填补正式制度的真空。例如,在工资未能按时发放时,人们要向主管官员行贿以寻求照顾,原来一些黑市网络转化成了黑手党。但这些网络不但不能支持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反而侵蚀了正式制度的正常功能(Rose,1999),阻碍了新的商业网络的形成(Raiser,1999)。
这些从前苏联时期传承下来的反市场经济的非正式网络和缺乏扩展的信任关系,在俄罗斯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消极作用。但应该看到,消极社会资本传承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市场经济赖以运转的正式制度。一个无法有效保护产权的政府和缺乏实施力的司法体系,是俄罗斯转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Roland,2000)。 这就导致黑手党组织普遍蔓延。而当政府无力通过正式税收系统获得收入时,它就会依靠腐败网络通过出售某些特权来换取收入,或对现有税基进行掠夺,而这又刺激了私有部门向非正式网络寻求保护。这些都阻碍了非正式网络向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方向转化。同样,正式制度本来可以通过保护产权、保障合同执行、建立廉洁政府等来促进新的商业合作网络和扩展信任关系(Zak and Knack,1998;Raiser,1999),但正式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俄罗斯的扩展信任保持在低水平上(Rose,1999;Raiser,Haerpfer,Nowotny and Wallace,2001)。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社会资本的影响与制约
与俄罗斯的情况相反,中国的渐进改革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增长。在研究正式制度的文献中,渐进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价格双轨制”和财政放权所形成的“财政联邦主义”,这些改革都极大地促进了作为增量的非国有部门快速发展,同时也保持了国有部门的相对稳定。与俄罗斯的情况不同,非正式制度对中国改革起到了支持作用。
改革前,中国与前苏联一样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扩展信任没有自发形成。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那些非正式网络,包括个人与政府官员(和厂长)的关系网,以及黑市交易网络等,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府协调全社会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信任也是通过人们相信国家有能力制定和实施计划来维系的。这是计划经济的共同基础。但是,非正式网络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没有像俄罗斯那样起太大的消极作用;相反,在转型的特殊时期,它还起到了某些正面作用,正面作用甚至超过负面作用。原因在于,中国的转型方式、计划经济的组织形式,以及诸如家族、乡村这样的一些非正式网络都与俄罗斯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的渐进改革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了政府的控制力和制度的连续性。这使得人们对国家有能力组织、管理和维持全社会经济活动的信心得以维系下来(注:另外,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文革之后在中国“左”的路线已经得不到群众的认同,但党仍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号召力,这与前苏联末期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在双轨制改革中,国有部门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防止了类似前苏联生产链条解体那样的情况出现,这作为双轨制改革的最大意义已经得到了承认(Roland,2000,张军,1997)。而从非正式制度角度看,在人们对国家协调经济活动能力的信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国有经济的信任,因此,双轨制下国有经济的保持和发展起到了维持信任链条的作用(注:这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尤其普遍,比如说在市场上企业都喜欢标榜自己是国营单位,人们也相信国营企业的产品正牌,服务正规(除了外资企业)。而且,国有企业级别越高(比如中央直属企业),所获得的信任感也会越强(当时的交往要靠国营单位开的介绍信来获取对方的信任)。当然这并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下社会资本正常体现。)。19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国有部门和乡镇企业(张军,1997)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国有制在双轨制中的另一个意义。
除了转型方式的不同外,中国的计划体制也明显不同于前苏联。中国的计划体制以“块块”为主,可以实现地区分权,并进行制度实验,而前苏联难以实行地方分权。在非正式网络中,这就意味着垂直型网络的层数较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非正式网络中的交往效率。此外,分权以后,各地方、各单位之间开始进行经济交往,所形成的交易关系不再通过中央计划协调,这意味着网络间水平合作的出现,也是准市场的形成(注:同时也有地方保护主义,这正说明它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这是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社会资本消极作用的表现之一。)。
地方分权改革的结果还促使了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独特产物。乡镇企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乡镇政府所有或拥有控制权,实际上是分权后政府所有制向乡镇的延伸;另一类实质上是私营企业,但除个别地方外基本都戴“红帽子”。没有非正式网络的支持,乡镇企业的出现是不可能的,乡镇企业的创办者,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私人,都需要利用当地政府的关系网并获取政府在土地、资金、销售渠道等方面的支持(刘世定,1995),这实际上还是国有经济信任链条的扩展。乡镇企业是在市场秩序不完善情况下出现与发展的,从体制过渡的意义看,它是非正式网络与市场形成互补关系的典型事例。
非国有部门还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非正式制度对私营企业影响中,除了上面所说的挂靠政府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资源外,主要的影响来自家族网络。家族制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改革后,一些地区的政府管制放松了,新兴的私营企业便利用家族内部的信任和关系网络取得了经营成本低和管理灵活的优势(注:中国的农业改革也实行了以家庭为基础的承包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家族或同乡关系的影响。非正式制度对外资企业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有港台及海外华人商业网络(也是以家族为主)可以利用,这对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俄罗斯所不具有的。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以及全球化对社会资本的正面影响,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这带来了信任关系的扩展,以及成熟市场经济下的行为规范。
总之,与俄罗斯不同,在经济转型期,尤其是转型初期,中国的政府关系网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正面作用。黑市网络则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政府执法,或者合法化,或者消失。但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以政府关系为支撑的社会资本所起到的正面作用,是转型背景下的产物,具有过渡性。而且,官员以及官商关系网络所固有的消极一面明显存在着。分权化改革一方面给予各地利用政府关系网络进行市场合作的动力,但另一方面其固有的排他性也制约着市场合作的深度。地方政府的排他性网络具有以邻为壑的倾向,而地方保护主义则造成了假冒伪劣商品、信用欺诈等一系列问题,这反过来又严重影响到市场运转所需的扩展信任的建立;而且官员网络容易滋生各种腐败和导致权力滥用,进而影响到政府执法的公正性,这反过来会侵蚀人们对国有制和公共制度的信任(Knack and Keefer,1997)。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改革初期的特殊环境已不复存在,官员关系网络的积极面正在淡化,而消极面正在强化,导致政府在保护产权、公正执法上产生偏离,使人们建立信誉或信任他人的动力受到削弱(张维迎,2001),市场经济所需的扩展信任的自发形成受到阻碍,从而诱发各种信用危机(童一秋、纪康保,2002)(注:对比俄罗斯的情况,说明政府过弱或政府强大到偏离法治,都会对扩展信任造成影响。这与转型正式制度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Roland,2000,第8章)。)。
四、结论
福山(1998)提到,在中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信任限于家族以内,而全社会的扩展信任水平很低,他将此类国家归类为低信任度社会。在低信任社会中,既然缺乏自发形成的社会资本的作用,那么就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才能把社会组织起来,这也是这些国家国有企业众多的原因之一。
这里所说的信任主要来源于民间的自发性交往(普特南,2001),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存在的社会中间组织就会对政府治理构成压力,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在社会资本存量高的社会里公共制度具有公正性和合理性,而对公共制度的信任又大大方便了信任的扩展。
而在前苏联和改革之前的中国,不存在自发性民间交往所形成的信任,但对公共制度的信任是存在的,它主要来源于群众对革命目标的信心,以及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在这种对公共制度信任的支持下,也会产生某些社会合作行为及非自发的扩展信任。
对比这两种不同的信任,可以看出,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制度宣传的影响力趋于平淡,如何通过树立制度的公正性来维系扩展信任,就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社会资本视角下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问题。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在转型时期的表现差异很大,但规范政府行为,建设一个支持市场的公共制度则是共同面临的转型任务。
标签:社会资本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休克疗法论文; 非正式论文;
